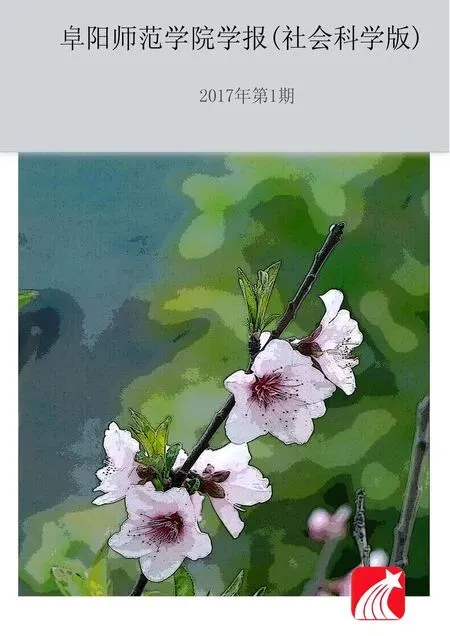论辞格的语言功能
刘春卉
论辞格的语言功能
刘春卉*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辞格可以分为语言辞格、言语辞格和元语言辞格三大类,它们在篇章衔接、词语构造、新义繁衍、构式形成以及文字创制等各个方面都具有强大的语言功能。语言辞格最主要的语言功能体现在各种类型的语篇衔接方式上,言语辞格和元语言辞格语言功能的实现则需要经历去修辞化的过程。言语辞格和元语言辞格系统是一个与常规语言系统对立而互动的系统:对立体现在它们突破了常规语言规则,互动体现在它们可以互相转化。
语言功能;语言辞格;言语辞格;元语言辞格
一、引言
突破常规语言的语义语法规则是大多数辞格最显著的特征,也是它们得以产生与存在的重要理据,所以修辞格一向被认为是语言的偏离形式或变体形式,相关研究也主要关注辞格的言语功能,即是否得体贴切、生动新奇等等。
其实,把辞格定义为语言的偏离形式或变异形式是不科学的,因为有不少辞格并没有偏离常规语言,或者说辞格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合乎常规语义语法规则的,如对偶、排比、反复、顶针、回环、镶嵌等辞格都没有突破常规语言规则,而且这些辞格的审美效果也主要体现在语言形式特点方面。此外,还有一些修辞格则是在元语言层面把语言形式本身作为表现对象,如反切、拆字、藏词等。因此,根据辞格审美效果所处的不同方面或不同层级,辞格可以分为语言辞格、言语辞格和元语言辞格三大类。
语言辞格的组合规则与常规语言无异,其特别之处体现语篇形式和语篇功能上,它们跟以“正偏离”为基本特征的其他辞格有本质区别。
言语辞格是常规语言的偏离形式,其审美功能分别通过能指的错位组合或能指与所指的选择置换来实现。
元语言辞格则是把各级各类语言形式本身作为审美或游戏的对象,主要是通过分解、拼合、变异等方式来形成特殊的能指,代替相关语言形式实现指称,这类辞格的形成与语言形式特点密切相关的,具有很强的民族性特征。
除修辞功能外,这三类修辞格都具有强大的语言功能,它们不仅是词义衍生的重要途径,也是新词构造与汉字创制的重要理据,还是某些句法构式的产生根源。甚至可以说,辞格是语言发展演变的重要方式或原动力,很多语言事实都是由辞格孳生出来的。
对辞格语言功能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促进辞格研究的深入化和科学化,而且有助于全面揭示语言发展的动力和方式,从而对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作出有益的补充。目前对辞格语言功能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因为大多数辞格研究仍是独立于语言系统之外,辞格与语言系统之间的互动和转换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系统考察各类辞格的语言功能很有必要。
此外,各类辞格的语言功能具有较大差异。语言辞格的语言功能主要体现在语篇衔接上,这些辞格的运用与语言功能的实现是同步的。言语辞格和元语言辞格语言功能的实现则是在去修辞化的过程中分阶段逐步完成的,而且去修辞化通常跟词汇化、语法化以及修辞化相伴而行,所以,全面考察这些辞格实现语言功能所经历的去修辞化过程,还能为研究语言的历时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语言辞格的语言功能
语言辞格不仅具有特殊的结构形式与表义功能,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语篇功能。有关对偶、排比、反复、顶针、回环、镶嵌等语言辞格在结构与表义上的特殊功能前人已有较多论述,此处主要讨论它们以篇章衔接为主的语言功能。尽管有关辞格的篇章衔接功能以前也有人论及,如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在论述顶针、对偶、排比等辞格时就谈及它们在语篇衔接方面的作用,但相关论述还不够全面系统,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不同语言辞格实现语篇功能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的通过相同的词句进行衔接,有的通过相同或相近的结构进行衔接,有的通过意义的关联进行衔接,还有的通过被拆散的成套的词语进行照应。
根据衔接手段或连贯方式的不同,语言辞格的语篇功能可以分为词句衔接、结构衔接、与分解衔接三大类。
(一)词句衔接
依靠词句衔接上下文的语言辞格包括顶针、回文、反复、同语等,其中以顶针最为典型。
顶针又称联珠、蝉联、连环,就是用上句结尾的词语作下句的开头,前后首尾相连,上递下接。如:
(1)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2)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未留胡子,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鲁迅《祝福》)
(3)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罗衣,白云堪卧君早归。(李白《白云歌》)
顶针的作用就是通过相同词句的上下衔接,使语篇中的各句(或段)首尾相连、环环紧扣,构成一个紧密的整体。这种语篇衔接方式不仅适用于场景描写与事件叙述,使状物叙事条理清晰、次序井然,也适用于说理论事,使分析论证环环相扣、逻辑严密,而且还适用于抒情写意,使情意的抒发细腻深刻、淋漓尽致。因此,顶针常常作为诗歌散文的语篇衔接手段,有些诗歌甚至通篇都是使用顶针组织起来的。
此外,顶针不只是用于衔接一组句子,也可以用于衔接一些语段甚至语篇以构成更大的话语单位,即下一段(或篇)第一句重复上一段(或篇)最后一句或最后一个词语。
顶针是严格运用新旧信息交替话轮的样板,是最符合话语交际或信息交换规律的衔接方式,因此,顶针具有强大的语篇功能,是语篇衔接的重要手段,而且在多数时候人们使用它并不像使用其他言语辞格那样是为了表达的新奇有趣,而是为了增强表达的逻辑性和条理性,有时甚至是别无选择,比如,一些场景描述和事理论证如果不使用顶针就很难说得清楚明白。
客观事物之间存在邻接锁合,客观事理具有承接递进,情感思绪需要绵延流动,而顶针格能够很好地表达这些关系,有时甚至是表达这些关系最完美的手段。因此,顶针是实现话题转换或新旧信息更替最便捷有效的方式,它直观地展现了事物或事理之间的邻接关系或递进关系,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顶针的语篇功能大大超越了它的言语功能,这在言语辞格当中是不大可能的。
与顶针相似,回文、反复和同语都是依靠重复相同的词句来组织语篇的语言辞格。回文作为顶针的特殊形式自不必多说。反复中的间隔反复在通过相同词、句或段的复现来加强语气和增强节奏的同时,也可以使语篇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它经常作为连段成篇的衔接手段。如柯岩的诗歌《周总理,你在哪里?》前面几段都是通过反复进行衔接的。
同语就是用动词“是”连接相同主语和宾语,构成一种重复判断表达超出字面的特殊意义。主语和宾语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和形容词。同语经常对举表示互不相干,如“你是你,我是我”“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等,此外,同语还经常用作话语衔接手段。
名词性的主宾同语作为语篇衔接手段经常用于肯定对方判断并暗示下面的转折,具有让步意味,如:
(4)——他不是主任吗?
——主任是主任,但这事他一个人也做不了主。
动词性的主宾同语通常用于对正在谈论的行为予以肯定并转向其他不同于预期的方面,如:
(5)——你们不是天天上课吗?
——上课是上课,但没几个人听,都是瞎混。
形容词性的主宾同语通常用来重复或肯定对方的评价,而且它后面的语句一般会作一个让步性的转折,如:
(6)——这件衣服真漂亮。
——漂亮是漂亮,就是太小了。
可见,这些同语都是用于肯定对方以紧扣前面的话题,而且它们都暗示下面要在此基础上作转折论述,构成让步复句。因此,在言语交际当中,同语是常用的话轮衔接手段,尤其是需要委婉地修正对方论点之时。
(二)结构衔接
对偶是通过对称排列两个结构相同、字数相等、意义相关的句子来组织语篇的,这跟顶针通过相同词语的重复来实现衔接不同。结构相同字数相等是对偶两个句子彼此联系最重要的基础,如:
(7)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偶的这种语篇功能在出上联对下联的语言文字游戏中体现得尤为充分。下联必须要在结构形式上跟上联完全一致才算是工整严密的对偶,这种以结构形式为制约原则所创作的下句自然主要依靠结构上的共同点跟上句进行衔接。
排比与对偶相似,只不过句子的数目更多,对结构和字数的要求相对宽松一些,而且与对偶比起来,排比具有更强大的语篇功能,它不仅可以衔接更多的词语或句子,而且还可以衔接复句或语段。
此外,由于排比不避重复,所以它经常跟反复和顶针套合在一起,由它们共同构成的语段兼用词句衔接和结构衔接两种手段,不仅首尾衔接更加紧密,而且结构一致,回环往复,读起来朗朗上口。
(三)分解衔接
分散在各句中的可以联系起来的字词也可能成为一种衔接手段,这在镶嵌格中体现得最为充分。镶嵌就是把要表达的话语或成套词语拆开后分别插入到一个完整的语段之中。镶嵌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隐性镶嵌,插入的是随机的自由语句,解码时需要找出它们并把它们组合起来,属于语言文字游戏,解码的难度比较大。还有一类是显性镶嵌,插入的是连续的数字、成组的方位词或表示属相、星宿、天干、地支等成套词语,这类镶嵌并没有隐藏其他意思。
第一种带有隐语性质的镶嵌对解读者而言并不是话语衔接手段,编码者把要说的话拆散并分别插入到各句话中就是要增加解码的难度,离开具体语境很难被外人解读,更不可能作为语句间彼此联系的纽带,因此,由这类镶嵌所创作的文本通常需要使用别的衔接手段,如对偶、顶针等。不过,对这类语段的创作而言,需要镶嵌的话语却是语篇衔接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类语篇创作的目的就是要把想表达的话语隐藏在外表看似毫不相关的文本当中,所以要表达话语的字词决定了语篇中各句话的先后位置和衔接关系。如:
(8)芦花滩上有扁舟,俊杰黄昏独自游。义到尽头原是命,反躬逃难必无忧。(《水浒传》)
第二种镶嵌则大都具有衔接语句、语段甚至语篇的作用,是话语衔接的常用手段。无论是连续的数字、成组的方位词,还是十二生肖、天干地支等,这些按照顺序散见于各句的成套词语彼此呼应,使相关话语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在某些语境中这些前后照应的成套词语还带有很强的趣味性和游戏色彩,它们在传达思想的同时也成为审美对象。如:
(9)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
(10)一别之后,二地悬念,只说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思想,千系念,万般无奈把郎怨!……(卓文君《倒顺书》)
除了词句衔接、结构衔接和分解衔接之外,还有单纯依靠意义相关性进行衔接的修辞格。尽管意义相关是所有话语衔接都必须具备的前提,但由于有些相关性比较特殊,所以它们还是被归纳为不同的辞格,如映衬、对照、层递等。映衬的前后连贯基于意义正相关,对照的彼此联系则基于意义负相关,而层递的语篇衔接则基于意义的程度增减。由于这些辞格跟前面具有形式标记的语言辞格具有很大不同,甚至很难把它们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辞格,所以本文不作深入论述。
总之,语言辞格通常都是构成大于句的语言单位,其语言功能主要体现在语篇衔接上,它们是组词成句、组句成段、组段成篇的常用手段,言功能甚至就是这类辞格的主要功能,也是它们区别于言语辞格与元语言辞格的重要方面。除语篇衔接外,语言辞格的其他语言功能较为少见,只有对偶具有造词功能,是词汇构造的常用手段,这在成语当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如“赴汤蹈火”“字正腔圆”等。
三、言语辞格的语言功能
言语辞格作为常规语言的偏离形式或变异形式,新奇有趣、形象生动是它们所追求的目标,因此其言语功能特别引人注目,如比喻、借代、双关、比拟、移就、拈连、通感、夸张、委婉、仿词等等。
除了带有很强场景性和临时性的言语功能之外,言语辞格也具有不容忽视的语言功能,而且其语言功能的类型和实现方式跟语言辞格有很大不同。语言辞格大多以合乎语言规则的语段形式体现,所以其语篇功能比较突出,但很少会对词义的发展、词语的构造、汉字创制以及构式的形成等产生较大影响,而言语辞格大都可以在单句之中体现,所以它们较少具有语篇功能,但经常作为词义发展的原因、新词构造的理据以及构式形成的促动力,甚至还可以作为汉字创制的重要认知基础。不过,不同的言语辞格在语言功能上也各不相同。
言语辞格的语言功能长期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可能是因为很多人仍然把修辞格当作临时性的个人言语行为,而忽视了它们对语言系统所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和作用。
(一)词语构造
造词功能较强的修辞格是借代,它是基于转喻思维的一种重要命名手段,很多词语都是基于借代产生的。如“布衣”“连襟”“便衣”“领袖”“青衣”“巾帼”等是用服装或衣物部件名来代指某一类人,“杜康”“茅台”“龙井”是用人名或地名作为酒名,“红娘”是用专名代指某类人,“丝竹”则是用材料代指乐器,等等。
用动词性成分或形容词性成分来代指相关事物的借代也可能构成新词,如:
月月红 映山红 夜来香 五点开 落花生
刹车 盖头 护膝 护腕 绑腿 裹脚 干事
第一组是植物名称,它们是用生长特点来称代相关植物,第二组则是以功能或用途来代指相关事物。
借代的造词功能有时需要语法手段或语音手段的辅助才能完成。语法手段主要是指添加后缀,常见的后缀有“子”“头”“儿”等,它们常常用在形容词或动词性语素的后面使之转指相关事物,如:
胖子 聋子 瞎子 瘸子 傻子 疯子 塞子 锄头
盖儿 塞儿 套儿 画儿 尖儿 破烂儿 亮儿
有些动词或形容词转指相关事物时要改变读音,以便跟原先的能指区别开来,相关语音手段主要表现为声调变化、轻声和儿化。
语音造词手段在上古到中古汉语中的运用相当广泛,“破读”就是通过改变声调来区别词性和词义的常用手段。如“王”破读为wàng、“语”读破为yǜ、“文”破读为wèn,都是为了区别动词用法与一般用法,这种声调的改变具有区分词性的语法作用。不同读法所对应的两种意义之间具有密切联系,是基于相关性的符号替换,只不过为了区别彼此能指形式作了规律性的变化。如果破读现象可以脱离语法环境而形成两种读音,就相当于另外造了一个新词,因为尽管它跟原词意义相关,但能指形式不同,所以仍然算两个不同的词,如读去声的动词“钉”与读阴平的名词“钉”。
使用轻声和儿化区别原词的也有不少,如“盖头”“尖儿”等,只不过后者有时也被看做是添加词缀的语法手段。
尽管这类具有语法或语音标记的词语不是由借代独立构造的,但借代也在其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语法或语音手段只是为了巩固这种新的符号关系而为它们作的形式区别。
可见,作为转喻思维在语言当中的应用和体现,借代不仅具有引人注目的修辞作用,而且还具有强大的构词功能。
谐音造词也可以算是借代造词的一类,只不过它们以此代彼的基础是能指形式相关,即借用语音相同或相近的词语表示本词,而且电脑汉字输入为这类谐音造词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使之突破了口语限制。很多谐音造词都可能随着使用的日益频繁而逐渐失去修辞色彩进入词汇系统,如“海龟派”“驴友”“斑竹”谐音造词等都在朝这一方向发展。
夸张造词也很常见,如“千层饼”“千头菊”“千里眼”“千里马”“千张”“千古”“万一”“万能胶”“万年青”“狗气杀”“一丝不苟”“一尘不染”“千钧一发”“肝肠寸断”“赴汤蹈火”,等等。
委婉也经常会引起新词的产生,如“夜壶”“大便”“小便”“解手”“发福”“耳背”“去世”“逝世”“同房”“房事”“口条”“白面儿”“挂彩”等最初都是用委婉的方式替代原词指称事物,后来这些词因为使用频繁广泛而逐渐进入语言系统成为语言词。近些年出现的委婉造词也为数不少,如“智障”“下岗”“待岗”“瘦身”“负增长”“欠发达”等等。
其实,委婉和夸张也都是以此代彼,只是它们除了事物之间的以此代彼外,还包括事件和属性的以此代彼以及三者之间的彼此替代,在这一意义上可以把它们看做是广义的借代。相关详细论述参见刘春卉《以转喻为基础的大借代修辞格系统》。
比喻也具有很强的造词功能,如“雀斑”“走狗”“爪牙”“鸡眼”“笔直”“雪白”“枣红”“银耳”“狐疑”“蚕食”“鲸吞”等。还有一些词的某个语素是比喻或拟人用法,如“壶嘴”、“路口”“山头”“山腰”“江心”等,这些词从本质上讲也是借助于比喻或拟人修辞格造出来的。
通感造词也有不少,如“响亮”“尖酸”“辛苦”“温馨”“圆滑”“苦涩”“痛苦”“甜蜜”等词语都是由通感造成的。我们之所以把它们看作是词语构造而不是词义衍生,是因为这些词语并不是在语素本义基础上复合成词的,或者说它们的构造成分并不能以本义组合,在这一点上它们跟“尖锐”等词语由通感造成的词义引申有很大不同,后者是本义与通感引申义并存,而前者的构造就是建立在语素通感引申义的基础上。
此外,仿词造词法在现代汉语中十分常用,很多新词都是用仿词的方式造出来并逐步去修辞化而进入语言系统中的。例如:
面的→货的 摩的 板的 轿的 驴的 马的
酒吧→网吧 氧吧 茶吧 书吧 水吧 陶吧
白领→蓝领 粉领 黑领 金领 红领 钢领
导游→导车 导购 导路 导医 导诊 导厕
每组箭头后面的词最先都是作为箭头前面词语的仿词出现的,带有较强的修辞色彩,属于言语词,后来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其修辞色彩逐渐淡化并最终进入词汇系统。
可见,修辞格不仅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手段,而且还是重要的造词方式,比喻、借代、夸张、拟人、委婉、仿词等几种重要辞格都具有很强的造词功能。
(二)词义衍生
比喻和借代都是词义衍生的重要动力或方式,很多词语的新义产生都是由比喻或借代引发的,除比喻和借代外,其他辞格也能促进词语新义的产生。
隐喻和转喻是比喻和借代的认知基础,认知语言学也已经对它们的运作机制作了比较深入系统地研究,所以本文主要考察其他修辞格在促进词义衍生方面的语言功能。
1.比拟是词义发展的重要方式,无论是拟人还是拟物都有可能引起词义的发展。比如,“打造”最初所适用的对象主要是钢铁等坚硬的金属器械,但近些年它的搭配对象越来越广,很多原本不能跟它组合的词语现在都可以跟它搭配了,如:
打造文明城市 打造先进团队 打造全新品牌 打造精品课程 打造卫生校园
打造快乐人生 打造梦幻效果 打造绿色奥运 打造金牌博客 打造新梦想
这些组合最初出现的时候具有很强的新鲜感和新奇性,属于把此物当作彼物来描述的拟物修辞格,是言语现象,但现在这类组合的使用日益普遍,修辞色彩也远不如以前那么明显,不难预见,这种用法最终会变成语言的事实,相关义项也很可能会被词典收入。
此外,“包装”等词语也跟“打造”一样是通过比拟的方式实现意义发展的,只不过“包装”的对象是从物扩大到人,是把人比拟成事物的结果,而且其意义的发展尚未最终完成,修辞色彩也还没有全部消失。
2.移就与比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它也是词义发展的重要动力。移就格最初打破词语组合规则主要是为了新奇有趣,但如果这种用法被越来越多的人广泛使用,久而久之很可能会失去修辞色彩,人们也不再觉得它们是超常搭配,这样原先的修辞用法就变成了常规组合,这也就意味着其中某个词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产生出一个与相关组合相适应的义项。如“绿色”的意义发展就是通过移就实现的,而且其去修辞化过程已经基本结束。
通感又叫“移觉”,算是移就的一种特殊类型,它也是词义衍生的重要推动力。如“苦”“甜”“香”“滑”“酸”“尖锐”等词语的引申义大都是由通感造成的。由于相关论述较多,此处也不再赘述。
3.有时辞格在促进新义衍生的同时还会引起词性的变化。很多兼类词都是在移就或借代的基础上逐步去修辞化而形成的。比如,名词“专业”“精神”最初用作形容词或受程度副词修饰时是超常搭配,属于移就,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这类用法更加频繁和广泛,其修辞色彩日益淡化以至于失去修辞意味,从而成为语言的事实,它们也就变成了兼类词。与这类移就衍义不同,“同学”“建筑”“导演”“报告”“管家”“翻译”“主编”“画”“钉”等动名兼类词则是通过借代去修辞化而形成的,只不过“画”和“钉”是由相关事物代指相关动作行为,而前面一些词则是由动作行为代指相关事物。
如果新义的产生伴有语音变化,则相当于另外造了一个新词,如“头儿”“眼儿”“盖头”等,它们应该属于词语构造,详见3.1借代造词相关论述。
(三)构式形成
言语辞格的反复使用也可能形成一些固定格式,这些固定格式的形成又进一步巩固了该辞格与相关形式之间的关系。如“跟(像)……一样”就是比喻句的常用格式,而且这一格式的形成是在跟之前的比喻格式竞争上岗的结果,这一替换过程是跟整个语言系统的发展相一致的。
“A(V)死了”“A(V)疯了”“A(V)得要命”“A(V)得要死”等则是夸张的常用句式,而且由于已经作为夸张构式长期使用,其修辞意味已经弱化了很多。
“A(V)死了”“A(V)疯了”可以表示两种意思,一种是字面意义,一种是表示夸张,字面义是夸张义产生的基础,而“A(V)得要命”“A(V)得要死”则通常只能表示夸张义。由于这些句式已经构式化,所以它们的夸张意味并不是很强。
委婉不但可以构造新词以便含蓄地指称事物,而且还可能形成特定的句式以婉转地表达思想,很多礼貌用语最初都是个别人为了表达的委婉含蓄而创造出来的,修辞色彩较重,后来因为人们的普遍使用而最终成为某种语用构式,比如,“如果我是你,我会……”就是由委婉形成的常用构式。英语中的“Could you please……”与“May I……”等也都是委婉语固化而成的礼貌用语句式。尽管这些由委婉语构成的句式已经成为一种语言构式,修辞色彩也已经淡化了很多,但仍然具有委婉礼貌的语用效果。
这些构式修辞色彩的弱化是由于这些修辞格式的长期反复使用使之逐渐失去新奇感,最后甚至可能变成没有修辞意味的语言构式。
(四)汉字创制
很多汉字的创制也是建立在辞格思维的基础上。辞格的形成是思维方式在语言当中的体现,相关思维方式在汉字构造方面也应该有所表现,所以辞格造字的说法似乎有点勉强,不过,文字的产生在语言之后,当时相关思维方式已经在辞格中得以体现并强化,所以我们暂且把体现了同样思维方式的汉字创制看作是辞格的语言功能。
特征代本体或部分代整体的借代,在汉字创制方面的体现较为突出。很多象形字都是用事物具有鲜明特征的部分来指称事物整体,如“牛”“羊”就是用头部的形象来构成的象形字。此外,不少会意字也算是借代,如“林”“森”“明”等等。
形声字是基于语音形式相关的借代,即借用某个同音字作为表音符号,然后再为它添加一个区分类属的义符来构成新字,如“慈”“放”“杨”等。
“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假借虽然不是造字法,但它常常会引起原字再造,如“北”“自”“然”“其”等,而且即便它没有引起原字再造,也使原字对应于两个不同的语言符号。因此,借用已有汉字表示某个在口语中与之音同或音近概念的假借也是基于能指相关的借代。
四、元语言辞格的语言功能
元语言辞格通过对能指的分解、拼合或变异来形成新的指称形式,如反切、拆字、藏词、断取、谐音等,这类辞格的形成受制于语言的形式特点,具有较大的民族差异。
元语言辞格的语言功能主要体现在造字和造词上。造字造词功能比较突出的元语言辞格是反切格。如“叵”“甭”“诸”等字就分别是“不可”“不用”与“之于”的反切合音,而且由于读音合并与意义合并,它们应该算是不同于对应的双音节形式的新词。此外,方言中的“冇”“覅”“嗦”“乍”等也是这类反切造词。
在现代汉语中,反切造字造词法也仍然还在发挥作用,如“羟”就是“氢氧”二字去气字头后合为一体,读音也是“氢氧”的反切,还有其他一些化学元素也是采用这种方法造字命名的,如“巯 qiǘ”“羰 tāng”等。
反切造词法在现代网络语言中也十分流行,如“表”(不要)、“哞”(没有)、“酱紫”(这样子)、“那样子”(酿紫)等。
反切造词不仅体现为双音词合成单音词,也可以体现为单音节词分解成双音节词,即把已有单音词的读音拆分为反切上字和下字,并构成双音节词,如 “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高祖还乡》)中的“胡阑”“曲连”就需要用“反切”的方法读成“环”“圈”。再如“囫囵(浑)”“呼噜(齁)”“胡弄(哄)”“窟窿(孔)”“舍予(舒)”“乎隆(轰)”“嘟噜(朵)”等都属于这类单音词双音化的反切造词现象。
谐音造词也可以归入元语言辞格造词。比如,“筷”就是由避讳与谐音共同造成的,筷子以前叫“箸”,“箸”字因为与“住”谐音,犯了忌讳,所以人们为避讳而称其为“快”,这种能指形式的改变,也相当于另外造了一个新词。后来由于筷子多为竹制,就又加了区别性的竹字偏旁,造出汉字“筷”。
拆字和藏词修辞格也都具有造词功能。拆字造词就是用分解汉字所得的成字部件组合成新词,比如,以前用“丘八”表示“兵”就属于拆字造词。拆字造词在古典小说中比较常用,如“禾火心”(愁)、“十八子”(李)、“十八公”(松)、“走肖”(趙)、“卯金刀”(劉)等。现代网络语言中这类造词也十分常见,如“走召”(超)、“弓虽”(强)、“木及”(极)等等。不过,这些词只是在部分网络语言中流行,还没有真正进入语言系统。
藏词格的造词功能也是由某个临时用法长期使用并逐渐达成全民共识而造成的,如“而立”“不惑”表示年龄就是由藏词格去修辞化而产生的。不过,很多藏词格并不能进入语言系统,而只能作为言语词使用,比如,陶渊明“一欣伺温颜,再喜见友于”(《庚子岁从都还》)根据《尚书·君陈》中的“友于兄弟”用“友于”替代“兄弟”就只是临时性的。再如,根据戏剧“秋胡戏妻”用“秋胡戏”表示“妻”也没有变成语言的事实。
五、辞格的语言功能与去修辞化
辞格在篇章衔接、词语构造、新义繁衍、构式形成以及文字创制等各个方面都具有强大的语言功能,我们甚至可以说辞格是语言发展的重要原动力,是人类认知方式在语言当中的运用和体现。
各级各类辞格除了语义语法规则及审美理趣不同外,语言功能也有较大差异,有些辞格可以衔接语篇,有些辞格易于构造新词,有些辞格经常引起词义衍生,而有些辞格则可以形成构式,等等。
语言辞格没有突破语言常规,语篇衔接就是它们最主要的语言功能,而言语辞格和元语言辞格语言功能的实现则是以临时组合、语境意义以及超常搭配的去修辞化为代价的。
去修辞化是修辞用例从言语转变为语言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通常伴有词汇化、语法化以及相关标记的修辞化。去修辞化一般需要长期的反复使用才能逐步完成,而且处在去修辞化过程中的辞格与非辞格的边界一般具有模糊性与动态性。
言语辞格和元语言辞格是语言发展与创新的重要途径和方式,由它们构造的言语形式可以经历去修辞化的过程而变成语言的事实,这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今天仍然如此,而且节奏更快、规模更大。因此,言语辞格和元语言辞格是一个特殊的系统,一个与常规语言系统对立而互动的系统:对立体现在不少修辞格都是通过对常规语言规则的突破而构成的,互动体现在有些语言要素可能会经历修辞化变为修辞标记,如“像”“似的”等,而有些辞格用例则可能会经历去修辞化的过程而变成语言的事实。
尽管各类辞格的语言功能具有较大差异,但语言功能的实现则大都是在去修辞化的过程中分阶段逐步完成的,而且去修辞化通常跟词汇化、语法化以及修辞化相伴而行,所以,全面考察这些辞格实现语言功能所经历的去修辞化过程还能为研究语言的历时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1]王希杰.修辞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吕文平,道尔吉.试论衣服词语的借代思维及文化内涵[J].汉字文化,2007(3).
[3]尹群,潘文.论汉语委婉语词的构造方式[J].南京社会科学,2007(12).
[4]高伟.浅谈借代思维在造字中的运用[J].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2).
[5]李国南.辞格与词汇[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6]刘春卉.移就修辞格的语法学及语义学视角[J].毕节学院学报,2008(2).
[7]任学良.汉语造词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8]于广元.汉语修辞格发展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On Language Functions of Rhetoric
LIU Chun-hui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Sichuan )
Rhetoric method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lasses: language rhetoric, parole rhetoric and meta-language rhetoric. The language functions of rhetoric include text function, word-formation, character creation, lexical broadening and sentence type formation, etc. The most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 of language rhetoric is to link sentences. The language functions of parole rhetoric and meta-language rhetoric are more complex, and they have to go through a long time to make the rhetoric speech to be normal language. Parole rhetoric and meta-language rhetoric are the opposite systems of language system because they always deviate the normal rules of language in the beginning. Howev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hetoric and language system also exist, because some rhetoric or language phenomena can change into each other.
Language function; language rhetoric; parole rhetoric; meta-language rhetoric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7.01.06
H08
A
1004-4310(2017)01-0033-08
2016-10-30
刘春卉(1975- )女,河南确山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语法学与修辞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