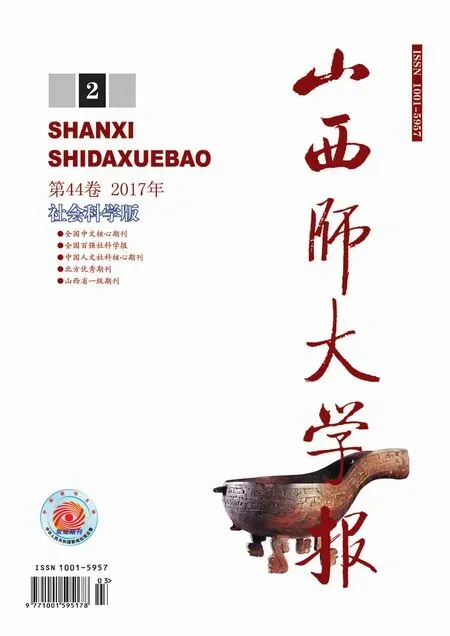中国古典诗词与史蒂文斯的诗歌创作
徐 畔,杨胜男
(哈尔滨师范大学 西语学院,哈尔滨 150025)
中国古典诗词韵律优美、蕴含丰富,在西方诗歌现代化的进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美国诗人W·S默温(William Stanley Merwin,1927—)所说:“到如今,不考虑中国诗的影响,美国诗就无法想象。这种影响已成为美国诗传统的一部分。”[1]20世纪初,新诗运动掀起了中国古典诗歌“西渐”的第一次浪潮,以庞德(Ezra Pound,1885—1972)为代表的欧美意象派诗人,积极投身于中国古典诗词的译介活动,并将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元素借鉴和融合入自己的创作中,这也为后来西方现代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先驱诗人发现了中国古典诗词中丰富的异域风情,贯穿于诗句里醒目的意象,蕴含其中深沉伟大的思考。中国古典诗词的这些特点让他们陶醉,也给予他们开创诗歌写作新时代莫大的帮助。”[2]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Stevens,1879—1955)作为意象派思潮中的代表作家之一,深受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然而,相较于其他同一时期接受东方文化熏陶的诗人,史蒂文斯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欣赏,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就显得十分内敛含蓄———他未在公开场合表示过自己的诗歌运用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技法,但据考证,确有资料记载史蒂文斯对中国诗歌的赞赏以及对他东方文化的向往。这为学界研究史蒂文斯诗歌中的中国古典诗词元素提供了有利的佐证。此外,由于史蒂文斯诗歌的晦涩,国内学界对于他的研究起步较晚,存在着较大的研究空间。本文将对中国古典诗词对史蒂文斯影响展开全面分析,希望能为史蒂文斯诗歌研究提供借鉴。
一、史蒂文斯的中国古典诗歌情结
早在1897年至1900年,史蒂文斯就读于哈佛大学时就开始接触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并对中国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赵毅衡先生曾指出:“他的同学兼好朋友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1881—1968 )和AD费克(Davison Ficke,1883—1945)对中国和日本的艺术和文学尤其感兴趣,他们两人曾经与史蒂文斯一起探讨中国文化,为史蒂文斯提供了更多了解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机会”。[3]在哈佛上学期间,宾纳被史蒂文斯邀请加入哈佛大学文学杂志《The Harvard Advocate》。同为反学院派的新诗倡导者,三人对中国古典诗词以及中国文化的喜爱有着不同形式的表达,其中曾两次到访中国的威特宾纳,为中国古典诗词在西方的推广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与江亢虎合译的《唐诗三百首》( The Jade Mountain,1929),与弗洛伦思·艾思柯(Florence Wheelock Ayscough,1878—1942)合译的《松花笺》(Fir-Flower Tablets: Poem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1921),与庞德和费诺罗莎(Earnest Francidco Fenollosa,1853—1908)合译的《华夏集》(Cathay,1915)和《诗经》(The Confucian Odes,1954),以及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0)的《汉诗一百七十首》 (One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1918),均为当时“东学西渐”思潮中中国古典诗词译介活动之典范。
史蒂文斯虽然掌握几种语言,具有极好的语言天赋,却并未投身于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他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喜爱体现在“他是北宋王安石诗歌在美国的推崇者”[4]。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意象派诗人,史蒂文斯很少直接在公开场合表达中国古典诗词对他的影响,也并未撰文深入阐述他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理解。他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欣赏,多表达在他的私人信件当中。 在1909年3月18日与未婚妻(Elsie Moll,1886—1963)的通信中,史蒂文斯分享了他对亚洲文化尤其是神秘遥远的中华文明的着迷,其中他对王安石的《夜直》一诗大加赞赏,称他再没有见过比这更美更有中国韵味的诗作了,并向王安石先生致敬。[5]“在后来写给未婚妻的书信中,史蒂文斯称自己为‘中国贤哲们的学生’……他还多次建议他的未婚妻多读中国唐朝的诗歌作品,因为他觉得这些诗歌作品能给予人们独特的美感。”[6]20世纪30年代,阿尔刻提斯(Alcestis)出版社神秘的编辑罗纳德·雷恩·拉蒂莫(Ronald Lane Latimer),真名为詹姆斯·雷珀特(James Leippert,1909—1964),写信要为史蒂文斯出版小诗集,后来他帮助史蒂文斯出版了诗集《秩序的观念》(Ideas of Order,1935)和《猫头鹰的丁香》(Owl's Clover,1937)。在1935年11月5日给他的回信中,史蒂文斯表明了中国以及日本诗词对他的影响,以及他曾经尝试将这些诗歌的特点融入他的创作。[7]38此外,在与当时还是学生的韩国诗人Peter H. Lee 的书信往来中,史蒂文斯也不止一次流露出自己对中国古典诗词的了解。在1952年2月26日的通信中,他用“庄严,真实,安静”[8]来描述中国古诗给他的最初印象。随后在1954年Peter要出版诗集之时,史蒂文斯建议他寻找中国诗集的出版商,并推荐当时流行的中国诗集译本[9],可见他对中国诗集的关注。除私人信件外,外国学界对史蒂文斯的评论,也间接认同了中国古典诗词对史蒂文斯的影响。学者哥翰姆5孟森(Gorham B.Munson,1896-1969)对史蒂文斯的评价,曾被国内学者多次引用:“史蒂文斯既受到法国诗的影响,也受到中国诗的影响,但是鉴于他的细腻诗风,史蒂文斯一直被人称作‘中国式的诗人’。”[10]
尽管如此,较之其他诗人丰富的研究资料,史蒂文斯研究资料相对匮乏,其诗歌作品、诗学论文、日记、信件以及相关国外研究者评论翻译的缺失,对于中国诗歌研究者是一大遗憾。国内对史蒂文斯的研究正处于萌芽期,此时引入国外学者对史蒂文斯诗歌诗论研究的相关文章和书籍是极其必要的。史蒂文斯书信、日记以及国外学界评论的译介无疑将为中国学者研究史蒂文斯晦涩难懂、玄之又玄的诗歌以及诗论提供重要线索和启发。
二、创作技法的借鉴与意境表达的效仿
学界普遍认为欧美意象派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兴趣,源于中国的象形文字。1919年东方学家费诺罗莎发表了《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汉字》(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1919)一文。庞德在研究费诺罗萨的手稿时,悟出了汉字的意象力,即汉字的组合往往能构成一幅动感的图景。随后意象派诗人将注意力进一步转移到用这些表意文字写成的诗歌,并通过意象组合等多种手法感悟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美的底蕴。意象派在摒弃颓废拖沓的旧诗风基础上创新了“现代派诗歌技巧如意象叠加、意象并置、独白和人格面具等……而且被T﹒S﹒艾略特、W﹒史蒂文斯……广泛使用”[11]。
史蒂文斯对意象的关注可在他的书信中窥见一斑。在一次给未婚妻的信中,他总结了中国古典诗画的意象主题并感叹这是他见过的最为奇妙的东西,因为它是如此广泛。[12]9在史蒂文斯诗歌里,随处可见难以捉摸的意象,这些晦涩玄妙的意象虽然给解读史蒂文斯诗歌带来了不小的障碍,但也成就了史蒂文斯诗歌的独特魅力。中国古典诗词中对自然山水旖旎风光意象的描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史蒂文斯的创作。“《风琴》诗集运用了大量的自然意象来表达作者的诗学理论和对现实的哲思。”[13]“想像和自然的关系几乎是史蒂文斯诗歌中惟一的主题。这个主题是通过反复出现的意象得以重申和强调的。这些意象不是随意的隐喻, 它们不断地出现, 重新组合, 给抽象的思想以具体的物质形状, 使其变得丰满。”[14]在史蒂文斯的经典之作《雪人》(The Snow Man)中,意象的使用十分鲜明。“诗中描绘了许多意象,霜雪松树残叶,这些都代表了自然万象……诗人呈现了一幅冬季的景观诗中意象赋予读者一种静谧。”[15]《坛子的轶事》(The Anecdote of the Jar)中坛子的意象也引发了学者的研究。“在释读当代诗歌文化时,一个醒目的意象, 带着奇异的光泽和花纹, 不断出现在我们的眼前:陶罐……如济慈曾写过著名的《希腊古瓮颂》, 史蒂文斯写过《坛子轶事》等。”[16]此外,《黑色的统治》(Domination of Black)中的意象也十分丰富:树叶、火苗、孔雀的啼叫,这些意象回环往复,层层递进,构成了强烈的画面冲击感,让这首诗具有更大的力量。
托马斯·厄内斯特· 休姆(Thomas Ernest Hulme, 1883-1917)为意象派诗人提出的创作原则证明了意象组合的魅力:“譬如某诗人为某些意象所打动,这些意象分行并置时,会暗示及唤起其感受之状态……两个视觉意象构成一个视觉和弦。它们结合而暗示一个崭新面貌的意象。”[17]史蒂文斯所喜爱的诗人王安石,在诗歌中也大量应用了意象并置等手法,如《题齐安驿》:“日净山如染,风喧草欲薰。梅残数点雪,麦涨一川云。”四句中每一句都渲染出一幅画面,通过“日”和“山”、“风”和“草”、“梅”与“雪”、“麦”与“云”的并置,通过虚实结合来完成意象的组合。虽然史蒂文斯并未谈及过意象并置这种表现手法,但学界还是在他的诗歌中找到了该技法应用的端倪。其中意象并置运用颇具代表性的一首诗是《六帧有趣的风景其一》(Six Significant Landscapes),这首诗通过意象的描写,清晰地使一位树下老叟的形象跃然纸上,体现了中国古典诗词悠然恬静之意境。“诗人在诗中通过树下的老人与树下的飞烟草、老人风中飘动的胡须与风中摇动的飞燕草、风中波动的松树与水漫过的芦苇,三组意象叠加,表达了他对在这个东方古国人与自然完美和谐的赞美之情。”[18]
隐士,是道家哲学术语,指崇尚自然无为的人生态度,选择隐修专注研究学问的生活方式的人。“隐士模式”是中国古典诗歌中一种典型的人物模式,而隐士模式诗则是对隐居生活吟咏和赞美,在中国古典诗词中这样的经典诗句不胜枚举,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苏轼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5夜归临皋》);王维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等。以陶渊明、王维为代表的诗人把自己向往的田园归隐生活描绘于作品当中,“这些人物的显著特点是不求荣华富贵,不屑大权高位,崇敬自然,向往天人合一,追求宁静,寻觅大智大慧。他们有的放弃高官厚禄,自我放逐于偏远,有的满足田园乡居,自我纵情于自然。这类中国隐士传统诗歌受到一些美国现代诗人的推崇和效仿。”[19]
史蒂文斯受中国古典诗歌影响,诗歌中的隐士形象曾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史蒂文斯诗中的中国人形象也与中国山水画中的隐士极为相似,不追求权力与荣华,享受宁静、和谐的自然之美。”[20]《六帧有趣的风景其一》(Six Significant Landscapes)中松树下的老人,是学界分析史蒂文斯诗歌中隐士模式的经典形象之一。这个“中国老人”还反复出现在其他诗中。“不仅如此,从《罐子轶事》中的罐子这个意象里和那位在克威斯特的海边唱歌的女人身上,我们都能隐约看到这位老人的影子”[21],这首诗的描摹使老人的形象与周遭自然景致达到了“天人合一”的意境。这正体现了道家隐士精神的内涵:“真正的隐士是与自然相融合,觅求到超越与智慧。”[22]此外,《叔叔的单片眼镜》(Le Monocle De Mon Oncle)中也同样出现了中国老人静坐冥想的画面,“诗中的中国人也许是诗人隐士,亦或是古代哲人,一副隐居生活的图景跃然纸上。史蒂文斯这首诗中的形象静坐山中,冥想感悟”[23],这一形象与王维《竹里馆》中“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的描绘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夏天的证明》(Credences of Summer)中,诗中再一次出现了隐士般的老人形象,他站在塔楼之上,虽未读书,也饱有岁月赋予他的智慧,以另一种高度俯瞰着世界,“同样作为诗人的史蒂文斯,或许也在追求沉思与冥想,重新思考人、现实与自然。”[24]
这种隐士形象的表达的背后是深层次的哲学思考,“需要说明的是,他们(意象派诗人)接受中国文学的影响是与接受中国哲学思想,即老庄思想、儒家思想和佛教分不开的”,因此“分析隐士模式的移入有利于挖掘诗歌的深层内涵,为体悟诗中的深刻寓意与哲学反思起到一定的作用”[25]。自古文学作品的表达源于却并不拘泥于人们对生活的思考感悟,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哲学思考同样贯穿于中国古典诗词歌赋的吟咏中。一方面,史蒂文斯通过诗歌间接地接受者中国古典思想的熏陶,在他阅读的中国古典诗歌中感悟出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哲学思索与自然情怀;另一方面,也有史料证明,史蒂文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也曾直接阅读道家佛家的译著,并在书信日记中写下当时的领悟。“史蒂文斯年轻时阅读广泛……他还研读了大量的关于中国宗教、哲学和文学的书籍。”“笔者近年有幸在美国亨廷顿图书馆史蒂文斯文档中搜寻出一本1909年版塞缪尔·比尔译著的《中国佛教》,扉页上留有史蒂文斯的亲笔签名……诗人阅读时留下的笔记大大有助于我们了解他所经历的困惑、惊叹、赞赏和醒悟……这些笔记都表明了史蒂文斯对佛教、禅宗的疑惑、感悟与相通。”[26]“隐士模式”作为一种诗歌创作的表现模式,被史蒂文斯运用在他的诗作中。但应该明确的是,这并不是简单的创作技法借鉴,更重要的是它体现出史蒂文斯创作背后对中国传统哲学思考的领悟,这种感悟还可从其诗歌作品中体现的“以物观物”“天人合一”“虚无”以及“冥想”等主题得以窥见。
三、“回返现象”与中国的史蒂文斯诗歌研究
国内学界关于欧美意象派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接受研究由来已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以赵毅衡、张子清等为代表的学者先后发表文章和专著来探讨中国古典诗词以及中国文化对包括意象派在内的美国现当代诗歌的影响。回顾中国的史蒂文斯研究,可以看出学界对史蒂文斯诗歌文本的分析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首先,研究过于集中在其主要作品及其形象上,如《叔叔的单片眼镜》中老人的形象,《坛子的轶事》中的中国瓷瓶,《六帧有趣的风景其一》中的中国老人,以及《夏天的证明》《雪人》等。以上作品在研究中反复出现,是学者研究的热点,然而在史蒂文斯上百首诗作中,仍有众多其他作品有待研究者挖掘。对史蒂文斯次要作品的关注是未来发展趋势的必然转向,如果只拘泥于以上的几部作品,那史蒂文斯研究无疑将会停滞不前。
其次,近年来,中国古典诗词对意象派诗歌的影响研究呈现出多视角、跨学科的局面,如顾明栋在《视觉诗学:英美现代派诗歌获自中国古诗的美学启示》中,论述了英美现代派诗人从中国古诗获得了视觉诗学的美学启示:“这种诗学表面上以视觉感知为特征,但其深层结构触及诗性无意识,直指诗歌之源,因而能够超越不同文学传统,促成中国古诗与英美现代派诗歌的成功对话,并对建立跨文化诗学有启迪作用。”[27]《误读视阈下意象派对中国古诗之接受》以误读视角探讨英美诗歌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接受是一种曲线下的再阐释和理解。以上这些不同的阐释视角,都为史蒂文斯诗歌研究者提供了启示[28]。刚刚起步的史蒂文斯与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应借鉴其中的跨学科手段,在未来更全面地剖析史蒂文斯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后,在分析史蒂文斯诗歌中的中国古典诗歌元素之余,不可忽略的是中国古典诗歌在传递发展中的回返现象。中国当代诗人对史蒂文斯诗歌中的中国诗歌元素的接受和改造,并如何将其投射在自己的诗作中,这在意象派诗歌回返现象研究中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回返现象的研究将把史蒂文斯与中国诗歌之间的关系从静态的、单向的影响扩展为动态的、双向的互动,进而为史蒂文斯诗学研究开辟出新的视野。
中国古典诗词对于史蒂文斯诗作影响的研究仍旧处在起步阶段,相信伴随中西文化交流渐进频繁,在文化共存的世界语境下,随着对外汉语和汉学发展逐渐深入,无疑将引发更多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研读中国诗、研究中国诗词以及中国诗词与美国诗歌间的影响与互动。受中国古典诗歌影响的史蒂文斯,必将在这场中国诗词研究热潮中吸引更多国外学者瞩目,由此带来的史蒂文斯相关诗论、日记、书信以及国外学者评论的译介引入将给学界注入新鲜活力。相信国内学界对史蒂文斯次要作品的挖掘,对同类主题研究视角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回返现象研究等方面的深入,均会为中国古典诗词观照下的史蒂文斯诗作研究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1] 赵毅衡.美国新诗运动中的中国热[J].读书,1983,(9).
[2] Goodwin,KL. The influence of Ezra Pound ,New York:Toronto,1996.
[3] 赵毅衡.关于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影响的几点刍议[J].文艺理论研究,1983,(4).
[4] 姜涛.美国现代诗歌的中国文化移入现象研究[J].外语学刊,2011,(3).
[5] 黄晓燕.论中国文化对史蒂文斯诗歌创作的影响[J].外国文学研究,2007,(3).
[6] 郭英杰.1919—1949年美国诗歌对中国诗歌的互文与戏仿[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5,(8).
[7] Stevens Wallace. 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Selected and edited by Holly Stevens,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54.
[8] Munson GB. The dandyism of Wallace Stevens ,Edited by Ashley Brown and Robert S. Haller ,The Achievement of Wallace Stevens,Philadelphia:J. B. Lippincott Co.,1962.
[9] 田朝旭.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影响[J].外语学刊,2003,(4).
[10] 孙冬.论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中的意象[J].学术交流,2005,(6).
[11] 杨革新.《风琴》里奏出的和声———史蒂文斯生态意识管窥[J].世界文学评论,2010,(1).
[12] Stevens Wallace.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allace Steven,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54.
[13] 徐畔.中国文化移入在华莱士5史蒂文斯诗歌中的体现[J].外语学刊,2012,(4).
[14] 向以鲜.神秘的陶罐——当代诗歌意象的历史文化诠释之一[J].当代文坛, 2007,(6).
[15] 陈植锷.诗歌意象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6] 郑殿臣.美中意象诗比较[J].大连大学学报,2003,(1).
[17] 徐畔.史蒂文斯诗歌的中国画意境[J].北方论丛, 2014,(4).
[18] 肖明翰.中国文化的影响与美国现代主义诗人对秩序的探寻[J].东方丛刊,1998,(1).
[19] 徐畔.中国古诗词元素在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中的移入现象研究[J].文艺评论,2014,(3).
[20] 张子清.中国文学和哲学对美国现当代诗歌的影响[J].国外文学, 1993,(1).
[21] 钱兆明.史蒂文斯早期诗歌中的禅宗意识[J].外国文学评论,2015,(1).
[22] 顾明栋.视觉诗学:英美现代派诗歌获自中国古诗的美学启示[J].外国文学,2012,(6).
[23] 邵志华.误读视阈下意象派对中国古诗之接受[J].南通大学学报,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