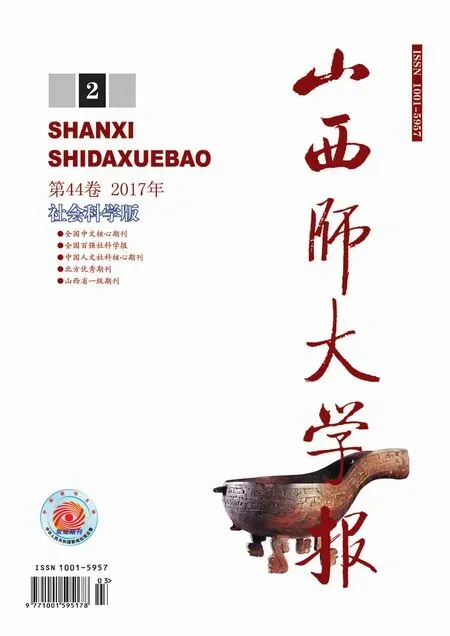“问题化”之后的虚无
----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批判
杨 文 臣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在当前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加拿大著名学者琳达·哈琴的“后现代主义诗学”正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她看到了后现代主义内在的矛盾和悖论,力图超越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准确客观的界定和阐说。通过对当代建筑、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编写等各个领域的立体透视,哈琴告诉我们,后现代主义的旨趣和价值在于:通过戏仿和反讽,将历史、真实、主体性、人文主义等宏大概念“问题化”。所谓问题化,即对这些似乎不言自明的概念保持质疑和发问,使人们意识到它们的话语建构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由此出发,我们才能真正取消中心和等级,看到多元和差异,从而保持思想的活力,并以更恰当的姿态介入到政治之中。
哈琴把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特里·伊格尔顿作为自己的论辩对手,坚决反对他们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否定性诊断;同时,她也不认为后现代主义像其支持者声称的那样具有革命性。“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模式是既/又,而不是非此/即彼。”[1]310对于批判对象,它既认可又质疑,既置身其中又对其进行消解。基于对后现代主义矛盾性、双重性的详尽阐说,哈琴摆出了貌似客观持中的评判姿态。这一招相当高明,不仅使自己巧妙地避开了来自后现代主义的反对派和支持派两个方向的攻击,而且颇能吸引和征服当代偏爱辩证思维的头脑。目前,国内不多的几篇关于哈琴的研究论文都站在认可和支持哈琴的立场上,代表性的有林元富的《琳达·哈琴后现代诗学初探》《后现代戏仿:自恋式的作业?——关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理论的一些争论》以及陈后亮的《论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的理论特征》《再现的政治:历史、现实与虚构》《后现代主义与怀旧病》等一系列文章。
实际上,哈琴是全心拥护后现代主义的,她认为后者将一切总体性的话语、概念加以“问题化”的策略是这个时代能够采取的最恰当的立场。鉴于后现代主义及其评判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关系重大的课题,关于它的一切理论学说我们都要谨慎对待。本文的研究旨在表明,哈琴的理论远非看上去那么完善,她推崇的后现代主义“问题化”本身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尤其在政治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
一、精英式的后现代主义与不适宜的理论模型
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更具明晰性和说服力,哈琴给后现代主义做了具体但狭隘的界定,单指那些有明确旨趣的艺术家和思想家进行的严肃的文化活动,诸如保罗·波多盖希的建筑、特里·吉列姆的电影、迈克尔·库切的小说以及迈克尔·阿舍的艺术品。而大众文化和商业化大潮中的那些我们冠之以后现代主义名号的拼贴、堆砌、模仿之作,根本不在哈琴的研究视野之内——“必须把查尔斯·穆尔的意大利广场同所有那些贴在现代主义建筑正面的时髦的古典拱门区分开来。”[1]310这样,哈琴便可以赋予后现代主义以严肃重大的思想意义,将“矛盾性、坚定不移的历史性和不可避免的政治性”视为其主要特点。哈琴没有费心阐发自己所认可的后现代主义同商业化了的后现代主义之间关系,这在她看来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任何东西都会被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所侵蚀,失去原有的品格和严肃性,变成无足轻重的嬉戏。这就产生了一个会让哈琴陷入尴尬的悖论:后现代主义强调消解等级和界限,而哈琴的后现代主义界定恰恰建立在等级观念之上。通常我们以精英立场和平民立场来区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但哈琴的后现代主义却比现代主义更具精英品格,基本上和平民没有瓜葛,理解她所认可的那些后现代主义作品需要有极高的理论素养和思维能力。
但在詹姆逊看来,哈琴对两种后现代主义的区分完全没有意义,二者在精神气质上是一脉相承的,都体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跨国资本在全球扩张中利用、侵蚀它所遇到的所有文化形式,给商品披上文化外衣的同时也掏空了文化的内涵。形形色色的文化形式脱离了原来的语境,成为仅供消费的形象被并置于一个空间之中,空间因而被改造成了一个充斥着幻影和模拟、压抑了时间性的“超空间”,人们的感知、经验和思维方式等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种后现代“超空间”的重塑。[2]172无论是哈琴认可的严肃的后现代主义还是她否认的商业化了的后现代主义,都在响应生产关系和社会状况变迁的要求,尽管与后者的有意推波助澜不同,前者的响应可能是无意识的。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针对的主要是和消费文化结盟的后现代主义,这种后现代主义是后期资本主义的主导美学,是正在对每个人的经验进行重塑的文化现实。当哈琴抱怨詹姆逊把后现代主义的戏仿和反讽误读为抄袭和拼贴并由此做出“保守的怀旧主义”的论断从而忽略了其严肃旨趣时,实际上是她没有看到两人关注点的不同。当然也有可能是哈琴为了使对詹姆逊的批驳更显得理直气壮而有意忽略这一点。可是,现代主义因其精英主义的诉求和封闭性已饱受包括哈琴本人在内的诸多理论家们的质疑,哈琴的精英式的后现代主义又能和现实的社会进程发生多大的关系?承认了后现代主义无法抗拒大众文化的收编,再去反驳对于后现代主义保守性的指责还能有什么说服力?哈琴简单地辩白说:在现代主义审美实践被高雅艺术市场与大众传媒文化吸收和中和时,人们选择了区分艺术本身和艺术的商品化,公平起见,对后现代主义也应如此。[1]310在此,她忽略了艺术市场和大众传媒是通过把商品价值附加于现代主义艺术之上对其进行收编的,艺术品本身的批判意识并没有削减;而后现代主义倡导的解构、差异、对历史和真实的质疑却为剽窃拼贴的、无足轻重的大众艺术打开了方便之门。哈琴的区分只能说是一种无原则的为后现代主义推卸责任之举。
为了凸显后现代主义的优越和增加理论的明晰性,哈琴把后现代主义建筑作为自己的理论模型。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现代主义建筑把功能视为建筑的本质,主张将一切和功能无关的多余东西——诸如隐喻、象征等建筑的形式表达——统统抛弃,从而发展起一种无视文化、历史和地域差异的国际风格,简洁、千篇一律、闪烁着冰冷金属光泽的摩天大厦成了一个时代的宠儿。20世纪后期,这种片面强调实用性、崇尚机器美学的现代主义建筑受到抵制,人们控诉它无视使用者的诉求、审美缺失和窒息人性。哈琴指出,现代主义建筑“相信科学和理性能把握现实,这等于是既隐晦又明确地拒绝了从过去继承、演化而来的文化的连续性”[1]39。作为反拨,后现代主义建筑应运而生。波多盖希、詹克斯等人呼吁恢复建筑与过去的连续性,将历史形式吸收到现代建筑中。不过,他们对复制历史没有兴趣,而是要通过戏仿、反讽与过去进行充满活力的对话。“现在的建筑师们在努力寻求一种公共话语,以便从过去的‘现在性’角度,从出于社会考量将艺术置于过去和现在的文化话语之中的角度表明现在。”[1]47这样,后现代建筑打破了现代建筑的封闭性,恢复了与历史的连续性,同时又并非是一种保守的怀旧主义,它在向历史致敬的同时保持了清醒的反思。尽管很多时候建筑师们的编码未必能够被理解,但后现代主义建筑还是因其糅合历史形式带给居民和观光者的多样化、温情脉脉的审美体验而受到欢迎。鉴于现代主义建筑和后现代主义建筑的高下已有公论,哈琴才把建筑作为自己的理论模型,来为后现代主义的戏仿和反讽做辩护。然而,哈琴在此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她简化了现代主义的复杂性,没有辨别建筑的现代主义和其他艺术形式的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异。史蒂文·康纳指出:“许多画家、雕塑家、作家和音乐家事实上同现代性的物质成功有着一种非常矛盾的关系,采取了与正在形成的机器文化相对抗的态度。由于建筑在物质和意识形态上与公众和经济领域相结合,这一点并不那么明显。……建筑从早期开始就被迫与商界和政界媾和。”[3]78用我国学者周宪的话说,现代主义是以审美的现代性对抗启蒙的现代性[4]149,而建筑领域的现代主义和启蒙现代性却是一种合作关系。以后现代建筑作为理论模型显然会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做出错误的判断,在论及现代主义的封闭性和非历史性时,哈琴正是由此走入迷误。
二、历史的问题化与历史的消解
哈琴之所以为自己的后现代理论冠以“诗学”的名号,一方面是因为她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主要围绕后现代艺术尤其是小说展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立足和海登·怀特一致的历史观,否认历史和小说之间可以划出清晰的、可维持的界限,认为所有的历史都具有虚构性。哈琴特别青睐她称之为“历史元小说”的文学样式,这类小说大都以为人熟知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题材,但却使其以一种令人陌生、愕然的面目出现;不过,它们拒绝用自己的叙事取代旧的历史叙事,而是自觉地反思其自身作为小说的属性,突出作者的形象和写作行为,藉以晓谕我们:一切历史都是文本中的历史,都是话语建构之物。据此,哈琴认为其他后现代理论家所提倡的纯粹自我指涉的小说——如罗伯5格里耶的新小说或雷蒙德·费德曼和罗纳德·苏肯尼克的超小说——不是“后现代主义”的,而是“超现代主义”的。现代主义文学是与世隔绝、非历史的,满足于自我修饰;而后现代主义文学谋求向历史开放。当然,与传统的历史小说不同,历史元小说不书写历史,它通过对过去的消遣来质疑历史书写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历史元小说特意提醒我们,虽然事件的确发生在真实的、经验上的过去,我们却是通过选择和叙事定位将这些事件命名和组建成历史事实。说得更到家一些,我们只是通过把这些过去的事件设定在话语里,通过其在现在的痕迹来了解这些事件。”[1]132换句话说,没有单一的历史,只有无数的关于历史的叙事和文本——所有这些叙事和文本无一例外地受到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形形色色的力量的制约。历史元小说要消解我们寻求那个根本无法捕捉的历史真实的冲动,使我们保持对一切号称客观和权威的历史叙事的质疑,这就是“历史的问题化”。
诚如哈琴所说,虽然对历史知识和历史叙事的中立性、客观性的质疑并非为后现代主义所特有,但后现代主义空前集中和强化了这种质疑。几乎所有的历史元小说都在喋喋不休地讲述同样的主题:权威的、连续性的、有意义的历史叙事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在此过程中谁的声音被压制而谁的又得以张扬;意识形态是怎样参与又被隐藏在历史叙事中。与此同时,它们也都念念不忘以断裂的形式打破自身的连续性以确保所有这些质疑的彻底性。哈琴赞赏地指出:“历史元小说公开肯定,真相只能有多种,从来就不是一种;几乎没有什么虚假之说,有的只是另外的真相。”[1]147
福柯、罗蒂、德里达、利奥塔、鲍德里亚等众多思想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对中心和本质进行过消解,因而,在谈到后现代主义对多元和差异的迷恋和维护时,哈琴很是理直气壮。在她看来,现代主义质疑为不合理的等级秩序提供合法性支撑的历史叙事的策略是:自己构建一套“真实的”叙事取而代之。往往他们诉诸浪漫、神秘的超验想象,或者构造一个丰富多彩的过去以衬托现在的荒芜贫乏。后现代主义则认为现代主义叙事同样是特定语境下的话语建构,并不具有他们自己所宣称的真理性。既然任何叙事都不可避免地是话语的建构,那么最具革命性的姿态就不是以一种取代另一种,而是保持对任何一统化叙事的质疑,揭櫫它们所遮蔽的差异,追求多元性的价值,从而保持思想的活力。
一切历史叙事都不可靠,一切连续性都来自人为的选择和编织——哈琴的这种后现代主义论调很难逃避历史虚无主义的指责。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历史形成过程,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清醒认识是我们进行变革以及保证变革朝一个好的方向发展的必要条件。因而,尽管困难重重,我们仍要不断接近历史,旨在诊断出社会的病因并开出正确的药方。固然,哈琴说得没错,任何历史叙事都是话语的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话语都不能说出我们可以相信的历史真实。伊格尔顿批判到,苦难和压迫顽固地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中,“如果历史的确是完全随机的和不连续的,那么我们怎么说明这一奇怪地持续着的连续性呢?它不是作为最极端的偶然赫然耸现在我们面前吗——按照某些人的看法只是万花筒无尽的随意翻滚的一部人类历史,应该一次又一次地将它的碎片组成了匮乏和压迫的形式吗?”[5]62福柯告诫我们不要相信通过对异己声音疯狂压制建立起来的理性和科学的宏大叙事,那我们是否应该相信福柯展示的疯癫史和身体受到规诫的历史?同样,女性主义者书写的女性受难和女性声音受到压制的历史呢?尽管哈琴也把福柯和女性主义引为同道,但按照她的逻辑,我们只能矜持地对他们进行质疑。
否定我们可以认识历史的真实,或者说,否定我们可以从历史维度对当前事物做出解释,也就意味着我们将失去任何行动的能力。哈琴认识到这一危险,于是一再辩解,后现代主义并不否定,只是质疑。它先确立对象的存在再对其进行质疑,依靠它所攻击的对象而存在,这是它固有的矛盾。后现代主义并不否定各种历史叙事作为功能性存在的必要,但它要求我们保持质疑,以避免任何一种一统化叙事奴役我们的思想。然而,一旦认定所有历史叙事都没有历史确定性作为支撑,我们就很难再施与信任,我们就会因此失去建基其上的对于现实的判断,进而失去建设一个美好未来的信念。米兰达·弗里克声称后现代主义根本不具有心理可能性,因为它的逻辑必将牵连自身:后现代主义者质疑一切历史叙事的立场本身也是一种一统化叙事,他们必须承认自身的陈述也是暂时性的、脆弱的,他们对自身笃信的信念和价值也不能给予最终的认真对待。那么,“在一种我们甚至不能十分认真地对待我们最为笃信的信念和价值的生活中,我们很可能会怀疑我们的心理健康前景。我们有权力去质疑那种生活是否值得去过:在其中,历史上的自我意识的成就已经在其中退化为一种心照不宣的虚伪”[6]167。
的确,没有一种叙事能绝对地揭示出历史的全部真相,基于某一学说的历史决定论可能会把我们引入歧途,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认识历史。新的视域、观念、方法在帮助我们不断修正和扩充旧有的历史叙事,使我们不断地接近历史真实。我们并不否认过去的无限丰富性和历史运行的极端复杂性,但我们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获得确定性的历史知识和可以信赖的历史规律,并用来有效地指导我们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活动。哈琴认为后现代主义质疑一切历史叙事的立场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历史意识,但这种将历史“问题化”的做法却如伊格尔顿所说,将历史变成了一个当前事态的星系,一个永恒在场的群组。消解了历史的深度和连续性,也就消解了历史。
三、主体性的破碎和空洞无力的政治姿态
詹姆逊认为,在后现代社会,由于历史连续感的丧失,人“无法使自我统一起来,没有一个中心的自我,也没有任何身份”[7]176。这是一种精神分裂式的、非真实存在的生命漂泊物,丧失了思考和行动的能力,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哈琴也乐意将主体性的瓦解和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只是她做出了完全相反的评价。不同于詹姆逊的痛心疾首,哈琴欣然指出,如同历史连续性本来就是一种离不开选择和排斥的人为建构,建立其上的传统主体观念也只是一种幻象,其后隐藏的是对性别、种族、阶级等差异的抹平和压制。事实上,个体总是深深卷入其所处的语境中,在矛盾重重的意识形态话语下进行着主体性的艰难构建,从来就不存在超出语境、与意识形态相疏离的超验主体。后现代艺术极力破坏自给自足的艺术对象以及与此相伴的超验的艺术主体观,恰恰是破除迷误之举。像《白色旅馆》这类小说,之所以让人困惑和烦躁,就在于它触犯了我们虚假的主体信念:身处各种话语权力交织的漩涡中,人们根本无法确认明确的身份和主体性。
没有了能够超脱于特定语境的主体,那么试图站在所处语境之外对其进行批判的行为也就失去了合法性。哈琴指出,一些大学教师和学者支持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拜物教性质的大加鞭挞时,忽略了他们本身就是教育产业这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而教育产业同文化产业是不可分割的。詹姆逊批判后现代主义所依据的基本论断,也是同人文主义主流学术环境串通一气的,他对这一点同样缺乏明确的意识。[1]284置身其中却又自以为超脱其外,詹姆逊的批判理论的革命性和彻底性就很值得怀疑。而后现代主义要明智得多,它意识到自己无法脱离自己的批判对象,于是放弃了那种坚固的、正义凛然的主体性,采取了既认可又质疑、既置身其中又对其颠覆的做法。具体地说,后现代主义不像现代主义,生怕受到玷污和同化,顽固地坚持与现实相疏离的审美统一性,而是慷慨地接纳现实社会的一切,从种种意识形态话语到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产品,然后,再通过戏仿或反讽对它们进行消解和颠覆,揭露其语境性和意识形态性。哈琴由此认定,和现代主义相比,后现代主义更具现实感和政治性。
哈琴不满詹姆逊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怀旧的、反动的攻击,也不承认后现代主义像一些支持者所声称的那样具有革命性。[1]299这种貌似客观的表态实际上却是一种褒扬。哈琴对启示录或乌托邦式的批判话语和革命理论很是反感,认为若将它们付诸实践很可能会带来新的压制,因为它们不过是试图以新的权威取代旧的权威,以新的总体性取代旧的总体性。20世纪人类走过的历程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既然全盘否定、推倒重建是一种虚妄,那么最合适的政治姿态当然是后现代主义这种温和的质疑和批判。
可是,后现代主义的质疑能够带来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吗?虽然启蒙运动书写的那一套以人类主体力量的增强和物质财富的增加为依据的“进步”话语已经遭到质疑,但我们还是要怀有希望和憧憬,还是要追求进步,还是要努力推进世界向更平等、更和谐、更人性化的方向前行。正因为此,詹姆逊仍然钟情于乌托邦的想象,认为这是任何有效的政治实践的前提。[8]371——当然,詹姆逊不会幼稚到仍然迷恋柏拉图、卢梭式的乌托邦蓝图,他的乌托邦毋宁说是基于对现实的洞察而谨慎地提出的一种理性展望,同时也是一种进行批判和分析的视角。詹姆逊反感后现代主义的原因之一就是后者导致了乌托邦的消失。的确,如果不指向某种美好的未来,任何质疑和批判就都失去了意义,政治性、革命性也成了一句空话。后现代主义从未试图给我们指出方向,它也不信任任何方向。它所做的一切就是质疑,质疑一切,包括不合理的现实和人们为改变这种不合理而设计的方案。哈琴声称,后现代主义只提出问题,不提供答案。问题是,后现代主义之后已经没有可能再得到答案,因为答案也是一种需要质疑和消解的叙事,与其他叙事没什么不同,人们没有动力也没有必要再去寻找。“后现代主义就通过将所有差异和价值平等看待,从而使价值这一概念变得空洞,并丧失了政治行动的目的,后现代主义也因此失去其批判性,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精神形成共谋。”[9]后现代主义就像一个懦弱的勘破红尘者,看透了世间的一切虚伪、不平和罪恶,也不相信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结果只能是与现实和解,心安理得地忘情红尘、游戏人间。提摩太·贝维斯对这种犬儒主义态度痛斥到,后现代主义“临时地逃避理性的政治律令,逃向寂静无能和懒惰无力,而且还要乔装打扮成对真实和真诚的追求,在‘新真诚’的旗号下行进却无法在政治上介入”[10]281。
对于后现代主义可能开启的政治前景,哈琴只是含糊其辞地称:“后现代主义对权威的质疑将为大众操纵社会铺平道路。”[1]283这种断言问题重重。首先,如伊格尔顿所说,“它的文化相对主义和道德约定主义,它的怀疑主义、实用主义和地方主义,它对团结和有纪律组织的观念的厌恶,它的缺乏任何关于政治中介力量的适用理论:所有这一切都将对它极为不利”。[5]152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逻辑内在地抵触有力的政治行动,它只能在思想领域质疑权威却无力也无意在政治实践中削弱权威。更根本的是,被消解掉主体性的大众并不可靠。不管詹姆逊还是哈琴,都认可主体总是受到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而当下占绝对优势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在大众的塑造中起支配作用的力量——并不是哈琴推崇的精英式后现代主义,而是被商业资本和大众传媒所收编的后现代主义:本来具有严肃旨趣的戏仿、反讽褪化为毫无价值的抄袭、拼凑、大杂烩,人们轻松而又麻木地游戏于支离破碎的表象之中,满足于廉价的消遣娱乐,丧失了任何批判精神,成为“一种娱乐至死的物种”[11]6。责任在商业化而不在后现代主义本身——这是哈琴给出的回答。然而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前文我们已经谈到,与追求深度和超越的现代主义相比,后现代主义对深度和真理的消解、混杂的风格以及隐含在戏仿和反讽中的游戏品格,都为其被商业收编敞开了方便之门。哈琴有选择地划定后现代主义以便为其辩护的策略并不成功,其政治上的空洞无力依然难以置辩。
通过哈琴的表述,不难看出她其实是单纯地立足解构主义思维来阐释后现代主义,理论视野远不及她的论敌詹姆逊和伊格尔顿。本文的批驳当然不是要全盘否定哈琴的后现代主义诗学的价值,她对于历史元小说的精彩阐释,对于戏仿和反讽的卓越探讨,都扩展了我们的视野。不过,必须清醒意识到其思想中的诸多混缪之处,否则会影响我们对后现代主义做出正确的判断。
[1] (加)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M].李杨,李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 (英)肖恩·霍默.弗雷德里克·詹姆森[M].孙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 (英)史蒂文·康纳.后现代主义文化——当代理论导引[M].严忠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 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 (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M].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6] (英)米兰达·弗里克、詹妮弗·霍恩斯比编.女性主义哲学指南[M].肖巍,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7]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乌托邦和实际存在[A].王逢振.詹姆逊文集·第3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9] 方钰.走出后现代主义的幻象——论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的解读[J].山东社会科学,2001,(1).
[10] (英)提摩太·贝维斯.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M].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11] (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吴艳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