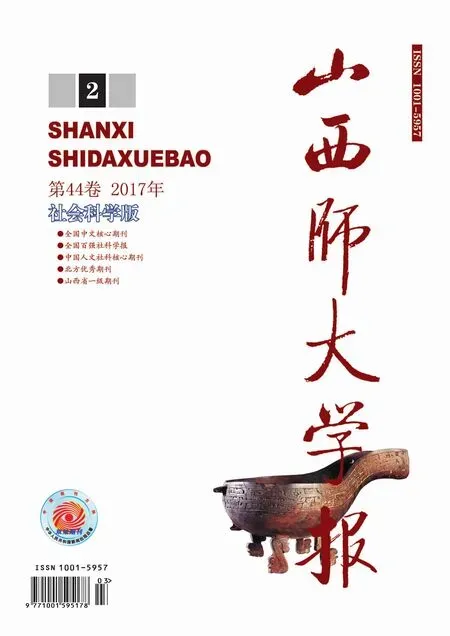钱穆的文学史料观及其史学实践
郭 士 礼
(成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 610059)
近百年来中外文化冲突融合的事实形成了现代史家文化观的基本框架:即试图将一切文化冲突融合及建构发展的现象都置放于外来文化输入与传统文化如何因应的语境中去考察理解,以异域文化思潮为参照系,对传统文化之意义与价值重新加以评估则是普遍遵循的基本范式。此一框架与范式对现代中国学术文化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以现代大学为依托的学术分科体系的建立。在此体系下,文学与史学隐然以学科独立是尚,严守学科畛域。而以文史不分、学贵尚通为基本特性的传统学术文化则逐渐从人们的学术视野中淡出。在此背景下,钱穆在民族文化史观立场下,以“尚通”为学术研究之旨归,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解读及运用所展现出的学术价值更值得探讨与挖掘。
一
在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之下,中国的现代史学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趋于成熟。在这一过程中,对边陲民族历史的重视,对比较语言学的研究,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偏重以及考古发现和新材料的发掘一时成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主流取向。经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等史家的共同努力,无论是议题、史料、方法、理论,还是表达和评判标准,以及所依托的制度等,都和传统史学呈现出明显差异,而这其中对史学的科学性定位更是中国现代史学的核心要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史料尽量扩充”的学术氛围中,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以其纪实性的品质进入了现代史家的视野。“史学就是史料学”这一颇具西方史学特质的宣言,也就成为大多数现代史家探讨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主要理论资源。
傅斯年提出要把历史学提高到如地质学和生物学一样,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必须准确地鉴别史料,因为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史料不准确,要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便失去依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傅斯年提出了“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口号,注重证据、强调新材料进而提升考据的准确性是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家们共同的诉求,他一再强调历史研究不需要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判断与情感介入,因为这样会影响历史的客观性。傅氏曾坚定地表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作疏通的事业。”[1]308傅斯年此论,强化了历史学科的科学性与独立性。但钱穆则认为史学的工作并不仅仅是科学的整理史料,更重要的是能否呼应现实,能否指出一个大方向来解决时代困局,此点才是史学的核心要义。且在钱穆看来,自守学科畛域将其他学科排斥在史学研究之外亦不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之全貌。尤其是在对待文学的态度上,只是将其视为单纯的考证性资料,对钱穆而言是不能接受的。在钱穆学术生涯中,文学发挥了一种基础性作用,他本人“基本上是透过吟咏古人文章,逐步进入古人的心境的,理解古人的心灵与境界”[2]146—147。此种由文入史的治学路径决定了文学在钱穆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
当然作为现代史家,钱穆对历史对象的客观性同样表示认可:“无论何种看法与想法,须求不背历史真实,则是一大原则。”[3]34但对于何谓历史的真实,钱穆则有自己的体认,首先他认为“史学是一种生命之学”,“历史是一种把握我们生命的学问,是认识我们生命的学问”。[4]10此种历史观就与傅斯年等人强调的科学与客观颇为不同,钱穆将历史的本来面目视为一种超自然的精神文化。历史既然是有生命的,那么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就是紧密联系着的,是一种从过去透过现在而直达将来的,有它一贯的精神。正如有学者观察到的,钱穆史学研究“所求的是一种古今的时间连续感 ,这些传统对他而言是活的 (living past),故他显然反对站在外面加以‘重估’或‘评判’的态度”[2]147。所以从这个意义上,钱穆认为“鉴古知今”、“究往穷来”就成为了传统史学最主要的追求。“鉴古”之所以能够“知今”,“究往”之所以能够“穷来”,就在于“历史乃人生之记载”,“历史本身,就是我们人生整个已往的经验”[4]5。据此可知,钱穆更为看重的是对历史这一文化生命体中蕴含的人生之经验的探求,而非史料的考证与史实的还原。既然历史的本质与主体是有生命的经验之学,那么历史就不能拒绝主观介入,“世界上绝无有纯客观的历史。因我们决不能把过去史实全部记载下来,不能不经过主观的观察和了解而去写历史”。[5]32既然强调主观与情感,那么钱穆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判断就远非傅斯年所追求的客观与真实那么简单。
与对历史内涵的“生命”“经验”界定相关联,“文学即人生”是钱穆对文学的总体认知与把握。立足于传统文化的立场上,钱穆对中国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作了独到的把握与解读。以诗文为代表的正统文学,“多以作家个人之内心情思及其日常生活为题材,即以作家之真实人生融入其作品中”[6]50,正是因为“真实”之故,方具有史料之基本价值。分而论之,钱穆认为以诗文为代表的古代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历史过程的全部”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文学作品内容的真实性可以了解作者生平,文学作品的形式也可以用来考察古书真伪及成书年代;其二,文学作品与历史环境的紧密结合,使得通过文学作品来考察社会观念及心态变迁有了可能;其三,文以载道,文学是了解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
二
中国传统诗歌、散文的真实性品质使其天然地具备了史料价值。此种价值最集中地体现在它是了解作者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史料。钱穆再三指出,中国传统文学之中,优秀的作品一定是真实的,“中国文学中之最上乘作品,必然多以作家个人之内心情思及其日常生活为题材,即以作家之真实人生融入其作品中,而始得称为最上乘”。[6]50传统文学正是具有此一真实性特质,“遂引起后人为各著名作家编年谱,及把诗文编年排列,这又是中国文学与史学发生了关系”[7]70。在这里,钱穆所谓文学与史学发生关系,是仅就著述体例而言。因为按年编排史料仍然是历史书写的基本要求,故而从史学最原初的样态上,中国古人的诗文集就蕴含着历史的气息。尤其是儒家色彩浓厚的作家更是如此,如杜甫、韩愈、苏轼、王安石,都可以按年代排列来读他们的诗,且从其诗文集之中能够大致了解作者一生之行状。“在他作品里,把他全部人生琐细详尽地写出来。这样便使我们读一个作家的全集,等于读一部传记或小说,或是一部活的电影或戏剧。他的一生,一幕幕地表现在诗里。”[8]120以杜甫为例,钱穆认为其诗作“不仅为杜甫时代之一种历史记录,而同时亦即是杜甫个人人生之一部历史记录”[7]40。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而言,能够真实反映作者的人生世界是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最基本的体现。
在实践层面,钱穆以文学作品来考察作者的身世的代表作是《读寒山诗》。寒山子作为唐代极富盛名的隐士之一,近代以来自胡适开启研究之风以后,便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关于此人的状况,历史资料记载极为匮乏,其个人的诗歌便成为众多学者了解其生平的最重要资料来源。钱穆也不例外,“偶温寒山诗,稍有勾稽其身世”,他的《读寒山诗》一文同样也是凭借流传至今的寒山诗歌大致勾勒出其人一生行状。从诗歌中钱穆大致总结出有关寒山子个人的基本信息,首先就是有关寒山子的个人及家庭状况。通过对其诗歌的分析钱穆认为他的身份是隐士,且是举家隐居,其早年亦曾应科举,并屡试不售。此外他也有兄弟,异地而居。其次有关寒山子的思想状况,钱穆认为,他早年“喜道家言,治老子书,而尤喜神仙长生修炼之术”,中年以后并兼涉佛理,而至晚年则出家为僧。关于寒山子生活的时代,钱穆从其“高高峰顶上,四顾极无边。独坐无人知,孤月照寒泉。泉中且无月,月自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终不是禅”一诗中认为,寒山“此诗已深具禅机,而自辨不是禅,知寒山生世,应在唐代禅学既盛之后”,且此类颇具禅意的诗多不胜举,故钱穆认为寒山生活的年代不应是在贞观年代,因为禅宗创始人慧能生活的年代是在贞观时期,此一时期禅宗刚开始产生,而寒山诗歌中所展现出的禅宗境界应该是在禅学极盛之后。“寒山诗极富禅理,其人亦为禅门所乐引重,其生世当在大历贞元间,不能上出贞观,即就禅学发展及其诗风格言,亦断无可疑。”[9]195
如果说文学作品自身内容的真实性能够考察作者的生平的话,那么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钱穆通过文章文体来辨别其古书真伪及其成书年代先后,便是此一史料价值的体现。他认为中国古代散文最先只是辞,“自西周书下及钟鼎文,其用字造句,终不失为一种上古文之面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尚书》中的《西周书》。但到了春秋时代,孔子作《春秋》,其“用字造句,则面目一新,骤看直与后代人之用字造句无大区别”。所以钱穆认为,从《尚书》到《春秋》实是中国古代散文演变一大进步。而从《论语》到《孟子》又是一个阶段,“论语多属短品,孟子尽有长篇,洋洋洒洒,雄奇瑰丽,在散文史进展上,可说又跨进了一大步”。所以说,中国散文到了论孟时代其文体形式就由辞发展到章。《孟子》以后便是《墨子》《庄子》。后两书与前者在文体上的差别是明显的,“孟子还是古人记言之体,仍可说是论语檀弓之旧格套……然墨子书如尚贤、尚同、非攻、兼爱等篇,显然是后世一篇议论文之体裁。孟子雄辩,墨子凝练,而墨子更见有从口语记述转变为行文作论之痕迹”。而从《墨子》到《庄子》亦能看出文体演变的痕迹,“墨子凝练,庄子恢奇,庄子既非记言记事,又非立论立议,简直可说是有意为文。但庄子多用寓言体,到底仍是沿袭着古代记言记事的旧体裁”。而从《庄子》到《老子》,就文学观点而言,钱穆认为更是大大一进步。“全部道德经,寥寥五千言,但一开始便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作为提纲,这又是文体上一大进步”。《中庸》《大学》的文章体例一如《老子》,即可证它们产生的时代约略与《老子》同时或稍后。《荀子》因其产生年代最晚,所以可以说是诸子散文中的集大成者,“若把后代散文立论建议之法度来讲,荀子文体在战国时可算是最进步,最接近后世之法度。”[10]343如果仅就史料价值而言,不论是对作者生平的考察,还是通过文辞来判断古书真伪及产生的时代先后,文学作品固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不得不指出的是,从考证与还原史实层面而言,文学的史料价值并不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然钱穆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考察进而探究时代内蕴及心情的实践,则展示了文学作品无法为其他史料替代的价值。
三
在钱穆看来,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对外在的、物质性或社会性事实的真实反映与忠实记录上,更重要的是可以以此来考察作者所处时代的“内蕴”与“心情”,传统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不可替代性在考察观念变迁与心态变化方面得到全方位呈现。钱穆认为,“中国的文学传统,每不远离于政治之外,而政治乃文学之最大舞台,文学必表演于政治意识中。”[7]38在这里,钱穆所谓政治系指传统观念下的政治,其内涵则是“以心性为基本,治平为标的”的儒家传统。作家只有将一己情感、生活与家国社会密切联系起来方能称其为正宗之文学,传统诗歌、散文便是此类代表。
在钱穆看来,反映作家真实“自我人生”的以诗文为代表的正统文学,不论是其表现的“人生道德”还是“人生艺术”均来源于作家对天地自然、现实社会、历史传统的整体关照与把握。一个理想的作家必须在其自身生活中,能密切与此整个社会相联系,“必期使此社会种种变故与事相,均能在此文学家之心情与智慧中,尤其明晰而恳切的反映。而此种反映,又必能把握到人心所同然”。正是由于这一传统,中国传统文学便具有了更高层次的史料价值,从中不但能够窥探作者人生之全部,更能把握时代信息,尤其是时代观念与心态,“中国文学重在即事生感,即景生情,重在即由其个人生活之种种情感中而反映出全时代与全人生。全时代之心情,全时代之歌哭,以及于全人生之想像与追求,则即由其一己之种种作品中透露呈现”。[7]39完全可以这么说,中国传统文学此种反映现实以及人生理想的特性使其史料价值更能充分彰显。
运用古人诗文集来探究“时代内蕴心情”的代表作是《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文章开篇,钱穆即指出:“本文作意,不在论诗文,……在借诗文以论其时代内蕴之心情。”[11]86所谓时代内蕴之心情,简而言之就是某一历史时期特定人群的观念及心理。这篇颇具代表性长文有意从史料学的角度切入,以明代的不同时期的文人对明初开国诸文人诗文集的认知与解读的演变的历程为考察的重点,对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进行了充分的阐释与挖掘,使其发挥出一般史料所没有的价值。
在文章开篇钱穆即指出,“胡元入主,最为中国史上惊心动魄一大变……中国全境沦于异族统治之下,亦为前史所未遇。”故而在一般读史者看来,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之举在当时应该赢得士人的响应与支持。然而通过翻检当时文人诗文集后,钱穆发现其内情远非后人所想像的那么简单,“当时群士大夫之心情,乃及一时从龙佐命诸名臣,其内心所蕴,乃有大不如后人读史者之所想象”。而欲对此时代心情予以发覆,必以文学作品为最重要的史料来源。以探讨宋濂、刘基、高诚等人的诗文集作为契机,钱穆在这篇文章中措意有三:其一,梳理不同时代的人对明初诸臣之诗文集的不同认知,以此来考察一时代观念变迁与心态变化;其二,重点分析探讨以宋濂、刘基、高诚等为代表的士人在元末明初的心理情结及观念认知;其三,有感于元末明初文人的观念畸变与心态之扭曲,进而表露出自己对传统文化核心要义之思。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根据钱穆的考察,元末之时,在时人为宋濂文集所作的序中,透露出这样一种史实:“当时士大夫,方以元之一统与汉唐宋争盛,至于其为胡虏入主,非我族类,则似已浑焉忘之矣。”[12]91也就是当时知识分子只知有所谓文章道德,而家国兴亡、夷夏之辨均不在考虑之列。更令钱穆感觉到奇怪的是,为宋濂文集作序之文人,皆自著其在元之官衔职名。“这些人出身虽微,要之言必称本朝,而其本朝则胡元也。彼辈之重视昭代,乃与在朝仕宦者无二致,则何其于亡元之崇重,而于兴明之轻蔑”。由此,钱穆准确得知一历史信息,就是当时知识分子对新兴的大明王朝普遍持不合作态度。“明祖之待元臣,实不可谓不宽大,而当时士大夫之忘其为华裔,仅知曾食元禄,亦可见世风士行之一斑矣。”[12]92在钱穆看来,怀念亡元政权,对新生大明王朝则持一种敌对态度,心中全无夷夏之辨是元末明初文人集团普遍共有之心态与观念。
稍后,到了宋濂学生方孝孺生活的时代,时人对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的解读又呈现出细微的变化。如方孝孺在为宋濂晚年文章《续文粹》所作序文中对宋濂的评价,与元末明初之时人们普遍只关注宋濂等人的文章业绩不同,盛称其师之业绩在于“正彝伦、复衣冠、制礼乐、立学校,凡先王之典,多讲行之”,“使中国之美,传于无极”,这在当时是首次对明初开国诸文臣之有功于世道的层面予以揭发。但在钱穆看来,方孝孺所序之文,“亦仅颂扬中国之有新朝,其于亡元,则亦止于为弦外之音而已,尚未遽畅厥辞也。”[12]100透过方序仍能隐约透露出时代风气之转向的意味。
明代立国一百年后,文人士群眼中的明初开国诸文臣的诗文集又是另外一番天地。嘉靖时期的杨守陈在《重锓刘诚意伯文集序》一文中开始称亡元为夷为胡,而朱元璋剪灭胡元回复华夏衣冠正统之观念方始盛行,“嗟乎!唯元奄四海而垂八极,极弊大乱,开辟以来未有也。高皇扫百年之胡俗,复三代之华风。”至是而华夷为防之大义,中国历史之正论,乃开始重见于文人之笔端。但在钱穆看来,“时移世易,后人不识前人之心情,若必以驱除鞑胡为宋刘诸人之功绩,恐宋刘在当时,初无此想,抑或将增其汗惭不安之私焉,亦未可知也。”[12]102此种解读与认知只能是百年后的士人的心态。
如果说通过不同历史时期士人对于宋濂文集的解读与认知反映出不同的时代内蕴,那么通过对刘基与高启等人文集的解读则更能体现元明易代之时,士人对新生的大明政权所秉持的复杂的群体心态。
刘基诗文在元亡之前以《覆瓿集》《郁离子》等为代表。钱穆通过对其《覆瓿集》一些经典篇章进行解读后,认为该集“约述伯温当日心事之见于诗者,不外如下之三端:终不忘情于大元之盛运,希其终能重临者一也;举朝昏聩,虽抱忠贞之心,匡济之姿,而屈在草莽,展布何从;时事不可为,中兴无望,而感置身之无地”[12]123。在钱穆看来,在此种心态之下,刘基即便是后来出山辅佐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其内心甚不获已之委曲,亦可想象而得矣”。此种“不获已之委曲”在其后来之《犁眉集》中有直接的反映,“所谓《犁眉集》者,常见为低沉衰飒,回视《覆瓿集》中与石抹宜孙唱和诸篇什飞扬而热烈,奋厉而生动者,远不侔矣”。[12]127言为心声,歌以咏志,诗歌创作历来是诗人精神世界的最真实的记录,故而其史料价值远较其他史料为高。
钱穆结合对宋濂、刘基的诗文集解读,认为在元末明初,此一现象并非孤例个案,实为当时一般儒士之共同问题,亦元明之际时情世态一特殊之点也。对于此种时代风气形成之原因,钱穆从社会政治环境、区域经济条件等因素予以阐发。首先就社会政治环境而言,在钱穆看来,元代的知识分子,在异族统治七八十年淫威之下,“心志不免日狭,意气不免日缩”,其表现就是只知道以文章为道统所寄立身之本,而对于夷夏之防、家国兴亡、民生疲敝等传统儒家之基本情怀均不在考虑之列。[12]103而从区域经济条件而论,钱穆以南北地域立论,认为“明初开国群士,率多南人,彼辈殆以生事优游,诗酒山林,所受感触,或不如北人之深,而遂浑忘夫胡元之非我族类乎?”[12]113
在钱穆看来,元明之际知识分子的此种政治选择与观望态度导致的最严重后果便是朱元璋大肆屠戮士人。在钱穆看来,“明初开国诸臣,人物皎然,能以文采自显者,乃无不系心胡元,情存彼此”,对新政权的这种不合作态度是导致朱元璋屠戮文人的重要原因,“明祖刻意搜罗,实可谓远超于历代之开国矣。然而诸儒不慕荣进,急求退避之心理,乃亦为历代开国所少有”。“然在上者求治之心既切,而在下者求退之意亦不免于过迫,相激相荡,而使心存恬退者不获善终”。而知识分子这种不合作乃至敌对的态度对任何一位统治者而言都是无法接受与容忍的,更何况是朱元璋这种崛起于草莽的枭雄之辈。从长远来看,知识分子的不合作以及后来朱元璋诛杀文人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钱穆以文学作品为载体,从某一历史群体的观念及心态变迁的角度来考察历史问题的研究方法,某种程度上与西方当代新史学中之心态史学及想象史学颇有暗合之处。众所周知,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在法国年鉴学派思潮影响之下,史学研究不断突破旧有的格局,“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认识到人和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历史学合适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一步步拓宽,从传统政治领域拓宽到经济史、社会史以及文化史领域。到了70年代,随着心态史学、想象史学的兴起,人们又突然发现了另外一片崭新的领域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那就是与可感知的现实相对应的精神观念与想象领域。勒高夫曾对心态一词作过概述,他认为:“心态,是指个人或人群无意识的精神内涵和不由自主的心理行为。史学家发现,每个人身上几乎都贮存着一些既成的观念,人的很大一部分思维和行动的习惯便由这些既成的观念所构成。”[13]109“每一个社会,甚至每一个复杂社会的每一个层次,都有其自己的想象领域。”[14]292想象领域的被发现对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社会历史的构成,从来就不仅仅是经过史料考证还原后的现实领域,想象领域无疑是纷繁复杂的历史诸多面相中的重要一环,只有“清理这一梦幻部分与其他历史现实的复杂关系”,才能“深入了解社会”。[15]38但西方学术分科传统造成了历史学家“缺乏这方面的技能和训练”,因而导致历史学家所重建的历史是有重大缺陷的历史。因为“没有想象史的历史学就是一种支离破碎的、空洞的历史学”,所以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在1985年出版的《中世纪的想象》一书中就指出:“已经到了废除那些设置于‘纯’历史、文学和语言史及艺术史之间的学院障碍的时候了。”[16]79虽然在理论上,中国学者并没有提出所谓心态史、想象史的概念并有意识地进行阐发,但在具体实践上,钱穆对明代不同时期士人对宋濂文集的解读与认知之中,探寻出时代观念及心态变迁之历程,某种程度上与所谓心态史与想象史不乏交集之处。当然,如果径直以西方所谓心态史、想象史等概念理论来指称描述钱穆的类似研究,不但与钱穆国史研究本意无涉,更有削足适履之感。但钱穆以文学作品来探讨历史观念变迁与精神面貌毕竟与法国所谓新史学有暗合之处。
四
以现代学术畛域而论,不论是以文学作品内容来考察作者生平及以文体演进为手段考证相关历史知识,还是通过文学作品来考察时代心情,均是一种跨学科研究,它不但要求研究者具备相关的史学功底,而深厚的文学修养更是不可或缺的。钱穆宽博的治学视野以及丰赡的传统文化积淀使其在此一领域的研究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虽然中西学术传统不同,但钱穆秉承的传统学术尚通学之特性与当代西方史学研究跨学科取向不乏交集。法国年鉴学派是当今史学跨学科研究潮流的引领者,从该学派第一代起一直到现在,不同时期代表人物对跨学科研究取向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付诸实践。其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对历史研究的跨学科取向有着精辟的阐释:“历史学家希望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所有的人文学科上。”[17]37布罗代尔虽然一直强调打通人文社会科学诸藩篱,但一直到年鉴学派发展到心态史、想象史之前,历史学与文学之间的交叉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在西方,由于一贯的学术分科取向,导致史学研究者罕有能够兼涉各学科领域的研究者,这也许是西方学者的遗憾。
但在中国传统学术氛围影响下的钱穆的相关著述中,不难发现不论是文学、史学还是所谓哲学均在钱穆的学术视野之内。西方学者不能实现的研究工作,在钱穆这里得到完美的呈现。立足于中国传统学术特质,钱穆向来对西方学术分科的做法颇为不满。在中西比较的基础上,钱穆认为西方学术传统偏重专业,而中国则尚“通学”。“中国人所重,乃在整体中寻求此一物之理,乃使此一物之理贯通于整体”。所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路径,必“先于国家民族文化大体有所认识,有所把捉,始能由源寻委,由本达末。于各种学问有入门,有出路”。所谓史学、文学、艺术相对于传统文化这个本体而言,只能说是“末”。 故而从这个层面上,钱穆认为:“苟非深切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便不易欣赏中国之文学艺术。换言之,亦可谓从欣赏中国文学艺术入门,亦最易得直入中国传统文化之堂奥。”[6]184而钱穆一生治学,虽然关涉领域颇多,如史学、文学、哲学、艺术,但肆力于儒家心性之学则是其学术重心之所在,这也是中国传统学术之一贯特性。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钱穆的文史研究与西方虽然表面相似,但究其实仍有质的不同。
因为在钱穆看来,不论是文学还是史学均是传统文化具体而微的体现,虽表现形式不一,但殊途同归。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反映与折射。钱穆从孔子“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述出发,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之特性予以发挥。根据钱穆的观察,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认为,一切学问,均发源于人类各自具有之内在德性。“德性之大通者存于心,谓之仁。其见于事,谓之道。故德、道与仁乃人类一切学问之共同根本”。[6]153至于言语、政事、文学三者,皆属“艺”的范畴。庄子亦曾提及,“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所谓“艺”者,与庄子所谓的“技”大体类似。中国文学富含艺术人生与道德人生的内涵便是从儒道而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根本宗旨的文以载道、明道传道更是把将传统文学与传统文化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且就传统文学与史学而论,二者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中国文学重在诗,西洋文学重在剧。诗须能吐出心中话,戏剧在表演世上事。中国文学重心,西洋文学重事。此处便见中国文学与历史合一,亦即是人生与文化合一之真骨髓所在”。[6]173所谓心者系指作者于作品中所投放的真实的人生,此一人生实是传统文化之体现,故而一人之人生便成为群体之人生。文学作品何以能够做到人生与文化合一?钱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文学创作,在中国传统理想下,必先能植根于六经,必先泛览诸史百家,必先通贯社会一切人情世故,必先在文化传统中锻炼得自己这一个人成为此文化传统中一合理想之人,然后发而为文,将见无往而不宜。”[6]57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作者一定是为传统文化所化之人方能在作品中做到与时代交融合一之境界。只有达此境界的作品方能全方位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之要义,同时也是其史料价值的最高显现。
钱穆的文史对话的主要用意在于“道”,即在于阐释与传承传统文化之核心要义。而西方所谓文史交叉,所谓想象史、心态史则仍然停留在“技”的层面。当然单就纯学术研究而言,两者之间仍然可以借此对话。而如何借鉴当代法国的想象史研究,结合中国的固有传统去开拓中国的想象史是十分必要的,中西学术对话从钱穆对文学作品及其史料价值的阐发与解读中可以得到启发。
[1] 傅斯年全集:第2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2] 王汎森.钱穆与民国学风[A].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C].北京:三联书店,2005.
[3]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4]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5] 钱穆.中国史学发微[M].北京:三联书店,2009.
[6]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7] 钱穆.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A].中国文学论丛[C].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8] 钱穆.中国文学史概观论[A].中国文学论丛[C].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9] 钱穆.谈诗论[A].中国文学论丛[C].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10] 钱穆.读寒山诗论[A].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四)[C].北京:三联书店,2009.
[11] 钱穆.中国古代散文[A].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C].北京:三联书店,2009.
[12] 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论[A].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C].北京:三联书店,2009.
[13] 刘文立.年鉴运动史学家勒高夫访谈录,法国研究[J].1995,(2).
[14] (法)艾芙琳娜·帕特拉让.想象史学论[A].姚蒙编.新史学[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15] (法)J.勒高夫.新史学[M].姚蒙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16] 转引自徐善伟.想象史研究述,学术研究[J].2002,(7).
[17] 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M].刘北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