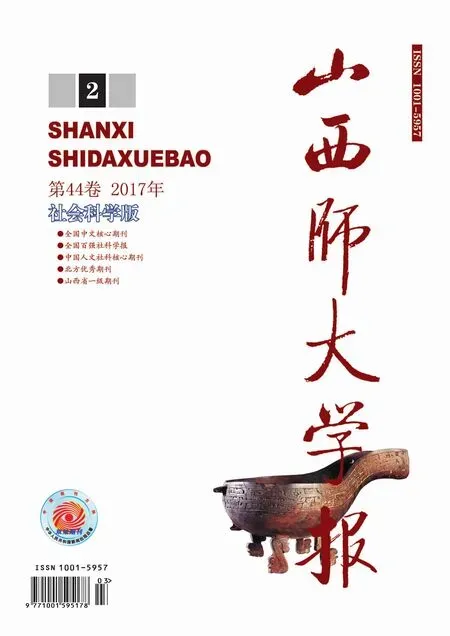民国女性性解放与贞操观的吊诡及司法判解论析
----以1935年北京刘景桂案为中心
张 淑 娟
(聊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民国以后,女性法律地位显著提升,女权的社会思潮更为激进,女性性解放是其议题之一。其直接指向,显然是通过解放女性传统的贞操观,改变中国女性千年来对男性的人身依附状态,提高女性的权利。但这种法律文本上的进步和媒体的宣扬,是否给民国女性带来了切实的益处?从实际生活和司法实践看,对一些女性而言,这种提升非但未能给其提供更多保护,甚至相反,引起了其思想行为上的混乱,以及犯罪之后更重的处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吊诡现象?司法判解又有何启示?目前相关研究已经注意到法律及舆论的理想化与社会现实的差距,但对这种吊诡的发生及其影响却呈现较粗*大多文章描述法律条文或媒体论证,对于其与实际生活的脱离皆是几句话带过,缺少深入分析。见徐静莉:《男女平等原则在近代中国民法中的确立》,《妇女研究论丛》2012年第7期,第61~66页;王新宇:《近代女子财产继承权的解读与反思》,《政法论坛》2011年第6期,第164页;艾晶:《离婚的权利与离婚的难局:民国女性离婚状况的研究》,《新疆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第115页。对舆论媒体的关注有林郁沁:《30年代北平的大众文化与媒体炒作——关于刘景桂情杀案》,载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页。。这里以1935年新女性刘景桂的情杀案为例,从法律条文、舆论风潮与社会普通心理的断裂、隔膜,基层法院与高层法院间司法理念的冲突两个维度进行解析,为法律移植和借鉴提供历史的参照。
一
1935年3月,北京志成中学发生一起枪杀案。犯罪嫌疑人刘景桂,女,察哈尔宣化(今属河北)人,24岁,察哈尔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曾在宣化县女子高级小学任教员,作案时在北平北华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其情夫逯明,系被害人丈夫,全国知名运动员。逯在与原配离婚后,先与被害人滕爽认识,订口头婚约,1933年4月又经人介绍与刘景桂订立纸上婚约,一个月后逯以书信形式与刘景桂解约,未果;11月与被害人结婚,婚后才以600元与刘解除婚约;但不久与刘恢复往来,并发生关系。1935年3月刘买枪杀人。案发后,刘景桂、逯明分别被检察机关以杀人罪、妨害风化罪提起公诉,引起全国舆论报道、评判,轰动一时。
在此三角恋情中,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刘景桂一方面在与逯的交往中表现得积极主动(包括性关系),但另一方面,却不能接受失贞又失婚约的现实而买枪杀人。如此极具冲突性的思想行为,非单纯的个性缺陷所能解释,背后隐含着深层的社会历史因素。
首先,在法律条文上,从《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到《民国民法典》,在婚约订立及解除、婚姻权、财产继承权等方面,女性权利逐步提高,男女平等的法律原则贯穿其间。在婚约订废上,否定了家长、尊长对子女婚嫁的控制、干涉,树立了男女双方当事人的自主决定权,订婚及悔婚均须尊重婚约双方当事人(包括女性)的意愿。[1]61—66对民国女性尤其是刘景桂这样受过系统学校教育的民国新女性而言,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自主选择订婚的对象,也可以决定是否(同意)解除,甚至可以任意同居。婚前性行为,关涉女子贞操,在王朝时代属刑事“无夫奸”,违者将受严厉处罚。至清末律例改革,爆发了一场激烈的礼法大辩论,“无夫奸”被赶出正式的《钦定大清刑律》(《大清新刑律》),而仅在作为附则的《暂行章程》中偏安。[2]民国后,废暂行章程,改《钦定大清刑律》为《暂行新刑律》,其中通奸罪仅对有夫之妇适用,无夫奸放由社会道德调整。此为1928年民国刑法第256条继承。1935年民国新刑法颁布,第239条依男女平等原则,对已婚及其通奸者同等治罪。但刘景桂案案发时适用1928年刑法,对未婚女子与男子发生关系不惩罚,亦无保护。意即,在男女平等的精神下,未婚女子的贞洁归属其自身负责。
显然,作为移植法律,这种西式权利和义务的理念与民国实际存在较大差距。从政治与社会的宏观面来看,其实施的阻力可谓不小。中华民国初成立之时,《临时约法》所谓的国民一律平等,仍不包含男女平权的内容,女子的社会地位及贞操观未有根本改观。相反,在1914、1917年,袁世凯和冯国璋先后颁布、修订了《褒扬条例》,对妇女守节进行褒扬,掀起复辟及尊孔复古的逆流。至1918、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思想界对这种守旧的贞操观进行了激烈批判,但1934年蒋介石又兴起新生活运动,儒家道德被重新塑造和强化。此外,在广袤的旧中国,据民国初期的调查来看[3],社会风俗并未如政治运动般惊天动地,历经三十年树立起来的男女平等及贞操女性自负的精神,仍难为已承继传统文化千年的民国社会认同。因此,一方面,新法律作为国家意志,其司法实践会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给民国知识女性在婚恋问题上独立自主的选择提供了权威的倚靠力量;另一方面,当新法律推行时,必然遭遇本土社会意识的无形抵制,而法律严谨、规范,不但其精神主要依赖司法实践间接展示,而且对当事人的支持也受条文局限。
相较之下,大众媒体不受此拘束,其文字自由激进,给民国女性追求性自由以直接推力。五四以后,恋爱自由、性解放大力倡行。顺着对旧式伦理道德激烈批判的趋势,1920年后许多报刊杂志展开了恋爱中“灵”与“肉”的关系、性解放与贞操观的讨论。主张性欲是恋爱组成部分的“灵肉一致”论战胜柏拉图精神之恋说,获得更多青年学生的支持,相应的新性道德论提出“打破传统贞操观对于恋爱自由的束缚,为此不惜过度强调恋爱的肉欲因素和自由程度”,一些人甚至走向极端的“性交自由”论。[4]20—31这些论点在文化思想界引起极大震荡,对社会风气尤其大城市的知识青年产生了极大影响。社会上不但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渐成风潮,甚至出现了非婚同居现象,在统计数据上女性性犯罪的比例也大为增加。[5]71—72因此,一方面,该股思潮可进一步瓦解压抑女性的传统贞操观。另一方面,他们超前的女性解放论述并非学术研究深厚的自然成果,而更多地出于杂志编辑的职业要求,[6]129—130更遑论针对当时女性面临的社会环境,以及女性因受教育及经济独立上的有限而羸弱的抗争能力而提出建设性的对策。因而,在缺少社会革命的同步支持下,这些理论必然流于浮泛的空谈。更大的负面作用在于,一些知识女性在性解放风暴下盲目放松自我保护的意识,酿成很多悲剧事件。*这在当时的文学作品里均有反映,如鲁迅的《伤逝》、林徽因《九十九度中》等,参见章敏:《民国女性婚姻权与中国现代文学书写》,《东南学术》2013年第6期;倪海燕:《民国法律形态与女性写作》,《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刘景桂即是典型一例。
上述来自法律和舆论的两种力量,有一个共同点,即均站在本位立场上一味按照自己的方式推销新理念,而忽略与本土社会的衔接。如此,受众要选择哪一种,是全力迎新还是持续守旧,抑或是新旧杂糅,完全依赖自身的判断,如此极易引发人们在思想上的困惑及行为方式上的错乱。从刘景桂的表现来看,她有过多次自由恋爱、订婚、解除婚约的经历,并自愿与逯明发生关系,明显接受了自主订废婚约、与男性自由交往的观念。但在承认与逯明发生性关系系出于自愿的同时,在供述作案动机时却表示,失去贞操是她怨恨逯明,并因之产生复仇心理的首要因素,[7]即对失身之后解除婚约无法接受,并据此指责逯欺骗了她。这表明,刘景桂对于权利与义务相随相生这一新法律精神理解有限,因而缺失随之应有的义务意识,即对自己的失贞负责。也就是说,在性关系上,她并没有把自己看作一个与逯明平等独立的个人,无论她自己是否有意,逯明与其发生两性关系又不履行婚约便形同欺骗。这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传统贞操观的思维模式:女子在男子地位之下,性关系由男子主导并负责其后果,女子失贞值得同情。
这一思维模式也符合当时社会的普遍心理。案件发生后,公众对刘景桂表现出广泛的同情。有人给法院写信,怜悯刘景桂受了奸污,丧失终身名节;更有人明确提出刘景桂是因“贞操问题”才杀人泄愤,因此“情节可悯”[8]。虽然刘景桂杀害了逯明的妻子,在古代可算是“奸妇谋害本妻”[9]4,但公众却把一切责任推在男方逯明身上,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双方奸情中女方的主动,把刘景桂杀人泄愤看作因失贞而进行的“复仇”行动。[10]268就连官方批准代表新女性的组织北平妇女会,也谴责逯明“实属此惨案之祸首……社会上之败类,玩弄女子之魔鬼。希望法官能根据人情与法律,将其定罪,而警将来”,对刘景桂并无批评,仅提醒女性打破旧的贞操观念。[11]359这种把女子失贞归责于男子的说法,与普通民众的看法并无本质区别,凸显出旧式贞操观在当时社会的强大影响力。
刘景桂这种只知权利不知义务,以新思潮倡导的男女交往标准行事,却在责任意识上停留在旧时代(女性失贞应由男性负责)的冲突性思维模式,导致其在思想言行上失序,在民国女性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二
民国女性贞操观与性解放的吊诡,是中西方两种文化冲突的反映,也是近代中国向现代化过渡早期阶段的一个正常现象,但当其酿成案件后,司法判解的过程和结果将对其走向产生重要的影响。从理论上讲,作为新法律的推行机关,各级法庭应遵从新法律的精神(即男女平等、恋爱自由、贞操责任女性自负等项原则)审理判结,但刘景桂案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到北平地方法院、河北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最高法院三级三审,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认定和审断标准。本土传统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它不仅表现在普通社会成员的言行上,而且隐藏在警检法机关人员的思想中。在刘景桂案中,突出表现在对关系人逯明的公诉及对犯罪嫌疑人刘景桂的审判上。
如前所述,关系人逯明在该案中的行为,社会舆论的各层虽对之大力挞伐,仅停留在妨害风化的道德范畴内。但自侦查阶段开始,警察、检察官均受传统道德观的影响而把逯明从道德上的妨害风化推到了法律上的妨害风化罪。
1935年3月30日,北平地方法院检察处对逯明提起公诉,指其犯妨害风化罪中以诈术使妇女误信有夫妻关系而听从其奸淫条款,其理由谓:一,逯明承认与滕爽结合并与刘景桂解除婚约后,与刘景桂通信并赠与相片及物品;二,在刘景桂衣箱内存有逯相片及其所赠物品;三,查北京旅馆底簿上有李纪文(逯明化名)带眷属(刘景桂)入住的记载,并已经旅馆茶役指认。[6]然而细加分析,这些不过是基本事实,关于“诈”在哪里,即这些事实与犯罪结果之间,并没有建立直接而必然的证据链条。再看检察官的法条解释,认为其所依据的法条中所谓“妇女”应包括已结婚之妇人及未结婚之女子二者,又解释“夫妻关系”指男女经过性交,放弃自由的意思,“误认为有夫妻关系”指本无夫妻关系而误认为有者而言。
查看警察署及北平地方法院检察处的询问笔录[6],刘景桂关于自己主动接近逯明以复仇的内容清晰可见,公诉书却丝毫未提。公诉书明确以逯明以诈术欺骗刘景桂并对其行奸,作为刘景桂杀人的动机来源。这说明,在检察官的认识中,也存在这样的推理链条:逯明欺骗刘景桂——刘景桂被奸——刘景桂得知逯明结婚后杀人,其中亦隐含着对刘景桂失贞行凶的同情。
针对检察机关的指控,逯明的律师辩护:首先,逯明施行“诈术”不成立。双方发生关系可分两个阶段,在双方婚约解除之前,逯明对刘景桂的承诺(婚姻)是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而婚约解除之后,刘逯来往信件证明,刘为主动。这种主动一直维持到最后一次奸淫,因此应定为合奸(原文如此),而在现行刑法中合奸二十岁以上女子并不定罪。其次,刘景桂把其与逯之关系误认为“夫妻关系”不成立。夫妻关系本是指结婚后的男女关系,当然不包括订婚后的男女关系。刘景桂作为成年人和受过健全教育的女子,对此不可能没有认知。在婚约解除后,刘曾登报詈骂逯明,可见在其内心已明确双方婚约解除的事实,更不可能误认为夫妻关系了。[6]而且,1935年实施的新刑法把其中的“夫妻关系”修改为“配偶”,更加明确这所谓“妇女”乃指已婚女子。至于刘景桂,作为未婚女子,在主动意愿下与人发生关系,在清代可以治罪(即使是已经订婚,律例也禁止男女通奸)[12]129,而在民国,既不受法律惩罚,也不受法律保护。总之,刘景桂既不能积极证明逯明有强暴胁迫及诈术或其他不正当的方法,即不能依妨害风化罪论处。
对比公诉书与辩护意见,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检察官抱有传统的情感偏向,因此扭曲了对法条的理解。一审法院采纳了辩护律师的意见,认为被告奸淫刘景桂“属实”,但“妨害风化罪以误信有夫妻关系为构成要件,其夫妻关系系指已结婚之夫妻关系而言”,此点司法院已经做过解释,而“刘景桂系未嫁之女,其与逯明所订婚约又已解除,无所谓夫妻关系”,且据刘景桂情书——“徘徊在爱的歧途上的我,一颗收不回的心无法处置奈何”,可见其并无“受骗误信”。故此宣判逯明无罪。
确认逯明是否犯妨害风化罪和刘景桂是否值得“悯恕”是一个二而一的关系,其实质指向是司法该怎样面对传统的贞操观?检察机关指控逯明犯罪,即认定刘景桂是受害者,其失贞杀人值得同情。正是循着这一链条,刘景桂的辩护律师请求法庭给予“悯恕”,其辩护书描述刘景桂“既被夺爱,又失童贞……杀人之动机实由于逯明之骗奸”[13]。1928年的《中华民国刑法》第77条规定,“犯罪之情状可悯恕者,得酌减本刑”。但“情状可悯恕”的范围和性质,都没有具体的规范,而有待具体的法官认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新法典的一个条文,“悯恕”的内容不能漫无标准,且不应明显与新法典的精神背离。在实际的审判中,法官还应在可以“悯恕”的犯罪情状与量刑依据之间做出法律上的联结。
在当时媒体及社会舆论对刘景桂几乎一边倒的同情下,一审法庭对刘景桂做出了“酌减本刑二分之一”即十二年徒刑的判决*林郁沁认为这十二年徒刑的轻判,是因为刘景桂的律师对“自首”情节的辩护在法庭上奏效(见林郁沁:《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页)。事实上,档案显示,其“自首”情节始终没有被法院认定,在一审判决中的减刑处理,乃是根据“情可悯恕”做出的。,理由是“情状可悯”。其具体的描述为:“查该被告之谋杀滕爽由于滕爽与逯明结婚,致将该被告与逯明之婚约解除,其情不无可悯。”[14]说明极为简单,未使用任何法律术语来论证“情状可悯”在刘景桂杀人案中适用理由和标准,似有欲言又止之态。因为婚约的解除,在古时亦有之,即受之于第三者搅扰的亦不会少见,何能导致杀人的严重后果,并认为杀人者情状可悯?正如近代法学家燕树棠所言,这一在旧法律上可认作“谋害‘本妻’的犯罪,奸妇即刘景桂有什么可以怜悯之处呢?”[8]故此,这里有一个判决书中未言却暗含的重要情节——刘景桂的失贞,只有对刘景桂的生活能造成破坏性影响的贞操问题,才能让“情状可悯”的论断合乎逻辑。但是如果明确提出贞操问题符合“情状可悯”的要求,等于承认在通奸行为中责任归属男方,女方始终被同情的旧贞操观念,而这与新法律中尊重个体自由的精神相悖,故而法官在判决书中对刘景桂“自首不成立”长篇大论,而到关键性的直接影响量刑的“悯恕”环节却一笔带过。
一审判决以含混不清的方式支持了舆论对刘景桂的同情,变相认可了贞操观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力。但矛盾是显而易见的:法庭认定逯明没有使用诈术,二人性关系乃出于双方自愿,逯明妨害风化罪不成立。但逯明无罪,即等于认为刘景桂应对自己的失贞负责,如何同时又以婚约的解除给刘景桂造成的伤害(主要是失贞)予以“悯恕”?
一审判决后,刘景桂和检察机关均上诉。二审对刘景桂则撤销原判,改判无期徒刑。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谓,虽然逯明在与刘景桂、滕爽的三角关系中存在过错,但在解除婚约后,刘景桂“即应洁身自爱行己有耻以作终身之计,乃复与逯明恋奸不已”,却因逯解除婚约产生怨恨,终致杀人,无悯恕可言。[15]这传达出两个信息:第一,所谓“应洁身自爱”与“无悯恕可言”者,二审法院解读一审法庭的“悯恕”正是针对刘景桂的“失贞”;第二,刘景桂应对自己的失贞负责,法律不予宽容。二审判决后,刘景桂再上诉。三审即最高法院的终审驳回上诉,维持二审判决。理由书以“上诉人年非幼稚,并属智识分子,既与逯明解除婚约,乃复与逯明恋奸不已”[14]的描述,把刘景桂定义为新法律下的“新女性”,明确拒绝了传统贞操观的影响。
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均立场鲜明地用新法律的标准衡量刘景桂案及嫌疑人,把刘景桂看作一个与男子人格平等的人,在法律上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并对其后果负完全之责。贞操非但不再是国家保护的对象,即作为“悯恕”的情节亦不可容。这本符合新法律的精神,但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是,民国时期女子失贞对其生活的影响仍十分重大,这从刘景桂本人的陈述及案件发生后社会舆论的激荡可见一斑。然而司法判决对嫌疑人面临的实际困境置之不理,与真实生活隔膜如在两个社会。如此,民国女性在无能力按新法律下之标准行动的前提下,亦无力摆脱旧传统风俗的束缚,并没有也不利于真正提高其社会地位,且因其部分接受了新思想而受到了更严厉(较之王朝时代)的惩罚。
结语
“权利的行使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具有权利能力,二是具有行为能力。权利能力是法律赋予主体的一种法律资格,具有合法性,就自然人而言,是人人生而具有的,始于出生,止于死亡;行为能力则是行为人真实行使权利的行为条件,也称‘法律行为能力’。”而所谓“行为能力”,是指“该人是否具有足够的判断能力来决定自己与他人间的私法关系,并进而对此负责”[16]164。可以明确的是,民国时期的女性已经具有法律赋予的权利能力,但从经济上、教育水平上、心理独立性上均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行为能力”。①刘景桂犯罪的深层根源即是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不一致的典型表现。
刘景桂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不同步,是近代法律移植在文本上的高歌猛进、大众媒体的盲目引导与社会法律文化变迁缓慢相矛盾造成的一种个体反应。即其没有接受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而表现出行为上的性解放与思想上维持传统贞操观的吊诡。而立法者们对此预期不够及法庭拒绝予以矜悯,则使由此吊诡引发的犯罪受到了相对法律变革前更重的处刑。因此,从根源上言,这种吊诡虽然在客观上是移植法律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但立法者们及司法官们也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刘景桂案的司法判解过程及其结果表明,这种与立法预期正相反的司法实践结果,既超出立法者们的预料,也因其不能给个体提供实际帮助、缺乏与社会的有效衔接而不利于过渡期新法律文化的成长。为此,民国有法官曾做出调和两者的努力,尤其在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的特定领域。
比如对于女子在财产继承与宗祧继承中的权利处置,民国最高法院的精英们曾坚持传统的宗祧决定财产继承的规则,甚至在贯彻男女平等的《民国民法典》颁布之后,仍然有部分法官坚持传统宗祧财产合一继承的必要性。[17]直至今日,女性在家庭财产继承中的角色仍然带有深深的传统观念烙印,而女子贞操观与性解放的吊诡同样困扰着现代女性。故此,面对传统的强大惯性,要降低法律移植过程中吊诡现象的影响,应在司法实践中有意识地留存一定的空间,以调节移植法律与本土传统之间的脱节。而民国法律留给法官一定自由度的“悯恕”条文恰好为一个合适的选择。其更深远的意义,正如学者李启成提倡的:民国法官们在祭田案件中力图沟通外来规则与固有习惯的思路应为当代民事司法继承。[18]笔者以为,不独民事司法,刑事司法亦然。
① 这方面的探讨多集中在某一个角度,缺少综合分析,参见艾晶:《民国初年女性的教育问题与女性性犯罪探析》,《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张洪阳、艾晶:《民国初年女性被告人的经济和职业状况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余华林:《现代性爱观念与民国时期的非婚同居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20~31页,等。
[1] 徐静莉.男女平等原则在近代中国民法中的确立[J].妇女研究论丛,2012,(7).
[2] 李欣荣.清末关于“无夫奸”的思想论争[J].中华文史论丛,2011,(3).
[3] 胡旭晟,夏新华,等点校.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4] 余华林.现代性爱观念与民国时期的非婚同居问题[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9,(1).
[5] 艾晶.罪与罚:民国时期女性性犯罪初探(1914—1936)[J].福建论坛,2006,(9).
[6] 邱雪松.“新性道德论争”始末及影响[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5).
[7] 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诉讼档案[Z]. J065-004-00197.
[8] 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诉讼档案[Z]. J065-004-00206.
[9] 燕树棠.北平滕爽情杀案与社会问题[J].清华周刊,1935,(4).
[10] 林郁沁.30年代北平的大众文化与媒体炒作——关于刘景桂情杀案[A].陈平原、王德威.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1] 刘宁元,等.北京的社团·第二辑(妇女社团专辑)[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
[12] 钱泳宏.防控与失控:清代重惩奸罪与“因奸杀夫[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1).
[13] 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诉讼档案[Z].J065-004-00199.
[14] 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诉讼档案[Z]. J065-004-00198.
[15] 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诉讼档案[Z]. J191-002-04836.
[16] 王新宇.近代女子财产继承权的解读与反思[J].政法论坛,2011,(6).
[17] 尹伟琴.论宗祧继承与财产继承的分离——以民国时期女儿的祭田权利为例[J].法学,2011,(2).
[18] 李启成.法律近代化过程中的外来规则与固有习惯——以祭田案件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