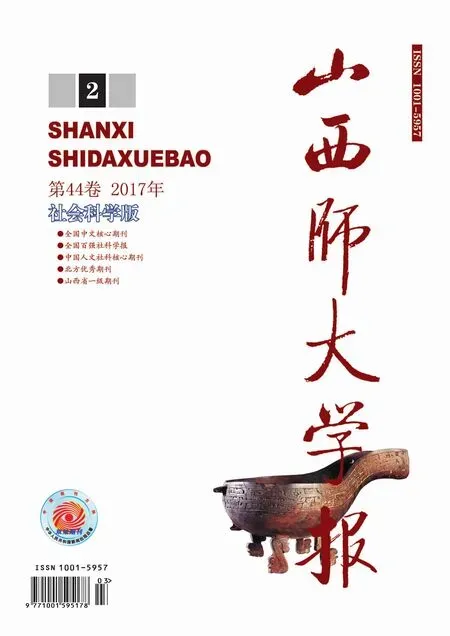底层妇女的身体呈现
----以三部当代女性小说为例
刘 希
(西交利物浦大学 中国研究系,江苏 苏州 215123)
“身体写作”曾是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界的一个焦点话题,这一文学景观的创作主体常常被认为是前后几代的城市、中产女作家,即陈染、林白、卫慧、棉棉、九丹、春树和木子美等,而作品主题也以表达城市、中产、小资的年轻女性的情感和欲望为主。然而在当代文学的创作中,有一部分作品,特别是女作家作品极力呈现了农村的、流动(打工)的底层妇女在城乡急剧变迁的社会语境中的身体经验。比起主流“身体写作”作品中大胆而肯定的身体话语和对城市年轻女性主体意识的表达,呈现底层妇女情欲、性经验的文本并不多,赋予女性主义视角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关注这个主题的几位重要女作家有孙惠芬、盛可以、林白,以及底层女诗人郑小琼和余秀华等。本文要讨论的是当代女作家在世纪之初创作的几部小说,即孙惠芬的《一树槐香》(2005),盛可以的《北妹》(2003)和林白的《妇女闲聊录》(2005)。这三篇小说以当代中国社会中底层妇女的身体经验为描写对象,刻画了处于性别、阶级和城乡等不平等关系中的女性怎样能动地表达自己身体欲望,积极建立自己的性别和性认同,以不同于城市中产女性们的方式追寻身体自由和女性自主。对这些不一样“身体写作”作品已经有一些讨论,但并不充分,本文尝试对这几篇作品中的性别话语做深入讨论,并且考察这些作品的评论中呈现出的文学批评界对底层文学、女性写作以及当代中国社会的不同看法。
谈及“底层”,以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底层经验为写作对象的“底层文学”中,充满了种种受害受辱的农村和进城打工的男男女女。创伤的身体经验常常被塑造为巨大的社会转变带来的后果的象征。“作为农村中最严重的边缘人,当代社会底层中的底层,大量的对留守或流动的农村女性的描写都是被作为转型期‘社会危机’的表现和症候的悲剧故事。”[1]本文所要探讨的话题则是创伤的身体经验如何在当代文学作品中被性别化地予以刻画。所选三篇小说描写了底层妇女们情欲的实现与无法实现,性别抗争及主体性的追寻,并艺术化地传达了作家们性别化的“底层意识”,女权主义及对当代中国社会整体的看法。本文通过考察女作家们面对其笔下写作对象的不同立场,发掘她们对底层妇女身体经验描写中不同的性别和文本政治。对底层妇女身体和情欲的描写是否仍然用以转喻当代中国社会?对底层妇女的叙述是否是女性作家们建构自身主题立场的重要部分?这些作品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界定为女权主义的或后女权主义的?在对底层妇女形象的构建中,性别、阶级、城乡问题是否彼此勾连?这些都是本文要展开探讨的问题。本文认为这些重要的文本形成了一种当代新“问题小说”,丰富和延伸了以中产阶级趣味为主的女性主义写作,同时也赋予底层文学以不同的性别视角。
一、“身体写作”的创作景观和批评史
对“身体写作”这个兴盛于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初的文学现象的考察,必须将它放回改革开放后至新世纪的新启蒙主义继而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语境中。1980年代逐渐兴起的“女性文学”思潮与批判、告别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启蒙主义式的“人性论”“欲望论”密切相关,或者说女性文学本身成为承担去革命、去政治化任务的重要文化阵地。90年代陈染、林白为代表的个体化、私人化写作因其走出集体、公众、政治领域,去肯定个体和自我而具有了对抗宏大叙事的先锋姿态。有欲望的有性身体被作为颠覆革命时代“禁欲的”“无性的”(被认为取消了性别差异的)身体的强劲的话语场。“女性书写成为某种不断地与政治议题分离的‘回归’过程:从‘政治’回到‘自然’,从‘社会’回到‘自我’,从‘集体’回到‘个人’。”[2]
但是,对有性身体的建构却在90年代市场体制中参与到了对本质主义的性别差异的建构中,并且被市场收编和利用。本质化的性别差异使得女性身体被凸显、被客体化,成为差异的最终表征。“身体写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批评语言和接受视野中逐渐被简化、定型化为女性写作、女性性经验和欲望写作。”[3]文学批评界对“身体写作”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它在大众消费文化中将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的客体化、商品化、景观化。钟雪萍曾谈到:“80年代开始的‘向文化转移’,在‘女性特质’领域中追寻 ‘真正的’女人,将‘女人’的含义狭隘化 ,导致了对女性的性别特征‘自然而然’地被所谓女性气质(femininity)和‘性存在’(sexuality) 所界定 ,到了消费主义时代 ,被90年代的文化逻辑推向极致。”[4]宓瑞新也在对“身体写作”做学理总结的《“身体写作”在中国的旅行及反思》一文中提出:“这个本来就存在理论缺陷的西方女性主义身体写作理论也因为与中国女性个体化/身体写作的似是而非的联系,以及被市场、媒体和批评话语任意引申、挪用而显得空洞和浮泛化了。”[5]这些评论都将“身体写作”及其诞生的母体——八九十年代女性文学所产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做了剖析,梳理出这样一条线索:首先以身体作为批判性武器反“异化”,继而在消费文化中身体符号的政治对抗性被市场收编,失却了其最初的批判性和先锋意义。在这一过程中,本质化的“女性特质”的言说、对女性身体的消费构成了改革开放后新的男权话语,因此在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为旗帜的女性文学兴盛之后,新的“身体“和“美女”写作促成了消费资本主义和复活的男性中心主义共谋。
本文正是在这一历史线索和创作景观中考察几篇不一样的“身体写作”是如何刻画底层妇女的身体、欲望和性存在的,从中表达对于城乡变动中的女性命运、女性自我与主体性确立的观念。同时,本文也梳理批评界对这些欲望身体叙事的评论,追溯其中的或褒扬或忧心或矛盾的态度显示出的对当代文学与当代社会关系的整体思考。也即是说,围绕着“底层妇女身体叙事”的创作、批评及背后理论的话语场究竟是怎样的。
二、《一树槐香》与身体自主的困境
当代东北女作家孙惠芬的乡土题材小说里充满了对乡村女性性爱心理和性爱体验的描写,如《歇马山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天窗》和《一树槐香》等。而其中短篇小说《一树槐香》[6]有对农村女性情欲的大胆描写,并从女主角二妹子的视角对其性爱心理有着细微和浪漫化的表现。孙惠芬将二妹子对美好性爱的追寻放置在农村以男性中心的,女性的情感和身体欲求被贬抑的家庭关系和性文化中,对比了二妹子“子宫都在动”[6]52的美好记忆与嫂子“一辈子也没有尝到女人的滋味”[6]55的心酸记忆。作者书写了农村女性的情感和身体欲求被压抑的普遍气氛,对二妹子因曾经美好性爱体验而尊重自己的情感身体需求给予了理解和肯定;同时又从歇马山庄人的视角,描写了这种大胆找寻美好性爱的女性如何在保守压抑的山村被视为异端。
小说在两种叙事视角和语言中展开,一方面是二妹子对美好性爱经历的回忆和新的性爱体验的细致入微的刻画,从二妹子的视角去描写身体的舒展和欢乐,语调温柔、浪漫而感人,如“二妹子渐渐酥松开来,蓬勃开来,使二妹子身体的芳香一汪水似的从骨缝里流出,流遍了山野,如同那些不知名的花开遍山野”[6]72。在二妹子自己看来,“身体只是身体,与嫁人无关,也与道德无关”。[6]85这里的“道德”其实是强迫女性守贞的封建道德。另外一层的叙事视角和语言则是以嫂子和李所长为代表的歇马山庄人眼中的二妹子的故事。在嫂子眼中二妹子小馆只要开一天就是耸在歇马山庄眼里的“脊梁骨”,而在李所长眼中,二妹子就是她哥哥用以交换实际利益的工具,是有着可以随意被占有的身体的妓女。不是恪守男权贞操标准的贞女节妇,就是满足男性欲望的妓女荡妇,两种角色之间,女人自身的情感欲求被完全剥夺和压抑。于是“关于二妹子命运的猜想,关于二妹子当鸡的故事,关于二妹子身体的故事,就如同苍蝇一样,在歇马山庄一带四处飞舞”[6]91,二妹子的故事成为一部身体堕落的肮脏历史。《一树槐香》中两种叙述,女性视角话语和男权话语交替出现,最后以歇马山庄人嘲讽鄙夷的叙述和视角作结:“露着白白的胸脯和白白的大腿,要多妖气有多妖气”[6]91,表明了二妹子寻求身体自由的反叛话语最终不敌男性中心主义话语的倾轧,如同在现实生活中底层妇女表达自我意识的努力不仅难以得到认同,而且往往被误解乃至否定。 《一树槐香》作为一个女权主义文学文本的意义就在于它用两层叙事的交汇和抗争表现男权社会造成的女性身体压抑及其批判。
对于《一树槐香》的主题和意义,论者往往以二妹子这类乡村女性在“封建礼教观念”里的挣扎和困境喻示“乡土世界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用乡村女性性爱心理的镜像折射着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文明进程。”[7]这种对底层妇女命运的解读表现出一种对“现代化”特别是农村现代化的焦虑,却没有对这一过程中不公的性别秩序为何延续作出评论或思考。对于二妹子自身的身体情欲的呈现,有一类评论惯例援引了张京媛主编论文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的文章用以肯定《一树槐香》中的身体叙事,如“美杜莎的笑声”,“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中“身体写作”的概念。同时,有论者也借用新启蒙主义话语肯定对底层妇女的自主意识的表现,如“底层特别是农村妇女,因为与土地有更为密切的关系”,他们那种身体、情感、欲望的潜流,更有可能形成“一种侵蚀甚至是颠覆革命时代乌托邦性别话语的力量”。[8]56因此这类评论基本上是借助之前“身体写作”潮流的积极意义来解读《一树槐香》。
但是对于二妹子不畏污名化,如此大胆而坚定地追寻情欲自主,一些评论在认可以上女性主义批评话语的情况下还是表达了对于所谓“过度的身体自由”的忧心[9],如“身体觉醒了的二妹子最终成了身体的奴隶”,“身体和心终于相连后,却由于出了‘丑事’,感受到了身体里的黑暗,最后真的成了一只‘鸡’”[10]的论述。这种对于女性身体自由的忧心会在对盛可以小说《北妹》的评论中更加清晰地表露出来。
三、《北妹》与底层妇女主体性
盛可以的处女作《北妹》[11]在当代底层妇女命运的记录中具有重要地位。作品还原了打工妹们进入城市的艰辛道路和城市对她们的冷酷无情,呈现了一部父权社会性别和资本主义压迫下底层妇女身体的受难史。打工妹们或成为现代企业工厂里被压榨的廉价劳动力,或进入服务行业里女性做得最多的职业如发廊、私企陪酒、歌厅陪唱、宾馆前台、宠物保姆,以及出卖肉体的性产业。她们在不同行业里随时随地面临着劳动力剥削以及基于阶级、性别、年龄的歧视乃至侮辱。在《北妹》里,女性的身体和对身体的使用必须完全服从男权制度的安排,对女性性魅力的期待与其顺从的要求同时存在,不仅身体生育功能的使用和关闭完全不由女性参与决定,也常常成为被随意榨取的性资源。对钱小红“荡妇”性唤起的期待和对其性魅力恐惧、侮辱的厌女症同时存在。总之,她们成为男性主体建构的必然的次等的“他者”。如果说《一树槐香》主要塑造的是农村封建男权秩序为主,市场秩序中将女性身体商品化为辅的男权文化,那么《北妹》则主要刻画了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里资本的力量、商品经济与男权性别秩序的结合对女性特别是出卖劳动力的打工女性带来的巨大倾轧。
《北妹》正是在彻底揭露城市里商品经济和市场逻辑,性别秩序和性观念的基础上描写底层妇女艰难地追寻女性独立、自决和性自主。盛可以在《北妹》再版后记中说,她塑造的是钱小红强劲的生命力,“对虚妄生活的透察和对自身欲望的尊重”,并在接受《羊城晚报》访谈时说:“一个大胆自我、追求性自由的小姑娘,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偏僻农村,这是大逆不道。但她善良活泼、热情侠义,视性为天然。某种意义上,她其实是一个‘思想的革命家’。”[12]因此在各式各样的男性霸权的威吓中,女主角钱小红仍然正直、自尊自立,尊重女性自由表达身体欲望却不让欲望被任何权力、金钱关系所操控,在性关系中拒绝被动和弱势,嘲弄男权对“贞操”的规定,用自己的身体力量反拨解构了“贱”这个对女性的污名。钱小红巨大的乳房是全书一个重要的意象和象征,它的寓意究竟为何?盛可以曾经在澳大利亚一次作家工作坊的访谈中说:“乳房是女人这个第二性的性别的象征,我给了女主人公这个外在的符号去象征她们迁移入城市过程中的担忧和焦虑。钱小红的巨乳对她来说是个麻烦,同时也带来了好处。她喜欢她的身体,却从来没有拿去做任何交易。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一个反叛。”[13]因此,钱小红们在深圳这座资本主义城市中即使遭遇阶级、性别的巨大不平等和伤害也没有屈从,拒绝将自己的身体商品化和客体化,在污名化女性性愉悦的男权机制中没有放弃自己的性权利和身体欲望。《北妹》就是这样塑造了底层妇女的主体性。对比《一树槐香》中二妹子的那句“身体只是身体,与嫁人无关,也与道德无关”,《北妹》所描绘的其实是在这样一个“不道德”的社会中一个底层打工妹如何抗拒各种“男权道德”的规约而保持了“自己的道德”。底层妇女的身体是诸种不平等关系施加威力的地方,在小说中却也成为个体反抗的最终战场。
对于《北妹》这部描写底层妇女身体经验的作品,很多评论将其跟之前以城市中产女性为创作主体的身体写作予以对比,肯定其记录底层妇女经验的现实主义价值。[14]但是,在对《北妹》的评论中影响力很大的一篇是马策的《身体批判的时代——评盛可以长篇小说〈北妹〉》。文章认为,“《北妹》事涉身体的自由秩序,但更为重要的是揭示出身体自由的危机。”马策回溯了身体写作的历史,认为盛可以这篇作品的具体价值在于为私小说和“美女作家”时期划上了句号,“中国女性写作身体批判的时代来临了”。钱小红“咬着牙,低着头,拖着两袋泥沙一样的乳房,爬出了脚的包围,爬下了天桥,爬进了拥挤的街道”[11]278,这个象征被马策解读为身体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和危相,并得出结论说:“盛可以将身体的批判,落脚于对作为一种制度的自由秩序的反思,在此意义上,《北妹》堪称女性文本的高峰之作,并且大大的超越了中国女性写作的美学边界。”[15]同样,有论者也仅仅围绕《北妹》结尾处钱小红“被无限膨大的乳房压垮”的描写去讨论以身体自由和欲望去反抗现实性别秩序怎样陷入新的焦虑,认为“建立在欲望享乐上的反抗意识很难说是独立的女性意识,它形成了某种虚妄的女性主体,不仅难以对男权文化造成真实、有力的冲击,在现实层面上,则表现为女性更严重地陷入到男性文化的控制之下”,“狭隘地将情欲的率性表达等同于身体自由的实现。钱小红放逐‘爱’与男性一起性狂欢,完全放弃对灵魂、精神的思考和寻找,将女性‘性自由’高举成现代女性意识的标志。……这种性自由一旦与社会政治、思想精神的追求无涉,就会成为女性重新‘异化’的原因”。[16]
围绕“身体自由危机”的这两篇评论确实涉及到了《北妹》文本内外的一些问题,如有论者认为,“钱小红是在性的焦虑中产生了乳房的变异。女性的性问题并没有随着女性身体自主权的获得而迎刃而解,这是盛可以、乔叶、孙惠芬均意识到的并且在各自的作品中试图展现的主题。”[17]但是这些评论将文本中呈现出的底层妇女的现实困境主要归结于女性身体自由内在的问题,而非外在的社会转型和市场体制,这就遮蔽了很多并非“自由放任过度”或者“欲望享乐”能解释的问题,并且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限制,对“与思想精神无涉的性自由”的指责,有对于女性身体再道德化的危险。如前面所讨论的,钱小红绝非享受纯粹的“性狂欢”,而是以身体为战场争取女性的性自主和进行性别抗争,即使异常艰难并且常常被污名化,她也没有放弃,因为这是她最后唯一可以自主选择的抗争方式。如同《中国女工》中打工妹的梦魇和呓语成为抗争的“次文体”[18],北妹钱小红的自由情欲表达则成为身体对于来自性别和资本双重压迫而不屈从的表达方式。
这些忧心的评论所触及的问题不在于自由“过度”,而是自由远不足以对抗当下传统封建男权和资本主义市场的新男权(将女性身体客体化商品化进行交易)结合起来的残酷现实,正当的自由无法实现。或者说,应该探讨的是如果当代“女性主体性”的构建仍然基于一种性别本质主义的、以性存在为主要向度的“主体性”是否有问题,如宋少鹏所说,对个体主体性的关注“悬置了对当下资本制度对于妇女压迫的质问,……因为资本制度和市场社会被看成了妇女主体性和自由的制度性保障”。[19]对于《北妹》这部小说来说,以一个追寻自由的女性的艰辛之路揭露现实资本制度和性别秩序的残酷,正是作品女权主义社会批判的重要议题。目前底层妇女所拥有的自由绝非过多,反而因被污名化而远远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以马策为代表的呼吁对“自由限定”和对“身体批判”的评论,触碰到了个体仅仅靠身体自主权远不足以对抗一个男权社会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社会的重要问题,但却从这种对身体抗争局限性的思考和对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现实的焦虑不恰当地推导出了“女性性自由会导致危机/异化”这样的观点。钱小红为“身体自由所付出的代价”的问题绝不在于她追寻身体自主和自由,而在于一方面贬斥女性性自主,另一方面将“身体”商品化资本化的男权社会。这些忧心于“自由”的评论以其模糊不明的批判“自由”的说辞有再道德化和对身体再压抑的危险,并且无法正视《北妹》以打工妹的艰难抗争史,特别是在“性”这个最为保守的领域展开的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力量。
四、《妇女闲聊录》:女性主义本土言说?
相比《一树槐香》和《北妹》,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及姊妹篇《万物花开》受到了文学界极大的关注和肯定。作为曾经的“个体化写作”和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林白在写作对象、主题和手法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因而这两篇代表作品也被赋以了“个体化写作”在新世纪寻求突围,以及女性主义文学发展新方向的意义。《妇女闲聊录》[20](以下简称《妇》)以湖北王榨农村一种“无政府主义式”的群体生活样态和民风民俗为描写对象,以农村妇女木珍这个底层妇女的回溯和记忆为叙事视角,语言采纳了“粗糙、拖沓、重复、单调,同时也生动朴素,眉飞色舞”[20]的民间口语。林白自己非常高调地将它标榜为打开了她“和世界之间的通道”,是“最朴素、最具现实感、最口语、与人世的痛痒最有关联,并且也最有趣味的一部作品,它有着另一种文学伦理和另一种小说观”[21]。众多评论家纷纷认可和赞赏林白“低于大地”、“跟他者平等”的姿态。[22]如某文学奖授奖词赞颂《妇》这部作品为:“有意以闲聊和回述的方式,让小说人物直接说话,把面对辽阔大地上的种种生命情状作为新的叙事伦理,把耐心倾听、敬畏生活作为基本的写作精神,从而使中国最为普通的乡村生活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23]一些评论家通过对《妇》中农民的“主体意识”和“心灵世界”的肯定而反思知识分子的自满与面对农民或隔阂冷漠或高高在上的启蒙、优越姿态,赞赏林白“能在这个世界面前保持一种低姿态,尽量过滤掉自己的主观性”[24]。
《妇女闲聊录》中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湖北王榨乡村开放、自由的两性关系,以及叙述者传达出的对这种性自由特别是多元关系的女主角们的理解和宽容。如木珍对王榨的各种奔放的村妇如双红等甚至是自己丈夫相好的冬梅的理解,莲儿和香桂的超越“情敌”的关系,木匠妈妈对小儿媳妇说的“你闲着也是闲着,他大哥也不用给别人钱”[20]的另类态度。叙述者欣赏的是冬梅那种“从来不议论别人的风流事,她不像线儿火,自己是歪的,还老议论别人,冬梅不干”[20]的“人生哲学”,与“都说这种事,只要是女的在一起,都说,不管年纪大的年纪小的,都说,只要不是姑娘就行”[20]的宽松的女性空间。这种宽松的气氛与《一树槐香》中保守、压抑的气氛截然相反。王榨的这种另类道德样态成为作者林白从底层生活,所谓“辽阔光明的世界”和“活泼的生命”中寻找到的新的思想资源和写作对象,它可以说继承了其之前“个人化”写作中对女性世界的关注和对个体的自由自主的认可。王榨农村女性在身体和性方面的流动性和自主性比之知识女性的追求目标来说似乎已成为现实,同时,这种自由的状态又是来自不同于私人化写作孤芳自赏的小天地的“民间”和“底层”,因此这部作品就成为评论者对女性主义写作的新的题材、写作手法和发展方向的肯定。
荒林曾提及《妇》因“到更深入的内心世界”“写出人的史意”而“体现了女性主义写作的历史性成长”[25],并认为其价值在于“女性主义对于妇女和弱势群体的赋权,正是话语权的赋予”,成为书写“本土经验”即“中国农村在时代巨大变迁中的生动经验”上为“中国女性主义提供了丰富的诗学资源”[26]。其他几位从女性主义书写转变的视角讨论《妇》的重要评论者包括寿静心、王宇和董丽敏。寿静心看到了《妇》与林白之前的女性写作一样依然是对抗宏大叙事和主流话语,表达对个体自由不懈追求的文本。[27]王宇认为包括《妇》在内的女性写作的乡土转向并非放弃女性主义立场,她认为林白对鸡零狗碎的乡间生活的记录“价值立场含混”,从而“最大限度地祛除了表述 (话语) 中所隐含的权力机制”。董丽敏的讨论更复杂些。她看到了《妇》中表达出来的价值空间的混沌“大多数时候甚至是颠覆和消解已有的女性主义价值观念的”这一点,但认为这种对底层生活的描述更加“真实”,“标识着其女性立场的深化。至少,她开始让有可能蕴蓄着中国本土经验的女性生存状态无拘无束地呈现出来,在此基础上,探索属于中国女性主义的言说方式。”董文的讨论建立在她对“西方意味十足”的中国女性文学话语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她认为《妇》中女性主义的“本土性”在于超越了“原本立足于‘个人言说’的‘现代性话语’前提下的中国女性文学”的那种“自恋乃至自我封闭的倾向”,虽然《妇》的实验包含的这种反思超越意识模糊、未成型,但董相信它可以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本土言说的开始”。[28]
以上几位评论者或者肯定林白一以贯之的“个人化”立场(无论是知识女性私人生活的个人化还是对抗主流宏大叙事的民间立场和姿态的个人化)是女性主义视角的延续,或者赞扬《妇》包含的“本土女性主义”可能性,认为它是对受到西方女性主义影响的、“局限于”个人言说的女性文学的纠偏和“清算”,总体都在肯定《妇》是“女性主义”的。但是问题在于,《妇》作为一部有着“粉碎世界的整体性”的“后现代精神”[29]的作品,其提供的对底层民间世界的批判性和反思性有几何?它究竟在何种程度和意义上可以被界定为是女性主义的呢?
作者赋底层妇女以自我表现的权力,她们的轻松活泼的语言再现了王榨农村在“性”上的自由态度,在性以及谈论性上的自主意识。这样一种题材和写作姿态与女性主义文本反对性的压抑、肯定女性的身体欲求的追求的确是一致的。木珍正是在她大胆自如的言说过程之中确立起她作为一个底层妇女的主体性的。农村女性从自己口中说出农妇们自己生活中种种细枝末节,有着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这种底层妇女能动的自我言说和表达是《妇》的巨大贡献。《妇》中还通过木珍之口表现了农村中诸多性别不平等状况,诸种封建思想的存留以及城市化过程中的性别不平等:冬梅年轻的女儿以及更多年轻女孩被富人包作二奶;王榨的大男子主义男人们家暴严重,福贵“把他老婆打得死过去了”[20],三岁这个人对妻女的辱骂;外出的打工妹们因怀孕影响了人生;学生们特别是女孩子辍学打工;新娘的女伴们遭到严重的性骚扰;种种“女儿沤粪”的可怜状况如生育的性别筛选,小莲的父母对她的虐待等等。可以说,在对于性的相对宽松的气氛之外,女性在转型的乡村社会中的遭遇依然没有享有足够的自主权。这种纪实文学式的对妇女生存现实的揭露也被一些论者认为是“林白见证农村女性的残酷生存和韧性的一部激进作品”,因而具有“女权主义性质”。[30]16在《妇》这部勾画了支离破碎的农村生活世界的,具有“后现代精神”的作品中,作者林白的立场其实并不明晰。可是她在小说的副文本——两篇后记中却清楚卓然地昭示了一种亲近赞颂底层、“敬畏生活”的姿态。如果说在“性”的方面,作者自身的立场隐含于木珍的立场背后其实也是一种对木珍的认同,那么,《妇》中其他对农村中诸多性别不平等状况的呈现,作者声音的隐没则与小说后记中的姿态不相协调。
作者的隐身正是林白在《妇》中追求的目标和新的“伦理观和文艺观”的表现,她刻意取消知识分子的立场和介入,让底层自己说话。如果说林白的个人化写作是尽力抵制和清除国族公共话语和宏大叙事对个人生活再现的影响,那么林白在《妇》上的努力则更是对知识分子精英话语的反思和摒弃,让底层在自然自由的话语空间下呈现他们自己眼中的流动性的生活。但是《妇》还呈现了农村生活中诸种性别歧视和压迫。木珍除了在叙述计生办对她捡到女儿的不支持表达出不满和可惜之外,在叙述其他女性的遭遇时基本上跟谈论王榨的喜闻乐见的偷情一样平静而自然,仿佛这些都属于乡间的各种鸡零狗碎而“见惯不惯”,无法改变。仔细通读小说,木珍对王榨的诸种悲惨女性状况的描述有着一种自然发生、无能为力的语气,并不能完全被林白在后记中所描述的那种对“辽阔大地上的种种生命情状”的“眉飞色舞”[20]的语调所概括。《妇》里“乡村”的形象,其实和木珍自我言说中的“底层立场”一样驳杂多面,其中甚至包含着对女性悲惨遭遇和对城乡共存的男权思想和行为自然而平静的接受。在这些时候,作者的沉默不语则与其赞颂乡土底层生命活力的意图形成了紧张不和谐的对照。有评论者注意到:当林白试图呈示一个原生态的“真实乡村”时,她看见的只能是杂乱无序、缺乏声色的乡村,……这样的乡村明显缺乏诗意,它只能驻留在素材层面,无法为林白的写作带来精神价值和审美趣味。然而,发掘盎然多姿的民间生命力,营构一个别有意味的美学地图,又是林白念念以求的乡村叙事目标。这就导致了无法调和写实与写意之间冲突的写作难题,最终的结果是林白的乡村写作遭到极大破坏。[31]如果说“写意”背后有着作者肯定女性身体自主的女性主义立场和赞颂底层的意图,“写实”对底层生活中诸多社会不平等和性别不公正的现象的揭露其实已然颠覆了“底层”的可亲近感,《妇》中“狂欢化”的语言所呈现的既有女性自由,也有非理想化的底层妇女的艰难生存状况。“《妇女闲聊录》所呈现的价值空间显然是以前的林白难以想象的,她原本已经很明晰的女性书写者的形象也在这样的混沌中受到了挑战,变得难以归类。”[27]这种“难以归类”是林白刻意告别自己曾经的女性主义作家身份的结果,这种“混沌的价值空间”也使得对《妇》在多大意义上可以被界定为是女性/权主义的文本的问题得到继续讨论的可能。对知识分子的女性主义所沾染的中产、精英气息的反思的结果是林白试图退到对“民间世界观/意识形态”的一种不经介入(unmediated)的再现之中,但作者在《妇》的副文本(后记)中所表达的立场却是赞颂和敬畏。《妇》排除了由作者经由文本政治的介入可以达成的批判或反思(或者说把这种价值判断的工作全盘转交给读者),直接让底层自我表达,但这种自我表达所再现出的底层世界其实有很多驳杂甚至是自相矛盾的面向,并非一个可供“敬畏”和膜拜的范型。如果说《妇》“最大限度地祛除了表述(话语) 中所隐含的权力机制”,那么对于农村妇女生活中存留的压抑性结构和文化中的“权力机制”,小说叙事则呈现出某种暧昧的“低姿态”。可以说,《妇》在成为“与人世的痛痒最有关联”的文本上非常成功,但作者通过完全隐身和退场而反拨女性主义精英姿态的做法是否可以使得《妇》成为“女性主义写作的历史性成长”、“女性立场的深化”、“本土女性主义言说开端”的标志文本则值得继续商榷。
五、结语
孙惠芬的《一树槐香》和盛可以的《北妹》艺术化地表现了底层妇女们的性别抗争及主体性的追寻,从思想内涵和文本形式上都是女权主义文本。它们通过对底层妇女身体经验的困境和主体意识的刻画,揭露了转型社会中底层妇女面临的危机是由新旧两种不平等社会性别秩序,更是将女性劳动和身体商品化的资本制度和市场社会造成的。从商品化浪潮刚刚开始的农村到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中的南方沿海城市,农村和打工底层妇女都遭遇了父权制度文化的威压以及市场和资本的侵袭。两位女主人公——二妹子和钱小红,都不惧对女性自由的不容忍和污名化而追寻身体自主权,在艰难地争取经济自由之时,将被性别、阶级和城乡不平等重重压迫的身体作为最后的战场,以女性情欲的不让步成为底层妇女最后的坚守。这种关于底层妇女创伤经历的“身体写作”成为考察当下城乡社会中诸多互相交叉的不平等问题的切入点。两位女作家性别化的“底层意识”和女权主义以相应的文本和叙事策略很好地表达了出来。而这两篇作品评论中表露出的对这种“身体自由”的忧心和焦虑,则反映出背后隐藏的一个问题,即面对强大的资本和男权机制,什么样的主体性可以或者仅仅是个体本身可否具有真正有力的对抗性和政治性。
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对于王榨农村妇女在性以及谈论性上的自主权的书写和肯定延续了作者对个体特别是女性自由自主的女性主义立场,通过鼓励底层妇女的自我言说塑造了底层妇女的主体性。并且,对底层生活的重视和相应地隐藏作者态度的语录记载式写作方式出自于林白对醉心于个人言说的女性文学和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反拨。对底层世界特别是女性的叙述因此成为林白构建其“后身体写作时代”作家立场的重要部分。但是作者通过叙述者的隐身和退场来对抗女性主义中产和精英的姿态,这个认同底层的先验立场会否削弱在性别议题上的批判性? 这使得这个“后女性主义”文本值得继续讨论和辨析。
但是,以《一树槐香》《北妹》和《妇女闲聊录》为代表的当代女作家的文本形成了一种当代的新的“问题小说”,丰富和延伸了以中产阶级趣味为主的女性主义写作,同时也赋予底层文学以不同的性别视角。评论界对三个作品都曾赋予他们之前的女性“身体写作”对抗主流话语的先锋意义,也看到了其书写被压迫的底层妇女身体的现实主义价值,但对这种开放自由的身体的反叛意义则意见不一。如果说90年代的“身体写作”既有其先锋性、批判性,也有着误区,可能被市场和消费主义所收编,那么新世纪里这些“另类身体写作”以底层妇女的受创却不屈的身体揭示了当下社会里的性别、阶级、城乡等不平等,呈现了对自由的抗争和追寻,也促使我们去追问面对父权和资本的合力侵袭,何为真正具有反抗性的妇女“主体性”的问题。
[1] 刘希.现代性话语中的保姆故事——小说《芝麻》分析[J].妇女研究论丛,2013,(4).
[2] 贺桂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J].文艺研究,2003,(6).
[3] 宓瑞新.身体写作女性化探讨[J].妇女研究论丛,2006,(S2).
[4] 钟雪萍,冯苊芃.谁是女权主义者——由《 上海宝贝》 和 “身体写作”引发的对中国女权主义矛盾立场的思考 (上)[J].励耘学刊(文学卷),2007,(2).
[5] 宓瑞新.“身体写作”在中国的旅行及反思[J].妇女研究论丛,2010,(4).
[6] 孙惠芬.一树槐香[A].民工[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7] 郑晓明.农村女性性爱心理的压抑与彰显——孙惠芬《天窗》与《一树槐香》的比较阅读[J].名作欣赏,2014,(14).
[8] 马春花.被缚与反抗: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论[M].济南:齐鲁书社,2008.
[9] 如苏日娜.试论孙惠芬笔下的乡村女性形象[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1.
[10] 韩春燕.墨色槐香:女性心灵与身体的告白[J].电影文学,2007,(10).
[11] 盛可以.北妹[M].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
[12] 盛可以访谈录:盛可以绝不许对自己说:还有很多个明天.[N].羊城晚报(人文周刊).2013-02-24(B3).
[13] The Writer's Workshop,Freya Dumas:“Interview with Sheng Keyi”,2012年6月6日. http://lipmag.com/arts/books-arts/lit-lit-qa-sheng-keyi/comment-page-1/#comment-17595.
[14] 周婷.新世纪女性写作的异质性——盛可以小说创作[J].小说评论,2013(2);孟繁华.《北妹》底层女性生死书[N].北京青年周刊,2004 年6 月15 日;童献纲.关于另一类身体写作[J].长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15] 马策.身体批判的时代——评盛可以长篇小说,转载自盛可以新浪博客[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61481f0100ke9d.html.
[16] 马玲丽.身体自由:欲望与反抗的双重沉沦——以盛可以的《北妹》为例反观当下底层女性文学写作[J].名作欣赏,2010,(15).
[17] 童献纲.关于另一类身体写作[J].长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18] 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M].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
[19] 严海蓉,林春,何高潮,等.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性[J].开放时代,2012,(11).
[20] 林白.妇女闲聊录[J].长篇小说选刊,2005,(1).
[21] 林白.低于大地——关于《妇女闲聊录》[J].当代作家评论,2005,(1).
[22] 陈思和.“后”革命时期的精神漫游——略谈林白的两部长篇新作[J].西部,2007,(10);张新颖.如果文学不是“上升”的艺术,而是“下降”的艺术——谈《妇女闲聊录》[J].当代作家评论,2004;贺绍俊.叙述革命中的民间世界观[J].长篇小说选刊,2005,(1);施战军.让他者的声息切近我们的心灵生活——林白《妇女闲聊录》与今日文学的一种路向[J].当代作家评论,2005,(1).
[23] 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专辑[J].当代作家评论,2005,(3).
[24] 张新颖,刘志荣.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和打开文学的生活视野——从《妇女闲聊录》反省“文学性”[J].当代作家评论,2005,(1).
[25] 荒林.《妇女闲聊录》的史意[J].文学自由谈,2005,(6).
[26] 荒林.重构自我与历史: 1995 年以后中国女性主义写作的诗学贡献——论《无字》《 长恨歌》《 妇女闲聊录》[J].文艺研究,2006,(5).
[27] 寿静心.林白:从《一个人的战争》到《妇女闲聊录》[J].河南社会科学,2007,(3).
[28] 董丽敏.个人言说、底层经验与女性叙事——以林白为个案[J].社会科学,2006,(5).
[29] 贺绍俊.叙述革命中的民间世界观[J].长篇小说选刊,2005,(1).
[30] Schaffer, Kay, Xianlin Song. Women Writer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Routledge, 2013.
[31] 谢刚.分裂的乡村叙事及无效的成长忆述——林白近年写作的衰退兼及女性主义写作之困[J].文艺争鸣,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