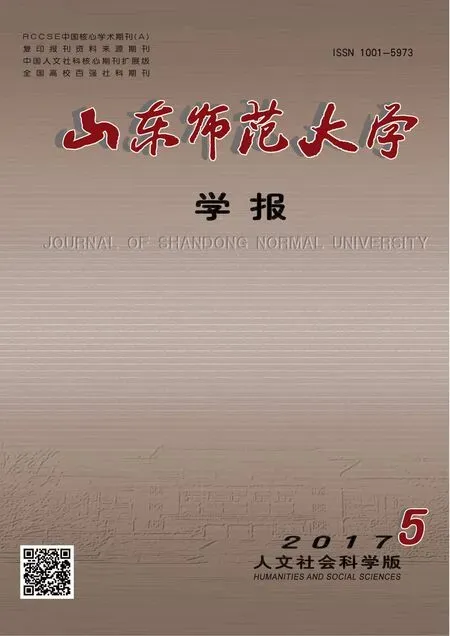优良品格的形成及德育镜鉴
——《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视角*①
李国祥 于洪波
(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山东 济南,250014 )
优良品格的形成及德育镜鉴
——《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视角*①
李国祥 于洪波
(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山东 济南,250014 )
亚里斯多德认为,优良品格的形成是个体与父母、社会及环境互动与强化进而形成习惯的过程。在习惯习得之初,尚需外在奖惩手段的辅佐;随着练习的不断强化,正向的习惯逐渐成为自然,最终成为人类浑然不觉的第二天性。品格习得的过程,不仅关乎“你做什么”,而且还关乎“你喜欢做什么”。品格的习得与完善,既需要实践智慧的不断试误与验证,又需要理性反思的持续萃取与升华。抑或说,需以“中庸”为尺度,合理地衡量人类天性中的欲望、欲求和激情,使之与“何为美德”的理性反思及判断达到均衡一致,最终获致理性与欲望及情感的和谐统一。
尼各马可伦理学;品格形成;实践智慧
“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和“品格形成”(character development),一直以来分别是中西方伦理学界长盛不衰的焦点论题。在伦理学或道德哲学中,“道德”通常是“品格”的上位概念;抑或说,“道德”囊括“品格”。中国伦理学界大多探究“道德”,而较少涉猎“品格”;而西方伦理学界则大多探究“品格”,较少涉猎“道德”。究其缘由,概因东方文化“长于综合”而西方文化“长于分析”所致。如果说,“道德”属于形上之道的宏观大词;那么“品格”则可归于形下之器的微观微言。一般而言,“道德大词”长于立志高远的“治国平天下”,而失于伦常日用的“格物致知”;而“品格微言”则长于亲躬力行的“实践智慧”,却失于明道救世的“家国情怀”。惟其二者交相借鉴融合,方可纠偏制衡乃至于中和之道。于此而言,西方伦理学的开山之作——亚里斯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可谓对二者兼容并蓄且融合贯通,对肉与灵、义与利、情与理、礼与权等诸多伦理学的重大命题予以了系统阐述。聚焦于“品格发展”的美德伦理学的复兴,意味着伦理学的关注重点从规范伦理学所强调的问题“人应该做什么”,重新转向美德伦理学所追求的“人应该成为什么”。*潘雷琼、黄甫全:《优良品德学习何以使人幸福》,《教育研究》2014年第8期。以亚里斯多德伦理学中的“品格发展”为视角对相关问题予以探究与比较,一则可以追溯西方伦理学关于品格发展的源头、形成机制及其内涵,二则可以对当下我国道德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有所借鉴。
一、品格形成中的天理与人欲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斯多德关于品格的论述在诸多方面承继了柏拉图的观点。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理性、意志和欲望是灵魂的三个要素;为了培育良好的道德行为,应适度地分别对三者进行培育。例如,体育的目的不仅在于强身健体,更在于磨练个体坚强的意志品质。柏拉图的上述观念,对西方的教育传统影响深远。例如,英国公学向来重视通过体育来培养学生顽强的意志品格,其理论依据甚或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之所以如此重视通过体育来养成个体坚强的意志,是因为他赋予意志一个关键的角色,即在理性的命令下意志需要对情绪进行控制。虽然柏拉图所认为的道德行为实际上是理性对情绪的控制,但他也认为这一规则需要其它动机的强化;而这些动机其实就是美好的、积极的品格,它们是意志的对等物。进而言之,柏拉图认为意志本身就是经过正确训练而培养的情感(affect),亦即一系列明智的、慎思的、有序的喜怒哀乐。
亚里斯多德对柏拉图的品格学说多有承继,但二者的分歧亦显而易见。首先,亚里斯多德的伦理自然主义(ethical naturalism)反对将人的灵魂、思维、理性与肉体的感觉、知觉、欲求隔离开来。他认为,美德蕴含着适度的情感和欲望,品格不仅关乎“你做什么”而且还关乎“你喜欢做什么”。于此,他断言:不以高尚的行为为快乐的人,就不是好人。*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II 3,1104b5ff.其次,人类有自己专属的目标追求——“向善”。他认为,人的灵魂是人性的代表,任何生命都是质料与形式的统一,而质料就是肉体,形式就是灵魂。*于洪波:《西方道德教育思想史比较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1页。对善的追求不是质料(gross material)属性的精神超越,而是人类努力的自然结果,正是这种努力造就了高贵与富有活力的人生。幸福作为“最高善”存在于现实的日常活动之中,这就要求人们不仅要“去做”,而且要“做得好”(acting-well)。就如同奥林匹克运动会不可能把桂冠戴在最强壮的人头上,而是戴在参与竞技且“做得好”的人头上。幸福亦是如此,它犹如一顶桂冠,总是戴在那些因“做得好”而获得高尚与善的人头上。这样的生命本身即令人愉悦,这种高贵的愉悦也是灵魂的习惯。亚里斯多德把美德与幸福联系在一起,认为一切引发人快乐和幸福的行为都是善的,只要这些行为出自于善良的品格。*Mill, J. S. Utilitarianism. London: Collins,The Fontana Library, 1970,pp.112-116.再次,优良品格暗含了由正当的欲望、激情和欲求所激发的道德动机,这意味着人类天性中的情感始终天然地(而非偶然人为地)根植于任何有关优良品格的养成之中。同时,这也意味着亚里斯多德没有贬低甚或否认对包括财富、荣誉、快乐等任何事物为对象的“欲求”(appetite)。亚里斯多德把这些称之为幸福所必需的“外在善”,舍弃这些“外在善”,人就很难做高尚的事情。抑或说,缺少了它们,人类的福祉就会变得黯然失色。亚里斯多德认为,可爱的子女、高贵的出身、健美的身材、适当的友谊等,对幸福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也没有否认更为基础的、单一的、对肉体快乐的“欲望”(desire)。最后,亚里斯多德认为如果没有激情、欲望和欲求,也就无所谓诸如公正、诚实、自律、勇气和仁慈等优良的品格。因为一个不热爱真理的人不会诚实;一个不渴望公正的人不会有正义感;一个不关心他人的人不会有同情心;一个没有经历过恐惧的人不会感受到勇气。鉴于此,亚里斯多德认为优良品格的目的是对人类天性的完善和履行,而非否认和压抑。
对亚里斯多德而言,“道德实体”(virtuous agents)绝不能仅仅退缩到纯粹的理性沉思,因为在这种理性沉思中身体的感觉与欲求无足轻重。他坚持认为,不是道德理性界定了善,而是它帮助我们成为善良者。道德“慎思”(deliberation)实际上是“实践智慧”(phronesis)的显著特点,“慎思”是达到以善为目的的有效途径,这种精心策划的“慎思”宜于实现艰难的“道德承诺”(moral engagement)。而实践中的“道德承诺”,往往与如何管理好人类的情绪和欲望相关。在“实践智慧”中,理性和欲望不可须臾分离,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余纪元:《亚里斯多德伦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0页。由此可知,亚里斯多德认为品格之形成,其实就是把美德培养与情感教育融为一体,并使二者和谐共生。抑或说,应该合理地安置人类天性中的欲望、欲求和激情,使之与美好的道德慎思达到和谐统一。*Carr, D. Virtue, mixed emotions and moral ambivalence. Philosophy,2009(4)
亚里斯多德所谓的“灵魂”、“思维”和“理性”类似于儒家的“天理”;而其所谓“欲望”、“欲求”和“激情”则相当于儒家的“人欲”。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向来为儒家所重。诸如,《礼记》载孔子所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论语》中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以及“贫而无怨难”,乃至于《孟子》中告子所说“食色性也”等,都承认并肯定“饮食”、“男女”以及“富贵”等所谓的“人欲”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共同天性,即孔子所谓的“性相近”。儒家认为,天生的“人欲”之性,并无善恶好坏之分。得孔门心传的曾子在其所作的《大学》中,也仅言“明明德”、“格物致知”以至于“修齐治平”;孔门嫡传的子思所作《中庸》,亦只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而绝口不言“人欲”之天性善恶与否,足见与生俱来的“人欲”之天性并无善恶好坏高下之分。那么,导致人们后天品格之差异的原因何在?孔子认为,乃“习相远”所致。此处之“习”,既是伦常日用而不自觉的积习成惯,又是心之“反身而诚”的结果,颇似亚里斯多德所谓“反思”式的“实践智慧”。抑或说,心习于善则善,心习于恶则恶。遗憾的是,宋大儒朱熹所言“存天理,灭人欲”,自近代以来被一再误读为:要发扬光大传统道德之“天理”,就必须要根绝“饮食男女”之“人欲”。实际上,朱熹自己对“存天理,灭人欲”之命题解释得明白无误:“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朱子语类》(第1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由此可见,朱熹认为正常的“饮食”和“夫妻”属于需要“存”的“天理”,而只有那些穷奢极欲的“山珍海味”和“三妻四妾”才是要“灭”的“人欲”。可见,朱熹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之命题,恰恰发扬了儒门“中庸”之正道。后世为政者、学界及民间对该命题非此即彼的二元式误读,诸如“大公无私”和“大义灭亲”等,或出于别有用心,或因学养不及,或因以讹传讹,以至于其流弊造成了深重的政治、文化乃至教育的灾难。学界通达的学者,对此不可不察,且当纠偏革弊,以正视听。
二、品格形成中的情感与理性
情绪可教吗?有些哲学家认为,既然情绪(emotions)是情感(affect)的消极状态,那么它就是与理性行为相互割裂的。这似乎表明情绪教育的空间是狭小的,因此我们与其忍受情绪,还不如对其进行控制和压抑。然而,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诸如贝德福德(Bedford )*Bedford,E. Emo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1956(3)、所罗门( Solomon)*Solomon,R. The Passions: The Myth and Nature of Human Emotion. Notre Dame: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1983,pp. 223-227.等,都反对把情绪视为消极与非理性的生活体验。他们认为,对情绪的理解不能完全与理性判断相剥离。脱离了客观对象,我们不可能理解包含愤怒、恐惧、憎恨、嫉妒和羡慕等在内的情绪体验,因为客观对象乃情绪所指所依。情绪是产生于人的基本欲求是否得到满足的主观体验,欲求的满足必须依赖于客观实体,它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实践智慧证明,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凭空产生的喜、怒、哀、乐。故而,情绪不仅有明确的指向,而且也有明确的现实基础。与此同时,如果没有人类思想和理性判断作为参照,我们对客观对象的辨认与表达也是不可能的。举例而言,倘若一个人理性地判断某个事件的状态是危险的,他才会体验到恐惧;倘若是惹人烦忧的,他才会体验到烦恼和憎恨。由德性伦理学观之,在理性判断的引领下所有的情绪体验过程总是指向引起这种情绪的事件或客观对象,情绪体验不亚于人类思想、信念和有意识的理性判断及思维活动。大凡概因,情绪体验亦不能与理性判断相剥离。
由是推断,人类与旷野上的野兽就有了本质的区别。人类不会仅仅满足于体验恐惧和愤怒,还渴望针对“正确的目标”或“正确的人”,在“正确的动机”驱使下,运用“正确的方式”适度合理地感受和表达这些情绪。因此,优良品格或多或少等同于“正确情绪状态”的体验。*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II 6,1106b18-23.就此而言,品格教育和情感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这种体验的正确性,建立在特定环境中对何为符合道德之事物的慎思基础上。亚里斯多德对美德的解析既反对禁欲主义(asceticism)式的压抑,亦不赞同对所谓消极的激情、欲望和欲求予以彻底消灭。相反,他认为恐惧、愤怒和欲望在人类“兴旺发展”(flourishing)的过程中占有近乎完美的位置,绝不能将其视为先天的消极或恶。因为在有些正义场合,若是没有愤怒或义愤那将是不道德的;这种不道德属于“麻木”(numb),是一种情绪表达极其不足的表现。一个民族的麻木是因为持续的情绪压抑而丧失了起码的道德直觉,以至于很难在短时期内被唤醒。尚若在危难之际也表现得出奇的坦然与自若,他们就很难发现特定情境中的伦理问题,并对此做出适当的反应,这样的民族在品格上必定具有不容置疑的瑕疵。个体亦复如此。长期恪守过分严酷的礼仪和规范,会使一个人不自觉地压抑基本的喜、怒、哀、乐等基本情绪,最终会丧失起码的尊严与勇气而沦为一个麻木不仁的人。杜威认为,没有“冲动”(impulse)就没有习惯,没有习惯就没有经验生长,没有经验生长就没有教育,没有教育就没有民主。杜威所认为的民主不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杜威之所以认为教育无目的,是因为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它自身就以培养民主的生活方式为内在的“善”与“目的”。这种民主生活方式不仅可以让儿童自由表达思想,而且还可以适度地表达情绪和情感体验。在久而久之的经验中,儿童会合理把控自己的情绪和情感。诸如此类的情绪都与美德融为一体,犹如欲望的适度表达之于人类的延续与兴旺,它实现了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与种群生命无限性的和谐统一。可见,对情绪的压抑或消灭,很难与良好品格的养成相容。
学界大多公认,我国传统哲学最本质的特征是实践理性主义。实则,传统儒家特别强调“情理不二”抑或“情理一体”。儒家鼻祖孔子哲学的精粹,可谓“仁学”,即“爱人之学”。“仁学”的起点或根本,是家庭中的“孝”,正如《论语》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认为,子女之“孝顺”与父母之“慈爱”,皆始于家庭中的“亲亲”之情,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最本真、最自然的日常人伦情感。孔子的伟大之处,就是在彼时农耕社会最基本、最稳定、最重要的组成细胞即家庭中,找到了维系封建礼乐文化的情感之根——“孝”。随之,以“孝”的“亲亲”之情为起点,培养出对他人的“忠恕”之情感和德性,进而通过“忠恕”推广“仁”或“泛爱众”的道德理想,最终达到“泛爱万物”的道德境界。儒家的亚圣孟子,将这个“情理一体”的展开和推广过程,归结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浑然一体,人们于不觉之中达到至高的道德境界。在当代科学理性主义的影响下,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界偏执于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二元论,其偏颇及其危害堪当以亚里斯多德和孔门之先见之明为纠偏救弊之鉴。
三、品格形成中的礼与权
“中庸之道”(golden mean)乃亚里斯多德伦理学的精髓所在。然而,其中庸之道及其在日常道德和现实政治中的适用性等问题,时常招致学术界的诘难和非议。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就认为,亚里斯多德式的公民领袖只能引领民众穿行于公正与不公正之间的“中间道路”。*Russell,B.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1991,pp.209-219.然而,罗素对亚里斯多德“中庸之道”的诘难,并非完全合情合理。若以罗素自己所引证的例子来分析,人们也很难清晰地得出道德正义必须无条件地、永恒地服从于公正原则的结论。如果一切如罗素所愿,那么在分配福利、公共服务和利益时,就会拒绝考虑个人的实际情况与具体因素。而现实并非如此,譬如,就教育系统内部而言,如果要使基本的社会公正目的得以实现,那么教育政策制定者就应该认识到处于弱势群体的学生需要额外的教育资源予以补偿。这是一个民主社会在贯彻民主时需要考虑的民主的补偿性原则。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也遵守这样的补偿原则:平等对待条件不平等的人和不平等对待条件平等的人均属于不公正,其结果别无二致。中庸的原则其实在公正、勇敢、克制、热情等方面,都具有普遍适应性。*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Poetics, and Politics, in McKeon, R.(Ed.),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New York: Random House,1941,pp.246-267.
至此,亚里斯多德关于“中庸之道”的核心观点业已清晰,其不外乎是实践智慧应当关心人类在纷呈复杂的生活中对情感与欲望的道德管理(moral management),而这些情感与欲望在理性层面上对个人和社会的兴旺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这必然会运用理性的秩序和尺度来处理人类天性中的自然欲望、情绪和倾向以及更为宽泛的欲求,以避免过分或不足,而非对其进行压抑或消灭。如前文所及,倘若一个人在危险环境中感受到太过分的恐惧,他就是一个怯懦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危险的环境中丝毫没有恐惧的体验,那么他也绝对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勇敢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面对危险完全缺乏恐惧感而在逻辑上排除了勇气,而是这种无所畏惧会滋生罪恶的愚蠢或鲁莽。同样的道理,虽然暴饮暴食或酩酊大醉都属于一种违背节制的原罪(sin),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者由于彻底否认了完全自然的、愉悦的和维持生命所必需的“食色”之欲,对亚里斯多德而言也是一种“恶”(vice)。这种“恶”虽然算不上“邪恶”,但也是一种“过分之恶”。在日常生活中,慷慨是一种美德,吝啬和贪婪属于恶;但无原则的、愚蠢的、浪费式的“给予”(非理性慷慨),则是另外一种恶。可见,亚里斯多德所认为的优良品格的培养与习得过程,实际上就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培养和习得适度的情感和欲望的过程。于是,作为德性目标的中庸,也就成为用以衡量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与他人关系、行为方式及目的的尺度。*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II 6,1106bff.
中庸的蕴义除了在过分和不及之间把握好适度之外,也要求人们能根据实践智慧合理、适度地掌控好道德规则和道德判断之间的协调关系。应该说,亚里斯多德也相信有“普遍的道德法则”(general moral principles),他并非所谓的道德虚无主义者。他确信,合理的道德反应来自于反思性的判断,来自于道德的实践智慧。这种智慧需要个体经历各种突发事件,并逐渐掌握“权变”时所需的、明智的应变能力。而这种能力常常以直觉的形式出现,因为具体情境中的道德判断往往是稍纵即逝的。
正如战国时期淳于髡诘难孟子:“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礼,乃普遍的道德法则;权,乃因时因地之制宜。有学者认为,权是发乎常理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并不违礼,而是因事制宜地、灵活地实现礼的规定。*黄济:《教育哲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94页。事实上,亚里斯多德关于规则与判断之间的妥协与协调,亦类似于罗尔斯的“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或普遍与特殊之间的权衡。因此,虽然勇气之于怯懦、同情之于冷漠等都是优良的品格,但勇气和同情在不同的情境中有不同的适宜性界定,切不可一概论之。
四、品格形成中的行为与反思
近代伊始,功利主义者一直过分地解读亚里斯多德关于品格教育的实践性观点。他们忽略了亚里斯多德对理性和反思层面的关注,仅仅将亚里斯多德的品格教育视为盲目的训练或对社会规则进行简单的“刺激-反应”。亚里斯多德的确把儿童早期的品格教育比喻为一种类似技能的启蒙,但他一直努力把美德作为一种个人的品格与技能区分开来。他坚持认为,美德智慧不是一种技能方面的技术性智慧。为此,亚里斯多德把作为道德的“实践智慧”(phronesis)的价值与教人如何做的“技艺”(techne)区别开来。简言之,品格发展的精髓在于:作为一个道德实体,如何在相应的道德情境中对自己的行为能够“思考得好”(thinking well)。这种思考可称之为“实践智慧”,它包括行为前的“慎思”(deliberation)和行为后的“反思”(reflection)。对亚里斯多德而言,一旦目标确定,实践智慧常常等同于“慎思”。慎思不是纯理智活动,不是理论思辨,而是关于行为的。对行为的慎思,是采取正确行动的前提条件。*余纪元:《亚里斯多德伦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1页。
事实上,把亚里斯多德的“品格伦理学”(ethics of character)和后来的功利主义道德理论相比较,并非是在品格伦理学和规则伦理学之间做一个划分,而是要突出亚里斯多德伦理学对“伦理判断”(ethical judgment)的重视远超于“规则”,因为所有严谨的伦理学都包含有规则与品格的双重取向。虽如前文所及,亚里斯多德的确认同普遍的道德规则,但是道德行为的最终目标不是让人仅仅遵从规则;确切而言,如果没有根据特定的环境即对规则做出理性的调整而一味地盲从规则,就很容易导致更坏而非更好的结果。譬如,如果不考虑个体的社会境遇,以正义的名义把有限的资源和福利进行平均分配,其实质无疑就是一种非正义。
人们虽然愿意遵从特定的道德规则,诸如诚实、节制、正义等,但却厌恶禁令式的规则。在“有德性的人”(virtuous agents)和“道德规则盲从者”之间,亚里斯多德做了极其清晰的阐述和划分。他认为,品格发展的终极目标在于立善修德,即有德性的人是那些在人性所及范围内达到一定程度的理性判断,且于欲望、情感、愿望之间达到和谐者,即“节制的人”(temperance agents)。“节制的人”已经不再有坏的欲望,他们在没有得到快乐或回避快乐时没有痛苦,他们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方式欲求适当的事物。因此,有德性的人是节制的,因为节制之人的欲望部分合乎罗格斯的要求。*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III 12,1119a30.相对而言,“自制的人”(continent agents)依旧有坏的欲望,虽然“自制的人”一直会坚持做他们认为符合道德规则的事情,但他们常常不具备“节制的人”所拥有的道德目的的和谐统一性,他们会常常受到与美德相冲突的动机的强烈干扰。
五、亚里斯多德品格发展观的德育镜鉴
亚里斯多德品格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通过循循善诱使个体做符合道德的事情,而且还在于使个体渐渐养成“向善的心性”(desire what is right)。亚里斯多德实践智慧的目的在于依照情感和欲望的适度(中庸)原则而进行理性判断与度量。实践智慧是极其有效的,其培养必须考虑情感与情绪的可教性。研究业已表明,“前理性”(pre-rational)人类的原始情绪和野兽是很难适合教育的(虽然可以对其训练),原因在于他们缺乏理性的约束与引领。然而对于理性主体的现代人而言,其情感已经与理性判断有潜在的联系,它们在观念转化与调整方面能保持相当的可融性和可塑性。
在教育层面,如何做到理性与情感和欲望的统一完整性?亚里斯多德认为,这种完整的统一最初基于儿童所养成的良好行为习惯。在对儿童进行早期训练中,成人的良好行为榜样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习惯的养成仅仅是一个起点而非品格培养的最终目的。舍此,就无法理解《尼各马可伦理学》最为核心的品格解读——实践智慧,即慎思与理性判断。实践智慧不仅关乎到对行为结果的理性评估,也关乎到如何选择实现道德承诺的方法。事实上,通过亚里斯多德对自制与德性之间的划分,亦可以洞悉在教育哲学的层面自律与他律之间的界限。亚里斯多德品格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自律者。
与“自制者”相对立的是“不能自制者”(incontinent)或自制障碍者。后者虽然通常也知道何为对错,但是他们仅有一定感性的道德知识。当他们屈从于自己的欲望时,他们所拥有的不是知识而仅仅是意见。他们虽然具备初步的道德认知能力,从而能大致把握一些道德原则,但却由于受自身欲望或情感的驱使,致使其不能根据道德认知在道德原则内合理行事。他们会出于情感而做他们知道是恶的事,因此他们常常充满了悔恨。亚里斯多德认为,不能自制和恶、兽性一样,是我们应当避免的品质。“自制者”(continent)是那些他律者,他们仅仅遵从于规则,但没有形成完善的自我,因此他们内心充满各种道德动机的冲突,进而给他们带来痛苦、失望等消极情绪。只有“美德品格”(virtuous character)或称“节制的人”(temperance or self-control),即使是在道德普遍法则不具备适应性的情况下,也能在变化的环境中根据实际情况,运用实践智慧准确地判断是非,在理性、欲望、情感的和谐统一下自然采取正确行为。有学者认为,所谓节制是受理智支配而不做明知不当之事的行为,因而极其符合道德目的,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善。*王海明:《伦理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4-295页。与节制相反的是“放纵”(acolasia)。亚里斯多德认为放纵应当受到谴责,放纵的人只追求快乐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人作为动物所具有的感觉,而不是作为人所独有的感觉。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坏人,他们出于选择而追求过度的而不是必要的动物式的快乐。亚里斯多德认为这种人不知悔改,因而无药可救。可见,品格形成过程首先要从保护好人的天性或从杜绝“放纵”开始。亚里斯多德认为,虽然放纵之人的具体行为出自于意愿,但他们的品格却不出自于意愿,因为没有人想成为放纵的人。*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III 12,1119a30.人类有“趋善”的天性,童年品格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创设良好环境以保护这一天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克服“不能自制”并渐渐形成“自制”的良好道德习惯,进而在慎思与反思的理性参与下逐渐形成以中庸为尺度的实践智慧,最后在道德自觉抑或德性的引领下通过立德修善达到“节制”,即理性、欲望和情感的和谐统一。
总之,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斯多德对培养良好品格的发展过程作了极为细致的论述。首先,考虑到品格教育具有非常强的实践导向,因此最基本的过程当属对其良好行为进行训练进而形成习惯。事实上,亚里斯多德明确地表示美德之习得犹如实用技能的练习,人们变得具有美德的过程犹如人们成为熟练的乐器演奏师一样,其核心秘诀在于日常练习。西谚有所谓“熟能生巧”(practice makes perfect),孔子亦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叹。优良的品格和美德之习得,亦复如此。其次,父母和老师要利用一切机会“强化”(reinforcement)儿童具备勇气、自制和体谅等方面的优良品格。因为儿童的道德教育,要牢牢地根植于在优良的环境中所养成的良好习惯。如此一来,当儿童面对小的挫折、轻微的伤害或小事故时,他们应该被鼓励要成为勇敢者。诸如,就餐时不能因为某道菜或甜品可口而占有超出自己的份额。这样教育他们不仅仅是要孩子戒除贪婪,而且要他们学会公正、体谅地对待他人。生活中的品格教育所起的作用主要在于长善救失,防微杜渐。亚里斯多德认为,“哲学的高谈阔论”(philosophical argument)对品格培养于事无补,除非我们能充分地利用儿童的经验,尤其是他们的早期经验。*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II 4,1105a12-18.教育者通过“顺其所易,矫其所难,成其美,变其恶”,方能达到教育目的。*《张子正蒙注》(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最后,习惯的养成除了利用生活中的种种机会给予强化之外,第三个关键方法就是“榜样”(exemplification)。儿童的行为模式是通过周围的人逐渐塑造起来的,因为儿童易于受到父母、老师等良好行为的影响而追求更好的行为,这必然要求教育者有责任为自己提出普遍的、高标准的道德诉求。*Carr,D. Character in Teaching.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2007(4).在学校教育中,教育者与学生的关系最为直接密切。教育者自身的品格是影响师生交往品质的核心因素。因此,教育者当以身作则,重视言传身教,而且身教的作用更为突出。*黄济:《教育哲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94页。言传的作用倾向于强化,旨在通过生活中对儿童的耳提面命达到习惯的养成;身教则侧重于榜样,旨在生活中为儿童提供行为标准而达到良好的模仿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亚里斯多德所认为的品格教育不是一种具体的教育策略,而是具备博雅教育的基本特征。
CharacterFormation:FromthePerspectiveofNicomacheanEthics
Li Guoxiang,Yu Hongb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 Shandong, 250014)
Aristotle claims that character develops over time as one acquires habits from parents and circumstance, first through reward and punishment. At the very beginning, one acquires a good character just as one may learn to play a musical instrument: initially, one may practice under some pressure, but eventually, enjoys playing with skill and understanding. The same is tru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virtuous character, which is not just concerned with what you do, but with what you enjoy doing. A full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 requires rational reflection and phronesis, in which the proper arrangement of human desire, appetites and passion is in line with reason by the “golden rule of the mean”.
Nicomachean Ethics; formation of character; phronesis
B502
A
1001-5973(2017)05-0096-08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7.05.010
2017-09-02
李国祥( 1975— ) ,男,甘肃天水人,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于洪波(1962— ) ,男,山东烟台人,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规划课题“先秦道家道德谱系及德育镜鉴——以老子为中心的考察(BOA14002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时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