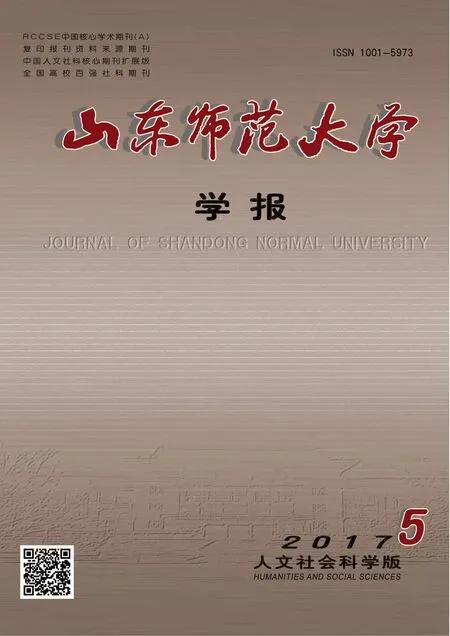老子“道知”性质探微
——兼论其对学科教学的启示*①
王康宁
(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山东 济南,250014 )
老子“道知”性质探微
——兼论其对学科教学的启示*①
王康宁
(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山东 济南,250014 )
老子“道知”须臾不离对“道”的阐释,“道”的特性既构成自身又构成有关自身的知识。老子“道知”所具有的先在合理性、不可尽言性、善性、工具性等性质,源于老子所预设的“道”,又反过来规定并揭示“道”的属性。探析老子“道知”的性质,一则可以深化对老子知识论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区分老子知识的类型以及明晰其“道知”的特征及范畴;二则可与当今知识尤其是学科知识形成比照,揭示古今知识的相通和差异之处,并对当前学科教学产生启示及借鉴。
老子;“道知”;学科教学
对于老子“道知”的探究,属于传统知识论哲学的范畴。作为一种以探究“存在”为主旨的知识,老子“道知”即是以“道”为核心而构成的,旨在揭示“道”的知识。在知识论哲学中,“存在作为一种对象,可以而且必须像科学一样,用逻辑范畴去予以表达和把握”*贺来:《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2页。。需要说明的是,传统西方哲学“天人分殊”的思维路径,对“存在”知识的研究可以形上形下二分,而此种情况依着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道器不离”的特征则不尽然。本文抛却中国古代是否有哲学,是否有知识论以及老子是否“反知”等历史辩论公案,以老子“道论”的存有作为研究的可行性辩护,观照老子思想的特色、探究老子“道知”,通过古今对比达成“古为今鉴”的目的,以期对当前知识观尤其是学科教学产生启示。
一、“万有之源”:“道知”的先在性
19世纪的实证主义代表孔德(Comte)认为,人类的知识必须经历“神学”、“形而上学”与“科学”三个阶段。在我国理论界,石中英也曾将人类知识发展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原始或神话知识型”、“古代或形而上学知识型”、“现代或科学知识型”、“后现代或文化知识型”。大致而言,神话知识型的存在时间应主要对应中国先秦三代之前的历史时期;古代或形而上学的知识型在中国则缘起于先秦三代时期,称其为古代知识型主要是将社会阶段作为划定标准;现代知识型以及后现代知识型则应指称近代以来的两种知识类型。
老子生活的春秋末年,从时空上划分属于古代社会,其知识属于形而上学知识型。古代知识作为形而上学知识型,是从某一特殊的本源派生出来的。“在古代言意范式中,物自身或者超越性的终极存在被视为知识的来源,人通过对这个来源的直观和内在的理性反思而获得知识”*陈越骅:《跨文化视域中的言意之辨——古代语言与知识的关系范式新探》,《学术月刊》2013年第5期。,形而上学的知识是揭示世界“本体”的知识。
作为揭示“本体”的知识,本体的逻辑优先性决定了本体知识的先在性。三代时期,天的观念早已存在,人们在面对诸多不解的自然现象时,往往向天发问,希翼从神秘莫测的天那里找到答案。彼时,人世间的一切自然现象以及人事变动,均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天的作用,人们因此敬天、崇天、畏天。西周之时,人们多将天视为主宰,考虑自然事物从天之“大”着眼。然而,老子构建了“以道统天”的自然图景,在老子语境中,“道”为至大,为通观世事的制高点。在先秦诸子中,唯有老子抬手将天拉入道之下。正如胡适所说:“老子的最大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别假设一个道”*胡适:《中国哲学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第43页。,使道成为天的法则,即所谓“天法道”。天地所法之道为永恒不变之“常”道,为周行不殆之“大”道。道为万物之所“奥”,生养并包容万物,万物由其出。“道”,这个原本包含所有的“大无”,衍生出不可尽数之“万有”。一切可见、可感之物皆带有道之特性,形而上的“大无”之道赋予万物成其自身的自然之道;万物依着各自之自然,成其本来该有之形质、态势。
在老子那里,作为终极原理的“道”替代之前的“天”,成为人们生活的原理和法则,成为人们知识的来源。正如有学者所说:“知识是宇宙这部戏剧的一部分,并且为一种宇宙的效用服务,那就是‘道’的成就。”*成中英:《中国哲学中的知识论》(上),《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老子对于“道”之先在性的肯定与之前将“天”作为“父”相仿。所不同处在于,老子将“道”视为万物之“母”。“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通行本《老子》第五十二章),王弼注曰:“母,本也”。在老子看来,“母”有资格作为天地万物的最初生产者,是天地万物之初始。“道者,万物之奥”(通行本《老子》第六十二章)。据河上公所注《老子》,“奥”字是“藏”的意思。王弼注曰“可得庇荫之辞”*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61页。,即说万物皆藏于“道”之中,“道”蕴含着万物生存发展的一切可能和潜力。“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通行本《老子》第四十二章)。天地为“一”所生,“一”为“道”之别称,故可以推论,“天”由“道”生。老子反复强调“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通行本《老子》第二十五章),再次认定道具有成为天下“母”之资格,肯定了道的先在性。
作为先在的宇宙之“母”,人们对于本体之“道”的认识,共同构成获得关于“道”的知识的前提及过程。按照哲学中认识论与知识论之间的紧密关系,对于道的定位及评价,是融意见显现及知识建构于一体的过程。对于本体之道所持的观点,即构成有关道的知识。
深入分析《老子》,可得见“道”的逻辑优先性与“道知”先在性的直接关联。老子将道预设为“帝之先”、“万物之所奥”,并设定了“道”的“恍惚”、“玄妙”、“周行不殆”的属性,却并未给予人们“道”何以如此的原因,亦未对“道”何以如此的必然性作出阐释。“(老子)并未告诉我们,‘道’是如何作为一个综合的、全面渗透的并且无所不能的过程,作为大千世界永不枯竭的源头,作为智慧和幸福的源泉而存在的。”*成中英:《中国哲学中的知识论》(下),《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老子对于“道”之书写的笃信,在于其将“道”视为理所当然、无需证实、不容怀疑的存在。在老子看来,形而上之道是不证自明的存在,其作为宇宙自然终极原理、法则的身份角色是业已既定、无需怀疑的,其所具有的万物之“母”的高位是本应如此的自然状态。
本体之道的逻辑优先性与不证自明性,使得关于形上之道的知识具有先在性。
二、“言不尽道”:“道知”的不可尽言性
老子形上之“道”恍惚、玄妙的特性,使得道不可尽言。自古以来,对于形上终极的解说及呈现,人们总是表现出无奈。佛家有言:“无相之体,同真际,等法性,言所不能及,意所不能思,越图度之境,过称量之域。”*僧肇:《维摩诘所说经》,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道家庄子亦言:“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757页。老子对“道”的形上属性的规定,同样使得关于“道”的知识不可尽言。“道知”不可尽言可通过老子对“道”的反复言说予以体现。
通观《老子》五千言,其中虽有对“道”的多次解说,却无一处肯定无疑之语气,无一处盖棺定论之言辞。在《老子》中,“道知”不能尽言体现为老子对道的谨慎言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通行本《老子》第二十五章)。在为“道”命名时,老子认为将终极原则命名为“道”仅是“勉强”的称谓。老子极力宣称道之名称的未定性,目的在于表明言说的局限性。此外,《老子》文本中存有多处“道”的别称,如第十四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八章、第三十五章、第三十九章等,都表明“道”具有“恍惚”、“朴”、“一”、“大象”、“无”等别称。
同于对“道”之命名,《老子》中也未给予“道”以明晰的形质。“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通行本《老子》第二十一章)。老子事实上认定“道”为物、有象,具有物质的特性。既为物则必有形质,而《老子》却又将“道”描述为“其上不皎,其下不昧”以及“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的“恍惚之物”。此与“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一致,皆承认道虽具有可视、可听、可博等物质特性,却并不停留在物质之上,而是在形质上超越物质的可感性,具有无状无象的模糊性。《老子》对“道”之特性的多方面描述,反而使得道更加“玄而又玄”。
在老子看来,面对着大而全的“道知”,任何一种言说都是片面的,人们“盲人摸象”似的言说,反倒割裂知识,导致更多的知识被忽略、被淹没。作为老子后学,《庄子》给出了“知识为何不能尽知”的解答,即“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关于本体之“道”的知识,虽是不能尽知的,但老子并未否定人们知“道”的可能性,而是主张通过多种方式“知道”。《老子》五千言以言说“道”为宗旨,“言”是老子所认可的一种认识、理解及传播“道知”的方式。言之功用可通过老子对于“道”之形、名的多次描述得见。白居易有诗言:“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白居易:《读〈老子〉》,《全唐诗》卷四百五十五(第十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150页。言说本身不可避免地成为知识出场的一种方式;依靠言说,知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人所知。然而,老子同样深知语言在与终极之“道”照面时的无力。换言之,仅靠言说不能完全揭示关于“道”的知识,道的特征及属性等绝非能够被语言全然提示与概括。基于此,老子提出另一种澄明本体之道的方式,此即“不言”。
在知识层面,老子所倡导的“不言”针对“言”而发。老子对于“不言”的提倡,起因于“不言”合于“道”的特性——无为而无不为,不言而无不言。老子的“不言”并非反对言说,而是反对将言说作为知识呈现的唯一方式。在老子看来,浩瀚的知识海洋中仅有一隅知识可通过言说予以显现,其他的知识则不得不通过其他途径。“五千言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告诉人们知识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获取真知。但是老子认识论的终极目标乃在于知道。”*孙以楷:《道家与中国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4页。面对不可尽言的“道知”,老子呼吁人们通过多样化的途径获得关于本体之“道”的知识,以弥补“言说”在呈现知识时的不足。
其一,老子主张通过“察”的方式获得“道知”。“察”即“观察”,是指人通过观察天地万物,从万物的生长、发展中探寻“道”的存在,并认识“道”、体认“道”。“察”是人“得道”的首要途径。《周易·系辞下》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取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观天地知宇宙之大法,察鸟兽虫鱼则得自然之精微。借自然之物以明自然之理,人世之“我”可得一二之“道”理。在《老子》中,“道”之不可摹状、不可尽言的特性,成为个体知“道”的阻碍;而从自身之外出发,借助我之外的宇宙内的他物探寻道之为何,是人们知道、得道的重要方式。
其二,个体的反思活动是获得“道知”的途径。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反”字有二解:“一为正反,违反之反;二为往返,回返之返。”*钱钟书:《管锥篇》(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45页。事实上,这里的“反”无论是“反面”抑或是“返回”,二者的意思是相通的,强调的都是一种对待事物的“逆向思维”。这种从事物反面着眼的方式,正是与常规思维活动不同的反思活动。老子主张人们通过反思,不断地向“道”靠近。“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通行本《老子》第二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通行本《老子》第五十八章)。人们通过反思“美”,得到有关“恶”的知识;通过反思“善”,得到有关“不善”的知识;通过反思“福”,获得有关“祸”的知识。人事生活的不断变化、转换是宇宙自然的规律,此与道的“周行不殆”相暗合。通过反思,人们可以依靠自身的思维进一步地体认、了解“道”。
其三,老子提倡通过实践的方式获得“道知”。“上士闻道,勤而行之。”(通行本《老子》第四十一章)人们对于“道”的不断践行,以“知道”为前提,并作为进一步“知道”的方式。“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通行本《老子》第六十四章)老子运用比喻的方式,主张通过亲躬力行的方法获得合于道的知识。在《庄子》中,通过实践的途径知“道”、得“道”的例子比比皆是。《庄子·养生主》所讲的“庖丁解牛”即是一个绝佳的例证。从庖丁解牛的整个过程看,其从最初的“见全牛”到后来的“不见全牛”再到后来的“不见牛”之“技”的形成,完全是一个在行动中不断积累经验,并最终达“道”的过程。通过实践的方式向“道”靠拢,既能够摒除在施力者与受力者之间的间接障碍,又能表现出一种“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的美感。
老子的“道知”可知却又不可尽知,其虽不能为言说所全面指涉,但可通过包括言说在内的多种方式呈现并获得。
三、“质善合德”:“道知”的善性
老子生活的春秋末年,由于政权及社会生活的动荡,人们开始怀疑德性之 “天”,“昊昊之天,不骏其德”(《诗经·小雅·雨无止》)。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老子将天拉入道之下,用“道”替代原本的德性之天。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通行本《老子》第二十五章),道的属性即自然性,道的德性亦体现为自然性。
与道之自然德性相符合,老子倡导那种合乎事物自然性的知识。“道家严格区分了两种知识,一种是儒家和法家的社会‘知识’,这是理性的,但却是虚假的;一种是他们想要获得的自然的知识,或洞察自然的知识,这是经验的,甚或是可能超越人类逻辑的,但却是非个人的、普遍的和真实的。”*[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史》,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7页。由于老子之“道”是善的,故而关于“道”的知识亦具善性。论及“道知”的善性,道家庄子亦对其持肯定态度。“在庄子那里,真知就是合‘道’的大知,也是其知识论的核心内容。”*石开斌:《论“善”在庄子知识论中的地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老子“道知”的善性,被蕴含在合于道的知识中。
其一,无之知。作为人们认识“道”时借助的重要概念,“无”的知识分有道之善性。老子甚为重视“无”之知。在老子看来,现实中的“万有”皆来源于“无”,“有”所产生的一切价值皆为“无”所赋予。世人皆汲汲追求产生实效的知识,却不知合世间之大德的无之知。在《老子》中,对于“无”的体认及获得,事实上体现为人的认知方式,其反映的是人们看待事物的角度以及所达至的精神境界。“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通行本《老子》第三十一章)。无之空虚、包容万物的本性合于道之德性,是善性之知。
其二,自知之知。对道家和禅宗来说,知识是自我认识和通向澄明与智慧的途径。*金吾伦:《知识涵义的转变》,《哲学动态》1991年第11期。在老子看来,“道”及“德”蕴于人的本质之中,当俗知蒙蔽人之自然性时,人才变成不道、不德之人。比如,“婴儿”、“赤子”的天赋自然性显现为“含德之厚”的善性,个体在发展的过程中,若对外界俗知不加分辨和提防,则会减损甚至失却自身自然性和德性。由是,自知,即知自身之自然;自知之知,即使人们了解自身自然性的知识。在老子看来,凡是违背人之为人自然性的思想及行为都是不自知的表现,个体需有自知之明。他认为,个体在生活中应“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具备知其自身自然性并顺应之、扩充之的相关知识。对于持有“自知”知识的人,老子多有褒扬。“自知者明”(通行本《老子》第三十三章),认为掌握自知之知乃能促使个体得道。相比之下,老子对于不自知之人多有批判,“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通行本《老子》第二十四章)。不自知之人违背自身天性为人处世,所得结果往往与所期待的相反。循此,自知之知所具之善性概可得见。
其三,顺时之知。《国语·越语》有言:“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顺时而为乃是顺应事物起源、发展之自然性的表现,此存于以自然性为标榜的《老子》中。从整体上看,老子之“道”,亦动亦静,因动静皆顺其时,故能生养、化育万物。正所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通行本《老子》第三十二章),天地之所以降甘露,正因为天地合其时,顺其势,故万物和合,风调雨顺。相应地,天地不合,时势不顺,则“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通行本《老子》第二十三章),事之影响仅为短暂,难与道之恒常德性相符。正如魏源所言:“盖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如时雨之应会而至,不疾不徐若非自然,而强谈诡辩以惊世,此犹飘风暴雨,徒盛于暂时而已。”*魏源:《老子本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3页。此种具有自然之德的顺时之知,对于君王或圣人教化民众以及民众统筹协调自身生活大有裨益,为老子所提倡。
其四,处下之知。此处所谓处下之知,大抵包含不争、谦卑以及柔弱等与硬性、教条的知识相反的知识。基于《老子》“道器不离”、“道器合一”的理论基调,处下之知既是形上本体之道的属性,包含并体现道之自然属性;又是形下社会的法则,可用其指导伦常日用。对于此类知识,老子多有褒扬。“夫惟不争,故无尤”(通行本《老子》第八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通行本《老子》第七十三章)等,皆指出不争之知的重要性。“柔弱胜刚强”(通行本《老子》第三十六章)、“弱者道之用”(通行本《老子》第四十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通行本《老子》第四十三章)等,指出柔弱之知的力量所在。“大国”、“小国”、“江海”、“百谷”的例子,则表明谦卑之知的重要性。在老子看来,对于善性之知的体认有助于人们德性的养成,循着对此类知识的体认和践行,人们断不会养成争先、尚功、好利之品行,而是能够依循自然善性发展自身。
老子提倡合于“道”的知识,“道”是善的,合于“道”的知识是善知。然而,合于“道”的善知,在遭遇“不道”、“不德”的现实后,有可能改变其“善”本质,转而成为“恶知”。相比于对“道知”的肯定,在老子看来,那些促成人们欲求过度、争名夺利、好德贪功的知识,皆是不合道的“恶知”。老子后学庄子认为,知识有善恶之分,认为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之行为皆因“恶知”所致。《庄子·齐物论》指出:“道恶乎而有真伪,言恶乎而有是非?”关于知识何以有真伪,庄子亦对此作过说明:“牛马四足,是谓天;穿牛鼻,落马首,是为人。”(《庄子·秋水》)在庄子看来,牛马有四足是其自然天性使然,人对牛马的主观作为使其丧失通体之自然性,不再是原初应有之面貌。相较之下,知识亦然。“知也者,争之器也。”(《庄子·人世间》)原本的合道之知,经过人们有目的、有计划的加工及分配,失却了知识本身的自然善性,进而成为人们争夺权势、标榜自身的工具,使人们做出“不道”、“不德”的事情,成为背道、离德之人。
可见,老子“道知”所具有的善性,源于“道”的本体之善,成于人们心性的润化与陶冶以及德性的养成与保持。
四、“用而不竭”:“道知”的工具性
先秦时期,自然之天地抑或德性之天地皆有其功用。承天地之托,以为人世之主宰;借天地运行之道,以明人世伦常之纪;以天地为指归,将天地运行之规律作为人世生活应遵循的法则,是人世运用天之功用的体现。《尚书·泰誓》有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子》亦有言:“天网恢恢,疏而不失。”(通行本《老子》第七十三章)天之功用无处不在。更有甚者,在商朝危在旦夕之际,借着天之依托,商纣王发问:“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为?”*司马迁:《史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25页。对于终极原理、本体存在的依赖,源自人们对终极原理功用的认可。以三代之“天”反观老子之“道”,可得见“道”对于社会人事所具有的工具价值。
作为终极价值、权威及法则的“道”,其所具有的工具价值与老子赋予“道”的使命有关。结合《老子》主旨,其所创设的“道”虽最初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上的,但其论述的重心及关键并非形上层面的复杂概念及其逻辑关系,而是集中于对现实社会人事问题的关注。由于《老子》之“道”旨在为现实生活的开展提供权威的、可供参照的摹本;其立论目的也并不限于专门的哲学问题,而是旨在解决社会人事问题,因而对社会人事的论述和关照,是老子道论的最终落脚点。抑或说,老子并非将“道”作为“恍惚”、“玄妙”的知识,用以束缚和教化人们;而是将“道知”作为工具,以其理论上的严密性、完备性,向下促使形下社会人事的完满,向上“自构”形上理论的完善。
对于“道”的工具属性,学界多有认可,“老子道论不过是用以建构这些关于政治和人生学说的‘研究纲领’和‘理论框架’”*朱晓鹏:《老子哲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7页。。陈鼓应亦说:“当‘道’作用于各事各物时,可以显示出它的许多特性。‘道’所显现的基本特征足可为我们人类行为的准则。这样,形而上的‘道’渐渐向下落,落实到生活的层面,作为人间行为的指标,而成为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处世的方法了。”*陈鼓应:《老庄新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页。老子之道的工具属性,使得关于道以及由道所派生的知识,亦可作为指导、优化社会人世的理论工具。道的工具属性与“道知”的可用性之间存在着“体用不二”的关系。老子“道知”的功用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其一,“道知”能够使人具有先见。获得关于“道”的知识,即是获知宇宙、自然、人事运行及进展的规律、法则及原理。“关于终极本体的知识一旦被把握,它就必然是终极的,表现为永恒的、非历史的、一劳永逸的知识,是人类理性所能达到的绝对真理。”*于秀艳、王明文:《知识论的超越与实践哲学的当代阐释》,《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认识及掌握规律、法则、原理等“先见”能在绝对意义上促进现实生活的开展。一者,“先见”能使人们防患于未然,即老子所谓“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通行本《老子》第六十四章)。二者,先见能使人们成为智慧之人,具备“见微知著”的能力,从而在面对问题及困难时能够及时规划、尽早行动,即所谓“图难于易,为大于细”(通行本《老子》第六十三章)。对此,魏源称赞道:“天下之事,始易而终难,始细而终大,故图之为之于其始,则不劳心力,自能无为。若不早图而亟为之,以至易者渐难,细者渐大,心力俱困,无为其可得乎?”*魏源:《老子本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9页。再者,先见能够使人有意识地避免祸害,此即“道知”趋吉避凶之功用。“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通行本《老子》第三十章),依靠对不道德行为结果的反思及借鉴,人们得以自觉而有目的地趋利避害。
其二,“道知”成就人之自然性。中国传统思想“天人合一”、“道人合一”的特征,构成了本体知识的善性与人之善性互通的逻辑必然性。人们获得“道知”并将其作为生活的指导,是遵循并扩充自身自然性的前提。老子的“圣人”作为得道之人,其所得之道,即是本体之道所呈现在现实人世中的诸多规则、原理等,换句话说即是有关道的知识。依靠对于“道知”的掌握及运用,“圣人”在德性层面能够最大程度地成就自身,成为人之楷模、道之化身。对于“道知”的体认及遵行,是成就人之自然本性及德性的前提条件及关键因素。
老子“道知”具有的工具性,一方面使得“道知”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可为人世生活的开展提供指导,促成人性的完满与社会的进步。
五、老子“道知”的学科教学镜鉴
融先在性、不可尽言性、善性、工具性于一体的老子“道知”,可与今日的知识尤其教学中的学科知识形成诸多比对,对当前学科教学产生有益启示。
其一,老子“道知”的先在性使得知识具有不证自明的合理性、合法性。老子对于形上之道终极价值的预设,使得本体知识即是“真”知识,本体知识与“真理”之间无有鸿沟。面对先在的“真知”,人们获得知识、践行理论的目的不是检验本体之知的真伪,而在于以其作为行为的指导。因着本体知识的先在合理性,人们对待本体知识是笃信的、敬仰的。相比之下,在当今知识种类名目繁多、知识体系繁芜复杂的背景下,知识的权威性、真实性却大打折扣。知识存在的合理性随时被否定、知识运用的有效性随时被质疑。当今的知识处于一种看似至臻至备实则失位失信的处境,人们对待知识缺少虔诚与敬畏。相比于庞大、复杂的知识体系及结构,学校教学中的学科知识,因其面向的有限性、体系的连贯性、结构的有序性,而具备较强的合理性。学科知识的合理性建基于知识筛选、甄别的基础之上。对于教育主体及学科教学而言,学科知识是专业人士为着实现教育目的、教学目标,参照相关标准合理选择的结果。现有的学科知识在教学过程中的合理性、合法性是先在的、无需证明的,教学是教授、学习学科知识的过程,而非辨别学科知识真假的过程。如同老子“道知”的先在合理性,是老子向人们“说道”的前提,学科知识的合理性,是其能够成为专业知识及教学内容的前提。
教学中学科知识的合理性是知识辨别、知识筛选的结果,而实际上鉴于教学的特殊性,教学所需要的教学内容也必须是经过筛选、论证、辨别的合理知识。学科知识的先在合理性,是确保教学过程合理、合法的关键。面对着合理的学科知识,教师在开展教学之前,无需花费时间对知识的真伪、善恶作出判定;有鉴于学科知识的合理性,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的过程中,能够对学科知识进行系统的划分及设计;有赖于学科知识的合理性,教师可将更多的时间利用到教学设计、教法选择、教学规划方面;以学科知识的合理性为前提,教师无需考虑知识是否经得起检验,可放手对学科知识进行创造性地讲解及运用。
其二,老子本体知识不可尽言的性质与今日知识观颇为相似。当前的知识观同样认为,人与知识经历时空的不对等使得知识不可为人们所尽知。老子之时,言说方式的欠缺往往对知识的呈现及理解构成阻碍。相比之下,今日言说方式的多样化仍旧没有改变知识不可尽言的现实。古今知识不可尽言、不能尽知的一致性,共同表明“言说”功用的局限性,对今日人们理性把握知识与言说之间的关系或有助益。
知识不可尽言的特性,与知识多寡无有直接关联。人类语言的局限性,是构成知识言说有限性的关键原因。作为知识分门别类的结果,语言与知识之间的悖论,在学科知识中同样存在。知识是不可尽言的,学科知识作为专业性的知识,具有知识的一般性质,同样是言说不尽的。在教学过程中,教育者的“言不尽意”正表明语言对知识的无力。面对着不可尽言的“道知”,老子选择通过“不言”的方式“言道”。在老子那里,“不言”并非“不说话”,而是主张人们通过多种方式获得“道知”。
鉴于学科知识与老子“道知”共同具有“不可尽言”的性质,在教学过程中,教育者不可过分看重语言的功用,而是应当多给予受教育者直接学习、自我反思的机会。当讲授学科知识时,出现“词不达意”、“言不尽意”的情况,教育者可以暂时放弃“言说”,转而采用沉默不言的方式,给予学生独立思考的机会,或者通过运用眼神、手势等肢体动作打破语言的局限性,更加形象生动地呈现知识。“不言”作为教育方式的合理可用性已为当前教育所证实。当前教学所倡导的观察、实践、反省的教学方法都与老子“不言”的方式颇为契合。可以说,老子“道知”虽具特殊性,却也具有知识的一般性质,古今知识之间的相似性,使得古今知识的习得方式可互通有无。
其三,判定知识合理与否的重要标准是知识是否具备“善性”。按照几千年前希腊先贤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的观点,“善知”是成就“美德”的前提及依据,只有当知识具备善性时,才能对个体幸福、社会进步产生积极作用。与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的观点具有相似性,老子对于“道知”善性的肯定,以及对于“道知”的尽力言说,何尝不是欲以“道知”促进人们德性的提升及社会的良性发展。古代中西方对待“善知”持相同的肯定态度。以古观今,当前的知识观同样看重“善知”,摒弃“恶知”。在漫长的文化传播、传承过程中,保留、发扬“善知”,否定、摒弃“恶知”是贯穿始终的知识厘定及选择标准。教育中的知识,是知识精华中的精华,“善知”是促成教育善本质的关键因素。与此相同,作为专门的知识,学科知识亦是“善知”。学科知识的善性是构成学科知识合理性的前提及根本。抑或说,当学科知识具备合理性时,意味着学科知识一定是“善知”。学科知识的善性,确保学科教学内容、过程、目的的善性。老子“道知”作为“善知”,与当前学科知识的“善”,具有相同的取向,皆是旨在通过“善知”促成个体的“善生”及社会、国家的良性发展。作为教学内容,学科知识的善性,使得学科教学理当是传播、传承学科知识善性的主阵地。在学科教学过程中,通过传播学科知识,使学科知识与教育主体德性之间形成直接关联,在达成教师“教书”职责的基础上,促成“育人”目标的实现,此符合“教学具有教育性”的教育规律,也是当前学科教学的重要使命。
最后,在老子看来,“道知”的功用性体现为,通过对于“道知”的体认及获得,个体、国家、社会乃至宇宙自然均能够处于理想的发展状态,并可达至最终的完满结局。公允地说,老子“道知”的现实功用,仅是老子的理论预设。如同苏格拉底倡导通过“善知”获得“美德”的说法更多停留于理论自洽一样,以理论层面的“道知”促成现实生活的改进,并非如老子所设想的那般简单。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不因理论知识的理想性而得以完全弥合。相较于现实的复杂性、多变性,任何理想完备的知识,均需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获得其现实功用。
人类的实践无一不是建基于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及运用之上。知识是否有用,是当前判定知识价值的重要标准。对于知识功用性的判定,为人们有效运用知识提供衡量标准及行动依据。同样,学科知识能够成为教育内容并为广大人们所认识并接受,以对“学科知识有用”的判定为依据。然而,结合老子对于“道知”功用的预设,我们可以发现当前学科知识功用的重要缺失处。老子“道知”对于个体的主要功用体现为关注并旨在促使个体自然人性的获得及高尚德性的养成。相比之下,教学中的学科知识于教育主体而言,更多的是促进个体知识总量的增加及知识水平的提高。起于现实、用于现实的知识尤其是学科知识,当其作为教学内容,被教育主体教授及习得时,在增加人们知识总量、扩充知识种类之余,能在多大程度上助力于人之精神境界的提升,促成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各者之间和谐共生,此是老子本体“道知”对今日学科教学的至深启示,也是当前学科教学亟待反思与解决的问题。
AnalysisontheNatureof“KnowledgeofTao”
Wang Kangning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 Shandong,250014)
“Knowledge of Tao” can not be separated for a moment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Tao”, for the metaphysical nature of “Tao“ constructs both itself and its knowledge. ”Knowledge of Tao“ is pre-existently rational, inexplicable, good and instrumental in essence, which derives from Lao-tzu’s hypothesis of “Tao”, but, in return, regulates and reveals the nature of “Tao”. On the one hand, to analysis the nature of “ontology knowledge” can deepen the study on Lao-tzu’s epistemology and help people to distinguish the types of knowledge of Lao-Tzu and clarif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ategories of “Knowledge of Tao”. On the other, it can be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with today’s knowledge, especially subject knowledge, reveal the connection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knowledge, and inspire today’s subject teaching.
Lao-tzu; “knowledge of Tao”; subject teaching
B223;G40
A
1001-5973(2017)05-0104-09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7.05.011
2017-07-01
王康宁(1987— ),女,山东济南人,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博士。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先秦道家道德谱系及德育镜鉴——以老子为中心的考察”(BOA140024)和山东省社科规划年度项目(青年项目)“老子道德理论的德育转化与利用研究”(17DJYJ0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时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