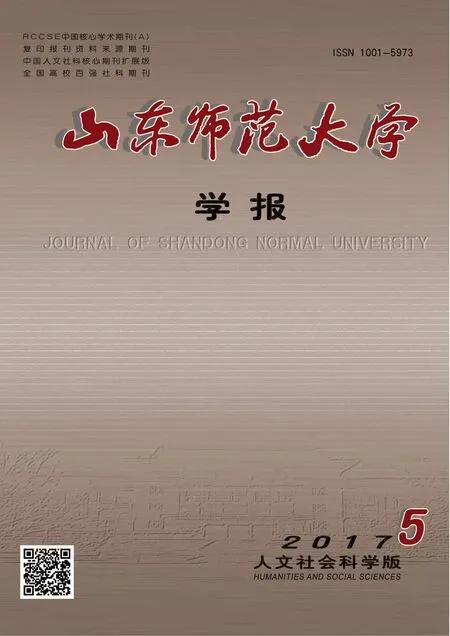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总体估价问题*①
王卫平
(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116081 )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总体估价问题*①
王卫平
(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116081 )
如何估价共和国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估价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这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问题,作家、学者往往各执一词,见仁见智。而要想令人信服地解说,必须有一个整体的背景和宏观的视野,必须将68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与此前的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相比照,否则是很难说清楚的;必须建构一个解析的、结构性的、整体性的综合坐标,我们才能对一个较长时段的文学作出相应的估价;同时,对于一体多面的中国当代文学还必须分类对待,避免笼而统之或“眉毛胡子一把抓”。 如果我们把文学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文学的一个标尺的话,那么,现代文学的成就和当代文学的成就相比是占一些优势的,因为现代文学接受、评论、研究的时间长于当代文学。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生态是多元复杂、一体多面的,我们可以进行总体估价,更应该进行分类评价。否则,极有可能以偏概全。
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新时期文学;总体估价;分类评价;综合坐标
几年前,在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讨论中,铁凝在致张江的信中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正确估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地位,可能最终还需要由历史来回答,可是,这并不意味着现在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没有意义。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重视对形势和现状的判断,经济、政治、社会方面如此,文化、文学方面也是如此。没有正确的判断,就会失去方向感,不知道该做什么。有了正确的判断,还需要分析形势和现状的由来,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铁凝:《致张江部长的信》,丁宗皓:《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4-5页。这道出了正确估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所在。
如何估价共和国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估价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这是庞大而又复杂的问题,作家、学者往往各执一词,见仁见智。而要想令人信服地解说,必须有一个整体的背景和宏观的视野,将68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与此前的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相比照,否则是很难说清楚的。
一、价值坐标:综合的、解析的、结构性的评断
在价值评说之前,首先遇到的就是价值坐标、评价标准问题。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2010年,在《辽宁日报》发起的“重估中国当代文学”的大讨论中,资深学者、鲁迅研究家彭定安的见解值得我们重温和珍视。他主张评价一个相当长时段的文学现象,决不可以使用“一言以蔽之”的断语来论定,“对于一个繁复的、复杂的、历经长时段的文化现象,必须采取综合的、解析的、结构性的评断”*彭定安:《评价当代文学的坐标是什么?》,《辽宁日报》,2010年1月11日。。有了这样一个解析的、结构性的、整体性的综合坐标,我们才能对一个较长时段的文学作出相应的估价,同时,对于一体多面的中国当代文学还必须分类对待,避免笼而统之或“眉毛胡子一把抓”。
2009年是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国当代文学也随之走过了60个春秋。以此为契机,文艺界和文学研究界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从文化中心的首都到各地召开了多个主题相近的学术研讨会,旨在回顾和总结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历史和经验教训。其中,如何估价中国当代文学这60年的总体成就,又如何看待它所存在的普遍问题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焦点。各种不同的意见见诸报刊,肯定者有“最高”、“最好”、“辉煌”说;否定者有“低谷”、“衰落”、“垃圾”说;有人将当代文学60年和现代文学30年进行对比,认为当代文学的总体成就已远远超过了现代文学的总体成就;有人则认为当代文学并没有超过现代文学的成就。还有人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有大作家却没有大作品,中国当代文学有大作品却没有大作家。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让人有些匪夷所思。
一般说来,一个时代或一个时期的文学样态和文学成就往往呈现出复杂的形态,与另一个时代或时期的文学样态和文学成就较难比出高下。按照文学进化论的观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不同时代的文学不可能重复,而总是要创新、求变,另辟蹊径,甚至标新立异,剑走偏锋。因此,不同时代的文学有时是不具有可比性的。拿中国文学来说,到底是先秦时期的文学成就高还是两汉时期的文学成就高?到底是唐代文学成就高还是宋代文学成就高?明代文学和清代文学相比孰高孰低?这些是较难回答清楚的。拿世界文学来说也是如此,19世纪欧美文学与20世纪欧美文学相比,哪个成就高?我们似乎难分伯仲。所以,到底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高还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高?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是否超过了中国现代文学?可能是一个难分胜负的争论,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即在很多情况下,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文学成就还是能够大体分出成就的高低的,特别是当我们采取综合的、分类的、解析的、结构的等多重角度进行梳理和归纳的时候就更容易看清对象的真相。以中国文学为例,先秦时期的散文(广义的)、唐宋的诗词、明清的小说,其成就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是超过其他朝代的;辽、金、元时期的文学成就在中国古代的各个朝代中是不高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远远超过中国近代文学的成就。这些是学者们有目共睹的,也是能够达成共识的。以世界文学为例,17、18世纪的欧美文学远不及19、20世纪的欧美文学发达;而中世纪的文学又不如古代文学辉煌。文学就是这样复杂,后代可能超越前代,也可能不如前代,要看具体的时代和环境,要看作家的创作实绩,要作具体的、结构性的分析,切不可一概而论。
回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上来。过去,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1927—1937)(或曰30年代)的文学成就远远超过第一个十年(1917—1927)(或曰20年代)的文学成就。不论从作家作品的数量来看,还是从作品的篇幅、规模来说,以至从作家把握生活、开掘生活的深广度来审视,都显出成熟,摆脱了稚嫩和初创的特征。而对中国现代文学第三个十年(1937—1949)(或曰40年代)的文学的理解和评价就见仁见智了。有人认为它是中国新文学的凋零期,是呈现出衰败迹象的一个历史时期;有人则认为它是中国新文学的丰收、成熟和老到的时期。
将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将中国当代文学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对照,然后评价孰高孰低,从1980年代就开始了。有论者指出“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比起“五四新文学”,“当代文学这30年无论是在作家、作品,还是在文艺斗争方面都远不如前30年”*赵祖武:《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新文学论丛》1980年第3期。。到了1997年,王晓明曾非常生动地描述过由于评价体系的不同而造成对中国20世纪文学总体评价的变化:
人们一定还记得,早在八十年代,就有论者明确地指出,一九四九年以后三十年间的文学成就,远不及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三十年。这招来了不少愤怒的声讨,但大家很快就意识到了,他不过是率先说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一个人所共有的感觉。这感觉是那样鲜明,以致后来听说欧洲有汉学家断言中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当代文学”,许多人竟没有热情去作认真的反驳。……“新时期文学”又怎样呢?在八十年代中期,曾有人接二连三地预告过文学的“黄金时代”的来临。可是,目睹了最近十多年文学艰难挣扎的状况,我想是谁都不会真以为自己踩到了“黄金时代”的门槛吧,而二十世纪却已经快要结束了。*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序》,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1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1-2页。
目下,21世纪已经过去了十几个年头,人们又一次提出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文学的总体估价问题。
二、中国当代文学68年和中国现代文学60年相比孰高孰低
当今,学界有人提出应该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向前推进到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样的话,中国现代文学就是60年。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有68年。因此,今天的比较应该是60年和68年的比较。顾彬以“五粮液”和“二锅头”来比喻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引起了众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不满。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一问题?我们不想以“一言以蔽之”的断语来论定,而是想描述一些基本的事实。
(一)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所占的比重
仅以20世纪末以来较有影响的将中国现代、当代文学打通的文学史作为观照对象,看看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整体格局中所占的比重如何。
1996年出版的由苏光文、胡国强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苏光文、胡国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是较早将中国现代与当代打通的文学史。其中,上卷为现代文学,从1901年算起,36万字;下卷为当代文学,写到1995年,27万字。现代文学所占篇幅明显多于当代文学。
1997年出版的由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是一部126.1万字的鸿篇巨著,它从1898年写起,止于1990年。其中,现代文学约占64.2万字,当代文学约占61.9万字(其中包括港、台文学约30万字),现代文学所占篇幅也多于当代文学。
1999年出版的由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上册为现代文学,从1917年写到1949年,39万字。下册为当代文学,从1949年写到1997年,30万字。
2004年出版的由黄修己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黄修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全书76万字,从1900年写到2000年,整整一个世纪。其中,现代文学约占44万字,当代文学约占32万字。
2007年出版的由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朱栋霖、朱晓进、龙明泉:《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从1917年写到2000年。其中,现代文学39.7万字,当代文学38万字。
同一年出版的由曹万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黄万生:《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百万余字,从1898年写到2006年。其中,现代文学约56万字,当代文学约44万字。
2010年出版的由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从19世纪末写起,一直到20世纪末,分上、中、下册,其中,上册为现代文学,44万字,中册也是现代文学46万字,下册为当代文学,只占39万字。
2013年出版的由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丁帆:《中国新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分上下两册,将民国元年作为中国新文学的起点,一直写到2010年。其中,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所占的篇幅基本持平。
从以上的梳理和列举中,我们发现,在多数版本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格局中,现代文学所占的比重都多于当代文学,只有新近出版的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所占的比重基本持平,其原因是所描述的现代文学的历史是37年(1912-1949),而当代文学是61年(1949-2010),时间的拉长必然造成篇幅的增多。在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现代文学所占的比重最大,超过了三分之二,而当代文学所占的比重不足三分之一;它们所描述的文学时间都是60年,因此,它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
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可能有三:一是现代文学经典的作家作品、优秀的作家作品较多,因此在文学史中所占的比重自然较大。文学史不是作家作品的汇总,它必然有所遴选和择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二是现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历史比当代文学长,在不断地批评和阐释中,经典也不断地生成,其影响自然要比当代文学大。正如有学者所说:“经典的形成必须要有反复和重复的阐释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很难成为经典。”*张福贵:《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与当下的价值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当代文学阐释的历史相对较短,经典的遴选和经典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一方面,需要历史的沉淀和时间的检验;另一方面,需要研究者、文学史家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理直气壮地去筛选、研究和认定经典,完成经典化的任务。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披沙拣金,发掘优秀的作品比痛快地否定困难得多。三是上述这些文学史著作的主编多为现代文学研究者,因此,可能不自觉、无意识地对现代文学有所偏爱,而对当代文学重视不够。中国现当代文学本来是一个学科,应该进行一体化的研究,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先有现代文学,后有当代文学,于是就出现了侧重现代文学研究和侧重当代文学研究的分野。如果研究者尤其是文学史家超越了后两点限制,不受其影响和左右,那么,只能说明现代文学的成就高于当代文学了。
(二)中国现代、当代作家作品在百年中国文学评比情况
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国内文学界、文化界、教育界纷纷总结过去这100年的文学和文化成果,如遴选文学大师、评出百强作品、确认优秀文学图书、推出文化偶像、推荐阅读图书等活动。其中,现代作家、作品和当代作家、作品入选的情况和比例是怎样的?我们列举如下五项活动:
1.1994年,由戴定南策划、王一川、张同道任总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在文学界产生很大影响和广泛争议。他们有自己的标准和评价体系,即审美的标准和“四种品质”(语言、文体、精神含蕴、形而上意味),以此来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该文库以文学体裁为单元,分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四种。每种体裁以20世纪为单位,遴选包括港台地区在内的10位左右的中国文学大师(如不足则宁缺毋滥),将他们堪称典范的作品选入文库。小说卷中遴选出9位大师,座次依次是: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其中,现代作家占6位,当代作家占3位。散文卷中遴选出15位大师,座次依次是:鲁迅、梁实秋、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贾平凹、毛泽东、林语堂、三毛、丰子恺、冰心、许地山、李敖、余秋雨、王蒙。其中,现代作家占10位,当代作家占5位。诗歌卷中遴选出12位大师,座次依次是:穆旦、北岛、冯至、徐志摩、戴望舒、艾青、闻一多、郭沫若、纪弦、舒婷、海子、何其芳。其中,现代诗人占8位,当代诗人占4位。戏剧卷遴选出9位大师,座次依次是:曹禺、田汉、夏衍、郭沫若、老舍、姚苇、杨健、杨利民、李龙云。其中,现代戏剧家占4位,当代戏剧家占5位。
2.1999年6月,《亚洲周刊》评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进入“100强”的小说,主要是三四十年代的作品,中国大陆1949年以后的作品只占25本。
3.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北京图书大厦联合发起“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评选活动,邀请一批著名的文学专家,经过三轮评审,最终评出100种中国文学图书,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五大文体。在评出的百年百种中国文学图书中,前50年占60种,后50年占40种。
4.2001年,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几十位教授经过长时间酝酿和反复讨论,向全国高等学校中文系的本科生推荐100部阅读书目,覆盖七门专业主干课,涉及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推荐21部,现代文学占14部,当代文学占7部。
5.2003年,新浪网与中国国内17家媒体共同推出大型公众调查:“20世纪文化偶像评选活动”。经过网友和多家报纸读者的热心投票,最后统计出“10大文化偶像排名”, 依次是:鲁迅(57259票)、金庸(42462票)、钱锺书(30912票)、巴金(25337票)、老舍(25220票)、钱学森(24126票)、张国荣(23371票)、雷锋(23138票)、梅兰芳(22492票)、王菲(17915票)。在这10大文化偶像中,现代作家占4位,当代作家占1位(香港作家)。这个排名,代表精英文化、革命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重要人物首次赫然并列其中。
上述五个例证有一个共同现象:人们对现代作家作品的推崇远远多于当代作家作品。这说明,现代作家作品在读者心目中的影响力是超过当代作家作品的。如果我们把文学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文学的一个标尺的话,那么,现代文学的成就和当代文学的成就相比是占一些优势的。当然,这里也有一个现代文学接受、评论、研究的时间长于当代文学的原因,因而,现代文学的影响力自然就大一些。
我们据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当代文学68年,前30年的文学成就、文学价值是超不过中国现代文学60年的;加上新时期的38年,中国当代文学的平均成绩、平均分数是不能低估的,但它的经典作家的社会影响力不如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的社会影响力。
三、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总体估价与分类评价
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文学,到底是不是中国文学最好的时候?是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为辉煌的篇章?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还是处在前所未有的低谷?持高度肯定和极端否定观点的人都能从文本中、从创作实践中找到依据,这说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形态是混合复杂、一体多面的,我们可以进行总体估价,更应该进行分类评价。
从总体上看,客观公正地说,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并未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不一定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为辉煌的篇章;当然,也不是前所未有的低谷,不像否定者所描绘的那么糟糕。对它的总体估价应该是:它是有成绩的,也是有问题的;是有贡献的,也是有局限的;是处在文学的常态时期。这是一个多元、多样、多种文学混杂在一起的时代,其中,有垃圾,也有黄金。“垃圾深处有黄金”,莫言为《辽宁日报》大讨论的这句题词,可以作为估价新时期文学的基本观点。*莫言为《辽宁日报》关于“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题词全文如下:“时人眼里看英雄,骗子最怕老乡亲。三十年文学如何说,垃圾深处有黄金。”见丁宗皓:《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51页。当陈晓明和肖鹰的争论引起广泛反响之后,中国文学是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就成了整个“重估”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凤凰网为此问题专设网上调查,截止2010年3月11日,有4242名读者参与,在‘你认为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吗’的问题中,选择‘达到了’的占2.2%,选择‘未达到’的占89.8%,选择‘不好说,做这样的判断为时尚早’的占8%。而参与调查者学历分布,大学本科占52.48%;职业分布占最大比例的为事业单位调查者,占23.15%。”*丁宗皓:《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66页。这个调查具有相当的覆盖面,因此也是具有说服力的。绝大多数的网民认为,中国文学没有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应该说,群众的眼光还是雪亮的。
新时期30多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经济上取得了辉煌的、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文学上也应取得与之相匹配的成绩,这可能是一些人正常的思维逻辑和文学期待。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艺术应该协调发展,而且马克思早在当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深刻地论述过物质生活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制约和影响,因此,经济的辉煌理应带来文学的繁荣。中国古代的“盛唐之音”即是经济盛世带来文学盛世的表现。
但是,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并不总是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完全一致的,相反,它会呈现出不平衡的态势。这一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也作过深刻的论述。中国素有“国家不幸诗家幸”、“苦难是艺术的秧田”的说法。灾难、不幸、苦难、挑战,往往是文学创作的契机和作品上达的动力。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社会,虽然结构性的矛盾和挑战时有出现,但整个社会越来越走向平稳发展时期,经济上的发展突飞猛进,成就辉煌。文学艺术创作在数量上也突飞猛进,但在质量上,在社会影响力方面,越来越走向常态化和弱化,这是时代发展、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回想20世纪初,从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始,人们把小说(文学)看作是改变社会、改变政治、改变风俗、改变道德、改变人心、改变人格的利器。到了五四时期,人们主张“人的文学”,把文学看作是为人生、改良人生、启人心智、催人觉醒的神圣的事业,是思想启蒙的重要武器,而不是游戏、消遣和娱乐的工具。鲁迅、郭沫若相继“弃医从文”。20年代的蒋光慈、三四十年代的巴金、救亡文学、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小说”、政治抒情诗等,其作品均影响、鼓舞、激励了无数的人们,尤其是促使青年人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显示出强大的正能量,发挥着巨大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再次充当思想解放、思想启蒙、观念更新的先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无不引起广泛的社会效应。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过去,使相当一些人仍按照这样的逻辑和期待要求后来的文学。殊不知,时代、社会和文学自身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过去,文学是受众阅读、接受的主要对象,甚至是唯一的形式,那时的文学是受宠的,是时代的宠儿。但当影视、游戏、网络、新兴媒体等高度发达以后,文学变成了众多艺术接受形式的一种,文学在价值多元、艺术多元、娱乐多样的时代自然而然地失宠了,变成了非主流的、边缘化的艺术样式,接受起来远比手机、电脑、微信、影视、游戏、KTV等视觉的东西、身体的表演笨拙、枯燥和单一,远不如后者来得痛快、过瘾。在这样的时代,文学产生巨大的影响力、震撼力等轰动效应的情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文学进入了普通的、正常的状态。正如洪子诚所说:“可以肯定的是”,当今“不论从什么样的意义上说,都不会再有托尔斯泰,不会有《红楼梦》,不会有鲁迅;虽然很遗憾,但也不会再有杜甫。我们只有,譬如说北岛、多多,譬如说西川、翟永明、王家新……如果王家新就是杜甫,能比肩杜甫那很好,我们的焦虑顿消;如果不是,成就难以企及,那也只能接受这个事实。这就是我们的正常(而非特殊)的情境”*《中国文学与当代汉学的互动——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文学圆桌会纪要》,《文艺争鸣》2010年第4期。。洪子诚深刻地指出,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焦虑症”,即“焦躁地期盼、等待出现大师、出现伟大作家、出现文学辉煌时期”。这种“渴望和等待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应该去做自己的工作,”“譬如说,对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实践,进行一些认真的反思、总结”*《中国文学与当代汉学的互动——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文学圆桌会纪要》,《文艺争鸣》2010年第4期。。和谐盛世,既是物质、精神不断超越的时代,也是精神面临危机的时代。全社会无不为“物”、“物欲”所挤压,超功利的精神空间日益萎缩。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边缘化使其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差,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比,文学已退出了社会公众生活空间,而越来越失去轰动效应和社会影响力,即便产生一些影响力,也只在文学的圈子里产生一些反响。而大量低劣的文学可能永远默默无闻。从长远来看,这也许是文学的常态,所以,中国文学不可能取得与中国辉煌经济相匹配的成绩。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又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在形态、类别、层次、种类等方面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复杂得多,呈现出杂多化的特征,令人眼花缭乱。文学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垃圾丛生,给否定者留下了充分的口实。因此,在总体评价的同时,还必须进行分类评价,否则,极有可能以偏概全。从文学的种类来说,新时期的文学呈现出种类的空前繁多和发展的不平衡的特点。按载体划分的口头文学、书面(纸质)文学、网络文学等几部分文学中,口头文学越来越衰落;书面(纸质)文学的创作不减;而网络文学则迅速崛起,其接受的广度越来越超过纸质文学,甚至有人预言将取代纸质文学。但由于网络文学没有门槛,缺少准入的把关,致使网络文学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同时,网络文学多以赚钱为目的,因此,难免寻找卖点和噱头,导致网络文学出现特殊的行文特点和文本特征。肖鹰、丁帆认为网络文学不能进入文学史的视野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但网络文学又有其众多的接受群体,其影响面、影响力不可小视,因此,必须加以规范、引导和提升。而对于网络文学的批评和研究还相当薄弱,甚至连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也亟待建立,前不久《光明日报》等媒体讨论此问题着实具有意义。广大接受者所反映的网络小说读起来轻松、不累、离他们的生活经验近等特点也值得纸质文学学习和借鉴。传统的书面(纸质)文学虽然数量不减,但其阅读和接受却在萎缩,社会影响力也在下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书面(纸质)文学中,各种文学体裁的文学成就也参差不齐,其中,小说的成就最为卓著,甚至成为文坛的霸主。一说新时期的文学成就,主要以小说为例,似乎新时期的文学成就只有小说。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以短篇开启端,中篇的成就紧随其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愈加繁盛起来,从每年的几百部很快攀升到上千部,以致到几千部。从数量来说,这是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当然,任何一种文学样式的成就又不能完全以数量论。在严肃文学中,新时期的确成长起一批小说家,从老一辈的汪曾祺、王蒙、张贤亮、高晓声、张洁、谌容、陆文夫、林斤澜、冯骥才,到中年作家、知青一代,以“50后”为最,包括贾平凹、莫言、张炜、铁凝、王安忆、韩少功、阿城、刘震云、阎连科等,从“60后”的余华、苏童、格非,到“70后”、“80后”青年小说家。其中,“50后”的一批作家,其小说创作的总量多已超过了中国现代的小说大家。
在书面(纸质)文学中,新时期以来的散文、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儿童文学的总体成就不仅超过了当代文学的前一时期,而且超过了中国现代文学。其中,散文创作,他们也许不及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周作人、朱自清、冰心、梁实秋、林语堂、何其芳等名声显赫,并有自己的鲜明风格,但新时期以来的散文,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散文的“平均分数”还是大大超过了中国现代散文,尤其是学者散文、文化散文的崛起给散文注入了新生命。只不过它和中国现代散文相比,还缺少散文名家、大家。同时,也由于散文的铺天盖地,使其影响力自然变小、变弱了。
在书面(纸质)文学中,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呈现出与小说不同的情形。在“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争论中,研究者往往以小说为例来解说,诗歌是缺席的,对此,文学史家洪子诚颇为不满。他说:“现在评价文学,谈论文学,诗歌往往被排除在外。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成为谈论文学的全部。这是很不正常的。缺乏诗歌的文学是有重大欠缺、跛脚的文学。在我们这里,作家协会成了小说家协会。”*丁宗皓:《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06页。洪子诚所说的这种现象是完全属实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是人们对诗歌存在偏见吗?恐怕不是。我们认为,主要是因为诗歌的成就与小说无法相比。新时期以后,自20世纪80年代“新生代”诗人出现以后,诗歌创作已经布不成阵,尽管发表诗歌的刊物照样出刊,诗集照样出版,诗篇照样发表,但毋庸讳言,诗歌越来越无人问津。这与诗歌所处的环境有关,在艺术的接受走向多元化以后,阅读诗歌、喜欢诗歌的人越来越少。今天的读者,不仅青年人不读诗,就是批评家也很少读诗,这是一个叙事的时代,而不是一个抒情的时代,诗歌的影响力日益减弱。从诗歌创作本身来说,外部环境不利于其生长,内部原因也不容忽视,主要是诗歌抒写时代之情、人民之情、追求真善美、关注重大问题、关注民生问题表现得越来越差,诗歌远离了现实人生,现实中的人们自然就远离了诗歌。诗歌研究也严重缺失,以研究诗歌而著名的学者也越来越少,诗歌在文学史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少,“新生代”以后的诗人诗篇在文学史上基本没有什么地位,难怪研究者言必称小说。洪子诚对“新生代”诗人褒奖有加,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不少诗人写得很好,如大家熟悉的多多等,如海子、西川、王家新、于坚、萧开愚、翟永明……”*丁宗皓:《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06页。,但新生代以后的诗歌就愈加不尽如人意了。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最有成就的不是小说,而是诗歌的观点,是中国绝大多数学者所不能同意的。诗在“新生代”以后,已经陷入了尴尬的境地,陷入了孤芳自赏的境地。这不全是诗人的错,而更重要的是时代造成的。曹文轩分析得好:“对于目前诗歌的尴尬处境,我以为,除了在诗本身寻找原因外,也应在文学样式与时代之关系上来寻找原因。唐为诗宋为词元为曲,到了明清,则小说一统天下,都与时代的精神与情趣息息相关。怎么可能中国人到了明清,就都没了诗才,而却一个个都是写小说的材料?则是因为到了那样一个时代,人们不怎么需要诗了。今天任何一位诗人的诗句,都十倍几十倍地超过大跃进民歌的发烧胡言。然而,大跃进诗歌可以走红,今天的诗却只能由诗人孤芳自赏。诗人只好勒紧裤带自出诗集,然后相赠友人,以博粲然一笑。”*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6页。
戏剧在文学艺术的家族中又属于另一种形态和类别。从剧本创作来说,它属于语言艺术,从演出实践来看,它又属于综合艺术。王富仁说:“现代话剧在中国的运气也是不好的,在它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时候又遇到了电影的冲击。”“在观念上,戏剧的地位提高了,被现代知识分子抬到了雅文学的圣坛上来,但就实际的创作,它还很难说有与此相称的成就。”*王富仁:《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232—233页。到了当代,话剧不仅继续受到电影的冲击,还受到电视的冲击,受到网络、游戏等多种娱乐形式的冲击。一些杰出的编剧跳槽去“触电”,因此,一度出现剧本荒。新时期以来,只有初期的《于无声处》《丹心谱》《报春花》《陈毅市长》以及接下来的《小井胡同》《天下第一楼》《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等较有成就和影响,因而被写进了文学史、戏剧史。除此以外,话剧创作越来越平庸和窄化,其艺术的高度、成就、影响终难超越曹禺的《雷雨》《原野》和老舍的《茶馆》。进入新世纪,偶有像《立秋》这样的佳作,但终难与小说相提并论。所以,我们看到,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对戏剧的书写一般止于80年代的上述作品,包括话剧和其他一些地方戏曲。新近出版的、有重要影响的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册,在新时期文学的描述中,戏剧是空缺的,诗歌和散文也占极小的比重,小说几乎是一统天下。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下册,对新时期的戏剧也只用一节的篇幅。这一方面说明新时期戏剧的成就的确不能与小说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对于戏剧的研究,尤其是对其进行“史”的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事实上,新时期以来的戏剧,不论是话剧,还是京剧和其他地方戏,不论是现实主义戏剧,还是实验戏剧、小剧场戏剧,不论是史诗性的大剧,还是荒诞戏剧,国家和各省市院、剧团都曾推出过一些精品力作,我们的文学史家、戏剧史家对它们的关注、研究以及进行“史”的总结还很不够。
从创作理念、创作方法来说,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文学成为两大主流,而浪漫主义文学则夹在中间,处境艰难,甚至可以说走向衰落。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后起的现代主义是几大基本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在中外文学史上,浪漫主义都有过辉煌的历史。“中国文学史上离不开屈原、李白一直到现代郭沫若等人的创造。同样,德国离不开歌德、席勒,法国离不开雨果、大仲马、乔治桑,英国文学离不开拜伦和雪莱。”*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96页。但是,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尤其在新时期文学中,浪漫主义并没有继续迎来它的繁荣和昌盛。相反,浪漫主义文学处境艰难,成就甚微,研究者甚寡。新时期以来,浪漫主义文学是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夹缝中默默地生长,声音较为微弱。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以至到21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走过的是在场——缺席——终结的道路。在新时期文学中,浪漫主义的“在场”在张承志、铁凝、白桦等作家的作品中以鲜明的抒情性体现出来,曹文轩把它称为“浪漫主义的复归”,具体体现为主观、抒情、情感的流动、憧憬、神秘感等特征。然而,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和文学的大量涌入以及经济大潮的冲击,浪漫主义文学由“在场”到“缺席”,以致到“终结”,“尤其是1985年之后,浪漫主义受到现代主义的强大挑战,受到商品经济大潮、世俗化追求的猛烈冲击,在夹缝中生存,备受冷落,更加飘散游移。浪漫主义的尴尬处境让‘在场论’者找不到更多文本支撑,也看不到振兴的希望,坚持既已困难,‘终结’论就此产生”*石兴泽、杨春忠:《转型时期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页。。新时期以来影响巨大的先锋文学的叙事圈套、新写实小说的“零度叙事”,以及王朔的消解崇高、追逐世俗、理想放逐都构成了对浪漫主义文学的致命一击,是对浪漫主义精神的一种解构。
曹文轩在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现象的描述中,以“浪漫主义的复归”来指认20世纪80年代的的文学,而他在对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的研究中,则用了“激情淡出”来表达,这足以说明浪漫主义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到世纪末的命运。何以如此?曹文轩分析说:“文学失去激情,是因为时代在失去激情(在谈到时代失去激情时,我们分析到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这个时代在面对一段激情反复洗劫而显得穷困潦倒的历史之后,对激情本能地产生了拒斥心理。一个是这个时代在金钱终于成为上帝而产生社会性拜金主义,生活滚滚不息,劳心劳力,再也难以有剩余精力产生激情)。然而,中国文学失去激情的原因,远不止‘时代’制约与需要这样一个原因。在这一部分,我们将看到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原因是纯粹中国的,是特定的。这个原因的揭示,将提醒我们注意:中国文学失去激情,乃是有着历史文化的缘由的。这个缘由使中国文学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更容易失去激情。”*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7页。曹文轩进一步分析中国传统的人生态度“大致可以归纳为:去激情,走淡泊。也可说是弃动择静”,“它一方面讲‘克己’,让人自我压制,另一方面则用平和缓解激情”*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7—268页。。而文学一旦失去激情,便和浪漫主义相去甚远。也许正是因为新时期文学中浪漫主义文学的不发达,所以,曹文轩格外看重张承志作品的浪漫主义特征:“当大量作家不论在政治态度上,还是在人生态度、生活态度、叙事态度上,都对激情不再抱有情趣,而纷纷背离,走向中年的稳重与老年的平和时,惟独张承志却一如既往,执拗地不肯走向‘成熟’,反倒愈演愈烈地倾倒于‘血性的’青春状态。这是一个颇为壮观的奇迹。”*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7—273页。20世纪90年代以及其后的21世纪文学,应该重振张承志式的浪漫主义激情。
总之,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是十分复杂的,对其进行价值估衡,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我们可以进行总体审视,更应该分类梳理。限于篇幅,更为详尽地梳理它的复杂表现,将在另文中完成,这里只能从略了。
OverallEvaluationofChineseModernandContemporaryLiterature
Wang Weip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81)
How to evaluate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since the Republic? How to evaluate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se are huge and complicated problems. To these problems, writers and scholars often stick to their own opinions. However, to explain convincingly, there must be a holistic background and a macro perspective.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the past 68 years must be compared with the earlier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and even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otherwise it would be very hard to give a clear explanation. An analytical, structural and holistic integrated coordinate system must be constructed so that we can make a relevant evaluation of the literature which covers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Meanwhile,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ith diverse classifications must be treated differently and specifically. If we regard influence as a measure of literature, the achievements of modern literature are more advantageous than those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because modern literature takes longer time for acceptance, discussion and study. The ecology of literature since the new period is diverse and complicated, so we can make an overall evaluation and should even make an evaluation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Otherwise, it would be a hastily-generalized evaluation.
modern literature;contemporary literature; literature in the new period;overall evaluation; evaluation according to classification; integrated coordinate
I206.7
A
1001-5973(2017)05-0001-1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7.05.001
2017-09-03
王卫平(1957— ),男,吉林长春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学价值评估体系的重建与文学价值新探”(11BZW025)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李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