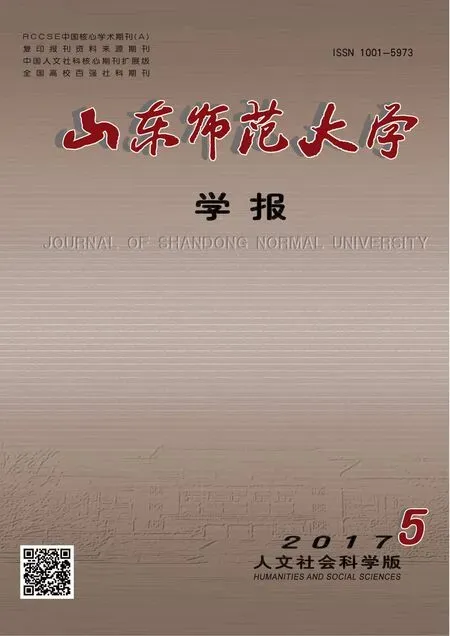新生代小说家游戏性历史叙事研究*①
张琴凤
( 山东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
新生代小说家游戏性历史叙事研究*①
张琴凤
( 山东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
新生代小说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90年代在大陆文坛产生广泛影响的青年作家群体。他们反叛、颠覆文学传统,以“游戏”(即幽默轻松、自由虚构)姿态对历史进行个人化解构叙事,颠覆传统宏大历史叙事,以此建构新的历史观和历史叙事形态,即追求个体自由的自我历史叙事。后现代的解构、颠覆和个体生命、人性的彰显是新生代小说家游戏性历史叙事的核心精神。新生代小说家游戏性历史叙事主要表现为戏仿、反讽、拼贴等多元形式,其价值在于解构宏大历史叙事,将叙事从传统的压制下解脱出来,开创新的个人化历史叙事模式。但是,游戏性历史叙事应避免陷入无限制的形式狂欢和虚无主义,要考虑社会接受性和文学审美性,形成一种具有自身规则和限度的严肃性游戏历史叙事。
新生代小说家;历史叙事;游戏性
一、“游戏”的概念与价值
“游戏”是西方文学艺术和美学的重要概念。从古典主义游戏观到现代、后现代游戏说,游戏的概念和内涵在各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古典主义认为游戏是一种美育,它具有教育功能,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如柏拉图认为游戏、文学、诗歌都是一种教育方式,游戏能使人变得完整和谐。*[古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300-309页。康德从美学、艺术等角度指出游戏具有自由性和非强制性,它追求快乐舒适的享受,审美的游戏通过主观感觉和想象力实现教育目的。*[德]康德:《判断力批判:审美判断力的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50、179页。席勒从人学和美学角度将古典游戏观发展成熟,他认为游戏是一种美学教育,它将艺术美的娱乐和教育的严肃相结合,追求完整全面的人,以实现人的感性和理性统一的自由。*毛崇杰:《席勒的人本主义美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7、190页。现代、后现代游戏观分别从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文化学等角度阐释游戏的多元内涵。加达默尔指出:“游戏的存在方式就是自我表现(Selbstdarstellung)。而自我表现乃是自然的普遍的存在状态(SeinSaspekt)。”*[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139页。他从存在方式角度阐释了游戏本身就是认识和意义的观点。胡伊青加从文化学、史学层面指出:“游戏是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这种活动或消遣是在某一固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的;其规则是游戏者自由接受的,但又有绝对的约束力;它以自身为目的并且伴有一种紧张、愉快的情感以及对它‘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意识。……我们大胆地把‘游戏’称为生活的一个最根本的范畴。”*[荷兰]J.胡伊青加:《人:游戏者——对文化中游戏因素的研究》,成穷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页。他从人的本体论角度指出了人类身份角色中的“游戏者”特性和人类社会文化中的游戏性因素,从而阐明了游戏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游戏”在后现代语境中被赋予了更多新的内涵:解构传统的宏大叙事规范,追求主体自由的个人小我叙事;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下单一化的宏大意义,强调个体叙事的多重意义;个人生命和真实人性成为叙事的核心。在后现代历史叙事中,游戏承担了后现代主义消解意义,否定历史真相和历史必然性的多重解构功能。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很少有游戏性的文学观,文以载道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是文学的主流传统,它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性,文学成为某种社会思想、政治观念的反映和表现。为艺术、表现个人自我的文学始终处于边缘,很难成为文学主流。启蒙国民、救亡图存、政治革命等各种社会要求强化了文艺的社会服务作用,而弱化了文艺自身的审美特性,忽略了作家个人的主体性表现,作家的审美经验大都依附于宏大主流话语。具体到历史叙事上,作家们对历史的书写大多呈现为特定时空背景下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宏大历史记忆,历史叙事变为对宏大历史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具体化阐释。在此,历史成为官方、宏大的群体性历史,拥有单一性的话语霸权,个人被淹没其中,失去发言权,个体生命的复杂历史体验和历史真实被遮蔽、忽略、压制,历史叙事变成单一化的宏大历史叙事。但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使政治、经济发生迅速转型,中国都市化、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及政治意识形态的淡化、宽松,使90年代的中国形成以商业消费为主的大众文化语境,这引起了文学、艺术领域的巨大变化。西方文学思潮(如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大量涌入中国,中国文学开始出现了多元化的文学观。中国文学从单一化的集体话语中逐步解脱出来,开始进行多元化、个体化的文学实验,传统主流的社会文化成规、宏大历史叙事成了作家们解构和颠覆的对象。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90年代在中国大陆盛行并掀起研究高潮,而90年代正是大陆新生代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因此后现代主义成为大陆新生代小说产生的重要文化背景。此外,80年代的先锋小说、新生代诗歌所倡导的后现代文学实验,如元小说、叙事圈套、叙事迷宫、游戏手法也为新生代小说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资源。中国大陆新生代小说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90年代崛起于大陆文坛,主要包括韩东、朱文、毕飞宇、李洱、吴晨骏、鲁羊、述平、张旻、刁斗、邱华栋、刘继明、何顿、李冯、东西、鬼子、荆歌、艾伟、罗望子、王彪、红柯、叶弥、魏微、李大卫、李修文、张生、须兰、朱文颖、丁天等人。新生代小说家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和中国多元化、实验化文学语境的影响下,开始彰显自身个人化的文学立场,反叛、颠覆文学传统,与前代作家断裂,追求前卫的文学实验和新奇的叙事形式,以多元化、个体化的开放包容思维和新型审美观念实现了文学观念的裂变和重构。具体到历史叙事上,就是以“游戏”(即幽默诙谐轻松、自我表现、自由虚构)姿态对历史进行个人化解构叙事,颠覆传统宏大历史叙事,追求后现代解构色彩的游戏性历史叙事,强调叙事的主体性,以此建构新的历史观和历史叙事形态,即追求个体自由的个人化、小我化历史叙事。后现代的解构和个体生命的彰显是新生代小说家游戏性历史叙事的核心精神。
新生代小说家这种游戏性历史叙事消解了历史所谓的客观、真实性,强调历史的主观叙事性和虚构想象,将客观的历史再现变为主体的游戏行为,所谓的历史已成为作家自我主体的主观想象和叙事游戏。“小说将根深扎在历史文献之中,总是与历史有着亲密的联系。然而与历史不同的是,小说的任务是将我们心智的、精神的以及想像的视野拓展到极致。”*[意大利]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柯里尼编,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68页。可见,新生代的历史叙事以其主观想象的自由和虚构而具有了后现代的“游戏”性。新生代小说家的游戏性历史叙事还呈现出作家深层的生命哲学观和人生态度。他们认为游戏是作家回归文学自身,回归生命主体自我的一种自由精神。基于此,新生代小说家摆脱了文学的社会性、政治性、商业性等外在束缚,而进入一种较纯粹的个人化层面,开始关注文学自身,开始思索个人眼中的历史、世界、生命、人性的本质所在。游戏性历史叙事使新生代小说家摆脱了传统历史的重负,重构了个体自我的历史观和历史叙事形态,体现了作家超越文学传统、探索自身特色的一种努力。
新生代小说家游戏性历史叙事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使文学摆脱了宏大历史叙事的社会功利性和政治虚假性,使文学回归自身的艺术审美性,回归自我生命本体和自然人性。个人的生命和复杂真实的人性欲望不再被宏大话语排斥压制,而得以强调和彰显。个人不再是历史叙事中被动的沉默者,而成为历史叙事的主体和主动言说者。新生代小说家通过游戏性历史叙事追求一种自由张扬、特立独行、反叛传统的自我生命意识和个人化历史真实,揭示了另一种曾被官方遮蔽、压制的历史真相,提供了言说历史的新方式。可见,后现代的解构、颠覆精神和个体生命、人性欲望的彰显已构成新生代小说家游戏性历史叙事的重要主题,这一主题使新生代小说家颠覆并超越了官方僵化的文学传统和宏大历史叙事,形成了回归生命本体意识和自然人性、追求个体精神自由张扬的历史叙事伦理。另一方面,这种游戏性历史叙事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观,即历史的本质是一种轻松有趣的文学叙事,充满个人主观化的自由虚构和想象,不同的叙事主体产生不同的历史,纯粹客观的历史真实是不存在的。这种游戏性历史叙事观颠覆了传统文学中单一化的严肃的历史真实观,使中国文学具有了个体虚构的自由性、多元开放性和轻松幽默性,开拓了中国文学创作的新路径。
总之,新生代小说家的游戏性历史叙事在反叛传统历史真实观、张扬自我、关注个人的生命人性等层面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促进作用,使中国文学重新发现个人的存在,开始重视个体生命,追求历史的个人化想象和自由虚构。这种游戏性历史叙事主要通过戏仿、反讽、拼贴等多元化形式得以表现。
二、游戏性历史叙事的表现形式
(一)谐谑化的戏仿
戏仿(Parody)又称戏拟或仿拟,是源自西方文艺批评的一个概念。美国学者吉尔伯特·哈特对“戏拟”的界定是:“讽刺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是通过扭曲和夸张来进行模仿,以唤起人们的兴致、嘲弄和讥讽。”“……讽刺家取用一部现成的作品——这部作品原是以严肃的目的创作出来的,……他把一些不一致不协调的观念掺和进作品,或者把它的美学技巧加以夸张,使这部作品和这种文学形式看起来滑稽可笑。”*[美]吉尔伯特·哈特:《讽刺论》,万书元、江宁康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8、12页。
戏仿是后现代游戏叙事的重要策略,它是对前人文本(即源文本)的游戏性模仿、重新改写和再创造。戏仿文本作为一种衍生文本,它是源文本和戏拟文本的复合体。戏仿的复合性和派生性使其具有了互文性特征,戏仿文本和源文本之间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而差异、对抗和革新则是其主要特征。在戏仿叙事中源文本一般为经典历史文本,其价值观念和艺术形式具有典型性和权威性,而戏仿文本则以幽默戏谑的滑稽模仿对源文本进行嘲弄、讥讽,解构其神圣性和严肃性,揭穿其宏大叙事的虚假性。戏仿从当代人的个体生命体验出发,重新解读历史文本,表达现代人对历史的不同理解,揭示历史叙事的新型目的和意图,以实现对前文本的改造、演绎和新编。中国新生代小说家的游戏性历史叙事吸收了戏仿的观念和策略,以诙谐幽默的戏仿叙事颠覆了源文本的经典权威,重构了当代人的戏仿历史文本,实现了对经典历史的重新诠释和现代性书写。
李冯的历史戏仿小说主要是对中国经典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名人传记的重新改写。作家以戏仿的手法将孙悟空、武松、孔子、牛郎、卖油郎、徐志摩、庐隐等经典历史人物现代生活化和世俗化,赋予古典人物现代气质,借古人的外衣表现现代人的生存现状,如情爱、金钱、权力、人格等,揭示古典精神(如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等)在现代的衰落悲剧,并赋予它新的现代意义。李冯通过对前文本自由随意的戏谑模仿,描写了众多荒诞虚构的现代故事,超越了人们对古典文本的常规阅读方式,打破了古典故事的原有统一性。至此,传统的古典历史文本被作者加工改造成一些后现代的技术化故事,融入了作家的主体想象,具有很强的解构性。
小说《另一种声音》戏仿的是古典名著《西游记》,小说中孙悟空取经归来后生活无聊琐碎,除了打水吃饭就是在水帘洞睡觉。他睡醒之后丧失了神奇法术,以至于变成女人后无法返回原形,被强盗抢去做新娘,后又成为名妓,最终变成老秀才吴承恩的女仆。多年后,她又在长途跋涉的行走中变为一个现代社会中穿西装、坐出租车的普通世俗男人。小说跨越漫长时空,对孙悟空形象进行了颠覆性的世俗化改写和重构。
作者借对《西游记》和吴承恩生平经历的游戏性模仿,嘲讽解构了神话英雄孙悟空,将其从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英雄还原为具有七情六欲的市井俗人,弱化了他的古典英雄精神,突出了他的现代世俗意识。如小说中,孙悟空失去了曾经的辉煌荣耀,金箍棒、斤斗云、七十二变都失灵了。他变得渺小懦弱无能,要靠猪八戒的儿子护送他回花果山。此外,他在现代社会中也无法生存,失忆、聋哑伴随他的生活,虽然他通过阅读吴承恩的《西游记》而恢复了活力,但其本身却遭到了异化。他由一只猴子变成了一个穿西装的现代男人,这种异化暗喻了现代生活对古典英雄精神的瓦解。小说通过虚构孙悟空取经归来后各种离奇、古怪遭遇,揭示了孙悟空逐渐世俗化的过程,这种世俗性颠覆了孙悟空身上的古典神性,还原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个体生命形态。
李冯通过想象和虚构对古典西游故事进行戏谑化的模仿,解构了传统经典历史叙事的神圣性、宏大性,以一种个人化的世俗“小叙事”祛除了孙悟空身上的神性,将其还原为世俗中人,呈现出其生存奔波中的无聊、苦闷和心酸,实现了新生代作家对古代历史文本的改写与重构。
小说《我作为英雄武松的生活片断》以古典名著《水浒传》《金瓶梅》的故事为戏仿对象。小说通过解构武松等传奇英雄,消解了古典英雄理想,反向表达了古典英雄主义在现代社会失落的遗憾以及现代人对英雄主义的怀恋情绪。小说以“梦中的老虎”、“嫂子潘金莲”、“景阳岗”三段叙事为基点,摆脱了古典文本《水浒传》中的宏大历史场景,小说中的宋江化身为小人,武松由“英雄”变成借酒消愁的醉鬼,而打虎则成了其酒醉之后的即兴游戏。李冯通过对宋江、武松等传奇英雄的贬低和俗化,解构了古典英雄精神,实现了对源文本的戏仿和嘲讽,揭示了英雄主义在现代社会的失落和虚幻,以及现代人的怀疑主义情绪。作者借古典英雄的衰颓,呈现出现代社会中普通人的渺小、平庸和猥琐,这是对古典英雄的非神圣化、非英雄化、世俗化描写。李冯用原文本《水浒传》中的正义英雄武松反衬戏仿文本中的俗人武松,暗喻讽刺了现代人的精神卑微和孱弱。
现代和古代相比是缺乏英雄、缺乏信仰的年代,人们拥有的只是当下世俗生活。李冯以后现代的历史戏仿小说解构了古典历史中的神话英雄、传奇英雄和浪漫英雄,祛除了他们身上的神圣性、崇高性,还原他们平庸的世俗本性。这暗含了作者对神圣文化、英雄文化、理想主义、崇高道德的消解与颠覆。
新生代的历史戏仿小说以嘲讽、谐谑的手法戏拟了中国传统的历史文本和民间传说,以当代人的思想、情感去摹拟原文本中的人物、情节,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互文。作家们在对古代历史文本的模拟中,以游戏、嘲弄的笔调解构、颠覆了经典历史中人物和情节的神圣性,将神圣化事物世俗化、平庸化,重构了回归主体自我的个人化“小我”历史,呈现了自身对历史的新的理解。在这里,后现代的游戏戏仿形式并不是唯一目的,作家通过戏仿旨在探求历史的另一种意义,即在戏仿中借经典历史人物、历史故事的外壳书写当代人的生存、情感、人性、欲望,发现当下现实与古代的联系,因此,这种游戏性戏仿历史叙事最终完成了历史的现在性转换,发出了不同于传统的另一种声音。
(二)多元化的反讽
反讽(irony)作为西方文学批评的重要概念,可追溯至古希腊喜剧,是指“希腊古典戏剧中的一种固定角色类型,即‘佯作无知者’,在自以为高明的对手前说傻话,但最后这些傻话证明是真理,从而使对方只得认输。后来,这个词的意思变成‘讽刺’、‘嘲弄’”*[美]克利安思·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1949)》,赵毅衡译,《“新批评”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76页。。之后,反讽由戏剧角色而发展成修辞学里的一种辞格,是指语言表层所说和深层所指之间矛盾相反的嘲讽性修辞手法。随着文学理论的发展,反讽又被引入到文学创作中,被众多理论家如布鲁克斯、詹姆逊等作为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布鲁克斯认为反讽表现了诗歌自身矛盾悖论的特性,是诗歌中“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美]克利安思·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1949)》,赵毅衡译,《“新批评”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79页。,即词语、意象等与诗歌语境之间的相悖、冲突。后来,反讽从诗歌领域扩展到小说等其他文学领域,被认为是现代小说的基本要素之一。英国批评家D·C·米克形容反讽“既有表面又有深度,既暖味又透明,即(原文如此,引者注)使我们的注意力关注形式层次,又引导它投向内容层次”*[英]D·C·米克:《论反讽》,周发祥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年,第7页。。浦安迪认为反讽是:“作者用来指明小说本意上的表里虚实之悬殊的一整套结构和修辞手法。”*[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3页。反讽的主要特征在于包含矛盾对立的两方面,如形式和内容、表象和事实之间存在悖论,并通过这悖立冲突的两项呈现一种人生态度和哲学思考。
反讽在文学中既是一种叙述方式,也是一种叙述态度。它不仅表达语言修辞的意义,还表达一种生活态度和感觉方式。如表层意义是肯定而深层意义却是否定(反之亦然)的矛盾与悖立构成一种存在本质的冲突与对比,这种对比使文本超越单一性而具有了复调和张力。反讽中的两个悖立面在相互冲突中常常呈现出滑稽荒唐、调侃戏谑等喜剧性因素。反讽在喜剧的外观下蕴含了严肃的批判性精神,在嬉笑调侃的游戏形式中寄寓了作者对人类生存境遇和人生价值的深层探求。因此,表面的喜剧性和深层的悲剧感构成了反讽的内在张力。反讽的矛盾悖论既表现为言语层面,又表现为文本的情节、结构、主题等层面,基于此,反讽可分为言语反讽、结构反讽和情境反讽等多种类型,“反讽”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新生代小说家的游戏性历史叙事技巧。
新生代小说家的游戏性反讽历史叙事呈现出多元化形态,包括言语反讽、情境反讽等多种类型。言语反讽主要指语言表层和深层意义之间的矛盾,它通过语言自身的悖论性使读者产生阅读的陌生化与荒诞感,进而反思挖掘语言的真实内涵。情境反讽是指小说的情节设置或场景安排存在矛盾悖论和非逻辑性,比如崇高与卑劣、神圣与庸俗并存的情节场景。新生代作家李洱在其新历史小说《花腔》中广泛运用了反讽叙事*宗培玉:《站在地狱的屋顶上凝望花朵——李洱小说修辞解读》,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作者使用反讽解构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宏大革命叙事和政治意识形态。《花腔》中的言语反讽丰富鲜活且极具特色。比如对革命历史话语“托派”一词的反讽性描写,“他一开始也是嘴硬,拒不承认自己是托派,于是乎,他很快就被提溜起来,吊到了房梁上。——刚吊了一袋烟工夫,他就承认自己是托派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你乖乖地承认自己是托派,你就可以吃到一碗鸡蛋面条。’”*李洱:《花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5-16页。“托派”作为一个政治词汇,本义是指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左翼革命群体,由于它反对斯大林主义,因而被视为异己和叛徒而惨遭镇压。中国共产国际受苏联斯大林“肃托”模式影响,也把党内“异己人士”、“汉奸”、“叛徒”等定义为“托派”,因此历史上的“托派”是一种包含敌意的、遭遇悲剧命运的负面身份,而小说中的“托派”则是一个被歪曲的、是非颠倒的虚假概念,这从“托派”的产生过程中可以看出。暴力加怀柔,威逼加利诱,一个被冤屈的虚假托派就产生了。在此,托派的真实内涵与小说文本义构成了鲜明反讽,揭示了政治历史的畸形与荒谬。个人为了活命被迫屈打成招,放弃身份和人格,承认自己是“托派”是特务,暗示了政治权力对个体生命的践踏和扭曲。
医生白圣韬被打成“托派”后的一些“自我批评”式语言也有较强的反讽性:“我打心眼里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拿拾粪来说吧,……那些毛驴,口料已经一减再减,……肚子本来已经够空了,但是为了响应拾粪运动,它们有条件要拉,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拉,……可我呢,……却一点也不体谅毛驴,竟然还要求它们一直拉下去……阶级感情都到哪里去了,……难道你的觉悟还不及一头毛驴?”*李洱:《花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7页。在此,严肃的革命政治话语,如承认错误、响应运动、阶级感情、革命觉悟等词语与“毛驴拉粪”这类无聊庸俗的日常生活语言产生语境错位,形成强烈反讽,揭示了政治革命的谎言、暴力和对人性的控制异化。作者在此解构、祛除了宏大意识形态中严肃革命的庄严和神圣,还原了某些所谓的“革命”的平庸与世俗的本质存在。此外,小说还将大量的革命、政治、军事术语如“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量变寻求质变,穷则思变,谦虚使人进步,创造条件,水深火热”等用于平庸的世俗生活语境,并与表现私人龌龊情欲的粗俗话语,如“传宗接代,遍地撒种,把那女人弄到手”等混用,构成语言和语境的错位并置。革命话语在世俗语境压力下其严肃的革命本义和小说中的文本义(即私人情欲)产生矛盾悖离,形成言语反讽效果。在此作者以嬉笑调侃的反讽语言解构、颠覆了宏大革命话语的庄严、权威和价值。李洱在《花腔》中常以政治革命话语表现个人的世俗欲望和卑微情感,作家通过反语和语境错位等多种言语反讽形式实现了对官方宏大历史叙事的质疑和批判。
《花腔》除了狂欢化的言语反讽,还存在大量的情境反讽,即小说情节在不同时空叙述中呈现出不同形态,这些形态彼此矛盾对立,互相颠覆,进而形成情境的反讽。情境反讽的多层次对立性叙述使小说情节具有了多义性和张力,使读者产生多元立体化的阅读认知。小说中近代革命英雄邹容生前被捕入狱、被世人遗忘和邹容死后出名这两个情节相互矛盾对立,形成情境上的反讽。邹容在狱中时饱受折磨,骨瘦如柴,却无人对其进行营救,世人已将其遗忘。但邹容病死于狱中之后,世人反而开始宣传他的革命事迹,《革命军》也被争相再版或盗版。小说中邹容的死后成名并非因为世人对他革命精神的敬仰和崇拜,而是“多派政治力量都借炒作邹容之死来宣传自己”*李洱:《花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21页。。在此,革命者的崇高牺牲变成了政治集团利益斗争的工具,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和政治历史之间形成对立与冲突,个人在历史进程中被忽略、变形,得不到真正的尊重,这呈现出作者深层的反讽意图。
此外,白圣韬被打成“托派”“毛驴茨基”的整个情节过程,也因与毛驴有关而极具反讽意味。延安为给美国记者留下整洁的好印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拾粪运动”。人们响应党的号召,见粪就拾,很快就没粪可拾了。为了让人们有粪可拾,再掀拾粪运动新高潮,牛、羊、驴等畜牲们被盛装打扮上街游行。在唢呐、腰鼓队和舞狮子的欢庆声中,街上的粪也很快拾完了。这时,白圣韬发现马路中央还剩下几颗驴粪,就高兴地铲进粪筐。他以为自己正在响应拾粪运动,可是没想到这仅剩的几颗驴粪是给首长们预备的。当他面对拾粪组长的“你拾了,首长们拾甚么?”的质问时,他玩笑地说了句“毛驴还会再拉呀”*李洱:《花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4页。。正是他的这句玩笑让拾粪组长恼羞成怒,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第二天就偷了他的日记上缴给组织,他因此被定性为“托派”收审。在此,个体生命被强权政治压制、摧残,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最终成为官方权力祭坛的牺牲品。严肃的政治“托派”与日常庸俗的拾粪被阴差阳错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强烈的情境反讽,揭示了历史的荒诞性和偶然性,否定了宏大历史的神圣和必然。
毕飞宇的历史小说常以言语反讽呈现“文革”历史记忆。《玉米》以“文革”思维、“文革”话语进行个人化历史叙事,个人日常生活话语对“文革”政治话语形成了戏谑嘲弄,具有较强的反讽性。如把王连方与村里的女人发生性关系说成是“斗争”;把施桂芳怀孕时的干呕说成“作报告”,是“空洞,没有观点”的“八股腔”,要对其进行“批评”等*毕飞宇:《玉米》,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2页。。小说用“文革”严肃空洞的政治话语说明男女性关系、女人妊娠反应这一类的私人生理现象,产生了荒唐可笑的反讽效果。再如“阴历年刚过,施桂芳生下了小八子。这个阴历年不同寻常,有要求的,老百姓们必须把它过成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村子里严禁放鞭炮,严禁打扑克。……我们的春节要过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毕飞宇:《玉米》,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4页。。这里世俗的私人生活语境“施桂芳生下了小八子”对虚假高调的“文革”政治话语形成了反讽,使王连方“严肃”的“革命化”宣传变成虚张声势、滑稽可笑的荒诞闹剧,从而对“文革”政治话语的欺骗性、虚假性进行颠覆、解构。
新生代小说家以多类型的反讽历史叙事解构了传统宏大历史叙事,呈现出一种回归个体自我的游戏性历史叙事姿态。新生代小说的反讽叙事在调侃的叙述,嬉笑的态度和悖论的情境等喜剧性的表层下蕴含了作家对世界、人生、自我、历史的深刻批判与反思,因此反讽在精神特质上具有严肃的批判性。作者在戏谑性的反向嘲讽中揭示出历史存在的对立和悖论性本质,呈现出历史本身所具有的自我矛盾性,进而表达人类在面对这种根本性的矛盾和悖论时的痛苦与困惑。可见,反讽的喜剧性外表并未消解其深层的悲剧批判精神,但作为一种后现代的游戏性修辞技巧,反讽的使用毕竟有其限度。它有时表现出较强的负面否定力量,而缺乏正面的肯定和建构。克尔凯郭尔曾指出:“反讽家必然总是提出什么,但他以这种方式提出的是虚无”,“反讽是同虚无的无限微妙的游戏”*[丹麦]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汤晨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71页。。对新生代小说家而言,反讽是一把双刃剑。作家们在用它解构世界的同时,也要警惕将自己淹没于虚无。因此,为了减少反讽的负面否定效应,新生代小说家也积极探寻反讽的正面肯定作用,即通过反讽凸显自我主体精神,建构新型的文学理想和历史哲学观。新生代小说家游戏反讽的价值不仅在于颠覆解构,而且还从哲学层面揭示了游戏性反讽叙事的本质,即对生命存在和历史本体所具有的悖论、荒谬性的深刻认知,呈现了作家对历史本质的清醒洞察和深入反思。
(三)跨时空的拼贴
拼贴,也称拼凑,是西方后现代叙事的重要手法。法国文艺批评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指出:“语词(或文本)是众多语词(或文本)的交汇,……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拼凑,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Julia Kristeva, “Word, Dialogue and Novel”,in The Kristeva Reader, Toril Moie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86, p35.在此,拼贴是指多种文本、引语的拼合融汇,是对不同文本的再创造。它将不同视角、不同文体和话语的各类素材拼凑并置呈现作者的叙事意图。传统叙述强调文本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性、同质性,它是一种线性的逻辑叙事,而拼贴叙事则强调文本的断裂性、异质性和叙述的非逻辑性,它是开放的、碎片化的文本。拼贴抽空了历时性和时间性,使文本在共时性的层面上展开。拼贴不仅是一种表现手法,还是一种对世界的认知观念,拼贴揭示了世界本质的无序性、杂乱性和随机性。拼贴叙事使文学创作变成一种没有任何预设目标的随意性叙事冒险,表现在历史叙事中,拼贴解构了传统历史叙事的整体性、连贯性和统一性,而追求历史的片断性、断裂性和偶然性,它使历史叙事具有了后现代的游戏性特征。对中国新生代小说家而言,“拼贴”叙事在反抗、颠覆历史整体叙事的同时还呈现出后现代复调狂欢的游戏形态。复调和狂欢源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文本间性,是指文本内各自独立的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和多声部呈现,它强调的是不确定性、破碎性和混杂性。新生代小说家的狂欢化游戏叙事将不同文类、职业、地域的语言相互拼贴,使高雅与粗俗、神圣与卑微相融合,打破语言和叙述的单一类别,形成众声喧哗的杂语世界。
李洱的《花腔》是一个典型的后现代历史“拼贴”文本,正如作家所说:“这并非我一个人写的书。它是由众多引文组成的。”*李洱:《花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小说由不同人的口述、笔录、各种文章、录音、采访、谈话等看似杂乱无章的历史史料拼贴而成,在结构上分为两部分,即正文部分和副本部分,分别用@和&两个符号表示。小说的正文部分是由三个历史当事人“白圣韬、赵耀庆、范继槐”各自在1943年、1970年、2000年的回忆和讲述构成的,他们以不同的叙述声音跨时空的拼贴出了主人公“葛任”起伏多变的人生历史和生死之谜。小说的副本部分则是由众多人物冰莹女士、宗布先生、黄炎先生、孔繁泰先生以及外国友人安东尼先生、埃利斯牧师、费朗先生、川井先生的文章、著作,如《绝色》《申埠报》《无尽的谈话》《东方的盛典》等,以及各种史书记载、回忆录、采访录、报纸新闻、杂志摘录等组成的,是对正文部分的补充和说明。
“葛任”在小说中只是一个被叙述者,并未直接出现,他的历史是通过不同的叙述声音和文本而呈现出来的。小说打破了传统历史叙事的线性时间顺序和必然因果逻辑,在不同叙事者的讲述中将葛任的生死之谜、身世出生、文学创作、游行被捕、初恋爱情、日本学医、肺病之扰等各种琐碎细小的历史片断和当事人的故事散乱无序地拼贴组合在一起,突出了个人历史的偶然性、随机性和不可知性,实现了对宏大历史叙事的颠覆与解构。小说中的叙述者因身份、性情、目的各异,分别选择不同的叙述腔调来叙述葛任的历史,虽然他们一直强调自己没耍花腔,说的都是实话,但由于故事讲述时间和讲述故事时间的不同以及讲述者本人身份的变化,使得他们的讲述漏洞百出,充满了真实与错误、记忆与虚构、饶舌与谎言等各种矛盾。作家在此将不同的声音、文本拼贴在一起时,突出了各种叙述声音之间的重叠、对话和冲突,实现了历史叙事的复调狂欢和众声喧哗,进而揭示了历史的“花腔”化本质,即历史是一种经过人为加工、改造的个人化叙事,具有叙事主体的想象与虚构,不同叙事主体讲述出不同的历史,构成了各说各话的“花腔”历史。
历史的“花腔”化否定了所谓的历史真相。历史真相是不确定的,它充满了各种言说性和游移性,历史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学叙事。《花腔》中的“拼贴”不仅是一种后现代的游戏性艺术手法和叙事形式,而且也体现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即后现代的“游戏”性历史观。它颠覆了传统历史的整体化、统一化,凸显了历史的个体化、零散化,它消解了宏大历史的严肃性和本质性,突出了历史的“游戏”性、随机性和偶然性。
李冯的历史小说也大量运用了游戏拼贴手法。其小说缺乏现实的因果逻辑,具有很强的随意性、片断性。作者将各种叙述、抒情、评论、剪贴片断、断裂情节等杂乱拼贴在一起,形成众声喧哗的复调狂欢效果,如《我作为英雄武松的生活片断》在武松打虎、武松与兄嫂生活、武松被发配的各种故事片断中随意穿插进美国科学家的婚姻研究报告;《另一种声音》将西游故事、吴承恩生平经历、北宋灭亡、李师师、宋徽宗、吴承恩墓碑的考古调查和鉴定以及20世纪末的各种报告、杂志、影视等相互交织拼合,形成跨越千年的时空拼贴,打破了小说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凸显了小说的虚构性和对现实的隐喻性。作者以拼贴手法解构了传统历史的连贯性和真实性,使历史呈现出断裂性、无序性和平面化、碎片化的另一种存在状态。
李洱《遗忘》采用跨时空文本拼贴的手法,叙述了一群知识分子对个人身份的主动书写和重新建构的过程。小说中各种广告、文学论文、神话传说、历史考证和注释、图表图片、新闻报道等十几种文类的杂烩拼贴呈现出一幅后现代狂欢图景。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根据“灵魂转世说”发现自己在历史神话中的“原形”和“身份”,实现自己现实身份的重新建构。小说中当代世俗生活、中国历史神话和后现代文化背景通过跨时空的“拼贴”,形成了结构上的多元对话。
新生代小说家通过游戏性历史拼贴叙事颠覆、解构了传统整体性、统一性历史叙事,追求零散化、片断化的个人化历史叙事。这种跨时空的历史拼贴强调对传统主流历史的对抗色彩,呈现出复调狂欢和众声喧哗的风格,具有鲜明的后现代解构特征。
三、结论
综上所述,新生代小说家的游戏性历史叙事如戏仿、反讽、拼贴等,其实质都是对宏大意义的消解和对传统形式的解构。这种以后现代的颠覆和解构为核心的游戏性历史叙事反映了新生代小说家新的历史品格,即回归主体自我、追求独立自由精神的个人化历史叙事品格。其意义在于,首先,颠覆了传统虚假的历史元叙事,将叙事从宏大话语压制下解脱出来,获得一种新的社会、美学的合法性存在。其次,冲破了传统经典历史和官方历史的束缚,呈现了当代人对历史的重新认知,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强调主体自由和虚构想象的个人化历史叙事观,形成了个体自由的历史叙事伦理和美学态度。但这种游戏性历史叙事的后现代反叛和个人化想象也要有一定规则和限度,不能变成一种无限度自由扩张、随意书写的叙事形式狂欢,而应将形式和思想相融合,在游戏叙事的同时对历史、生命、人性等多元内涵进行深层拷问,凸显游戏性历史叙事的精神特质。
文学不是局限于文本的,它还应关注文本外的读者和世界。文学不是无规则、无约束的个人随意书写,应考虑到自身的社会接受性和文学审美性。保·瓦雷里指出:“只对一个人有价值的东西便没有价值。这就是文学的铁的规律。”*[法]保·瓦雷里:《诗,语言和思想》,袁可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851页。因而新生代小说家的游戏性历史叙事既要保持自身的思想、美学价值,又要有广泛的社会受众性,在游戏化叙事的同时,坚守自身的历史叙事精神和叙事品格。可见,游戏的本质应是严肃、深刻的,新生代文学要追求一种严肃的游戏性*刘永春:《在后现代性的地平线上——新生代小说论》,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5年。,单一强调游戏或严肃都是片面的。
ResearchonGame-likeHistoricalNarrativeofChineseNew-generationNovelists
Zhang Qinfe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The new-generation novelists in mainland China are those who were born in the 1960s-1970s and had a broad impact on mainland China’s literary circles in the 1980s-1990s.They rebelled against and overturned the old literary traditions, and broke away from the previous writers by making avant-garde literary experiments and pursuing novel narrative forms. Their way is to deconstruct and personalize history in a game-like style (i.e. humorous and relaxing, and free-fabricating), to overturn the traditional gr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construct a new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narrative form, that is, an individual free personal historical narrative form in which postmodern deconstruction and subversion, and the demonstration of individual life and human nature are the core spirit. As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new-generation novelists’ historical narrative, “game-like” style features the d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norms, diminishment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individual rules. The game-like historical narrative is mainly expressed in “parody”, “Irony”, “collage” and other diverse forms. The new-generation novelists’ game-like historical narrative subverted the gr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broke the shackles of old ideas, freed narrative form from the tradition, and created a new personalized historical narrative mode, which bears considerable significance. But this game-like narrative should avoid falling into the form of unlimited form carnival and nihilism, take social acceptance and literary aesthetics into consideration and form a serious game-like historical narrative with its own rules and limits.
new-generation novelists;historical narrative;game-like
I207.42
A
1001-5973(2017)05-0021-1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7.05.003
2017-08-05
张琴凤(1977— ),女,山东新泰人,山东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华人新生代作家历史文化品格比较研究——以中国大陆、台湾、马来西亚为例”(08JC751029)、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中国大陆和台湾新生代作家历史创伤叙事比较研究”(15CWXJ1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李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