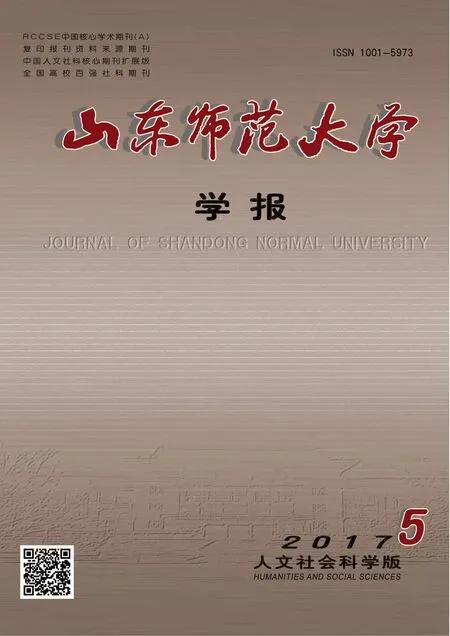教师实践智慧:缘起、内涵与养成*
曹珺玮
(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上海,200062 )
教师实践智慧:缘起、内涵与养成*
曹珺玮
(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上海,200062 )
教师实践智慧的提出,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对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识程度有关。它一方面是教师成长的应然选择,另一方面也是教育实践发展的逻辑必然。教师实践智慧是教师按照特定的目的与教育实践互动的过程,其中既凝结着德性,又包含着对具体教育情境中“度”的把握。教师实践智慧的养成是以“善”为根本追求,通过“践行”和“反省”,在自身与学校的联合行动中养成“实践智慧”。
教师实践智慧;教育理论;教育实践
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否定教师在教育中的重要位置。尽管“教师”这一群体正在遭遇着一定的角色(或身份)认同危机、专业性危机乃至教师教育性的本质丧失*有论者认为,教师在学校从事的活动并不都具有教育性。[英]大卫·卡尔:《教育意义的重构——教育哲学引论》,黄藿、但昭伟等译,台北:学富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7年,第19~24页。等问题的困扰,但是,作为“教育”活动的要素之一,“教师”不可缺失。否则,教育就不能称之为教育。进入新世纪,伴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推进,人们开始反思技术理性背景下教师实践智慧的培育和养成。从“教师”自身来讲,实践智慧以教师的存在为前提,它既渗入了“应当做什么”的价值关切,也包含“应当如何做”的理性判断*杨国荣:《论实践智慧》,《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因而是教师成长的应然选择;从教育实践上看,它又是教育实践发展的逻辑必然。笔者认为,教师实践智慧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关系的认识程度有关。本文旨在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演变的脉络中,寻找教师实践智慧的缘起,并尝试厘清教师实践智慧的内涵与养成。
一、教师实践智慧的缘起
(一)作为“落实”教育理论工作者的教师
改革开放之初,教育学亟待在新的历史机遇下恢复自身的知识生产机制和理论建设,从而为指导教育实践提供必要的理论前提。因此,教育学界把建设的重点放在了丰富和发展教育理论上,力求着眼于中国的教育实践,建构中国的教育理论,同时“引介”、“改造”古今中外的合理理论,并运用到教育实践中去。1979年,全国教育理论研究刊物《教育研究》创刊,其宗旨即是引领教育理论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吸取古今中外的学术营养”,“推进教育理论研究”*《教育研究》编辑部:《编者的话》,《教育研究》1979年第1期。。这里涉及的主要是如何从中国教育实践出发建构教育理论的问题。然而,随着教育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人们的认识停留在“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实践,正确的教育理论就能促进教育实践的发展”这一层面上。而且人们也相信,没有正确的教育理论,教育实践就可能是盲目的。换句话说,教师只要完全地“贯彻”已经建构好的教育理论,就能促进教育实践的发展。这一时期,作为教育实践主体的教师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自身主体性的存在,也缺乏对教育理论进行反思,更没有意识到教育理论走向教育实践的方式问题。
因此,教育理论如何走向教育实践的问题就开始凸显出来。人们开始意识到,教育理论并不必然能保证在教育实践上的“有效性”,也就是说,教育理论并不必然直接指导教育实践,甚至不能直接指导教育实践。*扈中平、刘朝晖:《对教育理论脱离实际的几点看法》,《教育研究》1991年第7期。因此,教育理论工作者开始反思自身在建构理论过程中的问题,毕竟此时教育理论的建构主要涉及教育理论基本范畴的问题,如教育起源、教育本质、教育目的、教育功能与价值、教育与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观以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众多议题。*瞿葆奎、郑金洲:《教育基本理论之研究1978—1995》,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教育理论还无法完全关涉丰富多样的教育实践,更无法替代实际工作者自己的思考、选择、运用和创造。围绕这个问题,《教育研究》杂志甚至还从1991年5月起开辟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专栏开展讨论。当时的讨论主要针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相脱离,主张教育理论工作者摒弃轻视实践的姿态,要深入到第一线去,总结和研究实践中的经验和问题。
(二)作为“转化”教育理论“中介”的教师
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了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的审视:有论者认为,实践哲学视野下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是本然统一的*周浩波:《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瞿葆奎:《元教育学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7~188页。李长伟:《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本然统一——从实践哲学的角度观照》,《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4期;《再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本然统一》,《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3年第2期;宁虹、胡萨:《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本然统一》,《教育研究》2006年第5期。;也有论者针锋相对地认为脱离才是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本然*郭元祥:《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的逻辑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易森林、李娟:《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本然脱离》,《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而更多的论者认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应该是统一的,但是教育理论并不能“直通”教育实践,因为二者之间存在诸多内在的差异。教育理论走向教育实践必须借助某种“中介”或“桥梁”。因此,人们开始了对教育理论向教育实践转化的机制探讨,比较典型的“中介”有教育模式、教育政策、教育评价、教育实验、教育思维、行动研究等。无论何种“中介”或“桥梁”,其实质都指向了“人”这一主体。也就是说,从这时起,在教育实践过程中,教师的主体地位开始受到重视,教师不再被视为“忠实”地“贯彻”教育理论的执行者,而是有自己思想和行动的教育主体。但此时人们重视教师的作用,仍然没有上升到教师实践智慧的层面,而是作为沟通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中介”的身份出现,这里仍然透露出某种“理论实践化”或“理论操作化”的技术观和应用观,而支配这种观念的仍然是一种技术理性。正如有论者所说的那样:“技术或应用科学乃是关于制作或生产某种东西并且服务于制作者目的的一种与偶性相联系并能为人们学习的知识”*洪汉鼎:《论实践智慧》,《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换句话说,这似乎意味着如果教师能够将已经建构的理论变得更具“实践化”和“操作化”,那么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是,随着人们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本身认识的不断深化,这种预设便受到了挑战。
(三)作为“实践理性”主体的教师
无论是“中介”还是“桥梁”,实际上都是以教育理论为立足点来探索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而在教育实践中,这种做法并未有效地缓解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紧张。既然中介并不是有效的方式,于是人们不得不回到事物本身,重新思考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自身的性质,以及教育理论作用于教育实践的方式。
事实上,人们发现,教育理论并非某种在性质、类型或层次上单一的知识体(a body of knowledge),而是由多种不同性质、类型或层次的知识构成的复杂体系。*程亮、杜明峰、张芸:《重心转移与问题转换——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研究之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3年第6期。教育理论本身也有性质和层次的区分,这也就意味着,一定的教育理论可能比其他一些理论更切近教育实践。在教育实践中,可以将切近教育实践的那部分教育理论充分运用,以便实现教育理论向教育实践的转化,诚如迪尔登(Dearden,R.F.)所言:“什么样的理论能够向教育实践提供最多的帮助,这是一个真问题;而教育理论是否能够提供帮助,这只是一个假问题。”*[英]迪尔登:《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唐莹、沈剑平译,瞿葆奎:《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56页。在探寻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实践理论”或“实践教育学”的概念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里涉及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是规范研究,即从“应当是什么”、“应该怎么做”等应然角度来探讨的规范研究;另一种立场则是从受教育者出发,认为“实践教育学”旨在研究受教育者怎样有效地理解和掌握教育“应当”,从而形成教育实践能力。*熊川武等:《实践教育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页。这些都表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的复杂性是与教育理论的复杂性密切相关的。然而,更不能忽视的是,教育实践也有自身的运行逻辑,教育实践处于实践主体、时间、空间及实践对象构成的情境之中,是“实践着的实践”;教育实践也有许多层次或角度的划分,有历史的、现实的角度,也有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层次,还有地域上的不同,任何单个的教育要素都不是教育实践。*石中英:《论教育实践的逻辑》,《教育研究》2006年第1期;李润洲:《实践逻辑:审视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新视角》,《教育研究》2006年第5期。
那么,怎样才能把教育理论的普遍性与教育实践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呢?人们对此又进行了诸多努力。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从研究者及其建构的“公共知识”,转向实践者及其内含的“个人知识”,寻求“实践中的理论”(theory in practice)*程亮:《教育学的“理论—实践”观》,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6页。。人们改变了过去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重新定位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教师实践的个人特征受到重视,如有人汲取波兰尼(Polanyi,M.)的缄默认识论,探寻教师个人知识的样态*石中英:《波兰尼的知识理论及其教育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年第2期;张立昌:《“教师个人知识”:涵义、特征及其自我更新的构想》,《教育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10期。;也有人借鉴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伽达默尔(Gadamer,H.-G.)的实践哲学,开掘教师的实践智慧或教育智慧*邓友超、李小红:《论教师实践智慧》,《教育研究》2003年第9期。。或许,从这时起,教师个人特征才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人们也才把视角投向了教师的实践智慧。诸如“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叙事研究”(narrative inquiry)、“反思性教学”(reflective teaching)等概念,都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回归教师实践经验、诉诸教师“实践理性”的初衷。
二、教师实践智慧的内涵
在教师实践智慧的内涵上,论者们见仁见智,进行了诸多富有智慧的解析,也产生了一些认识上的分歧,这在客观上丰富和发展了人们对教师实践智慧的认识。
何为“智慧”?鲜见众人认可的定义。这里仅列举一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说:“智慧显然是各种科学中的最为完善者,有智慧的人不仅知道从始点推出的结论,而且真切地知晓那些始点。所以,智慧必定是努斯与科学的结合,必定是关于最高等的题材的、居首位的科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75页。朗克尔(Runkle,G.)认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不仅知道实在是什么,而且知道它能是什么。他还能区分世界的哪些方面更有价值,以这样的方式行动,进而改进这个世界”*G. Runkle. Theory and Practice: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New York:CBS College Publishing,1985:208.。《辞海》上解释有三:“(1)对事物能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2)犹言才智,智谋。《孟子·公孙丑上》:‘虽有智慧,不如乘势。’(3)译自梵语Prajā。”*夏征农:《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1691页。洛克也称:“我对于智慧的解释和一般流行的解释是一样的,它使得一个人能干并有远见,能很好地处理他的事务,并对事务专心致志。”*[英]洛克:《教育漫话》,傅任敢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17~118页。显然,从这些认识中,我们可以对“智慧”进行如下的基本判断:(1)它必定内在于人的观念之中,并包含有特定的知识经验;(2)它必定体现着价值取向的善意,并以这种方式行动;(3)它必定作用于实践过程,并显示出机智的选择。认识(1)属于观念层面,区别于知识。观念的主体(或其表现形式)虽然是知识,但是奠基部分却是智慧。智慧是知识的基础,是用来解决重要问题的。只是能否转化为智慧,全赖于实际运用;认识(2)属于价值层面,表示智慧与狡黠的区别。智慧包含善的意图,也包含使人向善的意图,并且是以善的方式行动;认识(3)则是过程层面,区别于技术。技术的本质是普遍意义上的应用,而智慧的本质则致力于人类生存价值和意义的体验。更进一步,智慧不能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它表现为人的一种现实能力,即是说它体现为人的一种机智的选择。那么,教师实践智慧究竟指什么呢?
(一)教师实践智慧是教师与教育实践的互动过程
首先,从教师与实践的关系看,教师与实践的互动并非简单的适应与被适应的关系。教师一方面运用不同的手段,以不同的方式认识和理解实践;另一方面又主动地改造实践,使之合乎教师自身存在的需要。认识实践回答的是实践“是什么”的问题,这里更多关涉的是关于实践知识的问题;改造实践回答的是“应当怎样”的问题,更多涉及的是价值问题。纯粹科学是一种致力于寻求“是什么”的学科,它依赖于推理证明,它研讨的对象不是人能改变的东西。在这种知识体系里,主体和客体是对立的、不相干的,客体既不能影响主体,主体也不能影响客体。主体在研讨和考察其对象时尽量保持某种客观中立的态度,所使用的方法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法,以使之服从于严格的科学证明,因此这样的科学概念必然以不关联人的生存和价值的所谓客观的真理为其追求对象。*洪汉鼎:《论实践智慧》,《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而在实践智慧中,教师不仅关注“是什么”的问题,也关注“应当怎样”的问题。因为“是什么”追问一定程度上关乎“应当做什么”的回答,而“应当做什么”的问题则必须以“是什么”为基础。这种基于事实的理性追问,构成了教师实践智慧的内在特点,即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把握。其次,从教师自身看,教师也面临认识自己与改变自己的问题。教师实践智慧就其共性而言,大抵有“成事”的智慧和“成人”的智慧两大类型,实践智慧成长的理想状态是把“成事”的智慧与“成人”的智慧统一为同一过程。*杨小微:《转型时代教育者的生存智慧》,《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1期。
(二)教师实践智慧是“有意”的动作
教育必然包含道德的目的和有价值的内容,这就意味着教育旨在促进人的成长、进步。如果教育既不退步也不进步,或者退步,那么就不能称之为教育。因此,教育必然包含使人发展、进步并不断生长的积极的精神影响。“教育要对人类进行启蒙,即使人性中存在着邪恶,道德的教化和形成也是人性最伟大、最困难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任务。”*Randall Curren:《教育哲学指南》,彭正梅等译,彭正梅、徐梦杰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7页。教育是一个刻意塑造或者有意影响(人)的过程,它必然涉及到“干预”。而承担道德教化对人进行有意干预的就是教师。前面提到,教师实践智慧包含着“应当怎样”的价值追求,“培养人”理应包含在教师实践智慧之中。教师实践智慧所内含的目的内在地规定了实践和行动的方向,它规定了“应当做什么”的问题。而要实现“应当做什么”,就涉及实现的手段问题,也就是如何做的问题。在实践智慧中,“应当做什么”所内含的价值理性与“应当如何做”所涉及的工具理性,分别作为教师之于实践的目的和手段,彼此交融在一起。同时,“应当做什么”和“应当如何做”的问题也是选择的问题。选择是实践的动因,离开理智和某种品质也就无所谓选择。
(三)教师实践智慧包含对“度”的把握
适时地把握教育时机,是教师实践智慧的重要方面。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实践智慧体现为选择处于两个极端的中间,它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适度。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具体情境)之间是有张力的,在二者如何沟通方面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程式,这需要诉诸实践智慧。实践智慧在更为内在的层面上表现为对“度”的把握。对此,黑格尔(Hegel,G.W.F.)有着较为系统的阐释:首先,从名词意义上讲,质与量统一于度,存在由此得到完成。也就是说,“度”指一定事物的相关规定或相关方面之间适当而具体的融合。这种融合与统一既保证了事物性质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又使事物处于一定条件之下最合适的形态,超出了一定的限度,事物的性质便会发生变化。其次,从动词意义上讲,“度”表现为通过比较、权衡、判断等,作出合乎当然之则与必然之理的选择,从而使实践过程所涉及的各种关系获得一定境域中最为适当的定位,由此达到理想的实践结果。*杨国荣:《论实践智慧》,《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也就是说,教师在具体教育教学实践中,要准确把握“时”、“机”。“时”侧重于时间,“机”则关乎空间境遇。*杨国荣:《论实践智慧》,《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这种时机的把握,是建立在教师个人丰富扎实的教育理论知识、长期个人经验积累以及个人反省认知共同作用的基础之上。
(四)教师实践智慧是一种德性实践
有德性即是有实践智慧。德性与实践智慧在个体道德发展过程中共同作用,没有先后之分。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页。这种德性既包含本体论的意义,也具有价值的内涵:在本体论上,德性可理解为与人同在的内在规定;在价值论上,德性则呈现为一种善的品格。*杨国荣:《论实践智慧》,《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从这种意义上讲,实践智慧首先体现于教师个体的行动,实践智慧既与教师同在,又融合于具体教育实践过程,既表现为富有教育意义的意识,又包含一种缄默的行动机能。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明智不是只同普遍的东西相关,它也要考虑具体的事实,因为明智是与实践相关的,而实践就是要处理具体的事情。”*[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76~177页。其次,德性贯穿于教育实践整个过程。教育实践不同的环节、阶段相互交叉,呈现为一个统一、连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善应该贯穿教育实践的始终,而不是简单的、固定的、操作式的技术活动。
(五)教师实践智慧是教师的实践
作为教师实践智慧的表现形式,无论是审时度势还是彰显德性,都要通过作为认识与实践主体的教师来实现。首先,作为德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教师的实践智慧首先体现于个体的行动。在教师个体的行动过程中,实践智慧表现为内在已有的感知、体悟、经验和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自然结合,它既与教师同在,又融合于教师实践过程;既表现为内在的意识,又超乎言语。其次,教育实践本身不仅是个体性的活动,也是涉及个体之间关系的整体的活动。教育实践过程中需要个体之间在观念层面的理解与沟通。第一步要明确目标,也就是说教师在实践过程伊始就要就关于“应当做什么”、“应当如何做”等观念层面的问题进行沟通,即所谓的理论理性。没有一致的目标,不同的个体就难以开展共同行动。这种观念层面的沟通、理解,不仅关涉了理论理性,其本身也渗入了实践智慧。接下来,与观念层面的沟通相关的是行动过程中的协调和配合。教育实践是复杂的活动,教师之间可以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但最重要的是要维持彼此之间的协调和配合。教师的实践智慧也就是在这种具体的教育实践情境的沟通、协调、妥协中孕育的。因此,无论在观念层面的理解和沟通上,还是在实践层面的协调与配合中,处处彰显着教师的实践智慧。再次,教师的实践活动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无论是教师个体还是教师的合作,都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呈现彼此互动的关系,并统一在教育实践的始终。这或许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杜威(Dewey,J.)所谓的经验的“连续性与交互性”的标准。*[美]杜威:《经验与教育》,姜文闵译,吕达、刘立德、邹海燕:《杜威教育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23~335页。
三、教师实践智慧的养成
(一)以“善”为根本追求
从根本上讲,教育是一种使人向善的实践活动。亚里斯多德说:“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页。对于善的追求应该贯穿教育实践的始终,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作为目的或结果的善,对于教育内容,也应该以一种善的方式传递给学生。善的事物被分为三类:一些被称为外在的善,另外的被称为灵魂的善和身体的善。在这三类善的事物中,灵魂的善是最恰当意义上的、最真实的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2页。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灵魂的善的活动是合乎德性的活动,而教育实践活动也就是善的活动。这也就是说,一个有实践智慧的人就是能够分辨出善的人,因为“教育实践所追求的善不是局部的、分裂的,而是整体的、融贯的;不是外在的、功利的,而是内在的、自足的。只有具有这种总体善的教师,才称得上是智慧的或德性的教师”*程亮:《教育学的“理论—实践”观》,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17页。。
(二)以“践行”为依归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斯多德根据人类灵魂的功能,区分了五类知识类型:技艺、科学、实践智慧、智慧和努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69页。由此看来,实践智慧不同于纯粹科学,因为它研讨的对象是可改变的并且是人们可以做到的东西。对于它来说,更重要的是关于具体的特殊事物的知识以及经验,只有通晓特殊事物并具有丰富经验的人才能具有实践智慧。也就是说,实践智慧的本质则是践行,有实践智慧的人一定是乐于行动的人,即“知道去做”,而不仅仅是“知道如此”。伯明翰(Birmingham,C.)说:“实践智慧是处在特定时空所构成的情境之中,是与特定的任何事相关联的。在教育理论中,科学知识可以为实践智慧提供信息,但实践智慧绝不是教育理论的简单应用,因为教育情境是如此的复杂。”*Birmingham,C.,Phronesis:A Model for Pedagogical Reflection,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Vol.55,No.4,2004.再加上实践智慧既不能学习又不能传授,因而教师必须对具体情境进行深入的认知和思考。这可能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就是善于正确考虑的人”的原因了。也就是说,在教育实践中,实践理性意味着不能简单地“贯彻”或“应用”某种先在的教育理论,而应该视自身情况,根据具体的教育情境,做出理性、明智而又适合的选择。
(三)以“反省”为手段
教师实践智慧是在教师个体的道德实践和其他主体的互动中形成的,在具体教育实践过程中,需要教师主动反思。有研究者把教师反思的内容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一般性和相关的背景性问题层面;二是具体性和确切性问题层面。前者主要包括教育教学的目的、目标和价值观、学生观、师生观等理念层面的问题,以及教师自身所拥有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基础等。后者主要指教育教学目标和教师的现实关心与特别关照,尤其是与课堂内的事件紧密相关,包括课堂内的行为选择、方法选择、多方互动策略选择以及判断等。*张立昌:《试论教师的反思及其策略》,《教育研究》2001年第12期。概括起来,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理论理性反思与实践理性反思。杜威也对反省思维进行了分析,认为反省包含观察和暗示,观察到的事实与观念是相关的,观察到的事实称为资料,资料和观念是所有反省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两个因素的存在和保持分别依靠观察和推论。观念的形成需要由现时实际观察到的情境来核查,观念形成后需要由行动来核查。他还分析了反省的五个阶段:(1)暗示,在暗示中,心智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法;(2)使感觉到的困惑理智化,成为有待解决的难题和必须寻求的答案;(3)以一个接一个的暗示作为导向意见,或假设,在搜集事实资料中开始并指导观察及其他工作;(4)对一种概念或假设从理智上加以认真的推敲;(5)通过外显的或想象的行动来检验假设。*[美]杜威:《我们怎样思维——再论反省思维与教学的关系》,姜文闵译,吕达、刘立德、邹海燕:《杜威教育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25~129页。这就意味着教师要在亲身教育实践过程中,充分利用个人现有经验,不断学习典型,主动深入专家型教师或其他优秀教师的教学场景,领悟他人的实践智慧;同时通过自我诘难,筛选并淘汰不良的行为习惯;教师还要主动与他人沟通,挖掘个人实践背后的理论支撑,并对此进行必要的辩护。对于学校来讲,通过必要的制度安排和环境创设,促进教师理论学习与实践改进共同体的达成,并使之日常化、制度化。
(四)以“联合行动”为保障
教师实践智慧可以使教师作为真正的“教育”者,对自身、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有清醒的意识。如果没有实践智慧,教师就难以很好地理解教育的本质问题,也就无法清晰自身在其中的角色和任务。联合行动是一种可能的手段,它包括教师自身与学校两个层面。首先,教师要有一种统一的活动。所谓统一的活动,用杜威的话来说就是兴趣——真正的兴趣是自我通过行动与某一对象或观念融为一体的伴随物,因为必须由那个对象或观念维持自我主动的活动*[美]杜威:《教育中的兴趣与努力》,任钟印译,吕达、刘立德、邹海燕:《杜威教育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66~167页。。也就是说,任何外部强加给教师的措施对教师来说是无用的,对养成教师实践智慧更是缘木求鱼。诚如杜威所言:“努力意味着自我和所要掌握的事实或所要完成的任务之间的分离,并引发一种习惯性的活动的分裂。”*[美]杜威:《教育中的兴趣与努力》,任钟印译,吕达、刘立德、邹海燕:《杜威教育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66页。这意味着教师如果仅仅为了完成某种任务、指示、指标而“努力”向它靠近,实际上是与教师实践智慧背道而驰的。教师实践智慧的获得与运用,无疑应该源于并内含于兴趣之中。这或许也是当下中小学教师感觉“累人”的原因所在。其次,学校是专门的教育机构,也是教育教学的共同体,在教师实践智慧上,学校应该发挥作用。学校要营造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教师自身以及教师之间能够进行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的沟通和融合,即便是在鲜活、变动不居的具体教育情境中,教师也能够默契配合。这种氛围也应该是一种统一的活动,这样教师才能够联合行动。更主要的是,学校不应该仅仅把这种联合行动作为目的和方法,还要考虑在它背后激发它的条件,通过对这种条件的把握,营造这种氛围。正如杜威在谈到儿童的兴趣时所说的那样,“就是要提供一个能够促成教育性的和发展性的环境,哪里出现了这种环境,教育所需要的唯一的事情就具备了”*[美]杜威:《教育中的兴趣与努力》,任钟印译,吕达、刘立德、邹海燕:《杜威教育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01页。。
Teachers’PracticalWisdom:Origin,ConnotationandDevelopment
Cao Junwei
(Faculty of Education,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200062)
Teachers’ practical wisdom is proposed largely from the awarenes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proposal is put forth because of the actual choice of the growth of teacher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logical inevitabi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on the other. Teachers’ practical wisdom is a process in which teachers interact in accordance with specific aims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both coagulating virtues and containing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the “degree” in the specific educational context.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practical wisdom takes “goodness” as the fundamental pursuit, and teachers develop “practical wisdom” through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in their joint operation with schools.
teachers’ practical wisdom; educational theory; educational practice
G40
A
1001-5973(2017)05-0113-08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7.05.012
2017-08-30
曹珺玮(1987— ),女,山东青州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时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