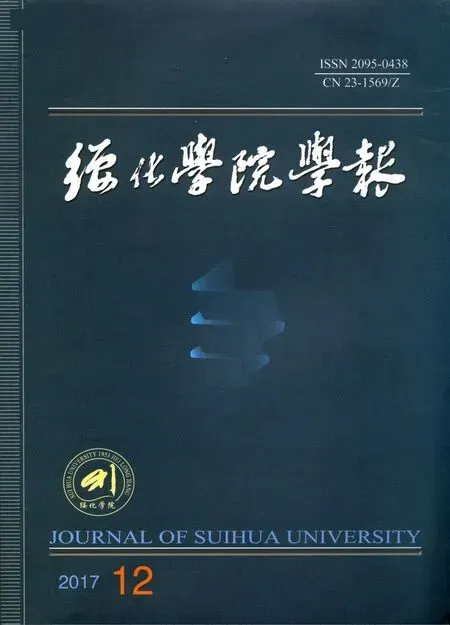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中方法运用及书写体例的抒情特质
吴 丹 吴有丽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吉首 416000)
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中方法运用及书写体例的抒情特质
吴 丹 吴有丽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吉首 416000)
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在物质文化史研究方面,沈从文运用文图互证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可以说是对“二重证据法”的发展。沈从文对文字的遮蔽与局限性的认识与反思,与他采取这种研究方法是有联系的。同时,沈从文运用综合分析的治学态度,与中国传统的不受现代学科体制限制的治学方法有相通之处。沈从文延续“有情”的书写,使得笔下的纹案、器物变得生动可感、充满生命力。
沈从文;物质文化史;文图互证;综合分析能力;抒情
一、“图文互证”法以及对文字局限性的认识
沈从文在物质文化史领域的研究方法是以文见物、文图互证。在对文献、实物、图案的对比研究中,沈从文发现物本身的历史性以及物之间相互的影响和关联。同时,通过对物的研究,发现物与文化的关系、与人的关系。有论者指出,沈从文物质文化研究的方法与王国维“两重证据法”是密切关联的[1]。然而二者又存在差异。沈从文对文字的遮蔽与局限性的认识与反思,与他采取“图文互证”的研究方法密切相关。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对沈从文的研究方法是有影响的。沈从文写道:“王静安先生对于古史问题的探索,所得到的较大成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新的工作指标。证明对于古代文献历史叙述的肯定或否定,都必需把眼光放开,用文物知识和文献相互印证,作新史学和文化各部门深入一层认识,才会有新发现。”[2](31卷,P321)《古史新证》里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是要运用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偏重于利用出土材料来解读纸上材料,如用甲骨卜辞证实《史记》殷商世系,用卜辞证明晚出的《山海经》《楚辞·天问》等“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3](P53),而“二重证据法”其地下之材料在今天看来恐怕主要仍然是甲骨、金文[4]。有论者认为沈从文的“图文互证”一方面是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一脉相承,另一方面是对“二重证据法”的修正、补充和发展[5](P28),是有道理的。
综观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他的方法是将文献、文物、图像三方面结合在一起的。有论者认为,沈从文的研究方法正是上世纪年代以来学界所广泛提倡的“三重证据法”,“将出土实物、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三者有机结合进行互证研究,在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方面开创的崭新的研究方法”[6]。例如谈到瓷工艺研究,沈从文认为:“从书本和实物两者间切实研究,分别提出报告和结论,才能荟萃处理”[2](28卷,P52),“让文物、图像、文献三结合,作点综合分析工作,有系统整理出来”[7](21卷,P305)。在沈从文这里,实物包括出土之文物和工艺品,实物的造型之美、图案之美是沈从文关注的重点。从造型与图案的发展变迁不仅可以得到历史性的发展印象,也可以得到共时性的比较。因此,在沈从文经纬编织中,“物”的范围已从传统的金石之器扩展到诸多器物上,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文字,而且包括器物的造型、纹案。“图文互证”的研究方法,是与沈从文对文字的遮蔽作用和局限性认识是相关联的。
我国历有“敬天惜字”的传统,焚烧字纸成了一种礼仪,说明文字早已被人赋予了非常神圣的意义[8]。中国儒家学派有“崇文抑画”的传统,如果将图像放在“文以载道”的历史语境中,由于它的虚指性,显然不能和语言命名相提并论,难以成就“文”一样的“载道”伟业[9](P28)。文字在中国历史中无疑是精英文化的凝聚,而文字之外的“无名”历史是被忽略的。沈从文曾经发现,通过文字可以连接历史,那么,“历史”在沈从文的观念里是什么呢?“一本历史书除了告诉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正的历史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沙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我们平时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7](11卷,P188)“历史书”作为特定时代下的产物,记载更多的是朝代递嬗、政权更替,而丰饶人类历史的文化以及真正的人生,却在另外一本大书里。作为人类心智外化的文字、器物、图案,在沈从文“有情”的关注下,具有别样的意义。对无名款的民间工艺品的注目,可以说是对“无名”历史的发现。沈从文对文物和工艺美术满怀热忱,而器物的制作者将自己的情感心智体现为器物的形态、图案之美,这些是不被包含在传统的研究视野中的。沈从文对器物观看的角度,在某一方面是颠覆传统的价值秩序,而企图起到“价值重估”的作用。对“物”的重新发现在沈从文的前半生已经表现出来,发展到后期,便是他自己所说的“从文物出发,来研究劳动人民成就的‘劳动文化史’、‘物质文化史’,及以劳动人民为主的‘新美术史’”[7](27卷,P245)。
文字不仅具有遮蔽作用,同时,也有自身的局限,在文学创作中,沈从文已经感觉到文字自身的局限性。对文字局限性的认识与他对图像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在《湘行书简》中,沈从文面对“如画”的风景,想将风景的形色用文字向新妇一一描绘,可他发现他描绘不出自然的声音、颜色。“这里小河两岸全是如此美丽动人,我画得出它的轮廓,但声音、颜色、光,可永远无本领画出了。”[7](11卷,P119)“在先一时我以为人类是个万能的东西,看到的一切,并各种官能感到的一切,总有办法用点什么东西保留下来,我且有这点自信,我的笔是可以作到这件事情的。现在我方明白我的力量差得很远。”[7](11卷,P119)面对可见可听的自然,文字作为表达媒介是有局限性的,于是沈从文用画笔来画。文字书写之外,呈现出他画笔下的风景。图画在沈从文这里,成为文字之外的另一种有效的表达媒介。翻阅沈从文1949年之后的信件,也可发现许多他对风景、器物的小画。因此,沈从文在物质文化研究中采用“图文互证”的研究方法是有迹可循的。“文字是固定的,死的,甚至是不可信的。而物是实在的,又是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用来研究它的发展和成就”,“得到十分明确的认识和结论”[7](24卷,P464)。“文献”作为文字,在文物研究上是有局限的,将文献与文物与图案结合起来,可以补足文字的局限性。
沈从文的这种结合文献、实物,重视文字、图案的研究方法与他重视的综合分析能力是有关联的。
二、“综合感知能力”和综合文物研究
沈从文运用联想的方法,将器物的发展与历史连接起来的研究方法,与他在文学创作方面所用的方法具有相通性。沈从文在给家人的信中多次提到“综合分析能力”,这种综合分析能力反映了他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方法又是与中国传统的不受现代学科体制限制的治学方法有相通处。可以说,沈从文的综合分析能力,使得他在文献、实物、图案中看到关联,不仅从对物的体悟中发现制物者的情感,也让他发现物的历时性演变以及共时性的相互影响。这种“综合分析能力”直接影响到书写体例。
沈从文将自己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工作称为“综合文物研究”[7](20卷,P301),而他所用的“图文互证”的研究方法,他认为是建立在综合分析能力之上。之所以称之为“综合”,可以从沈从文研究对象的选择上、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找到内在理路。沈从文认为自己埋头于“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之中,而这些都是杂文物。翻阅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卷,可以发现这些杂文物的具体所指。这里的“杂”,是相对于传统的金石之学以及同时代的学院派考古学而言。而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沈从文有一套自己的治学方法,即“图文互证”。沈从文在研究中,从实物出发,“给材料排排队”,结合文献,“物”的历时性的发展以及共时性的影响逐渐清晰明确。在这一过程中,涵盖了历史学、文学、工艺美术、图案学等等方面的知识,可谓广而博。沈从文在这种治学方法下,将目光投入到人类文化诸方面,且寄予了文化理想——即希求文化的发展,包括历史学、文学、美术、电影、戏剧、工艺品生产等方面。
1975年,年过古稀的沈从文,在家书中写道:“大致是经过了自我学习,总觉得从生物学和人类学来看,人这一万年以来,大致只充分发展了人对付人的机能,把对付自然的嗅觉、听觉和不能理解的一些鸟兽虫鱼的敏感慢慢的全失去了。”[7](24卷,P277)在这里,沈从文一方面强调运用听觉、视觉、嗅觉对自然的观察能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一方面将这种能力与“综合分析能力”并举。而这种综合分析能力首先又是建立在对自然的观察能力之上,且与联想能力、记忆力相关联。因此可以说,沈从文的这种“综合分析能力”一方面来源于对自然的感知,一方面来源于他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治学观念。
沈从文喜爱美术和音乐,都从对自然的观察开始。同时,他所受的文化影响也是这种“综合分析能力”生长的土壤之一。沈从文并未受过系统的学院训练,因此可以避免概念的先入为主。因此,沈从文能自由地在文学、美术、音乐之间畅游,不受“概念”的束缚。综合分析能力可以说既是对学科界线的突破,又是对人自身感知能力的注重。钱穆曾说:“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无[毋]宁是看重其相互关系,及其可相通合一处。因此中国人看学问,常认为其是一整体,多主张会通各方面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10](P4)在这样一种世风学风之下,读书人对各种学问多兼而治之。沈从文的治学态度是游离于现代学科分类制度之外的,这从他给年青人的信中可见出。“我觉得学专业能深入,有必要,但业余不妨放宽范围,各方面去接触,至少文化各部门能做广泛接触,生命会充实得多。和各种人事接触,也有同样好处。也有这种可能,即另外一种业余注意到一定时候,成就却会比原有专业的还大一些”,“没有更大的综合各部门成就能力知识,新的断代史、通识、文化史......通写不好的。”[7](21卷,P427)可以说,沈从文的综合感知能力、分析能力构成了他的治学态度,这种态度来自于前半生对生命的思考,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他后期转向物质文化研究,延续了这一治学原则。在综合分析能力的观念下,沈从文形成了以文见物,文物互见的研究方法。他强调文献、实物、美学意义、现实意义之间的融会贯通。
李之檀认为,沈从文有能力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正是因为他有在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知识的广泛性,与综合文物研究的能力分不开。“沈先生不仅懂得美术,而且懂得文学,他看了很多古代文献,还重视对图像的观察,同时也非常关心考古发掘的成就。知识的广泛性使他能够编写这本书,并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11](P294)这种综合分析能力使得沈从文能发现物之间的关联性,因此能作出许多预见性的推论,而且这些推论许多都被不断出土的文物而证实。1958年,沈从文看到一堆带孔的小方玉片。据他推测,这是汉代服饰一种,应该是金缕玉衣。这种葬服20多年后经被发掘出来,和他的推测一样。
那么,这种“综合分析能力”是如何在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研究的书写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呢?
三、综合分析的治学态度对书写体例的影响
沈从文的综合文物研究视野以及综合分析能力的研究方法,影响到物质文化史研究的书写方式以及体例选择。联想与记忆力,在沈从文的综合分析能力占据重要位置,这都直接影响到体例选择与书写方式。
首先,联想和比较的方法是沈从文综合分析能力的重要一环。沈从文运用联想和比较的方法,结合文献和实物对图案作细致生动的描写。沈从文不仅发现花纹自身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每个时代不同的呈现特征,也发现花纹之间的相互影响,同时,综合分析的能力,使得他发现花纹与文化、美学、文学等方面的联系。例如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的《战国青铜壶上采桑、习射、宴乐、弋猎纹》[2](32卷,P70)一文,并非是对服饰的直观分析,而是采用综合分析的方法,涉及到古代生活、文化的诸多方面。沈从文用文献互证的方法,分析了一个战国青铜壶上的采桑、习射,宴乐,用矰缴弋猎天空鸿雁的图案。首先,从图案分析入手,由此涉及到古代生活各方面的问题。从《左传》《国语》《尔雅》等文献,可得知高级丝织物已成为贵重商品以及蚕的种类和培养状况,这些都与当时的纺织技术有关联。沈从文认为青铜壶上所见的采桑图像,是极早有关蚕事生产图像之一,或本于《诗经》“女执懿筐......爰求柔桑”语意而作。这样,文学又与图像发生联系,由图像可知文学中具体形象所代表。分析习射和宴乐的形象,采用文图互证的方法,涉及到了古代生活、文化诸方面的问题。而且,这种通过联想的对比分析方法,不仅仅体现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其他关于物质文化的著述中也是贯穿这一研究方法的。例如,从铜镜的实物中,发现纹案的美感,除此之外,纹案中的扇子式样又对研究扇子实物的历史有用。
其次,记忆力也是沈从文综合分析能力的重要因素。联想的研究方法使得记忆更加深刻,记忆力的发展又与沈从文的呈散文的物质文化史书写相关联。沈从文综合实物、文献、纹案的研究方法,使得他能通过联想加深记忆。他常说这些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在自己大脑褶皱中无从忘记。这种通过联想得来的记忆力影响到行文体例。在时代动荡中,沈从文的研究资料经常散落——要么被抄走,要么被借走,下放干校时,他希望着手研究工作,但手边竟“无一本书,无一图像”[7](22卷,P465)。沈从文不得不凭借综合感知能力得来的联想、记忆进行书写,“也居然还能全凭记忆回想,写成两个约五百个图的文章”[7](22卷,P465),在极端孤寂中,“仅凭记忆,写写陈列中诸文物问题,性质与《谈文字》相近,方法多用叙事散文,重在它的发展和联系。”[7](22卷,P501)
这些因素,都影响到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的书写体例。沈从文说《中国服饰史研究》“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是有原因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香港出版之后,沈从文认为并“不算是什么‘中国服装史’,书店为宣传说是‘史’,不足信。只是个带试点性资料图书”[7](26卷,P339),沈从文宁愿称其为“服装资料”。“本来只是本试点资料,书店中却宣称为‘中国服装史’,不免使得我感到狼狈”[7](26卷,P349)。黄裳认为:“象这样的著作,过去的学人是常常称之为‘札记’的,水平高的就会成为小型论文的集合体。其间发生了有机的联系,得到贯通,就自然形成完整论著雏形。”[12]
再次,沈从文的综合分析能力体现在物质文化史研究的著述中,表现为抒情的写作方式。在书写方面,沈从文“说明本重在释疑理惑,为减少过于枯燥起见,又间或略作抒情叙述。”[2](30卷,P241)。汪曾祺说到沈从文的转业:“他搞的文物工作,我真想给它起一个名字,叫作‘抒情考古学’”[13](P191)。黄裳认为:“作者研究的对象时服饰,这就要求将形态万方、彩色斑斓的实物用文字再现在纸上。需要散文家的出色才能,不只是忠实的再现,还得写出事物活泼的情趣。”[12]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发现一批古丝绸织物,沈从文对龙凤大花纹彩绣衾被纹样作了分析。对花纹作细致生动的描绘,纹样似乎变得富有生气。沈从文的“有情”关注,得以在对“纹”的体悟与书写中得到延续。“有情”的关注,使得笔下的纹案、器物变得生动可感、充满生命力。
至此,沈从文通过对文字遮蔽性和局限性的认识,采取文图互证的方法,运用联想、记忆、对比的综合分析方法和抒情笔触,完成了对“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抒情写作。
结 语
1949年,沈从文试图在新的社会寻求新生。他“试一试把自己当成一株苹果树”,接枝、移植到新社会的土壤之中。他意识到“苹果树”可能枯萎、被砍伐,但也希求移植后的“苹果树”“重新移植,结点对下一代还有益的果子”[7](27卷,P6、7)。虽然土壤不同,气候有别,“苹果树”却依旧有自身的生命连续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沈从文运用以文见物、文图互证,这种研究方法可以说是对“二重证据法”的发展。沈从文对文字的遮蔽与局限性的认识与反思,与他采取“图文互证”的研究方法是密切相关的。同时,沈从文运用综合分析的治学态度,与中国传统的不受现代学科体制限制的治学方法有相通处。正是通过综合分析,运用联想、记忆等方法,沈从文延续“有情”的书写,使得笔下的纹案、器物变得生动可感、充满生命力。
[1]张新颖.“联接历史沟通人我”而长久活在历史中——门外谈沈从文的杂文物研究[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6):7.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8-32 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3]王国维.古史新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4]李锐.“二重证据法”的界定及规则探析[J].历史研究,2012(4):120.
[5]毕德广.以“物”见“文”:沈从文文物研究的成就和意义[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08.
[6]张鑫,李建平.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与三重证据法的理论与实践[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28.
[7]沈从文.沈从文全集(1-27卷及附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8]赵宪章.文学和图像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江海学刊,2010(1):185.
[9]赵宪章.语图传播的可名与可悦——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J].文艺研究,2012(11):28.
[10]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四部概论[M]//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11]王亚蓉.沈从文晚年口述(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2]黄裳.沈从文和他的新书——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J].读书,1982(6):48-50.
[13]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
I207.6
A
2095-0438(2017)12-0049-04
2017-08-16
吴丹(1991-),女,土家族,湖南张家界人,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湖南省2016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X2016B622)。
[责任编辑 王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