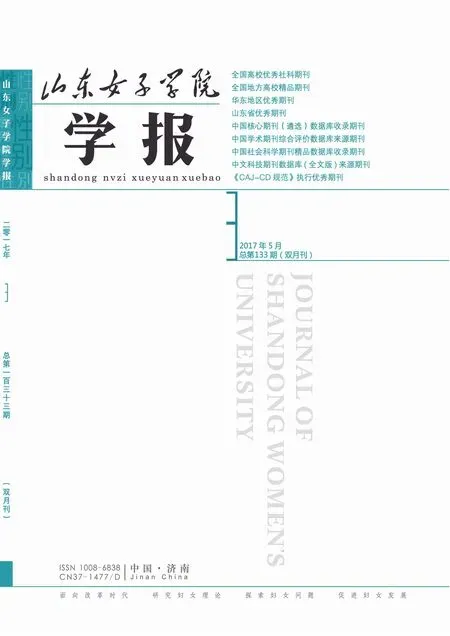暧昧的现代性
——论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身体书写与国族认同
王怀昭
(厦门大学,福建厦门 361005)
·女性文学研究·
暧昧的现代性
——论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身体书写与国族认同
王怀昭
(厦门大学,福建厦门 361005)
萧红在《生死场》中借着宏大历史叙事的结构框架,表现最底层的广大乡村女性的日常生活,反复书写她们被强暴、被殴打、被迫怀孕,以及生育过程中遭受到的种种苦痛的生命体验,力图揭示女性身体的性别困境,同时看到女性主义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既冲突又重叠、同构的关系。战争的破坏性力量让萧红自觉认同国家话语,作家的女性主体立场又使得她袒露战争中沉默女性的真实声音。
萧红;女性身体书写;国族认同;暧昧的现代性
萧红的小说《生死场》在发表之初,鲁迅于《生死场·序》中有着这样的评价:“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小说被解读为“民族寓言”。其后,刘禾在《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一书中,以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为例,检视了现代性在被译介的过程中国族建构如何形成,在文学批评的话语实践中,女作家的作品是如何被纳入国族范畴并得以合法化。她从“女性的身体”这一文化符码中挖掘萧红小说中对民族革命与性别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并进一步辨析民族主义内部性别权力关系的形成,从而突破了以往评论界对萧红小说的民族主义话语诠释。刘禾的观点对萧红作品的研究具有相当大程度的启发性,后来的评论者基本上都是依循她的解读思路继续展开,多数评论者认为文本中的女性声音与民族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民族主义掩盖和遮蔽了女性声音。然而,一味地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来解读文本,而不思考、进而厘清文本内部的杂音,只会导致《生死场》这一复杂文本的意蕴丰富性的流失。小说文本中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具有怎样的形态关系,在何种程度上对立、纠缠或同构?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为重新诠释《生死场》提供一个可供参照的向度。
与男性作家不同,萧红体悟到在残酷的战争中,民族国家话语并不能抹除女性永恒的性别困境,在由传统趋向现代的历史过程中,男高女低的性别制度依然存在。与其他女性作家不同,萧红把笔触伸到乡村,书写乡村女性的身体经验,怀孕、生育、身体被施压、毁形,斥责男性威权,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更可贵的是,她在小说中思考并突出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女性身体书写和国族认同,成为探讨《生死场》现代性内涵的两个必不可少的层面。
一、女性身体的性别化困境
童年的创伤性体验和被施压、遗弃,以及疼痛生育的生命体验让内心敏感的萧红看到作为女性的真实社会处境,她曾在《女子装饰的心理》中尖锐地指出在文明社会,“男子处处站在优越地位,社会上一切法律权利都握在男子手中,女子全居于被动地位”[1]。对男性来说,女性是“他者”,是被动的一方,是不可言说的黑暗大陆。萧红在她的小说中揭示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战争之际广大乡村女性所面临的无法摆脱男性威权、被无休止地役用、毫无自己的思想与意识的性别困境,从而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女性意识。女性的生命是沉重而残酷的,她们如衰弱的白棉,无法形成反思自身处境的能力,也就不能形成独立的人格。《生死场》中的女性在婚后开始诅咒男人,意识到“男人是炎凉的人类”[2](P45),可是除了王婆,她们谁也不曾想到要反抗,她们屈服在男人的威权之下,忍受着来自生活的重压、生育的疼痛,甚至连叹息都不敢发出。
于是我们在小说当中看到的不是女性面对男性的压迫而奋起的反抗,而是形形色色的乡村女性的灰暗人生,以及她们充满疼痛、不断被损害的生命体验,背后隐含了萧红对女性苦难人生的温爱眷注和尖锐批判。五姑姑的姐姐因难产而受尽生育的惩罚,金枝的分娩历尽艰辛,二里半的傻媳妇在怨恨男人的哭喊声中挣扎。王婆的三岁女儿小钟被摔死,小金枝被父亲杀害,金枝在进城之后遭到主顾的强暴……在萧红笔下,女性身体成为作家揭露女性性别困境的叙事符码,乡村妇女的身体遭受着农活的重压以及家务活的重担等种种日常暴力,而来自男性的肉体虐待和精神威压则更为内在地残毁女性的生命。没有寻到羊,二里半便把气撒在麻面婆身上,大骂:“混蛋,谁吃你的焦饭!”[2](P5)而麻面婆只是“惊惶着,带着愚蠢的举动”“她的心永远像一块衰弱的白棉”[2](P5),不曾想到要反抗。面对成业的怒气,“金枝垂了头把饭摆好”,不吭一声,可是对于被穷困逼疯的男人来说,金枝和女儿不过是被他嫌弃的累赘和私有财产,随时可以被当成商品出售:“把你们都一块卖掉,要你们这些吵家鬼有什么用……”[2](P54)最后,婴儿成为夫妻争吵的牺牲品,无辜地被男人摔死,结束了她短暂的生命。女人遭受着男人的欺凌,甚至在生育时都不能幸免。五姑姑的姐姐由于难产,“苦痛得脸色灰白,脸色转黄”[2](P43),丈夫对她的疼痛毫不怜惜,拿起身边的长烟袋投向她,后来又泼了她满身的冷水,而她“几乎一动不敢动,仿佛是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2](P44)。对于乡村男性来说,生育的女人对他们而言就是罪恶本身,女人只是他们泄欲的本质化对象和劳作的必备辅助工具。
以无家可归的女性身份写作的萧红,用细腻而敏感的笔致书写乡村女人苦痛的身体经验,于是,漂泊、流浪成为萧红作品中女性人物命运的生命底色;而辗转流离的人生体验成为萧红写作的情感动力,作家不断寻求被拘囿在性别化困境中的女性之人生出路。可是绝望而无助的女性要走到哪里去呢?王婆年轻时候嫁的第一任丈夫纵欲过度,因此她义无反顾地出走,留下她的孩子。可是此种出走不过是毫无意义的行为之重复,其结果是再置身于另一个男人的威权之下,继续过着身体被男人奴役的无爱生活,即使王婆后来再一次出走,嫁给赵三,可是女人的生存困境并没有得到本质上的改变。又如金枝,成业引诱了她的身体,使她未婚先被强暴;而当年盘转动,日本国旗插在山岗临时军营门前,为了活命的金枝离家到城里当缝穷妇时再一次被主顾强暴。可见,女性的悲惨命运并不会因为出走的虚幻光明前景或者年盘所象征的现代性时间之前进而得以突围,并发生本质上的转变。女人身体的困境并不只是来自家庭内男性的占有,更是来自女人之为女人本身的困境:让男人占尽便宜的性别规范下女人被作为物质一样的存在这一卑下身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萧红全面呈现了中国广袤土地上最广大乡村女性因陷于生育、疾病、衰老等惨痛身体经验而无法自拔、不能自主的身体困境以及难堪卑下的生存本相。反过来说,由于“身体是唯一可以被用来作自我表现的媒介”[3](P167),因此女性身体成为小说意义生产的场所,不断遭受残害、惩罚和损毁的女性身体以及女性所特有的生育经验构筑起萧红独一无二的文学世界,女性身体的无言诉说成为她们区分于男性,获得某种女性主体性的有效方式,至此,女性的声音得以浮出乡村大地的地表。
在萧红看来,女性的不幸不止来自她们无法突围的性别困境,还在于女性在这种男权的威压下被形塑被奴役后自觉不自觉地屈从、认同男权意识形态,并把这种奴役化状态内化为集体的无意识。她们既是受男权意识形态催逼的受害者,也是逼压其他女性,使之屈从于菲勒斯中心文化下的施虐者。在文本中,面对像刑罚一样的生育,乡村女性们咒诅着男人,却仍旧频繁地生育着孩子,从不曾想到要反抗。又如,金枝的母亲爱惜农作物甚于爱惜女儿,因为在农家,一棵菜或一株茅草都要超过人的价值。当金枝上城做缝穷妇,却被主顾强奸时,她那颗羞恨的心灵并没有得到来自周围女人的同情和安慰,一个秃胖子反而劝她习惯,因为弄到钱才是最实在的。身体成为她们满足物质欲望的工具,屈从于男人的性要求对她们来说变得极为正常,毫无羞耻可言,更谈不上要奋起反抗。当她回家,母亲见到票子后一味地沉浸在金钱的喜悦中,丝毫没有察觉到女儿有什么异样,反而催促她再回到城市中挣钱。金枝受伤的心灵得不到抚慰和怜惜,就这样被母亲的自私给无情地遗忘了。小说中的女性就是这样在女性同类当中相互迫害着,形成一幅骇人的女性生存镜像。
二、女性身体与民族国家话语的复杂形态
萧红对女性身体与女性生存困境之间的关系显然有着独到的体悟。面对她笔下的北方乡村女性,就好像面对疼痛的自己;而她所思考的女性的性别化困境,也正是她的人生困境。那么,她是如何看待女性、女性解放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呢?
刘禾在现代性的框架内观照文本,以敏锐的眼光洞察出《生死场》中女性身体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的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由于女性的身体被男性占有,失去了支配自己身体的自主性,因此无法产生与男性一样的国族认同,也无法共享那种男性中心的领土感。其次,小说文本中叙述的乡村女性的恐怖、毁形、残损等一系列女性身体经验瓦解了故事中不断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话语,她力图挖掘出缝合在国族认同中的沉默女性的真实声音[4]。
其实,小说中女性身体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的冲突不止有这两个面向。朱莉亚·克里斯多娃在《妇女与时间》中别具洞察力地指出,女性的时间与男性的时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女性的时间是循环时间和永恒时间,女性身体的节奏(如周期、妊娠)与自然界循环相连,因而女性与反复性和永恒性相关。而线性时间以进步和发展为前提,趋向未来,是父系的历史时间。“如果把女性主体置身于‘男性’价值的建构中,那么,就某一时间概念来说,女性主体就成了问题。”[3](P351)萧红以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来描摹打渔村中形形色色的男性和女性的生存境况。前半部分主要是书写女性的疼痛的身体经验,以及她们的内在依赖心态和卑下的生命本相,后半部分则展现这些蚂蚁一样的乡村男性以及作为他们同盟者的女性如何悲壮地站上民族战争的前线。在她笔下,诸多乡村女性的怀孕、生育等与自然节律相关的生物节律之重复出现所显示的循环时间和为了拯救民族危亡而奋起的有计划的反抗、国族所允诺的美好光明的未来所暗合的线性时间发生了龃龉,从而使文本清晰显示了线性时间试图隐匿的循环时间之破裂和痛苦。其次,在小说文本中,作家运用追叙的叙事手段,让女性回忆她们人生中的苦痛时刻,比如王婆不断地絮叨她年轻时候摔死孩子的具体场景。此种反复、琐碎、颓废悲观的妇女絮语显然与男性所推崇的具有进步意义和正面价值的革命、国家、民族话语相抵牾。再次,萧红在揭穿民族国家话语的虚假性和空洞性的同时也呈现了女性身体所隐喻的循环不已、无法自拔的女性生存困境。金枝先是被引诱,后来又被凌辱,不断遭受强暴的女性身体的文化符码成为国族建构进程中的异质性存在。在小说结尾,金枝欲入尼姑庵而不得,最终陷入无家可归的悲惨境地。女性的生存困境不会因为时间的线性流逝而有所改变,她们悲剧的生命走向背离了进步时间观所蕴含的对未来的美好期待,沉溺或被沉溺在循环的时间观之中,泣血挣扎,无始无终。小说中循环的时间观与进步的时间观复杂交织,女性身体、女性解放与宏大的民族国家话语之间的关系也就呈现出多元而非单一、复杂而非清晰的冲突样态。
那么,萧红在《生死场》中是否只表现了女性身体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的冲突样态,而没有考虑到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重叠与同构关系呢?
小说中的寡妇形象值得我们进一步玩味和思考。所谓寡妇,“是指和丈夫死别的”那群人[5]。在抗日的队伍中,她们似乎更具积极性,喊声先从寡妇群里传出:“是呀!千刀万剐也愿意!”她们“必须在以某种自戕方式拒绝其女性身份之后,才能成为国家的一员并为民族国家而战”[4](P289),即在认同国族的同时也失去了女性言说的真实声音,应该追问的是,为何小说中参军的农妇无一例外都是寡妇呢?“寡妇”这一社会角色的定义本身意味着随着丈夫的死亡,丈夫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和性压迫也消失了,她们的身体不再被男人占有,当民族国家遭受威胁,她们内心深处的主体意识也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松动, 她们与男性齐心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就是一种表现。虽然抗日的行为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妇女的生存困境,寡妇的生活也不一定比有夫之妇的生活来得轻松和幸福,但她们到底不必受到男权的压迫和折磨,在这一基础上,女性解放与民族国家话语产生了重叠和同构的可能性。
需要指出的是,小说中的年轻寡妇金枝是一个例外。她之所以无法像参军的寡妇那样拿起武器为民族国家的独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也无法获得像男性中心那样的领土感,是因为从其被强暴的惨痛身体经验来说,中国男人比日本鬼子更可恨。被中国男人还是日本鬼子蹂躏对女性来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被侵略的“国家是一个女人的身体”“强暴是对国家进行羞辱和污秽的策略”[6]等种种把女性身体和国家主体相同构的言辞其实是一种语言策略,它激励男性为争夺女性身体的主权和国家领土的主权而斗争。“被强暴的女性身体”这一文化符码所指向的是女性居于卑下地位的不平等的性别秩序。同时,虽然被强暴的女性身体与民族国家话语所允诺的光明未来相抵牾(小说结尾,被强暴后的金枝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但“遭受痛苦的女性身体的瓦解性的力量”反过来又成为作家叙事的压制策略,“性的原始力量被重新组织”[7],升华成一种崇高的叙事效果和艺术魅力。由此,女性的破坏性体验既揭穿了民族国家话语的虚假性,反过来又自觉不自觉地与民族国家话语融为一体,从而通向积极的国族认同的文化重构。可以说,女性主义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具有复杂的双向互动关系,二者产生了不可言喻的美学张力。
三、认同与拒斥:萧红对现代性的暧昧态度
萧红在小说中对女性身体经验的反复书写、对女性身体困境的揭示,以及对女性身体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的复杂形态关系的思考,是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怀疑和拒斥,还是认同和接受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五四”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厘清“中国人的国族建构及其关于‘现代人’幻想的想象的(imaginary/imaginative)建构”[8]是如何形成的。
“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民族以一些外部刺激为契机,通过对以前所依存的环境或多或少自觉的转换,把自己提高为政治上的民族。通常促使这种转换的外部刺激,就是外国势力,也就是所谓外患。”[9]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人原来的天朝上国的中心观念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国家民族的观念。中国从此进入西方资本主义所建构的社会秩序之中。作为相对于西方的“他者”的中国,一方面迫切地吸收西方现代文明以求自立,一方面又拒斥西方的文化渗透和文化殖民。因此,中国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打上了国家救亡和民族启蒙的双重标识,“所谓现代性从根本上来说不外是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个人主体的双重建构”[10]。
在现代文学中,大多数男作家以主体性的身份纷纷拥抱现代性,自觉参与到现代性的建构当中。相较于男作家,女作家是主动参与还是被动纳入现代性的建构呢?显然,如果把现代性进程中女性的能动作用简化为单一的可能性:共谋或抵抗,那么这无疑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统治者的权威僵化,它陷入了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而不考虑二者之间可能产生的复杂交融关系。
在日本侵略者的烽火蔓延中国大地的时候,要求作家书写人民遭受侵略者的凌辱、揭露满目疮痍的现实世界而不是蜷缩在个人的天地里诉说私人絮语、表达一己的苦闷,这固然成为1930年代文学的普遍性话语,有着男权话语宰制文坛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战争的破坏性力量让包括女性在内的全中国人意识到国家民族的危亡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萧红曾在信中为弟弟成为战士感到由衷的高兴,“恰巧在抗战不久,我也到山西去,有人告诉我你在洪洞的前线……我心里可开心极了,因为我看到不少和你那样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快乐而活泼,他们跑着跑着,当工作的时候嘴里唱着歌。这一群快乐的小战士,胜利一定属于你们的,你们也拿枪,你们也担水,中国有你们,中国是不会亡的……”[11]可见,萧红对民族国家话语并不是拒斥的,甚至可以说是有某种程度上的认同。饱受流离之苦,因战争而不得不四处漂泊的萧红不可能不在她的作品中表达她对革命、战争、国家民族的思考。因此她在小说中书写了东北乡村的农人们如何从麻木而愚昧的生存状态中被迫拿起武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过程,虽然他们并不是自觉地觉醒,反抗侵略者的最终结果不过是回到原来那种卑下低俗的生活,但小说中的人们如二里半、赵三以及寡妇们,到底是从日本人的侵略行为中获得了国家民族的领土感和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的国族认同感。这种关于国家民族话语的书写显然是作家自觉参与文学现代性的建构之努力,显示了萧红与主流知识分子在文化身份特别是在书写现代性上的“重合”。
那么,萧红对作为现代性面向之一的民族国家话语是否完全认同和接受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小说文本,思考萧红的小说与1930年代男性作家的小说有何不同。
在现代文学里,男性作家向来把女性当成“被启蒙”的对象,或者是被纳入革命的队伍,成为革命的坚实后盾或同盟者,或如1930年代的大部分男性作家,以萧军的《八月乡村》为代表,把农村寡妇李七嫂的身体设置为被蹂躏的牺牲品;而萧红却把笔触深入到战争之际的广大乡村土地上,书写乡村女性的被逼压、被毁形、被惩罚的疼痛生命经验。战争给女性带来的伤害无法因国家民族话语的崇高而被缝合、被抹灭,女性的丧身之辱也不能化约为激发中华儿女踏上革命道路的崇高力量。为了逃避日本人的强暴,金枝打扮成老婆子上城谋生,却没想到还是无法逃脱身体被强暴的悲惨命运。吊诡的是,民族国家话语又成为女性身体得以被表现、女性声音得以被言说的叙述空间。恰恰是在有了身体遭受强暴的惨痛生命体验后金枝才体悟到:不管是中国男人还是日本男人,都一样可恨!一直处于蒙昧混沌状态中的金枝的女性意识正是在战争以及身体被侮辱之后才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觉醒。可以说,她的女性主体性的获得是以女性身体的毁坏为代价的。小说中女性身体、女性主体性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的纠结、暧昧之处即在于此。
可见,萧红对作为现代性的态度并非完全认同,她既认同主流的国族话语之进步性修辞,又因为她作为女作家所拥有的女性立场以及自身疼痛的生命体验,力图挖掘出缝合在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女性声音,书写民族战争中女性身体经验的细节之处,揭示女性身体的永恒困境。文本既隐含了相当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尖锐的批判意识,又展现出对残酷战争现实的揭露、对男性和女性的国族认同感建构的不一致路径的思考,从而表现出复杂多变的现代性面向,以及现代性的诸多面向之间相互冲突又重叠同构的矛盾、纠结关系。现代性作为萧红小说作品中的一个基本精神向度,构成了她作品的深度。
表现女性身体的疼痛经验,言说女性的精神性别困境,显然成为萧红宣泄不断被男人抛弃又不断地寻求男人的庇护之复杂情感的出口,而揭露残酷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骇人现实、叙述民族国家话语则是对以萧军、鲁迅之类具有亲密关系的男性的行为之有意无意的模仿,以寻求自我的确证。当然,对战争、国族的书写也是20世纪30年代的萧红之自觉选择。
四、结语
萧红在《生死场》中借着宏大历史叙事的结构框架,表现最底层的广大乡村女性的日常生活,反复书写她们所面临的无法摆脱男性威权、被无休止地役用、毫无自己的思想与意识的性别困境,从而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女性意识。被强暴、被殴打、被迫怀孕,以及生育过程中遭受到的种种苦痛的生命体验,揭示了本质意义上的女性性别化困境:对男性来说,女性不过是满足他们低层次的物质和感官存在的“一团肉”;在男高女低的不平等性别秩序下,女性受尽肉体的虐待和精神的威压,而男性却占尽便宜。可以说,由于萧红自身辗转流离、不断追求又不断遭受遗弃的生命历程,当她面对北方的女性,就好像面对疼痛的自己;而她所思考的女性的性别化困境,也正是她的人生困境。另外,女性的敏锐视角和对时事的敏感体悟让作家看到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纠缠、重叠、同构的复杂关系。萧红对中国现代性表现出极为纠结的态度。民族主义没有性别之分,关于国族主义的话语之叙述显然表现出作家自觉参与文学现代性的努力,而女性立场和自身的疼痛生命体验又让她自觉挖掘出缝合在民族主义话语中的女性声音,书写民族、革命战争中女性的细节之处,从而揭示出女性本质意义上的性别化困境,表现出复杂多变的现代性面向。可以说,萧红《生死场》的魅力之处,即在于此。
[1] 萧红.萧红经典作品[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311.
[2] 萧红.生死场·萧红文萃[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 [3] [法]朱莉亚·克里斯多娃.妇女的时间[A].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4] [美]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5] 鲁迅.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277. [6] [克罗地亚]克内则威克.情感的民族主义[A].陈顺馨,戴锦华.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45. [7] [美]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94. [8] 汪晖.汪晖自选集[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 [9] [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M].王中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270.[10] 旷新年.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J].文学评论,2003,(1):38-39. [11] 萧红.“九一八”致弟弟书[A].萧红.萧红自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59.
(责任编辑 赵莉萍)
The Ambiguous Modernity: Female Body Writing and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in Xiao Hung’sBattlefieldofLifeandDeath
WANG Huai-zhao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China)
In theBattlefieldofLifeandDeath, with a gr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framework, Xiao Hung describes the daily life of country women. She writes their life experience of being raped, beaten, forced to be pregnant and the pain in the process of child delivering. Furthermore, Xiao Hung both represents woman’s body plight, and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feminism and nation-state discourse. The destructive forces of war urge Xiao Hung identify with the nation-state discourse consciously, while the position of female author also makes her to express the true voice of silent woman during the war.
Xiao Hung; female body writing; national identity;ambiguous modernity
2017-02-27
王怀昭(1989—),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性别与文学、文化研究。
I206.7
A
1008-6838(2017)03-0076-06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