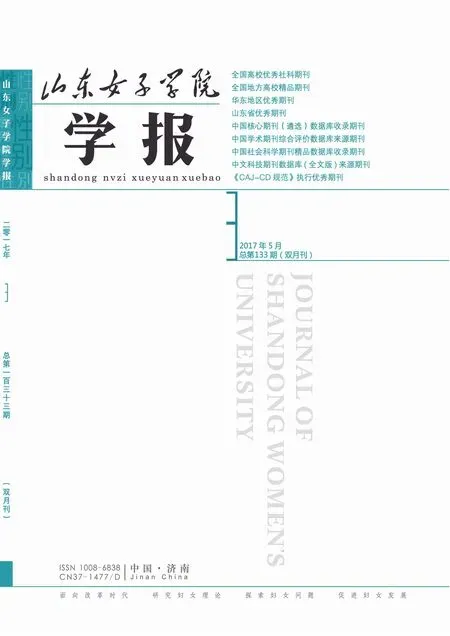性别隔离与男权话语中的权力运作
施文斐
(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宁夏银川 750000)
·性别平等理论研究·
性别隔离与男权话语中的权力运作
施文斐
(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宁夏银川 750000)
性别隔离发源于古老的女体禁忌,最初仅为出于生命安全忧虑而向特定女性实施的周期性隔离措施。男权话语通过提炼女体禁忌中的歧视“因子”、预设虚构的话语前提以及实施种种话语策略等一系列的话语权力运作,巧妙地将原本保持中立立场的安全保障措施置换为歧视女性、压迫女性的性别政治工具。而且话语权力运作的隐蔽性,使得性别隔离直至今日仍在社会性别分工、性别角色定位等方面保持着强大的现实干预力,职业性别隔离更可视为传统性别隔离在现代职场中的变相延伸。明确男权话语于其间的具体运作将有助于我们充分认清性别隔离的本质,以及时至今日仍“经久不衰”的“奥秘”所在,从而对女性解放的现状保持更为清醒的认识。
性别隔离;女体禁忌;女性劣等论;身体控制;话语权;话语权力
性别隔离,亦即“严男女内外之别”的性别空间区域划分,性别隔离自古有之,《礼记》有云,“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外内。”(《礼记·则》)“辨”,别也,“别的功能是为了要建立秩序”[1](P266),以家内、家外的物理界限将男女两性各自所应归属的空间区域区别开来被认为是社会秩序(礼)得以建立的原初与根基。唯有“男女有别”,而后才能“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礼记·昏义》)性别隔离被赋予的意义远不止于两性层面,更被上升到了政治伦理的高度。性别隔离之于秩序,无论是性别秩序还是政治秩序的建立至关重要。
性别隔离对两性关系格局的影响极其深远,为世俗观念所普遍接受的“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易·人·彖》)、“男治外事,女治内事”(司马光《温公书仪》卷三《婚仪上》)的社会性别分工,以及在女性性别群体中享有极高认同度的“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都与此有着密切关联。然而,这一以“隔离”(“别”)为重要表征的性别秩序究其实质却正是产生于针对女性的偏见与歧视,建立于生物差异上的女性劣等论于背后发挥着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然而,仅有理论支撑是远远不够的,任何“有偏见的态度和歧视行为”的有效实施都必须得到权力的保障。权力首先存在于话语之中,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话语即为权力①,“影响和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因素就是权力,而真正具有特殊效应的权力,也是通过话语来执行的”[1](P201)。厘清性别隔离产生的源头,明确为男权社会所掌控的话语权力于其间的具体运作将有助于我们充分认清性别隔离的本质,对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着的性别隔离,如职业性别隔离的强大现实干预力保持清醒的认识,从而为女性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为女性解放的真正实现铺平道路。
一、性别隔离的话语探源:女体禁忌与歧视“因子”的提炼
据文化人类学的考察可知,性别隔离早在原始社会即已有之。就其原初动机而言,性别隔离的实施主要是出于对处于经、孕、产等特殊生命期的女性身体(女体)的一种禁忌,伴随着特殊生命期产生的大量出血(经血、产血)是导致此类女性被隔离对待的重要原因。
著名的文化人类学者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通过对“德内(美洲)和大多数其他美洲氏族部落”的考察发现,在这些原始部落中,“几乎没有任何人像来月经期间的妇女那样为人们所畏惧”,一旦处于行经期,她就会“立刻被谨慎地同一切异性人们隔开,独自住在为本村男人或来往行人中的男子看不见的偏僻小屋里”[2](P199),产妇也同样会“被隔绝起来,直到健康和体力恢复,想象的危险期度过为止。”[2](P200)处于行经期的女性以及产妇之所以被认定为危险的存在而被隔离对待,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出于对其间大量产生的经血、产血的污秽恐惧,“她们可能会污染她们接触的任何人和任何东西”[2](P199—P200),为此,即便已被隔离开来,处于行经期的女性也要小心翼翼地“不得触及任何属于男人用过的东西或任何猎获的鸟兽与其他动物的皮肉,以免因此玷污了这些东西”[2](P199)。在一些地区,“妇女坐月子期间丈夫必须隔离八天,不得在家居住”,同样惧怕的是“受污染”[2](P200)。围绕着女性特殊生命期的血污恐惧进一步促成了大量迷信的产生,譬如“沾上女人的经血会让鲜花枯萎、果实腐烂、象牙失去光泽、长剑不再锋利、狗儿发疯”等等[3](P90)。在一些地区,人们甚至相信只要此类女性的身影出现即能导致上述灾害的发生,而无论是否发生过实际接触。
正是出于对女性神秘力量的极度困惑、强烈的血污恐惧以及深重的生存忧虑,人们才会普遍相信必须要将处于特殊生命期的女性这一“污染源”与整个社会公共空间隔离开来,通过将其神秘力量尽可能地控制在一个可掌控的范围内以保障整个社会公共空间的生存安全,以女体禁忌为特征的性别隔离正是在这一朴素的原始认知下逐渐形成的。
这一有关性别隔离的原始认知与古老禁忌在巫术信仰与宗教教律中都得到了继承与延伸。在记载了利未族的祭司团所应遵奉的一切律例的《利未记》中,就将古老的女体禁忌形成了明确、细致,甚至有些烦琐的话语表述②,并规定“她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圣经·利未记》12:4)[4](P182)。与西方的宗教教律相似,在巫术氛围浓重的宋人社会中,有着鲜明巫术色彩的医药操作中同样蕴含了对特定女性实施的女体禁忌。这一禁忌不仅如汉唐时期那样体现在“合药、用药之时”,而且还进一步扩大到了“药物从采摘、收藏、制备,到取拿、服用的全过程”③,女体禁忌也由最初的只针对特定女性扩展到了整个女性群体,“切忌妇人、鸡犬见”(朱端章《卫生家宝产科备要》卷六),“忌见丧服、色衣、妇人、猫犬之类”(苏轼、沈括,《苏沈内翰良方》),“忌僧尼、妇人、孝子、鸡犬,一切厌秽见之”(佚名,《卫济宝书》卷下),“勿令妇女、小儿、丧孝、产妇及痼疾、六根不具之人及六畜见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附《指南总论》上)④之类的话语表述大量充斥于宋人医书之中,其所传达的正是唯恐女性尤其是处于特殊生命期的女性的“不洁与污秽”导致药效失效,并进而危害生命安全的严重忧虑。
通过以上对古老禁忌、宗教以及巫术思维下的医药操作的简要考察可知,女体禁忌早在原始社会以及以巫术、宗教为代表的古老意识观念中即已存在。需明确的一点是,此时的女体禁忌并不必然意味着针对女性群体的性别歧视。诚如上文分析所示,对特定女性实施的周期性隔离措施主要是出于生命安全的考虑,而且,人们相信隔离措施的实施对女性自身也是有益的,否则她们就会“瘦得皮包骨头”或者“全身就会溃疡”[2](P542)。性别隔离正是为了保障女性自身以及他人的生命健康而实施的安全保护措施。
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性别隔离中确实已然内含了针对女性这一性别群体的歧视“因子”。“最低的私密的身体过程,能够赋予最复杂的和形而上学的解释”[5],将处于特殊生命期的女体视为“不洁与污秽”,其本身就是在进行着善恶、正邪的道德判断,《利未记》中规定的女性因经血不洁、产血不洁而须献祭、赎罪的条例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⑤。在古代中国,处于特殊生命期的女性也同样“不得参与家族祭祀这类严肃、庄重的场合,不得接近神龛、祭桌、祭品和巫师,否则的话就会亵渎祖先的亡灵,是对祖先的不敬。”[1](P94)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女性之所以被加之“不洁与污秽”的道德判断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而恰恰是根源于女性自身特有的、先天存在的、无法避免的生理现象。“在父权社会中,女性的生理特征往往被贬低和歪曲为不健全、不洁净,尤其是行经和生育现象,多半被视为神圣的对立面而加以禁忌。”[6]仅仅因生理差异而成为禁忌,更进而遭到歧视,这完全是一种生物决定论的论调。这样一种论调在十六、十七世纪曾普遍流行于近代早期西欧社会的“体液学说”中并得到了继承。这一性别阐释话语将人体视为“一副容纳着体液的皮囊”,“男人性属热干,女人则属冷湿”[3](P82),男女两性的一切差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道德判断都起源于所谓“体液”的不同。例如当时的学者曾以这一理论解释过何以女人沉在水里时会面朝下而男人一般面朝上的现象,认为其原因就在于“男人、热量、光线和上帝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而女人则与潮湿、阴冷联系在一起,所以很少会面向天空。”[3](P90)显然,男性体内的热干性体液象征着一种阳性的力量,与太阳、热量、光线保持着某种神秘的内在联系;而女性体内的冷湿性体液则与阴性的力量非常相似,总是与潮湿、阴冷发生着联系。这一性别差异上的本质主义倾向更进而取得了宗教层面上的支撑,“女人的本性是造物主创造的阴暗面,她比男人更接近魔鬼,而男人受到的更多的则是上帝的好影响”[3](P89)。从古老的女体禁忌中“提炼”出“不洁与污秽”的歧视“因子”,再将对特定女性的血污恐惧扩展到面向整个女性群体的体液厌恶,最后借由宗教层面上对“上帝”(善)与“魔鬼”(恶)的比附作出“相应的”道德判断,女性这一性别群体就这样在男权话语的一系列运作下被无可辩驳地贴上了劣等的标签。
二、性别隔离的预设话语前提:“不完整的人”与沉默的失语者
通过上一部分的分析可知,古老的女体禁忌虽并不必然意味着针对女性的偏见与歧视,但确实促发于为女性所独有的生理现象。对女性特殊的生理现象,如月经、生育及经血、产血的困惑与恐惧都是围绕着为女性所特有的生殖场域而发生的,这一生殖场域的存在无可辩驳地标志了女性的身体与男性的是多么地不同,多么地异质。相较于男性,女性身体所表现出的“异质性”是女性遭到性别歧视的又一重要原因。
这里,显然有一个预设的假定前提,即“将男性身体定义为标准人类躯体”[7](P8),女性身体由于其自身呈现出的巨大异质性而被视为有缺陷的、不标准的、不完整的,13世纪著名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即将女性看作“有缺陷的男人,是由于性交失误而生下来的男人”[1](P151),是“不完全的人类”[8]。“女性并不被视为独立的个体……女性是参照男性来定义和区分的”[7](P7),以男性身体为参照,将女性贬低为“不完整的人”这一观念意识可以一直追溯到神话时代。最初的女性夏娃仅仅是从亚当身上所取的一根肋骨,神出于“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圣经·旧约·创世纪》2:18)[4](P10)的愿望而创造出了夏娃,她的诞生完全取决于男性的需求,不仅在身体上是不完整的,在意志上也同样是从属的。这一“神说”话语的运用之于女性从属性的确立具有重大意义。原型—神话批评的著名学者诺思洛普·弗莱曾就神话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表述过这样的观点,即“每种意识形态开始时都就其传统神话体系中意义重大部分提出自己的认识,并利用这种认识去形成和实施一种社会契约”[9](P30)。依据这一观点,《圣经》将关于人类始祖的伊甸园神话紧随于创世纪神话之后,又将女性的“肋骨诞生说”置放于伊甸园神话之始,这一话语策略本身即体现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认知,即性别秩序的建立是与宇宙生成同样重要的头等大事,而确立女性的从属性则是性别秩序得以建立的关键。恰如亚当所说的,“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圣经·旧约·创世纪》2:23)[4](P10),由男权话语主导的神话完全成为了“一种为了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并设法将其永远置于此从属地位的一系列观念、偏见、趣味和价值观系统”⑥。女性的先天缺陷,即身体上的不完整性以及意志上的从属性都从“神说”话语的权威性中得到了认定。
女性“先天缺陷”的权威认定,或者说女性劣等论的确立之于性别隔离的实施具有重大意义,既是性别隔离的预设前提,又由性别隔离的实施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由于女性被认定为先天就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因此女性的智力水准乃至于道德品质也就顺理成章地遭到了否定。圣保罗曾将男性比作女性的“头”,“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圣经·新约·以弗所书》5:22、23)[4](P357),女性的存在价值仅与“身”等同,而“身”无疑是要服从“头”,听从“头”的意愿的。这一观点与西方社会惯于将男性与理性、精神相联系,而将女性与肉体、欲望相联系这一性别上的二元(灵、肉)对立论完全一致,女性被视为“永远也不能发育成熟的‘孩子’”,她们“既愚蠢又浅见”,其智力水平永远只停留在“男性成人和小孩之间”[10]。
正是因为“她”的缺乏头脑、极端愚蠢,女性被剥夺了于社会公共空间发声的权力。圣保罗曾要求“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她们说话。她们总要顺服,正如法律所说的。她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14:34、35)[4](P311)。于社会公共空间发声的权力被完全赋予了男性,有资格与神对话的永远是拥有话语权的亚当,而夏娃仅仅是亚当背后的一个沉默的失语者。作为男权社会中的他者,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女性群体也只能保持沉默,语言中蕴含着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威力”以及“从语言权力与威力中派生出来的暴力”都为男性所独享[9](P24)。尽管女性有时也会滔滔不绝,“不停地说,唠唠叨叨,口腔充满着声音,从嘴里发出声音”,但她说出的话并不具备任何话语权威,仅仅是“talk”,而不是“speak”,“她们实际上并没有表达,因为她们没有什么可表达的。”[11]失去了话语权的女性即使在社会公共空间现身,甚至于偶然发声,但也仍是一种“缺席”,仍是一种“失语”,她的身体与声音不具任何意义。
恩格斯曾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12]在此基础上,笔者更进而认为女性话语权的丧失是进入父权制社会后,女性这一性别群体所遭受的又一重大失败。由于话语权的被剥夺,女性失去了反击性别歧视的重要途径,而只能任由掌控了话语权的男性社会擅自界定女性的身体、智力乃至于道德品质。不仅如此,凭借着手中掌控的话语权,女性劣等论被男性社会以各种话语方式反复灌输给了女性群体,直至内化为女性“自觉”的自我性别体认,“贱妾”“贱婢”之类的自称无疑是女性劣等论内化成功的体现,反映了女性主体性丧失后的一种低自尊状态,而“保持女性低自尊对父权力量结构是有利的”[13],譬如,性别隔离的有效实施。
女性劣等论这一话语前提的预设,以及随之促成的女性话语权的丧失,尤其是女性对自身“劣等性”的自我认同使得性别隔离的实施变得更加畅通无阻。被驱逐出社会公共空间的女性从此失去了从事公众社会劳动的机会,只能“安心”于“贤妻良母”这一家内角色的扮演,而公众社会劳动恰恰是获得“社会性成人身份”的物质基础。男性社会正是通过将女性排斥于社会公共空间与公众社会劳动之外的性别隔离,从而否定了“她”的社会性成人身份。女性“被排除出严肃的事情和公共事务空间,她们长期以来扎根于家庭空间和与子嗣的生物和社会再生产相关的活动中”[14],“在这个没有她参与创造的世界上,在这个男人的世界上,她得完全依附于男人的保护,她永远也不可能成长起来”[15](P84)。长此以往,其结果只能是被局限在家内空间的女性变得愈来愈肤浅、愈来愈幼稚,反而进一步证明了女性的确是一群智力低下、行为可笑的“劣等”生物,“不完整的人”,这一原本纯属虚构的话语前提于此得到了意想不到的“证据”支持。女性劣等论与性别隔离二者之间就此形成了相互促进、彼此转化的循环呼应,性别隔离存在的合法性得到了证明与巩固。
三、性别隔离的话语策略:“天使”“妖妇”与身体控制技术
“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礼记·内则》)性别隔离,如仅就话语表层来看,可视为面向男、女两性实施内、外空间隔离的公平之举,但谁也无法否认有关性别隔离的种种话语总是针对女性施加了更为详细、更为琐碎的身体限制。就其实质而言,性别隔离更多地只是针对女性实施的空间隔离,即通过将女性的身体限制于家内空间的私人领域,借以达到将女性从社会公共空间驱逐出去的目的。性别隔离,或者更明确地说,将女性驱逐出社会公共空间的性别歧视行为,归根到底,正是对女性身体实施的一种控制。
由于女性被认定为“不完整的人”,更多地仅与身体相关,而缺乏头脑与理性,因此,男性社会对所谓的“提升女性智力水准”并不抱任何幻想,而仅将关注点更多地投注到对女性身体的控制与驯化上。正如尼采所言,“你到女人那里去?别忘带你的鞭子!”[16]⑦对于“女性”,这一在身体、智力、道德上都存在着严重缺陷的“劣等”生物而言,能使其得到“驯服”的唯一方法也就只有身体控制了。恰如马戏团的驯兽师训练动物一样,男性社会所要做的就是通过“操纵”“塑造”和“规训”以使女性(或者说女性的身体)学会“服从”和“配合”[17],并通过对女性身体的驯化,在两性之间建立起一种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使女性的身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是因顺从而变得更有用。”[18]
在男性社会的身体规训下,“她”的身体不仅被驱除出社会公共空间,而且即使在家庭领域也会受到进一步的“内”“外”限制,如“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礼记·内则》)“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男仆非有缮修,及有大故,不入中门,入中门,妇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仆无故,不出中门,有故出中门,亦必拥蔽其面。”(司马光《温公书仪》卷三《婚仪上》)除了家内进一步的身体回避外,女性还被要求应有意识地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控制,如“不敢哕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视,不敢唾洟;寒不敢袭,痒不敢搔。”(礼记·内则》)“不登高,不临深,不苟訾,不苟笑,立必正方,不倾听,毋嗷应,毋怠荒。”(《礼记·曲礼》)“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女论语·第一“立身”》)在中世纪那些为新兴资产阶级女性编写的关于行为举止的书籍里,也有类似的一些训诫,如“走路不要太快,不要猛然回头,不要晃动肩膀”等等,“不雅的大笑、直视的眼神、胡说八道的舌头和放肆的步态”[19](P199)等都被视为禁忌。
此类女教书中之于女性身体的种种规训自然可以被视为对女性仪态举止的一种“礼仪训练”,然而正如上文分析所示,这种“礼”的训练并不是通过提升内在的道德精神来实现的,而更多地仅仅体现为对身体这一“物质”的完美控制。女性身体成为男权话语权力运作的对象与场所,对女性的限制几乎全部聚焦到了“她”的身体上,女性的存在意义在相当程度上也仅限于“她”的身体。一个服从约束、符合规范、安心于家内空间的身体本身即被视为道德的体现。在中国的古典小说《林兰香》中,不幸早逝的封建淑女燕梦卿之所以被人们长期怀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她能对自我身体实施有效的控制,“遇着可喜的事,从不见她大说大笑;遇着可忧的事,也不见她愁眼愁眉。总然身体清爽,从不见她催酒索茶,胡游乱走。就是疾病深沉,也不见她蓬头垢面,迟起早眠。”(《林兰香》第三十八回)接受身体控制,尤其是“自觉自愿”地进行自我身体控制就是美德,身体控制的道德化是男权话语权力运作的一个重要策略。
被道德绑架的女性于是只能被困守于家内空间的狭小天地中,这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男权话语权力作用的结果。然而,单纯依靠强权、暴力的压制必然会引起受压迫者的反抗,将男权话语中蕴含的权力通过一定的话语策略巧妙地发挥出来无疑更为明智。在众多的男权话语策略中,“最深层、最隐蔽、最具有欺骗性”的莫过于“神化和歌颂女性”[20](P29)的“母性神话”。它以“一种控制和驯服心灵的缜密温柔型的权力技术”[21]巧妙地诱导着女性“自觉自愿”地按照男性的愿望需求、男性的价值尺度来形塑自身,而实现母性(包括妻性)的最佳场所无疑是家内空间,实现母性(包括妻性)的角色定位无疑是“贤妻良母”,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女性向家外的社会公共空间拓展的动力与愿望。“女性的形象和声音被边缘化了,女性只是男性角色的陪衬”[22],成为“具有母性、有社会道德、举止文雅、钟爱自己的丈夫和家庭”[19](P73)的“贤妻良母”成为女性生存价值的全部体现,其独立的主体性因此被取消,丰富的生命需求因此被遮蔽,充分发展的可能性因此被制约,“她的身份就只能是妻子和母亲,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是谁”[15](P18),这一身份危机的产生正是源于身体的受限。
对“贤妻良母”这一角色的神化与“社会不愿把妇女作为完整的人来对待”[15](P284)有着密切关联。将女性认定为“不完整的人”,是性别隔离预设的话语前提;专注于贤妻良母角色的“母性神话”,是性别隔离实施的话语策略,其共同指向的是使女性“自觉自愿”地留守于家内空间这一直接目的,最终促成的则是性别隔离的完美实现。
在将接受身体规训、安心于家内空间、专心于角色扮演(“贤妻良母”)的女性美化为“家庭天使”的同时,男权话语更积极地借助于包括通俗小说在内的各种话语形式对那些拒绝被纳入性别隔离秩序的女性进行丑化、性化、妖魔化等异质化处理。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中,女尼、道姑、三姑六婆等游走于社会公共空间的女性其道德品质就总是会遭到男性社会的严重质疑,古典小说中写到的许多犯罪事件,尤其是奸情的发生往往都与此类女性有着直接关联。其中,男性社会对“三姑六婆”这一特殊女性群体的抨击最为强烈。她们凭借着女性性别身份的便利而得以出入内宅,热心于为私情男女暗中撮合以便从中牟利,其频繁跨越内、外界限的行为使得本应处于封闭状态的家内空间变得有隙可乘。相较于引诱良家妇女堕落的罪名,对严守内、外之别的性别隔离秩序造成的破坏无疑更为严重,这也正是这一特殊女性群体遭到男权话语集中攻击的深层原因所在。诸如“话说三姑六婆,最是人家不可与他往来出入”(《初刻拍案惊奇》第六卷《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以及“一句良言须听取,妇人不可出闺房”(《初刻拍案惊奇》第六卷《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所以内外之防,不可不严也”(《二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五卷《徐茶酒乘闹劫新人郑蕊珠鸣冤完旧案》)之类于小说行文间不时穿插的训诫都可视为男权话语的直接表态。在西方社会中,倡导女性走出家门的女权主义者也同样遭到了男权话语的妖魔化处理。她们往往被描述为“缺乏幽默感的自私鬼,不修边幅,刻意把自己打扮成没有女人味的‘变态狂’,以及整日争风吃醋、吵吵闹闹地争辩不休的‘泼妇’”,有时甚至会被骂成“妓女”“猪”“淫妇”“巫婆”等等,那些支持或同情女权运动的男性也未能幸免,他们不是被视为“没有男子汉气概”的“无用和懦弱之流”“事业上的失败者或感情上的失意者”,就是被无端地贬低为“阳痿患者”“畸形人”或者“害怕老婆唠叨的‘气管炎’患者”⑧。
上述列举的所有这些具有歧视性、侮辱性的“标签”无疑是语言暴力的体现,“语言不仅有着它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威力,同时,更有从语言权力与威力中派生出来的暴力”[9](P24),这一语言暴力更多地只为掌控了话语权的男性社会所独享,那些被认为破坏或蓄意破坏了性别隔离秩序的女性(有时也包括男性)只能任由男权话语贴上这些“标签”。标签策略得到了广泛而持久的运用,20世纪30年代被称作“花瓶”的职业女性,民国时期被称作“交际花”的女记者们等莫不如此。
美化与丑化的并用,促成了女性形象的“天使”与“妖妇”的两极分化。以是否遵从内、外隔离的性别秩序为界,不是“天使”,就是“妖妇”,非此即彼,几无回转的余地。女性形象的刻板化使得“一种使女性压抑和限制自己的方式”[23]得以创建起来,在“妖妇”标签的“震慑”下,许多女性都对逾越内、外空间的界限感到深深的恐惧,清代的一些才女甚至有自焚诗稿的举动,即便仅仅是自己的文字流出家内空间也足以令人忧惧。无论是身体,还是话语,一切“越界”行为都将是不被允许的。然而即便如此,在男性作家书写的小说文本中也还是客观地捕捉到了女性渴望一窥家外空间的潜在欲念。在许多中国古典小说,如在章回小说《金瓶梅》《醒世姻缘传》,话本小说《任君用恣乐深闺杨太尉戏宫馆客》(《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四卷)、《王娇鸾百年长恨》(《警世通言》第三十四卷)中我们都会发现,为女性所最为热衷的娱乐项目就是“荡秋千”,这一象征着冲破封闭空间的意象在当代女性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书写的具有穿越色彩的小说《红王妃》(2004)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借着故事的女主人公——18世纪朝鲜李氏王朝洪夫人的幽灵的回忆,描述了那些仿佛过着“幽闭恐怖症患者的生活”的女人们用尽全身的力量奋力地将秋千高高荡起,也就是为了“在高高荡起的时候能瞅一眼高墙之外的风光”[24]。
无论是男性作家的客观呈现,还是女性作家的主观书写,“禁闭”的空间与“逃离”的欲念所反映的正是女性“身”的不自由与“心”的渴望自由。然而,以女性的身份公然出现在社会公共空间势必又会遭到男权话语的异质化处理,既渴望突破内、外界限,又不愿被贴上“妖妇”标签的女性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拒绝女性身份而将自己消逝为男人。这种女性身份的消逝不仅止于身体上的女扮男装,更指的是“丢弃自己作为女性特有的生存方式、体验方式和言说方式”,而完全以“男性社会已经僵化的、制度化的、理性化的口吻、词汇、意向和符号去说话”[1](P202),这是女性在这个为男性所操控的世界中获得话语权的唯一方式,也是将自己消逝成男人的关键所在。唯如此,才有可能跳出被局限在家内空间的“女人宿命”,使自己被禁锢、受限制的身体得到真正的自由。在清代的女性弹词作家书写的大量故事中,“僭越”着男性话语并在男性社会努力寻求个人发展的男装丽人们即使最终被识破了女儿身份,也往往拒绝重返家内空间,她们共同的愿望,同时也是这些女性作家们发出的共同声音,就是“拒绝自己的性别角色,走出闺阁,成为男人”[25]。
四、结语
在男权社会中,话语权完全为男性所操控,其不仅“具有文化符号体系的操作权”,同时也具有“话语理论的创作权和语言意义的解释权”[1](P202)。话语中的权力,以及衍生而出的强制力、暴力、威慑力都为男权社会所垄断。由于掌控了话语权,男性社会有权从古老禁忌中任意“提炼”出歧视“因子”并加以发挥,使其成为性别隔离的生物学依据;有权借助“神说”的权威将女性界定为“不完整的人”,从而为性别隔离的实施预设下话语前提;有权运用身体控制的道德化、“母性神话”“妖妇”标签等各种话语策略使女性“自觉自愿”地将自己的身体限制于家内空间。话语权的掌控赋予了男性社会支配话语权力的权力,男性社会的权力正是通过话语中的一系列的权力运作得以实现的。从提炼生物学依据到预设话语前提,再到种种话语策略的巧妙运用,在性别隔离得以实施的每一个重要环节上都体现着话语权力的强烈干预,性别隔离的完美实现正是男权话语中权力运作下的必然结果。
男权社会虽然掌控了警察、法庭、监狱等一系列暴力机关,或者说一整套权力系统,但话语中的权力运作无疑是最为文明、最为隐蔽的。通过一整套话语操作,话语中蕴含的权力得以以一种“隐性,不容察觉的,甚至是科学的,友好的形式表现出来”[20](P30),使得受其支配者深陷其中却又难以觉察,“传统社会性别的角色定型并没有发生改变,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变得更加艰难”[26]。时至今日,尽管绝大多数女性已经走出了狭小的家内空间,打破了内、外界限的制约,但即便进入到以现代职场为代表的社会公共空间内,也很难说就没有继续遭到性别隔离的隐性禁锢。作为传统性别隔离在现代职场中的延续,职业性别隔离中所谓的“男性职业”“女性职业”、横向隔离、纵向隔离,以及那个看不见的玻璃天花板⑨的实际存在都无不在证明着这一点,而且,“对于不同性别类型的职业,职业性别刻板印象普遍存在”[27]。将女性劳动力更多地视为应急的临时补充,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号召“让女性回家”以保障男性优先就业等诸如此类的职场性别歧视中同样可以看到传统社会性别分工(男外女内)与传统女性角色定位(贤妻良母)的强力影响,而这些又无不与传统性别隔离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借助于话语权力的隐性运作,而非“鞭子”式的直接暴力,正是性别隔离“经久不衰”的“奥秘”所在。
注释:
① “话语权”与“话语权力”这两个概念既彼此关联,又相互区别。“话语权”,简而言之,就是说话权、发言权,即说话、发言的权力;“话语权力”则更接近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界定,即话语并不仅仅体现为交际工具的“手段”,更体现为权力这一“目的”,话语本身即内蕴了权力,权力通过话语得以实现。拥有话语权者才有资格支配话语中的权力,而丧失话语权者则与话语中的权力处于绝缘状态,即使他在说话,他的话也无足轻重,不具任何权力效应。
② 如“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女人在污秽之中,凡她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所坐的物件也都不洁净。凡摸她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凡摸她所坐什么物件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在女人的床上,或在她坐的物上,若有别的物件,人一摸了,必不洁净到晚上”(《圣经·旧约·利未记》15:19—23),《圣经》精读本,香港:牧声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第189页。“……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她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要家居三十三天……”(《圣经·旧约·利未记》12:2、4)《圣经》精读本,香港:牧声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第182页。)
③ 参见李贞德的《汉唐之间医方中的忌见妇人与女体为药》,转引自方燕的《巫文化视域下的宋代女性——立足于女性生育、疾病的考察》,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10~111页。
④ 以上宋医药文献皆转引自方燕的《巫文化视域下的宋代女性——立足于女性生育、疾病的考察》,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11页。
⑤ 关于经血不洁赎罪的条例,“……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给祭司。祭司要献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那人血漏不洁,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她赎罪”(《圣经·旧约·利未记》15:29、30),《圣经》精读本,香港:牧声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第190页)。关于产血不洁赎罪的条例,“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她要把一岁的羊羔为燔祭,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她赎罪,她的血源就洁净了……”(《圣经·旧约·利未记》12:6、7)《圣经》精读本,香港:牧声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第182页。)
⑥ 参见林幸谦的《历史、女性与性别政治:重读张爱玲》,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210页。转引自林丹娅的《语言的神力:神话隐喻的性别观》,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27页。
⑦ “你到女人那里去?别忘带你的鞭子!”出自尼采的著作《扎拉特斯图拉如是说》中的《年老的和年轻的女人》一篇。该篇以“我”与一位老妇人之间对话的形式展开,这句话实出于老妇人之口,但完全可视为尼采个人的观点,正如《扎拉特斯图拉如是说》托名于扎拉特斯图拉,但完全可视为“尼采如是说”一样。
⑧ 与“女权主义者形象的妖魔化”相关的论述参见姚桂桂的《论美国媒体与反女权运动》,《妇女研究论丛》2011年11月第6期,第83页。
⑨ “玻璃天花板”,意指就个人发展而言,虽然看不见但又实际存在的阻碍。
[1] 贺璋瑢.东西文化经典中的女性与性别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13.
[2] [英]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M].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3] [法]罗贝尔·穆尚布莱.魔鬼的历史[M].张庭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 圣经(精读本)[M].香港:牧声出版有限公司,2012.[5] [英]菲奥纳·鲍伊.宗教人类学导论[M].金泽,何其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51. [6] 杨莉.宗教与妇女的悖相关系[J].宗教学研究,1991,(Z2):49-58. [7] 桑德拉·利普斯茨·班.关于性别不平等争议的演变:从生物差异到大男子主义制度化[A].[美]琼·C·克莱斯勒,卡拉·高尔顿,帕特里夏·D·罗泽.女性心理学[C].汤震宇,杨茜,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8] 张晓玲.妇女与人权[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60. [9] 林丹娅.语言的神力:神话隐喻的性别观[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10] 袁曦临.潘多拉的匣子——女性意识的觉醒[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37.
[11] 刘岩,邱小轻,詹俊峰.女性身份研究读本[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40.
[1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4.
[13] 克里斯特·A·史密斯.女性、体重和体形意象[A].[美]琼·C·克莱斯勒,卡拉·高尔顿,帕特里夏·D·罗泽.女性心理学[C].汤震宇,杨茜,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73.
[14]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M].刘晖,译.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135.
[15] [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M].程锡麟,朱徽,王晓路,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
[16] [德]尼采.扎拉特斯图拉如是说[M].北京:三联书店,2007.72.
[17]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154.
[18] 陆扬.文化研究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51.
[19] [美]苏珊·布朗米勒.女性特质[M].徐飚,朱萍,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0] 杨凤,田阡.性别政治下的女性发展边缘化[J].思想战线,2006,(1).
[21] [美]马克·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M].宋践,李茹,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8.
[22] 谈思嘉.女性神学思想述评[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6,(4):9.
[23] 帕特里夏·D·罗泽.针对女性的暴力[A].[美]琼·C·克莱斯勒,卡拉·高尔顿,帕特里夏·D·罗泽.女性心理学[C].汤震宇,杨茜,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242.
[24] [英]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红王妃[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51.
[25] 盛志梅.清代女性弹词中女扮男装现象论析[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27.
[26] 王蓓敏.“女性发展与性别平等——中德比较研究”研讨会综述[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6,(5):50.
[27] 王炳成,王俐,王森.大学生就业性别刻板印象的logistic回归研究[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6,(5):36.
(责任编辑 鲁玉玲)
Gender Segregation and Power Operation in Male Discourse
SHI Wen-fei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Yinchuan College, Yinchuan 750000, China)
Gender segregation originated from some ancient taboos about female body, when periodic separation was applied to certain women for safety concerns. Male discourse, by refining the discrimination “factor”, creating fictional presupposition and implementing various discourse strategies, skillfully substitutes the neutral safety measures with sextually political tool of discrimination and oppression. And because its elusiveness, gender segregation is still at work in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dentity. The occupational gender segregation in modern workplace can be regarded as more disguised extension of traditional gender segregation. Awareness of the specific operation of male discourse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gender segregation and reveal the “mystery” of its “enduring” nature, and realize the status of women’s liberation.
gender segregation;female body taboo; inferiority of women; body control;right to speak;discourse power
2017-03-07
陕西师范大学优秀博士论文资助项目“性别书写研究与近世白话小说”(项目编号:2014YB11)
施文斐(1978—),女,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中文系讲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近世白话小说、性别研究。
C913.68
A
1008-6838(2017)03-00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