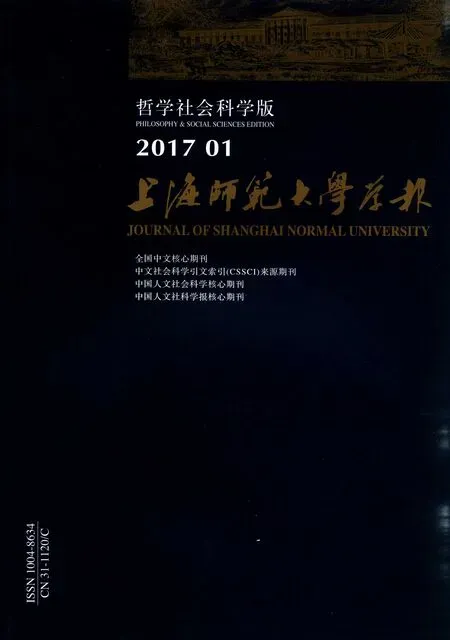什么是真正的问题?
——也谈“主义”和“朴学”之争
吴 炫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什么是真正的问题?
——也谈“主义”和“朴学”之争
吴 炫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迄今为止的“主义”和“朴学”之争,往往停留在捍卫自己的研究的重要性之层次,可能不同程度忽略了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发展需要解决什么问题的理解。只有独特的问题理解,才会产生独特的思想、理论和主义,学术的甄别也才能有自己的价值坐标。王国维和李泽厚正是在这样的问题的理解上,过于依赖中西方现有的思想文化,而看不到他们对自己认同的思想理论的批判和改造,从而产生问题模糊和理论矛盾之现象。在此意义上,直面中西方思想冲突的焦点,注意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异质性经验,吸收戴震等学者打通思想与学术的方法,或许可以为当代中国理论家和学者找到共同的突破途径。
主义;朴学;问题;途径
王建疆转来他的《朴学与主义》,是与夏中义《学术史提问与“新世代”焦虑》商榷的文章,并希望我这个20年前就提出“否定主义美学”的“主义实践者”也发表一点看法。其实,很多年前我曾写过“什么思想与什么学术”以及“思辨与实证”方面的文章,本不想再多说什么。但是拜读了两位的文章后,觉得在“主义”和“朴学”之争论背后有可能存在被双方忽略了的盲点。这种盲点可能会阻碍当代学术和思想对“主义”和“朴学”之争的深化。“什么是真正的问题”之追问,就是这种盲点之一。
一、思想生产和学术诊断的“问题坐标”
应该说,思想是理论的基础,但一般我们所说的思想因为与经验和感受性的看法有关,很难避免矛盾和凌乱,故容易造成中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是一种思想、在另一个问题上又是另一种思想的碎片状况;尤其是把自己赞同的思想当作自己的思想,从而不会思考什么才是自己的思想,更是中国当代学者普遍的状况。所以系统化、逻辑化,而且有独特的问题和独特的观念所揭示的理论,就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性要求,以突破传统的注释、阐释、印象式把握、选择和认同世界的思想方式。如果这样的理论操作性强,也能介入一定的实践并产生普遍影响与作用,就可以称之为“主义”(主义与理论在性质上并没有根本的区别)。①
在这个意义上,我当然认同并支持王建疆关于“主义”的倡导,便也因此常常感怀自己几十年否定主义建构和实践的艰难和孤独。但从王建疆和夏中义的论争中,我似乎又隐隐发现了这种艰难和孤独的原因所在,那就是:无论是对“主义”和“别现代”倡导的王建疆,还是坚持学术史的发生学考释研究的夏中义,可能都多少忽略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化究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的理解,既决定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思想、理论和主义,也决定着学术史的梳理是在怎样的问题坐标下进行的,并直接决定着我们对中国语境下出现的各种思想、理论和学术研究的价值判断。所以我对王建疆说:今天再倡导“主义”和“别现代”,已经不能停留在告别对西方理论和主义依附和移植的呼吁层次,而应该提出自己所理解的中国文化和美学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才可以建立能解决这样的问题的思想、理论和主义。问题的独特性,才能产生理论和主义的独特性。今天不少学者之所以对西方的理论和主义在中国的运用持审慎的眼光,这是因为西方思想和理论解决不了中国自己的文化现代性问题。如果认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就是诸如建立西方宪政的问题,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政治哲学。王建疆把“别现代”理解为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同时涌入,虽然有区别西方的倾向,但问题很可能是堆积的、模糊的。因为相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突出“我思”之理性、后现代突出“生命”审视理性的局限,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应该从中国自己的突破伦理束缚的文化经验和资源中去提取,这是一种“去伦理化但又尊重伦理”的中国式现代理性创造问题,也是整体性与个体性都能得到尊重的问题。所以不可能是西方有亚里士多德理性传统的“我思”之认识论以及以理性文化为前提的“质疑理性”之审美现代性问题,也不可能是以二元对立为前提的西方个体权利、宪政体制观照下的问题,在儒家伦理没有改变的前提下,甚至也不是科学主义、自由主义呼吁的问题,否则,西方任何理论概念在中国都会被异化。可惜的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各种理论和主义,基本上都是依附于西方这些理论和主义来提出中国问题的,这些问题在中国当代理论、主义创造的意义上可以是“伪问题”而需要审视改造——这样的工作会导致什么样的、有明确内涵的问题提出,才是王建疆的“别现代”需要面对的。
与此同时,夏中义近些年对中国现代学术个案的研究,当然彰显出严谨扎实的学术意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美学理论建设需要对本土资源认真梳理的意义上,这样的研究可以提供给理论和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学术性养分。夏中义倡导的“去症候”“重诊断”,在纠正以西方思想理论判断中国美学与文论之问题的意义上,也是有助于中国思想、理论的中国文化特性考量的。如果说“诊断”既包含对隐藏在学术中的思想的“甄别、挖掘、梳理”,也包含研究者具有美学和文论的现代问题产生的价值判断,出于乾嘉学派的“朴学”今天同样就会体现出明显的缺陷。我的看法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夏中义和王建疆讨论的中国传统文论是否有思想而无系统理论,而在于即便是“有思想”的诊断,也需要放在研究者所认定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化问题下进行判断。否则,中国任何学者的思想其实都可以在文献发生的意义上进行泛价值认定,任何学者的任何思想也就都可以做历史还原性研究,从而可能与一个学者“如何对文学自身负责”这样的文学现代性问题失之交臂,也难以培养中国当代学者对传统文学美学资源的审视能力。夏中义在《学术史提问与“新世代”焦虑》中谈到刘勰的《文心雕龙》,认为这部著作未见“上编、中编、下编有总体性逻辑过渡”,“确乎没有‘体系’构成所特有的概念系列的亲缘性思辨延绵”,触及中国的现代理论体系是否必须与西方理论体系完全一致的问题。但《文心雕龙》开了文学“宗经”的先河,导致中国文学只是在文体、表达、修辞的层面上谈自我实现,才是当代学术研究面对文学独立问题不可回避的诊断。因为早于刘勰的司马迁,其实在《史记》中就已经突破了“宗经”的思维定势;而后于刘勰的苏轼,更是在《东坡易传》中突破了儒家对阴阳八卦的“多元统一”的解释。这种相互比较的“诊断”是可以衬托出中国第一部相对系统的文艺理论的思想局限的。夏中义认为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从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钟嵘《诗品》→萧统《文选序》,不懈爬梳出一条魏晋南朝‘纯文学’意识逐代觉醒而臻于‘文学的自觉’的大线索”,但郭绍虞将“文学自觉”或“纯文学”放在“欲丽”“缘情”“能文”上,却未必触及文学独立之现代理解的问题,当然也就很难在这个问题下分析中国的“文学的自觉”,是否突破了刘勰奠定的对文学“宗经”的理解格局(包括萧统的“典雅”规范和王国维的“古雅”规范)。其实,直到汤显祖提出文学的“情在而理亡”为止,文学独立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思想上的深刻定位。就中国的太极文化不可能区别出纯粹的“理”和“情”而言,我们不可能说《红楼梦》是“纯情的”,因为贾宝玉对女孩子的“尊重和怜爱”,其实包含着曹雪芹自己的“理”;我们也不可能说鲁迅只有对中国文化严酷的理性批判,因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已经是鲁迅很个体化的情感了。在此意义上,中国古代文论在“文学本体”“文学独立”等根本的文艺理论问题上,可能还没有苏轼、曹雪芹的作品更能言说出文学突破儒家、道家哲学的精神——苏轼的哲学突破了“天人合一”之规范,曹雪芹突破了男尊女卑文化和纯情文化之规范,才涉及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真正独立之精神,而这样的精神是突破“情”与“理”的框架的。所以,好的文学不是“重理”还是“重情”的问题,而是无论是“理”还是“情”均需要突破儒家经典束缚的问题。中国古代文论没有从穿越“宗经”的角度考虑文学自觉问题,无论这样的文学批评史演变是怎样的,可能都不是夏中义说的“远未发育成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理论’婴儿”的问题了,而是要慎言他所说的“中国古代美学‘有’‘思想(言论)’的丰饶与深刻”这个问题了。
二、王国维和李泽厚的“问题模糊”
另一方面,就深刻的理论—深刻的思想—深刻的问题之逻辑关系而言,我觉得“思想”和“理论”“何以可能”这个问题,才是牵涉到思想、理论“有”和“无”的关键。思想和理论是建立在坚实的学术和知识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从独特的问题展开的对既有思想知识的审视思考上,也决定了关于“主义”之争是否可以更加深入。胡适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之所以是皮相之论,是因为中国现代学者谈的大都是中西方既定理论观照下的问题,而不是自己所发现的理论和社会问题;所说的主义也是西方现有的各种理论和主义。问题的置换和主义的置换,正好暴露出中国学者不能提出自己的文学问题,以及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文学思想、理论、主义和学术观念的原因所在。
基于独特的思想、理论和主义,是建立在独特的问题发现之上的古今中外经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发现了“劳动异化”问题,还是雅各布森立足于“文学与非文学之边界”的问题,抑或是存在主义发现了“诗性之在被理性遮蔽”的问题,如没有独特的理论问题的提出,不用说自己的理论和主义,即便是自己的文学思想,也不可能诞生。夏中义所青睐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四位著名学者——王国维、朱光潜、钱钟书、李泽厚,其学术功底虽然有差异,但学养应该都值得我们钦佩。但要说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文学思想和美学理论,是区别于传统文论和西方哲学、美学的,就有些难说了。先不说王国维的“无用说”“古雅说”作为现代中国美学的开端能否解释中国近现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也不说王国维用叔本华的生命哲学解释《红楼梦》是否牵强,仅仅就“境界说”区分“有我”和“无我”是西方主客体认识论的植入,“无用”说依托的是康德的超功利美学,“境界”和“古雅”又有中国传统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就可以判断王国维是在中西方哲学和美学之间徘徊、嫁接来形成自己的美学和文学概念的。这些美学和文学概念放在一起,正好使王国维的文学观和美学观在“自己的思想”意义上模糊起来。这种模糊究竟是一种“准体系的创造”,还是既定思想的“非有机性组合”,才是问题的关键。
如果王国维的美学概念和中国近现代优秀文学作品评价的脱节揭示的是后者的问题,用西方生命哲学解释中国《红楼梦》的牵强性揭示的也是后者的问题,那么上述四种美学概念放在一起的矛盾,可能同样是后者的问题。由于“天才”感悟宇宙人生的超功利性常常也是“突破艺术程式”的,所以强调艺术程式的“古雅”与“天才”是有矛盾的,至少“古雅”不是“天才”的逻辑延伸。如果“古雅”是给“非天才”准备的,实际上也就消解了“天才”说提出的意义,除非将“天才”内涵“古雅”。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因为王国维受叔本华哲学影响,想在中国给“天才”和“人间”划分界限所致。而这样的界限,到了“境界”说区分“趣、性、魂”三个层次时,同样遇到了麻烦。由于这三个层次在中国文化中是相互缠绕的,中国文学经典的“宇宙人生关怀”基本上不是超越“趣”和“性”层面的“纯粹关怀”,而是“不限于趣和性”的“缠绕性关怀”,这是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所致。《红楼梦》中贾宝玉和他所关爱的女孩子的“清纯之美”,是生长于日常吃喝玩乐等性、趣之中的,而且在贾宝玉身上也是包含日常赏心之愉悦与性感之乐的,甚至大观园本身就是依附于世俗权势才能存在的。这就使得中国文学经典很难剥离出一个纯粹的“魂的关怀”。这个问题,揭示的是王国维对叔本华和康德的哲学美学缺乏哲学批判的问题,所以在“审美无用”和“世俗之用”的中国式复杂关系上,王国维基本没有自己的哲学创造。这种局限,使得王国维即便将“天才”的“魂”之境界定位在“宇宙人生关怀”上,也未必能突出文学独立和文学高下之问题。因为至少在把握世界的方式上,孔子作为哲学家的人生关怀,与曹雪芹作为文学家的人生关怀就是不同的。由于一切文化性的人生关怀是观念性的,而文学的人生关怀是体验性的,所以不能突出文学的宇宙人生关怀对文化观念的消解,文学又怎么可能从“观念之道”的承载要求中突围出来,获得独立的品格呢?同时,文化的宇宙人生关怀是以群体性、普遍性为特征的,而作家的宇宙人生关怀是个体性、孤独性的,以前者作为作家自己的人生和世界关怀,在文学的价值上反而是不高的。20世纪中国的启蒙文学以西方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为准绳,文学价值高的反而是审视和疏离启蒙的鲁迅与张爱玲,是否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出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一个中国现代美学家或文论家对中国文化现代化与文学现代化的联系与区别,没有放在中国文化和文学经验中去提取,他就很可能依附中西方既定的思想和理论,在徘徊和矛盾中提问题,从而也会不断置换自己的理论概念,使自己的思想模糊起来。这种模糊说好听是融合中西,说不好听是思想碎片。在此方面,李泽厚的“积淀说”和“情本体”的置换与矛盾,就是一个典范。
“积淀说”强调的是儒家伦理对文学情感和形式的规范,造成李泽厚《美的历程》对儒家伦理之美的历史性书写,应该说是一种伦理历史化的本体之实践。这样的本体论主要是在分析和描述儒家文化为什么在历史发展中成为中国人集体性的审美无意识,但却看不到中国文化经验中突破儒家文化积淀的个案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如夏中义谈《美的历程》所说的,“第一步,他总是确定每一历史时期的总倾向或主导‘理性’,它在文人——艺术家身上沉积为价值文化态度;第二步,再找出该时期的艺术经典在意蕴、情调、形式方面对上述‘理性’的微妙感应;第三步,从给定艺术经验(作品与技法)中提炼出该时代的审美尺度”,但却“看不到民族审美意识和艺术形态为什么和怎么发生变异的”。②如此说来,“积淀说”如果也有问题意识,那也是强调需要传承历史性文化内容比突破这些内容显示从独特的、难以概括的艺术独创性更为重要的意识。其直接结果,就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化需要改变儒家文化以及如何改变等理论问题被忽略了,从而在思想上与刘勰的“宗经”思维并无二致。因为“六经”其实就是贯穿中国文化各个历史时期的“主导理性”。将艺术作为“主导理性”的外化形式,无论怎样绚丽多彩,艺术自身异于“六经”的“理”,就不可能被“积淀说”所重视——这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美何以可能”“优秀文学何以可能”的问题。李泽厚近些年又提出“情本体”,③通过“创造一个以情为本,融理、欲为一体的美丽世界”④来针对西方理性文化、宗教文化式微之后的人类生活出路问题。但是因为在“积淀说”中“情”是被儒家伦理所规定的个体显现方式(所谓“合情合理”),与“情”相关的“个体人格”也只是“圣性人格”的外化,所以汤显祖尊重人性、人欲的“情”只能是悲剧性命运,而文革时期顾准和张志新不屈的情感靠的是自己思想信念的支撑,这三种不同的“情”基本没有进入李泽厚的“个体主体性”思考的视野。也就是说“什么情”“什么理”的问题没有被李泽厚重视,这就使他的“情本体”很难面对中国文化现代化需要激发个体思想(理)创造的问题,回避了苏轼、曹雪芹有自己的“理”规定的“情”从而突破“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问题,也使得他想通过“情本体”解决西方后现代问题的愿望可能落空——用儒家讲群体性、血缘性规范的亲情、友情、爱情建立的“情”,怎么可能诊治讲个体权利、思想创造、逻辑理性并且有超现实宗教传统支撑的西方人的人生价值重新选择的问题?其可行性论证如何展开?
究其实质而言,“情本体”误解了西方后现代其实不是不需要理性而是审视理性的局限性之问题。以为连理性思考力都很弱的民族凭着自己伦理化的“情”就可以为人类理想的生活指明方向,也同样误解了中国文化所讲的“情”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根本的范畴,如何能成为本体论?⑤如果李泽厚注意到中国文化中“个体化的理”能接纳又挑战“群体化的理”这种“异类”现象,他的重点就可能会放在“个体化之理”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突破上了,也就没有必要在“理”的外化形式(情)上做文章;中国文化能与西方文化打通的也就不是历史积淀的仁义化的“情”,而是尊重儒家文化、又异于儒家文化的“个体化的理和情”。由于“创造工具”可以不受“使用工具”支配,“活得怎么样”可以不受“活着”支配,所以“主体论”强调“人类性主体”对“个体性主体”的支配作用即便给“个体主体性”留下自由选择的空间,个体能通过自己的思想创造突破这种支配吗?如果能突破,那就是两种本体论;如果不能突破,区分“人类主体”与“个体主体”就没有多少意义。从李泽厚想兼顾两者的思维方式来看,我认为这正好暴露出他其实是没有自己明确的哲学问题的,从而才造成他不断调整自己理论命题的状况。但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哪一个不是可以在本体论问题上与时俱进、改头换面的?
三、独特的中国现代问题如何提出?
在如何产生自己的哲学、美学和文学“中国问题”上,我的基本看法是:突破在既有的思想、理论和学术观念之间进行“选择”“综合”的批评和创新方法,直面和审视各种思想理论相对于自己生命感受的矛盾点,才有可能发现自己的“中国问题”之萌芽。批判不是用一种思想理论去批判另一种思想理论(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而是用自己的“问题”去批判所有与此问题相关的中西方思想、理论和主义,当然也包括批判既定的学术观念与方法。
在《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这本书中,李泽厚说,“我现在提出的情本体,或者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这是一个世界的视角,人类的视角,不是一个民族的视角”。又说,中国实践理性或者历史理性的最大缺陷就是“忽视思辨、逻辑的力量”。⑥这是典型的用西方理性文化看待中国“问题”、又用中国情理文化看待西方产生的“问题”,应该说,代表了中国学人普遍的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之所以不可能发现中国原创性的现代问题,是因为李泽厚一方面是凭感觉说中国缺少西方人的理性思维,但却无法论证中国人如何在伦理情感框架中培养这样的逻辑思维能力,这是学术上的盲点。另一方面,李泽厚又没有注意到中国学者模仿西方人的逻辑推理能力,也具备、甚至可以产生很经院化的规范论文,但为什么就不能产生自己独创性的哲学思想呢?这个问题可以提出逻辑思维与批判思维的矛盾点。而中国古代资源中,司马迁、苏轼、戴震、陈亮为什么可以在批判儒家哲学中提出自己的天人观念、人学观念、尊欲观念,但已经学习西方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学人却不能?这是儒学积淀和突破积淀的矛盾点。对这三个矛盾点的关注,自然会产生中国文化现代化究竟是要加强学习西方的创造之果(逻辑思维),还是需要发掘传统中的创造资源里隐性的思想能力和方法,⑦就成为现实、传统、西方之复杂关系的问题焦点。对这些焦点的关注,自然就使得儒家情理文化和西方逻辑思维都不一定是中国文化现代化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反而会成为中国现代哲学批判改造的对象(儒家情理文化对人的欲望和思想创造力的抑制,是必须予以批判改造的;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性文化与中国情理文化和隐性突破的批判性文化结合后,也必然会发生性质与结构的改变)。可惜的是,李泽厚只看到儒家文化历史化的中国,却没有看到尊重而又挑战儒家不断出场的另一个隐性批判儒家的中国。如果后一个中国进入思考视域,我们就不会受儒家化的“情理”束缚,也不会执迷于在学术形式上模仿西方了——逻辑思维如果不与批判思维相结合,只能是一个精致的皮囊而不会生产思想与理论;逻辑思维如果不在生活中落实,就只能是中国伪善文化的另一种翻版。更重要的是,李泽厚因此也看不到另一个中国才是与西方后现代哲学对话的资源,那就是中国的弱逻辑化、具有隐性批判张力的思想文化可以弥补西方逻辑化、绝对化思想文化带来的负面缺陷,而不是非逻辑化的儒家情理文化可以直接弥补西方理性式微的文化局限。在此意义上,哲学实在不应该是李泽厚意义上的人类问题与中国问题的分离,而是只有通过中国问题的有效解决才能向世界贡献一种东方现代人类哲学。再进一步推究,我们在中外哲学史上似乎也没有发现一个本民族文化问题解决不了、却能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哲学家。
比较起来,皖派朴学代表人物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⑧则给我们突破乾嘉朴学以这样的启示:鉴于中国是太极文化,学术和思想本不应该疏离或对立,而是相互缠绕的关系;更因为知识分子对社会和人类生活的责任不可能脱离思想,所以乾嘉学派承袭两汉古今文经学在文献考证上没有多少学术观念的创新,本身就应该进入现代中国学术的思想审视视野。这种审视自然会使得我们注意戴震将思想批判引入字义考证的重要意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戴震首先发现了人性的根本是人的生物性之问题,因此“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理在事中”的思想来自于戴震对古人的还原考证得出的看法,以“古人所谓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谓理者矣”⑨来展开对朱子“灭人欲”之理的批判。这样的思想还原本身就是思想批判,我们已经很难分清这是思想、理论,还是学术、朴学。可惜戴震这种突破“主义”和“朴学”分野的创新,似乎并没有被今天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史研究和文献考证研究重视,也没有被中国理论界的思想和理论研究重视。其结果就是,王国维和李泽厚所说的中国古雅文化和文化心理结构,其实都是儒家解释八卦之后的思想产物,并不一定是古老的八卦符号的唯一解释。如果对中国文化思想进行还原研究,应该还原到伏羲的“先天八卦”之中,从而通过对“先天八卦”的新的解释展开对儒家思想文化的批判。事实上,儒、道之争已经展开了这样的批判,后来的荀子和苏轼也不同程度以自己所理解的“天”和“道”加上事实论证来突破儒家文化的思想结构——苏轼甚至以对“水”的“随物赋形”的性质观察,还原并改造了老子的“水往低处流”⑩的思想。这些其实都可以成为思想与学术交融的先例。关键是,无论是戴震还是苏轼,即便是在做学术研究时,也是具有以自己的生命感受为出发点的思想批判活动的。这种活动制约着学术甄别和还原研究的方位,并通过学术研究建立起自己的思想观念。
我想,说到这里,王建疆和夏中义所争论的“主义”和“朴学”问题,是否应该可以有一个交汇点了?
注释:
①“主义”也可以在创作方法和流派意义上使用,如现实主义、印象主义等,这就不一定与特定的理论体系有直接关系。
②见夏中义:《李泽厚“积淀说”论纲》,《上海文化》1995年第4期。
③参见李泽厚、刘悦笛:《关于“情本体”的中国哲学对话录》,《文史哲》2014年第3期。
④李泽厚:《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页。
⑤陈来认为应该是“仁本体”,但实质内容与李泽厚伦理化的“情”尚未有根本区别。见陈来:《仁学本体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⑥李泽厚:《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80、86-87页。
⑦在否定主义哲学中,这是一种中国化的尊重儒家、又能质疑改造儒家的思想能力,其表现形态并不是西方思辨和逻辑的。司马迁一方面尊敬孔子,另一方面又将“一视同仁”改造成“一视同人”,可以说明。
⑧[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
⑨同上,第1页。
⑩见《经部·东坡易传—钦定四库全书》,线装书局2014年版。
(责任编辑:陈 吉)
What Is the Real Problem?——On the Debate Between “Isms” and Pu Xue
WU X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The debates between “ism” and “Pu Xue” (philology) remain at the level of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ir own researches respectively, and ignore the real problems of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to some extent. Only a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problems can lead to unique thoughts, theory and “ism”. Academic judgment should be based on real value. Both Wang Guowei and Li Zehou depended too much on the exis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thoughts and cultures and failed to realize their own criticism and reform of the theories, thus leading to the ambiguity of problems and contradictories of theories. In this sense, contemporary Chinese theorists and scholars may find breakthroughs by facing the confrontation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hought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heterogeneous experi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s, and absorbing the combination methods proposed by scholars like Dai Zhen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thoughts and academic studies.
ism, Pu Xue (philology), problem, approach
2016-10-09
吴 炫,江苏南京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和哲学原创性研究。
I0-02
A
1004-8634(2017)01-0052-(06)
10.13852/J.CNKI.JSHNU.2017.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