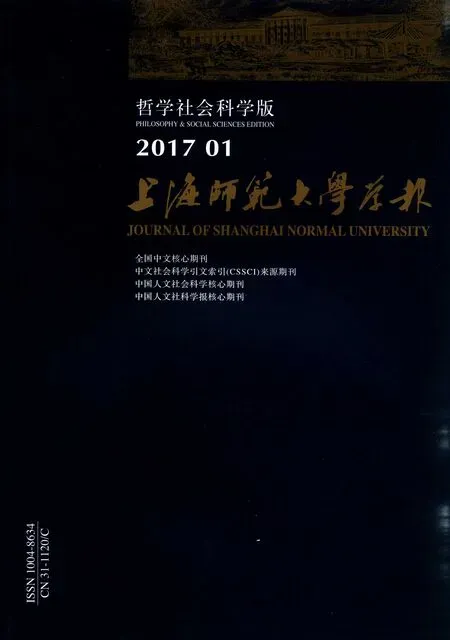琱生诸器与西周宗族内部诉讼
王 沛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 201620)
琱生诸器与西周宗族内部诉讼
王 沛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 201620)
2006年11月琱生尊出土之后,如何将其铭文与传世琱生二簋铭文联读,成为学界极为关注的问题。林沄先生提出不应受铭文历日影响,而是根据铜器种类联读簋铭,并将尊铭视为独立篇章,这是很有启发的观点。以此为基础重新解读三篇铭文,可看出琱生诸器与西周宗族内部诉讼相关。在诉讼中,宗君与审判官的关系、领主与仆庸的关系、大宗与小宗的关系均体现其中。铭文揭示,西周时期王朝司法与宗族司法并行于西周王畿。由于战国以后中央集权格局逐步形成,宗族司法渐渐消亡,而琱生诸器则将湮没已久的宗族司法场景再次展现在今人的面前,故具有重要的法制史意义。
琱生尊;琱生簋;西周;宗族司法
琱生诸器是一套充满传奇色彩的西周青铜器,这组青铜器共4件,即五年琱生簋、六年琱生簋以及两件五年琱生尊,3000多年前由西周关中地区的琱生家族铸造,现在分别陈列在美国耶鲁大学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及陕西扶风县博物馆。这4件铜器包含了3篇长篇铭文(两件尊的铭文相同),内容涉及西周时代诉讼、家族、田土制度,信息非常丰富,是探讨早期中国法制的宝贵资料。4件铜器里,2件铜簋早在清代就进入了学者的视野。之后,从阮元、孙诒让、郭沫若一直到林沄、朱凤瀚、王玉哲,很多重要学者都撰写过相关论文。①尽管学界从各个角度探讨铭文中的案例,但其情节仍显得扑朔迷离。
非常意外的是,2006年11月在陕西扶风县又出土了两件大口铜尊,其铭文与前述铜簋所载的案情直接相关,且铭文历日和两件铜簋前后相接,这令研究者十分振奋,大家普遍认为案情在3篇铭文提示的时间点中依次展开,事件始末将得以贯通。笔者亦曾依这种思路撰写论文,认为3篇铭文揭示了西周时代大家族在应对王朝的司法侦讯时析分族产的场景。②但是,在琱生尊出土近10年后,重新研读诸位学者的讨论,发现3铭通读的思路存在很大局限。特别是结合器形、纹饰等因素来考察铜器间的相互关系时,就更需要重新推敲铭文联读的方式。在调整铭文阅读顺序后,我们发现其内容与西周时期的宗族内部诉讼密切相关,而这种宗族内部诉讼在文献中是绝少被提及的。
一、铭文排序与案情理解
琱生诸器中的3篇铭文在其开篇均记录了明确的日期。五年琱生簋开篇说“惟五年正月己丑”,五年琱生尊开篇说“惟五年九月初吉”,六年琱生簋开篇说“惟六年四月甲子”。有了这样明确的记录,大家自然会依照铭文的时间顺序加以解读。五年琱生簋铭文如下:

这段铭文的大意是:在某位周王五年正月己丑那天,琱生有事,召氏大宗来协同处理此事。琱生向宗妇进献,③宗妇赠送琱生壶,并转告宗君的命令说,我老了,而公室的仆庸土田却多有争扰,希望伯氏(召伯虎)听从如下安排:公室占有三份的话,琱生就占有两份;公室占有两份的话,琱生就占有一份。琱生献给了宗君一件大璋,送给宗妇帛束、玉璜。召伯虎说,我已讯问有关人员,我能贯彻我父母的命令。琱生则觐献玉圭。
五年琱生尊铭文如下:
其又(有)乱兹命,曰:“女事召人”,公则明亟!
这段铭文的大意是:在某位周王五年九月初吉那天,宗妇召姜送给琱生五件帛、两件壶,传达君氏的命令说:我老了,我们的仆庸土田多有扰乱,要答应我,别让田土散亡。我占有三份,你占有两份。兄长公正,弟弟服从。琱生献给宗君一件大璋,送给宗妇一件帛、一件璜。有司举行盥礼,两厢验看。琱生称赞宗君的休美,制作了纪念先祖召公的这件尊,用来祈求厚禄,有德有终。子孙永远珍藏使用。如有违抗裁决,说琱生在役使召人的话,公族将会严惩。
六年琱生簋铭文如下:
在琱生尊出土以后,学界的解释对3篇铭文的背景、人物关系理解虽有不同,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3篇铭文体现出一个案件的3个发展阶段。在五年正月的时候,召氏家族遇有官司或其他原因,遂将相关族产予以分割,并且提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大宗占有三份,小宗占有两份;另一种方案是大宗占有两份,小宗占有一份。到了五年九月时,族产分割方案正式敲定,采用更有利于小宗的方案,即大宗占有三份,小宗占有两份。次年,也就是六年四月的时候,官司正式结案,族产交接完毕。
这样的解释虽似顺理成章,不过仍存在不少疑点。比如第一篇铭文仅从格式上来看,就不完整,说完“琱生则堇圭”便戛然而止,缺少称颂辞与嘏辞。而第二篇铭文和第三篇铭文均格式完整。若将第一篇和第三篇看做是一篇长铭的两部分,则会通顺很多:“琱生则堇圭”(第一篇)、“伯氏则报璧”(第三篇)相对成文,前后呼应;第一、三篇铭文联读,叙说整齐完备,且第三篇结尾出现的称颂辞、嘏辞,正是全文结束的标志。此外还要引起重视的是,第一篇和第三篇铭文的载体,正是造型几乎完全一致的两件簋,④反观第二篇铭文的载体,则是造型独特的两件大口尊,与前述二簋大异其趣。林沄先生由此出发,认为两件簋乃同时铸造,其铭文前后相连而共叙一事,而尊为另行铸造,其铭文虽与簋铭相关,但自成一体。林沄先生指出:
两件琱生簋器形和花纹一致,应是同时所铸的成对彝器,所记是一场讼事的全过程,都是六年四月所铸,而五年正月则是铭文追述往事的岁月。琱生尊乃是五年九月先已铸造,主要是为了记录对调解讼事其决定性作用的君氏之命。⑤
林先生的观点很具有启发性。两件青铜簋器形非常相似,完全有同时铸造的可能,器物既属一套,铭文亦共构一篇。而尊的造型十分独特,有明显的模仿陶器特征,其文字亦当单独对待。通过对琱生尊器形、纹饰分析可知,其与周公庙遗址出土的大口陶尊类似。周公庙位于陕西省岐山县,而琱生所属的召氏家族正分布于此,⑥琱生尊当为高级贵族家族所属的独立作坊制作,具有鲜明的家族特征,其铭文也更突出小宗家族的举措。我们不必一定要排列簋和尊铸造时间的先后顺序,即便琱生尊铭文开头云“惟五年九月初吉”,也只是说明事件的发生是这天,而并不是指琱生尊铸造于这天。只要根据器物之种类不同以区分内容,两件簋铭联读成篇,尊铭自成一篇,不少疑难问题就能解开。
在林先生观点的基础上,笔者进而对铭文性质及法史意义加以阐述。笔者认为,两件铜簋的铭文侧重讲述整个诉讼事情的经过,目的在于体现琱生对宗君宗妇的干预行为及召伯虎裁判行为的称颂,这是小宗琱生对外的表态。而两件铜尊的铭文,侧重指出自身哪些权益得到了确认,并宣示了宗君的命令,以告诫新归附的仆庸,其目的在于体现小宗琱生对内的权威。从法制史的角度来看,琱生三器铭文是记录西周宗族内部诉讼的难得资料,这些资料同时反映出西周宗族社会的政治格局。下面我们将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
二、诉讼中的仆庸、宗君与审判官
琱生器铭文有不少用语的省称,仅就单篇来看,会给理解带来巨大阻碍。幸而诸器全部面世,我们才明白铭文的用意。比如五年琱生尊、琱生簋中都说“仆庸土田多扰”,若非六年琱生尊将其表述为“狱扰”,我们就无法获知“扰”专指与狱讼有关的田土纷扰。而五年琱生簋说五年正月己丑这天“琱生有事”,即指此讼事。
这场小宗琱生提起的狱讼,事关“仆庸土田”纠纷。在西周时代,仆庸和土田是联系在一起的,土田的领主是谁,耕作于其上的仆庸之领主就是谁。从琱生尊铭文中仆庸对小宗有“汝事召人”、即“小宗你们役使我们召人”的怨言可知,琱生所属的某些仆庸并不认为他们的领主是琱生,而认为他们的领主应当是属于大宗,也即公族。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其耕作的土田不属于琱生,而属于大宗公族。琱生向大宗提起诉讼,应当即与这种仆庸权属的纷扰相关。
“仆庸”何许人也?仆庸就是领主所属的人民。西周后期铜器逆钟铭文中将“公室仆庸、臣妾、小子室家”连用,⑦表明仆庸身份地位并不低下。裘锡圭先生说仆大部分使用在战斗、守卫等工作上,庸主要提供农业和土木工程的劳役以及各种生产品,应当是符合西周实际情况的。⑧仆庸、特别是众仆不服管束,而其领主提起诉讼,由再上级贵族加以制裁,这在西周铭文中并非罕见。除了琱生诸器外,我们还看到两篇铭文涉及领主与众仆的紧张关系,众仆不服从命令,甚至会引发诉讼。如师旂鼎铭文说:

铭文的大义是,在三月丁卯这天,师旂的众仆不随从周王征讨方雷。师旂将其众仆告到了伯懋父那里,伯懋父对其仆众处以罚金,而其仆居然不缴纳罚金。于是伯懋父再次下令,说本当判处其众仆以流放之刑,⑩现在不处此刑,仍然让其缴纳罚金与师旂。伯懋父显然是师旂的上级,当师旂不能控制自己的众仆时,便向其上级提起诉讼。新近公布的肃卣铭文则体现出大小宗的众仆纠纷,众仆不听新领主的指挥,而纠纷最后的解决,竟然需要周王出面。肃卣铭文如下:

既然琱生尊铭文的最后一段话已经提示,琱生的官司与大小宗仆从归属问题相关,那我们就可以之为基础,进一步还原两件琱生簋所载的案情始末了。
五年琱生簋说五年正月己丑这天,琱生向宗族提起诉讼,“召来合事”,是说宗族指定大宗的召伯虎来解决这桩讼事。在六年琱生簋中,召伯虎对琱生说“公厥秉贝用狱扰,为伯有祗有成”,即“公族提交费用于狱扰之事,我都处理完毕”。这都表明召伯虎是具体处理案件之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召伯虎是承担了审判官的角色,但真正决定裁判结果的乃是宗族的首领宗君、宗妇。五年琱生簋、琱生尊中都记录了非常口语化的宗君命令,在五年琱生簋中,宗君说:“我老了,但公族的仆庸土田多有纷争,请召伯虎加以这样裁定……”之后审判官召伯虎说他已经讯问有司,但至于判决,则要“或致我考我母令”,即听从其父母的命令。这都表明这种情形。我们可以更简单地描述宗族内诉讼的程序,即向宗族提起诉讼,宗族指定审判官,而审判官根据宗君的意见处理案件。过了一年多后,案件终于处理完毕,六年琱生簋说召伯虎来向琱生庆祝,说他处理好了案件,同时又强调“亦我考幽伯幽姜令”,即这是根据其父母宗君宗妇的命令做出的裁决,琱生则称赞了宗君的休美,并将此事铸造在两件簋上,以纪念其先祖,并让子孙永远珍藏使用。
在两周时代,宗族内部的管理模式、机构设置和王朝、诸侯国非常相似,在狱讼方面也是如此。如《左传·襄公十年》所载,王朝两位贵族王叔陈生与伯舆因争夺权位而引发诉讼,王朝临时任命晋国的贵族范宣子来成周王庭担任审判官。而范宣子在讯狱时,第一句话就说“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这和召伯虎担任审判官时说“亦我考幽伯幽姜令”是一脉相承的。在王朝,虽然任命审判官,但其实际上为天子的代言人;在宗族,虽然任命审判官,但其实际上为宗君的代言人。换句话说,天子、诸侯、宗君在其所辖区域中,是最高的裁判者,尽管他们不必亲自出面处理案件。到了战国中后期,司法官员的专职化特征已经非常鲜明了,但古来遗风的印记仍然存在。如在包山出土的战国楚简案卷中,左尹是楚国的高级官僚,负责重要案件的审理工作,但在审判中,我们却不时可以看到楚王的身影,包山楚简会出现“左尹以王命告汤公”“左尹以王命告子苑公”之类的表述,道理就在这里。
关于琱生的诉讼,还有一个问题或会产生疑惑,即本案的原告是琱生、那被告是谁?对此铭文中并没有提及。在金文所载的案例中,通常会用“以某甲告(讼)于某乙”的句式加以表述原被告身份,相互关系一目了然,琱生诸器中则未出现这样的语句。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宗族内部诉讼不愿声张矛盾,而琱生提起的诉讼又类似于今天的“确权之诉”,其目的重在消除争议,确定其利益范围,既然大宗做出让步,使琱生获得不少好处,召伯虎又重新制作典册,使琱生的权益得到了确认,那么就没有必要再将争议相对方的名字铸之于铭了。
三、琱生尊中的裁决与命令
琱生二簋的铭文联读,阐明了狱讼事件的来龙去脉,而琱生尊只记录最终处理结果。琱生尊铭文共113字,行文十分讲究,耐人寻味,透露出很多值得关注的信息。琱生簋在阐明狱讼事件的过程时,也提及了案件处理的方案以及最后的裁定结果。但将琱生二簋与琱生尊加以比较时我们会发现,在记录最终裁决结果方面,簋、尊铭文有不少差异,尊铭较簋铭的文字有雷同、有减少、有增加,铭文差异中有深意蕴含。尊铭所载的裁决结果就三句话:
1.我仆庸土田多扰,弋许,勿使散亡。
2.余宕其三,汝宕其二。
3.其兄公,其弟乃。
第一句话与簋铭雷同。簋铭写作“公仆庸土田多扰,弋伯氏从许,勿使散亡”,尊铭只是用字稍有不同——“公”写作“我”,“弋伯氏从许”简略为“弋许”。这体现出铭文转录命令时,并不求绝对忠于原话,只是表其意而已。这句表述的重点在于彰显原则——不要让仆庸田土散亡,乃是处理宗族纠纷的最高原则,所以宗君指示审判官召伯虎,一定要承诺依照这个原则来断案。这个原则是如此的重要,簋铭尊铭都加以著录,并放在文句之首。
第二句话尊铭比簋铭所录相关内容大幅减少,不再提及最初曾考虑过的两种处理方案。五年琱生簋提到宗君曾说,或三比二分割族产、或二比一分割族产,那些未定方案都已经是过去式了。尊铭只关心最后确定的结果,即三比二的方案,这才是琱生家族最需要铭记的。
第三句话在簋铭中没有出现。这句话是宗君发布的告诫:“其兄公,其弟乃(仍)”,即兄长处理公正,弟弟应从。此处的兄长,指召伯虎。尽管实际的裁决者是宗君,但宗君仍然会强调这是召伯虎的处理决定,亦维护其作为审判官的权威,说既然审判官是公正的,那么小宗琱生就应该服从。
以上三句话非常紧凑,是相当严密的裁判书摘要。第一句话表明案件处理的原则,第二句话是案件处理的结果,第三句话是对案件执行的期许。在与琱生簋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琱生尊铭文的重心就在于记录案件结果,而不在于记录案件过程。由此可知,尊铭、簋铭文本的性质是判然有别的,并不能等同视为一个案件的不同阶段记录。
接下来琱生尊铭文叙述了一些礼仪活动,随后便是金文末尾常见的“子孙永宝用”之类的套语。根据一般金文格式,行文到此就要结束了。但在铭文末尾,突然又出现了一段琱生发布的命令:
其有乱兹命,曰:“汝事召人”,公则明亟!

通观琱生尊铭文的整体结构,除了纪年、礼仪和嘏辞而外,其余内容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裁决结果,裁决结果是对小宗琱生的诉讼请求而做出的,将案件处理的原则、案件处理的结果以及对小宗服从履行的期望简明扼要地展现出来。而裁决结果就是小宗对内宣誓权力的依据。第二部分是小宗发布的命令,小宗根据上述裁决,要求以前权属有争议、现在确定属于自己的仆庸服从自己。无论从哪一部分来看,这篇铭文都会成为小宗对内行使权力的依据。那这篇文字是写给谁看的呢?铭文嘏辞套语已给出了答案——子孙永宝用之享。礼器是子孙珍藏使用,铭文自然为家族阅读。家族子孙们将永远知晓此事,遇有仆庸作乱,就可以根据铭文所载的方法,交付公族处理。这或许就是铸造这些礼器的目的所在。
四、结语
西周时期的国家结构和秦以后大不相同。在王畿之外的广大地区,诸侯国是以相当独立的方式进行统治的,而在王朝直辖的畿内地地区,各宗族的独立性亦不容小觑。西周金文显示,宗族通常会设置“三有司”之类的机构处理族内事务,这与王朝的政治架构基本相同。《周礼·秋官》等较晚出现的文献将周代的司法系统放置于类似大一统王朝的格局之下加以描述,其中县、遂、乡直至中央的垂直管理模式清晰可见,然而这种状况必须以领土国家之存在为前提,西周社会尚不具备这种条件。与王朝权力与宗族权力并行的状况类似,王朝司法与宗族司法也并行于西周王畿。我们从金文资料中看到,在不同宗族之间的贵族发生纠纷时,可以通过王朝司法途径加以解决,典型案例出现于曶鼎、五祀卫鼎铭文;宗族内部出现纠纷时,则通过宗族内部的司法途径解决,琱生诸器便提供了这样的案例。当然王朝、宗族这两套系统并不是截然分离的。我们发现,在王权鼎盛时,天子的权力可以干涉到宗族内部纠纷,如本文所举的肃卣铭文便是一例。而宗族势力强大时,国家司法力量亦要退避三舍,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了东周。春秋前期卫国发生州吁之乱,卫国大夫石碏之子石厚参与作乱,在案件处理时,“卫人使右宰丑莅杀州吁于濮”,这是卫国法权力量的体现,而“石碏使其宰獳羊肩莅杀石厚于陈”,则是宗族法权力量的体现。到了春秋后期,郑国子产在处理公孙楚案件时,仍要征询其族长大叔的意见,亦是宗族司法权力的体现。战国以后,宗族权力逐渐被国家权力吸收,宗族司法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而早期宗族内部诉讼的运作方式、社会功能就很少为人所知了。
(本文之写作受益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李峰教授的启发,特此致谢。)
注释:
①参见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卷六,清嘉庆九年自刻本;孙诒让:《古籀拾遗、古籀余论》,中华书局1988年版,“古籀拾遗”第26-27页、“古籀余论”第30-31页;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144页;林沄:《琱生簋新释》,载《古文字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朱凤瀚:《琱生簋新探》,载《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1期;王玉哲:《〈琱生簋铭新探〉跋》,载《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1期。
②参见王沛:《“狱刺”背景下的西周族产析分——以琱生诸器及相关器铭为主的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5期。
③李学勤先生认为“献”指“献酒”,参见李学勤:《琱生诸器铭文联读研究》,载《文物》2007年第8期。
④甚至两篇铭文的行数、字数都基本相同。
⑤林沄:《琱生尊与琱生簋的联读》,载《古文字研究》(第27辑),中华书局2008年版。陈美兰先生亦赞成林沄先生的观点,并从铭文格式、语法上加以证明。参见陈美兰:《说琱生器两种“以”字的用法》,载张光裕、黄德宽主编:《古文字学论集》,安徽大学2008年版。
⑥郑玄:《诗谱·周南召南谱》:“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今属扶风美阳县。”参见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2000年版,第11页。关于琱生尊器形问题的探讨,参见种建荣、杨晓芳:《浅谈扶风五郡出土“琱生尊”的器形及相关问题》,载《文博》2010年第6期。
⑦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1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1页。
⑧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69页。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第2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478页。
⑩铭文中的“播”释为流放、放逐,参见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6页。亦有其他不同释读意见,不具引。
(责任编辑:知 鱼)
Diaosheng Statue and Clan Lawsuit in Western Zhou Dynasty
WANG Pei
(College of Law,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China)
After the unearth of Diaosheng Statue in November 2006, the problem of how to read its inscriptions coherently with the inscriptions of Diaosheng Er Gu hand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s becomes a great concern of the academic world. Lin Yun advocated that their reading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bronze vessels rather than the calendar dates of inscriptions. Accordingly, the reading of the three inscriptions show clan lawsuits in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ongjun (head of the clan) and judges, seignior and appendage, and big Zong (clan) and small Zong (clan) are also reflected. The inscriptions indicated that official judicature and clan judicature coexisted in Western Zhou dynasty. After the period of Warring States, the centralized system was established, and clan judicature gradually perished. The unearthed Diaosheng Statue displayed once again the clan judicature, 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legal history.
Diaosheng Statue, Diaosheng Gu, Western Zhou dynasty, clan judicature
2016-08-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出金文、简牍所见周秦法制变革研究”(16BFX018)
王 沛,陕西西安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法制史研究。
D929
A
1004-8634(2017)01-0065-(07)
10.13852/J.CNKI.JSHNU.2017.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