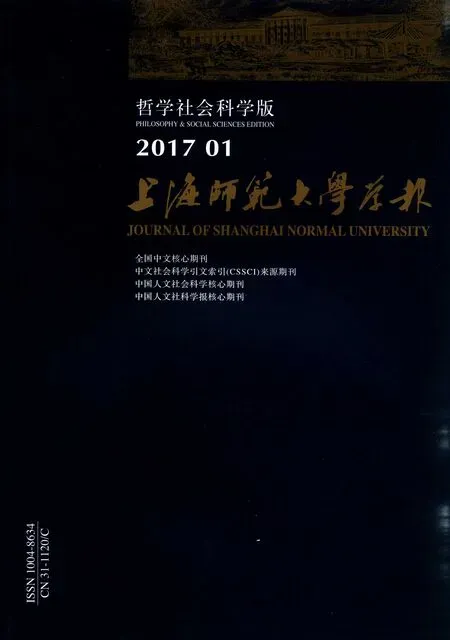宋代两浙路海洋灾害防御工程资金来源考察
刘恒武,金 城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宋代两浙路海洋灾害防御工程资金来源考察
刘恒武,金 城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宋代两浙路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易遭受海溢灾害和咸潮倒灌的侵袭。为了保障沿海邑落及农田的安全,宋代特别注重塘、堰、碶等海洋灾害防御设施的修建与维护。宋代两浙路防海限潮工程得到多渠道的资金支持,塘、堤等大型防海工程的建设经费,主要来自中央财政的拨付;碶、堰等限潮阻咸设施的营造资费,通常依靠地方政府筹集和民间捐助;海洋灾害防御工程的维护资金,则出自军费或地方政府经费。
宋代;两浙路;海洋灾害防御工程;资金来源
宋代沿海地区社会经济较前代有了长足进步,尤其是宋室南迁,定都临安后,沿海农业、渔业、盐业、造船业、航运以及航海贸易发展迅速,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空间与海洋的关系更加密切,故而从海洋获取更多资源的同时,遭受海洋灾害的频度也在增高。宋代两浙路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夏秋季节易受台风影响,导致海溢灾害较多,[1]因此,沿海岸线修筑的海塘,成为宋代政府海洋灾害防御工程的重点。另外,日常海水咸潮沿着滨海河道的回灌,也容易对农业用水和生活淡水造成危害,在这种情况下,防止咸潮浸漫的碶、堰工程也成为必要。
关于宋代两浙路地区海洋灾害防御工程的研究,以往学界常常将其置于江南水利史专题之中加以探讨,如张俊飞的《宋代江南地区水利建设经费来源讨论》一文,主要讨论了宋代江南地区水利建设的经费来源问题;[2]孙垂利、康武刚则从劳动力的角度论述了宋代江南水利建设问题,[3~4]这些成果均触及海塘工程建设。另外,一些海溢灾害和海塘史专论文章也将宋代两浙路纳入考察范围,例如:金城、刘恒武的《宋元时期海溢灾害初探》一文,在探讨宋元时期海溢灾害产生的原因以及海溢灾害之后的政府救助措施之际,列举了大量宋代两浙路的相关史料;[5]陈吉余的《海塘:中国海岸变迁和海塘工程》一书,也述及宋代两浙路海塘工程。[6]就两浙地区海洋灾害防御工程资金来源问题,其相关成果集中于明清时段,复旦大学王大学博士的毕业论文及其发表的系列论文,关注到明清时期浙江海塘工程的经费筹措;[7~9]刘丹、陈君静的《试论清代宁绍地区海塘修筑的经费来源与筹措方式》一文,则就清代宁绍地区的海塘修建资金来源问题做了具体研究。[10]可以说,目前有关宋代两浙路海洋灾害防御工程资金来源问题的成果还相对匮乏,本文拟聚焦这一课题进行系统考察。
一、宋代两浙路海洋灾害防御工程概况
宋代两浙路相当大的区域地处滨海,而且经济生活与海洋息息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宋代两浙路也是海溢灾害发生频度最高的地区。宋元时期共发生102次海溢灾害,江浙沿海地区计有77次,占到总次数的75.5%;其中宋代两浙路海溢灾害共有62次,占到宋元海溢灾害总次数的60.8%。[5]因此,海洋灾害防御工程事关两浙路地域社会的安危。宋代海洋灾害防御工程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沿海岸线修筑的海塘、海堤等防海工程,第二种是沿入海江河的河道修建的碶、堰等限潮阻咸工程。
海塘工程,是为了应对突发性海溢和时发性潮汐而沿海岸线修建的防海设施。两浙路修筑海塘的事例频见于文献中。例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杭州湾一带的海塘毁坏,发运使李溥、内供奉官庐守勤经度,请旨朝廷“请复用钱氏旧法,实石于竹笼,倚叠为岸,固以桩木,环亘可七里。斩材役工,凡数百万,逾年乃成、而钩末壁立,以捍潮势,虽湍涌数丈,不能为害”,[11](卷97《河渠七·东南诸水下》,P2396)之后20余年,杭城无溢潮之虞。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杭州大风雨,江潮溢岸,高六尺,坏堤千余丈”,[11](卷61《五行一上·水上》,P1326)工部郎中张夏在修建海塘时,首次将柴塘改为石塘;[11](卷97《河渠七·东南诸水下》,P2396)庆历七年(1047),谢景初修建余姚海塘,“长二千二百丈,崇五仞,广四丈。自龙山距官浦二千丈修旧而成,增石五版为三十级,自御香亭下创为二百丈”。[12](丁宝臣《石堤记》,P208)此次海塘建设取得良好的成效,使得余姚北部沿海百姓得以安生。
宋室南移,建都临安,浙地成为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两浙海塘建设进一步受到政府重视。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秀州守臣丘崈上奏朝廷,建议重新修建华亭海塘:“华亭县东南大海,古有十八堰,捍御碱潮。其十七久皆捺断,不通里河;独有新泾塘一所不曾筑捺,海水往来,遂害一县民田。缘新泾旧堰迫近大海,潮势湍急,其港面阔难以施工,设或筑捺,决不经久。运港在泾塘向里二十里,比之新泾水势稍缓。若就此筑堰,决可永久,堰外凡管民田,皆无碱潮之害。其运港只可捺堰,不可置闸。不惟濒海土性虚燥,难以建置;兼一日两潮,通放盐运,不减数十百艘,先后不齐,以至通放尽绝,势必昼夜启而不闭,则碱潮无缘断绝。运港堰外别有港汊大小十六,亦合兴修。”[11](卷96《河渠六·东南诸水上》,P2414)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十二月,监察御史崈政殿说书陈大方言:“江潮侵啮堤岸,乞戒饬殿、步两司帅臣,同天府守臣措置修筑,留心任责,或有溃决,咎有攸归。”[11](卷97《河渠七·东南诸水下》,P2396)上述材料反映出宋代政府对两浙路的海塘建设关注有加,已将海塘建设与维护作为地方政府官员的日常责任。海塘的修建与维护事关重大,正如《宝庆四明志》所言:“稍失堤防,风潮冲击,则平田高岸悉为水乡。”[13](卷18《慈溪县志卷第一·叙水》,P977)
本文所说的第二种海洋灾害防御工程——碶、堰,主要是就布设于通海河道沿线、专用于限潮阻咸的沿海地区碶、堰而言的。众所周知,海水在涨潮时会沿着入海河道回流内陆,若沿河两岸低洼处不注意修建堤坝,就会导致咸潮漫灌。北宋水利专家赵霖曾指出:“今濒海之田,惧咸潮之害,皆作堰坝以隔海潮。”[14](卷19《水利上》,P285)
沿海碶、堰等限潮设施的功能是“阻咸”和“蓄淡”。当海潮沿江道回流之际,河水含盐量升高,沿江的居民无法取河水灌溉田地以及饮用;而咸潮一旦外溢,则会造成农田卤化。碶、闸、堰等即是为控制咸潮经路而建设的。一方面,堰、碶等水利设施防止了咸潮的漫溢;另一方面,它们还起到隔离咸水和淡流的作用,蓄涵淡水使之不受咸潮污染,从而保证沿海地区农田灌溉用水的需要。宋代两浙路沿海地区在通海的河道上相继修建了不少碶、堰及通海河口的水闸。宝祐五年(1257),慈溪县修建的新堰“捍江潮而护河流”,因而使“慈溪、定海两邑之田,无斥卤浸淫之害”。[15](卷3《水利》,P106)
浙东地区独有的碶,是一种设有闸口的止水设施,有内外之分。内碶如乌金碶、积渎碶,外碶如镇海穿山碶、象山朝宗碶等。其中外碶具有截潮阻咸功能,是为“治石碶以御海潮”;内碶具有却潮爆、纳淡之功能。宋代浙东地区最为著名的它山堰,它和乌金碶、积渎碶、行春碶等配套设施形成完整的水利系统,不仅可以阻断咸潮对内地的侵蚀,还可以在旱灾时提供水源,可谓一举两得。它山堰虽建于唐代,但宋代两浙路政府却多次进行维修。如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两浙路政府对乌金碶、积渎碶、行春碶进行维修。淳祐二年(1242)秋,因井泉咸卤,农不能耕,庆元知府陈垲对它山堰进行了维修,同时又新建保丰碶。[13](卷12《鄞县志卷第一·叙水》,P665)唐代象山有朝宗、理川、灵长、会源四碶,入宋后依然发挥断咸蓄淡的功能,造福当地百姓。例如,治平年间(1064—1067)知县林旦对朝宗碶进行过维修,绍兴八年(1138)和隆兴元年(1163)当地县政府也都对此碶进行过修缮,为民称颂。[16](卷10《重修朝宗石碶记》,P347~354)除了鄞县、象山之外,浙东其他地方的碶还有很多,如慈溪的茅针碶、[15](卷3《水利》,P102)定海县的通山碶等。[13](卷18《定海县志卷第一·叙水》,P981)
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可以了解到,宋代两浙路政府为了防御海溢灾害而大力兴建海塘工程,为了应对咸潮回灌而不遗余力地建设碶堰设施。这些沿海水利工程的兴建与新修需要巨额财政的投入,下文将对宋代两浙路沿海水利工程的资金问题进行详细探讨。
二、宋代两浙路海洋灾害防御工程的资金来源
宋代两浙路抗御海溢灾害的海塘工程往往规模巨大,不仅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去施工建设,还需要源源不断地投入资金进行维护。兼具限潮防咸和蓄水防旱功能的碶、堰工程,亦需要汇集多方力量才能完成。查诸史料,两宋时期两浙路海洋灾害防御工程资金分别来自中央朝廷、地方官府和民间社会,以下对其具体情况进行考察。
1.朝廷拨付
首先,根据文献记载可知,无论内陆与沿海,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规模水利工程,大都需要朝廷中央财政的支持才能完成。宋代特别注重水利建设,宋神宗曾言,在利农防灾的关键水利设施修建上“纵用内藏钱,亦何惜也”。[18](卷240,P5832)熙宁五年(1072),浙西水灾,朝廷“赐谷十万石赈之,仍募民兴水利”。[11](卷15《神宗二》,P281)熙宁六年(1073)九月,“诏各拨常平司粮三万石,(真、扬、润三州) 募饥民兴修农田水利”。[18](卷247,P6011)熙宁期间,全国各地的水利设施建设进入高潮,也必然带动两浙路海洋灾害防御工程的兴建,然而囿于史料的不足,两浙路防海限潮工程的具体数量尚无法计查。不过冀朝鼎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一书中有关浙江水利工程建设的统计,可为我们了解两浙路沿海水利工程建设的时代变化趋势提供参考,兹将其研究改录如表1:[19](P40)

表1 古代浙江水利工程建设统计简表 单位:个
以上冀朝鼎的统计数据虽聚焦于浙江水利工程,但两浙路水利建设工程的量增趋势应该是与之吻合的。从表1中可以看出,南宋浙江地区水利工程数量骤增,远远超过北宋,这无疑与宋室南渡后两浙成为京畿腹地有关。孝宗即位之初曾下诏重申兴修水利之重要性:“朕惟旱干、水溢之灾……农为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谷也。今诸道名川,山原甚众,民未知其利。然则通沟渎、瀦陂泽,监司、守令顾非其职欤?其为朕相丘陵原隰之宜,勉农桑,尽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时。虽有丰凶,而力田不至拱于受弊,亦天人相因之理也。朕将即勤惰而富赏罚焉。”[11](卷173《食货上一·农田》,P4187)需要指出的是,南宋定都临安,两浙沿海随之成为京畿赋税重地,沿海水利工程自然受到宋廷的关注。孝宗诏令的宣谕内容,应涵盖两浙路海洋灾害防御工程的营造。
根据文献中记载的事例,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宋廷对于两浙路防海限潮工程建设的财政支持。如乾道二年(1166)十月孝宗诏曰:“温州近被大风驾潮,淹死户口,排到屋舍,失坏官物,其灾异常,合行宽恤,可令度支郎中唐瑑同提举常平宋藻、知州刘孝韪共议,酌参措置,条具闻奏。仍令内藏库支降钱二万贯,付温州专充修筑塘埭斗门使用,疾速如法修整,不得灭裂。”[17](《食货》59之43,P5860)再如,淳熙年间(1174-1189)朝廷筹划修建定海石塘,下诏“令唐叔翰与水军统制王彦举统领董珍申府闻于朝,支降钱米效钱塘江例”,[13](卷18《定海县志卷第一·叙水》,P977)林栗的《海塘记》对此次明州定海县新建的海塘有详细的记载,用役工、军民凡30余万人,海塘“高十有一层,侧厚数尺,敷平倍之;广袤六千五十尺有赢,基广九尺”,核其费用“诏赐缗钱六万五千有奇”;[12](林栗《海塘记》,P70)嘉定十四年(1221),宁宗“诏令葑桩库于见桩管度牒内,支拨一十二道付庆元府,每道作八百贯文,变卖价钱,充修砌上水、乌金等处碶坝,及开掘夹砌、道士堰、朱赖堰工物等使用”;[17](《食货》61之49,P5948)嘉定十五年(1222),宁宗又下诏,令有关部门支拨资费,开工修定海海塘“接连增甃五百二十丈,盖府荐有请朝廷续赐费也”。[13](卷18《定海县志卷第一·叙水》,P978)
以上文献史料中言及的“内藏库”和“葑桩库”均为宋廷中央财库,而“诏赐缗钱”“朝廷续赐费”等记录也都是言指朝廷拨付钱费的财务行为。同时,上述史料还反映出,中央拨款资助的海洋灾害防御工程,以沿海岸线的大规模海塘修筑工事为主。类似宁宗诏助庆元府修砌限潮碶坝的事例并不多见,而且这一事例亦非直拨钱款,而是以支拨有价度牒的形式进行资助。
2.州县筹措
宋代地方政府既是防海工程的督建方,也是部分资金的出资方。文献史料显示,宋代两浙沿海州县筹资兴建了相当数量的水利工程,其中包括不少诸如碶之类具有海洋灾害防御功能的设施。例如,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知鄞县,筹资在海晏乡修建通山碶;[13](卷18《定海县志卷第一·叙水》,P981)绍兴八年(1138),象山县令宋砥筹措300万钱对朝宗碶进行大修,“不避盲风苦雾之毒,躬即其地,以勉民作,浚其流泉,增其堤围,尽发旧址,革而新之,余堰例加修之”;[16](卷10《修朝宗石碶记》,P347~354)宝祐五年(1257),慈溪县在旧址旁修建茅针碶,支出钱42717贯,米213石;[15](卷3《水利》,P101)宝祐六年(1258),浙东制置使吴潜对鄞县它山洪水湾原有碶闸进行增建,扩大原有规模,“其地为坝三,一濒江以御狂澜,一濒河以防罅漏,一则介其间为表里之”。[15](卷3《水利》,P103~104)开庆元年(1259)夏,吴潜又在庆元(今宁波)府城保丰碶右侧建立永丰碶,整个工程共用钱44628贯900文、米168石5斗4升。[15](卷3《水利》,P100~101)以上列举的工程费用均由地方官府筹集,常平仓钱谷是地方州县兴修水利的常费。文献记曰:“诸兴修农田水利而募被灾饥流民充役者,其工直粮食以常平钱谷给。”[20](P13)不过,州县官方另筹款项的情况也属常态。
《开庆四明续志》中记录了它山洪水湾工程费用的主要清单:[15](卷3《水利》,P103~104)
买何仪曾园地三十二亩一角二十六步,内一契何津之买赵念一省元地一片,计二十三亩二角四十九步,价钱六十贯足。内一契林千十一娘,男何津买葛子昇户下,千十地八亩二角三十七步,价钱三十贯文九十八陌钱,会各半共纽计一千三百四十贯四百五十五文。木桩一千五百口,计钱一万五百贯;搭脑八十条,计钱一千六百贯;篠二百把,计钱三百贯。下(木)桩搭脑七百九十工,计钱二千六百七十五贯。监宫(官)人从口券,二千八百八十贯;监官主簿特送三百贯,正将郑琼、都吏王松犒二千贯、酒二十瓶。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洪水湾碶闸的修建费用主要涉及了购地费、工程材料费和劳务费等,同时清单中也记载了府署官员集纳的款额;这些费用都是保障该工程实施的硬性条件。另外,从文献材料可以看到,沿海州县官府筹资完成的海洋灾害防御工程,以碶、堰、闸等限潮阻咸设施为主,这反映出地方财政难以支持海塘等大规模防海工程营建的现实。
3.民间捐助
宋代政府一向重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尤其是神宗时期颁布的《农田利害条约》,让各路常平官专领农田水利。[11](卷95《河渠五》,P2367)该法案的颁布并实施,对两浙路的水利工程建设影响巨大,不仅促进了水利灌溉的兴修,而且为两浙路水利工程建设上财力与人力的民间动员确立了制度依据。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二月,“两浙西路宣谕胡蒙言:‘乞行下两浙诸州军府,委官相度管下县分乡村,劝诱有田产上中户量出工料,相度利害,预行补治堤防、圩岸等,以备水患,庶免将来有害民田’”。[17](《食货》7之42,P4926)由此可知,如遇水利工程建设需要,地方政府可要求上、中富户进行襄助。
相关史料表明,宋代地方新建沿海水利工程(包括海洋灾害防御工程)时,相当一部分资金源自民间捐募,民间大富之家为沿海水利工程建设解囊出资的事例屡见不鲜。例如,熙宁年间(1068—1077)奉化县人王元章的先人曾出资兴建刘大河碶;建炎三年(1129),王元章请于政府,对刘大河碶进行重修。[13](卷14,P790)再如,绍兴十五年(1145),温州平阳人吴蕴古捐材料建设沙塘斗门;绍兴十六年(1146)春,在修建新的沙塘斗门时,“役工于千,糜钱百余万,皆二邑民辅之”。[12](宋之才《沙塘斗门记》,P212)淳熙十三年(1186),慈溪县主簿赵汝积令西屿乡民众“凡田于西者,亩出钱三百”,用于翻修彭山堰。[13](卷16《慈溪县志卷第一·叙水》,P888)楼钥的《海堤记》中记载:庆元二年(1196)余姚修海堤,“监司提举常平刘公诚之,首助谷三百斛……县出缗钱四千三百有奇,县之士夫与其乡人助工三百万”。[12](P215)宝祐五年(1257),庆元府鄞塘乡修练木碶,“官劝谕首以千券十斛助费,已而乡民见义,不勇讼牒纷如助者仅五千余缗力绵,而役大委之民,曷溃于成公。乃一力捐金谷为之。以明年正月二十八日经始碶,当江湖之冲,虑其损碶臂也,增新碶为四眼,杀其势,阅三月而碶成。凡给钱四万四千六百二十八贯九百文,米一百六十八石五斗四升,力役于伍籍费取于公帑,民无毫发扰,持羊酒以劳役夫者,日络绎于道也”。[15](卷3《水利》,P103~104)类似事例在宋代地方志中多有记载,此处不再赘举。
宋代经济发达,社会繁荣,因此,海洋灾害防御工程能够得到多渠道的财务支持。一方面朝廷通过拨款修建工程,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会筹措经费用于工程建设。此外,民间力量也在防海限潮设施的营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地方的大富之家,或旨在造福乡梓,或为了抬升自身声望,往往以出资捐料的形式助修沿海碶、堰以及海堤。
三、宋代两浙路防海限潮设施维护资金来源
宋代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重视海洋灾害防御工程的建设,每每投入巨资营建海塘、碶、堰等设施,但由于两浙路海溢灾害时常发生,海塘屡有毁堕。如宋孝宗淳熙四年(1176)五月,“钱塘江涛大溢,败临安府隄八十余丈,庚子又败百余丈。明州滨海大风,海涛败定海县隄二千五百余丈;鄞县五千一百余丈,漂没民田”。[11](卷61《五行一上·水上》,P1332)是年九月,海溢灾害又突然发生,而且比五月发生的范围更广、灾情更为严重,“大风雨驾海涛,败钱塘县隄三百余丈;余姚县溺死四十余人,败隄二千五百六十余丈;败上虞县隄及梁湖堰及运河岸;定海县败隄二千五百余丈;鄞县败隄五千一百余丈”。[11](卷61《五行一上·水上》,P1322)
宋代政府为了维持防海限潮设施的正常功能,延长工程使用寿命,需要对相关设施进行日常性和定期性的养护与修治。宋代专门组织捍江兵或堰兵负责海塘的日常修治,两浙路相关文献中可以找到这样的事例。如景祐四年(1037),工部郎中张夏在督治钱江石塘时,“置捍江兵士五指挥专采石修塘,随损随治”。[11](卷97《河渠七·东南诸水下》,P2396)南宋乾道九年(1173),宋廷在华亭县招兵50人,巡逻堤堰,专一禁戢,将卑薄处时加修捺。[11](卷96《河渠六·东南诸水上》,P2415)捍江兵应属于宋代正规部队序列,虽然宋代捍江兵具体人数不可知,但应该不在少数。如淳祐《临安志》卷第六载,五指挥共有兵额两千人。[21](P103)依宋代官兵的最高月俸可达5贯,最低为300文,则捍江兵的军费诚为一笔不小的开支。宝祐五年(1257)慈溪修治茅针碶,都吏王松曰:“本府即为民间办此一事,钱不须科之都保,本府一切自办以了一方悠久无穷之利,工役之人,不若只用军兵,日增支钱一贯五百文,米三升,庶可钤束。”[15](卷3《水利》,P103)由此可见,在宋代,军兵参与维修防海设施是一种常态,士兵俸禄由宋廷财政支付,这实际上相当于将部分军费转用在了防海设施的维护上。
除此之外,两浙路地方政府还通过自筹工费、雇募力役来对所建防海设施进行定期修治和养护。如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十一月,浙西提举刘颖曰:“华亭县塘岸西绵亘七十余里,所管堰兵不多,每遇修葺,全藉食利人户。以为所筑堤岸,止是沙土,每岁未少有坍损……目今潮泥填塞,生出芦柴,约岁可得柴三万余束,若以一半为看管、采斫工力之费外,岁可得钱三数百千。”[17](食货61之130,P5938)此处所举的华亭县塘事例中,地方官府通过售卖塘外潮泥所生芦柴,解决了塘堤年度维修的资费。
由此可见,宋代政府对于海洋灾害的防御十分重视,这不但体现在启动相关工程时投入巨资,也体现在防海限潮设施建成投入使用之后,官方通过多种方式筹措资金、安排人力进行维护和修治。
四、结 论
综上所述,有宋一代我国东南沿海得到充分开发,尤其是南宋时期,两浙路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随着沿海地域社会的发展,两浙路地区近海、涉海的经济活动不断增多,海溢等灾害造成的危害性大大超过以往,不仅给沿海地区造成人员伤亡,而且还造成大量的财产损失,严重地影响到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为了应对频发的海洋灾害,宋代两浙路十分重视海洋灾害防御工程建设。根据上文考察,相关工程资金来源有三:朝廷拨付、州县筹措、民间捐助。宋廷拨付的钱款主要用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型海洋灾害防御工程建设,相关工程以海塘为主;地方政府筹集和民间捐助的资费,大多用于局部区域日常限潮、阻咸、蓄淡的碶、堰工程。在海洋灾害防御工程的日常性管理和维护上,宋代两浙路一方面借助捍江兵力量(中央廪费支持)进行日常的检视和养护,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往往自行筹款对海洋灾害防御设施进行必要的维护。海洋灾害防御工程的营造和修治,为两浙路沿海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1] 张培坤,等.浙江气候及其应用[M].北京:气象出版社,1999.
[2] 张俊飞.宋代江南地区水利建设经费来源讨论[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6).
[3] 孙垂利.从在水利事业中的作用看宋代的民间力量——以江南地区为中心考察[J].井冈山学院学报,2006,(2).
[4] 康武刚.宋代江南水利建设中劳动力的筹措[J].农业考古,2014,(3).
[5] 金城,刘恒武.宋元时期海溢灾害初探[J].太平洋学报,2015,(11).
[6] 陈吉余.海塘:中国海岸变迁和海塘工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7] 王大学.明清江南海塘的建设与环境[D]. 复旦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07.
[8] 王大学.古代大型公共水利工程日常维修制度形成中的环境与政治——以清代两浙海塘岁修、抢修制度为中心[J].社会科学, 2014,(8).
[9] 王大学.政令、时令与江南海塘北段工程[J]. 史林,2008,(5).
[10] 刘丹,陈君静.试论清代宁绍地区海塘修筑的经费来源与筹措方式[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4).
[11]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2] 闫彦,等.浙江海潮·海塘艺文[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13] 宁波明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宝庆四明志[M]. 宁波:宁波出版社,2011.
[14] 范成大.吴郡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15] 宁波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开庆四明续志[M]. 宁波:宁波出版社,2011.
[16] 宁波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乾道四明图经[M]. 宁波:宁波出版社,2011.
[17] 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9]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M].朱诗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0] 朱熹.晦庵先生文集[M].北京:线装书局出版社,2004.
[21] 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宋元地方志集成[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申 浩)
A Study on Construction Funding Sources of the Preventive Facilities Against Marine Disaster of Liangzhe Area in Song Dynasty
LIU Hengwu, JIN Cheng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and Communication,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Liangzhe area, located in the southeast coast of China, is vulnerable to the marine disasters and seawater invasion. In order to guarantee the security of the coastal settlement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government of Song Dynasty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ang (seawall), Yan, Qi and other marine disaster preventive facilities. According to this study, the constructions of such large-scale as seawalls mainly depended on the funding allotmen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Qi, Yan and other seawater invasion-preventive projects relied on the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ng and private donations. As to the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f the marine disaster preventive facilities, the main sources of funding were from the military fund and loc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Song Dynasty, the Liangzhe area, marine disaster preventive facilities, funding source
2016-05-21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5NDJC075YB)资助成果;2016年宁波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危机与应对:宋代两浙路灾害与社会研究”阶段性成果
刘恒武,陕西岐山人,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海洋文化交流史研究。
K244
A
1004-8634(2017)01-0139-(06)
10.13852/J.CNKI.JSHNU.2017.01.018
金 城,安徽六安人,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主要从事宋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