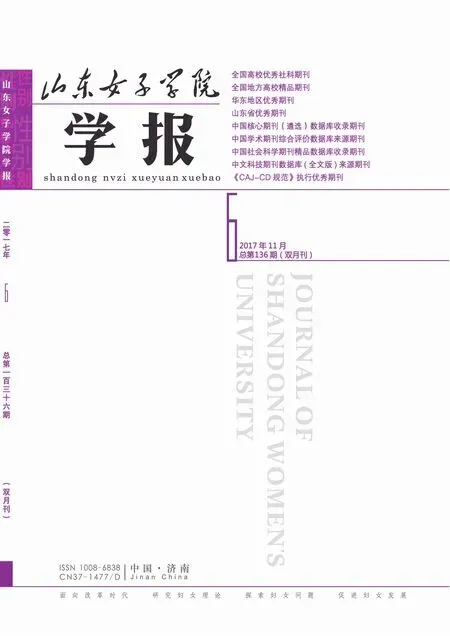女涉外业:晚明闺阁生活之新动向
蓝 青
(中山大学,广东 珠海 519082)
·女性文化研究·
女涉外业:晚明闺阁生活之新动向
蓝 青
(中山大学,广东 珠海 519082)
“女涉外业”是晚明颇值得关注的社会与文化现象。晚明特殊的社会环境为知识女性提供了相对宽松的舆论空间,她们开始不安于阃内、不甘以织纫为本业,而是积极涉足史学、佛学、旅游、政治等本属男性之领域。女涉外业不仅使女性自身气质向文人名士转化,亦深刻地影响了才女们的文学创作,促使其作品在题材内容上由阃内转向阃外,艺术风格上由纤细柔弱转向豪迈宏阔,也对封建礼法造成了一定冲击。
晚明;女性;史学;佛学;政治
传统的儒家性别伦理对于男女之职有着严格的区分,“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1],“妇人之事,存于织纴组紃、酒浆醯醢而已”[2],女性应当安于阃内、以饔飱井臼为本业,而诸如佛禅文史等则属于外业,受到严格的限制。至晚明,这种观念频遭质疑。晚明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思想领域之解放,社会上兴起一股张扬个性与释放人欲的思潮,这对封建伦理道德产生了一定冲击,不少开明世家颇以才女为荣,社会上亦形成了重视才女文化的良好氛围。如泰州学派领袖人物李贽勇于批判“妇人见短,不堪学道”的言论,其《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关于男女见识长短之言论广为现代学者征引。李贽大胆宣称:“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3]李贽认为女性同样可以修德习文,其才学与能力并不亚于男性。类似的观点在晚明几可谓俯拾皆是,如徐咸清曰:“夫闺阁亦人耳,少苟诵读,与男儿何异”[4]。葛征奇曰:“非以天地灵秀之气,不钟于男子;若将宇宙文字之场,应属乎妇人。”[5]这就为晚明女性涉足“外业”奠定了必要的舆论基础。
在这种较为宽松的社会舆论空间中,女性对文学、史学、佛学、旅游、政治等本不属于女性之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大有“外业”超过本业之势,如屠隆称其家中女眷“但有图书箧,都无针线箱”[6];钱谦益称桐城才女方维仪、吴令仪皆“以文史代织纫”[7](下册,P736),这是前代所少有的现象,颇值得深入探讨。然而,目前除文学外,史学、禅学等晚明女性所涉及领域并未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晚明闺阁生活内容之变化不仅对女性的思想心态与精神气质产生了深刻影响,亦对其夫妻关系与社会交游形成了一定影响,还促使其作品的题材内容与艺术风格发生重要改变,所以研究晚明知识女性生活之新动向,具有多维度的意义。本文拟对晚明女性读史咏史、奉佛参禅、外出游历、经世济民等问题逐一考察,以期对晚明女性史及女性文学研究有所助益。
一、读史咏史
在古代社会,史学领域向来为男性所专属,虽然汉代即有班昭治史,但毕竟属于少数。至晚明,治史作为一种风气在闺阁中盛行开来,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女性涉猎史学的例子可谓俯拾皆是,如吴令仪“喜读书史、女传”[8](卷19,P229),周琼“喜纵观古史书”[9](卷12,P636),董少玉“喜读史汉诸子书”[10],朱中楣“女红之余,朝夕一小楼,丹铅批阅于纲鉴史记及诸家诗集,成诵不遗一字”[11](卷8,P468),顾若璞自述“自四子经传,以及《古史鉴》《皇明通纪》《大政纪》之属,日夜披览如不及”[12](卷6,P839),张娴倩自称“尝因读史忘春去”[13](上册,P558)。这一时期不少女性对史学的热衷程度甚至达到了取代女红的地步,如王端淑自幼痴迷于史学,其夫丁圣肇称其“性嗜史书,工笔墨,不屑女工”[14]。晚明知识女性对史学的热衷与其家学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卞梦钰“幼颖慧,其父母教之以文史之学,靡不博通”[15](卷1,P1728),桑贞白“幼荷严母庭诲,日究女训、列传、经史,以明古今”[16](P148),袁九淑“少读经史”[16](P151)。良好的家学环境无疑是史学流行于晚明闺阁的一个重要因素。
晚明女性不仅热衷于阅读史书,而且对历史有着自己的判断。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女性创作的史论著作。如余玉馨著有史论数百篇,“皆自出己见”[17];陆静专著有《读史评》,“于古今疑义,多所阐发”[16](P138);徐德英著有《批点二十一史》以及六朝隋唐史论数十篇,姚旅评其“即老吏断狱不如也”[18];王端淑著有《史愚》《历代帝王后妃考》,陈维崧称其“意气落落,尤长史学”[19](P19),毛奇龄更是赞其“著书不让汉时史”[20]。
对史学的浸染深刻地影响了女性的文学创作,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女性咏史诗。这些诗歌或感叹历史兴衰无常,如顾若璞《秋夜读史》中的“六出奇谋美丈夫,只今尺土姓刘无”[21];或表达对忠臣的仰慕与钦佩,如王端淑《方文正忠烈公孝孺》中的“慨题绝命词,正气宁甘戮”[22](卷4,P12);或指斥权奸误国,如邓铃《读岳武鄂王传》中的“英雄誓复旧山河,曾奈奸邪误国何”[23];或感慨荒淫亡国,如戴玺《读隋史》中的“佳人剪彩争新宠,一瞬繁华万古愁”[24],等等。闺阁诗历来以抒情为主,较少思辨性与哲理性,故“以女子能组织史事,殊为难得”[25]。咏史诗凝聚了女性对于历史的思考与体悟,为以感性为主的闺阁创作注入了一股强烈的理性色彩。
晚明女性审视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时,往往从女性自身出发,体现出迥异于男性的独特的历史视角。如王端淑的《西施》:“倩水照颜色,飘流逐片纱。固知随国灭,应悔误夫差。”[22](卷11,P56)既没有将西施写成红颜祸水,亦没有将其写成有大觉悟的女英雄,而是将着眼点放在女性命运上,关注政治斗争给女性自身带来的影响,以女性视角审视历史,颇具特色。又如黄幼藻的《题明妃出塞图》:“天外边风扑面沙,举头何处是中华。早知身被丹青误,但嫁巫山百姓家。”[26]从女性自身处境出发,重新思索昭君命运,认为与其深锁宫闱、远嫁塞外,反不如普通百姓的生活自在,独树新说,尤为卓见。
中国古代史书绝大多数为男性叙写,不少杰出的女性人物被史家忽略或边缘化,晚明女性对此表现出一定的不满,她们极力发掘被男性书写所遮蔽的女性形象。如方维仪的《读苏武传》:“从军老大还,白发生已久。但有汉忠臣,谁怜苏氏妇。”[27]方维仪一反以往将着眼点全部放在苏武身上的论调,将注意力集中到苏武家中的妻子,感叹苏武妻子多年来默默承担的苦痛,视角独特,观点新颖。又如周淑禧的《杜康庙》:“酺有新糟醊有醨,杜康桥上客题诗。最为苦相身为女,千载曾无仪狄祠。”[28](第8册,P4195)为身为女性的仪狄扼腕叹息,并借以阐发对男性历史书写的不满。对史学的浸染亦推动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开始认识到女性独立的人格与价值。如徐媛的《班婕妤二首·其二》:“半道恩销谢辇余,搦残银管夜窗虚。高情不问羊车路,独对寒窗自校书。”[29](卷8,P372)班婕妤在诗歌史上历来多为备受冷落、哀怨凄婉的形象,而徐媛笔下的班婕妤不再依附于男性,而是拥有了独立的思想与自尊,并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是尤为可贵的。又如徐媛的《明妃三首·其二》:“塞外无春边草枯,玉关音信向来孤。自将花貌平戎虏,不用中朝金仆姑。”[29](卷8,P377)赋予昭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亦反映出女性渴望做出一番救国济民的壮举。这种独立的人格意识开启了女性觉醒的先河,其意义自不待言。
二、奉佛参禅
万历时期,士大夫阶层兴起一股佛禅之风,其影响所及,家中女性奉佛者颇众。如张履祥称:“近世士大夫多师沙门,江南为甚,至帅其妻子妇女,以称弟子于和尚之门。”[30]晚明知识女性崇佛好禅多受家庭环境影响,呈现家庭化特征。如屠隆罢官后,以参禅修佛为己任,自号鸿苞居士;妻子杨枚颇通佛理,屠隆的《鸿苞集》中存有不少与杨氏探讨佛法的记载;女儿屠瑶瑟、子媳沈七襄亦喜佛禅,传奇《修文记》即屠隆一家奉佛之写照。吴江叶绍袁一家皆奉佛禅,“精心禅悦,庭闱颇似莲邦”[13](P22);叶绍袁素究心禅学,妻子沈宜修“究心内典,竺干秘函,无不彼观,楞严维摩,朗晰大旨”[13](P226),家奉戒杀甚严,儿女自幼“即知以放生为乐”[13](P227),长女叶纨纨、次女叶小纨、三女叶小鸾皆通佛禅典籍,“皈心法门,日诵梵荚,精专自课”[7](下册,P755)。袁宗道一家女眷皆“长素念佛,精勤之甚,辰昏梵呗,宛同兰若。”[31](卷16,P230)
明太祖规定男性四十岁以上、女性五十岁以上方可出家,晚明女信徒大多属于居家修行,因此更多注重心性修持,较少关注戒律,且往往采取宗教信仰与家庭伦理兼重的修行模式。如吴令仪“乐禅妙,能读《楞严》《悟真》诸篇”[16](P101),同时“孝翁姑,相夫教子,具有仪法”[8];沈宜修不仅“日诵诸梵荚,以为常课”,而且“克谐伉俪,适太翁早逝,事姑太夫人独以孝闻”[13](P22-23);范姝既“布衣椎髻,长斋绣佛前”,又与其夫李延公“风雨相慰劳,不少辍”[15](卷1,P1751)。这些才女虽颇通禅学,然而佛教于其只是一种修养,并未与家庭伦理产生冲突。当然,晚明才女中亦有执意弃绝家庭伦理者。如袁宏道之女袁禅那,性格沉静,“闻佛法欲受戒”,父母以“儿女身且适人,不得具戒”[32](中册,P735)相劝,但禅那却执意出家,未几染病而逝。又如黄埈,生而隽慧,十四五即精虔梵呗,“见世间欢喜恩爱事,辄曰:‘此热闹场苦海轮回,何时得已。’”黄埈“力求出家”,众人劝之未果,后“披剃而即逝,年十九”[33]。再如黄双蕙“髫年禅悦,绝意家室”[34],年十六而卒。然而,相较居家修行,脱离家庭伦理者毕竟属于少数。
明清才女不仅奉佛者众,而且颇具宗教修养,甚至出现了宗教领袖式人物,这是前代所不多见的。如袁宗道之女对佛经颇有研究,“能通竺典,诵《金刚经》,时有问答,皆出意外”[31](卷16,229),袁宗道赞其为“灵照”;梅国桢之女梅澹然精通佛典,常与其父及李贽探讨佛教教义,“书牍往来,颇有问难”[32](中册,P718);屠隆之妻杨枚、女屠瑶瑟、子媳沈七襄皆具有一定的佛教修养,一家人常相聚探究佛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锡爵之女昙阳子。昙阳子俗名王焘贞,主张三教合一,创恬澹教,“以静悟为入门,以恬澹无欲为教主”[35]。她在晚明颇具影响力与号召力,众多文人名士如王世贞、王世懋、王锡爵、王衡、管志道、屠隆、冯梦祯、虞淳熙等纷纷拜其门下。昙阳子升仙之日,前来围观者多达十余万,轰动一时。昙阳子对当时文人的精神与文学创作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例如王世贞晚年思想由经世济民转向清虚恬澹,作品由雄浑悲壮转向“以恬澹自然为宗”[36],即与昙阳子之教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①。
晚明才女纷纷涉足释教,佛禅信仰在闺阁生活与诗歌创作中有多层面的体现:或与僧尼交游酬赠,如王端淑的《赠比丘尼纯宗师寿》、沈宜修的《赠灵仪师》、袁九淑的《赠尼无垢朝普陀二首》等;或幽居参禅,如吴山《禅堂》中的“坐石禅机逸,宣经法性森”[13](P574),王端淑《新居·其三》中的“残篇饶课子,啜茗学参禅”[22](卷7,P29);或拜佛礼佛,如屠瑶瑟《礼观音大士》中的“千江一片月轮孤,直是禅心映玉壶”[37](P88),沈七襄《礼观音大士和湘灵》中的“莲花宝坐百由旬,莲表禅心不染尘”[37](P88);或诵经念佛,如袁九淑《晨起读〈楞严〉、〈圆觉〉诸经二首·其二》中的“朗诵金函三万字,舌端仿佛现青莲”[38],邢慈静《有感》中的“忏悔身心淡幻情,名香一烛读心经”[39]等等。佛禅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女性的文学创作,不少才女在诗中大量连缀佛语,阐扬佛禅教义。如邢慈静的《念佛》:“佛本在心不在天,心却无佛何用念。但将一片念佛心,当做三尺降魔剑。”[39]叶小鸾的《晓起闻梵声感悟》:“悟时心共冰俱冷,迷处安知麝是香。堪叹阎浮多苦恼,何时同得度慈航。”[13](P324)佛禅信仰亦影响了才女们的审美取向,突出表现在对清静幽僻意境的偏好,她们创作出众多富有禅意的佳句。如邢慈静的《静坐》:“闲来抛线坐来深,静里频将面目寻。天地两忘身是幻,一潭清影月沉沉”[39];王端淑的《山居夜咏》:“欲知更漏永,远寺断钟声。月接清溪影,风飕败竹鸣”[22](卷8,P31)等等,澄净清远,幽寒明寂,耐人寻绎。佛教讲求“戒绮语”,故相较脂粉气,诸奉佛才女集中更多清疏气。如钱庄嘉的“偈语如病体,若孤灯,微微映东壁,竟似唐人清妙之辞”[16](P201);吴琪诗“灵气飘渺,如梦中变幻”[16](P104)。
三、外出游历
儒家性别伦理对于男女有着严格的空间规定,男性被定位于“外”,女性被定位于“内”,整个社会建立在内外空间严格分离的基础上,女性被幽禁于闺阁内已经成为一种规范。自程朱理学兴起,女性的活动范围受到更加严苛的限制。限制女性出行自由这一观念在明代依然存在,如庞尚鹏的《庞氏家训》云:“女子六岁诵《女诫》,不许出闺门”[40]。许相卿的《许云村贻谋》云:“女妇日守闺阁,躬习纺织,至老勿逾内门,下及侍女,亦同约束。”[41]然而,实际上晚明不少闺秀都有走出闺门的经历,她们或是随夫宦游,或是夫妻同游,甚至如男性般自由地览尽名山大川,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至老勿逾内门”的儒家伦理规训。
晚明女性在节日时具有一定的出行自由,这在地方志文献中屡见不鲜。如《(万历)扬州府志》载:“清明前后三五日,郡人士女靓容冶服,游集胜地,陆行踏青,舟行游湖。”[42]《苏州府志》载,端午节时,“龙舟竞渡,以朔日始,士女出游,灯船奇丽,甲于天下”[43]。不少才女都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描述过节日外出游玩的情景。如朱中楣描绘元夕游灯市所见繁华街景:“落梅惊舞鹤,高火矗遥天。皓魄层层雪,香尘步步莲。”[37](卷12,P95)徐媛记录元夕时女子出游之乐:“灯火三展乐事浓,君王不禁夜行踪。踏歌少妇娇如玉,对对妆临淡月容。”[29](卷8,P376)沈宪英在《水龙吟·胥江竞渡》中描绘端午节外出游玩所见熙攘人群:“纨扇初裁,罗衣乍试,又逢重午。万户千门,游人争出,争悬艾虎。”[44]叶小鸾述闺中姐妹端午泛舟之事:“酒泛菖蒲香玉碎,嫩红双靥横秋。画船何处闹歌楼,萧萧烟雨外,还锁楚江愁。”[13](P341)外出郊游给人带来的不仅仅是与山水自然亲近的机会,更有着情怀释放的愉悦和暂获自由的欣喜。
晚明商业的繁荣以及士人价值观念的转变,促使山水游赏风气在士大夫阶层甚为盛行。由于这一时期夫妻关系较前代有所变化,许多夫妻“伦则夫妇,契兼朋友”[13](P211),夫妇同游遂成为一时风气。如邓太妙与其夫文翔凤伉俪情深,“太青以谢蕴、徐淑视邓,而邓则以孔、孟、伊、周事太青,交相得也”,二人常于春秋佳日“访未央之故丘,问城南之遗迹,登车吊古,夫妇唱酬,笔墨横飞,争先斗捷”[7](下册,P758)。梁孟昭与其夫茅九仍感情深厚,“尝偕九仍游金陵,历姑苏,出京口,溯金、焦大江而上。诗亦满箧,乐其山水风土”[15](卷1,P1733)。值得注意的是,晚明还出现了女性独立游览名山大川的情况。如吴琪性耽山水,“意殊慷慨,不作男女态。慕钱塘山水之胜,乃与才女周羽步为六桥三竺之游”[45](P12);翁孺安时常“令侍女为胡奴装,跨骏骑,壻御之游,蹀躞不休。春秋佳日,扁舟自放,绿波红蓼,吴越山川,踪迹殆遍”[16](P150);吴绡癖于山水,尝“游神州之五岳,泛溟海之三山”[46]。而社会舆论对女子独立外出游历亦给予相当的宽容,如吴山尝与徐智珠“登金焦、游虎阜;后至明圣湖,纵览孤山、葛岭之胜”[47],钱塘、仁和两地县令闻之,竟“为分俸见存湖上,传为佳话”[9](卷12,P640)。这些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得上以山水之游为业,她们的活动范围由闺房扩展至广阔的社会,其在空间上对闺阁藩篱的突破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
古代女性长期囿于闺阁之内,见闻局限于酒浆织纴、花鸟云露,不免内容单薄,气格纤弱。如冒俊曰:“诗于闺阁中才綦难矣!……无名山大川之涉历,见闻所限,才气易孱。”[48]王璊亦感叹女诗人“足不逾闺闱,身未历尘俗。茫茫大块中,见闻苦拘束”[49]。对于常年幽闭于闺阁的女性来说,外出游历使她们脱离了狭小沉闷的闺房空间,领略到闺门外广阔丰富的社会生活,这对于扩大女性视野是十分必要的。梁孟昭称:“江山胜游,较之穷愁一室,与枯管蠹鱼作椽者,相去何若哉。”[50]邹斯漪称卞梦钰诗“获舟车江山之助,宜非寻常纨绮足不离绣阁、手不离珠玉、耳目不离歌舞珮环者所敢望也”[16](P218)。徐媛与其夫游历四垂,“而石城,而芜阴。吊古中宵,酸风射眸。触境成咏,郁为名作”[29](卷首,P301)。可见外出游历是激发才女诗兴的重要因素,她们将旅途见闻感受形诸文字,留下了大量的山水行旅作品。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女性诗歌创作题材,亦促使女性书写走出绮丽纤弱的狭小格局。如徐媛的《塞原秋晚》其一:“日日惊沙素草斑,秋空霜雁洞庭还。几多瀚海滩头骨,泪尽红闺镜里颜。”[29](卷8,P378)境界沉雄阔大,不输须眉。又如王端淑的《蜀阜寒月》:“半分林壑敛山烟,历乱清规笑客颠。惟有卧龙桥上月,寒雪点捡放归船。”[22](卷13,P58)恬澹清远,幽峭冷逸,一改传统女性书写习见的闺阁气与脂粉气。
四、经世济民
自商周起,“女祸论”在封建社会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武王讨伐商纣的一条重要罪状即“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惟妇言是听”历来为封建统治者所忌。受“女祸论”影响,女性长期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然至晚明,不少闺秀博通经史,对政事与民生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如顾若璞“常与闺友宴坐,则讲究河槽、屯田、马政、边备诸大计”,其文集中“多经济理学大文,率经生所不能为者”[15](卷1,P1731);丁如玉“慷慨好大略,常于酒间与灿(笔者按:丁如玉之夫)论天下大事,以屯田法坏为恨”[15](卷1,P1731);吴琪“尤好大略”,常与密友周琼“红烛夜谈兵”[9](卷12,P636)。晚明才女们也表现出杰出的治世才能,如丁如玉尝曰:“边屯则患戎马,官屯则患空言,鲜实事。妾与子戮力经营,倘得金钱十二万,便当北阙上书,请淮南北闲田垦万亩,好义者出而助之,则粟贱而饷足,兵宿饱矣。然后仍举盐荚召商田塞下,则天下可平也。”[15](卷1,P1731)她深谙屯田之法,充分认识到屯田对于社稷的重要性,远见卓识,不输须眉。又如瞿式耜之妻邵氏有《与夫论兵机书》一文,对战局及战术有着独到的论断:“以妾愚论,南宁矫健无伦,冲锋陷阵,实足令万人辟易。不若于敌阵未结之先,令率锐骑先陷其中坚,而以胡一清殿南宁之后,相公再以正兵分为二大翼,左右包抄,使敌人入我算中,必无噍类。乘势逐北,连州诸郡不难恢复矣。”[51]邵氏精通兵法,为夫献制敌之策,颇具将帅风度。
晚明女性虽然被摒于封建官吏体制之外,但她们通过辅佐丈夫,在某种程度上间接参与了政事。朱中楣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其夫李元鼎自述“每闲居相对,私与扬扢。凡朝政之得失,人才之贤否,与夫古今治乱兴亡之故,仕宦升沉显晦之数,未尝不若烛照而数计”,并感慨受妻子之助良多,“余素位而行,不以险夷生死婴其心,则内子之力居多焉”[52]。李振裕称父李鼎元晋升兵部左侍郎,“条陈职掌一疏,先淑人(笔者按:朱中楣)实资赞画焉”,并赞母朱中楣“识见机警,料事多奇中”[11](卷8,P469)。又如桐城才媛方孟式精于经世之学,“随官远游,经涉燕、闽、楚、粤、清泉、浔阳,间辅佐清政。…于是方伯公(笔者按:方孟式之夫)多赖其内助焉”[53];王锡爵之女孙、徐本高之妻王氏博通政事经济,随夫仕宦京师,“一切章奏文牒咸经手裁”[54]。晚明更有部分女性精通武略、剑术,直接参与到战争之中。如毕著尝“率精锐劫贼营,手刃其渠,众溃”[15](卷1,P1719);秦良玉能征善战,曾数次大败流寇,崇祯帝赐诗赞曰“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28](第1册,P22);刘淑于“剑术、孙吴兵法,莫不精晓”,闻甲申鼎湖之变,遂“散家财,募士卒,得千人,并其童仆,悉以司马法部署指挥,成一旅”[15](卷1,P1718);邹平刘孔和之妻王氏“善骑射”,清军南渡时,与其夫“各将一军。妇号令之严,过于节之(笔者按:‘节之’即刘孔和)”[19](P27)。这些女性以经世济民为己任,亲赴沙场,为国御敌,展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王嵩高曾评论闺秀诗“总有习气,非调脂弄粉,剪翠裁红,失之纤小,即妆台镜阁,剌剌与婢子语,俚俗尤多”[55]。经世之学与政治热情极大地影响了闺秀的诗歌创作,促使她们脱离闺阁情爱的狭小天地,不再“沾沾于一己之穷通得失”[56],抚时感世,缘事而发,以慷慨激愤而又深挚悲凉的笔触,书写时局民瘼,实现了女性感怀题材由家到国的转变。如王端淑素有经世济民之志,“喜为丈夫妆,常剪纸为旗,以母为帅,列婢为兵将,自行队伍中,拔帜为戏”[57](卷4),其时政感怀诗直言朝政弊端与民生疾苦,有着强烈的危机感与批判意识。如《先翁文忠公殉珰纪述》以犀利的笔调揭露了阉党“肆横任恣行,朝野尽结合”[22](卷1,P13)的腐败现状,愤懑之情,溢于言表;《贪吏》《秽吏》二诗更是将矛头直指“株连蔓益滋,竭血敲空髓”的贪官污吏,高呼“问天假霹雳,立击除奸酷”[22](卷1,P14),慷慨直率,淋漓犀利。经世之学亦引发了女性对英雄事业的向往以及对性别伦理的牢骚不满,如王端淑的《侠士》“一目识肝胆,头颅值几何。异书临水读,利铗傍崖磨。”[22](卷8,P34)周琼的《次韵答张词臣》:“莫道天涯不感伤,十年闲恨付苍茫。每怜侠骨惭红粉,肯学蛾眉理艳妆。”[9](卷12,P637)她们渴望成为披坚执锐的豪杰侠士,然英雄之志最终只能沦为壮志难酬的郁愤,巾帼之恨,颇令人唏嘘。
五、余论
明清时期,不少女性不再安于酒浆织纴,而是广泛涉足本属于男性之领域,这深刻地影响了她们的精神气质,促使其逐渐脱离闺阁气与脂粉气,走向文士化、居士化与名士化。如倪仁吉“类山泽耆儒硕士,不复如闺阁中人”[15](卷1,P1754);吴山“吐辞温文,出入经史,与人相对如士大夫”[58];王端淑“博极群书,湛深理学,居然有儒者之风”[57](卷42);周琼“作人萧散,不以世务经怀,傀俄有名士态”[15](卷1,P1750)。她们或研习史书,俨然学者;或谈禅论佛,颇具居士气质;或外出游历,洒脱如魏晋名士。与之相应,才媛们在文学创作上亦冲击着性别界限。女性诗歌向来多脂粉气、香奁气,少名士气、英雄气,正如邹斯漪所言:“儿女情多,英雄气少,此从来所以病彤管玑囊也,清照之《漱玉》、淑真之《断肠》犹不免焉。”[59]晚明女性生活内容之改变深刻地影响了其文学创作,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艺术风格,她们都力图脱离闺阁气,向男性诗风靠拢。如黄鸿诗“时得遒警,所谓骎骎有丈夫胜气者也”[16](P181);周琼诗“俱慷慨英俊,无闺帏脂粉态”[45](P16);朱中楣诗“一段渊秀朗彻之神,博大澹远之思,绝无脂粉,如列须眉”[52](卷13,P81);卞梦钰诗“清越澹远,嵚崎历落,读之者但见如高人,如逸民,如宿衲,……求一闺阁相了不可得,盖香奁粉黛一洗尽矣”[59]。
女涉外业对传统的儒家礼法亦形成了一定冲击,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对男女之大防的突破。传统的儒家性别伦理强调男女之间疏远甚至隔离,对于男女交往有着严格限制。如《礼记·曲礼》曰:“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嫂叔不通问,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于梱,内言不出于梱。”[60]非夫妻关系的男女之间更不允许有过多的接触与交流,否则往往被目为有伤风化。晚明女性广泛涉足外业,共同的兴趣爱好为男女交往奠定了基础。如李贽与梅湛然、自信、明因等女弟子书信往来,谈禅论道。毛奇龄更是以广交才媛为荣,他不仅招收徐昭华为弟子,更与商景兰、商景徽、祁德渊、黄媛介等才女保持文字之交。不少才女亦突破“男女授受不亲”的藩篱,积极结纳文人名士,如王端淑“负才荦荦,能对座客挥毫,……后寓武林之吴山,与四方名流相倡和”[12](卷5,P790);黄媛介与钱谦益、吴伟业、李渔、汪汝谦等文坛名士均有酬唱。其次是促使夫妻关系由“夫义妇听”向“夫妻而兼擅朋友”转变。女性才学的提升与共同的兴趣促使夫妻如朋友般交流,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良友式夫妻。如李元鼎与妻朱中楣常共论朝政得失,探讨治乱兴亡,李元鼎直称妻“闺中吾益友”[52](卷12,P79);叶绍袁与妻沈宜修皆笃信佛教,并酷嗜诗歌,二人“情虽伉俪,谊胜友生”[13](上册,P21)。女性在史学、政事、禅学等方面彰显的才华无疑是促使其平等交流的一个重要因素。总之,无论从女性史、文学史角度来看,还是从婚姻史角度来看,女涉外业都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值得学术界高度关注。
注释:
① 参见魏宏远的《论晚年王世贞对昙阳子思想的接受》,载于《中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2期。
[1] 郑玄,王应麟.周易郑注:卷4[M].丁杰,等,校订.北京:中华书局,1985.50.
[2] 魏收.魏书:卷92[M].北京:中华书局,1974.1997.
[3] 李贽.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A].陈仁仁,校释.焚书·续焚书校释[M].长沙:岳麓书社,2011.108.
[4] 毛奇龄.西河集:卷64.[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77.
[5] 江元祚.续玉台文苑:卷首[M].济南:齐鲁书社,1997.424.
[6] 胡文学.甬上耆旧诗:卷30[M].袁元龙,点注.宁波:宁波出版社,2010.877.
[7]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8] 潘江辑.龙眠风雅[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9] 邓汉仪.诗观初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10] 钟惺.名媛诗归:卷27[M].济南:齐鲁书社,1997.310.
[11] 李振裕.白石山房文稿[M].济南:齐鲁书社,1997.
[12] 王蕴章.燃脂余韵[A].王英志.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1册[C].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13] 叶绍袁.午梦堂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4] 丁圣肇.吟红集序[A].王端淑.吟红集[M].日本内阁书库藏清顺治十七年刻本.
[15] 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A].王英志.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3册[C].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16]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7] 戴肇辰,苏佩训.广州府志:卷147[M].史澄,李光廷,纂.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五年广州粤秀书院刻本.
[18] 姚旅.露书:卷5[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136.
[19] 陈维崧.妇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0] 毛奇龄.西河集:卷159[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638.
[21] 顾若璞.卧月轩稿:卷2[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228.
[22] 王端淑.吟红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82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3] 郑方坤.全闽诗话:卷10[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519.
[24] 戴玺.读隋史[A].光铁夫.安徽名媛诗词征略[C].合肥:黄山书社,1986.169.
[25]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下册卷31[M].长沙:岳麓书社,1998.977.
[26] 沈德潜,周准.明诗别裁集:卷1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35.
[27]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第4册[M].北京:中国书店,1988.526.
[28] 朱彝尊.明诗综[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9] 徐媛.络纬吟[A].四库未收书辑刊:7辑16册[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30] 张履祥.愿学记二[A].杨园先生全集:中册卷27[C].北京:中华书局,2002.748.
[31] 袁宗道.白苏斋类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2] 袁中道.珂雪斋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3] 顾若璞.黄夫人卧月轩续稿[M].北京:国家图书馆藏顺治八年刻本.
[34] 陶元藻.全浙诗话:下册卷37[M].俞志慧,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1068.
[35]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250[M].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五年刻本.
[36] 王文肃公文集:卷1[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48.
[37] 揆叙.历朝闺雅[M].四库未收书辑刊:10辑第30册[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38] 袁九淑.伽音集:卷5[M].沈阳:辽宁省图书馆藏明抄本.
[39] 邢慈静.芝兰室非非草[M].临邑:临邑邢侗纪念馆藏清刻本.
[40] 庞尚鹏.庞氏家训[A].丛书集成新编:第33册[C].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193.
[41] 许相卿.许云村贻谋[A].丛书集成新编:第33册[C].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181.
[42] 杨洵,陆君弼,等.(万历)扬州府志:卷20[Z].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5册[C].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348.
[43] 李铭皖.(同治)苏州府志:卷3[Z].冯桂芬,等,纂.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139.
[44]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全清词》编纂研究室.全清词·顺康卷:第4册[C].北京:中华书局,2002.2359.
[45] 徐树敏,钱岳.众香词[C].上海:大东书局,1933年影印本.
[46] 吴绡.啸雪庵诗集自序[A].啸雪庵诗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68.
[47] 陈文述.西泠闺咏:卷10[M].王国平.西湖文献集成:第27册[C].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437.
[48] 冒俊.自然好学斋诗钞序[A].汪端.自然好学斋诗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十年刻本.
[49] 王璊.印月楼诗集:卷1[M].蔡殿齐,辑.国朝闺阁诗钞:第10册[C].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50] 梁孟昭.与陈夫人[A].王秀琴,编,胡文楷,选订.历代名媛文苑简编:卷上[C].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45.
[51] 无名氏.闺墨萃珍[M].笔记小说大观(五编):第8册[C].台北:新兴书局,1980.4867.
[52] 李元鼎.石园全集[M].济南:齐鲁书社,1997.
[53] 方维仪.纫兰阁诗集序[A].方孟式.纫兰阁诗集[M].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54] 宋如林.(嘉庆)松江府志:卷71[Z].孙星衍,莫晋,纂.上海府县志辑:第1册[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648.
[55] 王嵩高.跋清娱阁诗钞[A].王冉冉.江南女性别集·三编:上册[C].合肥:黄山书社,2012.335.
[56] 杨德建.竹笑轩吟草叙[A].李因.竹笑轩吟草[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102.
[57] 王端淑.名媛诗纬初编[M].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六年清音堂刻本.
[58] 王晫.今世说:卷7[M].北京:中华书局,1985.80.
[59] 邹斯漪.诗媛八名家集[C].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顺治十二年邹氏鷖宜斋刻本.
[60] 孙希旦.礼记集解:上册卷2[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43-44.
NewTrendsofBoudoirLifeintheLateMingDynasty
LAN Qing
(Zhongshan University, Zhuhai 519082,China)
Women doing things not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is a prominent phenomenon in the field of sociology and literature.Wome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ere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field of history,Buddhism,tourism and politics which belonged to the male before.This not only made their own temperament transform to the famous literati,but also profoundly affected their literary creations and transformed their works’ theme and content from the boudoir to the society,and their artistic style from being delicate to heroic.In addition,this caused certain impact on the feudal etiquette.
the late Ming Dynasty; female; historiography; Buddhism; politics
2017-09-12
蓝青(1988—),女,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G112
A
1008-6838(2017)06-0060-08
(责任编辑 赵莉萍)
——以近代上海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