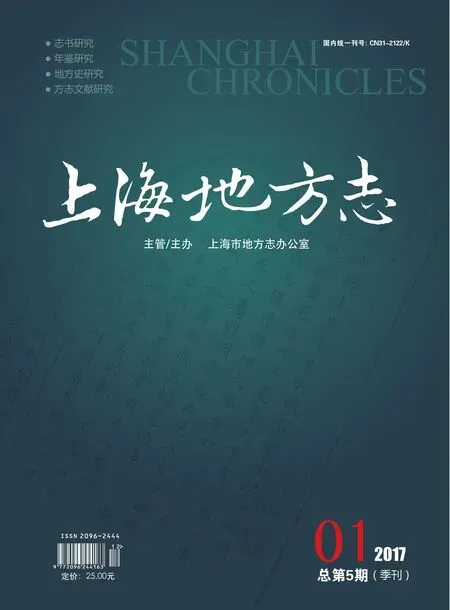2016年地方志理论研讨会评述
孙长青 刘雪芹
2016年地方志理论研讨会评述
孙长青 刘雪芹
2016年12月8—10日,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上海师范大学协办的“2016年地方志理论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
会议共收到来自境内外的论文81篇,主题涉及“地方志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年鉴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地方史理论的传承与创新”等;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名史志专家、学者与会,并围绕问题展开交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邱新立在“2016年地方志理论研讨会”上作“地方志理论的传承与创新”主题报告。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洪民荣、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滕建勇在开幕式上致辞。
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潘捷军、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牟国义、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科研处处长张英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剑光分别就“二轮志书评价体系”和方志理论、年鉴理论、地方史理论分组研讨情况进行大会交流。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室主任唐长国主持开幕式和大会交流。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王依群、生键红,入选论文作者代表,来自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上海市区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师范大学领导和相关人士,以及特邀专家和学者共120多人参加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立意高。研讨会主题定位为地方志理论研究和研讨,紧密围绕方志理论、年鉴理论和地方史理论三大议题,并分为方志理论专场、年鉴地方史理论研讨专场深入展开。二是全国性。研讨会面向全国开展征文,既不局限于上海,也不局限于地方志系统,既有史志界专家,也有研究所、高校、图书馆学者。三是入选严。会议正式代表全部通过征文评审产生,入选采取双向匿名评审,论文能否入选,不看领导身份、不看业内名望、不看个人学历,只看提交论文的本身质量,最终从全国以及境外81篇征文中,评选出参加会议论文26篇,其中,既有地方志领域专家学者,也有热爱地方志研究的青年人,甚至在校读书的硕士生、本科生。研讨会取得了理论研讨的预期效果。
一、邱新立关于“地方志理论的传承与创新”的主题报告
(一)“方志学研究”从民国开始
现代学术研究意义上的方志学研究是从民国时期开始的。方志理论从“理论”上升到‘学科’层面,是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的事情。梁启超可谓我国近代方志学研究的第一人。1924年,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中首次提出了“方志学”这一概念。而李泰棻于1935年编写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专著《方志学》,则被称为方志学的第一部完整著作。
在构建方志学理论的同时,一批民国学者纷纷开设方志学课程,开始探索方志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如河北通志馆馆长瞿宣颖曾在南开、燕京、清华等校讲授“方志概要”和“方志学”课程;朱希祖与罗香林分别在国立中山大学讲授地方志研究课程;顾颉刚在复旦大学史地系开设“方志实习课”等。同时,在“分科治学”理念的关照下,构建方志学“独立学科”的呼声日益高涨。
1944年,卢建虎在《东方杂志》开宗明义地提出“大学设志学系”的主张,并主张各校讲授“方志之学”。而在西方“分科”观念的持续影响下,学术研究“专科化”大行其道,伴随着近代方志学学科体系的逐步构建,方志学亦趋于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二)建国以后大规模发展
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1949年前8200余种中国方志。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方志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多、范围广。
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所发表的方志学理论研究文章,以万为统计单位,发表方志学理论文章的刊物遍及全国各地。正式出版的论著,累计650种以上,内部印行的也在430种以上。其中基础理论方面,有近120种,其中1980年至2000年的作品约60种、2001年至2013年的作品近60种。
2006年5月,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这标志着地方志工作进入了依法修志的新阶段。多年来新编地方志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专兼职相结合、具有良好作风的方志人才队伍,取得了大量具有资治、教化、存史作用的志鉴成果。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共出版各种理论著作1000多部,发表论文6万多篇。
目前,方志理论研究及学科体系建设有机制优势、人员优势和平台优势。数以万计的地方志工作者参与方志理论研究,各级地方志学会、各级地方史志期刊也为方志学研究提供了舞台。
(三)尚未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列入学科目录
时至今日,方志理论研究和方志学学科建设仍是比较薄弱的环节。主要问题包括部分方志工作者长于方志编修实践,理论研究能力不足,研究成果引用文献总体数量较低,学术含金量不高;有些研究成果内容创新少,而且在论点、论据、论证上没有太多新意;有些研究成果还存在思路不清、层次不清、逻辑不顺等情况;一稿多发现象仍很常见。
此外研究工作各自为战居多,合作研究水平不高,尚未形成一致公认的权威著作。整个学科的发展规划仍显不足,一些分支学科仍无人研究,或后继无人。截止目前方志学还只被承认是专门史下面的一个三级学科,尚未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列入学科目录,“学科定位、地位不够清晰,这是学科发展的瓶颈。”
而在学界,方志学是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意见也不统一。持否定观点的研究者认为,方志学是广义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持肯定意见的研究者认为,方志学虽与历史学关系密切,但已经或即将取得独立的学科地位。但争论本身掩盖了不少发展的实际情况,那就是经过几代学者和方志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方志学学科建设初见成效,已初步呈现出独立的学科面貌。
二、地方志理论研究
本次论坛关于地方志的论文有20篇,涉及方志理论、体例、内容、研究,以及名家、名志研究等方面,内容丰富。
(一)综合论述
曾荣的《新视角、新思路与新趋势:近代方志转型视域下的方志学研究述论》通过回顾方志学研究的历史,梳理近代方志转型视域下的方志学研究现状,预测方志学的未来研究趋势,剖析重点和难点问题。
(二)方志管理
张晨的《方志治理体系与方志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基层史志机构方志理论研究工作为视角》提出基层史志机构要重点通过责任主体和领导机制、评估考核和奖励机制、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机制三个方面加强方志研究,促进方志部门向地方智库、智慧型机关升级、转型。
(三)方志理论
池诚的《地方志批评理论初探》呼吁方志批评立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与现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科学、客观、真实地阐释地方志,建立自身的评价尺度和相对自律的话语体系,为地方志理论发展创新服务。王翠的《有关“不越境而书”的学术史及理论思考》梳理了建国以来“不越境而书”的演变过程,分析其原因与意义,指出“越境而书”目的不是打破志书的传统,而是为了记述更完整。王晖的《方志方向方法——论方志理论的传承与创新》提出建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方志学是方志研究最大的理论创新。
(四)方志编纂
沈松平的《试论第二轮新方志编修的实践创新》分析了二轮志书在体裁运用上增加了“特载”等,取消“经济综述”篇,增设改革开放、体制改革、民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等体现时代特色的篇章,但也存在假象创新、否定式创新等问题。李志英的《关于提高上海市二轮区志编纂质量的思考》指出区志在篇目框架体例结构和资料的选录与录用方面的两大问题,从稿源、资料、组稿方式三方面分析原因,提出多元化打造修志队伍、多途径收集资料、精雕细琢志稿三大对策建议。王景忠的《从事物的普遍联系观点看志书如何贯通──对志书贯通问题的几点粗浅看法》指出志书编纂过程中,编者应抓住一地的“社会、生态、地方特点”三条经络,发挥“概述”在志书中提要钩玄的贯通作用。朱玺的《谈修志人的视角问题》提出要换位思考,站在主编、修志人和用志人等不同角度开展修志工作,打造精品佳志。刘书峰的《正面人物的想象与政治标准的桎梏——广播电视志里的早期广播人物》通过梳理首轮广播电视志,发现对早期广播人物的收录存在“入志人物数量太少”“国民党官营及民营电台人物所占比例太小”“人物记述手法单一”等问题,其原因在于收录标准只认“政治正确”“正面人物”。
(五)方志体例
金雄波的《志书章节体与条目体的比较研究》通过从形式、运用实效两方面进行对比,认为二轮修志可以采用志书条目体,但要合理设置,并充分发挥条目体的“述”,同时融合章节体的长处。
(六)修志名家及其思想
陈郑云、牛文静的《从<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序>看修志者的编纂思想》认为修志取鉴、探考治道,志乃史流、无不备载,三长兼备、博采善择,考镜得失、信今传后这四方面的思想理论构成了《五凉全志》纂修者的主要方志思想,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郭达祥的《论邬庆时的方志思想》阐述了邬庆时为保全民族文化命脉,提出志书“不惟不可不修,且不可不急修”;创新修志方法,尝试“三不四最”法;与时俱进,顺势创新的三大方志思想。
(七)名志研究与评价
蔡宏、李爱华的《抄本地方文献价值的重现——以清抄本嘉靖<吴邑志>为例》从纂者生平、著录、抄写时代、内容、价值等几方面,重现了此书的全貌与价值。王文远的《<懋功屯志略>成书时间及纂修人再探》通过比较分析和实地考察,对前人研究的“兴元修”提出商榷,并提出成书于1862年(同治元年)的论断。龚应俊的《乡土志民族书写的文本与情境——以<盐边厅乡土志>为中心的研究》通过对《盐边厅乡土志》有关少数民族的特定时代和社会情境色彩从人类学角度进行分析,为当下的乡土志民族书写方式提供借鉴。龙麟的《清代普洱方志考述》通过对清代普洱方志的梳理,分析其编撰组织方式、体例与内容,为当下二轮修志提供借鉴。李艳玲的《道光时期“厦金二岛志”比较浅析》从体例、体裁、记述内容等方面对两部志书做比较分析,进而阐明两志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李昌志的《一部地情详备人文厚重的鸿篇巨制——评新版<肥东县志>(1986—2005)》从概述、篇目、结构、内容、志体等各方面对《肥东县志》作全面评价。
三、年鉴编纂、地方史研究方面
(一)年鉴编纂
高文智的《年鉴稿件编辑探微——浅析“实、简、加、换”法》一文,认为把握好了年鉴的文字稿件编辑,那么高质量的年鉴就成功了一半。提高年鉴文字编辑的质量和效率,可以从“资料详实、行文严谨朴实”的“实”法,“精简语言文字的表述,达到简而不漏、要而不缺”的“简”法,“充实稿件信息,补充完善相关资料,使年鉴信息翔实,资料可靠”的“加”法,以及“调整、调换那些不符合《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要求的话语表述”的“换”法,最终达到以“实”为原则,综合运用“简”“加”“换”的办法,使有存史价值的资料得以留存。
赵峰的《试论地方综合年鉴事类条目》一文,认为地方综合年鉴应该有集合型事类条目的地位。地方综合年鉴要为年度“特、重、新、热”事件单独设立条目;为年年不变的常规事件设立综合性事件条目;把介于两者之间的比较有价值、比较重要的多个同类事件,用集合型事类条目逐一进行简单记述。要在综合全记条目中增加集合型事类条目的记述方式,简要交代同类事件中各个重要、有价值事件的关键信息。
宋莉莉的《高校年鉴大事记编撰规范的对策研究——以上海师范大学年鉴大事记编撰为例》一文,立足对上海师范大学年鉴大事记编撰规范的分析,提出合理化建议和对策。认为,编撰角色认知方面要站在高校“管理者”、高校“文化使者”、高校“史官”以及站在全书“统编者”的高度;编写原则方面要坚守“实事求是、立场准确”“大事不漏、反映特色”“一事一记、精确成条”“不作追述、不作展望”四项标准;形成“动态管理”“节点前移”“上下联动”“交叉审核”四种机制;注意规范年鉴大事记的措辞表达,依据四个国家颁布的行文规范规定。
(二)地方史研究
李鹏的《现代性的回响:近代川江航道图志本土谱系的建构》一文,系统考察近代川江航道图志本土谱系的建构过程,认为近代中国本土精英在对西方“科学”地图知识的“现代性体验”中,往往不自觉地利用中国传统地图知识进行重新塑造,即通过“传统知识资源的再利用”,进而沟通与融合中西两种不同的地图绘制传统。是故,近代国人所绘的川江航道图志,在编绘方式上往往新旧杂陈,明显带有“旧瓶装新酒”的内容特征。在清末以来知识与制度转型的大背景下,近代国人特别是地方知识精英对西方现代测绘技术与制图体系的认同与接受,并非简单地是一个“他者”的渗入与移植过程,而是一场由西方文化传播者与本土地图绘制者共同参与的复杂的“在地化”知识生产。
傅健《金华万佛寺塔考略》一文,从地方志的角度来解读金华万佛寺塔的产生、发展、演变、毁灭和重生。万佛塔是于北宋治平年间,由僧居政建造而成;明代该塔所在的密印寺,曾作为僧纲司,地位显赫;清代的密印寺,是婺中一大道场;抗战时期,万佛塔毁于战火;解放初,万佛塔地宫曾被发掘清理。
褚半农《从方志、档案记载看承载历史沧桑的自留地——以上海闵行区褚家塘生产队为例》一文,通过褚家塘、吴家塘两个自然村中自留地的出现,以及其后受到政治运动影响,三次分配、三次收归的曲折和反复的发展过程,并与县志和乡镇村志中有关自留地的记载相对比,这期间的几十年过程,反映的是中国建设发展道路的探索、曲折和失误。
黄展《“荣昌祥”广告公司在民国时期的历史贡献》一文,考察了民国时期一家专营户外广告的公司“荣昌祥”。民国上海商业繁荣带动了广告行业的兴盛,很多广告公司(或公司广告部)专营户外类型的广告。“荣昌祥”作为当时规模最大、类型最全、设计水平最高的广告公司,为当时户外广告设计、设计人员的培养乃至新中国广告行业的建立都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其“西化”的广告管理模式更将“作坊式”的生产带入了现代企业的运行中,对当时户外广告行业与城市的近代化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根据“荣昌祥”所体现的多样化的设计形式、设计思路、设计经营等构成特征,研究荣昌祥广告公司自身的发展演变历程,剖析它对当时行业内外的影响与推动,从而探究其在民国这一时期的影响与贡献。
郭万隆)
——卯年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