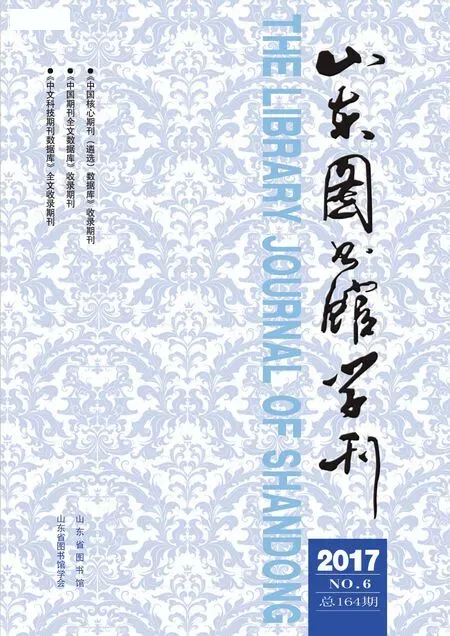东方文化图书馆始末述论*
王一心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学术论坛
东方文化图书馆始末述论*
王一心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东方文化图书馆是20世纪上半叶,日本政府在中国推行“对支文化事业”的重要项目之一。日本政府以“庚子赔款”在中国开展文化事业,却不愿与中国人就此商议;口称文化事业,当初却不将作为人文渊薮的图书馆列入项目。其居心叵测,引发中国文教界强烈反应,也使得东方文化图书馆从筹备到结束的整个过程充满变数、终难得到正常发展。
东方文化图书馆 “对支文化事业” 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 文化侵略
1 引言
东方文化图书馆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存续期长逾“十四年抗日战争”,是日本“对支文化事业”在北京实施的项目之一。日本政府既以“庚子赔款”为经费要在中国开展文化建设,却不愿与中国协商共同实施而欲单独进行并牢牢把持绝对控制权,其居心用意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我国文教界人士的怀疑乃至愤怒。单就其所建东方文化图书馆来说,初始进展迟缓碍难、过程复杂多变,建成之后也一直不大为社会所关注,乃至迄今为止对其研究极少。也由上述诸因,造成东方文化图书馆的来龙去脉混沌不清、众说纷纭,甚至有将其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相混淆者。故无论是对以往我国图书馆现代史忽略的部分有所弥补,还是从图书馆建设视角观测日本20世纪上半叶对我国文化侵略意图与行径,厘清东方文化图书馆的面貌、作用及前因后果都有必要也有意义。东方文化图书馆在筹备、设立、发展、结束的过程中,归属与名称几度变更,本文为述论简单明了,也为迁就时人的指称习惯,统以“东方文化图书馆”称之。
2 是否建图书馆折射日方居心
1923年3月12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3月14日提交众议院并获通过,3月25日又经参议院全体一致通过,该案于此成立。3月30日,日本以法律第三十六号形式公布了“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定为4月1日起实施。“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共十条,其中第五条关于资金支出的目的及事业范围为:“(1)资助在支那国所办的教育、学艺、卫生、救恤及其他相关文化事业;(2)侨居帝国的支那国人民与前项同种的事业;(3)在帝国所办的与支那国相关的学术研究事业。”[1]
虽然可以说设立图书馆,未逾“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第五条(1)所规定的范围,毕竟“文化事业”范围极其宽泛,其法条并未指明要建图书馆。而明确要求设立图书馆,是由中国人向日方提出的。中国官方正式向日方提出交涉的时间是在1923年4月4日,由我国教育部特使朱念祖偕驻日代理公使廖恩焘于当日午后同至日本外务省,与外相内田康哉、亚洲局局长芳泽谦吉等人会见,当面陈述中国方面希望将建图书馆等纳入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内田的回答是:中国的希望大可为日本政府计划之参考。[2]朱念祖还为此另外拜访了日本首相加藤高明。
不只北洋政府官方,一些社会团体也向日本政府发出相同或相近的呼吁,其中尤其以在日本及与日本有关的学生社会团体的呼声更为激烈,如中华留日各校同窗会对日庚子赔款讨论会发表《为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告国人》[3]、留日自费生联合会发表《对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宣言》[4],均提出设立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学术研究所的主张;以各学科成员组成的、与中国科学社并列为当时中国两大综合性学术社团的中华学艺社,也于1923年6月提出“在北京上海两处设立研究所、图书馆、博物馆……并拟于数年之后分期筹设图书馆于各省省会”[5]的主张。
1923年年底,朱念祖又为申告中国方面的主张,受中国教育总长黄郛之派再赴日本,“向日本朝野作热烈之运动”[6]。其间对《大阪朝日新闻》发表谈话称,他自夏季归国后,“即在上海北京等处,历访朝野识者,征求意见,大抵皆主张设立图书馆博物馆美术研究所等,王正廷氏更主张创办大学,包含以上各种设施……”[7]
而日本国内实际上也不乏赞同此主张的日本人。朱念祖撰文称,“……念祖等在东发表意见,如主张创办图书馆博物馆学术研究所之类,彼国教育会会长泽柳氏、及现内阁阁员犬养氏,与念祖等面谈时,均表赞同。而西京帝国大学各教授,曾联名上书于彼国政府,亦有同一之请求。”[8]
面对来自日本朝野及国内外要求建图书馆的呼声,日本政府终不能完全置若罔闻。事实上,早在1923年6月,日本政府有关部门就已注意到了。据《大阪朝日新闻》载,日本宪政会在本部召开政务调查会,由下冈总务报告,称关于对华文化事业,中国民间希望在北京上海,设立大规模之图书馆,渐次再在各省设立图书馆。至于其种类及其方法,提议设立特别委员会。[9]随即1923年7月,日本外务省书记官兼对华文化事业局事务官冈部与东京大学医学部长入泽达吉奉日本政府之命为“对华文化事业”前来中国调查,与中日各方接洽、交换意见。[10]
1923年12月29日、31日及1924年1月8日,中国驻日本公使汪荣宝与日本对华文化事务局局长出渊胜次代表各自政府,在日本外务省就“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召开非正式协商会议,先由汪荣宝提出“说帖”,与出渊胜次交换意见后,达成九项协议,经两国政府批准后,于1924年2月6日在东京正式签署,此即所谓“汪-出渊协定”。其第三项规定,在北京设立图书馆及人文科学研究所[11]。至此,建立图书馆作为“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之一项,终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文件的方式确定下来。
建图书馆与否,所反映出的不仅仅是日本政府于“对支文化事业”开办项目的初衷与中国文教界乃至政府的愿望相左的问题。虽然日本政府后来对计划做了调整,毕竟是迫于中日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其只从自己的设想出发,罔顾中国人愿望的行事方式,不仅使得“对支文化事业”开局不利,其居心给中国人留下了负面印象,更成为“对支文化事业”整个过程在中国的进行诸般不顺的症结之一。
3 东方文化图书馆曲折的筹备过程
3.1 筹备工作繁复拖延
日本“对支文化事业”设有一咨询机关,称作“对支文化事业调查会”,宣布成立于1923年12月27日,由外务大臣任会长,文化事业部部长任干事长[1]。日本外务省于1924年6月21日下午在外务大臣官邸,召开“对华文化事业调查会”第二次总会,与会者“一致赞成”实行“对支文化事业”第一期计划,共五项。第一项为:以6年时间,“在北京设置人文科学研究所并图书馆,在上海设置自然科学研究所,此三项事业之总预算为535万元。”第三项为:“北京之研究所及图书馆,系铁筋混凝土建筑,三层楼,地面广二千坪(每一坪六尺平方),五年竣工……”[12]
“对支文化事业调查会”的成立日期十分令人玩味——在此仅两日后,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即将在外务省与日方开始商谈相关事宜;而在中日两国签署双方合作的“汪-出渊协定”之后四五个月,日本仍自行通过“第一期计划”。这些都显示日本从方案制定到着手前期工作,都只想一己实行,委实不愿中方介入。而日本在调查会二次总会后派帝国大学教授服部宇之吉以“交换教授”身份来华,又派了文化事务局参赞朝冈健、事务小村俊三至北京上海等地,调查接洽设置图书馆、研究所事宜等等[13],这与日本同意建图书馆及签订“汪-出渊协定”同样是对来自中国社会呼声的貌似妥协,或仅欲以此姿态与动作获取中国官民的理解以平息怨怼,并非真切认识到此“文化事业”若缺少中国配合,日本独力难成。正因为如此,东方文化图书馆建设进程陷于迟缓,像一只老钟,呈现走走停停的怪象。
所以1925年5月4日,日本“对华文化事业调查会”第二次总会开过将近一年,日本才忽然向中国提出两国协商组织“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以作为管理在华文化事业的机构,请中国政府予以同意,且希望“从速”。[14]外交部总长沈瑞麟在接到日本照会的当日即行回复,称“一切当予同意。”并告诉对方,中国政府已经派定总委员会中的中国委员11名[15]。可见中方态度的积极且先已准备停当,而“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实际成立于1925年10月9日[16],又是五个月后的事了。距日本“对华文化事业调查会”第二次总会通过东方文化图书馆建设第一期计划整整两年后,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才召开了第一次临时总会[17],并在会上推举中日图书馆筹备委员[18];又三四个月后(1926年11月19日-22日),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才在日本东京帝国学士院会馆召开第二届年会上,决定设置图书馆筹备处负责图书馆筹备事务[19];通过“东方文化图书馆筹备处章程”及“东方文化图书馆筹备处1926、1927年度经常费预算书”[16];而将近一年后(1927年10月28日),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在北京该会事务所召开第二次临时总会暨第三届年会上,又再决定“东方文化图书筹备处章程”、成立图书筹备评议会并推举评议员等。可见东方文化图书馆筹备进程拖沓的节奏。
日本政府办理“对华文化事业”的期期艾艾、拖延迟缓显得缺少诚意,中日于此项目合作的维系本已十分脆弱,1928年5月3日又发生了“济南惨案”,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全体中方委员,遂于5月13日开会决议,一致声明退出该会以示抗议[20]。包括图书馆事宜在内的会务又回到由日方只手操持的老路上,东方文化图书馆的筹备进程更增加了不确定因素。
3.2 馆舍用地谋取失当
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在北京设有事务所,先于1926年8月14日设于王府井大街大甜水井胡同9号,后于1927年12月18日迁至东厂胡同1号与2号。
东厂胡同这块地,原是前大总统黎元洪的宅第,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以三十万元购得,以作为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及东方文化图书馆的用地[21]。1924年初的“汪-出渊协定”第八条规定:“北京图书馆及研究所用地,由中国政府免价拨给。”[11]“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在1925年10月9日-12日召开的第一届年会上,也曾做过一项决定,敦促中国政府拨地:“总委员会对于北京研究所、图书馆地基,希望中国政府从速拨给。”[16]而显然日本方面想免费获取图书馆等用地的愿望最终落空了。
“汪-出渊协定”出自曹锟任大总统期间;而“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在第一届年会上敦促中国政府拨地时,已进入段祺瑞执政府时期;等到日本人感觉到免费获得土地希望渺茫时,又是顾维钧为阁揆了。中国政局的急遽动荡与频繁变换鲁迅所谓“大王旗”,自然会对一些外交协定的落实造成影响。加上曹锟、段祺瑞、顾维钧似乎都非“亲日分子”——1924年5月,顾维钧的北京宅第发现炸弹,传与日本人有关;“九一八”后,段祺瑞不肯被日本人拉拢,与其虚与委蛇;“卢沟桥事变”后,寓居天津的曹锟拒绝了土肥原贤二策划的要他出面组织新政府的请求。
1926年10月24日《申报》:“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大内畅三由日来京,对中国委员之主张表示承认,惟以本年为经费不充裕为理由,对北京总会方面应办之事件为图书馆建筑等,拟暂缓举办。”[22]这可能是日本方面对免费获取图书馆用地无果的一时反应,所以在仅仅事隔半年之后——即1927年春季,就有消息称,东方文化总委员会预备购置地处西皇城根的礼王府约二万坪之地[23]。而同时也有媒体称:“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前曾有规定在北京设立图书馆一所,现已筹备妥协,正在进行。关于购置书籍事,兹闻日本对华文化事务局早将购书款项五十余万汇到,筹备主任汤中,现已延聘徐鸿宝、乔曾劬为馆员,近来正向各处搜购书籍,想开馆之期,当已不远云。”[24]可见购礼王府之地用于东方文化图书馆馆址并非空穴来风,而显然情况又发生变化,最终落实在东厂胡同的黎元洪宅第。
据称购买黎宅乃由江庸介绍,日本曾派工学博士伊藤忠太前往查勘设计[25]。黎元洪此宅第范围为东至王府井大街地,西至太平胡同,南至东厂胡同,北至翠花胡同,“实测面积四十七亩九分八厘四毫,住宅及厩舍之建筑间数凡五百零八间半。”[17]伊藤忠太认为黎宅原有房舍可直接用于研究所,但做图书馆馆舍则不适合,只能在宅第内空地上另行建造[26]。而图书馆馆舍开始动工,已是6年之后,建筑工期近一年半(1934年3月1日-1935年8月30日),施工方为天津赤山工程局,建筑总面积为1876.44平方米[16]。建筑主体为“三层的钢骨水泥新式建筑”,工程费25万元[27]。
东方文化图书馆馆舍用地一再出现变故,表面看来中日双方都有原因,实则主要原因在于日本。日本不愿将庚子赔款交由中国人支配,却还要中国为日本支配的款项建设项目提供配套,实为不宜。虽然中国政府签署了“汪-出渊协定”,允诺无偿提供馆舍用地,但条约的失当,埋下了约定难以落实的风险,也果然时局一旦发生变化,协定就成为了一张废纸。
4 东方文化图书馆归属与名称的多变
东方文化图书馆肇始于中国人提出、日本方面接受的建馆要求,从早先的计划来看,东方文化图书馆是与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并列的3个首建项目之一;1924年2月6日在东京正式签署的“汪-出渊协定”,从其第三项规定的“在北京设立图书馆及人文科学研究所”来看,图书馆与研究所也是独立的两个单位;在1924年6月下旬召开的“对华文化事业调查会”第二次总会上通过的“对华文化事业”第一期计划,其中也明确说明在北京设置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与在上海设置自然科学研究所为“三项事业”[12]。
1927年9月26日抵达北京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日方委员长大内畅造,10月11日在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还在说,上海与北京设立研究所“二事刻下正在进行中”,而“至目前之事业,则为北京之图书馆。本人到京后已与中国当局交涉一切,并整理图书戡定地址预备开设……”[28]可见直到此时,东方文化图书馆与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仍是3个独立的项目。
而仅仅过了半个月,在10月下旬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召开的第二次临时总会上,委员们认为,既然东方文化图书馆的设立,已完全变为人文科学研究所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资料之用,脱离了原先公共图书馆的设想,再称之为“馆”显然不大适宜。大会因此决定,将“东方文化图书馆筹备处”的“馆”字去掉,改为“东方文化图书筹备处”,变成附属于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一个机构了。[16]
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紧接临时总会又召开了第三届年会,会上通过了《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暂行章程》与《东方文化图书筹备处章程》,前者第四条明确了图书馆筹备人员——图书筹备委员及图书筹备评议员乃由研究所设置的规定[17]。而后者第三条也规定,图书筹备评议员的会议,须由研究所总裁召开并任主席;第五条则规定了从图书借阅规则到筹备处办事细则,须经研究所正副总裁的同意方可施行[21]。由此都可看出东方文化图书馆对于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的隶属关系。
1934年,东方文化图书筹备处更名为图书部,成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下设的四个部之一[17]。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东方文化图书馆”的名称最早出现于1926年11月中下旬召开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第二届年会上通过的“东方文化图书馆筹备处章程”及“东方文化图书馆筹备处1926、1927年度经常费预算书”等文件中,由次年10月下旬即把“图书馆筹备处”改作“图书筹备处”来计算,“东方文化图书馆”的名称实际只用了11个月,此后便不再在正式文件中出现,只不过在一般文章中,或人们口头上,仍被习惯性地继续沿用,直至抗日战争胜利为止。
从日本“对支文化事业”开端时未将图书馆明确列为拟建项目,到之后屈从于主要来自于中国的强烈呼声而造成的巨大压力,才将东方文化图书馆列为待建项目,却又将馆址定与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同址,也果然随后就将其变为研究所的附属机构了。从整个孕变过程来看,日本政府对于设立独立的东方文化图书馆自始至终都是不情愿的。
5 东方文化图书馆的运行
5.1 组织与人事
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第三届年会上通过了《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暂行章程》与《东方文化图书筹备处章程》,前者其中第四条规定:“本所设图书筹备委员二人及图书(筹备)评议员若干人。筹备员由总委员会共同推荐,中国及日本委员各一人充任。图书筹备评议员除由总委员会委员充任者外,得延聘会外专家充任之。会外专家经总委员会委员共同推荐,由总裁具书延聘。”后者共六条:“第一条,图书筹备委员掌图书之调查搜集事宜。前项图书即为将来应贮藏于图书馆及续修四库全书所需要之书籍。第二条,凡图书之购置,须经图书筹备评议员会之议决。第三条,图书筹备评议员会,由研究所总裁召集之,开会时,以研究所总裁为主席。第四条,图书筹备评议员对于图书之购置,得随时提议之。第五条,图书借阅规则及筹备处办事细则,均由图书筹备委员拟订,经研究所正副总裁同意后施行,并送总委员会委员长备案。第六条,本章程自民国16年11月施行。”[21]
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在成立后通过的“研究暂行细则”,其中多项有关文献购藏,比如划定了图书著录的范围:“著录须平正无门户之见,当选要典雅记之书,空疏无用者一概不著录”;分别规定了研究员及研究所总裁的责任:“各研究员于每月杪送致其起草书目表于研究所”,“正副总裁每三个月整理各研究员提出之书目”并提交全体研究员评议决定;规定了采购的程序:“被选定之著录书籍由研究所通知图书(馆)筹备处购买或传钞之。”[17]
在此前后,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分设总务、研究、图书、会计4个部,由总务委员总管。图书部设有主任,主任之下设有主事2人,司书若干人。又定《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事务所暂行办事细则》凡五章五十五条,自1934年2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一章第六条对图书部的职责范围作了规定,为“图书之采访搜集、购买估价、装订整理、抄录校对、对类登记、编目保管。”第二章中有八条以上条目对图书部的运行规程、工作制度作了十分具体的要求:
第十八条 本事务所一切图书之调查搜集由图书部承图书筹备委员及总务委员之命处理之。
第十九条 本事务所调查及搜集图书之范围,以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必需者为主。
第二十条 本事务所购买图书之手续先由图书部主任评定价格,经过图书评议员之评阅及筹备委员之认可,然后会计部付款购置。
第二十一条 图书部依据研究部编制之所用书籍目录采访购置之。
第二十二条 本事务所既购之书籍,由图书部逐一检查册数页数,补足其缺少。
第二十四条 图书部对既购书籍编制其目录,作分类及笔划索引卡片。
第二十五条 本事务所对有储藏必要而无法购置之书,由图书部设法借抄,其费用自图书费支出。
第二十七条 图书部关于书籍之借阅须遵借阅规则,不得擅自出借。书籍借出须随时登记。
当时图书部主任为徐鸿宝,萧璋负责藏书分类,图书部工作受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筹备委员狩野直喜指导。[17]
由此看来,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有关图书部门的组织架构与管理似有交叉重复乃至混乱之象。比如,既在总委员会下设人文科学研究所,在研究所下设图书筹备处,却又在总委会下直接设有图书部——图书部门似乎兼为二级与三级部门;图书部既受总委员会总务委员领导,又须听命于研究所图书筹备处图书筹备委员,规定中却也不明确哪一方为最终决策者,似乎两方都有决定权等等。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是日本于“对支文化事业”的操办存在随意性,政府内部意见分歧,进行过程主导思想时而更改;二是日方在主观意愿上不肯真正放弃“独办”此“事业”的初衷,因而得不到中方的支持;三是日本对中国不时挑起事端乃至侵略,引发中国各界产生敌对情绪而使“对支文化事业”的进程遭受阻碍,日方疲于应对而章法失措。
5.2 文献采购与收藏
东方文化图书馆购藏的目标,一说为地方志:东方文化图书馆“主要使命便是搜购中国的地方志。”[29]来自日本的史料对此叙述得较为详细:
图书筹备处时代之购书方针,以搜集将来成为独立之汉籍专门图书馆时所应储藏者为主,有善本主义之倾向,而于研究所续修提要必要之参考书,反形缺乏。近年以来则以续修四库全书编纂上必要之书籍为主,中止购买四库全书既收书籍,以研究部所编采访书目等为据,尤其努力搜集清人及近代人著述之深有关系于学术者。又以编纂工作上之必要,更着手采购满蒙文书,此外近代影印出版之戏曲小说等,其重要者亦随时购贮。[17]
1928年中国委员因“济南惨案”集体退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时,东方文化图书馆已搜藏“各国各种古籍,数达十余万部。”之后,日本委员濑川浅之进辞退图书馆一部分中国职员,并将保管图书之权收归日本职员担任。1930年中秋有中国职员检点图书时,忽然发现有大批珍贵图书失踪[30]。
1934年年底天津《益世报》称,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现已搜罗我国书籍不下数万卷,特在该会内设立中国图书馆,专陈列中国各种书籍,供给其来华日人阅览”[31]
在北京的日本人,称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为“旧书搜买所”,1937年时,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称其图书每年购买费为二万元,“研究所于购买续修事业所必要的书籍时,并收集中国古书,借防古书的散佚。现正计划设立专门中国书的图书馆。至昭和十年止,所购书籍,包括各方寄赠的在内,已有十三万二千余册,计购书之费达三十六万八千余元。”[27]
据1934年接手主持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编纂工作的桥川时雄称,该工程至1942年底因经费短绌而告中止。东方文化图书馆的经费来源自然也告枯竭。抗战胜利后东方文化图书馆被接收时,藏书达三四十万册[32],其中“各府县方志达三千余种,为当时国内第一。”[33]
抗战胜利后,桥川时雄在回日本前,把“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编纂稿件连同东方文化图书馆的藏书,一起交给了负责接收的沈兼士。藏书一部分被北京大学图书馆接收,部分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9年后,由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接收。东方文化图书馆至此终结。
6 结语
东方文化图书馆是民国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独特的案例,虽然在当时社会并不广泛地引人注意,迄今为止也一直淡出研究者的视野,但它毕竟有长达20年的存续期,非如鸟飞过眼倏忽而逝;与它的设立、发展、收束相伴随的,是日本政府的强势与中国政府及文教界的力争,还有双方对于珍贵文献的竞相购藏等,总之,其具研究价值,不应被我国现代图书馆史所忽略。
〔1〕 [日]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对支文化事业の概要[J].日华学报,1928(3):66-68
〔2〕 朱念祖陈述中国希望[N].顺天时报,1923-4-6
〔3〕 中华留日各校同窗会对日庚子赔款讨论会 为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告国人[N].益世报,1923-5-15
〔4〕 留日自费生联合会.对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宣言[N].益世报,1923-8-8,9
〔5〕 中华学艺社发表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之意见[N].民国日报,1924-2-24
〔6〕 黄教长希求日本增加我国留日学生补助费[N].顺天时报,1923-12-21
〔7〕 朱念祖抵日后之谈话[N].申报,1923-12-18
〔8〕 朱念祖,陈延龄.为日本对华文化事业敬告国人书[N].顺天时报,1923-12-8
〔9〕 日人调查对华文化事业[N].益世报,1923-6-27
〔10〕 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之进行[N].申报,1923-7-22
〔11〕 驻日汪公使与出渊局长在日外务省之非公式协定[J].铁路协会会报,1926(165):15-16
〔12〕 日对华文化事业第一期计划[N].民国日报,1924-6-29
〔13〕 朔一.日本对华文化事业的第二幕[J].东方杂志,1924,21(9):8
〔14〕 日本芳泽公使照会[J].铁路协会会报,1926(165):14-15
〔15〕 民国十四年五月四日外交部致日本公使照会[G]//民国外债档案史料(十二).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549
〔16〕 罗琳.《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纂史纪要[J].图书情报工作,1994(1):46-49
〔17〕 太初译,容媛编.东方文化总委员会及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之概况[J].燕京学报,1936(19):215-226
〔18〕 中日文化委员议决先在北京设图书馆[J].图书馆学季刊,1926,1(3):532
〔19〕 日本外务省.总委员会记录[Z].东京:日本外务省档案馆:167
〔20〕 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中国委员退出[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8,3(6):19
〔21〕 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议决案之追纪[J].教育杂志,1928,20(1):1
〔22〕 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展期举行[N].申报,1926-10-24
〔23〕 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之进行[N].申报,1927-3-23
〔24〕 东方文化图书馆之设立[J].山东教育月刊,1927,6(3-4):14
〔25〕 东方文化图书馆之进行[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7,3(2):12
〔26〕 东方文化事业北京研究所已购定黎宅为所址[N].益世报,1927-10-13
〔27〕 [日]大阪每日新闻,越生译.日本之对华文化事业[J].文化建设,1937,3(7):51-52
〔28〕 东方文化事业又在北京进行[N].申报,1927-10-12
〔29〕 张荣华.张元济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160
〔30〕 东方文化图书馆珍籍失踪[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0,6(2):17
〔31〕 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搜罗中国书籍以供日人阅览[N].益世报,1934-11-24
〔32〕 王锺翰.清史新考[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305
〔33〕 何朋.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简介[J].书目季刊,1966,1(1):59
TheWholeStoryofOrientalCulturalLibrary
WangYixin
Oriental Cultural Library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projects of “Cultural Cause of China” implemented by Japanese governm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in China.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carried out cultural undertakings in the name of “Boxer Indemnity” in China, but reluctant to discuss with Chinese people. Though called cultural undertakings, the library was not included in the project initially. Their ulterior motive triggered a strong reaction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ircle, and the entire process of cultural library was full of variables from the preparation to the end, so hard to get normal development.
Oriental cultural library; Cultural Cause of China; Beijing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Cultural aggression
*本文为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十四年抗日战争’日本文化侵略的图书馆视角”(项目批准号17YJA870019)成果之一。
G259.29
A
王一心(1960-),男,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研究馆员,文献资料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