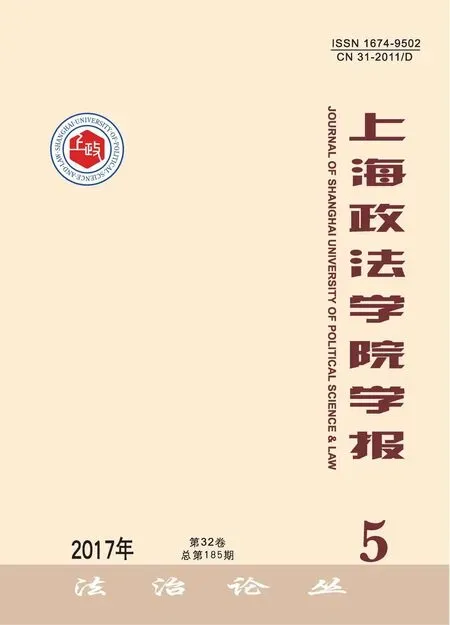论人保与物保并存时的“当事人约定”
——从(2016)最高法民终40号案切入
魏振华
论人保与物保并存时的“当事人约定”
——从(2016)最高法民终40号案切入
魏振华
《物权法》第176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其中,前一“约定”系指当事人关于担保物权实现条件的约定,后一“约定”则是当事人对债权人如何行使担保权的约定,在适用该条文时,不应将二者混淆。在债权人、债务人与担保人达成担保权行使顺序的约定时,该约定原则有效;在债权人分别与债务人、担保人达成相关约定时,只要无损于担保人之合法权益,亦属有效;而在债务人与担保人达成相关约定时,该约定不得约束债权人。根据当事人约定不同,可分为赋权型约定与限制型约定,且以前者为常见,于此情形,债权人无须再受法定限制,得自由选择行使担保权。
物的担保;人的担保;当事人约定;责任顺序;《物权法》
一、案情概要
2011年6月28日,松原天安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公司”)为归还原所欠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乾安县支行(以下简称“乾安支行”)贷款,以借新还旧方式与乾安支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天安公司向乾安支行借款17670.7万元人民币,用于偿还天安公司原所欠债务。
同日,乾安支行与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普公司”)、上海儒仕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儒仕公司”)以及吉林省酒精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精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其中第6.14条约定:“当债务人未履行债务时,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债权人均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
同日,乾安支行还分别与债务人天安公司、第三人吉林松原吉安生化丁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丁醇公司”)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其中第11.7条均约定:“当债务人未履行债务时,无论抵押权人对所担保的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抵押权人均有权直接要求抵押人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
以上合同签订后,对于本案新借贷款天安公司除偿还241万元外,其余均未偿还。2015年2月,乾安支行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索普公司、儒士公司共同连带承担保证责任,向乾安支行偿还天安公司所欠借款本金17429.7万元。①本案情形较为复杂,由于本文限于探讨人保与物保并存时的“当事人约定”问题,故而“案情概要”只截取相关事实内容。
二、裁判要旨
(一)一审判决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诉争《保证合同》关于‘当债务人天安公司未履行债务时,无论债务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乾安支行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的约定应视为各方对实现债权行使担保有明确约定,故本案即使存在债务人提供的最高额抵押担保,亦不影响乾安支行依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选择以保证方式实现债权。”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吉民二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因此,一审法院支持了乾安支行的诉讼请求。索普公司、儒士公司不服,提出上诉。
(二)二审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经审理认为,“本案《保证合同》的前述约定,仅仅是关于实现保证债权而非实现担保物权的约定,而且本案《保证合同》的前述条款也并没有明确涉及实现担保物权的内容,不能得出已就担保物权的实现顺序与方式等作出了明确约定,故不能将本案《保证合同》中的以上约定即理解为《物权法》第176条规定的‘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但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第11.7条所作的相同约定,却显然是关于实现担保物权所作的约定,是关于抵押权人直接要求抵押人在其物保范围内承担物保责任的约定,无疑属于就实现担保物权所作的明确约定……在此情形下,按照《物权法》第176条之规定,当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时,债权人即应当按照该约定实现债权,即本案乾安支行应当按照其与债务人天安公司以及第三人丁醇公司的明确约定,不仅应当先就债务人天安公司的物保实现其债权,而且也应当先就第三人丁醇公司的物保实现其债权。”③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40号民事判决书。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支持了索普公司、儒士公司的上诉请求,判决驳回乾安支行的诉讼请求。
(三)两审判决的主要分歧
两审法院均认定索普公司、儒士公司应当承担保证责任(责任是否免除属另外事项),同时本案主债权附着天安公司与丁醇公司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其主要分歧在于: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保证合同》的相关约定“应视为各方对实现债权行使担保有明确约定”。其据此依据《物权法》第176条之规定认为,即使存在债务人天安公司提供的最高额抵押担保,也不影响乾安支行选择以保证方式实现债权。故其支持了乾安支行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保证合同》的相关约定不应理解为《物权法》第176条规定的“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而2份《最高额抵押合同》所作约定却属于“就实现担保物权所作的明确约定”。于此情形,乾安支行应当按照2份《最高额抵押合同》所作约定先就债务人天安公司以及第三人丁醇公司的物保实现其债权。故其支持了索普公司、儒士公司的上诉请求。
两份判决对于如何理解《物权法》第176条规定的人保与物保并存时的“当事人约定”,存在较大分歧,由此导致截然不同的裁判结果。本文拟从规范解释的角度分析与界定此种情形下的“当事人约定”,俾益于相关规定理解的统一性。
三、判决评释
根据基本案情及两审法院的裁判说理,于此需要分析论证的主要问题有三:
第一,《物权法》第176条所作“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之规定中,“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与“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是否系属同一事项?换言之,两个“约定”的内涵是否应作统一理解,并应作何种理解?本案两审法院的裁判说理,何者更具合理性?
第二,所谓“当事人约定”是指债权人、债务人、担保人三方当事人共同约定,还是债权人与担保人或者债权人与债务人或者债务人与担保人两方当事人约定即可?两方当事人所作约定的效力如何?本案《保证合同》与2份《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否均为有效?
第三,“当事人约定”是对债权人的权利限制,还是对其赋予权利?如果存在不同的“当事人约定”时,应如何确定当事人的“真实约定”?假如本案《保证合同》与2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均为有效,那么债权人应如何行使担保权利?
下文拟就上述几个问题,在评析两审法院判决的基础上,探讨人保与物保并存时“当事人约定”的妥适理解与恰当适用。
(一)两个“约定”的规范解释
《物权法》第176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其中前句第一分句“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中出现“约定”,“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也出现“约定”,对此可能有两种理解:其一,两个“约定”含义作相同或者类似解释;其二,两个“约定”含义作不同解释。
1.同一内涵的“约定”
按照第一种理解,在当事人存在实现担保物权的“约定”情形时,债权人就应当按照该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的“约定”实现债权。显然,本案二审法院即持此立场。其认为,对《物权法》第176条可作以下三种情形的具体把握:
第一种情形,即对实现担保物权有明确约定的情形,在此情形下,无论是对人的担保合同还是对物的担保合同,均要审查是否存在“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即是否对实现担保物权作出明确约定,有此约定的,即应优先按照该类约定进行处理,无论该类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的约定是就债务人提供的物保所作约定,还是就第三人提供的物保所作约定,均应当按照该明确约定实现债权。很显然,此等情形下,隐含着意思自治可以排除物保优先的精神,这实际是将契约自由精神摆在更加重要的法律地位。但此等情形下,依然始终要围绕实现担保物权的约定进行审查,其实质亦同样体现着物保优先的法律原则。第二种情形,即先就债务人的物保实现债权的情形,经审查人保合同与物保合同,对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时,则债权人应当先就债务人提供的物保实现其债权,不得绕过债务人的物保而径行追究人保合同项下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此等情形,更是直接体现着物保优先的原则,尽管是就债务人的物保优先而言。第三种情形,即债权人对第三人提供的物保选择实现债权的情形,此等情形适用的前提与前述第二种情形应当相同,即依然是有关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时,因提供物保主体上存在差异,即物保系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所提供,则债权人既可选择向第三人物保实现债权,也可依据人保合同向保证人实现债权,或者同时向第三人物保以及人保提供者主张实现债权。此等情形,尽管赋予债权人以选择权,但此等情形的前提是没有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的明确约定,因此依然体现着物保优先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相结合的审查要求。
上述第一种情形所称“始终要围绕实现担保物权的约定进行审查”,并在有此约定时“优先按照该类约定进行处理”,实际上就是要求债权人按照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的“约定”实现债权。也就是说,《物权法》第176条前句第一分句所称两个“约定”均指实现担保物权的“约定”;进言之,第二分句所称“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亦是当事人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的“约定”。照此逻辑,只要当事人存在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的“约定”,债权人即应先按照此“约定”实现债权,而无论是否存在其他约定(如本案《保证合同》中的“约定”)。
2.不同内涵的“约定”
按照第二种理解,《物权法》第176条前句第一分句中第一个“约定”是针对当事人何时实现担保物权的,而第二个“约定”则是针对当事人如何实现担保权的。本案一审法院虽然没有如二审法院那样详细阐述《物权法》第176条所规定的“约定”含义,但其关于《保证合同》相关“约定”应视为“各方对实现债权行使担保有明确约定”的裁判说理,实则是在区分两个“约定”不同含义的基础上,针对第二个“约定”所作的具体认定。
其实,第一个“约定”较易理解,“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的条文本身即作出诸多限定。其一,该“约定”仅指向何时实现担保物权,与“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具有同质性;其二,该“约定”又明确排除了因“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而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除《物权法》第176条外,《物权法》第170条、第179条、第181条、第195条、第197条、第203条、第208条、第219条等均有相同或者近似表述,如第170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第179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第208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此类规定意在明确担保物权的实现条件:一是债务履行期届满时,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二是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可以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的。如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贷款只能用于教学楼建设,改变贷款用途时,双方借贷法律关系终止,债务人应即刻归还已贷出款项,不能归还的,债权人可以拍卖债务人的抵押财产,就卖得价款优先受偿。①参见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88页。又如当事人在担保合同中约定债务人履行债务的义务方式,若债务人不按合同约定方式履行债务,即则可构成实现质权的情形。②同注①,第456页。后一实现条件《担保法》并未作规定,③如《担保法》第33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本法规定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是《物权法》根据实践所需而作的新增规定。
第二个“约定”因前后缺乏明确限定条件,同时又没有其他可参照条文,故关于该“约定”内容的理解不乏分歧。《物权法》起草者认为其是对“物的担保和人的担保的关系”之约定;④同注①,第380页。最高司法机关则将其表述为“担保人承担责任的顺序”之约定;⑤最高人民法院物权法研究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520页。有的学者将其表述为“当事人对保证人和物上保证人之间的责任顺序和责任分担”之约定,⑥高圣平:《担保法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或者“先实行何种债权”及“各种担保的担保份额”之约定;⑦程啸:《混合共同担保中担保人的追偿权与代位权——对〈物权法〉第176条的理解》,《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6期。有的学者则将其进一步细划为“对担保人承担责任的顺序、形式和承担担保责任的份额、范围”所作的具体约定。⑧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0页。尽管上述关于第二个“约定”含义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其均认为此“约定”是针对债权人如何行使担保权的,与何种情形下方可行使担保物权的前一“约定”明显不同。《物权法》第176条旨在摒弃《担保法》第28条关于物保绝对优先的规定,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因而赋予当事人自治权利以实现担保权。
实际上,因为第一个“约定”内容甚为明确,所以关于《物权法》第176条中当事人“约定”的理论解读与司法适用一般系指第二个“约定”。如《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65条:“依照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当事人对实现担保物权的顺序有约定,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违反该约定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有当事人据此认为,《物权法》第176条所称“约定”系指“对实现担保物权顺位的约定”,“债权人只有在实现担保物权时有第一顺位、第二顺位及最后顺位等明确的排序才能按照约定实现债权,否则属于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债权人不具有选择顺序的权利”。⑨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314号民事判决书。于此情形,无论是《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65条所称“约定”,还是当事人主张中的“约定”均系指上文所述第二个“约定”。申言之,《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65条并非完整的构成规范,其隐藏了“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这一适用前提,故其完整表述应为“依照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当事人对实现担保物权的顺序有约定,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违反该约定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综上而言,前一“约定”迥异于后一“约定”:其一,前者系指担保物权的实现条件之一,后者则针对担保权的行使方式;其二,前一“约定”存在与否,与后一“约定”是否存在乃至担保权行使并无必然关系,并且现实中,前一“约定”并不多见,而后一“约定”却常常存在,如本案。
3.评释
如上文所述,《物权法》第176条前句第一分句中的两个“约定”含义明显不同,二审法院将其均认定为“实现担保物权的当事人约定”,实则是对后一“约定”的误解。如此,既有违本条规范的立法旨意,也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不相符合,殊为不妥。一审法院在区分两个“约定”的基础上,认定《保证合同》的相关“约定”系属“各方对实现债权行使担保”之约定,相对合理,值得赞同。其不足之处在于仅审查了《保证合同》项下关于实现保证债权的约定,而没有虑及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的约定,对此,二审法院也在二审判决中明确指出。
此外,即便如二审法院所阐释的两个“约定”应作同一理解,并应理解为“实现担保物权的当事人约定”,单本案是否属于“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亦值得怀疑。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均约定:“当债务人未履行债务时,无论抵押权人对所担保的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抵押权人均有权直接要求抵押人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显然,这是赋予抵押权人可以直接实现抵押权之选择权的“约定”,与所谓“实现担保物权的约定”情形相去甚远。而且,该约定所表述之“当债务人未履行债务时”,实则将抵押权的实现条件限定为“债务履行期届满时,债务人不履行债务”,从而排除了“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可以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如此来看,二审法院在法律适用方面将《物权法》第176条前句第一分句中的第二个“约定”错误地理解为“实现担保物权的约定”;而在事实认定方面又将《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相关约定错误地认定为“实现担保物权的明确约定”。因此,二审判决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与认定事实错误之处,值得检讨。
(二)“当事人约定”的主体要件
如上文所述,《物权法》第176条前句第一分句中的第一个“约定”较易理解,且作出该约定的当事人应为担保权人(债权人)与担保人(保证人、物上保证人)。但第二个“约定”的当事人因法无明确规定,理论上存在不同认识。如有的学者认为,该“约定”应是“债务人和担保人之间的约定,而不能仅仅是债权人和单个保证人或物上保证人之间的约定”;“如果债权人仅仅与个别保证人或物上保证人作出约定,则不能约束其他担保人”。①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0页。有的学者则认为债权人单独和个别担保人作出的约定,其效力如何应根据具体情况分析。①参见崔建远:《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5页;尹田:《物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7-508页。因此,下文所讨论的“当事人约定”效力问题亦仅限于第二个“约定”情形,同时“约定”内容也限于担保权的行使顺序。
1.三方当事人共同“约定”的效力
当事人约定既可以发生在设立担保权利之时,也可以发生在担保权利设立之后,其通常由债权人与数个担保人共同协商而达成协议。②参见尹田:《物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7页。如果加上债务人,则由债权人、债务人、担保人三方当事人作出如何实现担保权的“约定”。
于此情形,共同“约定”实际由三方主体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在不违反合同效力规定情形下,固然有效并应对各方当事人有拘束力。需注意的是,所称“三方当事人”并非确数,其意指包括债权人、债务人、担保人在内的三方主体,由于常常存在多个保证人或者物上保证人,因此实际可能是由多方当事人共同协商而达成协议。
2.两方当事人单独“约定”的效力
所谓两方当事人单独“约定”,系指由债权人与债务人或者债权人与担保人或者债务人与担保人两方主体达成的如何实现担保权的协议。
(1)债权人与债务人就担保权利的行使作出约定的,只要该约定不违反担保人与债权人之间的相反约定,则该约定原则上有效,③但在相关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就如何实现担保权达成的协议,是否对担保人产生约束力并不确定。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执监字第1号执行裁定书。但在债务人自己提供物保的情形下,该约定可能无效。因为根据《物权法》176条之规定,在第三人提供物保情形下,债权人行使担保权利时具有选择权,故债权人与债务人的约定原则上并不会损害担保人的利益。唯在债务人自己提供物保时,按照《物权法》176条之规定,当事人无约定时,债权人应先就债务人提供的物保行使担保权利,若此时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先要求其他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则该约定实有损于其他担保人的合法权益,故应归之无效。
(2)债权人与担保人(非债务人)共同就担保权利的行使作出约定的,该约定有效。此种情形与三方当事人共同“约定”实质无异,既是当事人达成合意,又无损于他人利益,固当有效。但由于现实交易中往往存在多个担保人,债权人可能与单个或者部分担保人(保证人、物上保证人)就如何行使担保权达成协议,此时该约定的效力如何?有学者认为,债权人仅仅与个别保证人或者物上保证人作出的约定,不能约束其他担保人。④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0页。如果债权人与部分担保人达成由其他担保人先承担担保责任约定,其他担保人可以援用合同对抗性原则,主张该约定对自己不发生拘束力,甚或可以主张此类约定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2项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而无效。⑤参见崔建远:《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5页。但实际上,此类约定是对债权人选择权的限制,并不会实质损害其他担保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有效。
具体而言,第一,当同时存在多个保证人,且债权人、部分保证人、物上保证人共同协商而作出如何实现担保权的“约定”时,无论该约定是要求先由参与协商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还是要求先由其他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只要其他保证人与债权人之间不存在相反约定,则该约定应属有效。因为此种约定实质上是对债权人所享有的选择请求权的限制,其不利于债权人,但对其他保证人的原有利益并无损害,故原则上应属有效。如果此种约定与债权人和其他保证人的约定发生抵触,则其因损害其他保证人的合法权益,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2项所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情形,应归之无效。另外,如果物上保证人为债务人,其约定先由其他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的,该约定无效。原因在于,根据《物权法》第176条前句第二分句之规定,在没有当事人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债权人就应先就债务人提供的物保实现债权,此约定未经其他保证人同意,损害了其原有利益,同属《合同法》第52条第2项所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第二,同时存在多个物上保证人,债权人、保证人、部分物上保证人共同协商而作出如何实现担保权的“约定”,该约定的效力判断与第二种情形基本一致。唯须注意,在没有参与协商的物上保证人为债务人时,则该约定应属有效。
此外,还可能存在更为复杂情形,如同时存在多个保证人和物上保证人,而参与协商的只有部分保证人和物上保证人,其作出的约定效力如何判断,亦可参照上述情形分析。
(3)债务人与担保人就担保权利的行使作出约定的,该约定不得约束债权人。有学者认为,《物权法》176条所称“约定”系指“债务人和担保人之间的约定,而不能仅仅是债权人和单个保证人或物上保证人之间的约定。”①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0页。此种认识可能并不妥当。因为无论“约定”由何人作出,最终按照“约定”行使担保权的只能是债权人。换言之,此类约定实际拘束或者限制的是债权人,在债权人没有参与协商情形下,由他人为其设置权利限制,既有违合同相对性原则,也可能因违反《合同法》第52条第2款而无效。根据《物权法》第176条,在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时,债务人自己提供物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债务人与担保人无论是约定债权人应先就物保实现债权,还是约定债权人应先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均是对债权人选择权的限制,于法不合。但在债务人与担保人约定债权人应先就债务人提供的物保实现债权时,该约定实际与债权人选择权的法定限制一致,债权人固应当先就债务人提供的物保实现债权,此亦非受此类约定之约束。当然,债务人与担保人约定赋予债权人自由选择权的,债权人应自由选择行使担保权,而无须再受法定限制。
此外,还可能存在担保人(如保证人与物上保证人)之间就担保权的行使作出约定的情形。对此,有学者认为,“无论是何人提供物保,物上保证人与保证人均可就顺位、份额等事项作出约定。”②江海、石冠彬:《论混合共同担保——兼评〈物权法〉第176条》,《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此种情形实际与上述情形无异,物上保证人与保证人所作出的约定不得约束债权人。
3.评释
本案《保证合同》系由债权人乾安支行与保证人索普公司、儒仕公司及酒精公司共同签订;2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系由债权人乾安支行分别与债务人天安公司、第三人丁醇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与《最高额抵押合同》均约定:当债务人未履行债务时,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债权人均有权直接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该约定均属于债权人与单个或者部分担保人达成协议的情形,根据上文分析,在债权人与其他担保人均不存在相反约定,且债权人与债务人并非约定先要求其他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时,3份担保合同中的相关约定应均属有效。两审法院均认定《保证合同》与《最高额抵押合同》合法有效的裁判结论,应予肯定。
(三)不同“约定”的合理确认
有学者指出,所谓当事人约定,不仅包括约定无论何种情形下,债权人均可自由选择实现任何一种担保,也包括约定即便物保是债务人提供的,债权人也必须先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①参见程啸:《混合共同担保中担保人的追偿权与代位权——对〈物权法〉第176条的理解》,《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6期。易言之,当事人约定可分为赋权型约定与限制型约定。
《物权法》第176条规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如上文所述,此项规定实际是对债权人选择权的法定限制。所谓赋权型约定,即指破除此项法定限制,赋予债权人自由选择权以实现担保权之约定。现实交易中,赋权型约定更为常见,其可能存在多种表述。有的直接表述为“债权人有权自行决定行使权利的顺序”;②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商再提字第0025号民事判决书;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6)桂民终356号民事判决书。更多则表述为“无论主债权是否存在其他担保,债权人均有权要求担保人(保证人或者物上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而无须行使其他担保权利”;③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46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359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55号民事判决书。甚或更为详细地表述为“无论主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不论上述其他担保何时成立、是否有效及债权人是否向其他担保人提出权利主张,也不论是否有第三方同意承担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务,也不论其他担保合同是否由债务人自己所提供,抵押人(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均不因此减免,债权人均可直接要求抵押人(保证人)依照本合同约定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抵押人(保证人)将不提出任何异议”。④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鄂民终495号民事判决书。此种表述意在穷尽各种可能保障债权人得以自由行使担保权,以使债权获偿。
所谓限制型约定,即指规避上述法定限制,明确设定债权人行使担保权顺序之约定,如约定债权人必须先就第三人提供物保实现债权,不足清偿时方可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就债务人提供的担保物变价受偿。限制型约定虽不常见,但其样态繁多,只要其明确了担保权的实行顺序,且无损于他人的合法权益,应均属有效之约定。实践中出现较多的是保证人就所担保债务先于物的担保承担担保责任,而无论该物保是否由债务人提供。①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0)二中民初字第2221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执复72号执行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383号民事判决书。当然,当事人也可能约定债权人应先就债务人提供的物保实现债权,此种约定与没有约定时的法定规则一致,并不影响债权人担保权的行使。
由于同一主债权下往往存在多个当事人约定,如何根据多项约定明确担保权的行使顺序,实应仔细分析具体约定内容。就本案而言,同时存在三项约定,三项约定内容基本相似。一审法院认为债权人可以根据《保证合同》中的约定选择以保证方式实现债权,实际认为该约定应属赋权型约定。二审法院则认为债权人应当根据《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的约定先行向物上保证人主张实现债权,实际认为该约定应属于限制型约定。《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当债务人未履行债务时,无论抵押权人对所担保的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抵押权人均有权直接要求抵押人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无论是该约定的表述语气(“无论”系假设条件关系连词,表示条件不同而结果不变),还是该约定的使用语词(“有权”、“直接”、“要求”),均表明当事人意在赋予债权人以自由选择权,而非设定行使顺序限制。二审法院置当事人真实意思于不顾,迳行认定该约定为债权人行使担保权设定顺序限制,其裁判殊为不妥,值得检讨。实际上,在其他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却根据类似约定认定此时债权人行使担保权“无担保责任顺位的限制”。②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554号民事判决书。尽管一审法院未能虑及《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的约定,但因其已认定《保证合同》相关约定赋予债权人以自由选择权,故亦不影响其对债权人如何行使担保权之判断。因此,在3项约定均属赋权型约定时,债权人实现担保权的选择权应得以强化,而非削弱。
四、结 语
由于《物权法》第176条前句第一分句中的第二个“约定”含义不甚明确,故在理解上可能存在分歧,但结合立法旨意与相关条文,实不应将其理解为“当事人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的约定”。本案二审法院不仅错误地将2个“约定”理解为同一内涵(当事人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的约定),而且错误地将“当事人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的约定”与“当事人关于实行担保权的约定”相混淆,因此作出了驳回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要求的不当裁判,殊值检讨。同时,对于“约定”究竟应由哪些当事人协商达成方为有效,也应根据具体情形作出判断。因此,尽管《物权法》第176条关于人保与物保并存时的处理规则甚为明确,但在具体适用时仍需作出进一步解释。
(责任编辑:王建民)
DF521
A
1674-9502(2017)05-136-10
作者:魏振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
——基于《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13条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