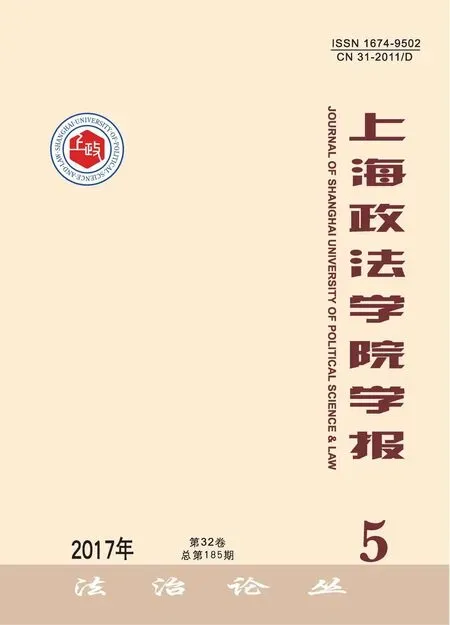我国性犯罪立法改革方向探讨
——基于德国最新立法的启示
田 然
我国性犯罪立法改革方向探讨
——基于德国最新立法的启示
田 然
当前,在性犯罪立法领域,学界关于性权利是否无关性别而平等保护、婚内有奸无奸以及被害人意志违背判断标准等问题争议较大,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廓清。新近以来,德国颁布了第50次性犯罪修正法案以加强对公民性权利的保护,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弱化违背被害人意志的认定标准,明确“不就是不”原则;二是增设性犯罪的“团体责任”条款;三是新增性骚扰罪;四是明确“婚内有奸”。德国立法关于性犯罪的改革为我国实现性权利平等保护、正确处理婚内强奸以及优化“违背被害人意志”的认定标准提供了有益借鉴。
德国性犯罪改革;性权利平等保护;婚内强奸;违背被害人意志
一、德国性犯罪改革的基本演进
近半个世纪以来,德国刑事立法中变更最大、修改最为频繁的领域非性犯罪莫属。时至今日,德国已先后颁布了2部改革法案(StRG)和6次修正法案(StG)①刑法第26次、第27次、第29次、第30次、第33次以及2016年11月颁布的第50次刑法修正法(S t),以及第4和第6德国刑法改革法(StRG),其中对性犯罪影响较大的改革主要是第4、第6刑法改革法以及第33次、第50次刑法修正法,本文也将着重介绍这4次修改法案。来完善性犯罪立法。2016年,德国科隆性侵事件的发生引发了社会对性犯罪的极度恐惧,人们强烈要求性权利保护的全面化、严格化。在此历史契机下,德国立即展开对刑法的修改,于2016年11月1日颁布了《第50次刑法修正法——改善对性自主权的保护》(BGBI.I S2460)。这一法案吸收了英美法系的经验和理论,对德国性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造,被誉为是对性权利的最严格保护。②华忆昕:《德国用刑法回应科隆性侵事件》,《检察风云》2016年第17期。
(一)破除性犯罪的性别局限
长期以来,德国与其他大陆法系的国家相似,性犯罪立法中一直弥漫着浓厚的道德情愫,性犯罪被看成是对社会风化秩序的侵害,并且性犯罪的对象被严格限定为女性,不包括男性。自1969年德国制定刑法第1改革法案时,学界对诸如同性恋、通奸等涉性道德犯罪进行了反思,但迫于道德和舆论压力,这些关于祛除性犯罪中道德因素的改革方案并未通过。①Friedrich-Christian Schroeder, Die Revolution Des Sexualstrafrechts 1992-1998, JZ,1999,S.827.而真正对性犯罪进行实质改革始于刑法第4改革法案,1973年德国颁布的第4刑法改革法(4.S t R G),将性犯罪的保护利益由侵害社会风化秩序犯罪(Sittlichkeitsdelikte)转变为侵害公民的“性自主权”(sexuellen Selbstbestimmungrecht),将性犯罪的保护利益与所谓的“性秩序”及善良风俗相脱钩,性自主权人人皆有且人人平等享有,性犯罪的被害人既包括男性也包括女性。②[德]汉斯·约格·阿尔布莱希特:《德国性犯罪刑法的改革与成果》,周子实译,《刑法论丛》2013年第3期。随后,1998年所颁布的第33次刑法修正法再次拓宽了强奸罪的打击面:增加了行为人强迫第三人向被害人实施性行为以及行为人强迫被害人向行为人自己或第三人实施性行为的同样也构成性侵、性强制以及强奸罪。③Richter Dr.Peter Reichenbach, Bielefeld/Meppen, Der Strafrechtliche Schutz Behinderter Menschen vor Sexuellem Missbrauch, Zur Verfassungskonformen Umgestaltung Des §179StGB.GA 2003,S.554-555.通过这两次的立法改革,德国性犯罪的犯罪对象和犯罪主体已经实现了“去性别化”,男女被害主体受到平等保护,性侵害的行为方式也包括异性相侵、同性相侵以及性侵第三人。
(二)弱化违背被害人意志的判断标准
目前,德国性犯罪立法改变了以往以客观立场或以行为人立场为视角的认定模式,逐渐向被害人主观意愿立场转变,这种关于违背被害人意志的判断标准被称之为“不就是不(Nein hei βt Nein)”标准,即只要被害人口头拒绝或者以动作明确或者以当时之情景应被推定为是拒绝的都应认定为是违背了被害人的意志。④Nein heit jetzt wirklich Nein, http://www.zeit.de/politik/2016-07/bundestag-sexualstrafrechtverschaerfung.2016年9月13日访问。德国第50次刑法修正案第一条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将原刑法第177条与第178合并为第177条(性侵、性强制、强奸),将该条重新表述为:违背他人的明显意志,对该人实施性行为或者让该人对其实施性行为,或者迫使该人对第三人或忍受第三人对其实施性行为。该法第2条规定,当存在以下情形时也应依照前款处罚:(1)行为人利用被害人处于无法形成或者表达反对意志的状况;(2)行为人利用被害人基于其自身或心理状态,在形成或者表达意志方面的重大限制,除非行为人得到了被害人的明确同意;(3)行为人利用了一个惊恐时刻(Uberraschungsmoment),行为人利用了被害人因明显的暴力威胁而不敢反抗的境地;(4)行为人利用了被害人的反抗被以明显的恶害相威胁之情形;(5)行为人以暴力或明显的恶害相威胁而迫使被害人忍受或实施性行为的。这5项条款是对违背被害人意志的细化规定,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对违背被害人意志的认定,除非被害人明确同意的性行为,其他情况下发生的不正常性行为一般都应推定为违背被害人的自主意愿。
(三)明确团伙犯罪适用团体责任
第50次刑法修正法还增设了第184j条团伙犯罪(Straftaten aus Gruppen),即参与一个要求其成员对他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团伙,如果该团伙中有人实施了第177条(性侵、性强迫、强奸)或第184j条(性骚扰罪),若对该行为未有其他更严厉的处罚规定的,则以本罪处2年以下自由刑或者罚金。亦即,只要行为人参与了一个犯罪团伙,而不论该犯罪团伙是否以实施性犯罪为目的而结伙,只要该团伙成员中有1人实施了涉性犯罪,如果没有更为严重的处罚,则所有团伙成员都以本罪处以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罚金。这种直接绕过责任主义的连带处罚,显然是对带有组织性的科隆性侵案件的强力回应。
(四)增设性骚扰罪
值得关注的是,德国第50次刑法修正法案增加了第184i条,即性骚扰罪(Sexuelle Belstigung),该罪的构成要件表述为:以与性相关的方式触摸他人身体或者骚扰他人,如果该行为未在其它规定中处以更为严重的刑罚,则处以2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特别严重的情形,处以3个月-5年自由刑。本罪属于亲告罪,性骚扰犯罪告诉才处理,但严重侵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国家权力机关提起公诉。
(五)明确“婚内有奸”
在德国的司法实践中,婚内强奸也是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一方面,德国刑法第4修正案将强奸罪定义为对性自主权的侵害,并强调对男女性权利的平等保护;另一方面刑法又将强奸罪规定为是“强迫性的婚外性行为”,这就造成了一种疑惑:丈夫强迫妻子的性行为到底是不是犯罪?妻子的性自主权是否可以对抗丈夫的同居权?德国在历经了近30年的讨论后,最终以修法的形式结束了这场论战。随着女权解放运动以及被害人学的兴起,一场旨在打破丈夫特权的“卧室革命”悄然兴起。德国1997年通过第33次刑法修正法案(33.StG),最终将婚内强奸(Vergewaltigung in der Ehe)纳入犯罪圈。①Vgl. Theodor Lenckner,Das 33.Strafrechts Underungsgesetz Das Ende Einer langen Geschichte.NJW1997,S.2801.但是,该法案拒绝了学界主张的将该罪设计成亲告罪的建议,而明确规定婚内强奸和其他性侵害犯罪一样,都属于公诉犯罪。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德国刑事实体法虽然未将婚内强奸规定为自诉犯罪,但在程序法中则充分考虑到了婚内强奸案件的特殊性,规定对于婚内强奸暴力和胁迫程度不明显的犯罪,可以免除刑事处罚,并且考虑到家庭关系或犯罪人的责任,可以对婚内强奸者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3 a条的规定适用暂缓起诉。②Vgl,Otto,Die Neufassung Der §§177-179 StGB ,Jura 1998,S.211f. M ü nchener Kommentar, Band 2/2,2005,§177 ,Rn.12-13.
二、对我国的启示之一:性权利平等保护
男性到底应不应该成为强奸罪的犯罪对象,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统一的:男性不能成为性犯罪的被害人。但如今,这一问题变得复杂,不少国家已将男性纳入了性犯罪的被害人行列,其中德国最先作出了表率:德国1973年颁布的第4刑法改革法(4.StRG)修改了强奸罪的构成要件,删除了“妇女”这一性别要素,性犯罪的行为人和被害人均是性别中立的自然人。与德国不同,对于强奸罪的犯罪对象,我国刑法明确规定是“妇女”和不满14周岁的“幼女”。有学者指出,强奸罪对男女性权利的保护是以表面上的不平等来实现实质上的平等,即在“性犯罪上刑法表现出对女性的特别保护”。③刘刚:《强奸罪的行为对象与量刑》,《行政与法》2010年第1期。然而对男、女性权利的保护并非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即便是女子的性权利需要特殊保护,但也并不能得出男子的性权利无需保护的结论。有学者指出:“将强奸罪规定为男人对女人的性暴力,主要是来自于立法者的主观建构,是男权主义思维惯性在现代社会的表现。”①李拥军:《掀开法律的男权主义面纱》,《法律科学》2007年第1期。笔者认为,将强奸罪犯罪对象扩展至一般人具有积极意义。
(一)男性霸权主义的观念去魅
亘古以来,除了人类早期出现的短暂的母系氏族社会外,男性是社会的主导者,而女性往往被看成是男性的附庸而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即便是女子的性权利也常常被高度物化,她不过是其父兄或丈夫的财物,对女子性权利的侵害也被看成是对男性的尊严或财产的挑战,“强奸这种违法行为是剥夺了丈夫或父亲有价值的资财,即其妻子的贞洁或其女儿的贞操”。②[美]理查德·A·波斯纳:《性与理性》,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2页。在这种父权主义和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下,强奸罪的规范价值也只是为了实现以男权为中心的性道德和风化秩序的稳定,女子的性权利完全被客体化,她并不是性权利的拥有者,而仅是男性财富或尊严的载体,因而性犯罪仅被视为是“一种加诸受害女性父亲、先生或未婚夫的罪行。”③[美]德肖维茨:《法律的创世纪:从圣经故事寻找法律的起源》,林为正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27页。事实上,在男性霸权主义观念下,表面上看是对女子性权利的特殊保护,实则是对男性霸权和女性弱势观念的在刑法中的制度性认可。直到上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和性解放运动的兴起,知识女性开始致力于打破男女不平等的局面,尤其强调性别平等、权利平等与性的自由和解放。④参见[英]简·弗里德曼:《女权主义》,雷艳红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新近以来,男性霸权主义观念日益被新时期性自主权平等观念所取代。为了适应新的社会思想变革,以往将性犯罪体系建立在男性霸权主义之上的国家纷纷改革其立法,将性犯罪的犯罪主体和对象均做去性别化修改,强奸罪的行为方式不再限定为两性之间,而是将以器官或物体对他人身体的带有奸淫意图的“侵入”行为都认定为是性犯罪。目前,我国性犯罪仍坚持认定强奸罪的主体仅为男性,犯罪对象为女性,性侵害的方式为两性性器官的媾和或接触。显然,这种立法已经滞后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性观念,也无法为女性强奸男性、同性相奸以及双性人、变性人性犯罪问题给出合适的解决方案。
(二)男性性权利刑法保护制度性匮乏的现状应予重视
我国刑法对于侵害公民性权利行为作了体系化的规制,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刑法直接处罚侵害公民性权利的行为,如通过规定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罪、猥亵儿童罪等罪名直接保护公民的性权利;二是在其他规定中间接保护公民的性权利,如在正当防卫条款中赋予被强奸者以“无限防卫权”;在组织卖淫、强制卖淫罪中规定有强奸行为的,按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⑤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对组织卖淫、强迫卖淫罪进行了修改,原立法中规定“强奸”是一种结果加重要件,修改后“强奸”行为要按照数罪并罚处理。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刑法构建了一个以“强奸罪”为中心的性犯罪体系,在这一体系内,刑法对男女性权利的保护力度出现了明显不对等现象:男童的保护力度与女童的保护力度不可等量齐观,对成年男子的保护也无法与对妇女的保护相提并论,并且男性主体被完全排除在强奸罪的保护范围外,仅可以构成强制猥亵罪或者故意伤害罪的犯罪对象。①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原强制猥亵罪的对象“妇女”修改为“他人”。然而,强奸行为与故意伤害行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性犯罪的本质在于侵害了公民的性自主权,而故意伤害罪侵害了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这是两种不同的权利属性,并且两种利益受损的认定标准也不同,生命健康权的衡量标准是外在的物理性损害程度,而性权利受损是对生理和精神的双重侵害,难以被量化,也不能比照物理性损害标准来计算。虽然《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对强制猥亵罪的行为主体和对象的限制,男性可以成为该罪的被害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但强奸和猥亵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犯罪,强奸是男性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行为,而猥亵是指奸淫以外有伤风化之色情行为,也就是说猥亵不包括“性交”行为。②参见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4页。但是,随着实践中女子强奸男子的案件的出现,这种案件中同样存在一个所谓的“性交”行为,如果按照强制猥亵处理,是不能完全评价该行为的不法和罪责的,并且还模糊了“猥亵”和“强奸”的实质差别。
除了上述罚不当罪的问题外,将男性排除出强奸罪的保护圈,还将引起刑法对男女性权利不平等保护的“蝴蝶效应”。这首先表现为男性在针对性侵害行为时是“正当防卫权限”的问题,由于强奸罪将男性性权利保护拒之门外,造成了性侵害男性的案件中公力救济的不足,从而导致了该类案件中私力救济的盛行,这种现象开启了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依照现行刑法的规定,女性面对正在进行的强奸犯罪时享有特殊防卫权,其防卫行为即便是造成了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也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而由于男性不能成为强奸罪的犯罪对象,对男性的强奸不构成强奸罪,男性在遭遇性侵害时并不享有与女性相同的特殊防卫权,于是在有的性侵案件中,男子防卫过当常被认定为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
再如,在禁止卖淫嫖娼的相关立法中,对强奸后又强迫其卖淫的行为,按照《刑法修正案(九)》之前的规定,是法定的加重处罚的情节,按照修改后的规定,组织、胁迫卖淫过程中若有强奸行为的,适用数罪并罚。然而,因男性不是强奸罪的受害人,若男性被强奸后又被组织、强迫卖淫的,也不能适用加重处罚条件,同样,因强奸男性也不构成强奸罪,数罪并罚的规定也无从适用。然而,依照司法机关的相关解释:组织、强迫他人卖淫中的“他人”,主要是指女人,也包括男人,也就是说男人可以成为组织、强迫卖淫罪的被害对象,但该罪所规定的对强奸加重处罚的条件并不能平等适用于男女被害人之间。从这些规定中均可看出,强奸罪排除了男性被害主体,同样也造成了刑法对男子性权利保护不公的连锁反应。
三、对我国的启示之二:“婚内强奸”行为应适当入罪
近年来,在我国婚内强奸能否入罪也是一个广为讨论的热点和难题。目前司法实践中较通行的做法是一般否认婚内强奸的成立,③我国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或者偶有矛盾期间,不能构成强奸罪。例如,2001年四川南江县人民法院判决的吴跃雄婚内强奸案,吴某和王某于1993年经人介绍后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1998年王某起诉离婚,后经人劝解撤诉。2000年王某再次提起离婚诉讼,法院判决准予离婚,吴某提起上诉,在上诉期间,吴某强行与王某发生性行为,次日早晨,王某感到委屈跳河自杀未遂,后报警,一审法院认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吴某的行为不构成强奸罪。但近年来,已有不少案例认为婚姻关系非正常状态下可以成立强奸罪,例如,2010年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判决的王卫明婚内强奸案,1992年王某与钱某经人介绍后结婚,婚后育有一子,后王某提起离婚诉讼,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在判决书生效之前,王某对钱某实施了强奸,法院判决王某构成强奸罪。再如,2011年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审理的孙建军婚内强奸案,被告人孙某与被害人金某于2008年登记结婚,婚后2人并未同居生活,2010年6月金某提出离婚诉讼后被驳回,孙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采用暴力殴打与胁迫的方式强行与金某发生性关系,法院判决孙某构成强奸罪。这两则案例均认为在婚姻关系非正常期间,丈夫可以构成强奸罪。但在婚姻关系非正常期间(诉讼或分居期间)可以成立强奸罪。①参见李风莲:《婚内强奸的立法问题探究》,《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5第4期。与司法实践的做法相反,我国刑法学界对婚内强奸入罪的看法不一,主流意见对婚内强奸仍持保留态度,其论据主要有二:一是“婚内无奸”。该观点认为“‘奸’的本质特征为夫妻以外的男女关系,婚内强奸也构成强奸罪的观点,超出了‘奸’的文字含义,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②刘宪权:《婚内定“强奸”不妥》,《法学》2000年第3期。也有学者从“奸”字的词源探究指出:所谓的“奸”是指不正当性行为,也就是指“婚外性行为”,进而得出“婚内无奸”的结论。③参见陈兴良:《婚内强奸犯罪化:能与不能——一种法解释学的分析》,《法学》2006年第2期。二是“夫权豁免”。该观点认为婚姻关系的缔结意味着夫妻双方互有同居的权利和义务,丈夫对妻子享有性生活的权利和义务,因此不能成为强奸罪的主体。④参见张贤钰:《评婚内无奸》,《法学》2000年第3期。因婚姻关系的合法性,丈夫的性行为被推定为是经过妻子同意的,即便存在强制行为,但被害人的同意能够阻却违法性。⑤参见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823页。但也有不少学者支持婚内强奸应当入罪,指出那些认为婚内无奸的观点是“以牺牲弱势妻子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来维护家庭与社会的稳定,是典型的性别霸权主义,是大男子主义传统观念的体现。”⑥参见苏彩霞:《我国关于婚内强奸的刑法理论下现状之探讨》,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01页。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中可以看出,在男权主义极度盛行的社会里不会有婚内强奸问题的存在,婚内强奸问题肇端于女权主义的兴起和性权利保护意识的觉醒,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推进,女性性权利意识的觉醒已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对婚内不存在强奸的认知也已随着价值观念的变迁而被不少学者所抛弃。事实上,有关学者提出的“婚内无奸”以及“夫权豁免”等阻碍婚内强奸入罪的屏障,在加强性权利保护的大势所趋之下早已不堪一击:
首先,“婚内无奸”是一个充满历史迷烟的伪命题。所谓的“婚内无奸”,有学者是从词源意义上分析“奸”的含义而得出的,并且认为自古以来“奸”就是专门指代婚外不正当的性关系,因而在合法缔结的婚姻关系中,其性行为当然也是正当的,从而得出了“婚内无奸”的结论。⑦参见张贤钰:《评“婚内无奸”》,《法学》2000年第3期。然而,对某一问题做历史性解读都必须考虑到该问题在其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以我国古代对“奸”的立法规定仅限于婚外,从而推出现今的强奸罪立法也只针对婚外不正当性关系,这种思维忽略了我国古代立法的历史局限性。我国古代立法中的“奸罪”与现代法治主义精神主导下的性犯罪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其立法目的和保护利益都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国古代惩罚性犯罪的目的在于维护宗法制度的稳定性而非对女子性权利的保护。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女性在严格的宗法制度、夫权的统治下地位十分卑贱,儒家先贤孔子曾言: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①参见《论语·阳货篇第十七》。后继者董仲舒也表达了严重的阳尊阴卑的思想: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②参见《春秋繁露·阳尊阴卑第四十三》。在“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观念影响下,古代婚姻制度充满了政治、宗法色彩,结婚的意义在于“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③《礼记·昏义》。婚姻制度中的“一妻多妾”制度以及男子单方面的“休妻”特权,使得婚后女子的家庭地位更是卑微,女性毫无性自主权。在这样一种家庭伦理制度下,女性的贞操、婚配、夫妻关系、家庭职责都被编制在宗法和伦理的罗网中,用以稳固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上下等级关系,这种男女地位严重不对等的现实之下,女子婚外的性行为,无论是强奸、和奸还是通奸均为不正当。与此相对应的是,受男性霸权思维的影响,丈夫对妻子的婚内性行为一律被肯定,因此“婚内无奸”便成为了铁律。然而,随着社会发展,性权利平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已婚女子同样享有性自主权,破除夫权专治的“卧室革命”不断兴起,不少国家的立法都已承认已婚女子的性自主权仍应受到严格的保护。
其次,“夫权豁免”过分夸大了丈夫的同居权利和误解了妻子的同意性行为的承诺。夫妻间有同居的权利和义务,但这种同意能否阻却婚内强奸的不法呢?答案不能一概而定。建立在婚姻自由、男女家庭地位平等之基础上的现代婚姻,夫妻间的性爱已经不单是原始的生理发泄或传宗接代,时代赋予其更多的内涵是两性情感上的认同和精神上的互助,在这样一种性观念下,婚姻既不是“君子协定”也不是“霸王条款”。因婚姻关系的存在,妻子让渡自己的部分性自主权,缔结婚姻便视为妻子对丈夫的性行为作出了同意承诺,但这并不意味着妻子的同意承诺在任何时期都有效,那种认为“丈夫享有同居的权利和义务,尽管是违法地行使其同居权,但是如果将其直接界定为强奸罪,则有违婚姻制度的本质”,④梁根林:《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婚内强奸犯罪化》,《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4期。以及“妇女一旦结婚,就意味着她同意与丈夫性交,而这种同意不能被撤回”的观点,⑤[英]J·C·史密斯、B·霍根:《英国刑法》,马清升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夸大了配偶的性承诺权的含义,也违背了“禁止权利滥用”的民事权利行使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在我国的立法中已有明确规定,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尤其是对性自主权这种高度私密的人身权利,其行使方式更是不能以违法的手段来实现。婚姻关系正常的情况下,可以推定妻子对丈夫所实施的性行为是同意的,丈夫要求妻子履行同居义务的请求即便是以轻微暴力或其他不够尊重的方式实现,因“法不理会琐之事(De minimis non curat lex)”,丈夫的这种行为也不具有严重的危害性,一般来说不构成侵权或犯罪;但当夫妻关系不融洽、婚姻处于非正常状态时,妻子可以收回其性同意承诺,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353条第2款规定:在婚姻生活建立之后,一方如果滥用(Missbrauch)其权利提出要求或者婚姻已经破裂的,则配偶另一方无义务满足其要求。①M ü nchen Kommentar zum BGB, 6.Aufl.2013,§ 1353,Rn.1-2.同样,妻子在婚姻关系非正常存续期间,以及丈夫滥用其权利时有权拒绝已丧失情感基础的性行为,丈夫是在明显违背妻子意愿的情形下实施的性行为,就是一种违背妇女意志的行为。
最后,“破坏家庭关系稳定”是强加给“婚内强奸入罪”莫须有的罪名。长期以来,学者抵制婚内强奸入罪的理由便是“不利于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的内部关系稳定,”②参见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823页。但是在本书之后的版本中这一观点已经不见踪迹,不知是学者的有意回避还是刻意删除。并且“对丈夫用强制手段与妻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不作刑事追究,有利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也符合我国的国情”。③肖中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这种婚内强奸入罪破坏家庭关系稳定的担忧也曾盛行于德国学者之间,例如许内曼教授就曾指出,婚内强奸入罪虽是女权运动的胜利,但同样也是对“婚姻结构”的一种实质性损害。④Vgl,Sch ü nnemann, GA 1989,S.307.转引自Theodor Lenkner, Das 33. Strafrechts Underungsgesetzdas Ende Einer Langen Geschichte NJW 1997, S.2802.Lenckner教授也对这一立法表达了质疑:婚内强奸入罪如同悬在夫妻关系上的一把利剑,丈夫或妻子随时有犯罪的可能,这难道是理性的胜利吗?⑤Vgl, Theodor Lenkner, Das 33. Strafrechts Underungsgesetz- das Ende Einer langen Geschichte NJW 1997, S.2803。这些观点提醒我们,将婚内强奸入罪还必须首先处理好社会整体秩序性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法律是平衡个人和群体利益的社会机制”。⑥[爱尔兰]J·M·凯利:《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王笑红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页。婚姻关系的稳定事关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一种秩序利益、整体利益,而丈夫强迫妻子的行为仅涉及到妻子性权利保护的问题,是一种个人利益,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便存在一个利益衡量的问题。在专制主义国家中,为了社会整体秩序的稳定而牺牲个人利益是较为普遍的做法。然而,在法治国家中,法治国刑法的任务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在所谓的家庭秩序稳定的整体利益与已婚妇女性权利保护的个人利益之间做出衡量与取舍时,我们还必须考虑个人利益该不该牺牲和值不值得牺牲的问题。随着男女平等以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观念的深入,对个人性权利的保护应该优先与对所谓的家庭关系稳定这种秩序性价值的保护,而需要靠性侵害、性强制来维系的婚姻已不值得法律以牺牲妻子的性自主权来维系,而一味地无视已婚妇女的合法权利片面强调家庭关系稳定则是在“感情用事”。
四、对我国的启示之三:细化违背被害人意志的认定标准
在强奸罪中,对于违背被害人意志的认定标准问题,司法实践中比较混乱。德国第50刑法修改法案对违背被害人意志的认定采取了更加注重被害人真实意愿的规定,对于被害人有明显的拒绝之意或者在特殊情形(如突然袭击等)下发生的性行为都认定为是违背被害人意志,放弃了以往所要求的自卫性反抗的标准,对于没有得到被害人明确同意的性行为,一般推定为是违背被害人意志。和德国不同,我国在强奸罪的构成要件上并未规定何为违背妇女意志,而只是简单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那么如何判断违背妇女意志就需要依靠实践经验。通常情况下,被害人有明显抗拒表现的很容易被认定为是违背了其主观意志,但当被害人无明显反抗行为或意思表示时,如何认定被害人的主观意志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一)违反被害人意志的两种判断路径
一般而言,对“违背被害人意志”的认定存在两种角度。长期以来,德国对违反被害人意志的考察一直是采取偏向行为人主观认知的客观视角,但随着新法案的颁布,“不就是不”原则得以确立,这一原则要求只要被害人明确表达了不同意或者被害人虽未表达反对之意,但以当时的客观情况能够推定被害人是不同意的,都应认定为是违背其意志。我国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意志的评价角度一般也是采取客观标准,而具体是倾向于被害人角度还是行为人角度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为了更合理地认定强奸罪,这需要我们寻找出科学的评价角度。
依据德国许乃曼教授的观点,对不法的认定存在两种角度,被害人角度和行为人角度,所谓被害人角度,是指从被害人的立场出发,行为的危害性是以被害人为视角去考察的。所谓行为人角度,是从行为人视角判断不法。①Sch ü nemann,Die Funktion der Abgrenzung von Unrecht und Schuld, 1995,S.160.在“违背被害人意志”的认定上,由于不同主体的价值观念不尽相同,其主观感受也存在差别,事实上,被害人的真实意愿只有其自己明确,这种真实感受是绝对的客观事实。然而,这种绝对的客观事实是难以被洞察的,因其仅被被害人一方所掌握,因此若单纯以被害人的角度去评价,将会导致只要被害人事后反悔或者否认,被告人就有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行为人所感知的被害人的意愿则具有传来性,行为人是通过其本身的主观罪过和所施加的手段以及被害人的当场反应来推断被害人究竟是同意还是排斥。被害人的感受在经过行为人主观化的理解后难免会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尤其是当行为人没有使用明显暴力以及被害人没有明显反抗或拒绝的案件中,这种误解可能会更严重,这种由行为人所感知到的“被害人意志”是相对的客观事实。单纯从行为人的角度考察也将存在问题,因为为了逃避责任,任何人都将会避重就轻。因此,单纯以被害人或行为人的角度去考察“违背被害人主观意愿”的做法都存在不妥,对“违背被害人意志”的认定应当跳出以被害人或行为人等个人角度的局限性。
(二)评价标准的选择
案例一:聚会女孩Gina-Lisa案(2012年德国柏林)②Die Familienministerin im“TeamGinaLisa”. http://www.zeit.de/2016/28/sexualstrafrechtverschaerfung-kritik. 2017年1月1日访问。
聚会女孩(Partygirl,经常出没风月场所的女子)Gina-Lisa Lohfink,在一次饮酒作乐后被两名同伴实施了强奸,Gina-Lisa为此控告两名同伴。柏林检察署审查后认为Gina-Lisa与两名被告交往过密,她在当时没有明显拒绝的意思表达(仅口头拒绝),也没有反抗或呼救行为,属于自愿发生性关系,并以Gina-Lisa诬告陷害他人而向柏林法院提起诉讼。为此,民众在社交网站上发起了标题为“Team GinaLisa”的大规模的支援和游行,要求放弃被害人必须反抗的认定标准,呼吁采用“不就是不(Nein heiβt Nein)”标准,主张口头拒绝即为违背被害人意志。
案例二:王某冒充警察骗奸案(2005年人民法院报公报案例)①参见刘文基:《冒充警察骗奸妇女如何定性》,《人民法院报》2005年4月13日。
王某冒充公安局刑警队长,以检查为由将洗头店女老板赵某哄到外面骗奸,后赵某与其丈夫说起王某的体态样貌后发现被骗,遂报警。法院认定为违背被害人意志。
案例三:因嫖资反目案(2007年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②参见陈利:《强奸罪违背妇女意志的细化分析》,《人民司法》2008年第22期。
盛某与被害人曹某网聊后约定:盛某支付1500元双方可开房发生性关系。盛某为了少付嫖资而先将曹某骗至某商场楼道内,并提出当场发生性关系,曹某不允,盛某打了被害人一耳光,见其未反抗也未呼救,继而从背后对其实施了性行为。后在去开房的途中曹某趁机逃跑。法院判决被告人违背了妇女意志构成强奸罪。
上述三则案例是反映了德国和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违背被害人意志”的认定标准。对于这一问题,德国一向采取的是“手段标准”和“被害人反抗”的标准,司法机关在认定性犯罪中违背被害人意志时总有一个暗自发力的隐形魔咒——要求被害人必须进行自卫性反抗,即要求被害人必须是屈服于暴力胁迫而不敢反抗或者不能反抗的程度时才能构成强奸罪。这种立法表达了一种对“典型强暴”的崇拜,被害人唯有尽力反抗的才能构成强奸罪。换言之,性犯罪司法认定的重点就是物理性的强制与抗拒,被害人被强制要求必须誓死抵抗的义务,否则就被当成是你情我愿的合意行为。直到1998年德国第6次刑法改革法案(6.StR G)的颁布这种倾向才有所改变,该法案修改了强奸罪的构成要件,增加了行为人“利用被害人任由行为人摆布的无保护处境”的规定。③Reichenbach, Der Strafrechtliche Schutz Behinderter Menschen vor Sexuellem Missbrauch Zur Verfassungskonformen Umgestaltung Des §179StGB, GA2003, S.550.2016年德国新颁布的第50次改革法案直接采用“不就是不”标准,规定在被害人无法形成或者无法表达反抗意志的、被害人因心理身体原因表意受限的、行为人利用一个惊慌时刻、行为人将会以明显暴力来抵制被害人的反抗、行为人以明显的恶害威胁被害人的,这些情形下实施的性行为都被推定为是违背被害人意志,除非得到了被害人的明确同意。如今,德国在“违背被害人意志”的认定标准上表现出了一种去手段化的倾向,即采取更注重从外部环境或者从被害人的主观感受来认定是否违背其意志。
与德国的认定标准日益细化不同,我国刑事立法仅在构成要件中规定“暴力、胁迫和其他手段强奸妇女”是强奸罪。由于立法过于简洁,理论以及实务界对“违背妇女意志”的认定标准并不统一,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3种主要标准:
1.手段标准。一种观点认为违背妇女意志的行为必须是采用了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由于强奸行为违背妇女意志,所以行为人必须采取某种足以使妇女不能反抗或不敢反抗的手段,这便是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这些手段是强奸行为的组成部分。如果行为人没有采取这些强制手段,即使其行为客观上违背妇女意志,也不成立强奸罪。”④江任天:《对强奸罪中“违背妇女意志”问题的再认识》,《法学研究》1984年第5期。还有观点认为暴力、胁迫等手段的标准必须到达被害人难以反抗的地步,“强奸罪中的行为内容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与妇女性交”,“强奸罪中的暴力、胁迫与其他手段都必须达到使妇女明显难以反抗的程度。”①张明楷:《刑法学》(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868、871页。
2.反抗标准。该观点认为,违背妇女意志的认定标准在于被害人是否反抗以及反抗程度如何,“性交时妇女必须是不能反抗的,如果妇女能抗拒而不抗拒,则不构成强奸罪。妇女能抗拒而不抗拒,或者不作真正的抗拒,则是通奸,而不是强奸”。②刘光显:《试论强奸罪》,《法学研究》1982年第5期。
3.同意标准。该观点认为被害人同意是判断是否违背妇女意志的标准。“判断是否违背妇女的意志,关键要看妇女对发生性行为是否同意,至于妇女表示同意是在发生性交之前还是性交过程中,均不影响同意的成立。”③何志勤:《“半推半就”不构成强奸罪》,《法治快报》2006年6月29日。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只要缺少受害人的同意,即可构成强奸罪。至于行为人是否使用暴力、恐吓或欺骗等手段并不影响强奸罪的成立。”④胡东飞、秦红:《违背妇女意志是强奸罪的本质特征》,《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3期。
上述3种标准各有优缺点,就手段标准而言,性行为如果是在暴力胁迫之下发生的则通常认为是违背了妇女意志,因而将暴力和胁迫等方式看成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有一定的合理之处。暴力、胁迫等手段很大程度上反应了被害人不情愿和被强迫程度,表明了性交行为的被动性,“正由于行为人采取了上述(暴力、胁迫或其他方式)强制手段,因而这种性交是违背妇女意志的,构成强奸。”⑤陈兴良:《规范刑法学》,中国人民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5页。但仅依靠暴力胁迫等手段而认定强奸罪的成立难免会沾染客观归罪的色彩,也使得暴力程度并不明显的性侵犯行为,常常因为暴力、胁迫程度不够而不能认定为违背妇女意志;反抗标准同样存在问题:被害人是否有反抗行为以及反抗程度如何,一定程度上能够判断是否违背妇女意志,但如果以将被害人是否反抗作为标准,则只要被害人没有反抗就是同意发生性行为,这是一个无罪推定的逻辑,无形中增加了被害人的举证责任,甚至还给被害人强加了在面对性侵害时必须要抵死反抗的义务;就被害人同意标准来看,同意标准意味着性行为必须是获得被害人同意的,没有获得被害人同意就是违背其意志,这遵循了有罪推定的思维,只要行为人无法证明自己明确得到了被害人的同意就可以归为是违背妇女意志,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强奸罪的打击面。被害人同意是违法性阻却事由,获得被害人同意的性行为当然不能认定为是强奸,但也应当意识到被害人同意是一个过于严苛的标准,它将“未明确同意”直接等同于“违背”,而同意与违背之间可能存在的模糊心态,如被害人默许或半推半就的心理状态都可能被一律认定为是违背了被害人意志。
本文认为,认定是否“违背被害人意志”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
首先,是对行为人主观意志的认定,强奸罪毕竟是一种故意犯罪,这要求行为人具有违背妇女意志而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目的和意图。对违背被害人意志的认定,应从客观一般人的角度来考察,对于此情此景下的性行为,存在违背被害人意志的可能性,且被害人的不同意是可以被行为人所知悉的,也即是说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当时的性行为有违被害人的意志。对行为人手段的考察是推测其主观心态的主要方式,认定强奸罪对行为人手段的考察和分析是不可避免的,强奸过程中使用了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是违背妇女性自主权的客观表现,暴力、胁迫手段能直观反映行为人主观上的犯罪心理,“违背妇女意志是强奸罪的实质,手段行为是对被害妇女人身、精神的强制性,是其实质的外部表现,认定强奸罪必须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①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462-463页。手段是一种客观现象,是“违背妇女意志”这一本质的外在表现,现象能够表现本质,但现象并不能尽数表现出事物的本质,因此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是认定强奸罪的充分条件,但并非是必要条件,对于行为人强制手段不明显的案件,如利用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醉酒等不能反抗或不敢反抗的,或者冒充被害人的配偶、男友的,即使被害人积极配合也应当认定为是违背其意志。因此本文认为,对违背被害人意志的认定应当去手段化,只要是行为人制造或者利用了被害人不敢反抗或不能反抗的条件的都可以认定为是违背了其意志,违背妇女意志的行为方式可能是多样的,应结合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关系、性行为发生的环境场所、行为人的动机、行为方式等因素综合考量。
其次,对被害人反抗的考察,司法实践中往往对被害人有能力反抗而没有反抗,或有被救助条件而未及时呼救的,推定其主观上同意性行为。本文认为,被害人的反应可能会依据社会关系而有所不同,例如基于熟人关系,如恋爱关系、情人关系甚至性交易关系等,对于被害人有能力抗拒而未有明显抗拒的,一般可以推定其主观上是同意的,但基于陌生人关系,即便被害人基于惧惮恶害威胁或担心名声受损而没有反抗或不敢反抗,或者认为明显处于弱势而放弃反抗,都应当认为是违背了其意志。对于有些案件中被害人有充分地意志自由的,如为逃避检查而同意与冒充警察的人进行性行为,为获取加薪、升职、升学或成绩加分而同意与他人性交的行为,在被害人未受到明显的胁迫的情况下,其有充分的选择自由,被害人作为一个人格健全的独立个体,应该考虑到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因而即便其违心作出了同意性交的选择,也不应认定为是违背了其意志。
最后,还应慎重对待被害人的同意,尤其是在钱色交易或权色交易的案件中。所谓的被害人的同意,“包括性交对象、时间、地点、方式等方面的决定权。”②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868页。被害人同意当然也包括对性交对象、时间、地点、方式等方面的同意,因此对于被害人一开始同意性行为或附条件同意的,后因为条件未满足而拒绝性行为的,此种情况应分别依据被害人表达不同意的时间,如在性行为之前被害人表达反对之意,行为人不顾被害人的反对而强行实施性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是违背了被害人的意志,如被害人同意甚至主动招嫖的,但行为人单方面改变了原商定的交易场所、时间、方式的,被害人不同意而行为人强行实施性行为的,构成强奸。如果被害人一开始同意性行为,在性行为时也没有表达反对之意,但事后因条件未满足或好处未兑现而不满的,如行为人答应事后支付嫖资、涨工资或升职但事后没有兑现或一开始就是哄骗被害人的,被害人在性行为时没有表达反对之意,但事后报警的,不应认定为是违背了其意志。
(责任编辑:丁亚秋)
DF624
A
1674-9502(2017)05-124-12
作者:田然,杭州师范大学讲师,华东政法大学与德国波恩大学联合培养法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