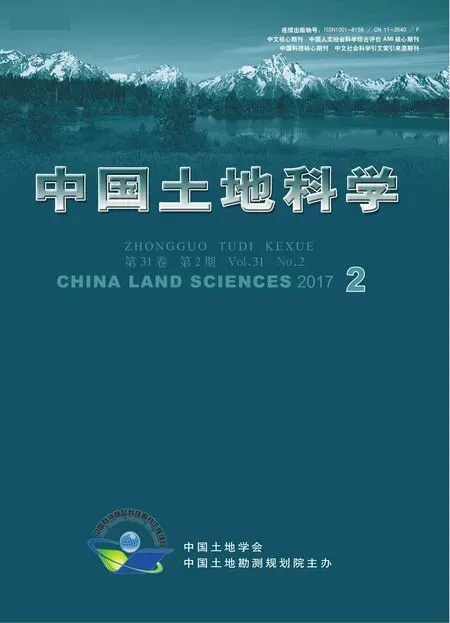农地“三权”分置的路径选择
陈胜祥
(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农地“三权”分置的路径选择
陈胜祥
(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研究目的:在“三权分置”背景下探索农地的集体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合理分置路径。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比较法。研究结果:(1)官方主流观点认为,“三权分置”就是坚持集体所有权不变,将原承包经营权拆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2)法学界质疑这种分离逻辑,认为承包经营权并不包含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就是坚持集体所有权不变,在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上创设另一个经营权。(3)这两种“三权”分置路径均排除了集体所有权的参与,也未意识到“三权分置”改革对集体所有权缺陷的修补作用。研究结论:经比较发现,更合理的农地“三权”的分置路径应当是,在具有“总有”性质的集体所有权之上创设出具有成员权性质的农户承包权,籍此将集体所有权改造为可在实践中经由个人支配的产权形态;将原承包经营权更名为经营权,使之成为去身份化后的用益物权。
土地法学;农地“三权分置”;权利分离;经济学逻辑;法学逻辑
众所周知,最新一轮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就是要突破之前的农民集体所有权加农户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格局,走一条农民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的“三权”分置路径,由此掀起了一场有关中国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研究热潮,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综观已有的相关研究发现,各界对于农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简称为“三权”)的分置路径有不同的看法,从而对分离后“三权”的权能边界及相互关系存在诸多歧见,影响后继的立法实践,需要在理论上予以辨析和澄清。为此,本文拟在全面梳理和比较不同学术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求教于学界,为进一步繁荣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学术研究做出贡献。
1 政策层面解读出的农地“三权”分置路径
迄今,中央颁发的相关政策多次提到要实行农地的“三权分置”改革,但真正提到过“三权”如何分置问题的文件仅有2016年10月30日颁发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下文简称“2016年两办意见”)。就此,下文拟分两个阶段对相关政策的文本内容进行回顾和梳理。
第一阶段主要是提出并强调农地“三权”分置的重要意义,未具体明确“三权”究竟应当如何分置。例如,2014年11月,中办发〔2014〕61号文件《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指出:“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201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提出:“在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2015年2月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抓紧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方面的法律,明确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具体形式,界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之间的关系。”2015年11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指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实行三权分置”。
随着“三权分置”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任职于相关政府研究机构的官员或学者对农地“三权”的分置路径进行了权威解读,多认为“三权分置”就是在坚持原农民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为农户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例如,陈锡文认为:“现实中农民……需要资金,商业银行每一笔贷款都必须有有效抵押物,而农民又缺乏,造成了贷款难。所以这次中央就把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单独分离出来,允许抵押担保,但承包权作为物权依然不许抵押。”[1]叶兴庆认为,“集体所有制土地是农村集体资产的主体部分,把土地承包经营权分设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是农用地产权制度演变的大趋势。”[2]张红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农村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是合一的,……在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承包权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承包权的取得和实现)两个方面。”[3]冯海发在解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时指出:“顺应实践要求,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承包权’和‘经营权’分权设置,明确经营权流转及行使的法律地位, 建立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并行分置’的新型农地制度,显得十分必要。”[4]当然,学术界也有人持类似的观点。例如,郑志峰认为,“新两权”应统属在承包经营权概念之下,是承包经营权下的两种子权利,不同于权利的权能,两权都有其存在的独立性[5]。张力、郑志峰进一步提出承包权的析出逻辑:“承包权本就来自承包经营权,其性质(物权)与承包经营权一样,符合权利分离的构造规则。”[6]刘若江描绘了“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关系”示意图,反映其所持的观点是“承包经营权包含承包权和经营权”[7]。
与前一阶段不同,“2016年两办意见”第一条明确提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并行……”。同时,该“意见”第三条第(四)项又提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是土地承包权的前提,农户享有承包经营权是集体所有的具体实现形式,在土地流转中,农户承包经营权派生出土地经营权”。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作了相应的解释和说明:“在这个框架下,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归集体所有,是土地承包权的前提。农户享有的承包经营权在土地流转中又派生出经营权,集体所有权是根本,农户承包权是基础,土地经营权是关键,这三者统一于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①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6年11月3日举行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办法发布会”,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33978/35411/ index.htm。
综上可知,笔者从中央政策层面大致可以解读出农地“三权”分置的三种路径:(1)坚持集体所有权不变,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无疑,这是早期权威解读所认可及“2016年两办意见”首先提到的“三权”分置路径,代表了官方的主流意见。(2)坚持集体所有权不变,(在土地流转中)由农户承包经营权派生出土地经营权。这是“2016年两办意见”新提出的“三权”分置路径,笔者估计是在前述第(1)种意见受到法学界的强烈批判后(详见下文)而主动作出的调整。(3)肯定集体所有权是农户承包权的前提,似乎表明可从集体所有权中派生出农户承包权,从而将原承包经营权变更为经营权。这种分置路径未得到官方任何文字上的肯定,也暂未见到学界的专门阐述。
2 法学视角解读出的农地“三权”分置路径
相比于上述政策界的模糊表达,法学界的分析思路更为明确,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三层不断递进的学术观点。
首先,多数法学家认为,官方主流观点所表述的“三权”分置路径主要是经济学的产权权能分离思维,不符合法学逻辑。例如,高圣平认为,经济学界提出的以“三权分离”学说为基础构建农地产权的观点,曲解了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之间的关系,不符合他物权设立的基本法理,无法在法律上得以表达[8]。申惠文认为,中央文件将农村土地三个产权的分离理解为三个权利的分离,将经营权视为独立的民事权利,经济学主导的色彩明显浓厚,不符合法学基本原理[9]。笔者认为,应当肯定,法学家的这一评价恰如其分。业内周知,现代产权经济学始于科斯,之后在阿尔钦、德姆塞茨、张五常、巴泽尔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产权理论逐步形成。在现代产权经济学理论中,产权为一个复数名词(Property-rights),意味着对特定财产完整的产权,不是单项权利,而是一组权利或权利体系;以(广义)所有权中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为例,任何一项权利的权能和利益都可能划分得更细[10]。
紧接着,诸多法学家认为,两权分离时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包含承包权和经营权,无法直接从中析出独立的承包权和经营权。例如,丁文指出,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包含土地承包权的观点和做法,既缺乏理论依据,又会造成一系列的不利后果[11]。朱继胜认为,在法律逻辑上,要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为土地承包权(成员权)和土地经营权,既不具可能性,也没有必要[12]。这是因为,在物权法学视野中,一项新型他物权的设立并非如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产权权能分离的结果,而是“将所有权单一内容的一部分予以具体化,让他物权人享有而已”[13]。据此,土地承包经营权并非所有权权能分离的结果[14],而是在土地所有权之上派生的一项独立完整的物权,并没有细分为“农户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就此启示,法学家对农地“三权”分置路径的理解,取的是权利派生或创设的逻辑,而不是经济学家的权能分离逻辑。
最后,法学界普遍认为,农地“三权”分置路径应当是坚持集体所有权不变,在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上创设另一个经营权;经营权是设定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上的权利用益物权;承包权则为其行使受到经营权限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代称,只是因承包经营权的部分权能让渡于经营权而产生的新的权利内容,并非单纯承包土地这样一种权利资格。持类似观点的法学家非常之多,代表性文献有孙宪忠[15]、蔡立东、姜楠[16]、李国强[17]、潘俊[18]等。
综上可知,法学界基本否定了官方主流观点所阐述的“三权”分置路径,与“2016年两办意见”关于“在土地流转中,农户承包经营权派生出土地经营权”的提法相一致,极大深化和拓展了人们对农地“三权”分置逻辑路径的相关认识。然而,“2016年两办意见”中还提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是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似乎表明集体所有权也有参与“三权分置”改革的可能性;而且,农地集体所有权一直因为其自身的缺陷而饱受诟病,学术界本还应探讨本轮“三权分置”改革对修补集体所有权缺陷中的意义和作用;就此,法学界对于“三权”分置路径的阐释仍然未曾涉及。由此表明,我们还应将集体所有权纳入农地“三权分置”框架,继续探讨农地“三权”的分置路径。
3 集体所有权参与下的农地“三权”分置路径
承前,要了解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对农民集体所有权缺陷的修补作用,需要先行了解现行农民集体所有权究竟有什么缺陷?
3.1 农地集体所有权制度究竟有何缺陷?
关于中国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缺陷问题,学术界大致有三类不同的看法:一是“所有权主体虚置说”、二是“产权模糊说”、三是“有意的制度模糊说”。长期以来,各种说法并存且偶有争鸣,似乎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
首先,“所有权主体虚置说”的核心思想是,现行法律明确规定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为三类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村内农民集体和乡(镇)农民集体,自然赋予了它们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但是,它们还应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才有保护其土地权利的能力;然而,中国立法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没有规定农民集体的机关设置和运行机制,所规定的行使代表要么“无能”、要么“不能”代表农民集体的意志和利益,由此导致“农民集体”的法律人格处于虚置现象[19-20]。
其次,持“产权模糊说”的文献非常之多,主要集中于经济学界,不同的文献又有不同的支持理由,对其进行归纳整理非常难;我们只有从整体上对这类文献的研究思路作一个逻辑划分,然后按逻辑索引对它们进行评析。就此而言,“产权模糊说”应属于下列三种情况中的一种或多种:一是在法律制度层面认为相关制度模糊,或所规定的权利内容(权利束)模糊;二是在所有权主体层面认为“农民集体”存在缺陷,即认为该组织是虚置的,没有行为能力控制或保护其土地所有权;三是在所有权运行层面,认为法律规定的所有权行使主体不能代表农民集体的意志和利益,导致现实中的“集体所有(大家都有)”成为“人人没有”。对此三种情况,王金红作了一个总括式评析:“纯粹从法律意义上讲,产权本身没有不明晰的问题,……,所谓的‘集体所有制不明确’也并非指集体产权的权利束不明确,而是‘(农民)集体’作为产权的主体是否被清晰界定,是否可操作,是否得到有效保护。”[21]据此可以判断,所谓“产权模糊”并非指是法律制度模糊(法律规定农地归三类农民集体所有的文义是很清晰的),也不是指权利内容(权利束)模糊,而应是指所有权主体——农民集体组织不能控制、保护其土地权利,这与前述的“主体虚置说”是同一个意思。
最后,“有意的制度模糊”一说由荷兰学者何·皮特教授首先提出,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仔细推敲发现,该学说实质上和“主体虚置说”并无二致。因为何·皮特教授在其书中多次承认:“既然党的政策和条例已经明文规定,农村集体依法拥有土地的所有权,那么为什么集体土地的所有权还是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呢?对此我的回答是,因为自然村(即生产队)并不具有保护其土地的任何权利。”[22]
综上,通过对三类观点进行仔细辨析和比较后发现,它们所表达的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区别在于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表达方式不同。当然,若仅从恰当用词的角度而言,“所有权主体虚置说”无疑是最精准的。因为“产权模糊”中的“产权”一词本就有财产权利、产权制度、产权关系等多种所指;“有意的制度模糊”一说在“是否有意”、“制度是否模糊”等方面也遭到了学界的质疑[23-24],更是一种内涵不清的表述。
3.2 消除农地集体所有权缺陷的“三权”分置路径
从理论上讲,要解决农民集体这一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虚置问题,不外乎如下三种思路:
第一,做实农民集体组织,使其拥有现实的行使能力。但是,这种途径明显走不通。因为,即使法律在形式上赋予了农民集体以某种民事主体资格,即有法律文本意义上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但在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的当下,多数地区的农民集体处于极为松散的状态,事实上不可能拥有行使所有权的行为能力。
第二,设法完善委托—代理机制,消除代理人的道德风险;这种做法已被实践证明不可行。因为在一盘散沙似的农村社会,要消除委托—代理困境的监督成本非常之高,加上严重的行政干预[25],导致实践中多以村委会的意思表示(甚至是村干部的个人意志)来取代、代替农民集体的意思表示,以至无法消除严重的委托—代理困境问题[26]。
第三,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中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类似于历史上的“总有”制[27-30]。但是,总有制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团体成员的共同生存,天然地有不利于财产的最大化利用和财产流转的缺陷,且在当代社会中,此种团体所有处于消亡的趋势,……不应当继续严格按照总有的规则来贯彻集体所有权,而是应当对之进行改造,使之更接近于个人支配的权利形态。基于此,通过确立并做实农户承包权,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予以改造,使之更接近于个人支配的权利形态,能够有效消除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虚置问题。
综上可知,如在本轮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中,将农户承包权视为从具有“总有”性质的农民集体所有权中创设出来的权利形态,并赋予其“成员所有”的权利内涵,则能有效克服“农民集体”行为能力虚置问题,还将集体土地所有权朝向可在实践中经由个人支配的权利形态进行大力改进;同时,维持原承包经营权的权能不变,但更名为经营权,并将其界定为去身份化后的用益物权。这即是本文所主张的允许集体所有权参与的农地“三权”分置路径。
4 允许集体所有权参与“三权”分置之路径的优势
如果允许集体所有权参与到“三权”分置中,分置路径则具有明显的优势:一方面,按该路径得到的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各得其所、各显其能,真正达到了前述“2016年两办意见”所要求的“充分发挥‘三权’的各自功能和整体效用,形成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平等保护的格局。”为了清晰说明此问题,特将前文所述的三种“三权”分置路径及由其得到的“三权”关系列陈如下(表1)。
表1显示,(1)在集体所有权方面,前两种“三权”分置路径均沿用两权分离时期的集体所有权不变,对集体所有权的主体虚置缺陷无动于衷。与此不同,本文提出的“三权”分置路径,要求从具有“总有”性质的集体所有权中派生出具有成员所有权性质的农户承包权,以此将集体所有权改造为可由个人支配的产权形态,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集体产权主体虚置的缺陷。(2)在承包权和经营权方面:①第一种“三权”分置路径要求将原承包经营权一分为二,这在法学理论上不能成立,不可能指导相关的修法实践。②按第二种“三权”分置路径,经营权从原承包经营权中派生出来,原承包经营权虽可简称为承包权,但其性质难以界定。如果将其界定为用益物权,则没有体现出承包权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本质特征,这是该分置路径不甚合理的一面。如果将其界定为成员权,则又与相关法学理论不相容,因为从承包经营权中创设出经营权后,承包经营权仍为用益物权[9]。③按本文提出的“三权”分置路径,承包权无疑体现了农户作为集体组织成员的成员权特征,并与“2016年两办意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是土地承包权的前提”相吻合;而且,按本路径得到的(承包)经营权,系已经去除身份性质的法定用益物权,较两权分离时期承载了成员身份权的“承包经营权”更有利于发挥农村土地流转和产权融资的功能。综上可知,本文提出的有集体所有权参与的“三权”分置路径具有更明显的优势。

表1 三种“三权”分置路径及其衍生的“三权”性质比较①参见“国新办关于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办法发布会”。http: //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33978/35411/index.htm。Tab.1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ree paths of “Tripartite Rural Land Entitlement System(TRLES)” and the nature of three property rights derived from TRLES respectively
另一方面,该农地“三权”分置路径既遵循了相关法学原理,也符合主流经济学对产权的研究范式,是法学和经济学都能接受的权利分置路径。
首先,该“三权”分置路径符合经济学对产权的研究范式。前文已述,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产权的研究始于科斯,其核心思想被后来者总结为三个层次的科斯定理。按约瑟夫·费尔德的表述:“科斯第一定理的实质是,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权利的初始界定不重要;第二定理认为,当交易成本为正时,产权的初始界定有利于提高效率;科斯第三定理的结论是,通过政府来较为准确地界定初始权利,将优于私人之间通过交易来纠正权利的初始配置。”[31]本文提出的“三权”分置路径实质上就是科斯定理的现实应用。因为在经济学的视野中,两权分离时期的农地产权实有两大模糊之处:一是如前所述,集体所有权存在主体虚置问题,在经济学视野中就是“产权模糊”;二是在承包权没有独立的情况下,承包经营权就对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具有很强的依附性,若承包经营权发生流转,是否也将农民的成员权转了出去?这是另一个产权不清问题。就此,依据科斯第三定理,农地产权的这两个缺陷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通过私人之间的市场交易进行纠正,需要政府出面对之进行较为准确地界定。
那么,如何界定才算是较为准确呢?据表1可知,(1)第一条“三权”分置路径,既未关注如何利用“三权分置”改革来修补集体所有权的缺陷,又违背法学原理简单地将承包经营权拆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自然不可能算得上是“较为准确”地界定产权。(2)第二条分置路径也未关注如何利用“三权分置”改革来修补集体所有权的缺陷;所得到的承包权,实质上是两权分离时期承包经营权的简称,没有体现出农民身份权(成员权)的独立化的思想,也算不上是“较为准确”地界定产权。(3)本文提出的“三权”分置路径,同时关注了已有农地产权的两大缺陷,应是一个对农地产权较为准确的界定,能被经济学界广为接受。
其次,在法学理论中,农地集体所有权具有传统“总有”性质,本就意味着各个成员(农户)共同拥有所有权,只不过不能请求分割集体财产而已。因此,从具有团体“总有”性质的集体所有权中创设出具有成员所有权意义上的农户承包权,并没有违背法学原理。实际上,《物权法》第59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就是试图通过引入“成员权”来进一步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立法活动[30]。而且,也已经有法学学者试图构建农地的“双层所有权”结构来解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问题[32]。
5 简短结论
总结前文可知,迄今官方主流观点和法学界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农地“三权”分置路径:一是维持原集体所有权不变,将原承包经营权分离为承包权和经营权;二是认为维持原集体所有权不变,在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上创设另外一个经营权。这两种“三权”分置路径具有共同的不足,即均排除了集体所有权的参与,也忽略了本轮“三权分置”改革对于集体所有权虚置缺陷的修补作用。与此不同,本文提出了另一条路径,即从具有“总有”性质的集体所有权之中派生出具有成员所有权含义的农户承包权,以此对集体所有权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一种可在实践中经由个人支配的产权形态;同时维持原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和权能不变,但将其更名为经营权,使之成为去身份化后的用益物权。经比较分析发现,按本文的“三权”分置路径得到的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均体现了其各自应有的权利性质,拥有其应有的权利内容,扮演其各自应当充当的角色。而且,这种有所有权参与的“三权”分置路径不仅遵循了相关法学原理,也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产权的分析范式,是法学和经济学都能接受的“三权”分置路径。
(References):
[1] 陈锡文.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底线不能突破[N] . 人民日报,2013 - 12 - 05.
[2] 叶兴庆. 集体所有制下农用地的产权重构[J] .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2):1 - 8.
[3] 张红宇. 构建“三权分离”的新型农地制度[N] . 中国城乡金融报,2014 - 02 - 19(B03).
[4] 冯海发. 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关农村改革几个重大问题的理解[N] . 农民日报,2013 - 11 - 18.
[5] 郑志峰.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再分离的法制框架创新研究[J] . 求实,2014,(10):87.
[6] 张力,郑志峰. 推进农村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再分离的法制构造研究[J] . 农业经济问题,2015,(1):83.
[7] 刘若江. 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启示[J] .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143.
[8] 高圣平.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下农地产权结构的法律逻辑[J] . 法学研究,2014,(4):85.
[9] 申惠文. 法学视角中的农村土地三权分离改革[J] . 中国土地科学,2015,29(3):39 - 44.
[10] 黄少安. 产权经济学导论[M]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66 - 67.
[11] 丁文. 论土地承包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离[J] . 中国法学,2015,(3):159 - 178.
[12] 朱继胜. 论三权分置下的土地承包权[J] . 河北法学,2016,(3):37 - 47.
[13] 谢在全. 民法物权论[M] .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109.
[14] 房绍坤. 用益物权基本问题研究[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4.
[15] 孙宪忠. 推进农地三权分置经营模式的立法研究[J] . 中国社会科学,2016,(7):145 - 163.
[16] 蔡立东,姜楠. 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置的法构造[J] . 法学研究,2015,(3):31 - 46.
[17] 李国强. 论农地流转中“三权分置”的法律关系[J] . 法律科学,2015,(6):179 - 188.
[18] 潘俊. 新型农地产权权能构造——基于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权利体系[J] . 求实,2015,(3):88 - 96.
[19] 于建嵘.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虚置成因[J] .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1,(3):1 - 6.
[20] 宋志红,仲济香. 论农民集体的重塑[J] . 中国土地科学,2011,25(5):29 - 34.
[21] 王金红. 告别“有意的制度模糊”——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核心问题与改革目标[J] .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2):6.
[22] 何·皮特. 林韵然,译. 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制度变迁、产权和社会冲突[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67,94.
[23] 陈胜祥. 农地产权“有意的制度模糊说”质疑[J] . 中国土地科学,2014,28(6):3 - 9.
[24] 钱龙,洪名勇. 农地产权是“有意的制度模糊说”吗——兼论土地确权的路径选择[J] . 经济学家,2015,(8):24 - 29.
[25] 高飞. 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运行状况的实证分析——基于全国10省30县的调查[J] . 中国农村观察,2008,(6):35.
[26] 陈剑波. 农地制度:所有权问题还是委托—代理问题?[J] . 经济研究,2006,(7):83 - 90.
[27] 胡吕银.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法分析[M]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46.
[28] 小川竹一. 中国集体所有土地所有权与总有论[J] . 经济法论坛,2014,(11):256 - 280.
[29] 于飞. 集体所有、共同共有、总有、合有的关系[A]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研讨会会议论文[C] . 2014.
[30] 王利明,周友军. 论我国农村土地权利制度的完善[J] . 中国法学,2012,(1):47.
[31] 约瑟夫·费尔德. 科斯定理1-2-3[J] .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5):72 - 79.
[32] 胡萧力. 模糊的清晰: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概念的再建构[J] . 法学杂志,2015,(2):133 - 140.
(本文责编:陈美景)
Path Selection of Tripartite Rural Land Entitlement System of Farmland Property Rights
CHEN Sheng-xiang
(School of Financ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best way to divide the ownership, the contractual right and the management right of farmland in China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Tripartite Rural Land Entitlement System(TRLES)”.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ry research and comparative study are employ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the dominant official viewpoints deem that given the unchanged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the original contractual management right would be divided into the contractual right and the management right. 2)The jurists usually disagreeing with the official opinion state that the contractual management right doesn’t contain the contractual right and the management right and given the unchanged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a new management right should be created regardless of the contractual management right. 3)There are common defects in the two aforementioned TRLES, namely, both opinions exclude the ownership from the TRLES and ignore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TRLES on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s shortcoming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after the comparison, the best path of TRLES should be that 1)the new contractual right which is a membership should be created based on the co-ownership of farmland, by means of which the co-ownership will become a kind of individual disposal right. 2)The original contractual management right should be named as themanagement right, making it a kind of legal usufruct.
land law; tripartite rural land entitlement system of farmland property rights; rights division; economic logic; legal logic
D922.3
A
1001-8158(2017)02-0022-07
10.11994/zgtdkx.20170215.091812
2016-11-17;
2017-01-15
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三权分离背景下农村土地承包权研究”(15JL01)。
陈胜祥(1972-),男,江西鄱阳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制度与农村经济。E-mail: chenshx122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