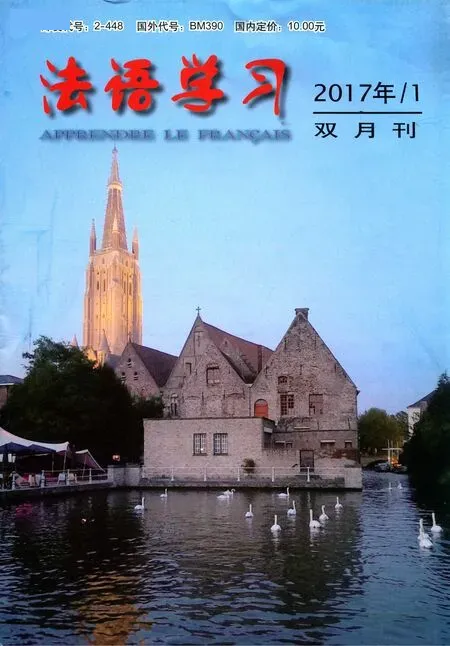从语音符号的即逝性看口译的特征①
陈 伟
从语音符号的即逝性看口译的特征①
陈 伟
在口译和笔译当中,承载意义的语言形式不尽相同,因此两种类型的翻译活动所遵循的逻辑也各有差异。“话语易逝,文字永存。”口语交际中承载信息的语音符号的即逝性,无疑会对口译活动的特征产生巨大的影响。本文试图从语音符号的即逝性出发,探讨其对口译活动造成的后果,并籍此对一些相关的问题——如口译活动覆盖的范围、其所遵循的逻辑、译员记忆的内容、口译质量的标准、翻译语言的方向等——阐述笔者的看法。
口译;语音符号;即逝性;记忆;意义
①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区域国别研究中心项目《法国翻译思想史》(项目编号QYGBYJ15CW)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
“翻译,就是在译语中用最为贴切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首先是就意义而言,其次是就风格而言。”奈达(Eugene A. Nida)这一被引用了无数次的关于翻译的经典定义告诉我们:翻译的对象是信息,翻译的目的是传递意义;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译语和源语的表达形式必然会发生变化,但其所表达的内容——即意义——则应对等。
奈达的上述论述得到了广大译者和学者的广泛认同。然而,由于在口译和笔译当中,承载意义的语言形式不尽相同,因此两种类型的翻译活动所遵循的逻辑也各有差异。“话语易逝,文字永存。”*《 Verba volant, scripta manent 》. ( Les paroles s’envolent, les écrits restent. )口语交际中承载信息的语音符号的即逝性,无疑会对口译活动的特征产生巨大的影响。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语音符号的即逝性出发,探讨其对口译活动造成的后果,并籍此对一些相关的问题——如口译活动覆盖的范围、其所遵循的逻辑、译员记忆的内容、口译质量的标准、翻译语言的方向等——阐述笔者的看法。
一、 语音符号的即逝性
在语言交际中,信息的发布者主要是通过语言符号来承载意义、传达意义的。根据交流方式的不同,承载意义的媒介大致可分为文字符号(笔语)和语音符号(口语)两种。虽然它们同属语言符号,但在滞留的时间性上,却迥然相异。
文字符号一旦落到纸上,即可长久地保存下来,供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读者反复阅读,正如千百年来,一些脍炙人口的文字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能够为世界各国的不同读者反复诵读、长久流传一样。
但在口语中,语音符号却没有像文字符号那样可长期滞留的特性。事实上,声音由物体振动而产生,以声波的形式存在,并通过某种介质传播。尽管所有固体、液体和气体都可以充当声音传播的介质,但通常我们听到的声音则是经过空气传播的。随着声波振动的停止,声音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告消逝。由此可见,构成语音链的语音符号,无论是其存在形式(声波)、还是其承载媒体(空气),都不像文字符号那样有形、具体、可捉摸。语音符号几乎在其被发出的同时,便消失于无形之中,没有任何稳定性可言。
诚然,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已经掌握了保留声音的技术,可以通过各种不同手段,将语音符号记录下来,使其和文字符号一样,具备跨越时空的可能性。但是,就口译活动——特别是同声传译和交替传译——而言,这样的声音保留技术,除了方便事后的资料查阅和翻译质量评估之外,对口译特征的影响或改变不起作用。在口译译员眼里,语音符号仍然是转瞬即逝的意义载体,这一点并没有因为录音技术的发明和广泛使用而改变。
语音符号的即逝性,不仅仅取决于该符号所赖以存在的形式及其承载媒体的无形性,更重要的还与人类记忆的特点有关。
早在上世纪70年代,达尼察·塞莱斯科维奇(Danica Seleskovitch)就指出:人的记忆有短期和长期之分。*Danica Seleskovitch, Langage, langues et mémoires, Étude de la prise de notes en interprétation consécutive, Minard Lettres Modernes, Paris, 1975.在她的论著中,“短期记忆”(mémoirecourt terme)也被称为“即时记忆”(mémoire immédiate)、“言语记忆”(mémoire verbale)、“听觉记忆”(mémoire auditive)、“操作性记忆”(mémoire opérationnelle)、或“记忆阈限”(empan mnésique),这一类记忆能够将读者或听者所感知到的语言符号及其意义记录下来,在头脑中保留极短的一段时间。“长期记忆”(mémoirelong terme),亦称“认知记忆”(mémoire cognitive),它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记住已经和语言符号剥离——也就是已经褪去语言外壳——的意义内容。无论是笔译还是口译,任何一位译员在其翻译过程中,均会不同程度地调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记忆。
“长期记忆”之所以能够长期保存意义内容,是因为后者已经与其载体——即语言符号——剥离,意义犹如经过压缩的文件,使得记忆有足够的空间来储存它们。这解释了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凭借其短期记忆,将一部电影中的某一段对白、或一本小说中的某一段文字逐词逐句地复述出来,但在较长时间以后,他能够记住并回忆的只可能是这部电影或小说的内容,而不会是原原本本的相关对白或文字。
较储存意义内容的“长期记忆”而言,储存语言符号的“短期记忆”,其记忆时间功能要弱得多。事实上,短期记忆的能力——或“记忆阈限”(empan mnésique,一个人最大限度所能记住的符号数量)——因人而异,但毋庸置疑的是,它的容量是非常有限的,也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文化程度或教育水平。实验表明:在笔语中,一个人的短期记忆能力“等于其视觉几乎同时感知的7—8个字或词”*许钧、袁筱一,《当代法国翻译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p.218.;而在口语中,一个人“在意识清楚的情况下,可以记住由5—9个‘符号’(词语、字母、数字等)构成的语音链片段,并能在记忆中保存2—3秒钟”*G. A/ Miller, cité par Danica Seleskovitch & Marianne Lederer, Pédagogie raisonnée de l’interprétation, Paris, Didier Érudition/Office des publications officielles des Communautés européennes, 2002, p.243.。此后,这些语言符号就会逐渐淡化乃至消逝,以便腾出短期记忆的空间,接受下一个“阈限”的语言符号。
短期记忆的上述特点,在笔译中并不影响文字符号的稳定性,因为虽然文字译者的短期记忆能力通常无异于口译译员,但鉴于承载文字符号的载体的物质性特点,文字译者可以随时随地依靠反复阅读,弥补短期记忆的不足。而在口译中,语音符号的不可捉摸性、以及译员在获取信息时所使用的记忆的短期性,决定了他不可能拥有和文字译者同样的优势。从这个意义而言,语音符号是即逝的。
语音符号的这种即逝性,对口译的特征有很大影响。
二、语音符号的即逝性对口译特征的影响
1. 口译通常不以文学作品为对象
索绪尔(F. de Saussure)将语言符号的形式——即声音或文字——称为“能指”,将该形式所承载的概念称为“所指”。米歇尔·阿吉安(Michèle Aquien)借用索绪尔的上述概念,指出口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的是“所指逻辑”(logique du signifié)*Michèle Aquien, L’Autre Versant du langage, Paris, José Corti, 1997, p.59.。在口译过程中,“话语易逝”,随着说话者嗓音的消逝,语音符号的形式很快淡出于译员的短期记忆,但其所承载的意义却在被译员理解之后,存入长期记忆之中;后者的任务,就是将他所理解并且记住的意义用译入语重新表达出来。鉴于语音符号的易逝性,译员难以对承载意义的语言形式做更多的关注,因此在信息再表达的过程中,他的工作重点通常是信息内容而非形式的再现。这一点和笔译——特别是文学翻译——有着本质的区别。
阿吉安还认为,笔译——特别是文学翻译——所遵循的逻辑是“能指逻辑”(logique du signifiant)*同上。。这不仅是因为在笔译过程中,译者有可能对长期滞留在眼前的文字符号进行反复阅读,更重要的是,笔译、尤其是作为其最高境界的文学翻译,对语言形式有着特殊的要求。在文学作品中,文字被视为拥有特殊内在功能的载体,是内容表达的重要手段,有时甚至还成为内容本身的组成部分。作者通过遣词造句,充分运用音韵、节奏等各种文体手段,令读者在脑海中产生丰富的形象和联想。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把文学作品中语言符号的这种内在特殊功能称为“诗性功能”,认为它“突出了符号可触知的一面”*Roman Jakobson, 《 Linguistique et poétique 》, in Essai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trad. N. Ruwet,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63, p.218.。而文字符号的“诗性功能”,正是笔译不可忽视的因素:译者不仅必须理解、而且必须再现这些功能。换言之,他有责任在向译语读者传递原作内容的同时,再现其修辞和美学特点,包括原作者的风格、文字的音韵、句子的节奏,等等。如果译文不能满足语言形式上的要求,那么译文作品的文学效果只能是一种奢望。
从翻译的角度来看,笔译的“能指逻辑”和口译的“所指逻辑”是不相兼容的。虽然两种翻译活动均以忠实传递源语文本或话语的信息为原则,但它们传递信息的方式却大相径庭。由于文字符号的稳定性特点,意义的产生变得更加复杂:译者往往只要在阅读中稍微停顿一下,便可能发现隐藏在文字符号背后的更加丰富、更为深邃的涵义——而在口译过程中,除非发生特殊情况,否则译员是不可能打断连贯的口语交际,要求说话者停顿或重复的。换言之,鉴于笔译的“能指逻辑”,译者在意义的理解、信息的表达、以及译语形式的选择等方面,往往需要比口译译员花费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精力,以便深入思考和反复推敲;而文字符号可以反复阅读的特点,事实上也给了译者这样的可能性。古今中外,一部文学品花去译者几年、几十年、甚至毕生精力的例子比比皆是。
此外,文字符号无法为译者的短期记忆所储存。前文所言,由于语言形式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因此它是翻译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说,文字的稳定性特点使得笔译译者有条件重视语言形式的话,那么,口译译员受其短期记忆能力的限制,根本不可能给予语言形式过多的关注。
因此,鉴于口、笔译所遵循的逻辑的不同,口译、特别是同声传译,一般涉及的都是那些遵循“所指逻辑”——即以传递信息内容为主要目标——的功能类文本,而不会把文学作品列入翻译的对象之列;即使迫于需要,必须对文学作品进行口译时,译员通常也只能满足传递内容的要求,而无暇顾及作品的形式再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作品是不适合以口译的方式加以传播的。
2. 口译以意义为记忆内容
维奈(Vinay)和达尔贝勒奈(Darbelnet)曾经说:“译者传递的是思想和情感,而非文字。基于这一原则,(他)需要寻求的(翻译)单位是思想单位(unité de pensée)。”*Jean-Paul Vinay & Jean Darbelnet, Stylistique comparée du français et de l’anglais, Paris, Didier, 1977 (1958), p.37.从这个意义而言,如果不谈文学翻译对文字的特殊要求,那么口译的本质和笔译是一样的。
维奈和达尔贝勒奈所说的“思想单位”,在释义派翻译理论家的笔下被称为“意义单位”(unité de sens)。“意义单位是翻译中帮助建立等值的最小成分”*许钧、袁筱一,《当代法国翻译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p.196.,它与特定的语言长度并不吻合,既不是字、词,也不是句子或其他语法单位,而是储存在短期记忆中的语言符号作用于长期记忆中的语言知识和言外知识、并与后者交互交融的产物。在口译中,译员捕捉到语音链并对其语义进行初步识别,识别的结果和该语音链一起进入他的短期记忆,唤起他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的认知认识,加上交际环境、语言环境等因素的介入,从而产生意义单位。意义单位相互叠加、相互渗透,最终形成意义。而新的意义则作为新记忆的内容,被储存到译员的长期记忆乃至认知认识库中,为他的后续理解活动提供支持和帮助。
可见,在口译译员对意义单位及意义的捕捉和理解过程中,记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反之,也只有意义单位和意义——亦即被理解的内容,才可能成为译员长期记忆的组成部分。正因如此,塞莱斯科维奇指出:“在口译中,记忆和理解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D. Seleskovitch, L’interprète dans les conférences internationales — problèmes de langage et de communication, Paris, Lettres Modernes Minard, 1968, p.74.“绝对的不理解意味着忘却(……),而理解则是记忆的同义词。”*同上, p.76.换言之,理解是记忆的前提,记忆是理解的结果,有时两者甚至混淆在一起,难分彼此。
在口语交流中,构成语音链的符号通常以5—9个的数量进入短期记忆,在那里停留2—3秒,随即淡化乃至消逝。如果一个讲话者的语速是每分钟180个字,那么记忆力再好的译员,也不可能按讲话顺序记住所有的词。不过,虽然符号在记忆中消逝,但其唤起的意义,一旦被译员理解,便可同语言形式剥离,留存在长期记忆之中。因此,其实“(口译译员)毋需具备超乎寻常的记忆能力,他只需关注意义的分析,一旦达成理解,意义便自动被记录在记忆当中”*F. Isra⊇l & M. Lederer, La Théorie interprétative de la traduction (tome I), Genèse et développement, Paris, Lettres Modernes Minard, 2005, p.60.。事实上,译员在聆听讲话时的时候,并不进行语言分析,也不试图记住构成讲话的每一个词;也就是说,他关注的并非是捕捉语音符号(能指),而是对交际意义(所指)的理解——“理解是记忆的同义词”。
但在口译实践中,似乎存在着一个与上述论断相悖的现象,就是译员的笔记。从表面上看,译员通过记录,将听到的语音符号转换为文字符号,使其拥有了更大的稳定性,从而解决了因语音符号的易逝性而造成的短期记忆不足的问题。但就笔记的本质而言,事实并非如此:译员的笔记不以语音符号为内容、也不以记录语音符号为目的。任何一位有经验的译员,他的笔记从来都不会全部由文字组成,而是文字和其他各种符号的混杂,甚至只有符号而没有文字;即使是口译笔记中的文字,它们的地位和功能也与其他符号无异。这是因为,口译笔记只是“一种记忆的技术手段,一种‘备忘录’,用以唤起对听话时所理解的意义的记忆”*同上, p.81.。换言之,笔记的功能是唤起译者对意义内容的记忆,而非承载该意义的符号。因此,如果说,口译中笔记的本质,的确是为了解决语音符号的易逝性问题、进而弥补译员短期记忆不足的话,那么笔记的内容和目的,从来就不是语言的符号或形式。
3. 口译以目标受众为导向
在意义被理解并且被记忆之后,译员就必须使用最符合译入语的口语表达方式,将其表达出来。在这一阶段,语音符号即逝性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
与口译相比,一篇在用词、文法、或表达方式上存在这样或那样问题的笔译译文,通常更容易为译入语受众所理解。因为,后者可以通过耐心反复地阅读、大量地查阅资料,弥补译文在表达上的不足,进而实现对译文的理解。口译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口译听众和口译译员一样,他们所捕捉到的语音符号同样也是转瞬即逝,他们的短期记忆同样也只能持续2—3秒钟,所以他们没有时间像笔译读者那样,在遇到晦涩难懂的文字、或有悖于规范的表达手段的时候,可以通过反复阅读和思考达到最后理解。口译听众需要的,是能够帮助自己即时抓住话语意义的翻译。因此,正如释义派翻译理论家们所主张的那样,口译必须清晰易懂:“口译译员的表达必须非常清晰,同声传译听起来不能像多少有点笨拙的翻译,而应该像正常的话语。”*Danica Seleskovitch & Marianne Lederer, Pédagogie raisonnée de l’interprétation, Paris, Didier Érudition/Office des publications officielles des Communautés européennes, 2002, p.137.
有鉴于此,很多人认为,在表达方式上,口译是以取悦目标受众为目的、以目标受众的接受习惯为导向的翻译活动;衡量口译质量的标准,除了信息再现的准确之外,同样重要的还有表达的清晰度。而表达是否清晰,恰恰取决于译员所用的译入语是否符合目的语听众的接受习惯:译员所用语言越是为听众所熟悉,后者对意义的捕捉和理解就越容易,他也就越会认为信息的表达是流畅、清晰的。由此可见,口译应力图使用听众所习惯和熟悉的译语表达方式,以使其方便快捷地理解话语的意义,从而满足“清晰”的标准。“如果口译表达不清晰、不能即时被理解,如果译员不能做到像原说话者那样自如地运用自己的语言、而是用另一种语言的方式来表达思想,那么他的翻译立刻就会变得晦涩难懂。”*同上, P.137.
也正是为了满足口译表达的“清晰”原则和目标受众导向的要求,翻译界一致公认,理想的口译方向是从B语言(外语)译成A语言(母语)。的确,一名译员,无论他对B语言及其文化的掌握有多么精深,但在表达思想和情感的时候,肯定是使用A语言更加得心应手。如果说一名高水平的译员使用B语言进行表达,也可能达到遣词的规范、造句的正确,那么当他使用A语言时,毫无疑问会显得更加自如、更加贴切、甚至更加优雅。因为A语言是他自幼浸润于其中的语言,使用A语言是他发自本能的、几乎是下意识的行为;他在使用A语言时所表现出的自信、自然,是任何一个使用B语言的人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在从B语言翻译到A语言的情况下,译员更有可能做到“像原说话者那样自如地进行表达”,从而使意义的传递更加清晰易懂,更好地满足听众的理解需求。
结论
口译是一个难得的实验室,通过它我们可以发现语言在某些特殊条件下转换的机制。
语音符号的即逝性,决定了口译是一种遵循“所指逻辑”的跨语言交际活动。受到上述特性和逻辑的影响或者说限制,口译活动在其覆盖的范围、针对的内容、翻译产品的质量评判、翻译语言的方向等方面,都显示出与笔译的诸多不同。
语音符号的即逝性,要求口译译员不仅仅做到对信息的“实时”理解和传递(这意味着译员必须以正常的交流语速捕捉信息、实施翻译),而且还必须自然、清晰地进行实时传递——也就是说,译员应让目标听众觉得,信息似乎并未经过翻译、而是直接用译入语表达出来。正因如此,研究语音符号的即逝性,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口译本质、特点、及其与笔译的差异,进而更加深刻地认识“目标受众导向”的口译理念。
许钧,袁筱一.《当代法国翻译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Aquien, M.L’AutreVersantdulangage. Paris, José Corti, 1997.
Israёl, F., Lederer, M.LaThéorieinterprétativedelatraduction(tome I),Genèseetdéveloppement. Paris, Lettres Modernes Minard, 2005.
Jakobson, R. 《 Linguistique et poétique 》, inEssaisdelinguistiquegénérale, trad. N. Ruwet,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63.
Lederer, M.Latraductionaujourd’hui,Lemodèleinterprétatif. Hachette F.L.E., 1994.
Oustionoff, M.LaTraduction. Coll.Quesais-je? PUF, 2003.
Seleskovitch, D.L’interprètedanslesconférencesinternationales—problèmesdelangageetdecommunocation. Paris, Lettres Modernes Minard, 1968.
Seleskovitch, D.Langage,languesetmémoires, Étudedelaprisedenoteseninterprétationconsécutive. Minard Lettres Modernes, Paris, 1975.
Seleskovitch, D., Lederer, M.Pédagogieraisonnéedel’interprétation. Paris, Didier Érudition/Office des publications officielles des Communautés européennes, 2002.
Vinay, J.-P., Darbelnet, J.Stylistiquecomparéedufrançaisetdel’anglais. Paris, Didier, 1977 (1958).
Quelquesparticularitésdel’interprétationvuetraverslecaractèreévanescentdessignessonores
Résumé : Dans la traduction écrite et l’interprétation, les formes linguistiques véhiculant le sens se diffèrent. Pour cette raison, les logiques suivies respectivement par les deux types d’activités traduisantes précédemment mentionnés sont aussi différentes. 《 Les paroles s’envolent, les écrits restent. 》 Il va sans dire que le caractère évanescent de signes sonores a un impact important sur l’interprétation. Le présent article essaie donc d’étudier les conséquences engendrées par l’évanescence des signes sonores sur l’interprétation, tout en envisageant certaines questions corrélatives, telles que le champ d’action de l’interprétation, la logique qu’elle suit, l’objet de la mémorisation de l’interprète, le critère de jugement de la qualité de l’interprétation, le sens idéal de l’interprétation, etc.
Motsclés: interprétation ; signe sonore ; évanescence ; mémoire ; sens
(作者信息:陈伟,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研究领域:翻译理论与实践)
H059
A
1002-1434(2017)01-004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