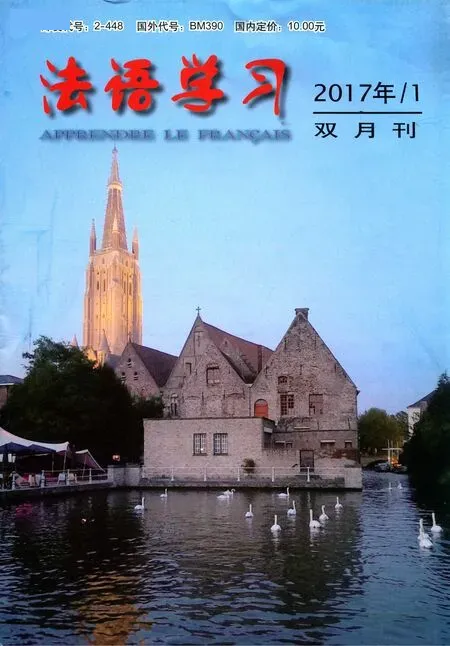《罗茜·卡尔普》节译①
[法] 玛丽·恩迪亚耶 李诺 译
《罗茜·卡尔普》节译①
[法] 玛丽·恩迪亚耶 李诺 译
①NDiaye Marie. Rosie Carpe. Paris :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2001. 147—150.
圣诞节前一天,拉扎尔乘飞机去了瓜德鲁普。后来有一天早上,罗茜路过卡尔普一家住的街道时,发现他们家的房子里已经住进了一户陌生人,她这才知道,原来父母也已经离开了。
自她上次在院子里见到父亲已过去数月,他那时顽固地想模仿园艺师的伎俩,却姿势僵硬,手法笨拙,愁容满面。几个月来,罗茜屡屡沿着黄杨篱笆走过,再没多瞧他们家的草坪一眼。黄杨散发着馥郁的味道,这气味中却从未传来过他们的声音。没有人招呼她,没有人叫她的名字,没有人请她进去坐坐,没有人关心她和她的孩子。走到院子的栅栏门前,扑面而来的是一片陌生的沉默,跟旁边所有院落里冰冷自私的沉默一模一样:无论是哪座房子里的人,都没有任何理由对罗茜·卡尔普嘘寒问暖。
直到她的父母离开,她始终没有把孩子带来见他们,想道:“何必给缇缇徒增烦恼?何必带他认识将来会对他恶语相向,让他不得不报复的人呢?”
她这样想着,心中添了几分无法排遣的辛酸。她早晨出门,走在雾蒙蒙的天空下,在心里默念,她是一个名叫罗茜·卡尔普的年轻女子,在圣诞节后的一天出门上班,行走在雾蒙蒙的天空下。描述这番场景没能给她带来半点愉悦或是轻松,尽管她现在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就是罗茜·卡尔普,这个罗茜·卡尔普每天早晨出门上班,和她一样行走在安东尼这地方的同一片天空下。如今,罗茜的哥哥拉扎尔走了,罗茜的父母也走了,只有罗茜还在这里,行走在泥泞的雪地里,而罗茜,就是她自己。
马克斯现在几乎不再来接缇缇了。起初,他来探望他们母子的次数越来越少,后来干脆就不露面了,只有在旅馆里碰到罗茜时,才会问问她孩子的近况。他的声音听起来倒是很愉悦,却总显得空洞苍白、毫无感情,仿佛例行公事一般。“嗯,都挺好的。”罗茜总是微笑着,迅速做出回答,同时在心里祈祷,他可千万不要向她解释没去看望他们母子的原因。不过她随即明白,马克斯根本就没打算解释一个字,于是她也懒得挤出微笑了,只是疲惫地重复道:“都挺好的,我觉得都挺好。”
每天晚上,她在去幼儿园接缇缇之前,都会绕路到一个小超市买一打啤酒,顺带买点别的,让买酒这事不那么显眼。
拉扎尔走了,父母也走了。她确实是罗茜·卡尔普,罗茜·卡尔普就在这里,形单影只。一回公寓,等缇缇吃完奶睡下,她就坐到床上,背靠着墙,一罐接一罐地喝下一打啤酒,两眼盯着昏暗的窗户,神情冷漠苍白,觉得自己只不过是罗茜·卡尔普毫无意义的驱壳,没有心灵,没有爱,对谁都不感兴趣,或许缇缇要除外,因为他的名字和面庞隐约能唤醒某种可能算作爱或是趣味的遥远回忆。
有时候她会多买一倍的啤酒,24罐,跟平常一样灌下去,一丝不苟,干净利落。她不高兴也不烦闷,就那么坐在床上,放任自己逐渐从现实抽离、融解。罗茜那个冰冷的家造就了她这般淡漠的性情。隔壁房间时时传来孩子的哭闹声,但罗茜一动不动,仿佛那哭声来自杳渺的远方,与她之间隔了无法跨越的混沌。缇缇尖细的哭声似乎并不是在执拗地催促她,反而像是开口前就蕴含了审慎和沮丧的意味。哭声渐弱渐缓,好像他是因为心疼母亲而有意克制似的。罗茜此刻泫然欲泣,想道:“这孩子也明白,我离他太远了,来不及赶去安抚他的。”那晚和往常一样,罗茜没法陪在孩子身边,她呆在四四方方的小房间里,因为喝酒而水肿的身体无力地靠在墙上。于她而言,孩子的哭声和这栋破房子发出的噪音别无二致,而缇缇哭几声就会很快停歇,反正哭闹也是白费力气。罗茜想,孩子早就明白她是不会来哄他的。“瓜德鲁普,天哪,瓜德鲁普。”她时不时喃喃道。
但是缇缇是明白的,她仿佛能洞穿他的心思,断定这孩子明白:他不该对罗茜,他的母亲,罗茜·卡尔普,有太多的要求。毕竟她只有二十一二岁,每日早晚独自行走在覆盖着肮脏的灰色积雪的人行道上,茫然而孤独地迷失在冬日的篱笆散发的气味中,这气味越发微弱,却经久不散,砭人肌骨。缇缇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很少哭,这个孤单的孩子就这样下意识地迁就和保护着她。每天起床时,罗茜发现,缇缇醒来的时候总是紧紧靠在婴儿床的内侧,一动不动,似乎他不仅明白他唯一的依靠只有自己,再无旁人,而且知道他所依靠的这个身形瘦弱、面色苍白的小人儿,也就是他自己,随时都能令人指摘罗茜身上的缺陷,揭露罗茜致命的弱点——他的诞生即是耻辱。他瞪大眼睛,忧虑而专注地望着她,眼神中不掺杂一丝期待。面对这样的缇缇,罗茜心中顿时产生了极为深沉的感激之情,把他紧紧地搂在了怀里,却因为搂得过于紧,感觉到了他如怯弱的小鸟一般的惊惧之情。她这才尴尬地意识到,这孩子从未享受过片刻的绝对安宁,而他竟也默然接受了这种如履薄冰般的生活,知道母亲随时可能把自己掐死或闷死,只不过还没下定决心——她,他的母亲,罗茜·卡尔普。
她才刚刚二十岁出头,小腹上就已经有了赘肉。她心想,不知道这孩子会不会感觉到,是啤酒填塞起了她愈加臃肿的身躯。“瓜德鲁普,除了我,卡尔普家的人都在瓜德鲁普”,她向缇缇耳边絮絮念叨,“到底为什么,为什么这一家子里,没有一个人把我们一起带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