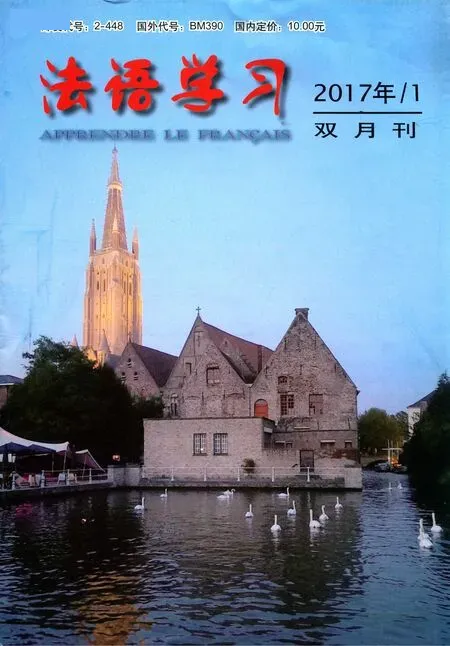玛丽·恩迪亚耶《罗茜·卡尔普》中的遗弃主题
李 诺
玛丽·恩迪亚耶《罗茜·卡尔普》中的遗弃主题
李 诺
玛丽·恩迪亚耶(Marie NDiaye)是法国当代知名女作家。她幼年时被塞内加尔籍父亲抛弃,由法国籍的母亲抚养长大,颇为坎坷的童年经历使得“遗弃”成为了她的作品中的重要主题之一。恩迪亚耶的小说《罗茜·卡尔普》(RosieCarpe)于2001年获得费米娜文学奖,书中以女主人公罗茜为代表的多个“弃儿”形象,体现了作者对家庭观和身份意识的格外关注。本文以《罗茜·卡尔普》一书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遗弃”对书中多个人物性格命运产生的不同影响,并结合恩迪亚耶的叙述特色及本人生活经历,探讨其作品中由“遗弃”引发的身份危机。
玛丽·恩迪亚耶;《罗茜·卡尔普》;遗弃;身份意识
在谈到创作《罗茜·卡尔普》这本书的初衷时,玛丽·恩迪亚耶说道:“我想写一本书来探讨已成年的孩子与他们父母之间的关系。”*《玛丽·恩迪亚耶访谈》,法国《读书》杂志2001年4月刊。与传统意义上温暖、和谐、安宁等家庭的定义不同,恩迪亚耶笔下的家成为了冷漠、残酷和怪诞的代名词,而家庭中的一切残酷之最,依恩迪亚耶之见,正是遗弃。《罗茜·卡尔普》中塑造了多个不同意义上的“弃儿”形象,他们遭到遗弃的原因和结果各不相同。本文将分析“遗弃”对书中多个人物性格命运产生的不同影响,结合恩迪亚耶的叙述特色及其生活经历,分析其作品中由“遗弃”引发的身份危机。
一、 罗茜:承载遗弃的烙印
小说《罗茜·卡尔普》在前两章和后两章中分别着重刻画了两个曾在不同意义上遭到遗弃的人物——罗茜和拉格朗。
罗茜的一生可谓在被遗弃中度过。父母送她和哥哥拉扎尔到巴黎读书,随后却突然宣布要他们从此自谋生路。拉扎尔的消失使得罗茜不得不独自搬到巴黎郊区,找了一份旅馆接待员的工作。结识旅馆老板马克斯后,罗茜毫无感情地与其保持着伴侣关系,后来生下儿子缇缇,却视孩子为羞耻的象征。一次偶然的机会让罗茜发现父母与哥哥早已发迹,他们就住在不远处的一栋别墅里,却根本无意寻找自己。罗茜被马克斯抛弃,意外怀上第二个孩子,山穷水尽之时,决心前往瓜德鲁普投奔哥哥并寻找孩子的父亲,然而家人的冷漠抹杀了她的最后一丝希望。她的儿子缇缇虽然成年后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却始终与罗茜保持着距离。人到中年时,罗茜与拉扎尔的朋友拉格朗结为夫妻,生活中总算开始出现明亮的色彩,小说却于此处戛然而止。
罗茜第一次被父母遗弃时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她默默接受了这个事实,性情中既保有一份无知的天真,又暗含几分麻木和厌倦。她将名字由“露丝·玛丽”(Rose Marie)缩短改为“罗茜”(Rosie),一遍遍对外人固执地重复自己的新名字,仿佛要与过去的自己强行区别开来,与曾经拥有家庭的露丝·玛丽断然决裂。此时的罗茜就像一个无知而无畏的孩子,以为换上一身新衣就能告别苦楚的过往。在发现父母和哥哥早已团聚时,她孤身走在街道上,不断地重复和确认自己的身份:“她很清楚,她就是罗茜·卡尔普,罗茜和罗茜·卡尔普都是她。”*NDiaye Marie. Rosie Carpe. Paris :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2001. 本文引用凡出自此书者将只夹注页码。仿佛是这个名字给了她存在的根基——当罗茜从原来的生活中被莫名抽离出来时,她需要自己建立起新的空间和新的身份,继续存在下去。
就在这种茫然无畏的状态下,罗茜遇到了马克斯,随后经历了第二次抛弃。罗茜对马克斯并无感情,实际上,她对包括自己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感情:过早地体会到亲情的断裂,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使她丧失了接受和表达感情的能力。面对马克斯的调情,她不说拒绝,不感悲凉,不抱期待,而是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姿态默默接受了这段关系,甚至在马克斯带来一个妇人拍摄他们的色情录像带时,她也只是淡淡地觉得这个女人很像她的妈妈。罗茜习惯用利益得失而非感情交互来衡量自己与马克斯的关系。在床上时,她觉得自己任他摆布是因为她欠他的,毕竟是他让她第一次体验到了恨的滋味。憎恨马克斯给她带来了变态般的快感,而怀上他的孩子则使她愤然:这不是她的骨血,只是摄像机镜头前她与马克斯苟且的见证。生下缇缇后,她对哥哥拉扎尔说马克斯待他们母子不错,一再强调“这辆婴儿车是马克斯付钱买的……不是我要他买的,是他自己愿意付钱的”(98—99)。然而身为有妇之夫的马克斯,并不曾将罗茜这样一个飘萍一般的女孩放在眼里,等待她的只能是被抛弃的结局。这次被抛弃的经历让身陷深渊的罗茜加速坠落,在被父母亲手推下悬崖后,当时还只是个孩子的罗茜在黑暗中肆无忌惮地挣扎、需求一个支点,触到手的是却尽是寒冰。如果说第一次遗弃塑造了罗茜冷漠麻木的性格,那么第二次遗弃则激发了她对感情歇斯底里的渴望。
第三次抛弃罗茜的人,一度是她唯一的牵挂——哥哥拉扎尔。多次遭受遗弃后的罗茜几乎无法再对他人付出感情,然而哥哥拉扎尔始终占据着她心中独特的位置:每每提及拉扎尔的名字,她总要补充一句“他是我的哥哥”,依恋之情可见一斑。刚到旅馆工作时,罗茜就一再强调她有个哥哥叫拉扎尔,或许有一天会来找她。当拉扎尔以一副落魄潦倒的面孔出现时,罗茜虽然自己过着清苦的生活,却不惜倾囊相助。而当她发现父母和哥哥早已团聚,她对父母的态度依旧漠然,但坚持要见到拉扎尔才肯离开。尽管她知道拉扎尔是个无赖,却还是甘愿把自己的全部积蓄拿给他做生意用。当罗茜被马克斯抛弃时,走投无路的绝望激发了她内心最深的期待,她对拉扎尔的依恋与日俱增,最终决定去瓜德鲁普投奔声称发迹的哥哥。可惜她的热情和依赖在拉扎尔眼中毫无意义,他甚至从未打算让罗茜真正走进自己的生活。罗茜在亲眼看到不堪的真相后,明白自己已经彻底被哥哥抛弃,走投无路的她终于跌落至绝望的谷底。
其实,小说中几乎没有描写过两人兄妹情深的回忆,而拉扎尔也绝不是什么正直可靠、值得托付之人,罗茜对拉扎尔的感情无疑十分突兀且过于浓烈。而罗茜之所以任由自己对哥哥的依恋之情肆意生发,是因为她迫切地需要为自己的感情寻找一个出口,这个出口不可能是遗弃她的父母或者被她视为羞耻的缇缇,于是她在潜意识中选择了曾与她一同被抛弃的哥哥。当唯一的亲情寄托也弃她而去,罗茜再无希望,只想与过去完全剥离,第三次抛弃使罗茜面对命运的态度由逆来顺受转为冷酷报复,从而产生了抛弃缇缇的念头。
纵观罗茜的一生,“遗弃”成为她挣脱不开的牢笼。罗茜自从被父母抛弃,似乎就脱离了理智且有温度的生活,置身事外一般经营着自己的日子,无论是痛苦还是快感,都无法使她的内心丰富起来。她几乎成为了一个扁平化的形象,一个毫无意义的躯壳。正如她自己所说,“罗茜觉得,所有人的目光都能径直穿透她的身体,倘若她站在一堵墙前面,人们看到的也会是那面墙而不是她这个人,她不过是一个温度不定的庞大的影子:头发梳在脑后,眼神空洞苍白,无力的微笑挂在模糊不清的两片嘴唇上。”(81)被遗弃的经历,让罗茜厌弃甚至放弃自我。
除了看待自我的态度发生改变,在对待下一代的方式上,罗茜仿佛也渐渐向其父母靠拢。没有感受过父母亲情的她,仿佛丧失了作为母亲去爱孩子的能力。她在刚刚怀上缇缇时,认为“身体里这个东西,是在摄像机的注视下莫名诞生的,而摄像机录下的影片,正在无数个角落里——无数个污秽的不可想象的所在——呈现出若隐若现的蛛丝马迹,这影片展示的纵然不是班班可考的罪证,却也是无可磨灭的耻辱”(85)。缇缇出生后,罗茜对他的照顾就像例行公事一般,孩子整夜的啼哭,唤不起她的半点恻隐之心,“于她而言,孩子的哭声和这栋破房子发出的噪音别无二致,而缇缇哭几声就会很快停歇,反正哭闹也是白费力气。罗茜想,他早就知道她是不会来的。”(149)缇缇曾有两次患了重病,罗茜却茫然不知所措,反倒有几分令其自生自灭之意。住在巴黎郊区时,缇缇病重,罗茜却感到事不关己,仿佛不知道一个生病的孩子需要看医生。到了瓜德鲁普,缇缇因为接触老鼠又大病一场,罗茜依旧不管不顾,而拉格朗正是在此刻看出,罗茜想让这个孩子去死。当罗茜腹中的第二个孩子因拉扎尔不幸流产时,罗茜明明该对哥哥彻底绝望,却将过去承受的所有痛苦归结到缇缇身上,绝望地期盼着这个孩子消失。如果说拉扎尔曾经是罗茜寄托感情的出口,那么缇缇无疑成为了罗茜抒发恨意的对象。她对父母只是漠然,而这个孩子,不仅见证了罗茜所谓的耻辱,更标志着她最不堪和无助的岁月。罗茜曾经被抛弃的命运,只差一点就要在下一代的身上重演。
二、 拉格朗:打破遗弃的枷锁
与罗茜不同,拉格朗的母亲之所以弃他而去,是因为患有精神疾病。他从小在瓜德鲁普长大,十岁时,母亲被家人强行送往精神病院,她当时没有要求再见儿子,而拉格朗怀着纠结与疑虑之心,也没有再去探望她。直到二十年后,拉格朗经过几番踌躇,终于借着带缇缇看病的机会,在病房中见到了母亲,然而他的母亲却已无法认出他了。拉格朗虽然年少时被母亲遗弃,却始终对她保有几分怀念,而这段尘封的记忆在他遇到罗茜后被重新唤醒。在他眼中,罗茜与他的母亲有着相似的命运:同样是被家人抛弃,同样是过着平庸的日子,同样的渺小和微不足道,在人生的河流上泛不起一点波澜。他对母亲的怀恋之情逐渐转化为对罗茜的知己之感,在与罗茜分别十九年后,最终与她携手。
曾遭遗弃的经历对罗茜和拉格朗造成了几乎截然相反的影响,罗茜在潜意识中模仿着父母的行为,变得愈发冷漠和麻木,而拉格朗则不断受到这段回忆启发,成长为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如果说在人生的舞台上,罗茜始终戴着象征遗弃的镣铐艰难行走,那么拉格朗则选择打破枷锁,从阴影走到光下。
拉扎尔结识的第一个卡尔普家的人是拉扎尔。拉扎尔到达瓜德鲁普后,全然变成了流氓无赖一般的人物,他从事非法生意,与还是高中生的安妮塔育有一女,甚至犯下杀人罪行。拉格朗尽管对他的种种行为十分鄙夷,却总是带着出奇的耐心照顾他、容忍他、迁就他。究其原因,拉格朗自己说道,拉扎尔就像是母亲从前养的那条狗,拉扎尔在拉格朗身边转就好像那条狗和母亲都在不远处,而对待“一条狗”,他自然会给予更大限度的包容和忍让。拉格朗始终怀念着与母亲相伴的童年岁月,而拉扎尔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充当了连接当下的拉扎尔与记忆中旧时光的桥梁。尽管拉扎尔粗俗无礼,还肆意滥用拉格朗的善心,拉格朗仍愿以这种独特的形式纪念童年的安宁与母亲的柔情。被遗弃的经历无疑会带给拉格朗永久的遗憾与酸楚,但未被遗弃时“生活的原貌”却指引着他,一路对他人付出关怀,以一种不同寻常的姿态,一步步走向温暖和光明的所在。
拉格朗对罗茜的印象,似乎与他记忆中的母亲有所重合。在目睹了罗茜想要抛弃缇缇甚至让他去死的举动后,拉格朗如同顿悟一般,重新解读了母亲当年弃他而去的行为。“我的母亲只穿着一件黄色的连衣裙,就从自己的家里逃走了,她或许也是为了避免变成如今想让缇缇去死的罗茜,避免让自己变得如此可鄙可恶,避免将我拖入险境,所以她才咒骂着离去,这一切的一切,或许,或许都是为了保护我。”(217)拉格朗从罗茜的极致的恶中感悟到母亲扭曲的善,尽管在近二十年间他与母亲不曾来往,尽管他从前对母亲只有不解和怨念,但罗茜的出现赋予了这整个遗弃行为闪着光辉的母爱的意义。从此,他不由自主地爱上了罗茜。“从前,罗茜在拉格朗眼里,过于弱小、过于善良,仅仅是个年轻而温柔,走在迷途上的女人。其实他从前,根本没有看清她。”(213)而后来,当罗茜的所作所为与他被抛弃的人生经历相联系,甚至相重合时,“拉格朗对罗茜,再无怜悯之意……他就是想要罗茜留在他身边,倘若某种悲惨的命运一定要纠缠着她,那就让她沉浸在这宿命中,只要她能待在他身边。”(207)年幼时被遗弃的经历使他在感情方面表现得格外细腻敏感,如果说母爱曾经辜负了他,那么他在爱情中,其实是在无意地找寻母亲的痕迹,以此充实他的心灵和情感体验。他说,罗茜让他感到害怕,他自己也对这个念头感到惊异,这样一个柔弱的女人,怎么会引起他的恐惧。然而就在这种时空交错的恐惧之情中,拉格朗对罗茜的爱意不断生长,与其说他爱慕的是罗茜这个女人,不如说他珍惜的是他母亲的影子,这种奇异的联系引领着拉格朗,走进罗茜的生命里。拉格朗爱上罗茜的缘由令人哑然:正是年少时经历的遗弃激发了他接纳他人和爱他人的能量。
虽然同样曾遭遗弃,但拉格朗对待孩子,全然不似罗茜般冷漠无情。他对孩子的接纳首先源于他对罗茜的感情,“他想要罗茜·卡尔普,就算她得拖着这两个没父亲的孩子。他要她,而且他现在几乎是以一种谦卑的姿态接纳了她,就连那两个骨子里留着别人的血、面色苍白的孩子,他也愿意以同样谦卑的姿态,一并接纳。”(199)后来,他对孩子的感情愈发真挚,以至于促成了他对母亲的首度探望。缇缇初到瓜德鲁普时,因罗茜的刻意疏忽大病一场,而罗茜表现得出奇地冷静,甚至不屑于为“这点小事”带他去医院。拉格朗独自带缇缇去就诊时,几次三番被询问是否是缇缇的父亲,他的回答从最初模棱两可的“不是。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是的吧”,到轻巧简单的“是的”,最后变为语气坚定的“我是他的父亲,他唯一的父亲”。带缇缇看完病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去看望同样住在这家医院的母亲:“我已经成了一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正直体面的男人,她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心里会不会闪过一丝惊讶呢?”(273)被抛弃的经历,没有让拉格朗产生报复下一代的病态心理,反而使他愈发感念亲情的可贵。
罗茜和拉格朗都曾被父母抛弃,然而一个走上了消极冷漠、与亲情绝缘的道路,另一个则成长为正直善良、勇于追求感情的人。其实除这两人以外,被遗弃的孩子的故事远未终结。罗茜的母亲狄安娜和父亲弗朗西斯在到达瓜德鲁普生活后,分别与中年男人弗雷特及其女儿丽斯贝特建立起畸形的恋爱关系。狄安娜为弗雷特育有一女,取名为露丝·玛丽,正是罗茜曾经的名字。狄安娜全然不把罗茜当做自己的女儿,甚至在拉格朗到访并说明他已与罗茜结婚后,狄安娜还无不惋惜地说:“您本可以要我的女儿啊,露丝·玛丽……我可以把她送给您的。”(337)令人扼腕的是,露丝·玛丽也并未得到母亲的照拂,而是受母亲指使,小小年纪便沦为娼妓。至于丽斯贝特,在弗朗西斯去世后,就遵照狄安娜的意愿嫁给了缇缇——她的旧情人的外孙,过上了看似体面实则空虚的生活。露丝·玛丽和丽斯贝特都是受命运摆弄的女孩子,她们同样被家庭的温暖和正常的感情生活所抛弃,而缇缇也因被罗茜视作痛苦的见证,始终被他的母亲厌恶和无视,甚至险被遗弃。
从罗茜、拉格朗,到缇缇、露丝·玛丽、丽斯贝特,无一不是畸形的家庭和冷酷的亲人手下的的牺牲品。他们被遗弃的形式和原因多种多样,形成了一个命运相互交叉的独特群体,背负着相似的忧惧,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开去,在作者笔下展开一幅令人惊异的巨大画卷。恩迪亚耶塑造了多个被遗弃的人物形象,以冷静的笔触刻画着破碎的家庭为子女的人生打下的烙印。遗弃带来的后果无法归结为绝对负面或绝对正面,恩迪亚耶并不试图归纳出一定的结论,而是力图展现家庭对被遗弃的主人公的性格和行为造成深刻影响,引发人们思索在如此背景下生存的孩子,个人成长与家庭环境具有怎样的关系。
三、 遗弃的后果:身份的漂移与缺失
在《罗茜·卡尔普》一书中,以罗茜为代表的弃儿,在遭受遗弃后面临的重要创伤之一,便是身份的漂移与缺失。
身份是个人存在于文化社会的根基,身份认同则是确认“我”之所以为“我”的理由。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认为,“一个尚处于婴儿阶段的孩子,举步趔趄,仰倚母怀,却兴奋地将镜中形象归属于己,这在我们看来是在一种典型的情境中表现了象征性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我突进成一种首要的形式。以后,在与他人的认同过程的辩证关系中,我才客观化。”*拉康. 《拉康选集》. 褚孝泉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1. 第90页。一个人的自我认同首先是通过镜像建立起来的,婴儿正是通过凝视镜中自己的形象,建立起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因而,自我身份的形成必然依赖于对他者的参照,主体只有在他者的凝视下不断反观自身,才能完成对自我身份的主动建构。在小说《罗茜·卡尔普》中,女主人公的身份定义始终与他人紧密联系。罗茜童年时的身份只是单纯的“家庭中的女儿”,按部就班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在被父母遗弃后,她将哥哥当做世上唯一的亲情纽带,不惜代价地对他付出深情与爱,实际上将自身定义为“拉扎尔的妹妹”;怀抱巨大热忱却被哥哥抛弃后,罗茜陷入了绝望和麻木,对冷漠的世界几乎已经不再有留恋,而再次建立融入这个世界的自我身份自然无从谈起。罗茜的身份意识是以他人为参照方才构建起来的,而他们对她的一次次遗弃,其实正是在不停打碎罗茜以他们为媒介建立的自我身份,每次遗弃引发的身份认同破裂,都意味着她要拾起愈加零散的身份碎片,进行更加艰难的重建。当罗茜的身份认同感在接连的刺激下不断重建又不断失去,她面临的身份危机不断发酵,最终,这一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导致她对自我身份的彻底放弃。
在拉康的理论框架中,“主体是通过别人的言语来承担起他的历史”*同上,第266页。,因此“别人的言语”是解读自我身份的另一关键维度。主体的姓名,即他者对主体的呼唤,是重要的“别人的言语”之一,“在语义变化中,这回应了我独有的词汇的内涵及意义,就像回应了我的生活方式和我的性格一样。”*同上,第269页。在很大程度上,主体正是通过他人对自己的呼唤,将自我认同和外界认同联系起来的。在《罗茜·卡尔普》中,罗茜对自己的姓名有着非同一般的执念。被父母遗弃后,她将名字从最初的“露丝·玛丽”改为“罗茜”,固执地向马克斯多次强调自己取了新名字,然而他的眼中只有她的肉体,根本不在乎她姓甚名谁;罗茜后来与父母和哥哥重逢并被唤作“露丝·玛丽”时,几乎是愤然地喊出自己的新名字,要求他们以“罗茜”称呼自己,但家人对此不以为意,一笑了之。“他者的话语”在此处表现出较强的不可靠性和不确定性,罗茜象征新身份的名字没有得到他者肯定性的反馈,由此增加了其建构身份认同的困难与障碍,而她进行身份求证的对象也逐渐从他者转为自身。当罗茜独自一人行走在巴黎郊区的小道上,她屡屡向自己确认,她就是“罗茜·卡尔普”,“罗茜·卡尔普”就是她;当她感到笃定坚强时,她会说“自己身上满是罗茜·卡尔普的气息”;当她颓然潦倒时,她则认为“自己只不过是罗茜·卡尔普毫无意义的躯壳”。如果将姓名看做自我身份认知的象征性表达,那么罗茜面对自己的身份,始终是有距离感的,她无法做到完全接纳自我、掌控自我,而是尝试着给自己建立一个身份模型,然后以偏执的方式强行将自己锁进模型里。她似乎期待通过强烈的心理暗示完成身份构建,但他者的缺位无疑加剧了身份危机。
女性主义地理学认为,地域空间是女性意识和女性身份的起源,女性的气质是在空间中被空间化地建构起来的。在《罗茜·卡尔普》中,恩迪亚耶十分关注人物在地域空间中的移动,用动态的笔触描画出罗茜被遗弃的命运和挣扎的痕迹。罗茜出生在法国的南部小城布里夫(Brive),在这里度过了平和安宁的童年时光,这个城市为她后来经历的所有漂泊涂抹了一层暖色的背景,愈发反衬出色调阴沉的颠沛流离。后来罗茜和拉扎尔前往巴黎求学,两人随即被父母抛弃,巴黎成了分离的同义词,标志着罗茜的“弃儿”生活真正开始。在巴黎郊区的小镇安东尼(Antony),罗茜独自经营着自己一团糟的日子,不仅发现父母与哥哥再次将自己抛弃,而且生活愈发艰难,最终前往瓜德鲁普。瓜德鲁普则意味着转折,本想投奔哥哥的罗茜终于看清了亲人的淡漠和自己的无知,索性割舍了自己与家庭的一切联系,甚至毫不掩饰地展露出对缇缇的憎恨之情。地域空间中的移动同时体现出女主人公心境的变动,从宁静到无知,从痛苦到麻木,作者赋予每个地点不同的意义和功用,以独到的叙述策略从空间维度展现了罗茜身份建构的曲折经历。
实际上,玛丽·恩迪亚耶的作品中反复体现的身份问题与她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她也是一个在世界各个角落找寻身份认同的“异乡人”。恩迪亚耶于1967年出生于法国卢瓦雷省的皮蒂维耶(Pithiviers),母亲出身于法国中部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来自塞内加尔的留学生,两人在巴黎读书时相识。恩迪亚耶年仅一岁时,她的父亲就抛弃家庭回到了非洲,她将近20岁时才再次与他相见,后来也只再见过父亲两次。恩迪亚耶成长在法国,后来从西班牙移居到意大利,在荷兰居住一段时间后又回到法国,2007年以后则长期居住在德国,始终不曾选择一个永久的居所。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非洲,恩迪亚耶总是被视作“异乡人”,在某种意义上,她是一个被故乡遗弃的孩子。在法国,她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作家,却总因肤色和姓氏被误以为是非洲人;在非洲,她常常被不熟识的人看作同胞,却又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与当地的风俗环境格格不入。她将自己与非洲的关系描述为“陌生而遥远”,非洲于她而言更像是“虚幻的梦境而非现实”。诚然,恩迪亚耶是被这片热带大陆所吸引的,在她的诸多作品中,非洲几乎无处不在,然而她也坦言,自己对这片土地怀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玛丽·恩迪亚耶访谈:我不想用魔法取巧》,法国《电视全览》杂志 2013年2月15日刊。,这种恐惧或许正是她对身份认同的困惑,而对于自我身份的追问,为其作品提供了独特的养分。
结 语
玛丽·恩迪亚耶在小说《罗茜·卡尔普》中塑造了以罗茜和拉格朗为代表的多个“弃儿”形象,他们被遗弃的原因多种多样,既有父母主观上的憎恶,也有家人无奈下的选择。而面对被遗弃的事实,他们或是在逃避的途中变得冷漠厌世,或是在追忆的路上学会温暖他人。作者试图将人物置于极端的家庭环境中,去探究一个家庭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成长轨迹,同时也致力于探索个人忍耐力的弹性和限度。通过以几近无情的方式将书中的人物命运撕裂开来,恩迪亚耶在揭露残酷而怪诞的可怖真相的同时,提出了一个敏感而尖锐的问题:当一个人被家庭和故乡抛弃,当他的身份认同被他者不断打碎,面对身份的漂移和缺失,他该从何处寻找自我认同。
胡明华. 《法国当代女作家玛丽·恩迪耶访谈》. 外国文学动态. 2006(6):32-35.
拉康. 《拉康选集》. 褚孝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刘成富. 《玛丽·恩迪耶的非洲情结》. 外国文学动态. 2010(2):11-14.
石婷. 《浅析身份的缺失与认同——读简·里斯的〈藻海无边〉》. 鸭绿江. 2014年第11期.
王德峰. 《女性身份的迷惘与建构——读玛丽·恩迪亚耶的〈三个折不断的女人〉》. 兰州文理学院学报. 2014年第30卷第4期.
王茜. 《拉康:镜像、语符与自我认同》. 河北学刊. 2003年6月刊.
游晓航. 《〈三个女强人〉中的女性形象与身份意识》. 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 2015(12):28-34.
詹俊峰. 《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文化身份研究》.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2年第20卷第1期.
Argand Catherine. ed. 《 Marie NDiaye 》.Lire, 1 avril 2001. http://www.lexpress.fr/culture/livre/marie-ndiaye_804357.html.
Crom Nathalie.ed. 《 Marie NDiaye : “Je ne veux plus que la magie soit une ficelle” 》.Télérama, 15 février 2013. http://www.telerama.fr/livre/marie-ndiaye-je-ne-veux-plus-que-la-magie-soit-une-ficelle-litteraire,46107.php.
NDiaye Marie.RosieCarpe. Paris :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2001.
Raya Aurélie.ed. 《 Marie NDiaye, l’exilée volontaire 》,ParisMatch17 septembre 2009. http://www.parismatch.com/Culture/Livres/marie-ndiaye-trois-femmes-puissantes-142711.
L’abandondansleromanRosieCarpedeMarieNDiaye
Résumé : Lauréate du prix Femina en 2001 pourRosieCarpe, Marie NDiaye est un des grands noms du monde des lettres français. Abandonnée par son père sénégalais qui partit peu de temps après sa naissance, elle fait de l’abandon un de ses thèmes préférés.partir d’une analyse d’inspiration thématique, nous cherchonsprésenter notre interprétation sur la crise d’identité provoquée par l’abandon chez les personnages deRosieCarpe.
Motsclés: Marie NDiaye ;RosieCarpe; abandon ; identité
(作者信息:李诺,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2013级学生)
附:原文节译
I106
A
1002-1434(2017)01-003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