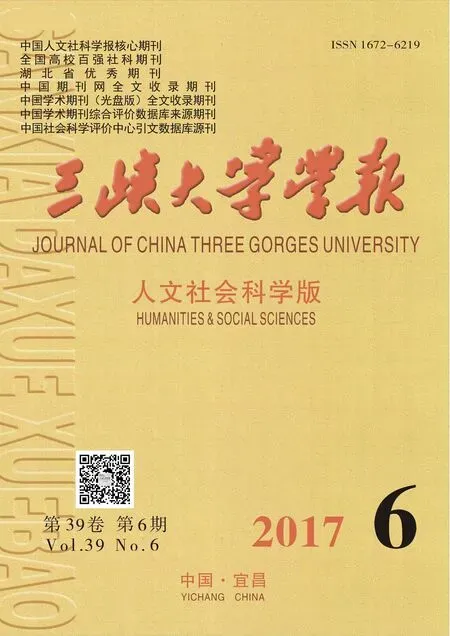英语世界唐代小说翻译的非文学取向
何文静
(三峡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英语世界唐代小说翻译的非文学取向
何文静
(三峡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通过对英语世界的中国传统小说翻译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唐代小说的翻译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非文学需求和取向,即典型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建构需求。由于对华关系和政策的发展和变化,英语世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关于中国的知识建构需求也不一样,其唐代小说翻译也反映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早期阶段,即对华认知的转轨时期,其认知需求的矛盾性决定了其在唐代小说翻译中表现出的俯视和仰慕共有的复杂态度;中期阶段,出于全面、深入认识中国的需要,唐代小说译介成为英语世界走近唐代和中国的重要途径之一;后期阶段,英语世界从蓬勃发展的当代中国身上发现了昔日“盛世唐朝”的影子,试图从唐代小说中找到中国复兴和发展的规律,满足其为意识形态服务的迫切需求。
英语世界; 唐代小说; 翻译; 需求
纵观英语世界的中国传统文学翻译历史,可以发现传统小说深受青睐。历代传教士、外交官和汉学家都将小说翻译视为进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门径”和他们了解中国社会风貌、人情习俗和历史文化的有效工具[1]。
通过对英语世界的中国传统小说翻译活动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尽管相较于宋元小说和明清小说而言,唐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开始得比较晚,但英语世界对唐代小说的重视程度不容忽视。其中最值得关注之处即在于来自英语世界的历代译者翻译唐代小说的动机不完全在于文学交流,很大程度上表现出非文学取向,即以这些小说文本作为正史的重要佐证,通过翻译唐代小说达到认识中国及其民族,从而建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的目的。
英语世界的唐代小说英译经过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在各个历史阶段中,英语世界的对华关系和政策存在差异,因而其关于中国的知识建构需求也不一样,因此,在各个历史阶段中,他们的唐代小说翻译也反映出不同价值取向。
一、早期:俯视与仰慕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是英语世界唐代小说翻译的早期阶段。由于脱胎于历史悠久的传教士“汉学”,此时的西方汉学很大程度上仍热衷于对中西宗教文化进行比较。这一时期,英语世界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著作中以唐代小说为研究素材的现象就非常集中和突出。“辨识中国神话的概貌、分析特定的神话传说以及古代习俗或典籍里的神话内含,是这时相对集中的研究课题。”[2]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通过战争“降服”了他们长期钦慕的东方帝国,侵略战争的胜利让他们产生极大的政治上的优越感,西方世界对眼前现实中的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同时,当时西方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头脑中仍然对这个古老民族及其古老文化充满神秘感,“对中国和中国文明的理想化和神秘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即便是进入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后,西方世界对位于遥远东方的中国的形象进行的理想化建构从来就没有停止过[3]。
“西方对中国感兴趣的另一个高潮则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普遍感到的沮丧和绝望为背景。这种时刻,人们最需要通过‘他性’,创造一个‘非我’来发泄不满和寄托希望。”[4]富于创见的作家、学者和翻译家总是要将视野投向于自己已知领域之外的异域,去寻找精神的“世外桃源”,或者一套符合其精神建构需求的价值,甚至仅仅是一个附会的基础。这种情况在英语世界的早期唐代小说翻译中也有很典型的体现:同样的唐代小说素材,不同的汉学家通过翻译来观察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是完全不同的,有的采用俯视的立场,有的则采用仰慕的态度。
荷兰汉学家高延的《中国宗教体系》选译了大量唐代小说作为素材研究中国古代宗教中的灵魂和祖先崇拜的思想和观念,大量征引以神仙、鬼魂、妖魅、怪异等志怪题材的唐代小说作为论证依据,高氏认为此类小说中隐藏着丰富的、有趣的“民族志和历史信息”。唐代小说于他而言简直就是一座“富矿”[5]。大致统计发现,高延的这部作品中第四至第六卷中一共引用和翻译了近160篇唐代小说,全为志怪题材小说。高氏认为,所有这些小说都显示了某种惊人一致的性质。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唐代的中国宗教观念相对于“(今天的宗教观念)找不到丝毫变化和进步”,“这一点就印证了我们的说法:(现在的)中国大体上还是她以前的那副模样。”他认为这一结论是建立在大量包括唐代小说在内的中国古代小说的占有基础上的:“我们所选取的(中国古代的小说)材料显示,中国现在盛行的思想和风俗习惯早(在文本创作的唐代时期)就存在了。”高氏阐明他的动机,“本书通过大量实例证实”:“中国的文明(从古至今)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中国的很多事情都已经发展了,但是(本质上)什么都没有改变。”很显然,在高氏决定从大量中国古代小说中选取唐代志怪小说等特定的一部分作为论证依据来支撑自己对中国宗教的认识和定位的[5],就已经为读者预设了这种结论。
《中国宗教体系》一类的译著本质上是对18世纪以来已经很盛行的关于中国的印象和评价的一种印证:18世纪以来,工业革命给欧洲带来了飞速发展,西方人发现历史的向前发展而不是传统认识中的周而复始的规律,带着这种眼光看待昔日的“神秘东方之国”——中国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东方的中国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明,有着高尚的道德和臻于完善的治国之道,却长期停滞不前,近千年来几乎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6]22;直至20世纪初期,由于科技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不断强大的西方需要一个站在“发展”和“进步”对立面的“停滞”和“落后”的他者作为衬托自己、否定对方的对象,中国正是他们需要的可以用来颠覆的想象。这种关于中国的知识“让扩张时代的英国人感到自豪、自信和种族优越”[6]23。可以说,无论高延的结论是否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也不管其论证方式在宏观层次上是否具有合理性,其研究的动机和目的与意识形态因素之间的关联是无法排除的。
相比之下,同时期米德的《中国古代鬼怪故事》就更多地体现了译者对中国文化的理性看法和认同。米氏选择的主要是唐代小说,在行文中经常用西方的文学作品作为突出这些小说中蕴含的价值的参照系,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态度不是一般意义的同情;从某种意义上理解,是一种带着仰慕的眼光在欣赏包括唐代小说在内的中国古代小说中蕴含的中国文化特质。米氏在译作前言中指出,自己并未将展示的重心放在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的不太好的一面[7],通过这些故事可以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这个勤奋、有才华、长期遭受苦难的民族”,她有着同样值得尊重的文化传统[7],希望英语世界的读者能从中读出蕴含在这些小说中的东方文明和智慧,最终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反思当时针对中国的那些狭隘的、偏颇的、不科学的观念,从而纠正西方长期以来对中国文明的误解和偏见:西方学者每每面对他们不能理解的事物的时候,很多人对中国人会产生误判,他们认为中国人与其他民族的人并无太大差别;他们认定地中海为人类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在他们评价东亚文明的时候,就将其视为异类,对之极尽贬抑之能事——仅仅因为其发源地不是地中海地区;仅仅因为东亚人的观念与西方人界定的人性的定义不吻合而已[7]388。在该书的结语部分展示了译者翻译包括唐代小说在内的中国传统小说的动机,即向西方读者展示小说作品中蕴含的哲理,希望引起西方读者的自我文化反省,因为这些作品某种程度上蕴含着中国古人认识和理解身外世界的哲理性思考[7]388。译者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深邃的一面去衬托西方人对世界的认识中表现出的“目光短浅”,指出欧洲中心主义者怀着很强的文化优越感而睥睨东方古老文明时表现出的无知和浅薄[8]。
早期阶段英语世界的中国传统小说译著中选择了大量唐代小说作为素材。从背景和动机来看,这些译著都是当时西方世界建构关于中国的知识系统所需,反映和代表了20世纪初期的西方对中国的矛盾态度。
二、中期:“发现”中国
20世纪30年代开始,英语世界的学术研究开始将关注的视野投向中国。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多方面的激发因素和发生基础。当时,“二战”刚结束,英、美等国家开始注重对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在政府资助不断加大投入、注重汉学专业人才培养和中英文化交流逐步加强的背景下,英、美汉学得以迅速发展,英美等国政府和财团在意识形态、外交政策等多方面利益的驱动下,不断加大对国内汉学的支持和资助,使得英语世界的汉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加强了对中国的学术研究,其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仍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英、美国家为发展汉学而制定的政策确切地反映出英语世界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更大需求,迫切需要进行关于中国的知识建构。这一点,大量基于唐代小说的文化研究中的相关信息和内容足以印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民俗学的关注视野投向民俗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中国。比如,首次将唐代小说中的“灰姑娘”故事——《叶限》介绍到西方世界的翟孟生在《中国民俗学三讲》①中指出,在中国,“人们对民间风俗一直保持着普遍的浓厚兴趣”,中国民俗在中国文化的形成中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这是这一时期的西方民俗学家对中国民俗的发现,他们对于中国这方面材料的丰富性是感到惊讶的:“而搜集中国民俗学的人们……要么被中国的大放异彩的民俗资料弄得眼花缭乱,要么被复杂繁多的民俗资料所困扰”,“中国的这些材料多得俯拾即是,他们存在于官修的史书中……存在于口头传说、故事、诗歌、小说、戏剧中……始终是中国民众生活中的一股生机勃勃的内容”[9]22。对于中国民俗研究在西方世界认识中国的问题上的重要性,他谈到:
中国民俗可能包含着从远古、甚至是史前时期保存下来的一些遗留物,并且只有在尽可能地把全部有关的资料搜集起来以后,我们才能答复一些令人头疼的问题,特别是有关中华民族与现在正引起巨大变动的西方民族的关系史,以及其他种种问题。[9]25
显然可见,即便是早期的西方民俗学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也是以认识和了解中国、为中西民族关系协调提供策略和信息参考为目的的。自此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半个多世纪,英语世界以唐代小说为素材的中国文化研究逐步深入,从最初的民俗研究领域,逐步发展到宗教文化、社会文化和历史等领域,对中国唐代文化的研究越来越广泛和深入。
专注于中国唐代文化研究的美国汉学家薛爱华以唐代小说作为重要素材创作了《唐代的外来文明》、《朱雀》、《神女》等一系列研究唐代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著作。这些著作都将唐代小说作为史料,借助唐代小说对唐代文化进行考察(包括地理、物产、习俗、风土、对外交流、历史、文学、制度、社会结构、科技、天文、哲学等诸多层面),形成了对唐代外来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文明发展史等的系统性知识建构。薛氏以唐代小说为素材进行唐代文化研究,没有顾忌其中的夸张、想象和虚构的成分,他们的目的不在于这些“史料”的真实与否,而是“着眼于史料记载背后所反映的思想观念,以及从这种思想观念中所投射出的当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模式”[10],从文学记载的唐人对日常生活琐事的微妙而又隐蔽的反映和态度中去发现宏观的历史特征。
上世纪80年代,部分西方汉学家在中国文化研究方面的探索已经触及比较深刻的层次和问题。英国汉学家杜桥德结合中国古典文学去研究中国的宗教、神话、民俗和历史,在实证研究中发掘中国古代社会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等方面的深层信息,从而实现对中国深层文化结构的解析。他的很多研究都是围绕唐代小说展开的,包括《〈李娃传〉:研究与评述》和一部分唐代论文②,在对10多个唐代小说经典篇目的考证、类比和解读中探查到唐代宗教文化与文学的彼此映照和互动的历史信息,从中发现宗教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的呈现形态。
在这一阶段,华裔学者的参与客观上所起的作用也是帮助西方世界“发现”中国,如刘若愚的《中华之侠》中翻译的九则唐代英雄豪杰小说是对唐代社会的一个特定侧面——“江湖”的展示,对唐代的社会现实、政治阶层、道德追求等文化层面进行了深刻的呈现。其它著作,如张心沧的《中国文学:志怪小说卷》等对唐代文学的研究属于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特定方面,对西方“发现”中国也起着客观上的推动作用。
发生在20世纪早期至90年代初期间的上述唐代小说翻译活动仍然只是西方世界建构关于中国的知识系统过程中的一个不断“发现”唐代文化的产物。
三、后期:当代中国的“盛唐”影子
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英语世界以文化研究为目的的唐代小说翻译,无论是翻译规模的猛然扩大,还是研究内容的陡然拓展,都显示出西方世界建构关于中国的知识的急迫性。
上个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此时西方意识到: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不可能了解和认识当代中国的。要了解和认识中国,应该“以史为鉴”来预测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未来表现的重要性[11]。希望“从古老的中华帝国的历史中寻找线索来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进行预判”[12],对研究了解中国人的民族根性,了解中国在历史盛衰的浪潮中如何追求发展和进步。在西方汉学家眼中,盛唐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知识等诸多方面卓然超群。原因在于西方世界发现中国的崛起和复兴之路与唐王朝的兴起以及发展历程有很大的相似性,“这种局面,让人想到其与二十一世纪初呈现出的世界秩序存在某种相似的地方”,借用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W.塔奇曼的一句话足以说明两者之间的联系——“八世纪就是今天的一面镜子”③。他们将当代的中国与盛世唐朝时期的中华帝国联系起来,因为他们认为时下的中国与昔日的强盛帝国的崛起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从唐代帝国这面遥远的镜子中,他们窥见了当代中国的身影。因此,要了解当代中国,就应该从唐代——当代中国的根本——中去寻找;只有通过研究唐代的发展规律,才可以找到认识中国、走近中国、应对中国的办法和途径。
美国汉学家杰尔逊翻译了《冥报记》等作品,他希望结合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创作动机去“发现”宗教志怪小说背后的深层信息——《冥报记》的作者唐临是唐代司法部门官吏,这些小说宣扬天网恢恢、善恶终受报的天律。很显然,唐纳德.杰尔逊旨在通过翻译《冥报记》等唐代宗教志怪小说,从而探究“报应”故事背后隐藏的中国古代司法理念和精神。无独有偶,杜桥德试图通过翻译《广异记》这部志怪小说集,透过戴孚这个唐代小吏的眼睛,去窥视唐代这个复杂的世俗社会的一斑——唐代佛道盛行,鬼神观念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巨大影响。他认为,在对人们关于短暂和永恒思索的解读中,能找到中国中世纪早期人们的信仰和观念转型的轨迹和根本规律[13]。
唐代小说是一只“万花筒”,折射和反映了唐代社会方方面面的社会现实。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西方汉学界爬罗剔抉,从数量庞大的唐代小说中选择出了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一部分篇文集和篇目,对唐代文化的更多方面加以探究和揭示,包括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甚至人们的心理特征和举止行为等。总体上看,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西方汉学界对唐代文化的研究覆盖面更广,因而选择的文本也涉及到更多的主题,反映宗教、阶级、制度、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社会和历史现实的题材得到了广泛和大量采用,因此得到翻译的小说篇目在数量上也大大地增加了。
西方世界将当代中国和曾经的盛世唐朝相互关联起来,西方汉学由此得到发展,在此阶段英语世界对唐代小说的翻译在数量和主题类型的选择等方面也体现出了明显的时代性。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以美国汉学对唐代文化的研究更为突出和集中,这一点也与美国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时更急于全面、深入地建构关于中国的知识系统的事实彼此印证,同时也切合西方汉学,尤其是美国汉学完全出于对自身政治、经济和文化战略利益考虑的文化本质。
四、结语
在操作层面上,英语世界基于唐代小说的翻译来塑造中国形象和建构关于中国的知识,有正负两个方面的取向,正面取向多是通过建构一个理想化、乌托邦式的文化和知识形象来反观自身的政治和道德秩序、利用一个虚构的“他者”形象作为政治和道德榜样来挑战自身的现实秩序,从而达到建立一种新秩序的最终目的。负面取向则是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下,汉学家们带着典型的优越心理去了解和认识传统中国,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上,倾向于那些对西方人而言显得神秘、甚至怪异的素材,希图以此作为西方世界了解东方、认识中国的“窗口”;或者使用西方既有的知识和理论体系作为模式和框架来搜寻翻译的文本,然后藉此衡量和判断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通过这种方式来衬托自身文化的优越性,或者产生跟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价值和形象并不相符的判断,表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见——这也是西方汉学对中国的固有认识和将东方和中国置于与西方完全对立的另一个极端的惯常做法。
总而言之,本着认识中国、剖析中国民族属性的目标,西方汉学家通过将唐代小说译入英语世界来建构他们关于中国唐代的知识体系——这是英语世界的古代中国认知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英语文化语境中的唐代中国这个“他者”形象的建构,不是完全、绝对地根据唐代中国本身的客观形态来反映的,而是英语文化体系以及西方文化体系根据自身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欲求来建构的。因此,整个英语世界的唐代小说翻译史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形态,也正是目标语文化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欲求在不断变化和调整的缘故。
注释:
① 美国著名民俗学家翟孟生1932年在北平华语学校三篇演讲稿合辑而成的著作,原书名为ThreeLecturesonChineseFolklore。国内学者钟敬文将书名译为《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
② 主要有“Three fables of paradise lost”、“Tang tales and Tang cults: some cases from the eighth century”、“The tale of Liu I and its analogues”、“A question of classification in Tang narrative: the story of Ding Yue”、“Tang Tales and Tang Cults”等。
③ 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 1912-1989) 1978年出版《遥远的镜子:14世纪的欧洲厄运》(A Distant Mirror. The Calamitous 14th Century)一书,认为14世纪的欧洲是20世纪的写照。
[1] Thwing, E. W. 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Far East[J]. Chinese Fiction, 1897(6): 759.
[2] 周发祥.西方的中国神话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1999(3).
[3] 顾明栋.汉学主义:中国知识生产中的认识论意识形态[J].文学评论,2010(4).
[4] 乐黛云.“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序史景迁《北大讲演录》[M]//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廖世奇,彭小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8.
[5] De Groot, J J M. “Introduction” to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Its Ancient Forms, Evolution, History and Present Aspect, Manners, Customs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Connected Therewith, Vol. 4[M]. Leiden: E. J. Brill, 1901.
[6] 姜智芹.镜像后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M].北京:中华书局,2008:22.
[7] G Willogughby-Meade. “Preface” to Chinese Ghouls and Goblins[M]. London: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Publishers, 1928: x.
[8] E D Edwards. Book Review: Chinese Ghouls and Goblins by G. Willoughby-Meade[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5, 2 (June), 1929: 409-410.
[9] 詹姆森.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M].田小杭,阎 萍,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22.
[10] 谢 孚(薛爱华)著.唐代的外来文明[M].吴玉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
[11] Christian Caryl. Unveiling Hidden China[J].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Dec. 9, 2010.
[12] William A. Callahan. Sino-Speak: Chinese Excep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1, No.1(Spring), 2012: 33-35.
[13] Glen Dudbridge. 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Lay Society in T’ang China:A Reading of Tai Fu’s ‘Kuang-i Chi’[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017-10-10
何文静,男,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翻译学博士。
10.13393/j.cnki.1672-6219.2017.06.011
H 315.9
A
1672-6219(2017)06-0050-04
[责任编辑:杨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