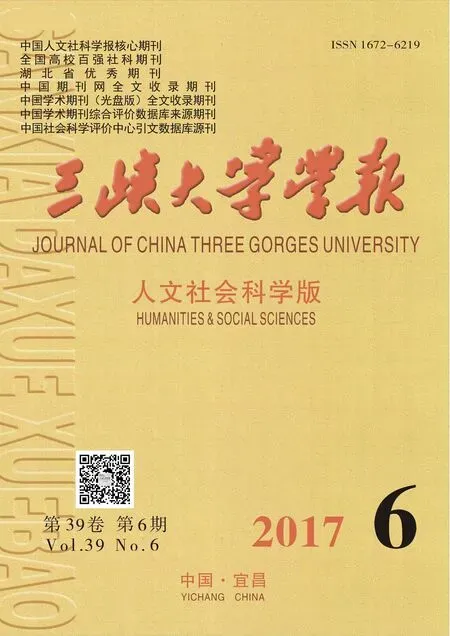对宋蒙战争中钓鱼城陷落之反思
邓 晓, 何 瑛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重庆 401331)
对宋蒙战争中钓鱼城陷落之反思
邓 晓, 何 瑛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重庆 401331)
公元1279年初合州钓鱼城即将失陷,并面临残酷的屠城结局。王立率众向元朝西川王府投降,虽然守城主将未能替大宋王朝及其皇帝尽忠,但城中十余万军民却因此幸免于难。无论蒙哥遗嘱是否真实,元朝代宋乃为历史的大势所趋;当时钓鱼城已陷绝境,十余万军民命在旦夕并非危言耸听;评说守将降元,是非功过当以大局为基线;弃宋降元,是对立双方审时度势的妥协结果。钓鱼城守将不因其最后的放弃而有损英雄形象,反倒凸显出封建社会为民尽责难得的人性。
钓鱼城; 宋蒙战争; 王立; 元朝代宋
宋蒙战争中,钓鱼城之战彪炳史册。在长江流域的抗蒙山城防御体系中,钓鱼城历时36年艰苦卓绝的坚守英豪辈出。其击毙蒙哥,折断“上帝之鞭”延续宋祚的壮举,数百年来尤为中外史家称道。而对该城1279年于南宋行将灭亡,且已三年未得朝廷音信之际,守将王立率众降元之举,长期争辩不休,文章拟就此略作讨论。
一、探究蒙哥遗嘱与元朝代宋
讨论这两个问题,一是为了探究“屠城”之说的可能性,二是涉及元王朝统治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定位。
首先,探讨蒙哥有无毁城遗嘱、确认蒙哥因何而亡,直接关系到钓鱼城的生死存亡。但史书对蒙哥的死因有多种说法[1]38-39,因而毁城遗诏的存在与否便成了疑案。
南宋开庆元年(1259)秋,蒙哥汗率军4万(号称10万)兵临钓鱼城下,向这个面积仅2.5平方公里山城发动猛烈进攻。孰料钓鱼城地势险要,加之宋将王坚指挥得法,军民同仇敌忾,蒙军屡攻屡败,其主将汪德成“几为飞石所中,遂感疾”[2]3653,不久殒命。同年8月11日,蒙哥于钓鱼城外马鞍山被炮锋所伤退走北温泉,6天后伤重而亡,万历《合州志》载,其临终前曾发布遗诏:“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讳之后,若克此城,当赭城剖赤,而尽诛之。”[3]10但令人疑惑的是,对此遗诏《元史》《新元史》和《史集》中均无记载,且皆表示蒙哥之死是因病重。
这三部书的权威性是明显的。《元史》经过洪武元年(1368)、洪武三年(1370)两次编修,主编宋濂、王祎,前后历时331天,记述了从蒙古族兴起到元朝建立及至灭亡的历史;合前后二书共成210卷,资料主要以徐达从元大都缴获的元十三朝实录和元代修的典章制度史《经世大典》为基础。《新元史》由清末民初的柯劭忞所修,它以明代《元史》为底本,又参考了《元经世大典》残本、《元典章》、元碑拓本、法国的《多桑蒙古史》、波斯人拉施特《蒙古全史》等资料,历时三十年于1920年成书,全书共257卷,1922年刊行。《史集》(亦《集史》)由波斯伊儿汗国宰相拉希德丁(Rashidal-Din,1247~1317)奉命主编,成书于1300年~1310年间,是以蒙古帝国史为核心的世界各民族史,且以14世纪前蒙古族材料最为丰富,完成了第一部、第二部和《阿拉伯、犹太、蒙古、拂郎、中华五民族世系谱》。
因正史不载,遂有学者置疑,蒙哥因城下受伤而亡或为野史遗闻。探究之,《元史》为系统记载元朝兴亡的纪传体断代史,于明朝初年成书,若真有蒙哥怀恨遗诏,编史的汉人理当着重记述;倘若《元史》因失之仓促而编修过简,忽略了蒙哥命丧钓鱼城的“重要”细节,则历30年之功的《新元史》却又为何只字不提?又,伊儿汗国(1256~1335),由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所建,权势如日中天,倘蒙哥真有毁城遗诏,当为王室珍藏,并于《史集》中有所反映,著书者是断不敢故意抹去“遗诏”的。那么,蒙哥因钓鱼城而伤亡并留下毁城“遗诏”的可能性确实值得认真考量,但这不是本文讨论的终极目的。
虽然从正史中,蒙哥之死似与钓鱼城无直接关联,但其在率军围攻钓鱼城的过程中死亡则是不争之事。无论蒙哥是否直接死于钓鱼城的炮矢,出师未捷身先死,就他来说对钓鱼城定是抱有极大遗恨的;同时蒙古军队对钓鱼城久攻不下,数员大将殒命、士兵伤亡惨重,按照蒙古军队“凡攻城邑,敌以矢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2]3459的旧制,屠城可能性应是极大的。因此,无论蒙哥有没有遗诏,顽强抗蒙36年的钓鱼城如果不出意外最终都难免屠城的命运。
其次,有元一代97年(1271~1368)的历史被纳入中华民族的历史大系,是我们讨论元朝代宋与钓鱼城降元的前提,对其民族大融合的性质应是不疑的。
基于此,一方面我们对中国历史上民族间的矛盾与战争,宏观地视为民族大家庭中的“兄弟阋墙”现象无可厚非;另一方面即便兄弟之间的矛盾争斗,分辨是非曲直仍有必要。元朝代宋虽为历史大势所趋,但蒙古贵族主导的野蛮劫掠和民族压迫的非正义性与南宋军民抗蒙斗争的正义性质亦必须确认。否则我们就难以公正、客观地对待钓鱼城的抗蒙军民。
探讨中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就当时的蒙古统治者而言。由于“当时的女真社会和蒙古社会处于刚进入封建社会的阶段,存留着奴隶社会的很多东西,它们的统治者、贵族仍有着极大的掠夺性”[4]。因此,从成吉思汗到蒙哥汗均把对他民族的野蛮劫掠视为首要任务。但是自忽必烈称帝后,其将对华夏的长治久安视为己任,大量依靠和使用汉族士人,颁发了“毋得妄行杀掠,父母妻孥家口,毋致分散”的“兴师征江南谕行省官军诏”(《元文类》卷九),及“无辜之民,初无预焉,将士毋得妄加杀掠。有去逆效顺,别立奇功者,验等第迁赏”[2]155-156等系列诏令。该自视为华夏之主(而非过客),依靠汉族士大夫(而非打击对象),视华夏为己土(而非游击对象),视华夏之民为子民(而非赶尽杀绝)的做法,已经明确了其自觉融入华夏民族的态度。
其二,就当时的南宋政局而言。虽然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尽管已经苟延残喘,但仍然安于享乐,其任人唯亲、疏于边防、鱼肉百姓的作为,已致使政权腐败、天怒人怨,政权行将就木;而与此同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5]的家天下思维,经程朱理学的强化业已深入人心。大敌当前,家国一体的意识盖过了内在矛盾,南宋军民保家、卫国与忠君思想互为表里,从而使“忠君”即“爱国”的集体认知,以随君主蹈海殉节的典型行为体现,这便在客观上较大地影响了后人对“元朝代宋”和“钓鱼城投降”的评价。
其三,就民族矛盾而言。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挑起的。”[6]由于蒙古贵族的野心,兄弟民族间的矛盾不幸在此时以惨烈战争的形式出现,它给汉民族带来了巨大的伤亡与灾难,也由此界定了南宋军民抗蒙斗争反侵略、反掠夺的正义性质,他们的英雄事迹亦因此可歌可泣。但是,错综复杂的矛盾又使我们在评价这场战争时,容易出现以偏概全或一概而论的盲点。对此我们赞同以下观点,“我们肯定元朝的历史地位,并不等于肯定元朝统治阶级所采取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政策”。“但是,我们肯定文天祥等南宋将领的抗元斗争,并不等于肯定他忠于南宋王朝的封建忠君思想,更不等于否定元朝的统一”[7]。
从对蒙哥遗嘱与元朝代宋两个问题的讨论,我们认识到蒙古军队屠城的可能性及钓鱼城军民弃宋降元的改朝换代性质;关注到抗蒙战争的正义性及其与民族矛盾、“君国一体”封建思想相互交织的复杂性。
二、试析蒙宋战局与钓鱼城困境
1259年的战争,靠钓鱼城对蒙哥致命一击的偶然机遇,南宋朝廷赢得了20年喘息之机,但却继续着它的腐败;而当忽必烈率大军卷土重来时,很快南宋半壁江山分崩离析,并将钓鱼城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先看蒙宋战局。1259年蒙哥命亡,急于回草原争夺汗位的忽必烈,接受了南宋的求和“似道乘机遣使约和阴许岁币兵解而去”[8]卷三,南宋君臣弹冠相庆,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1271年“是岁鞑靼国建国号曰大元”,但权臣贾似道仍不以为意,他任听“门客朝士称功颂徳,颂说太平夸咸淳为元佑,尊似道曰周公,谀言溢耳不复加意边事”[8]卷四。事实上,忽必烈在结束了阿不里哥内乱后,便考虑再次伐宋,1267年他采纳了南宋降将刘整“先攻襄阳,撤其扦蔽”[2]3786的建议,将进攻重点由川蜀战场改为襄樊。从1268年到1273年,蒙军先后攻下樊城、逼降襄阳,进而直下江陵。由于长江天险尽失,之后不到一年宋京西南路的一府八州军,就有七个州军失陷。
1271年11月忽必烈称帝,按照中国传统建国号“元”,是年为至正八年(其独掌大权第八年)。元军直逼南宋首都临安(杭州),德祐二年(1276)宋朝廷求和不成,谢太皇太后抱着5岁的小皇帝赵显(恭宗)投降,并下旨放弃抵抗。
同年,逃至福州的赵昰(端宗,7岁)被拥登基重组朝廷,改元“景炎”;其弟赵昺被封为卫王,景炎二年(1277),福州沦陷,小朝廷经泉州至广东。端宗在乘舟逃亡雷州途中翻船落水染病,不久亡故。1278年7岁的卫王登基,年号祥兴,几经转折逃至广东冈州的崖山(今新会)。不久,文天祥战败被缚,南宋陆上的抗元主力覆灭;次年二月,元兵十余万(一说三十万),战船数百艘攻溃宋军,左相陆秀夫见突围无望背负八岁的赵昺投海,十万军民随之,宋亡。
再看钓鱼城的困境。如果蒙军由陕西入长江东下,钓鱼城无疑扼守着重要通道。史载“钓鱼山,州东十二里。涪江在其南,嘉陵江径其北,东西南三面皆据江,峭壁悬崖。”[9]2491钓鱼城坐落在钓鱼山上,占地宽广、突兀耸立,相对高度约300米,战略地位重要,因此它倍受宋、蒙双方关注,并成了蒙哥亲征的对象。
宋军对钓鱼城的打造煞费苦心。自彭大雅任四川制置副使始(1239~1240),便命令甘闰初筑钓鱼城。待余玠任四川制置使后,又于1243年遣播州(今遵义)冉琎、冉璞兄弟复筑钓鱼城,并移合州治及兴元都统司于其上。他以钓鱼城为样板,采取“守点不守线,联点而成线”的策略,在四川各险要处修筑二十余座山城,形成了完备的山城防御体系。到1254年,合州守将王坚进一步完善钓鱼城建构,使城分内、外两重,外城有门8道,城内有良田数千亩和丰富水源,城中军民“春则出屯田野,以耕以耘;秋则收粮运薪,以战以守”[3]10,军民结合、耕战结合的钓鱼城被建成可攻可守的军事堡垒。
钓鱼城军民对抗蒙的艰苦卓绝亦是有目共睹的。1258年蒙哥派遣晋国宝至钓鱼城招降,被合州守将王坚所杀。1259年,蒙古大军在钓鱼城下累遭挫败,主将汪德成、大汗蒙哥先后受伤命亡。随后,合州的继任主将马千、张珏、王立也恪尽职守屡败元军。到南宋祥兴二年(1279)王立投降前,钓鱼城军民与蒙军经历大小战斗200余次,成功坚守36年。后人盛赞钓鱼城军民“能坚守力战而效忠节”[3]10。
宋末钓鱼城困境的出现,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其一,忽必烈改变了灭宋方略。此改弦更张之举,不仅使钓鱼城的防御体系能效大减,还断绝了它的后援。首先,自1267年忽必烈转移进攻重点,仅仅2年樊城便告破;而1273年襄阳投降后,南宋朝廷更是在风雨飘摇中度日,基本失去了有效的抵抗,这时的钓鱼城与重庆城一道,失去了南宋朝廷的后援。其次,元军步步为营、各个击破的新策略,也给精心部署的山城防御体系造成极大的破坏。至元四年(1267),元军在嘉陵江东西筑武胜军、母德章两城,“控扼江南,以当钓鱼之冲”[2]115-116。
扼住了合州宋军出路,元军遂得以“拔敌栅垒,掠敌府库,刈其人民,逞志于忠、涪、夔、黔、万施、云安之间,上功朝廷”[10]950。到至元十五年(1278)三月,“西川行枢密院招降西蜀、重庆等处,得府三、州六、军一、监一县二十、栅四十、蛮夷一。”[2]199是年因“王命不通三年”的钓鱼城已陷于孤立无援之境。其二,元军重兵围困,城内遭遇粮食危机。1278年重庆失守,使钓鱼城腹背受敌,而“北兵攻围加急”,元军更加大了进攻的力度;同时,合川又恰逢“两秋被旱,人民易子而食”[3]11的局面。城内军民粮草耗尽,城外蒙古东川大军虎视眈眈,使钓鱼城军民面临双重绝境。
1279年的钓鱼城,守将王立压力重重。一边是磨刀霍霍复仇心切的东川元军,另一边是城内军民粮食匮乏的绝境,他必须在继续进行无望的抵抗或是向元军投降保全民众两者间抉择。继续抗争必致屠城之祸,但自己可能因为宋尽忠而名垂千古,而投降或可为城中军民保存性命,但自己则可能招人唾骂遗臭万年,而对手是否同意受降还远未可知。
十万军民命悬一线,史载他曾与众人讨论:“某等荷国厚恩,当以死相报。然其如数十万生灵何?”[3]11这或许真是他的想法,最后大家决定向元军有条件妥协。在熊耳夫人帮助下他舍近求远,选择了向没有夙怨的元西川枢密院副统帅李德辉投降,与此同时亦有20多名将领以死尽忠,可见对是否投降在城内是有争议的。1279年1月,李氏亲往钓鱼城受降,次月,元军在广东新会取得了崖山之战灭宋的最后胜利,忽必烈终成其统一大业。
在钓鱼城危急关头,王立等人采取了妥协投降而没有血战到底,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此举却有三个还算不坏的结果:其一,成功地避免了蒙哥遗诏与蒙古东川军谋图的血腥复仇;其二,确保了十余万钓鱼城军民的生命安全;三,一定程度保留了民族尊严,实现了“不降旗、不收兵器、不改县志”的有条件投降。但这也正是后人产生评价分歧之处,倘对此采用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方式,或恐有失偏颇。
三、梳理降元是非古今评说
对钓鱼城在抗蒙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历史评价几乎众口一词,但是对钓鱼城最后的结局,后人则褒贬不一。分歧主要在对投降、忠君与爱国的解读上,焦点集中在对王立、李德辉、熊耳夫人的评价,具体体现为对他们应该是肯定仰或是否定。
前人评价多见于史料和碑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收藏于钓鱼城博物馆的四通石碑。其中第一、二两通因与上述三人无关均无异议,对后两通则不尽然,重点体现在对待王立的态度。
其一,奉祀王坚、张珏,明弘治年间合州人王玺上疏孝宗皇帝得允,于弘治七年(1494)建“王张祠”;明正德十二年(1517)佘祟凤知合州,命工伐石,又培修祠宇并立碑记,盛赞张、王二公。(《新建王张二公祠堂记》)
其二,到清初人们扩大了祭祀范围,奉祀余玠、王坚、张珏、冉琎、冉璞,乾隆二十五年(1760)知州王采珍,改祠名为“忠义祠”,祀此五公。(《重建忠义祠记》)
第三,将王立、熊耳夫人及李德辉与前五公合祀,乾隆四十四年(1779)郡守陈大文认为“王、张二公高风劲节因与日月争光,山川共久,而李公德辉,王公立与熊耳夫人实有再造之恩,亦应享民之祀”(《题钓鱼城功德祠》),遂将原“忠义祠”更名为“功德祠”合祀。
第四,对王立、熊耳夫人及李德辉态度前后不同,清光绪五年(1879)署合川事的华国英在《培修贤良祠碑记》中将上述八人同祀,并称王立的妥协“亦有合仁之道焉”,熊耳夫人“以一女子而能画策以救危城”;但两年后,其恢复“忠义祠”名,仅祀余玠、王坚、张珏、冉琎、冉璞五人(《重修钓鱼城忠义词记》),并认同时人朱奂的观点:“立为民降,心终可原,而既以城降元俾宋民得不死,即当以身殉宋,随宋祚以俱终。”[11]14
食宋奉禄非但不以身殉宋,还投降元朝,重点指责王立不忠。其实,对“忠义”原本就有不同解释: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忠义”原就是以民为本的,战国时孟子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2]之谓,“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13]亦是社会的共识,当时的有识之士常奔走于不同国家,“士为知己者死”,他们对“忠义”有着自己的评判标准;直到北宋,司马光的《四言铭》亦曰:“尽心于人曰忠,不欺于己曰信。”[14]14另一方面,又由于长期以来封建帝王对“朕即是国”观念的强化,“忠义”逐渐与“忠君爱国”画上了等号,遂至忠君等同于爱国的意识成为道学家的共识。这也便是王立的作为,虽然也是尽心于人、不欺于己,陈大文对王立等人的评价也遵从了中国人文传统,却仍然难免责难的主要原因。
在今人贬斥王立等人的评价中,尤以解放前郭沫若的观点为代表。抗战时期钓鱼城是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驻地,1942年6月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到此,并题诗“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见护国门外石壁题刻)且在其同年7月的文章《钓鱼城访古》中,斥陈大文的言行为“顺民教育”,慨叹:“可见清朝的顺民教育是怎样的彻底了。”[15]笔者以为,对先生的观点应因时因地而论,他在钓鱼城借题发挥,激励将士抗日乃时势所趋、情之所致,原本无可厚非;但细细想来却又不妥,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与元朝代宋的抗蒙战争似不便相提并论,何况陈大文立碑之时(1779),清王朝已经建立100多年,当时的统治者是否还会以鼓励投降来进行“顺民”教育也值得商榷。
对钓鱼城投降元朝持否定态度的观点,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直到1989年10月“中国钓鱼城南宋后期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重庆合川举行,才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其一,元朝统一中国是大势所趋,结束分裂,是人心所向;其二,南宋晚期权奸当道,政治腐败,灭不足惜;其三,降元是钓鱼城正确归宿,不必指责守将[16]。合川讨论会的意义,不仅在于对钓鱼城南宋后期历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深入,更在于学者的思想开始跳出了僵化的传统思维定式。近年来观点类似的文章也屡见不鲜,但争论仍在继续。
自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钓鱼城的研究取得了越来越丰富的成果,这与思想解放、摆脱传统思维定式、注重人文关怀不无相关,表明学术研究的宽容与实事求是的评判态度已经深入人心。
四、钓鱼城妥协应是双向促成
投降与受降本就不是一厢情愿的,它关系到对立的双方。事实上,在南宋末年即便山穷水尽的钓鱼城军民想要投降,其开出的条件,山下的敌军也是不可能答应的,他们已经结怨太深。然而,矛盾的双方最后毕竟在各自让步的前提下达成了共识,握手言和。笔者认为,这与当事者审时度势,所做的双向努力分不开。因此,我们将本节的重点用于对以下主要人物的剖析上。
首先,就钓鱼城方面,需要讨论的包括王立,熊耳夫人及全城军民,其中王立是关键。
王立,张珏之副将,景炎元年(1276)张珏升任四川制置使,镇守重庆,他才独当一面守卫钓鱼城。是年,他“益严守备,兵民相为腹心”,并主动出击“取果州之青居城,复潼、遂州境土,攻铁炉城堡”[3]11,杀死遂州元将熊耳。1278年,他率众死守钓鱼城,虽“危如累卵釜鱼,知其祸在顷刻,然皆协力而无异谋”[3]11,其一贯表现可圈可点。但他最终选择了投降,之前我们绝对看不到苗头。1278年底形势急转直下,钓鱼城孤城困斗、天灾粮尽、屠城危机,使王立面临两难选择:死守,他可以名垂青史,但十余万(或17万众)军民将生命涂炭;妥协,十余万人性命可保,但其本人可能遗臭万年。最终他选择了投降,后经李德辉保荐、忽必烈任命,做了怀远将军并合州安抚使。
对王立的指责,一是投降,二是做了元朝的官。对前者,史书以势不得已、情不得已作了谅解,即便如此也未躲过东川行院“械(王)立于长安狱,将诛之”[2]3930的危险;而对后者,或斥为贪生怕死,或指其贪图荣华富贵。其实王立是不怕死的,他于“咸淳二年,与史炤同奉珏命,以死士五十斧虎相山城西门入,大战城中,遂夺其城。后积战功,累官至都统制”[11]12。而其是否贪图荣华富贵,则应以百姓口碑为据,史载他在元为官期间,曾开仓赈民、禁戢剽掠,以至“王立去世不久,便由合州绅士发起,百姓捐银为其建祠,以称颂他审时度势,以降元拯救一城百姓的义举”[17]。事实上,王立继任元朝地方官,对当地百姓而言至少优于蒙古人,此当不言自明。王立拿了宋的饷银,并没有愧对大宋百姓,因此不必为君殉葬,更不便以其不为宋死相责。
熊耳夫人,李姓,汉人,元朝重臣李德辉同母异父妹妹,曾是元军遂州守将熊耳之妻。遂州被宋军攻破后,她随元将家属被俘,因假称姓王夫妻失散,遂被王立认成了义妹,伴随王母,相待以礼。在王立迫于局势、举棋不定的关键时刻她告知,“今成都总兵李德辉是吾亲兄,若知安抚待我恩礼,必尽心上闻,亲来救此一城人民”[3]11,遂促成王立举城投降的决心。随即,她又做鞋一双(其特色李德辉识得)为证,另附王立修书,遣儒生杨獬带往成都李府。
对熊耳夫人的评价也是泾渭分明的:或谓她蛊惑王立变节,是“元川西所遣女探”[18];或谓其深明大义,既对王立晓以利害,又力促其兄接受投降,从而拯救了一城百姓。前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就熊耳夫人而言,其身份即便钓鱼城被破,她也可轻易解困;而向王立公开与李德辉的关系、直言投降却是要冒杀头风险的,且事实上正因为她在关键时刻的仗义执言,化解了城毁人亡的危机。冯正峦有诗曰:“熊耳夫人奇女子,一封书救全城死。釜底游鱼鱼已生,千秋庙食张王比。”[11]51任逢也作诗感叹人们对熊耳夫人评价的不公:“天地有好生,谁复杀乃止。为何报德人,不说祀熊耳。”[1]130熊耳夫人是“妖妇”还是深明大义的女性,百姓自有公论。
对钓鱼城军民较为公允的评价是:他们的英勇抗战是正义和被迫之举,他们最后的妥协亦是无奈和明智的。首先,为了保家卫国,他们众志成城、上下齐心,大败蒙古军队,客观上起到了延续宋祚、乃至影响国际大局的重要作用;其次,他们顽强地坚持了36年抗蒙岁月,付出了两代人的鲜血和生命,作为大宋子民坚持到了国家存亡的最后,已经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第三,他们孤军作战,在信息全无、粮草断绝的境况下,倘若再继续坚持,结果必然是无谓的牺牲,这应是城中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若非如此仅凭王立一人,要想献城也是不可能的。
其次,就元朝方面,需要讨论的包括李德辉、忽必烈、忙哥刺及东川军,其中,李德辉是关键。
李德辉,其先为安西王相[19],后兼西川行枢密院副使。身为元朝汉臣,他忠实执行统一大计,致力化解民族矛盾,力斥东川屠城主张,坚持对钓鱼城实行招安。早在恭宗赵显投降后,他就遣使游说张珏:“汝之为臣,不亲于宋之子孙,合之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彼子孙已举天下而归我,汝犹偃然负阻穷山,而曰吾忠于所事,不亦惑哉!”[2]3817继后,他又“使谕其将王立如谕珏者,其辞益剀切。”[20]在得知王立有意妥协时,他力劝安西王以大局为重接受其有条件投降;之后,又单舸冒险前往受降,遂使钓鱼城危机得到化解;再后,为保证一方平安,他还向忽必烈举荐王立继续为官合州。
评价李德辉,责之者谓其助纣为虐、诱降钓鱼城,而笔者则看重他顺应大势,于客观上为钓鱼城不致毁灭所做的努力。就当时钓鱼城而言,被东川军团团围困,蒙哥屠城遗诏高悬,东川夙敌复仇呼声甚嚣尘上,灭顶之灾将至。于是,王立因该城军民“与东府有旧怨,惧诛”而舍近求远向成都的西川军投降,因此李德辉的受降之举,实为救钓鱼城军民于水火无疑。而李德辉建议忽必烈授以王立安抚使知合州,在客观上定是有利于当地百姓安定生活的。评价李德辉,笔者更关注以下两条史料:一是他怒斥东川行院阻扰钓鱼城受降:“吾为国活此民,岂计汝嫌怒为哉!”[2]3818二是他去世,“合州安抚使王立,衰绖率吏民拜哭,声震山谷,为发百人护丧。”[2]3819
要忽必烈放过钓鱼城很难,他是蒙哥的亲弟弟,无论有无屠城遗诏,蒙哥因钓鱼城而亡即是他血亲复仇的理由,因此他曾同意东院诛杀王立并屠城的建议。问题是他最终却降旨:“鱼城既降,可赦其罪,诸军毋得擅便杀掠,宜于秋毫无犯。”[3]11并继续任用王立,胸襟狭小者是断难做到这一点的。究其原因,一则他志在得人心进而得天下,二是他对汉文化传统的认同。还在漠南汉地时,他就“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2]57,亦曾因延揽汉族儒士被蒙哥罢官。登基为帝后他继续重用汉人,麾下聚集了如郝经、商挺、杨惟中、廉希宪、姚枢等大批谋士,其十路宣抚司中,儒士占了正副使中的多数[21]。他一改蒙军初期“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22]850的行径,对沦陷区百姓和战区的守城宋将采取了安抚与招安[23]。至元四年(1267)正月,他诏谕沿江诸城“官吏军民有能率众来降者,优加赏擢”[2]114。至元十二年(1275),五月他诏谕参知政事高达曰:“昔我国家出征,所获城邑,即委而去之,未尝置兵戍守,以此连年征伐不息。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虽得其地而无民,其谁与居?今欲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尔熟知其事,宜加勉旃诏令部下。”[2]116由此可见他的雄才大略与深谋远虑。
就钓鱼城问题评价忽必烈,他着眼大局、放弃报复,招安军民、续用王立,表现的是大气与大智慧。事实上,“会国朝以金始亡,将并力于宋。连兵入蜀,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谋出峡以逃生”[24],其人口、税收均落伍于其它行省。忽必烈的作为,有利于当地的政治稳定与经济恢复。他对钓鱼城的网开一面,既有其帝王韬略,也包含了对汉民族及其文化的敬畏,此点却被我们忽略。
忙哥刺,是忽必烈次子“皇太子真金同母弟也”[25]卷76,至元八年十月(1271)被封为安西王。他是忽必烈经营秦蜀的直接代理人,为助其执政忽必烈任命李德辉“以王相怃蜀”[2]3817。从至元八年到至元十七年六月,四川地区的具体军政主要由安西王及其相府负责,其间李德辉任职至头一年的六月。当时四川地方政权与元朝中央政府的关系是:“东院属西院,西院属安西王府,安西王府直属中央,其中西院处在这条轨迹的关节点上,是元朝征蜀治川的最为重要的军事机构。”[26]
安西王对和平解决钓鱼城危机,所起作用有三:一是他积极支持李德辉的招安行为;二是在紧要关头下达“教谕”[4]使东院未能实现诛杀王立的预谋;三是积极上书忽必烈促使其改变诛杀王立的决定,并召见授职[27]。因此,在讨论钓鱼城妥协的问题上,亦是一位重要人物,其所作所为是积极的。
东川军,是钓鱼城的主要对手和宿敌,也是积极主张屠城的力量。其主要由蒙古贵族及汪氏家族领导,他们曾随蒙哥进攻钓鱼城,在长期作战中伤亡惨重,遂与钓鱼城军民结怨甚深。但是他们的强硬恰恰不是钓鱼城选择妥协的根本原因,倘若没有李德辉认真执行忽必烈的方针,没有熊耳夫人的从中搭桥,王立选择的极有可能是鱼死网破的拼死一搏,如果那样的话十余万生命就真的玉殒了。不过,东川军对钓鱼城长期围困的现实,亦是迫使王立思考妥协的重要外在因素之一。
事实表明,钓鱼城的投降既是大势所趋,更是战争双方互相妥协的结果。由于敌对双方都为矛盾的和平解决做出了必要的让步,于是钓鱼城十万众得以生还,忽必烈也兵不血刃地得到了合川,此为明智之举亦是最佳结果。对忽必烈及其次子安西王忙哥刺之于钓鱼城的关系,实有讨论的必要。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四点认识:一是蒙哥屠城遗诏的真实性确值得探讨,但并不妨碍蒙古军队对钓鱼城报复的极大可能性;二是元朝代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其间又凸显了蒙古军队侵略之惨烈及汉民族反压迫斗争的正义;三是评价钓鱼城的投降,应实事求是充分考虑其中的“势”不得已与“情”不得已,幸其结果还算良好;四是钓鱼城的陷落原因错综复杂,实为对立双方理智妥协让步的结果。概言之,南宋末年钓鱼城的妥协,并无损其作为拯救民族危亡的英雄主义形象,同时“他们在1279年所作出的和平的选择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28]。实事求是,在承认民族矛盾、彰显社会正义的同时,也当认清民族融合的大势、尊重生命的价值。
[1] 唐唯目.钓鱼城志[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
[2] 宋 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 合州志(明万历七年刊)[M].合川:四川省合川县图书馆翻印,1978.
[4] 胡昭曦,邹重华.宋蒙(元)关系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8.
[5]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小雅·北山)[M].北京:中华书局,1999:643.
[6] 列宁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31.
[7] 舒振邦:忽必烈与元代的统一[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81(2).
[8] 纪 昀,等.宋季三朝政要[M].雲衢張氏刊本.元至治三年.
[9]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九[M].香港:天下出版社,2000.
[10] 任继愈.姚 燧.便宜副总汪公神道碑[M]//中国传世文选·元文类(卷62).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11] 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卷三十三·名宦二)[M].刻本.民国十一年(1922).
[12] 张以文.四书全译[M]//孟子·尽心(下).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0:541.
[13] 李梦生.左传译注:哀公十一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334.
[14] 增广司马温公全集(续):卷一百[M].四川大学宋集珍本丛刊 川大影印汲古书店影印本.
[15] 钓鱼城访古(附记)[M]//郭沫若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6] 刘道平.钓鱼城与南宋后期历史——中国钓鱼城暨南宋后期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17] 殷 殷.众说纷纭评王立[J].戏剧之家,2005(5).
[18] 郑知乐.“钓鱼城史蹟钞后语”[N].合州日报,1934-06-16.
[19] 李治安.元代四川行省沿革与特征[J].历史教学,2010(4).
[20] 王玉朋.元朝西南地区军事机构的设置及兵力的布置[J].贵州文史丛刊,2011(2).
[21] 赵文坦.忽必烈早期与汉族士人关系考[J].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4).
[22]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3] 淮建利.元初北方儒士历史价值新论——从儒士在元初征战中的作用谈起[J].江汉论坛2006(2).
[24] 虞 集.道园学古录:卷二十:史氏程夫人墓志铭[M].
[25] 屠 寄.蒙兀儿史记[M].上海:世界书局,1962.
[26] 肖建新.西川行院述论[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2(4).
[27] 陈世松,等.宋元关系史[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351.
[28] 王川平.钓鱼城有关碑刻的初步研究[J].四川文物,1990(1).
2017-06-15
邓 晓,男,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何 瑛,女,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10.13393/j.cnki.1672-6219.2017.06.001
K 298.72
A
1672-6219(2017)06-0001-06
[责任编辑:刘自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