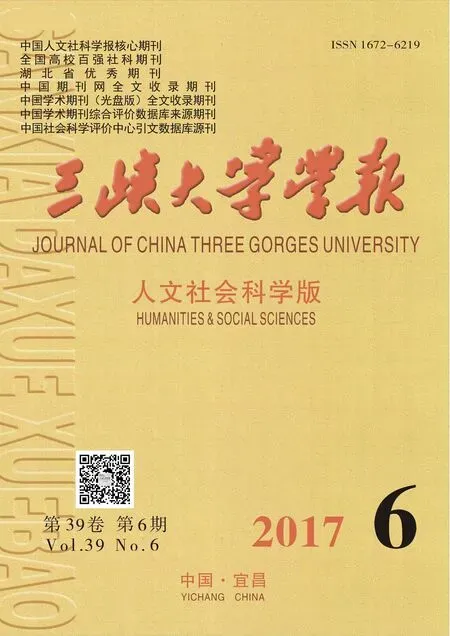《你们闪亮升起的天使》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与颠覆
陈世丹, 尹 宇,2
(1.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 2. 华北电力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2206)
《你们闪亮升起的天使》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与颠覆
陈世丹1, 尹 宇1,2
(1.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 2. 华北电力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2206)
生态后现代主义理论认为,人类并不是自然界的中心,人与其他实在物从本质上讲都是自主的实体,他们以某种与他物相互依赖的关系而存在,存在即是统一的整体。美国著名后现代主义作家威廉·特纳·沃尔曼的小说《你们闪亮升起的天使》通过对工业主义及科学主义的批判颠覆了人类/自然二元论对立,消解了现代性所奉行的人类中心主义,揭露了当下世界存在的各种集权、暴力、阶级和种族压迫的根源,表现了作家本人反对一切歧视,尊重生物主体性的生态后现代意识。
沃尔曼; 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后现代主义
威廉·特纳·沃尔曼 (William Tanner Vollmann)是美国当代杰出的后现代派小说家之一,创作了大量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散文。他的第一部小说《你们闪亮升起的天使》(以下简称《天使》)在1987年一经出版即广受好评,即便沃尔曼在2005年凭借《欧洲中心》一举赢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并在此前后不断有多部优秀作品问世,仍然有一些评论家认为《天使》是沃尔曼最好的小说。评论家迈克尔·海明森(Michael Hemmingson)盛赞《天使》“不像是一般的处女作那样手法生疏,并且完全就是作家的个人自传”,而是“类似于品钦的《V》,菲茨杰拉德的《人间天堂》以及梅勒的《裸者与死者》一样——这些作品都是由不到而立之年的作家创作的长篇巨著,运用了出色的、犹如特技般的语言和形式新颖的结构,标志着作家职业生涯的起航。”[1]17-18海明森和拉里·麦卡弗里(Larry McCaffery)合编的《逐出伊甸园》更是把《天使》一书推到了“宣告后品钦时代到来”[2]的高度。
《天使》的副标题是“一部漫画”,讲述了一场虚拟世界中一群被赋予人格的昆虫和以电力的产生和发展为标志的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国外学者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主要把它作为如同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场》一样的寓言式小说,认为它表现的是权力,尤其是集权的腐化作用。但笔者认为,作为一位后现代社会有学识有良知并且极为敏感的作家,沃尔曼在《天使》中更多的是从生态视角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糅合了科技、历史和地理知识,以夸张讽刺的笔触对社会及环境危机的根源进行了深刻挖掘,彻底否定并颠覆了现代性所奉行的人类中心主义,展现了一位人文主义者对历史和现状的凝重思考和深切的人道关怀。
一、揭露工业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弊端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带动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无可否认人类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我们的社会景观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同时,长期奉行工业主义和盲目信任科学技术一定会带来社会进步使人与自然渐行渐远,甚至到了决然对立的程度。人们视自然为自己的仆从,把自然客体化、低级化,把自然物质仅仅看作可以利用的“资源”而大肆掠夺和无限制的开采。英国著名生态研究者贝特曾在千禧年大声疾呼:“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已经危机四伏。……海洋被过度捕捞,沙漠迅猛扩展,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淡水越来越匮乏。这个星球上的物种正在加速灭绝。……环境已经完全变了,我们必须再次提出那个老问题: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3]2
作为一位具有敏锐生态意识的学者,沃尔曼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思考,他在《天使》中为读者勾勒出一幅后现代的自然和社会景观,并试图为现代社会的环境危机寻找出其社会根源。在小说的开头,一位自称的“作者”(the author)由于寂寞再一次按了电脑终端的复活键,从坟墓里复活了“你们闪亮升起的天使们”——一群由电和数据营造的虚拟人物和昆虫。昆虫们被赋予了人格,在大甲虫(the Great Beetle)的带领下决意对经年累月肆意伤害他们的人类进行报复行动。围绕这场战争,人类分化为反动派和革命派的两极,反动派以怀特先生(Mr.White)成立的丹尼尔协会(the Society of Daniel)为代表。革命派以巴格(Bug)领导的库兹布工会(Kuzbu Union)为代表。怀特先生被塑造为电力的发明者和应用者,一个蓝眼睛的雅利安人,一个现代的爱迪生,代表着技术进步和现代文明。但怀特先生一旦掌握电力立刻意识到它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于是成立了丹尼尔协会。丹尼尔意指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是美国著名的探险家和拓荒者。这个协会的主要功能就是培养电力工程师,怀特先生以皮鞭教育的方式让学员们进行各种电力发明和创造,修建并扩展电站,以便自己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牢牢控制住这个虚拟的大共和国(the Great Republic),之后再进一步累积军事力量,继而最终控制全世界。沃尔曼讽刺地描述,丹尼尔社团的学员们被要求“记住生铁生产的数据,准备成为电力工程师,建立形形色色的跨国上层建筑,例如‘白人的负担’,‘好邻居政策’,‘门户开放’和‘我们的东方遗产’。”[4]33怀特先生一方面开动国家机器对资源进行无节制的开采,另一方面对昆虫们的暴动采取残酷的镇压。他对丹尼尔社团的学员们棍棒相加,对自己的妻女也是非打即骂,以“婊子”称呼她们。他还告诉丹尼尔社团的学员们:“……你们要成为电力工程师,你们要喜欢做电力工程师,谁要是不同意就干掉他。……服从付给你薪水的人,因为对他好的就是对你好的,这,先生们,就是自由。”[4]103很显然,怀特先生对于自由的理解是完全建立在沙文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绝对个人主义之上的,他所要求的是掌握绝对的话语权和所有人、事物的绝对服从,压制一切差异和不同声音,他要建立的社会是一个所谓的安全而洁净的白人社会,他所认为的自由恰恰是他人的不自由。作者在小说开头引用了希特勒的一段话,可以更为深刻地看出怀特先生这一人物所包涵的象征意义——“如果我能把德意志民族的精英送到战争的地狱中却一点都不怜悯他们流下宝贵的德意志血液的话,我当然有权利把一个成百上千万像害虫一样孳生的劣等民族除掉。”[4]1怀特先生疯狂叫嚣要让所有没有电的人都对它渴望得要死,并且进一步掌握军事力量,用战争的手段保证自己的意志在全世界得以执行,把工业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通过战争手段发挥到极致,这使得怀特先生从一名现代文明的启蒙者和开拓者转变为反自然、反社会、集权、暴力、阶级压迫、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代名词,并必然会造成生态殖民主义和全球性生态危机。
美国著名后现代生态批评家查琳·斯普瑞特奈克在对现代性进行总结和批判时界定了科学技术对社会文化的建构作用。“技术既不是一种拖着我们尾随它而走的独立的力量,也不仅仅是一种中立的、非价值的工具的结合。每一种新的技术的目标和设计都反映了我们的文化。”[5]50正是由于科技的塑形作用,电的发明和应用才使《天使》中的世界阶层化。小说中沃尔曼借人物之口评价道:“你看,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相互分离却平等的……只是在后来,当电在我们周围发展壮大的神秘日子里才像野草疯长一样出现了小人物和大人物。”[4]38科技导致了掌握科技者和未掌握者之间的分化和对立,它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成为了帝国主义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精英群体统治普通民众、强势群体控制弱势群体以及人类征服、驾驭自然的工具。“科学怎么也回避不了这样的事实,即它把自己卖给了政治意识形态、军事力量和公司的利益。”[6]102反过来,人类在把科技工具化、对象化的同时也把自身工具化了。就像沃尔曼在小说中暗示的那样,“电”是一个实体,外观是“蓝色球体”,是一种超自然之力,并不依靠于人类存在,相反人类的命运却受到了“蓝色球体”的控制,世界是由它们控制的,即便强大专制的怀特先生也不过是它们统治世界的工具。所有的“天使”最终都要被“蓝色球体”毁于一旦。小说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大乔治(Big George),被描绘成一个身着大靴子,头戴牛仔帽,甩动着鞭子,并时时有蓝色球体围绕的形象,他是一种“纯粹的电的自我意识”[4]111,他不具有任何政治倾向,不帮助任何一派,也没有任何是非标准,他永生不死,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时常以各种人物形象出现在叙述中,甚至经常抢夺“作者”对小说的控制权。小说中有时是“作者”的声音,有时是大乔治的声音,甚至二者的声音同时出现在一句话中。在小说的末尾,“作者”声称想要拯救那些“天使”使他们免于死亡,而大乔治却囚禁了“作者”,并且告知读者巴格会在下一章被捕并执行死刑,所有的“天使们”都将被他杀死。即便是“作者”本人也会自杀,并成为大乔治的“天使”,成为在死亡的终端为大乔治编写程序的工具。可以说,大乔治象征着科技和超自然力。沃尔曼运用超绝的想象力表现了在人类视科技为工具统治自然的过程中与自然相脱离,自身也被工具化、物化,最终走到了自然的对立面。由此,沃尔曼对现代性所信奉的物质主义、工业主义和科学主义等核心观念做出了彻底批判。正如斯普瑞特奈克所说的,“……技术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却引发了新的问题。现代社会不愿意承认那些‘副作用’……在大量辉煌的向自然挑战的科学业绩深处,新苦难的种子就埋藏在其中。”[6]102工业主义与科技主义既没有带来和平,也没有带来自由,更没有带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如何才能消除集权和压迫,并让人类和自然之间处于平等地位?沃尔曼首先在另一个人物巴格身上寄予了希望。
二、取消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
深生态主义理论认为,从启蒙运动以来一直强调的个人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是环境恶化并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深生态主义反对人类/自然的二元对立观念,以一种非二元对立的一元论整体观审视这个世界,认为人类与非人类都有其内在性,而这一内在性与是否能服务于人类没有丝毫关系。人类不能视自然为可供开采和掠夺的客体,而应把自身看做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和谐共生,而非冲突对抗。社会生态学理论家莫里·布克金进一步阐述道:“几乎我们所有的生态问题都是出于深层的社会原因。”(Bookchin)人对自然的统治和控制实际上根源于人类社会中人对人的控制,人类对自然的对象化和客体化根源于人类社会的阶层化和歧视。因此“经济、伦理、文化和性别冲突……是我们当今面临的最为严重的生态混乱的核心。”[7]
《天使》的主人公巴格(Bug)就代表着人类中反二元论、反极权、反暴力、反歧视和压迫的一种势力。他在童年时代身形瘦弱,性格腼腆,对自然有一种天生的领悟力和亲和感,例如他可以知道近200种树木的名字。由于本性害羞懦弱,他经常被同龄人欺侮。对此他逆来顺受,甚至把他们轮番丢到自己脸上的鞋规规矩矩地抛回去以便对方再次朝他扔过来。巴格仅有一次提出了自己的控诉:“为什么你们都恨我?”结果反而遭到更为严酷的对待。夏令营活动期间,巴格的室友托尼被发现是一只假扮作人类的昆虫,在男孩子们轮番虐打下,奄奄一息的托尼向巴格交付了一副神奇的昆虫耳机。出于对同为弱者的同情,巴格接受了这副耳机,从此慢慢走上了与自己的同类截然相反的道路。他与大甲虫(the Great Beatle)——一个比人类更具有美好品质的昆虫世界的首领建立了某种神秘联系,最终毅然决定加入到被人类迫害和欺凌的昆虫群体中来。他带领他的追随者们接受了昆虫们的指示,反抗并破坏怀特先生所营造的充斥着电力和电子产品的世界,切断电路,烧毁保险丝,攻击计算机站、炸毁电站等等,甚至不惜搞暗杀和恐怖行动来使弱者的正义得以伸张,因为他认为自己的革命行为是“为了那些树木”[4]147。很显然,巴格是作者生态观的代言人之一。正如沃尔曼在小说开头部分说到的,“我们不会比一块地毯里的虫子来的更有用。”[4]14在沃尔曼看来,人类社会的林林总总都具有一种原始的生物性,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人与其他动物是浑为一体的,人类并不能自称万物之长。实际上从人类对待其他物种的态度来看,人类是所有物种中最为残忍而无情的——任何其他动物的杀戮没有道德是非标准,只是出于生存本能,而人类仅仅出于玩乐或厌恶情绪就可以随意虐待、残害其他动物。正是这种天性中的暴虐导致了人类对他人、动物和环境的压制和欺凌,这与人类社会中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独裁专制、大国沙文主义等等是一脉相承的,归根结底在于人类的二元论思维对于他者的歧视和边缘化。只要看一下沃尔曼的笔下夏令营的男孩子们是如何虐待托尼就可以看出作者对生态问题的凝重思考:“……他们撑开他(托尼)的眼睛拉出了他的眼珠子,就像螃蟹的眼睛一样连着肉茎。他们发现他盘在剪成平头的假发里的触角,把它们啪地折断。他们把他拖到前窗下日光照射到的位置上去,用放大镜烧灼他的胸部。他们脱掉他的裤子踢打他的生殖器。……小木屋里充满了昆虫肢体被碾碎的味道。”[4]151
沃尔曼在创作《天使》过程中深受奥维德《变形记》的影响,创造了人形的昆虫和部分为昆虫或植物的人,赋予昆虫人格,并且让人可以像昆虫那样进行蜕变。这种奇特的想象力和陌生化的手法迫使读者感受到过去从来没有意识到的人类对自然和其他物种的暴行。在一次访谈中,他谈到:“变形是人类的主要活动之一。我们一直试图在把自己转变为另外的样子,也许永远也转变不了。……从某种方式来说,历史就是对于变形的描述。”[1]87可以说,沃尔曼把人降低至昆虫角度或者把昆虫提高到了人的层面,以独特的视角审视人类对于自然犯下的罪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天使》中处处可见沃尔曼用辛辣的笔触鞭挞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如他借一个人物之口(很可能为怀特先生)以讽刺的语气谈到人类对待树木的态度。“我们用树木做绞刑架、棺材和报纸。……我们当然能把整个森林都做成纤维木板(尽管我们可能希望留下一棵树,一棵世界上最好的树,一棵橡树,也许,一棵法国梧桐,把一个士兵埋在下面,并把它叫做自由树),如果继续一步步执行我们的计划,将大大有助于毁掉所有的绿色,留下像瑞士那样的一块中立地带。”[4]149在作者眼中,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人从自然中走来,最终又回归自然,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沃尔曼试图让读者了解,正是人类自以为是的自由和民主观念造成了生态的失衡,如果想要改变这种观念就必须首先放弃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
耐人寻味的是,在小说的末尾,这场昆虫与人类的战争仅仅刚刚开始,作者并没有详细讲述战争过程,而是独具匠心地在小说的目录部分有所透露——这个目录题为“先验式目录”,为读者提供故事后续发展的标题式梗概。从中我们得知昆虫们和巴格领导的革命派最终并没有取得胜利,革命派的反抗行动也并没有给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改进,因为巴格的暗杀以及恐怖袭击使得他自身也成为了一个集权的代名词,用暴力对抗暴力,用杀戮对抗杀戮并不能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而所有小说中的人物,不论革命派还是反动派,最终面临的都是坟墓,正如“作者”在小说开头告知读者的那样,他们是生来就要分化为两派并相互杀戮至死的。在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彻底解构的同时,沃尔曼对自己的作品也进行了消解:在小说的最末尾,“作者”加上了一段由文字和涂鸦画构成的“作者笔记”:“本书写于——尿,石灰和硫酸盐中,在——饥饿和死亡的——情况下,为所有你们闪亮升起的——硫——磺——天使,住在——巨龙喷火之眼中,联合起来为——繁殖碱液和浓硫酸。为你们的丑行祷告。……”至此,沃尔曼对人类中心论进行了最为彻底的讽刺和消解。那么,在消解了二元对立的世界之后沃尔曼要给读者建构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笔者认为答案在于另外一个并不太起眼的人物凯瑟琳(Catherine)身上。
三、重构一个生态一体化世界
斯普瑞特奈克认为,“不仅所有的存在在结构上通过宇宙联系之链而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所有的存在内在地是由与他人的关系构成的。”“代替将我们自己视作人类社会中与其他孤立原子相冲撞、相结合的社会原子,人被看作是处在一个联系的链条之中的。”[5]52后现代生态批评的核心是人类处于一个生态社会之中,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要运用系统的、生态的、差异的、联系的、动态的、非线性的观点看待宇宙、自然和人类的相互作用,回归生命体的“真实”。人类如果想生存,就必须关爱周围其他人和其他有生命的动物和没有生命的物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一个生态一体化世界,人类也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凯瑟琳这一人物在小说中只出现过几次,对她的勾画也不过是寥寥数笔而已,主要集中在小说开头和结尾部分。但在她身上却凝聚着作者一种全新的生态伦理意识:她外形美丽纤细,心思细腻而敏感,有很强的正义感,但不习惯于接触人,对于“作者”的亲近过了很久才渐渐适应。但是她对周围任何生物和非生物都存在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关爱和尊重,从不伤害任何人和物。在她的眼中,一切事物皆有生命和灵性。她对万物的认识正像“作者”在最后一章中引用了楚克其族萨满的一句话:“一切存在皆有生命。房子的墙壁也有它们自己的声音。”[4]626凯瑟琳甚至给自己最喜欢的毯子起名字,即便破损也从不丢弃,缝补后继续使用,以保证它“仍然是懂得她照料她”的那一条。很显然凯瑟琳是以一种“纯自然”的姿态出现在读者视野中的,有着理解一切,包容一切的特殊能力。在她看来,一切事物都有其内在价值,而不是只有其工具价值。而“作者”对待凯瑟琳的态度更是可以看出沃尔曼本人的自然观。“作者”对凯瑟琳爱护有加,如珠似宝,从不以任何方式惊扰她,与她外出共进晚餐也十分注意不让她被任何灯光照到,以免大乔治可以通过灯光的电力找到并摧毁她。“作者”认为凯瑟琳身上隐藏这一个秘密,如果能够知晓这个秘密“作者”就可以从大乔治手里解救出每一个“天使”。这个秘密是什么?对此可以有多重解读的方式,笔者认为这个秘密就是人类和自然能够和谐共处的真正途径。如果能够解读这个秘密,“天使们”就不会被大乔治用“蓝色球体”一轰而亡,人类不会因为自我意志的过度膨胀和科学主义的负面作用而濒临绝境。但“作者”同时也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凯瑟琳藏起来,不干涉,不接触,避免用任何方式和手段使其脱离现有的状态,而让她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存在。
让自然还原为自然之然,这就是沃尔曼为处于后现代社会的人类解决环境问题所提供的出路。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的先驱奥尔多·利奥波德在被誉为“绿色圣经”的《沙乡年鉴》中指出:“我们蹂躏土地,是因为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属于我们的物品。当我们把土地看成是一个我们隶属于它的共同体时,我们可能就会带着热爱与尊敬来使用它。”[8]英文版序每个人都把自己看做生态整体的一份子,保护自然不再受到人类自身的伤害。无论人类社会怎样发展,都不得以牺牲环境因素为代价。由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过分介入和科技的肆意入侵而导致的环境恶化也必须由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修复和代偿逐步进行,有必要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更为长远的计划和更为缜密的思考。在小说结尾一章“瓶中世界”中,大乔治讲述了一个有关于果蝇的实验报告:把果蝇放入在一个封闭但可流通空气的瓶中,里面放上一块发酵食物以供果蝇食用。果蝇不停地取食、排泄、繁衍后代,并一代代死亡。食物越来越少,后代果蝇以同类的尸体为食,继续取食、排泄、繁衍,直至整个罐子都充满了果蝇的尸体和排泄物,令人见之作呕。最终食物耗尽,所有的果蝇死亡,瓶子被扔进了垃圾箱。这同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掠夺和消耗何其相似!又是多么能令人从迫在眉睫的环境危机中警醒!沃尔曼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致的理解力对后现代社会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指出人类中心主义和对科学技术的错误利用对社会和人类自身造成的危害,并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普遍伦理扩展到了人与其他生物、人与非生物之间的伦理关系,体现了一位后现代小说家的进步生态意识和全新的伦理观念。
[1] Hemmingson, Michael. A Critical Study and Seven Interviews[M].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and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2009.
[2] Mc Caffery, Larry & Hemmingson, Michael eds. Expelled by Eden: A William T. Vollmann Reader[M]. New York: Thunder’s Mouth Press, 2004.
[3] 王 诺. 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 Vollmann, William T, You Bright and Risen Angels[M]. Pennsylvania: The Haddon Craftsmen, Inc., 1987.
[5] 王治河. 斯普瑞特奈克和她的生态后现代主义[J].国外社会科学, 1997(6):49-55.
[6] 查伦·斯普瑞特奈克. 真实之复兴——极度现代的世界中的身体、自然和地方[M].张妮妮,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7] Bookchin, Murray. What is Social Ecology?[EB/OL]. http://dwardmacpitzer.edu/Anarchist_Archives/bookchin/socecol.htm. February 22, 2009.
[8] 利奥波德. 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2017-09-0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多克特罗小说艺术研究”(13BWW038);2016年度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总论”(16XNLG01)。
陈世丹,男,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尹 宇,女,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华北电力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10.13393/j.cnki.1672-6219.2017.06.008
J 712.074
A
1672-6219(2017)06-0034-05
[责任编辑:杨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