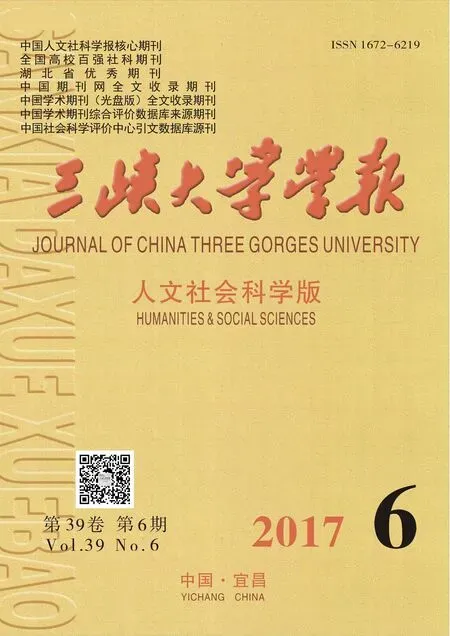西方身体哲学影响下的中国身体研究
章立明
(云南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西方身体哲学影响下的中国身体研究
章立明
(云南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中,身体研究的学科名目下已经衍生出身体哲学、身体历史学、身体社会学、身体人类学以及身体文学等诸多领域。文章以追溯西方哲学史上的身体哲学思想作为切入点,指出其对当代中国身体研究三大类别的影响,认为身体研究方法论上的转变将成为中国身体知识生产的新亮点。
西方哲学; 身体研究; 中国身体知识
“人类有一个显见和突出的现象:他们有身体并且他们是身体”[1]54。作为一门对世界本原问题进行不断追问的学说,哲学自然也少不了对身体的提问与作答。从仇视身体、漠视身体到身体的高调出场,西方身体哲学走过了2000余年的历程。随着西方身体哲学的全球扩散,以身体为视角已开始成为中国当代学术研究的切入点之一。通过梳理中国身体研究的三大领域,我们认为方法论上的变革有望为中国身体研究寻找知识生产的新生长点。
一、西方哲学中的身体:从仇视、漠视到高调出场
在西方哲学中,身体是一种与感觉、感性和欲望等相关联的肉体性存在,其对立面是灵魂、精神与理性等属灵性存在,两者的紧张关系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在柏拉图哲学中,灵魂享有对于身体的巨大优越感;在基督教哲学中,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对立使得人类身体从罪过的场所变成了罪过的原因;在笛卡尔身/心二元的意识哲学中,人类身体一直徘徊在理性的晦暗地带;而斯宾诺沙的“身心合一论”和莱布尼茨的“预定和谐论”则试图用同一性来解决身心的对立问题;在费尔巴哈和尼采等人的不懈努力下,身体对理性的全面抗拒才得以展开,尼采哲学终结了身体与灵魂的二元对立结构;此后在胡塞尔、梅洛-庞蒂、福柯和巴塔耶等人的推动下,身体视角最终成为西方现代学术思想中最醒目的切入点之一。如果以柏拉图、笛卡尔、尼采、梅洛-庞蒂和福柯的身体哲学思想为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西方身体哲学在2000余年中的发展史,它既是一部身体与灵魂紧张与抗拒的张力史,也是一部身体的“翻身解放史”。
1.柏拉图:死亡使灵魂摆脱肉体的束缚而重获自由
在《斐多篇》(公元前399年)一书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宣称:“真正的哲学家一直是在学习死亡,练习死亡,处于追求死亡的状态之中,因为在死亡的过程中,灵魂离开了肉体而独自存在”[2]13。也就是说,柏拉图将他本人对身体的宰制高扬为哲学家的应有姿态。
为什么柏拉图会对身体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敌意呢?在柏拉图看来,灵魂是不朽的、合理的、统一的、稳定的和不可变的,而身体是要死亡的、不合理的、不统一的、多样的、不稳定的和易变的,而且身体还会产生各式各样的麻烦,诸如烦恼、疾病和恐惧等,它们的存在会打扰纯粹的灵魂探究,并使知识的秘密得以继续掩藏起来,因为“带着肉体去探索任何事物,灵魂显然是要上当的”[2]15。正是由于身体及其需求、冲动和激情的存在,妨碍了真理和知识的出场,并最终会导向谬误的结果,因此,柏拉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要接近知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除非万不得已,得尽量不和肉体交往,不沾染肉体的情欲,保持自身的纯洁”[2]17。正是基于以上认知,身体才在柏拉图笔下受到了最严厉地谴责。
在柏拉图看来,身体不仅象征着“高耸的令人恐怖与战栗的围墙”,同时也代表着“温柔的陷阱、罪恶的渊薮和堕落的胎盘”,灵魂与肉体的结合只不过是理念堕落的结果。正因为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摆脱身体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活着就意味着存在一个身体。只有当个人的身体消失了,求真的坦途才能顺利地铺开,这就是苏格拉底之所以死而无憾的真正原因,“我们所期望和决心获得的智慧,只有在我们死后而不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才有可能”[2]17。
虽然柏拉图的灵魂观是从毕达哥拉斯的类似观点中生发而来的,但是由于柏拉图思想体系几乎囊括了西方哲学的所有重要问题,以至于怀德海感慨地说道:“2500年的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一系列的注脚而已”[3]45。因此,身体-灵魂二元说也就挂在柏拉图名下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2.笛卡尔:我思故我在
身体在经历了漫长中世纪对它的钳制与禁锢后,终于迎来了文艺复兴对它的热烈赞美,身体是爱与美的化身,或者就是它们本身。然而好景不长,在理性主义的观念中,是人的意识和心灵而不是身体通向知识之路,活生生的身体仍然受到来自知识的压迫和诘难。也就是说,在19世纪之前,身体就一直在灵魂和意识为它编织的晦暗地带里低吟徘徊。
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表述中,标识“我”存在的是“思”所代表的智慧、理性和真理,而不是作为一种感性、偶然性、不确定性、错觉和虚幻存在的身体。也就是说,在笛卡尔看来,只有心灵的能力才能揭开知识和真理的秘密。他说:“我是一个实体,其整个的本质或本性仅仅是思考,而且为了它的存在,它不需要空间,也不需要任何物质的材料”[4]173,这样一来,“生命及其元现象的基本范畴就被一笔从世界中勾销掉了”[5]67-68。当然,意识哲学的集大成者是黑格尔。在黑格尔看来,“我”是彻底抽象的意识和精神,而身体则是“绝对理念”的产物,只是巨大思辨体系中的物质载体。也就是说,到了意识哲学阶段,人们不怎么在哲学中谴责身体了,但这也意味着身体真正地消失了,消失在心灵对知识的孜孜探索当中。这是因为“以前人们压制身体,是因为身体是个问题;而现在人们忽视身体,是因为身体不再是个问题了”[4]8。
3.尼采:以身体为准绳
如果说,西方古典哲学习惯于通过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来把身体划分为肉体与灵魂的话,那么灵魂无疑是起决定作用的一方,而肉体只不过是灵魂活动中一个令人烦恼的障碍而已。然而到了尼采哲学时代,这种二元对立的身体哲学观已经难以为继了,曾经不可撼动的地基不可思议地出现了松动现象。
其实尼采的身体哲学观完全可以用一个最通俗而简洁的句子来表达,那就是“我的身体与你的身体是不同的”[4]1。在尼采看来,人和人之间最根本的差异不再是从思想、意识和精神的角度来划分的,甚至也不再是从观念、教养和文化的角度来测定的,而是由身体来决定的,因为个人之间最根本的差别其实是铭写在身体表面的。
尼采之所以要选择身体来作为衡量世界的标尺,就因为“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6]37-38。这样一来,身体就完全可以自我做主了,从自身的角度来对世界作出解释、评价和透视。而尼采所说的身体,已经不仅仅是作为灵魂或者意识附庸的“被阉割”的身体,而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肉体。在尼采看来,身体完全可以作为个体存在的唯一方式,除身体之外就别无他物,世界本来就存在于身体的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的永恒运动当中。正是尼采哲学使得身体变成了哲学世界的研究中心,或者说,成了真理领域中对世界作出评价的阐释中心。
4.梅洛-庞蒂:身体是我们能拥有世界的总媒介
在将身体拖出意识哲学深渊的几大理论中,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功不可没。在1945年出版的《知觉现象学》一书中,梅洛-庞蒂以“身体”为题宣称只有从身体的知觉出发,人才能感知世界。他说:“身体是这种奇特的物体,它把自己的各部分当作世界的一般象征来使用,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得以经常接触这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发现这个世界的一种意义”[7]302。
此外,梅洛-庞蒂还发明了“身体图式”一词来消解身体和心灵之间的对立。他说:“我在一种共有中拥有我的整个身体。我通过身体图式得知我的每一条肢体的位置,因为我的全部肢体都包含在身体图式中”[7]135。这样一来,梅洛-庞蒂毫不留情地剥夺了意识看似不可移易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将意识交付给作为整体的身体,而身体则是与情感、意志、语言和处境等相联,它不再只是意识的对象,或者说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诸器官的组合体。也就是说,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才是一种将“身体图式”与“世界图式”合二为一的活生生的整体。
5.福柯:身体是权力摆布的微型模型
把身体视为权力的对象或者目标并不是福柯的首创,但福柯通过《疯癫与文明》(1961)、《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规训与惩罚》(1975)和《性的经验史》(1976)等著述,阐释了国家强权、社会文化以及个人的微观权力是怎样规训、惩罚和宰制身体的,把医学、精神病学、犯罪的惩罚等与身体有关的权力运作机制揭示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规训与惩罚》一书,福柯描述了在现代性过程中,社会力量是如何作用于身体,从直接的、公开的身体惩罚转变为间接的、隐蔽的身体控制与身体规训。
在福柯看来,身体是各种权力争相追逐的目标,因为“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8]27。而在现代社会体系中,身体已成为政治与文化活动的基本领域和主要场所,被政治体制与知识权力安排是个人身体无法回避的选择,因为“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监狱等各种各样的规训手段,完全将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8]193。
从尼采哲学开始,身体终于可以释放出它许久以来被压抑的一面,由被贬损和禁锢的对象一跃而为存在的基础和准绳,特别是随着身体哲学研究的日益深入,身体问题被推进到文化理论、制度安排、社会秩序等各个层面,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和《疯癫与文明》,德勒兹和伽塔里的《反俄狄浦斯》以及巴塔耶的《色情史》等无一不是在书写着身体的快感、欲望、力比多和无意识等,在他们看来,人类的历史不过是身体历史的变奏而已。
二、中国身体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生产的地方性知识
随着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西方的身体哲学已经对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产生显著影响,从而衍生出“身体政治、身体话语、身体消费、身体文化和身体叙事等众多知识领域”[9],其中依据学科分野,大致可以把中国身体研究的地方性知识生产划分为三大类别。
1.寻找哲学典籍中的古代身体研究
加拿大学者安乐哲认为:“在早期中国哲学文献所理解的身体观中,身心是一对两极相关而非二元对立的关系……在古典中国的两极相关性的形而上学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身/心的问题。这不是说中国思想家能调和这种分歧,而是说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10]。
虽然此说对中国古典哲学的身体观颇为嘉许,但是其中确有值得商榷之处。一方面是因为东西方文化对身体一词的理解相去甚远。英文中的身体一词源于古德文中的“桶、瓮和酒桶”等容器,进而身体被比拟为“牢房、寺院与机器”等空间意象;而中国古代的身体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策》当中,指的是人或动物的整个生理组织,有时也特指“躯干”或者“四肢”,如《战国策·楚策四》:“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栗”;而且身体还有“体格”和“体魄”的意思,如《管子·任法》:“利身体,便形躯,养寿命,垂拱而天下治”;此外,身体还有“亲身履行”之意,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何也?”由于中国古代思想的主流是“言心重于言身”,因此“无论是从孟子、荀子等儒家的‘正心’、‘尽心’,还是《庄子》等道家的‘心斋’、‘坐忘’,其工夫的完成,必相应于体貌形躯的变化”[11]11。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涉及身体的哲学大致是“即心言心”或者“即身心互渗以言心”,与西方二元对立的身体哲学是泾渭分明的。
正因为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身体概念具有多重内涵,才使得台港学者们从《孟子》《荀子》《礼记》《道德经》《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甚至是《黄帝内经》中去寻找素材阐发中国古典身体哲学。如黄俊杰在《中国思想史中“身体观”研究的新视野》一文中,把身体分为了作为思维方法的身体、作为精神修养的身体和作为政治权力展现场所的身体[12]三种类型。杨儒宾在《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与身体观》一文中则把先秦儒学身体区分为四个面向:意识的身体、形躯的身体、自然气化的身体和社会文化的身体[13]8-9,阐发了儒家“四体一体的身体观”。杨荣丰在《先秦儒家践礼之身体观》一文中,把先秦儒家思想总结为“寓体于礼,以体行礼,以体扬礼”的身、心、礼一体观[14]125。此外,大陆学者周与沉与张再林等人亦对中国古典身体哲学进行过相应阐述。
2.破解政治意图的近现代身体研究
维特根斯坦认为:“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的最好图画”[15]248,而两岸三地学者也把身体视为破解中国社会政治的密钥之一。港台学者多从宏观视野来讨论古代身体,大陆学者则注重从具体身体部位来探讨近现代社会的政治意义。
1985年,以冯尔康在《史学集刊》上发表《清初的剃发与易衣冠》开风气之先,陈生玺、李喜所、高洪兴等人围绕剃发/缠足发表(出版)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从而印证了冯尔康在《近年大陆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趋势——以明清时期的研究为例》一文把“身体史视为大陆社会史研究的第九大发展趋势”[16]的观点。代表性成果还有王尔敏等人的《断发易服改元——变法论之象征旨趣》、侯杰和胡伟的《剃发、蓄发、剪发——清代辫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杨兴梅的《观念与社会:女子小脚的美丑与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杨巨源的《中国女子裹足小考》、潘洪钢的《汉族妇女缠足习俗的起因新解》、谢凤华等人的《中国妇女缠足放足探析》、樊学庆的《辫服风云:剪发易服与清季社会变革》、姚霏的《近代中国女子剪发运动初探(1903-1927)》、韩晗的《身体政治与政治身体——以义和团运动前后的科学思潮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为中心》、郭春林的《头发的故事——身体的政治》以及陈雁的《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等。其中尤以台湾学者王明珂的《羌族妇女服饰:一个“民族化”过程的例子》和黄金麟的《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成果最具代表性,特别是后者从深刻的民族生存危机和资本主义侵蚀的历史背景中,剖析了“身体的国家化和使命化开展、身体的法权化发展、身体的时间化走向以及身体的空间化展演”[17]7,为大陆的身体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研究经验与启示作用。
3.生产鲜活身体的当代身体研究
如果说前两种身体研究是建立在分析典籍与盘活民间文献上,当代身体研究则是综合了文献研究、人类学田野调查和社会学问卷调查等来进行资料的整理与分析工作,体现了一种鲜明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知识的生产特点。依据现有成果,当代身体研究可大致分为医学身体、消费身体和性别身体等主要类型。
(1)医学身体。出于对人类生命、健康以及社会福祉的强调,医学身体研究涉及了对暴力、传染病以及创伤方面的内容。如邵京在《走出乙肝:从身体的政治到政治的身体》[18]115-138一文中,揭示了一群身染乙肝的网络群体是如何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社会诉求并进而维护自身的权益。汪民安以《SARS危机中的身体政治》为例[19]255-263,将SARS期间的身体危机推到社会前台,尤其是对于那些感染者的身体更是如此。代表性研究成果还包括郑丹丹的《身体的社会形塑与性别象征——对阿文的疾病现象学分析及性别解读》以及张跃宏对中国男性阳萎患者的关注等[20]144。其实,这些涉及不同病理内容的身体研究就是通过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以及社会学的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方法来收集材料进行分析的结果。
(2)消费身体。在消费时代,时尚杂志、美容广告以及影视作品不厌其烦地向大众传递即时消费的理念,身体惟一的真实是欲望与享乐,而通过购买和消费每个人都可以马上拥有这种“真实”。相关的研究包括章立明的《身体消费中的性别本质主义》、邓景衡的《身体、权力、设计策略——塑身、脱脂、美体中心的空间文化剖析》、吴家翔的《解读美体瘦身广告的身体型塑意涵》、黄琼慧的《解读电视广告中的女性意涵——以美体瘦身广告为例》、祝平一的《雕给我一个身体:塑身美容广告中的女性主体》、高玉芳的《新衣裳——论美体工程、女性身体与女性主义》、张锦华的《女为悦己者容?瘦身广告的影响研究——以台北市一般高中职学生为例》、陈儒修的《我美故我在:论美体工程、女性身体与女性主义》以及简忆铃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暴食症女性的身心政治》等。以上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中的广告进行文本解读,以此揭示消费社会如何对身体消费和消费身体大做文章,从而引领与左右个体的消费。
(3)性别身体。由于女性主义理论的大量译介[21]78-108,人们意识到身体在传统社会科学中的缺席,部分地被归因于男性在这个领域长期占有主导地位,于是有关性别身体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如何春蕤的《豪爽女人:女性主义与性解放》和《不同国女人:性別、资本与文化》、王雅各的《女性身体的贸易——台湾/印尼新娘贸易的阶级、族群关系与性別分析》、张小虹和黄素卿的《性別、身体与意识形态——当代西方女性剧场与社会变革》、王蓝莹的《解析性别权力下的身体情欲表述:以报纸妇女信箱为例》、许郁兰的《台湾媳妇仔制度的社会文化分析——身体管训、主体性与性别权力网络》和黄盈盈的《身体·性·性感——对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等。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对于生产劳动领域中的性别身体研究也有著述。代表性成果有蓝佩嘉的《销售的政治——性别化的劳动身体规训,两种化妆品销售劳动体制(百货专柜、传销)的比较研究》一文就展现了百货店化妆品专柜女销售员被剥削的身体、规训的身体、镜像的身体以及沟通的身体等多元层面。潘毅通过深圳一家港资企业的田野调查[22],立体地展示与分析了年轻女工身体的痛楚,特别是女工的尖叫与梦魇展示了打工妹群体在异化劳动与农村生活中抗争的能动性。朱虹探讨了城市餐馆的打工妹是如何努力改变自身形象来建构“像个城市人”的社会适应问题[23]。秦洁则聚焦于对重庆搬运工群体“棒棒”的考察[24],描述了这些“下力”在搬运物件时获得的各种身体技术,而这些身体技术正是农业劳动与都市生存的混合产物。
三、方法论上的变革为中国身体研究寻找新的生长点
无论是梅洛-庞蒂的“挺身世界”说,尼采的“多重身体”说,还是福柯的“被权力铭刻的身体”说,都可以在已有的中国身体研究领域中找到对应。一方面,这是西方身体哲学全球扩散的结果,另一方面,借助中国丰饶的古代典籍、民间文献与社会生活世界,中国身体研究的地方性知识也在丰富与检验着以上身体理论,从而拓展着身体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当然,中国身体研究应该更重视自己的“身体实践”并最终塑造我们自己的“身体知识”,才有望寻找到中国身体研究的新生长点,尤其是要解决谁的身体在言说,谁有权代表身体在言说的方法论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要消解传统学术精英对身体研究对象的控制权和解释权,放弃简单的所谓“客观”和“公正”的姿态,特别是要放弃第三人称叙述方法,让身体的拥有者以叙述人的身份来表达自己的思考和感受,让身体的拥有者平等地参与研究。因此,研究者就需要平衡好自己的评论与研究对象本身声音之间的关系,不再单纯地把研究对象看作是信息的提供者,而是把他(她)们当作共同成果的解释者。
就已有的研究成果来说,最值得一提的是杨念群在《从科学话语到国家的控制——对女子缠足由美变丑历史进程的多元分析》[25]237-296一文中,就对缠足者本身的身体感受和文化意蕴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更多地表达了作为缠足者的女性的声音,并在资料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表现“缠足审美”过程中女性自主参与下的感觉作用。此外,杨扬的《摇晃的灵魂——探访中国最后一个小脚部落》以及李小江等人对于缠足妇女的访谈,都可以看出她们是要让“金莲的拥有者”自身来言说缠足的感受,而不象传统的金莲研究那样,由男性文人来代替女性亲历者发言,因为没有谁会比那些缠足妇女更有发言权。
就具体的方法而言,口述史法或许是最值得一试的,因为它能为身体拥有者提供更多的参与空间和可能性。如神经性厌食症中的患病女性本身是坚决抵制身体康复的,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女孩子想要成为胖乎乎的丑八怪”[26]162,这一现象已引起了学术界和专业人员的关注。近年来港台学者在对患病者身体进行研究方面已取得不俗的成绩,例如让子宫切除者、产妇或者颜面受损者讲述生病及治疗的经验,特别是她们有关身体的主观经验,代表性成果有陈玟秀的《子宫根除妇女在手术后初期重建身体心像的行为》、李淑如的《初产妇于产后初期对身体变化之认知行为》、周怡君的《化妆实践中女性认同的构成》、林怡欣的《医病互动关系中的身体自主权——以女性乳癌病患为例》和高玉凤等的《破碎的脸——一位颜面伤残患者之身体心像变化及心理反应》等。
此外,人类学的民族志法与社会学质性研究中的其他方法均可以为我们提供尽可能多的方法从不同角度切入身体领域的探索。
[1] 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M].马海良,等,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2] 柏拉图.斐多[M].杨 绛,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3] 段德智.死亡哲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
[4] 汪民安.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5] 马克斯·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M].李伯杰,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
[6] 尼 采.权力意志[M].张念东,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7]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8]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9] 章立明.身体研究的人类学转向[J].广西民族研究,2008(2).
[10] 安乐哲.古典中国哲学中身体的意义[J].陈 霞,等,译.世界哲学,2006(5).
[11] 蔡璧名.身体与自然——以《黄帝内经素问》为中心论古代思想传统中的身体观[M].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1995.
[12] 黄俊杰.中国思想史中“身体观”研究的新视野[J].现代哲学,2002(3).
[13] 杨儒宾.儒家身体观[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3.
[14] 杨荣丰.先秦儒家践礼之身体观[D].桃园:体育学院体育研究所,2000.
[15]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汤 潮,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
[16] 冯尔康.近年大陆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趋势——以明清时期的研究为例[J].台北:明代研究通讯,2002(5).
[17] 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8] 邵 京.走出乙肝:从身体的政治到政治的身体[M]//乔 健.异文化与多元媒体.台北:世新大学出版,2009..
[19] 汪民安.SARS危机中的身体政治[M]//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洛阳: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20] 王铭铭.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辑[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21] 苏红军,柏 棣.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2] 潘 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J].开放时代,2005(2).
[23] 朱 虹.身体资本与打工妹的城市适应[J].社会,2008(6).
[24] 秦 洁.“下力”的身体经验:重庆“棒棒”身份意识的形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3).
[25] 杨念群.从科学话语到国家控制——对女子缠足由“美”变“丑”历史进程的多元分析[M]//北京档案馆.北京档案史料.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26] 马丽庄.打开家锁:中国家庭治疗与厌食症的临床研究[M].龙 迪,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017-03-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子课题(10JJD850007)。
章立明,男,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10.13393/j.cnki.1672-6219.2017.06.010
B 152
A
1672-6219(2017)06-0045-05
[责任编辑:赵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