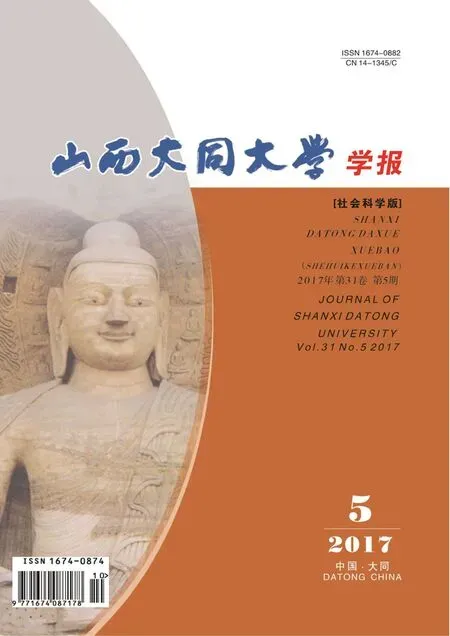黄炎培国魂观初探
郭明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 100029)
黄炎培国魂观初探
郭明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 100029)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于1942年借在成都金陵大学举办讨论之机,系统阐释中华复兴问题,正式提出“恢复国魂”的主张。他从忠、孝、信义、勇侠、气节等方面阐释中国国魂的内涵,认为当时中国国魂已处半丧失状态,强调以国民个体自我提升为主要途径来恢复国魂,力图通过恢复国魂激发国民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实现中华复兴。其国魂观具有战时色彩与实用主义的特点,呈现出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倾向,其中也有纠结于中西文化选择的困惑。
黄炎培;国魂观;中华复兴
“国魂”一词出现于晚清,其使用背景与民族危机加剧有关。早在1899年,梁启超即忧心忡忡地呼吁:“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1]“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亡矣”之类的表达曾常出现于报纸,[2]对于国魂的探讨成为中国人思考民族精神、国民性的先声。[3]“九·一八事变”之后尤其是1938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魂”一词再成热词,其思考延续了清末民初的余脉,其内涵多受三民主义影响,其特点具有战时色彩,其倡导加深对于中华民族精神探索和凝聚,有助于现代中华民族的认同。其中,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国魂”的思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黄炎培早年致力于探索救国方案,他先后尝试过教育救国、立宪救国、社会运动救国等多种努力。1931年秋天,在“九·一八事变”的刺激之下,正在主持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思想发生了较大转变。他重新阐释职业教育目标,将“为社会服务之预备”改为“为民族谋独立与繁荣”,[4](P139)强调救亡图存必须从根本上下手,只有改造国民性、更新民族心理、重振民族精神,进而才能达成中华复兴。1942年,他借在成都金陵大学举办讨论之机,系统阐释中华复兴问题,正式提出“恢复国魂”的主张。
一、“国魂”的内涵
什么是国魂?黄炎培说:所谓国魂,“质言之,即是研究国家所由构成的国人共同心理。”之所以用国魂来概括,“不过使名词单简,易于理会。”[5](P73)他从构成国家的三要素论起,认为除了土地、人民、政府以外,还应思考一国之内土地与人民、人民与人民之关系如何,应追溯一国之政治法律的渊源何在。欲回答这些问题,必先探讨支配一国社会人群的共同心理,这即是“国魂”。了解中国魂,即是要把握中国人的共同心理。
中国的国魂内涵怎样?黄炎培从民族历史上寻找答案。经过调查筛选,他锁定关羽、岳飞、诸葛亮等为中国人普遍钦佩者,认为这三个历史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品格德行即是中国人普遍认同、乐意遵从的精神特质;他还分析了中国传统正史人物传记的记述分类方法,认为“忠义”、“节义”、“刺客”、“游侠”、“贰臣”、“逆臣”等列目标题也能体现中国国魂的内涵。他坚信,应该在中国古来最大多数国民身上去寻觅国魂,[5](P88)因为国魂是长期民族历史积淀的结果,是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的根基,是中国百姓一贯秉持的信念,因而国魂是不会轻易消失的。
黄炎培把中国魂的内涵概括为:“忠”、“孝”、“信义”、“勇侠”、“气节”。简言之,“忠”要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孝”要孝顺父母,“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信义”是与人交往要有诚信,讲义气;“勇侠”是有打抱不平的精神,任侠好勇、锄强扶弱;“气节”是不怕死的精神,“是不得已时对国家民族最大的贡献”。[5](P85)
黄炎培从社会成员个体日常行为入手来思考国魂问题,他曾说,“今日读书目的何在”?“以简言概括之,学做人而已。”[6](P138)做人不仅止步于个人层面,还关系到国家层面。国魂之内涵并非高远艰深的大道理,而体现于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比如,“忠孝”是人生基本,是中国百姓传统准则;“信义”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必要条件,在帮会成员、生意人士之间尤其突出,所谓“信义通商”;“勇侠”以保护善良,扶持正义。“气节”在不得已之时于国家民族贡献最大,所谓杀身成仁,为国捐驱。
黄炎培的国魂思考深受孙中山关于“民族精神”论述的影响。孙中山将“民族精神”阐释为“固有的道德”、“固有的知识”和“固有的能力”三个方面。“固有的道德”首先体现为忠孝,次是仁爱,再次是信义,再次是和平。如要弘扬民族精神,亟需坚守固有道德、发展固有知识、提升固有能力。[7](P242)显然,黄炎培继承孙中山民族“固有的道德”的认识,并应合时代的需求做了取舍与增补。他放弃了“仁爱”、“和平”,增添了“勇侠”、“气节”。他说,平时需讲信义,而非常时期则需要鼓励勇侠、锄强扶弱,所谓“见义不为,无勇也”;一般情形之下有无气节并不为人所关注,而在国破家亡、无可奈何之时,气节就最为重要了。[5](P84)他关于“勇侠”和“气节”的解释,具有鲜明的战时色彩。
中国的国魂现状如何?中国近代关于国魂的思考开始于清末,梁启超等提出培养新民、重铸国魂的主张,认为“中国无魂”,“中国有旧魂无新魂”。黄炎培的判断则要乐观一些,认为中国的国魂处于“半丧失”状态。[5](P84)他很是强调国魂“半丧失”中尚存部分的意义,肯定中国国民共同心理中的积极因素。回溯历史,他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延绵千年生生不息、中国社会内层组织历经数朝而强韧维系、中国近代以来民主革命屡挫屡起终致成功,归其因,不能忽视国魂的意义;直面现实,他认为在欧洲战事一波三折、中国独撑东方大局的背景之下,中国之所以能坚持抗战、不屈不挠,其要因之一是国魂的力量,正是中国军民不惧牺牲贡献、恪守忠孝信义、发扬勇侠气节的结果。因而,他强调中国需要恢复恢复国魂,而非重铸国魂。
今天看来,黄炎培国魂观的思考以个体道德修养入手,其内涵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具有较强的战时色彩与实用主义的面相。无论讲个体做人之原则,还是论国魂之内涵,他很是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中国能否在非常时期团结国民、挽救危亡,其关键是传承与延续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他在国魂阐释中,常常引用中国谚语古训,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泛爱众而亲仁”,“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等。[5](P102-110)在国魂内涵的提炼中,他增添了“勇侠”和“气节”,在国魂内容表达中,他透露着对传统文化复兴中华国魂的乐观自信,这正是时代需要、战时色彩在黄炎培国魂观中的反映,正处于抗战相持阶段的中国人需要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与抗战到底的决心。
二、“国魂”之恢复
如何才能让国民将“忠”、“孝”、“信义”、“勇侠”、“气节”的优良品质真正内化为自身品格呢?黄炎培提出,通过呼吁宣传、身体力行来提高国民觉悟,改造国民心理。
首先,敢死、勤俭是恢复“国魂”的前提条件。
黄炎培分析国家民族的兴衰成败历程、总结民族兴亡周期律,认为国家兴衰逃不出这样一个圈子,[5](P54)即:勤俭敢死→成功→奢惰怕死→失败……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由失败到成功的转折时期,首先需要国人具备敢死与勤俭的品格。他分析说,“中国当前局势,既然相当艰险,究竟有没有生路呢?有……定要从死里求生”,“一个国家要在失败后从死里去求生,第一就只有靠‘不怕死’。”[5](P53)小我终有一死,但“死”并不可怕,“大我”精神不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完结,呼吁国民“认定大我不死”,“小我不足爱惜,只有大我才是宝贵,只要我们有牺牲精神,中华民族的前途一定乐观“。[5](P99-101)针对战时物资紧缺的现实困难,黄炎培强调,勤与俭是身陷国难之国民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呢?埋头苦干,努力工作,就是勤,增加生产,节约消费,就是俭”。[5](P53)他在各地宣讲极力倡导国民“勤俭”之风。此前,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星期讲座中也分析说,现在的国际形势可称之为“大时代”,中国国民应人人节衣缩食,以争取抗战胜利。在特别的历史条件之下,黄炎培从强调“敢死”和“勤俭”来入手,激励国人铸造个体精神品格,进而恢复国魂。
其次,民族团结是恢复“国魂”的现实基础。
黄炎培认为“国魂”的恢复需要国民众志成城,因而“一须有共同的目标;二须有信仰的领袖”。他强调,国人共同的目标就是抗战建国,为达成目标,在教育层面上,通过教育唤醒国民的现代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使国民认识到“苟无国何有民”,国民与国家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国民怀抱爱国热忱,甘愿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在政治层面上,政府要起组织凝聚作用,领袖需“爱民如子”,应不脱离群众,如此达成“君之使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到此地步,国家有难,民众也会一致起来奋斗的。”[8]
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中期,黄炎培一直主张通过“共同信仰的领袖”实现民族团结,由此强调国民政府的合法地位与蒋介石的领袖作用,认为欲“在整个中求生命”,则需要“拥护国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拥护政府,拥护领袖,”[9]以实现人民与政府的合作、中央与地方的合作、各党派之间的合作。他还以“三大合作”为己任,奔波于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以实现各阶层各党派之团结。黄炎培这一主张是民族危机下的产物,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政府认同已经很难区分。不过,到了抗日战争后期,当国民党惘顾民族大义与国家大局、专意于一党之利益的时候,黄炎培逐渐转向了争取民主自由运动。
第三,自我提升是恢复“国魂”的基本途径。
黄炎培认为,恢复“国魂”要从国民个人生活入手,国民的共同心理只能建立于国民个体的人格修养、道德品格之上,主张通过“公共行动”和“个人行动”两方面使国民得到自我提升,进而恢复“国魂”。
在“公共行动”方面,认定“大我”不死;尊崇忠、孝、信义、勇侠、气节;基于爱国、爱家、爱民族而对内团结,基于人道主义、泛爱主义而对外合作;养成守法精神和习惯;厉行军事训练。在“个人行动”方面,平时应讲求: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行必踏实;以“勤”来增加生产,以“俭”行节约物力;厉行身心锻炼,规律生活。战时须强调:精神镇定,设计周密;在政府领导之下,结合通知,严密组织;进则为开始游击战,退则保持力量。[5](P90-91)
这样,在自我提升、恢复国魂中,先要国民树立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进而“尊崇忠孝信义勇侠气节各以身为之倡,”[5](P90)激发国民爱群本性和抗战本能;其次,督促国民养成良好的习惯。通过厉行军事训练与身心锻炼,避免文弱胆怯,培养无所畏惧、坚忍不拔的国民精神;倡导规律生活,以保持身体健康,提高日常工作生活效率;做好抗战准备,训练国民临危不乱之素养与国家忧患意识,以最好状态抵御外敌;再次,呼吁国民在政府领导之下团结一心。通过游击战等形式达成进退自如,消灭牵制敌人,保存我方实力;最后,在实践中提升民族精神,恢复中国国魂。对内在爱国家、爱民族的基础上形成国内团结,对外民扬中华民族包容精神,把“大同”思想发扬至全世界。
三、“国魂”思考之困境与转机
黄炎培在《中华复兴十讲》中系统阐述“国魂”之内涵、恢复“国魂”之重要性与途径。但他的国魂观的构建与实践具有相当大的困难。其困境最主要体现于二:一是在复兴“国魂”中应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二是能否在现实中铸就超越意识形态之上的“国魂”。
面对近代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人最早的文化应对方策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通过一种调和来有限度地接受西方文化。因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进程逐渐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而及于思想文化层面,思考中国文化之得与失、中国国民性之优与劣成为不可回避的历史命题,关于国魂的思考一定程度上回应着这一历史命题。清末民初一代知识人的思考国魂时已不得不面对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继承与吸纳问题。中国封建文化的保守与落后影响中国的发展进步、导致近代改革的延误与失败,但是,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主体性即失去了民族自身的存在理由与前进动力,失去反对殖民反抗压迫的能力。比黄炎培国魂思考稍早一些时候,中国思想界曾有过关于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参与者研究“东西文化差异比较,新旧文化的关系看待和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等问题。[10](P174)“九·一八事变”、民族现实危机将这一思想论争推向高潮。为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抗战必胜信念,研究者积极发掘民族文化,寻找民族精神之所在、民族文化之出路,新儒家随之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思潮之一。
黄炎培并未直接参与文化争论,但他仍无法回避文化选择的难题,他不时表露出无所适从之感,“各种制度、学说、主义,但看他的本身,说不出是非利害的”,一切取决于时间、地点、人物。盲目跟从于某一流派,甚至“可以杀人,可以亡国”。[11](P46)在他看来,无论是“西化”还是“俄化”,势必要依循主体的需要加以适当的取舍。他深知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种“决不屑模仿人家”的流弊,因而提醒国人应摒除成见,“虚心选择吸收人家适合于需要的长处”;可他又担心一意跟风,失去自我,强调“不能盲目的跟人家跑”,否则,“一方面可以说是不会发挥同化力的结果,一方面可以说表现中国在精神上十足的不能自主,没有自信力。”[5](P34-35)说到底,他还是游移于中西之间,少有明确的文化主张。
黄炎培也提出过对西方文化的具体取舍标准:“(一)从远处说来,为吾中华国家民族复兴所需要者;(二)从近处说来,于个人经济上健康上或治事效能上实在有意者”。可以说,他一方面满怀希望地期待着近代显得黯然失色的中国文化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能够重新崛起,与西方文化竞争抗衡。另一方面,他又看到排斥外来文化、乃至于排拒马克思主义文化已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但是如何在他提倡的“国魂”之中,融合新旧、会通中西,他并未有更多的思考、更好的办法。
黄炎培面临的另一困境是能否超越于意识形态之上而复兴“国魂”。黄炎培不愿看到“国破山河在”的局面,他迫切期望国内消除主义之争、党派之异,促使国共两党及其他政治势力、政治派别不计前嫌、团结统一、共御外侮。如果能以一种超阶级、超阶层、超党派的理论以统一全国人心,就可能铸就一种超越于意识形态之上的“国魂”。
黄炎培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论述建构超越阶级的国魂的可能性。他认为,一切生物都是在竞争和进化中求生存,不过,人类有两个异于其他生物的本性——“求生”和“爱群”。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国家间的相互竞争与厮杀,虽也能推动人类的进化但未免残酷,破坏性极大。与西方民性天性好斗、执着于领土扩张不一样,长期处于农业社会、自古重视宗亲人伦的中华民族历来将“泛爱众而亲仁”视为行为的基本准则,如果在国魂恢复中,发掘民族传统,启发劝说民众,国人最终会认识到“群”之和谐的重要性、人与人之间互助互爱的必要性。黄炎培超阶级论国魂的构想中,国魂思想的核心仍是传统的儒家学说,其间,既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精神做激励,也以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现代政治理念相号召;既以忠、孝、信义、勇侠、气节为根本,也规劝国人“要充分发扬人道主义和泛爱主义的精神”。[5](P101)
于是,黄炎培的恢复国魂只能从国民个体入手,只能抛开个人的阶级属性来谈论道德修养、品行人格。如此,其国魂观中较多强调国民义务,少谈个人权利;只讲国民性改造,而不论制度变革;强调全民族团结一心、共赴国难,而忽略阶级对立、党派斗争的现实存在。这样的思考之下,其恢复国魂的方案就具有一定的空想性。现实中既没有超越于阶级之外的个体,也找不到调和阶级冲突的灵丹妙药,国魂观的思考不得不兼顾阶级差异与时代变迁。其实,黄炎培个人也无法摆脱阶级属性的烙印,作为一名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体现着社会中上层群体的心态与要求,比如,不希望变革制度、惧怕社会动荡、不想触动现实社会秩序等等。他只讲国民性改造,不讲制度变革的国魂铸造思路,实质上与国民政府所倡导的三民主义铸造就“民族精神”的思路十分相似。
通过改造国民性进而改造国家、复兴民族的救国思路,几乎绵延于整个中国近现代,随着时代的变动,其侧重略有不同。严复、梁启超倡言的“新民”之说、陈独秀和胡适等主张的国民思想启蒙、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甚至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等都有内在的连续性,但各种新国民、启民智的探索方案的最大不同是,思想启蒙是否与政治运动相携而行,相辅相承。在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面前,在民族危机不断出现的历史背景之下,放弃政治运动与制度变革,单谈专论国民性改造并不适合中国社会历史,也难以取得显著的成效,这也正是黄炎培关于国魂思考的局限所在。
黄炎培为中国设计了民族复兴、国魂恢复的方案,但中国并未给予黄炎培实施这一方案的历史机遇。抗战胜利之后,中国面临着是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建立新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抉择,在两种命运、两条道路的斗争已不可避免之争锋中,黄炎培所主张的超阶级的政见、走“第三条道路”的政党在现实中甚难找到容身空间。1947年值中国民主同盟这一政党组织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黄炎培曾赴南京试图与国民政府沟通无果,民盟最终被迫解散。
黄炎培致力于民族复兴、国魂恢复的构想与实践过程中,曾有过一次延安之行,1945年7月,他与毛泽东就“民族周期律”而展开一场窑洞对谈。与黄炎培立足国民性改造的“国魂”观不同,中国共产党人不止步于发动群众、开启民智,更要通过政治变革实现制度更替,在阶级解放基础上实现个人解放。与黄炎培试图弘扬儒家文化、却处于中西文化无法调和之纠结不同,窑洞对话发生于中共“七大”刚刚召开之际,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毛泽东思想已被视为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还特别以民族、科学、大众来概括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如何处置中西文化、如何解决外来新理论与中国固有国情之差异的问题方面,中国共产党探索着新路径。与黄炎培试图超越意识形态的做法不同,中国共产党毫不讳言其政党的阶级属性,坚持通过人民民主的方式使民众当家作主,从而激发他们热爱中华民族、献身国家建设的热情和信心。
关于延安之行之于“国魂”思考的意义,黄炎培可能在短时间内仍未能做系统的考虑。之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虽说他的情感天平已渐渐倾向于共产党,但他仍坚持自己的中间立场、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重要领导人。随着现实政治情况变化,他对于民族的命运有了更多的思考,最终在1947年底做出新的政治抉择。也许此时,窑洞对谈的思想意义才在黄炎培那里得到更好的发挥、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总的看来,黄炎培关于国魂观的思考延续了清末民初以来关于国民性、民族精神的讨论。他关于国魂内涵的认识中,强调忠、孝、信义、勇侠、气节等因素,强调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意义,肯定传统国民共同心理的积极意义;他判定中国国魂并未完全丧失,恢复国魂具有可能性与必要性,强调敢死、勤俭的前提条件、民族团结的现实基础、国民个体自我提升的基本途径。
在国难当头之机、通过恢复国魂来激发国民牺牲精神,提升民族抗战信心,进而实现中华复兴,黄炎培的国魂观具有战时色彩与实用性的一面。他的国魂恢复途径是从个人道德品格谈国魂恢复铸造,具有超越阶级、超越意识形态的空想倾向,与国民政府所倡导的、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国魂观内涵相一致。从传统文化入手恢复现代国魂,未免于中西文化选择之纠结困惑。1945年的延安之行、窑洞对谈中,黄炎培认识了另外一种重铸国魂国民、激发民族活力的新制度,他终在1947年做出新的政治选择。
[1]梁启超.中国魂安在乎[N].清议报,1899-12-23.
[2]南社啟[N].申报,1910-11-13.
[3]陈永霞.重铸国魂:20世纪初知识人对国魂的新思考[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07):76-80.
[4]陈伟忠.黄炎培诗画传[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5]黄炎培.中华复兴十讲[M].上海:国讯书店,1944.
[6]黄炎培.东南亚之新教育(后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
[7]孙中山.孙中山全集(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黄炎培.如何唤醒起民众[J].国讯,1936(140):683-684.
[9]黄炎培.自白[J],国讯,1942(286):3.
[10]郑大华.民族思想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1]黄炎培.五六镜[M].上海:生活书店,1935.
〔责任编辑 马志强〕
A Look at Huang Yanpei's Conception of Chinese Nation Spirit
GUO Ming-L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Beijing,100029)
Huang Yanpei was one of the well-known patriots and democratic personage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He raised the idea of rebuilding national spirit,When he was holding lectures in University of Nanking and discussing the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during the summer of 1942.He sum up Chinese nation spirit as loyalty,filial piety,credit and righteousness,valiant and chivalry,integrity.He thought Chinese nation spirit had been half-lost and could be rebuilt by citizens'self-improvement.Rebuilding national spirit could be helpful to spur spiritual attitude of citizen and enhance national confidence and realize Chinese nation renew.His conception shows a wartime character and tried to transcend class and ieaology.How to select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was still a confused issues for him.
Huang Yanpei;conception of nation spirit;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K265.5
A
1674-0882(2017)05-0036-05
2017-07-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国地理学与现代中华民族认同研究”(11BZS084)
郭明玲(1987-),女,吉林长春人,硕士,助理编辑,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