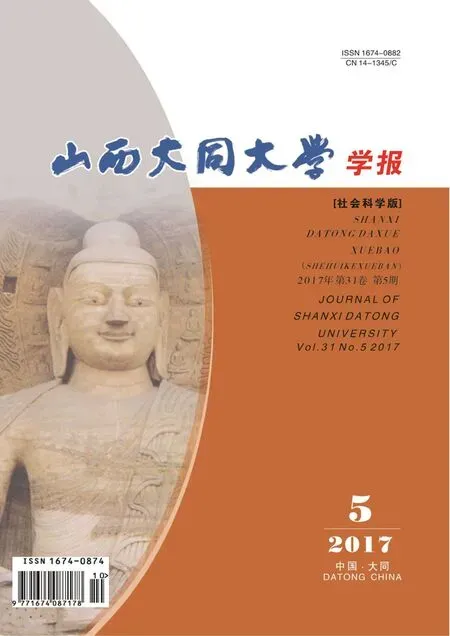茅盾笔下新女性服饰描写的性别想象
段文英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特约专栏·(郭剑卿教授主持)
主持人语:现代中国小说中的服饰书写是新的时代背景和新的文化观念(包括服饰观念)共同的产物,它充满魅惑的力量,刺激了许多作家的文学想象。这一组文章所关注的是茅盾、丁玲和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的服饰书写景观所蕴含的性别想象与现代认同。《茅盾笔下新女性服饰描写的性别想象》中,茅盾所塑造的新女性,摩登的服饰、性感的肉体与大胆开放的生活方式、高超的交际能力和激进的观念行为缺一不可。在茅盾的性别想象中,这些新女性既有着“莎菲”对灵肉释放的欲望,又有着强烈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意愿,由此传递了作家对她们复杂暧昧的现代认同。《丁玲作品中的服饰话语及其女性意识》指出,作为“后五四”女儿,丁玲从中式到西式,从初登文坛时叛逆的女性意识,到追逐革命潮流时对性别的刻意遮蔽,以及革命胜利后对女性意识的若即若离。外在着装堪称丁玲女性性别意识的现实映射,其文本服饰成为女性性别意识的潜在书写。在《新感觉派作家服饰描写中的女性叙事》中,新感觉派印象式的服饰描写一方面是对新的都市文化的描写,一方面也是继五四一代作家之后的新一代作家(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都市新女性的臆想。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的都市摩登女郎,身上服饰极具现代特色,色彩斑斓,款式新潮,或出没于舞厅等娱乐场所,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或成为两性关系中的“引诱者”,玩弄男性于股掌之上,颠覆了五四时期新女性刚刚举步出走时的羞涩迷茫与接受早期启蒙的单纯稚气,也颠覆着30年代前后从事革命的女工、女党员形象。
茅盾笔下新女性服饰描写的性别想象
段文英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茅盾的小说创作,一直坚持“为人生”的文学理念,其早期小说中的新女性,身着性感暴露的服装,大胆而热情地展示着她们妖娆的身体。她们在作品中既是满足男性欲望的对象,又承担着作者所赋予的社会责任与义务,进而寄寓了茅盾对中国现代女性复杂的性别想象。
新女性;服饰;性别想象
茅盾的小说创作,一直坚持文学“为人生”的理念,时代性非常鲜明,每写一部作品都凸显其社会用意,最早的《蚀》三部曲,再现社会革命中青年知识分子的迷茫与挣扎;《子夜》则明示走资本主义道路寻求救国的不可能性。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吴荪甫是拥有雄才大略却生不逢时的资本家形象代表,其承担着中国社会面临的来自国内外的种种矛盾与纠葛,而他的身份及其选择决定其最终必然惨败的结局,从而完成茅盾塑造其的社会意义与价值;方罗兰,是革命队伍中思想不稳定的知识分子典型代表,也是处于社会急剧变革状态下青年犹豫与彷徨心理的真实写照。这种社会价值体现,就茅盾早期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同样有着非常强的时代印记,而她们在作品中除了承担着茅盾所赋予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同时也是满足男性欲望的对象,寄寓了茅盾对中国现代女性的性别想象。
自从性别文化视角兴起以来,关于茅盾小说的性别彰显、女性形象塑造等研究已然不少,代表性的论文有朱德发的《现代知识女性章秋柳论——茅盾小说人物研究》、孙坚的《从革命的“尤物”到革命的女神——以茅盾小说中时代女性形象塑造为例》,徐涵的《茅盾的异性立场——谈茅盾二十年小说中新女性形象的塑造》、曾真《茅盾与谷崎文学的女性审美意识比较》等等,论点都集中在关于茅盾的性别视角,文学的社会意义等方面,但从人物服饰方面探讨茅盾塑造人物形象的甚少。本文拟在前人研究茅盾女性形象塑造的基础上,从女性服饰描写方面分析茅盾对现代女性的性别想象。
一、性感服饰描写下新女性的欲望表达
众所周知,日常生活的服饰是一个人身份、爱好、品味的一种象征,而文学作品中的服饰则是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运用服饰描绘展示人物性格地位、命运转折并推动故事发展是常用的一种创作方法。如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中通过服饰彰显罗敷的美丽动人。《红楼梦》更是运用服饰描写人物性格、地位的经典之作。通过王熙凤、林黛玉、贾宝玉等人的出场服饰,便可对其人物性格、地位等有个大概猜测。在现代文学开端,鲁迅笔下的“旧毡帽”描写出中国清末穷苦农民的真实形象,孔乙己对“长衫”的眷恋显示着中国旧知识分子对社会变革的无所适从。对服装颇有研究的沈从文,《边城》中写的翠翠的裤子是“泛紫的葱绿布”,《长河》中的夭夭“穿了件葱绿布衣”,为造希腊神话小庙而努力的沈从文对“葱绿”色的偏爱,显然也是对自然而健康的,性灵而纯洁的女性的偏爱。国外经典小说运用服装对人物身份、性格的描写与衬托也比比皆是,果戈里通过泼留希金肮脏到已经分不出是什么料子的睡袍,暗示其吝啬卑劣的守财奴形象;契诃夫用一件军大衣描绘出奥楚蔑洛夫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性格特征。有趣的是国外经典名著在描写女性与服饰时,舞会裙装是个重要的标志,《飘》中斯嘉丽为了在舞会上能够引起卫希力的注意,剪了妈妈留下的墨绿天鹅绒窗帘做成了裙子,《小妇人》中的艾米为了吸引劳里自己做了一件白色丝绸舞裙,《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吉蒂小姐为了取悦弗伦斯基花了大量的功夫做了一件玫瑰色裙子等等;此外,白雪公主也是一个为了参加舞会苦于缺少裙装的经典例证。“舞会”只是一个叙述外核,内核是通过“舞会”对人物性格命运的改变以及故事情节的推动,而作为服装的裙子就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茅盾,有着强烈的政治理想,自然会尽可能在创作中体现自己的文学理念以及社会抱负。在力求救国救民的时代,在反传统的年代,茅盾塑造的一系列新女性形象中,服装的反传统尤为突出。
“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一套关于女性的道德规范,由此而形成的封建社会妇女的服饰消费习俗,严格禁止妇女形体上‘性’的显露与挑逗,女性从脖子到脚尖,都要裹得严严实实。”[1]故而,除特殊职业,遵守传统道德的女性服饰是以遮蔽一切女性特征为主要特点,而茅盾早期小说的新女性服装却都性感暴露,大胆而热情地展示着她们凹凸的身体。《创造》中的新女性娴娴,在一个明媚的早晨,“侧着身子,只穿了一件羊毛织的长及膝弯的贴身背心(vest),所以臂和腿都裸浴在晨气中了,珠络纱筛碎了的太阳光落在她的白腿上就像是些跳动的水珠”。[2]《子夜》中的徐曼丽在舞会上“在那平稳光软的弹子台的绿呢上飞快地旋转,她的衣服的下缘,平张开来,像一把伞,她的白嫩的大腿,她的紧裹着臀部的淡红印度绸的亵衣,全都露出来了”。[3]《动摇》中的孙舞阳“短短的绿裙子飘起来,露出一段雪白的腿肉和淡红色短裤的边儿”。[4]
“贴身背心”、“淡红印度绸的亵衣”、“短短的绿裙子”、“淡红色短裤”,茅盾毫不吝啬地描绘着这些现代女性性感的服装,在她们身上想象着与传统不一样的新女性,她们在性感、裸露服装的包装下尽情敞开她们的欲望,这种开放的外包装之下有着非常明显的精神特征,她们既不依恋感伤于过去,也不管未来怎样,快乐在当下是这些现代女性的追求。如《创造》中的娴娴所说“过去的,让它过去,永远不要回顾;未来的,等来了时再说,不要空想;我们只抓住了现在,用我们现在的理想,做我们所应该做的”。[2]她们崇尚享乐,追求刺激,反对克己的清教徒生活,她们有着活跃的生命力,她们要完全掌控着自己。《追求》中的章秋柳说道:“我理应有完全的自主权,对于我的身体;我应该有要如何便如何的自由。”[5]这些女性无论从伦理道德还是欲望诉求,都表现出与传统女性完全不同的风格。对这类女性,茅盾自有批判的一面,但更多的是肯定,尤其在这些新女性对传统的反叛方面给以极大的认可,茅盾也曾多次强调:“如果读者并不觉得她们可爱可同情,那便是作者描写的失败。”[6]
茅盾的现代女性塑造并不是开创性的,晚清女权启蒙质问“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的合理性,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传统社会的一切价值都需要重新认识与界定。在这场运动中,众多仁人志士呼吁“人的解放”,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胡适等在文化革命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两性关系,批判封建社会礼教对女性的戕害,倡导妇女平等人权。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关于“妇女的发现”与“儿童的发现”,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发现”的核心内涵。他们在《新青年》上展开关于女性“贞操”问题专栏讨论,引起众多青年的关注。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明确传统女性节烈的极难、极苦,并指出此事既“不利自他”,又“无益社会国家”,是毫无意义的,是失去了存在的生命与价值的。周作人在《北沟沿通信》中也表达了自己对妇女的看法,他指出对于那些颂扬女人圣母的男人们或者女人们,是极为可恶的。五四的这场启蒙运动虽然是建立在男性启蒙的基础上,但客观上推进了女性启蒙。现代男性要建构自我主体,在两性关系上必然追求性别平等,而两性平等的关键在于女性的独立,虽然这些在五四时期并不能够给以满意的解决,但却积极推动女性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这一点也正使部分新女性成为五四性别文化建构的主体之一。在寻求女性独立的同时,五四性别文化的另一诉求便呼之欲出,那便是性意识的觉醒,尤其是女性意识。在传统社会性别的界定中,女性一直处于被动与接受,起而质问这种性别的不平等,并寻求主动权,最早在秋瑾作品便可见一斑,接着在冯沅君、庐隐、凌叔华等女作家作品中逐渐凸显现代女性对性别不平等的种种质疑与叩问,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发出了女性对欲望的大胆呐喊,理直气壮地表现了女性对正常男女情欲的渴求,颠覆了长久以来的男权文化对女性正常欲望追求的异化。
茅盾小说中的新女性的性意识觉醒呼应着这种思潮,她们拥有着主动性,并操控着男人们的渴求。《动摇》中的方罗兰向孙舞阳表达爱意时,孙舞阳回答道:“我不能爱你……我也是血肉做的人,我也有本能的冲动,有时我也不免——但是这些性欲的冲动,拘束不了我。所以,没有人被我爱过,只是被我玩过。”[2]对性欲如此大胆的直白,让作为男性的方罗兰深感“压瘪”之感,觉得自己是一个“猥琐”并“琐屑的庸人。”娴娴、章秋柳、徐曼丽、刘玉英等这些新女性都有着自我的欲望诉求,对于两性关系也表现出较强的主动性。而茅盾也借助这些新女性完成对女性的现代性想象。另一方面,通过吴老太爷们的过度反应,茅盾又传达出对新女性的复杂态度。最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当属《子夜》开篇:舞会上穿着各色旗袍的现代女性,她们拥有着“高耸的乳峰”和“嫩红的乳头”颤动着在满屋子里飞舞,让吴老太爷这些暮气蔼蔼的僵死之物在“颤动着飞舞着的乳房像乱箭一般”的舞厅里,因过度“震惊”而将一口痰卡在喉咙里结束了自己的时代。
二、新女性服饰描写下的男权意识与性别想象
在茅盾的小说里,营造着一个个穿着性感暴露充满欲望的现代女性,文字后却隐藏着男权意识与性别想象,每一件暴露性感的服装描写最终所指是女性身体本身。我们看到茅盾笔下的新女性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丰满的胸,肥硕的臀,细软的腰与白色的肉,这些充满肉感,并能激起男性欲望的身体,折射出茅盾传承文人病态积习的一面,即对笔下女性的观赏玩味难脱男性欲望窠臼。《动摇》中的孙舞阳有着“娇软的声浪”,在“紫色绸的旗袍”下裹着“圆软的乳峰”,在“淡绿色的衫裙”里包着“肥大的臀部”和“细软的腰肢”,这充满肉欲的身体尽可能地挑逗着男性的观赏欲望,满足着男性的性幻想。在茅盾的小说中类似描写比比皆是,每一位女性都是在性感服装的包裹下裸露着身体的信息,而这种信息无一例外是按照男性欲望需求设置的。《幻灭》中,“慧穿了件紫色绸的单旗袍,这软绸紧裹着她的身体,十二分合适,把全身的圆凸部分都暴露得淋漓尽致。一双清澈流动的眼睛,伏在弯弯的眉毛下面,和微黑的面庞对照,越显得晶莹。小嘴唇包在均整的细白牙外面,象一朵盛开的鲜花。”[6]在如此性感服装包裹下的女性符合男性的观赏需求,符合男权意识下的性别想象。《子夜》中的交际花徐曼丽出场时,身着玄色轻纱的“一九三○年式巴黎夏季新装,”通过巴黎夏季装最新款彰显徐曼丽的贵气,而玄色轻纱,则是黑里带微赤颜色的朦朦胧胧的薄纱材质,尽可能地展现着徐曼丽的性感与风骚,进而能更好地衬托出“皮肤的莹白和嘴唇的鲜红”来,这种描述无不满足着男性观赏的诉求。但是,需要清醒的是这些穿着性感暴露的女性,看似掌握着自我欲望的主动权,本质上并没有脱离对男性的依附,这种通过肉体交易获取的主动权面临的结局是女性最终的堕落。
茅盾小说中对旗袍的钟爱非常明显,这种能够完美体现女性婀娜与风情的服装是新文学男性作家在描写新女性时最喜描写的,它凸显着女人的风韵,承载着男人们的欲望想象。旗袍描写并不是新文学作家的专爱,在这一时期的通俗小说中也有过无数次的显现,无论是大家闺秀还是春楼妓女,都依靠着性感的旗袍在男性的笔墨下展示着自己的无限风情。只是在茅盾的笔下,这些风情女子不再追求琴棋书画、风花雪月,而是在舞厅里疯狂扭动身姿,放荡纵欲,陪在这些女性身边的男性也不再是文人雅士或者穷酸秀才,而是资本家、银行经理、买办官僚等。她们追求享乐,刺激,奢华的生活,有着所谓西洋人的气质,但是她们即使看起来有着主动权利,也仍然逃不脱被看的角色。《追求》中,曹志方借着暗淡的灯光,贪婪地看着章秋柳“两颗樱桃一般的小乳头和肥白的锥形的座儿”。这本身已具备了足够的挑逗欲望的描写,作家在后续又加重了笔墨,让它“随着那身体的转移而轻轻地颤动”。《子夜》中的寡妇刘玉英,“一位西洋美人型的少妇”,她清楚女人生财之道和男人不同,男人利用身外的本钱,而女子则利用身上的本钱,茅盾对这些新女性的每一次服饰笔墨,都指向她们服装下藏着的性感肉体。刘玉英出现在外滩华懋饭店门口的特写:“大风刮起那女子的开叉极高的旗袍下幅,就卷住了那手杖,嗤的一声,旗袍的轻绡上裂了一道缝儿……让风把她的旗袍下幅吹得高高地,露出一双赤裸裸的白腿。”[3]旗袍的作用在于能让这位女子在大街上裸露着“赤裸裸的白腿”。
当然,除了旗袍,其他任何裸露女性身体的服装都可以,包括一块毛巾。在描写刘玉英见李玉亭时,“浑身异香的女人”,“笑吟吟地袅着腰肢”,“一大幅雪白的毛巾披在她身上”,“异常高耸的乳房在毛布里面跳动”。买办赵伯韬之流“伸手就在那女人的丰腴的屁股上拧一把”。茅盾在作品中多次渲染这些女性的性感与肉体,每一位具有现代气质的女子几乎都在不经意间裸露着自己的内衣内裤,暴露出高耸的乳头和赤裸裸的白腿,而站在观赏方的男性几乎都是神魂颠倒,不知所以。这些摩登女性都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们知道男人需要美色,并很好地运用这种魅力征服男性的心智和金钱。
三、小结
在茅盾早期小说中,每一个现代女性都有着性感服饰下包裹的魔鬼身材和高贵服饰衬托下的迷人脸庞,似乎只有具备这种身材与脸蛋的女人才有资格追求新时代,成为一名新女性。相比之下,同时期的女性作家却呈现别样的创作风采,如丁玲,庐隐,梅娘,白薇等女性作家,并没有通过艳丽的服饰与性感的身姿来规范现代女性的特征,她们更多的笔墨是指向女性长久以来被规范的社会角色与在现代化诉求中自我灵与肉的冲突,更多呈现的是这些新女性在面临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孤独绝望与挣扎彷徨,不仅如此,同时期女作家都在尽力回避新女性美貌与性感的描述,她们对欲望的诉求亦是小心翼翼,即使“莎菲”也是如此。由此我们看出,茅盾在塑造新女性时强烈的男性意识,她们需要具备摩登的服饰、性感的肉体与大胆开放的生活方式、高超的交际能力和激进的观念行为,缺一不可。这些参与到社会生活中的时代女性,她们所担当的功能除了对传统的反叛,对自我欲望的肯定,也担当着暴露都市政客们、银行经理们的腐朽与肮脏,堕落且奢靡的生活与空虚无聊的精神状态,折射出茅盾对她们应承担的“为人生”的文学想象,而同时她们又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男权意识下被看和把玩的物品,呈现出茅盾对她们复杂的性别想象。
[1]叶 晖.我国女性服饰流变中的性别权力关系探析[J].阴山学刊,2005(04):100-103.
[2]丁尔纲.茅盾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
[3]茅 盾.子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
[4]茅 盾.动摇[A].茅盾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5]茅 盾.茅盾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6]茅 盾.从牯岭到北京[A].茅盾全集(第19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裴兴荣〕
The Gender Imagination of New Women's Clothes in Mao Dun's Early Novels
DUAN Wen-y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Shanxi Datong University,Datong Shanxi,037009)
Mao Dun's novel creation has always insisted on the literary notion of"to life".The new women in his early novels,dressed in the sexy and exposed clothes,enthusiastically and boldly displayed their enchanting body.In his works,they were objects of satisfying men's lust and bore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moral duty given by Mao Dun,and completing Mao Dun's gender imagination.
new women;dress;gender imagination
I206.6;I207.425
A
1674-0882(2017)05-0001-04
2017-08-2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1YYJA751017)
段文英(1981-),女,山西应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