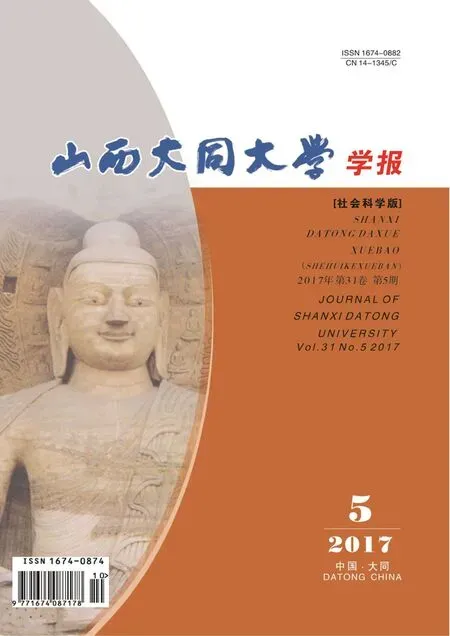新感觉派作家服饰描写中的女性叙事
杨馥菱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新感觉派作家服饰描写中的女性叙事
杨馥菱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中国服饰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服饰的发展演变反映了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的内涵。服饰的修饰装扮功能,体现了不同个体的审美情趣,传达着不同个体的内在韵味,因此文学家把服饰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服饰或多或少成为许多作家关注的审美对象,新感觉派作家也不例外,尤其是对女性服饰的书写,体现了新感觉派男性作家对于女性的审美想象。
新感觉派;服饰描写;女性叙事;性别想象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衣服不仅有遮寒蔽体的作用,人们还把风俗习惯、审美情趣、历史文化、政治等级等沉淀于服饰之中,共同构筑独特的中国服饰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文学家把服饰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通过描写人物繁复斑斓的服饰,刻画人物性格,体现写作主旨,所以我们要重视作家的服饰描写,深入了解作家的写作意图,体察作家的人文关怀。
新感觉派是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前半期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为代表的几位作家受到日本新感觉派影响,以快速的节奏、新奇的感觉描写大都市光怪陆离的生活,表现都市人的畸形心理和生活,是真正观照现代大都市的文学,新感觉派的出现与上海“现代消费文化的成形密切相关的。如果没有上海租界内南京路、霞飞路林立的百货商场、饭店、酒吧、电影院、跳舞厅,没有活动其间的白领阶层,也就没有了新感觉派的表现对象和消费对象”[1]。把上海大都市作为背景,新感觉派塑造了与同期的左翼作家和京派作家完全不一样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极具“现代”特色,是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产物。她们既不像传统女性那样温柔贤惠、顺从持家,自愿成为男人的陪衬,甘愿为男人或家庭付出一切,也不像走向革命道路的女性投身社会活动,模糊自己的性别属性。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的都市摩登女郎,身上服饰极具现代特色,服装色彩斑斓,款式新潮,或出没于舞厅等娱乐场所,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或成为两性关系中的“引诱者”,玩弄男性于股掌之上。这些都颠覆了传统的“男尊女卑”的道德观念,在新感觉派作家笔下,女性终于获得了主体地位。
一、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的服饰描写
刘呐鸥于1930年出版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表现了上海都市洋场中男女的爱情游戏,显示出现代都市社会中人的爱与性分离,以及人们在种种诱惑面前发生的人性扭曲。《风景》写的是一位要去县城与丈夫共度周末的女子与在火车上遇见的陌生男子野合的故事,表现出都市女性开放的性爱心态。男主人公燃青坐火车出差,与一个陌生女子坐在对面,燃青不自觉地“受眼前的实在的场面和人物的引诱”,这位女子“男孩式的短发和那欧化的痕迹显明的短裾的衣衫,谁也知道她是近代都会的所产,然而她那个理智的直线的鼻子和那对敏活而不容易受惊的眼睛却就是都会里也是不易找到的。肢体虽是娇小,但是胸前和腰边处处的丰腻的曲线是会使人想起肌肉的弹力的。若是从那颈部,经过了两边的圆小的肩头,直伸到上臂的两条曲线判断,人们总知道她是刚从德兰的画布上跳出来的。但是最有特长的却是那像一颗小小的,过于成熟而破开了的石榴一样的神经质的嘴唇”。[2](P9)正当燃青猜测女子的身份时,“耳边来了一阵响亮的金属声音”,“你还是对镜子看看自己哪,先生,多么可爱的一幅男性的脸子!”燃青这位久经情场的老手被女子的大胆震惊了,“他虽受不起她的眼光的压迫,但也不就把视线移开。”两人开始聊天,燃青得知女子是已婚身份,要去县里看她的丈夫,燃青从女子的谈吐中觉得“自由和大胆的表现像是她的天性,她像是把几世纪来被压迫在男性底下的女性的年深月久的积愤装在她口里和动作上的”。[2](P10)火车进站时,燃青听见眼前漂亮的旅伴对他说“我若是暂在这儿下车,你要陪我下车吗?”燃青恭敬说道“夫人直线的地请我,我只好直线的从命是了。两人在山野中行走,脱掉高跟鞋的女子,“用着那高价的丝袜踏着草地上爬上丘去……她是放出笼外的小鸟。她跳动着两只好像是只适合于柏油铺道上的行走的奢华的小足向前一步一步强健地爬上去,花边从裾里露出来了。”[2](P13)文中的女子,男孩似的短发、欧化的面容,短衣短裙,是典型的都市摩登女郎的装扮,主动挑逗男性,思想开放,不甘寂寞,与火车上认识的陌生人野合,大胆开放至极。写于早期的《流》带有一定的左翼文学色彩,男主人公吴镜秋是上海一家大纺织厂的职员,被老板看中,成为其13岁女儿的“未婚夫”,住在老板家里。但是吴镜秋却喜欢“未婚妻”的家庭女教师晓瑛,晓瑛面对吴镜秋的爱恋,毫不扭捏地“只挂着的一层薄薄的睡衣露出了……一跳就想钻入床里去”,当他吴镜秋问,“你是不是认真要嫁我了?”晓瑛回答,“有什么嫁不嫁。冷哪,让我睡了吧。”在这里,虽然晓瑛被作家塑造成一个革命者形象,但和以往许多作家笔下的革命者形象大为不同,晓瑛内里是一个摩登女郎,她“是一个近代的男性化的女子”,“发育了的四肢像是母兽的一样地粗大而有弹力”,不仅外表男性化,在与吴镜秋的男女关系上面也是占有主导地位,凌驾于男性之上。在小说《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里,不知姓名的摩登女郎对于爱情的态度更为随性,周旋于多个男人中间,完全把男人玩于股掌之上。
使中国的新感觉派小说发展到较为成熟状态的是穆时英,最早以“普罗作家”的姿态登上文坛,第一部小说集《南北极》描写了底层人们受压迫之后的反抗,表现了阶级压迫和社会贫富分化现象,受到了文坛的广泛关注。在这部小说集里面,作家通过服饰来表现阶层的分化,尤其是女性服饰。《黑旋风》里,“牛奶西施”小玉儿背叛了青梅竹马、穿着黑哗叽大褂子,给自己只能买得起丝袜的恋人汪国勋,投入“脚上都是一式的黑皮鞋”的学生怀抱,而自己也做学生打扮,穿上了高跟鞋。《南北极》中小狮子的青梅竹马的恋人玉姐儿,父亲带着她去城里走了一遭,便对城市生活念念不忘,总说“城里多么好,城里的姑娘小子全穿得花蝴蝶似的,全在学堂里念书会唱洋歌。”之后不愿在农村待着,经常去城里,最终背叛了小狮子,嫁给了城里的表哥。愤怒的小狮子跑到了上海,对于小狮子来说,上海这个世界处处新奇,简直是天堂,尤其是女人也奇怪,“穿着衣服就像没穿,走道儿飞快,只见那寸多高的高跟鞋儿一跺一跺的,好像是一对小白鸽儿在地上踩,怎么也不摔一交。”[3](P159)后来小狮子去刘公馆当保镖,见识了各种女性,公馆小姐“穿着件袍儿不像袍儿,褂儿不像褂儿的绒衣服,上面露着胸脯儿,下面磕膝盖儿,胳膊却藏在紧袖子里,手也藏在白手套里,穿着菲薄的丝袜子,可又连脚背带小腿扎着裹腿似的套子”。[3](P169)拍电影的段小姐也是打扮的妖娆无比,“穿的衣服浑身发银光,水红的高跟儿缎鞋,鞋口上一朵大白绸花儿。”[3](P173)小玉儿和玉姐儿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出于对物质生活和都市生活的向往,她们都背叛了和自己同一阶层的男性,投入上层男子的怀抱,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服饰装扮,向上层社会的女性靠拢,从而想改变自己的阶级属性,小玉儿与男学生相好后马上就“穿着高跟鞋”还有“雪白的真丝袜”;玉姐儿进城之后说话变得“又文气又慢”,“穿得多漂亮,我(小狮子)穿着新竹布大褂站在她面前就像是癞蛤蟆。”可以说,她们从衣服上不光改变了外在形象,更重要的改变了自己的阶级属性,从而摇身一变成为上等人,这当然使原先和她们处于同一阶层的男性受不了,引起他们的愤怒与不甘,甚至复仇。但是面对上流社会的女性,处于底层的男性称她们为“狐媚子”,带有一种既爱又恨的态度。既受不了她们的诱惑,小狮子和电影演员发生了关系;同时又憎恨她们,认为她们属于压迫剥削阶层,所以小狮子最后打了不断向自己挑逗的小姐“两个耳刮子”。从《南北极》这部小说集里,我们可以看出穆时英早期对于都市及都市女性的想象。
之后,穆时英的作品更加关注都市生活,关注生活在都市中的形形色色的人,而都市摩登女郎也成为其作品重要表现的对象,这些身穿各种摩登服饰的都市女郎把男性玩弄于股掌之间,令男性神魂颠倒,处处占在主动地位,这在《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黑牡丹》、《夜》、《某夫人》、《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等作品中尤为突出。如《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中把男人当成消遣品的蓉子,“穿着红绸的长旗袍儿,站在轻风上似的,飘荡着袍角。这脚一上眼就知道是一双跳舞的脚,践在海棠那么可爱的红缎的高跟儿鞋上。把腰肢当作花瓶的瓶颈,从这上面便开着一枝灿烂的牡丹花……一张会说谎的嘴,一双会骗人的眼——贵品哪!”[3](P21)身着艳丽服饰的蓉子热情奔放,大胆肆意,因此“我”第一次瞧见她就觉得是“危险的动物哪”,就在“自己和她之间用意志造了一道高墙”,但是在两人交往过程中,男子始终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患得患失,在与蓉子的男女交锋中失去自己的阵地,心理失衡,被蓉子抛弃,最终还是逃脱不了被当成消遣品的结局。《黑牡丹》里,同样寂寞的“我”,虽然在“奢侈里生活着”,但是如果“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气缸的跑车,埃及烟”,就成为没有灵魂的人,感到无比疲倦,只能在舞场流连,寻求刺激,被爱穿黑色的、同样疲倦的舞娘黑牡丹吸引,黑牡丹“鬓角上有一朵白的康纳馨,高鼻子长脸,大眼珠子,斜眉毛,眉尖躲在康纳馨底下,长睫毛,嘴唇软得发腻,耳朵下挂着两串宝塔形的耳坠子,直垂到肩上”。[3](P80)在舞场中,“那双纤细的黑缎高跟鞋,跟着音符飘动着,那么梦幻地,像是天边的一道彩虹下边飞着的乌鸦似的。”[3](P80)黑色象征着沉郁和寂寞,从黑牡丹喜欢黑色的服装、黑色的高跟鞋来看,黑牡丹这样的摩登女郎逃脱不了寂寞空虚,只能在声色犬马的场所发泄空虚寂寞的灵魂。我们从穆时英对于都市女性的外貌服饰描写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高鼻子长脸、红腻的嘴唇,大而黑的眼珠、弯而长的眉,颜色各异的旗袍和缎鞋是他心目中摩登女郎的标配,她们一方面漂亮、性感、时尚,在男人中间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她们寂寞、孤独、空虚,没有真正的爱情与归宿。
施蛰存在30年代确立了新感觉派的地位,与刘呐鸥和穆时英有不同的创作倾向,他的创作以心理分析著称。施蛰存笔下的一类人物,多是内心承受了巨大的压抑和苦闷,包括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久而久之,这种苦闷逐步演变成为性幻想和性冲动,不管男女都在这种痛苦中苦苦挣扎。其历史题材小说《石秀之恋》取材于《水浒传》中憎女情节的故事,施蛰存对潘巧云的服饰描写的很细致,其服饰颜色艳丽多彩、款式半遮半掩,这种装扮和中国传统女性形象大相径庭,是典型的妓女装扮,正是这种打扮,使得石秀沉湎堕落,施蛰存通过对潘巧云的服饰描写,表达了在男权社会里,一切灾难的缘由归于红颜祸水,将女性妖魔化的男权归于集体无意识。在《魔道》这篇描写现代都市生活的小说里,也反映了同样的主题。在这篇小说中,朋友的妻子陈夫人非常美艳,穿着暴露,袒露手臂,领口很低,“我”同样觉得陈夫人故意穿这样的衣服引诱他,又是一个被妖魔化的女子。在这一类叙事中,女性被异化成为“魔女”,男性对她们既垂涎又害怕,施蛰存通过描写这类女性形象,力图表现“一种都市人的不宁静情绪”,暗示了都市人被压抑的本性,被束缚的精神,折射了都市人潜意识中沉积已久的精神危机。
施蛰存还在《春阳》、《雾》等作品中用精神分析理论,洞察女性在性压抑和性苦闷中的痛苦与彷徨。如《雾》里的主人公素贞小姐爱好修饰,但是非常保守,“九年前,她的表姊从上海来探望她的时候,穿着新流行的旗袍,但她正和她父亲一样地不能接受。她还衷心地批评这种服装是太近于妖异了。直到后来,有几个小康的渔妇都穿着旗袍来做礼拜,她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托人到距离三十余里的城里去买了一块旗袍料来。至于她的发辫,也是在同样的情形中剪了的。所以,从这方面看起来,素贞小姐虽则爱修饰,虽则自以为很有点浪漫性,可是她实际上还和她父亲一样,是个守旧的人物。”[4](P206)当然,她对婚姻也是“固执着一个信仰”,她的梦中情人是古时那种“白面状元郎”——“能做诗,做文章,能说体己的谐话,还能够赏月和饮酒的美男子”,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男性已经很少见了,所以素贞的婚事一直蹉跎到28岁。这一年,她去上海参加表姐的婚宴,在火车上注意其他女性的穿着打扮,“她们穿着的旗袍,袖子短得几乎像一件背心了,袒露着大半支手臂,不觉得害羞吗?况且现在已是秋天,不觉得冷吗?她这样思想着,不禁抚摸着自己的长到手背的衣袖”,[4](P209)体现了她性格方面的中规中矩,在服饰“诱惑”下的微妙波动。
二、服饰叙事背后的男性审美想象
虽然都是新感觉派,但是由于作家各自的人生经历不同,所以作品呈现出不同的审美想象。刘呐鸥出生于望族之家,一直读书,除了谈文艺、办杂志外,就是逛窑子,逛舞厅,过纨绔子弟的生活。由于家庭包办婚姻,所以他对没受过教育的妻子很嫌弃,进而发展到嫌弃女人,从他的日记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女性的矛盾态度:既爱女性的肉体,又嫌恶女性没有智识,用色情的眼光审视女性,把女性看成性象征,因此他只能捕捉到女性的外表,完全无法深入女性的内在世界。在他的文本中,对于女性的描写,重点放在躯体线条、外貌服饰的刻画,少有内在的心理情感的探寻。他塑造的女性形象,有别于中国传统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似的女性,她们有着欧化的面孔,健美的身躯,西化的打扮,是一种带有异域色彩的全新的、现代化的女性形象。同时,她们不再遵守“三从四德”,在感情上大胆随性,及时行乐,享受刺激,忠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在两性关系里占有绝对的主导权。但这些“现代尤物”或“摩登女郎”内心极度空虚,靠在两性关系中寻找刺激,只是靠外表的华丽来支撑内心的空虚,而没有聪慧的头脑和丰富的心灵世界,这也体现出作家本身对女性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及狭隘的女性观。
在穆时英短暂的创作生涯中,从描写底层民众的抗争到描写都市人的堕落,其创作经历了大转变,从小生活优渥的他没有受过什么苦,少年得志,春风得意,但后来家庭遭受巨变,饱尝人情冷暖,虽然因为写作风光一时,但内心还是遭受了极大的刺激,所以在他后期作品,不论男女虽然身处灯红酒绿、热闹非凡的现代化大都市,但是空虚孤独、冷漠寂寞却在他们心中烙下深刻的印痕,最后只剩一片虚无。但正是因为这种经历,穆时英才给我们带来上海都市的别样想象,获得“中国新感觉派圣手”的称号。
施蛰存出生于书香之家,平稳向上的生活使他没有经历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深厚的古典文学的影响,使他一直保持平静顺和、多愁善感的心态。其创作以心理分析著称,与刘呐鸥和穆时英有不同的创作倾向。施蛰存生活在上海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接触的都市女性比较多,但其对上海的生活有不适应的一面:“上海是个坏地方,人与人都用了一种不信任的思想交际着!”所以与刘呐鸥和穆时英相比,他融入都市生活不彻底,隐隐有排斥的态度,对都市的疏离,再加上深厚的古典文化素养,使得他能更好观察都市女性和传统女性的差异,更好地把握各类女性的内心世界,超越了性别立场的局限性,较之新感觉派其他作家更贴近现实。
三、结语
通过对新感觉派代表作家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作品中女性服饰描写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出“服饰情结”是作家个体生命体验的结果,文本中形形色色的服饰书写,已不是简单的对客体的描写,也不仅仅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而是蕴含了深刻的内在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感觉派作家创造了全新的都市文学形象,再加上各种现代写作技巧,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海派文学的品味,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创作,也丰富了现代文学的美学范畴。
[1]吴福辉.五光十色的上海文坛[A].张炯等编.中华文学通史·现代文学(第7卷)[C].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
[2]刘呐鸥.都市风景线[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3]穆时英.穆时英文集[M].北京:线装书局,2009.
[4]施蛰存.施蛰存代表作[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裴兴荣〕
The Female Narrative in the Garment Description of Neosensulism Writer
YANG Fu-l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Shanxi Datong University,Datong Shanxi,037009)
Chinese costume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ulture.The evolution of clothing reflects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politics,economy,nationality and culture.The decoration function of the dress reflects the aesthetic taste of different individuals and conveys the inner flavor of different individuals.Therefore,the author uses the costume as a special linguistic symbol.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dress more or less becomes the aesthetic object of many writers,the Neosensulism writers iare not exceptional,especially the writing of the women's clothing reflects the male Neosensulism Writers'aesthetic Tmagination for women.
neosensulism;garment description;female narrative;imagination of femininity
I206.6;I207.425
A
1674-0882(2017)05-0008-04
2017-08-2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1YJA751017)
杨馥菱(1981-),女,山西大同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对其附逆之事的再思考
——从《文学界》追悼特辑到夭折的文艺团体“中日文艺家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