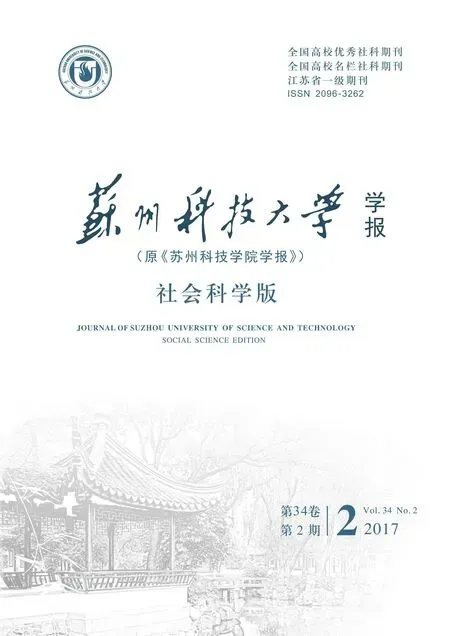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生命政治:福柯与马克思在当代的相遇*
童晓宇,孙乐强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生命政治:福柯与马克思在当代的相遇*
童晓宇,孙乐强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力再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资本对劳动力统治的三种形式:暴力、纪律规训和生命的操控,而福柯通过技术维度,揭示了惩罚、规训和生命政治的运行逻辑。虽然切入视角存在差异,但他们的整体逻辑却是内在一致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了福柯生命政治批判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援,这也是福柯所说的“不加引号的马克思”的真正意蕴所在。
马克思;福柯;政治经济学批判;生命政治
福柯和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种解读方式。确实,福柯在自己的著作中很少谈论马克思,倒是在访谈和发言中,他经常提到马克思。福柯说:“我经常会引用马克思的概念、句子和文章,但我觉得不一定非得要在页脚注明出处并附上毫不相干的评论……我引用马克思,但我不说明,不加引号,并且因为别人无法辨别是否是马克思的文章,因此我被认为是不引用马克思的人。物理学家在研究物理时感到有必要引用牛顿或爱因斯坦吗?”[1]这让人不得不思考,福柯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借鉴了马克思的思想?笔者将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探讨,以揭示被福柯掩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
一、 马克思隐含的“生命政治”逻辑
(一)劳动力再生产初期:“田园诗式”的暴力
资本积累的初期是“人类有罪”的原始积累时期。它不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不是温和的过渡,甚至可以说,“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2]821。这个时期,积累的原始特性表现为资本利用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来创造资本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此时的积累不是“田园诗式”的致富,而是暴力手段的强制分离。马克思用英国举例。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方式:(1)掠夺教会财产。16世纪,教会将地产送给国王和大臣,或者低价出让给租地农场主和市民,把旧的土地拥有者赶走,旧的佃户失去土地这一收入来源,成为流浪者、乞丐,被无情地抛入了无产阶级的行列。(2)盗窃公有地。首先,大封建主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夺去他们的公有地,于是就有一大批的雇佣工人流入无产阶级队伍。其次,王权为了求自身的发展,也用暴力促进雇佣工人的瓦解。此外,英国纺织业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把强占的土地变成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农民依旧一无所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迫使无产者大量流入劳动市场,投向工业。(3)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光荣革命”之后,英国资产阶级获得了充分的政治支持。国王与资本家沆瀣一气,把国有土地赠送出去或者便宜卖掉,再或用暴力掠夺直接变为私人财产。(4)封建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清扫领地”是暴力掠夺的顶点。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把这个名义上的所有权变为私有财产权,如果遇到反抗,就公开使用暴力把成员赶出去,同时禁止移居外国,又用暴力把这些成员赶到工业城市去。[2]823-842
在第一阶段的暴力驱赶之后,无产阶级迫于环境,大多数都沦为盗贼、流浪者、乞丐,他们并不愿意从事工场手工业工作。于是,在英国,政府颁布法律惩罚流浪者,对他们施以酷刑,如鞭打、烙印、处死,连他们的子女也不能幸免。因为暴力被赶入城市的无产阶级队伍又必须在暴力的压迫下进入工场,被迫习惯劳动制度所需的规律。这是原始积累的第二个阶段。资产阶级利用一次又一次的直接暴力获得了无尽的工人供给。
由此看出,原始积累的早期,劳动力的产生并不是如政治学家眼中那样“田园诗式”的过程,而是通过暴力手段强制农民与土地分离,新兴资产阶级、当权者勾结在一起,把土地纳入私有,赶走农民,把农民抛到一无所有的境地,抛到工业市场中去,迫使他们适应工场制度。这个阶段,统治者采取身体暴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为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不受法律保护的产业后备军。
(二)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生产:兵营式的纪律规训和无声的经济强制
资本主义获得劳动力的供给之后,社会进入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生产阶段,“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2]846,更多地是让工人自动服从支配,“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2]846。资本家对工人的控制从最初的暴力过渡到规训阶段,暴力成为例外。这种“无声的强制”表现在工厂制度的支配和机器的奴役。
工人进入工厂之后,必须“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2]488。工厂里将这种纪律发展成完整、统一的工厂制度。在工厂中,资本家将工人划分为劳工和监工。监督制度是确保整体生产活动得以运行的重要条件,而工厂制度恰好是监督的高级阶段。资本家把监督工人的职能交给特定的工人,特定的雇佣工人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管理生产过程的同时,也是管理价值的增殖过程。工人不仅在工作中受到监工的监督,而且还受到严格的工厂制度的奴役。工厂内部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工人的劳动时间、劳动强度、休息时间都是被规定好的,无论吃饭、睡觉都要听命令,工人的生活条件也在资本家的控制下。工厂变为傅里叶眼中“温和的监狱”。
工人进入工厂后,虽然摆脱了最初的暴力手段,但却受到来自机器的压迫,使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2]846。劳动由最初的形式从属到了实际从属阶段。
机器构成了工厂的躯体。机器大生产时期的工人不再是按照技术划分,而只是分为操作机器的工人和机器工人的下手。“一切在机器上从事的劳动,都要求训练工人从小就学会使自己的动作适应自动机的划一的连续的运动。”[2]484工厂的体系都围绕着机器运行,工人做什么是由机器决定的,因此对工人的技术要求非常低,甚至未成年人也可以完成流水线工作。过去在工场手工业中,机器是人们利用的工具,现在,“创造价值的力量或活动被自为存在的价值所占有”[3]91,工人成了服侍机器的工具。机器使工人的劳动成为毫无内容的活劳动,在机器面前,工人毫无主体性可言,劳动仅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机器的零件,机器作为吞噬“活劳动”的“死劳动”与工人相对立,表现为异化的力量,反过来控制了工人。“劳动自身仅仅是这个体系里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的统一不在于活的工人中,而是存在于活的(能动的)机器体系中。”[3]91
资本主义越发展,工人与机器的关系越是颠倒,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就越发分离,工人越是失去生产资料,越是依赖资本。“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本身的进行中,再生产出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分离。这样,它就再生产出剥削工人的条件,并使之永久化。它不断迫使工人为了生活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同时不断使资本家能够发财致富而购买劳动力。”[2]665-666工人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意味着工人不仅从属于机器,也完全成为了资本的奴隶,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
(三)资本统治的高级阶段:生命政治诞生
资本在把工人变成机器的傀儡后,又把力量扩散到工厂之外,包括妇女、儿童、残疾人在内的庞大的就业队伍时刻准备着为资本服务。
1.统治机制扩大
资本并不仅仅止步于对在业工人的压迫,妇女、儿童,甚至工厂之外的待业人员全都在资本关系的统治范围之内。
机器的发展使肌肉成为多余的东西,成年男工的优势丧失,“因此,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2]453。继成年男工被纳入资本统治后,资本又直接统治妇女和儿童。整个家庭都把使用价值卖给了工厂,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由于儿童和妇女的加入,男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反抗在这个时候已经消失,完全沦为工厂的奴隶。
对于淘汰到工厂之外的人,资本也实行了严密的控制。被工厂驱赶出来的工人、他们的代替者,以及企业在原有基础上实行一般扩大时通常会吸收的追加人员构成社会的相对过剩人口,这些人成为资本发展的产业后备军。过剩人口作为产业后备军,听从资本的指挥,“它绝对地从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2]729。只要资本有需要,过剩的工人就可以随时出卖自己的使用价值,供资本家剥削。并且,随着资本构成的变化,可变资本减少,不变资本扩大,表现在结果上就是一端是资本财富的积累,一端是相对剩余人口的积累,“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2]727。
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产业后备军增长的越多,并且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2]742*原著中编者提到马克思在亲自校对的法文版中将此处的“反比”改为“正比”。因此,在这里,我们采取“正比”的解释方式。。也就是说,产业后备军的贫困与现役劳动军的劳动折磨是成正比的。产业后备军越贫困,越是需要工作,对现役工人造成更多的压力,他们需要过度劳动来保住自己的工作,因此,就越受资本家的折磨,“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2]742。
劳动供求规律其实也纳入了资本的统治,“对劳动的需求同资本的增长并不是一回事,劳动的供给同工人阶级的增长也不是一回事”,而这幕后的操控者就是资本,资本一方面增加对劳动量的需求,一方面又排挤劳动力来扩大需求,使得“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以致“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2]737。
综上,资本通过把妇女、儿童赶进工厂来控制男工及其家庭,又通过控制相对过剩人口和现役劳动军的比例来掌握社会的全部人口,并且把工人自身的供求关系也推向“札格纳特车轮”下。
2.生命的生产
我们已然看到产业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庭、产业后备军都不可避免地进入资本的统治之下,现在机器大生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连生命的生产都是为资本而服务。 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的犹太历史学家的话那样:“既然一个毫无人性的母亲,竟牺牲自己的婴儿来解除无法抑制的饥饿的痛苦,那么耶路撒冷遭到了破坏,如此彻底的破坏,是不足为奇的。”[2]456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母亲如今也重复着这样残忍的事情。首先,父母变卖自己的孩子,让孩子进入那些不受年龄限制的工厂,获得其中的利润来维持生活。其次,在儿童从工厂下工,完成母亲指定他们完成的活之后,母亲还要孩子在家里继续劳动到半夜12点。这种虐待是不受任何约束和监督的。在资本的运作之下,亲情的脐带都被剪断了,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也是资本的关系。孩子被父母当作资本工具在利用。然而,“不是亲情的滥用造成了资本对未成熟劳动力的直接或间接地剥削,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通过消灭与亲权相适应的经济基础,造成了亲权的滥用”[2]563。
在英国,儿童的就业年龄越来越小。虽然英国在1833年立法,对童工的工作时间和最低年龄作了限定,然而在资本家的压力之下,政府很快又把最低就业年龄下调了。惊人的是,法律对于大资本家来说是没有任何效力的。英国花边产业就是一个例子。在这个产业之中,儿童开始劳动的平均最低年龄是6岁,但有些儿童不满5岁就开始劳动了。工作时间、工作强度比起成年人来说也没有减小。儿童们的劳动极其单调,长时间的劳动使他们的身体无法活动自如,劳动成为了真正的奴隶劳动。下工之后,资本家还会另外给他们布置活,并且会说:“这是给你母亲的。”但是,孩子非常清楚,他又要坐下来干活了。甚至,在花边工厂里,2岁到2岁半的儿童就开始干活了。孩子们从4岁起就学习编草辫。儿童无法享受到正规的教育,学校设备简陋,缺乏书籍,但可以拿到合格证书,这样就会被作为上学的儿童纳入官方数据。实际上,这些儿童是在工厂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仿佛他们生下来就是为了劳动的。
人口的再生产作为再生产的一部分,现在也已经堕入资本的统治之中。儿童从出生时,其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用工年龄的底线不断拉低,低到婴儿还没有学会说话就要成为机器的奴隶,在还没有学会选择的时候就被母亲卖给资本家,在还没有理解大千世界的奥秘之前就先学会了如何替母亲干活。生命的诞生除了供资本家剥削之外,没有别的可能性。人的生产只是为资本的运转提供无穷的劳动力资源。
二、 福柯的生命政治:不带引号的马克思
福柯与马克思的关系并不是完全远离的。福柯在研究过程中必定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就像他自己陈述的,他是“不加引号”的马克思思想引述者。如前所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条逻辑路线是暴力—规训—生命政治,但在福柯所著的《规训与惩罚》中我们会很惊奇地发现,这一逻辑也被福柯用在了对权力技术的研究上。
(一) 酷刑和惩罚
福柯在书的开头就描述了18世纪一个血腥的处死场面,这种刑罚的形式从1670年法令开始,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刑罚的主要形式是死刑、拷问、苦役、鞭刑、公开认罪、放逐等,肢解、车裂、烧死是常见的极刑。公开处决成为一种司法仪式,并且成为一种政治仪式。它不仅使犯罪成为自己罪行的宣告者,而且强调了君主的权力,用罪犯的肉体来使民众认识到君主的存在。此时的法国到处充斥着对肉体的酷刑和肢解,对人身体的折磨,将肉体作为惩罚的主要对象。但是,公开处决、酷刑引发了君主并没有预料的问题,本来彰显君主权威的仪式却成为了人们狂欢的节日,并且行刑之地也是暴动爆发的中心,诱发了打架斗殴、酗酒闹事等事件的频频发生。鉴于这个原因,再加上或许存在的人们的恻隐之心,国家逐步废除公开处决的仪式,人们关注的焦点转到了司法破案上,建立了新的刑罚体系。第一,酷刑被取消,惩罚走向节制,大大减少对肉体的惩罚,死刑也只用于杀人犯。身体不再是惩罚的目的,肉体折磨被其他措施代替。第二,惩罚机制的变化不仅使更多的人日益“理解人类、灵魂、正常或不正常的人是如何逐渐复制出作为刑罚干预对象的犯罪,一种特殊的征服方式是如何能够造就出一种作为具有某种‘科学’地位的话语的认识对象的人”[4]25,也促使社会的惩罚机制逐渐变得有据可依,不完全取决于当权者的个人意志。第三,更多的人参与到惩罚和判决中来,而这些人是由一群技术人员,如医生、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组成的团队,判决也变得越发理性。
中世纪向18世纪的跨越,也是酷刑向“再现式”惩罚的转变。权力不再作用于肉体,而是精神,福柯称之为“运用于在一切人脑海中谨慎地但也是必然地和明显地传播着的表象和符号的游戏”[4]111,只是“精心计算的惩罚经济权力学”。国家不再通过残酷的刑罚折磨人,而是建构新的话语,形成强烈的意识形态来控制人们的思想,这是超越肉体之上的惩罚。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权力技术学,然而,这种符号-技术的“意识形态权力”也是会被搁置的,新的权力统治模式将会到来。
(二)规训和纪律
终结了酷刑的文明时代到来后,人们却比以前受到更多的干涉与统治,一个更加精巧协调的司法对身体的控制日益繁多和完善。在新的惩罚形式中,仪式和展示的意义退出,对人民的引导、教育、规范的意义走向在场,使对罪犯的惩罚变成“秩序展览馆中那旨在教育人们的生动课程”[4]126。此时的规训通过规范农民“昂首挺胸、收腹垂臂、笔直站立”[4]153,可以使农民成为“具有军人气质的士兵”[4]153;此时的规训也是将个体进行分门别类、并在空间上进行固定的方式,“提取他们最大的时间和精力,训练他们的身体,对他们的连续行为进行编码,把他们保持在理想的能见度中,用监视机制包围他们,将他们登记注册,在他们之中建构一套累积、集中化的知识”[5]。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权力力学”,给人以不在场的、隐形的惩罚的联想,使其成为被驯服的人,同时授予人知识和技能,使其成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奴隶”,这样,就能达到对生命、个体的总体控制。
福柯认为,在17—18世纪,纪律变成了一般的支配方式,即对“人体的运作加以精心的控制,不断地征服人体的各种力量,并强加给这些力量以一种驯服-功利关系”[4]155的方法。纪律出现在工厂、监狱、学校中,表现为人们对法规发自内心的服从和遵守。在规训的开始——工厂中,是贯穿整个劳动过程的监视,不仅针对生产,而且也考虑人的活动、人的表现等劳动的其他方面,监视成为生产机构的一个重要部分,工人时刻都处于监工的监视下,甚至到了工人宁愿选择行会制度也不要被监视的地步。在学校,从优秀学生中选拔干事,每一个干事都负责监督一个部分,而班长负责监督所有的干事。这种监督关系是教学实践的核心,能有效地保证教学的效率。而监视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地方是在监狱。这种建筑的独特形式之一就是建筑中心有一座瞭望塔式环形监狱,监视者可以从瞭望塔里监管到所有囚室。不间断的可见性迫使主体陷在小小的囚室中,其中的每个囚员都是孤立的。这既能减少犯人与官员间直接肉体的对抗,也会由于权力的增强,使犯人加强自我控制。
(三)生命政治的诞生
福柯对于生命政治的完整定义要追寻到《必须保卫社会——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最后的总结中,福柯对他谈的战争和国家问题突然按下不表,把话题转向了在《规训与惩罚》中搁置的生命问题。他说:“我觉得,19世纪的一个基本现象是,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权力负担起生命的责任:如果你们不反对,就是对活着的人的权力。”[6]183这种对活着的人的控制是对人的生命行使权力的新技术,即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的“治理术”,运用的对象是“18世纪下半叶,出生率、死亡率、寿命这些过程,与所有经济和政治问题相联系”[6]186。权力不再关心个人的生死,而是从总体上来把握人口的比率。在这里,福柯明确了这种生命政治学的对象,进而作出对生命政治最为著名的判断:“君主专制使人死,让人活。而现在出现了我所说的调节的权力,它相反,要使人活,让人死。”[6]188-189权力机制建立在公共安全、卫生防疫这些“使人活”的层面,死反而成了权力之外、完全私人的事情。这种调控的方式,用福柯的话是:“首先当然是预测、统计评估、总体测量;同样它也不是改变某个特殊的现象,也不是改变某个作为个体的个人,而是主要在具有总体意义的普遍现象的决定因素的层面上进行干预……简单点说就是对生命,对作为类别的人的胜利过程承担责任,并在他们身上保证一种调节,而不是纪律。”[6]188纪律从规训机制中撤出了,现在是权力的调节机制在起作用。
三、福柯掩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
通过福柯的文本不难发现,他在不自觉地运用着马克思的思维逻辑,甚至直接引用了马克思的文本。这其中所隐藏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基础是我们需要揭示的。
首先,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陈述惩罚机制演变时,遵循的逻辑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述劳动再生产理论时的逻辑竟然如出一辙。我们很难说福柯对马克思是持批判态度的,至少在这个阶段,他内心对马克思是认同的。福柯研究中的暴力—规训—生命政治是马克思从生产领域批判向社会领域的挪用,在马克思那里,由工厂的规训推进到“生命诞生”,由微观透视宏观,而福柯是由工厂、监狱、学校等规训演变到对人口的控制,进而解释生命政治的含义,也是由小见大的演化方式。这种推理方式是极为相似的。福柯在微观层面上对于规训权力的细致观察,并未叛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批判。
其次,福柯研究的落脚点与马克思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马克思的构境是落在资本关系对人生产过程控制的基点上,福柯是建立在权力对人和社会生活的调节基础上。张一兵也认为,福柯晚期开始专注于有关新生的资产阶级权力场对人的生命肉体的微观支配的思考,并且“思想情境竟然就是当代后马克思思潮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和政治哲学塑形的全新起点”,“福柯这种批判真正的方法论基础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基始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商品-市场运作机制的透视!”[7]福柯说:“如果说经济剥削使劳动力与劳动产品分离,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规训的强制在肉体中建立了能力增强与支配加剧之间的聚敛联系。”[4]156显然,福柯是将自己的肉体规训与马克思的经济剥削等同起来的。不仅如此,福柯还逐步揭示了监督与惩罚等规训活动将人口(劳动力)增长累积与资本增长累积相互统一的过程。他认为,身体上的规训组成了司法的基础,而工业、农业的发展与规训方式的变化是同步的。生产机器、分工和纪律秩序的发展中存在的各种技术变化是相互紧密关联的,这些不同领域的技术革新彼此是对方的基础和条件。而这正与马克思在分析生产活动过程时提出的经济与政治、社会与国家之间发生碰撞时产生的效果相吻合。
虽然福柯在自己的生命政治诞生的逻辑构建中借鉴了马克思的观点,但他的理论也有自身的独特性。首先,在马克思的工厂理论中,工人在工厂内部受到压迫,在工厂外是拥有自己的剩余时间的。到了福柯这里,资本主义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权力对人的作用已经扩大到整个社会,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受着规训。其次,在马克思的解放理论中,人们是能够摆脱资本关系实现共产主义的,而福柯认为是没有办法摆脱权力对我们的统治的。这两者差异的原因在于马克思和福柯所处的时代不同,资本主义历经几百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福柯是站在他那个时代的基础上看权力统治的。我们不必去判定对错,只是客观地解释福柯那里的马克思主义元素,再现一个“不加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引述者。
[1]莱姆克.不带引号的马克思:福柯、规治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J].陈元,译.现代哲学,2007(4):3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5]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M].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79.
[6]福柯.必须保卫社会[M].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7]张一兵.回到福柯[J].学术月刊,2015(6):38.
(责任编辑:张 燕)
2016-11-20
童晓宇,女,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意大利自治主义思潮研究; 孙乐强,男,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B565.5
A
2096-3262(2017)02-0013-06
——从学科规训视角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