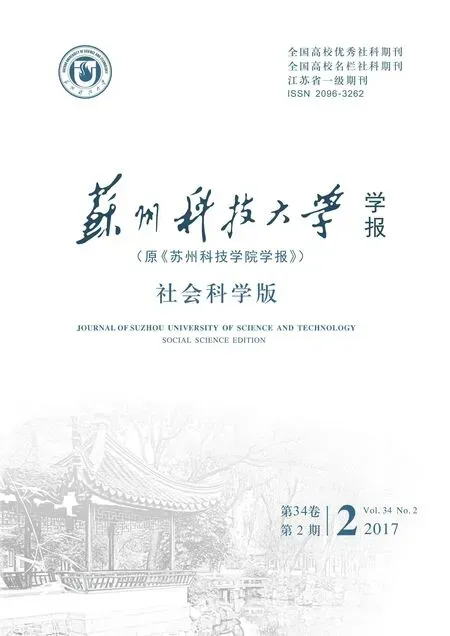长篇小说的日常生活时代*
——以2015年《收获》与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为中心
关 峰
(长安大学 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
长篇小说的日常生活时代*
——以2015年《收获》与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为中心
关 峰
(长安大学 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
日常生活成长为长篇小说和当代文学批评新的话语和空间中心。在长篇小说中,日常生活作为社会症候和现实缝隙的体现,用罪案寓意日常生活畸变,且以女性视角细腻、敏感地还原了日常生活,并审视日常生活背后的含义。日常生活转向是时代的要求,对长篇小说而言既是开放又是深化。人或生命这一日常生活性母题成为作者聚焦的中心,压力和孤独的体验将悲哀突显出来,升华为审美对象:一是人的日常生活化,二是日常生活反思和重建。社会问题和现实困境筑成了长篇小说高地,批判精神和启蒙自觉也塑造了长篇小说的反思品格。一方面,日常生活成为反思的领地,呈现了浮躁喧哗背后的疮痍和创伤;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也作为乌托邦的符码,寓示了拯救和再生产的可能。
长篇小说;日常生活;《收获》;茅盾文学奖
日常生活之所以成为当前文学批评的关键词,除了以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为代表的日常生活理论的推动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社会转型和政治制度赋予它的动力和张力。日常生活现场和视阈取代权力意识形态,成长为新的话语和空间中心,参与后革命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建设。以新世纪长篇小说为例,日常生活更多是一种态度,一种立场,一种预设,一种实践。莫言、余华、贾平凹、刘震云、阎连科、韩少功、叶兆言等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活跃于日常生活广场。笔者拟以2015年《收获》杂志所刊长篇小说及该年度揭晓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以下简称“茅奖”)获奖作品为例,探究日常生活视角及其实现,以追踪长篇小说的最新态势,构建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日常生活诗学。
一、日常生活寓意
富于反讽意味的是,出于文学史命名需要的新写实小说反倒使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凸显出来。事实上,新世纪文学的渊源也肇始于此。当然,在社会语境相对平稳的今天仍然适用。《收获》杂志2015年所刊五部新作*迟子建:《群山之巅》,《收获》第1期第96-189页;严歌苓:《护士万红》,《收获》第2期第134-187页;路内:《慈悲》,《收获》第3期第135-186页;韩东:《欢乐而隐秘》,《收获》第4期第114-188页;王安忆:《匿名》,《收获》第5期第115-188页。下文中与这五部小说相关的引文与阐述均以此为本,不再一一出注。就呈现了日常生活的面貌和景观。
没有狂欢和热烈,日常生活似显平淡而单调,有时甚至是苍凉和残酷,王安忆和迟子建的处置就透露了个中消息。王安忆的《匿名》开始于一桩绑架案,迟子建的《群山之巅》则写了强奸和杀人案。犯罪案件不只是对日常生活的破坏,更是完整而深刻地反映日常生活的视角。作为社会症候和现实缝隙的体现,罪案显示了日常生活的畸变。两位作家的女性视角以其细腻的敏感还原了日常生活,并审视日常生活背后的含义。同样,彰显了形而上意义的另外一位女作家严歌苓则延续了后英雄时代的日常生活话题,与以爱情为主题的韩东的《欢乐而隐秘》有异曲同工之妙。相比之下,路内的《慈悲》更紧凑。日常生活的河流回荡着呜咽之音,既明净又深沉。
新写实小说重建了日常生活美学。此后,虽有“人文精神”等论争相龃龉,但底层、草根、打工等日常生活符码还是兴盛和流传起来。秩序建立过程中的日常生活再祛魅化,迟子建的《群山之巅》就揭示了日常生活的尴尬和困境。小说的重心是一个名叫安雪儿的女孩被强奸的案件。这个被称为“小仙”的矮人精灵不只被“破了真身”,也把“神话”给破了。所谓“坠落凡尘”,就象征了从神到人的转变,或者说是日常生活的回归。安雪儿不仅怀了孕,连身体也发育生长起来,小说第六节“生长的声音”正是对生命的拜献。然而,“下凡”的安雪儿却难以静定,不仅孩子毛边的生父辛欣来被正法,而且她自己也又一次受辱——遭守护土地祠的单夏强吻。“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这个苍凉沉郁的结尾不只是她苦痛境遇的升华,也同时蕴含了日常生活的冷峻和隔膜。
如果说《群山之巅》是从正面表现日常生活的千疮百孔的话,那么严歌苓的《护士万红》则从反面呈现了日常生活的寥落。和《群山之巅》的多线索交叉相比,《护士万红》更集中,也更浓重。这个以主人公名字命名的题目(成书时更名《床畔》)俨然简练而又幽静的雕塑,无声地诉说着生命的传奇。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救出两个兵的英雄连长张谷雨成了植物人时,万红却以她特有的观察和体验相信并坚持自己截然不同的判断。在后英雄崇拜的时代,万红继续了英雄的神话,但孤独抗争的背后却是无边的荒凉和寂寞,就像一个日常生活的空洞。
不满足于展览和沉溺,以精细见长的王安忆把日常生活引上了超越之途。也许是对人文精神的认同,王安忆在打破日常生活的同时努力建构意义的世界。绑架案本身就象征了某种争夺,某种剥离,所以人不再重要,“匿名”成了主旨的暗示。当王安忆把老板吴宝宝嫁接到外公名上时,实际上她是在作双重否定。过去和现在,旧和新,都融进了历史和文明的时间之中。这时间不再是日常生活的当然和同质,而变得惊心动魄和刻骨铭心。与其说吴宝宝饱受侵害,陷入了苦难的泥淖,倒不如说他领受了精神洗礼,涅槃更生。哑子、二点、小先心(张乐然)、新鹏飞都是他复活的生命。
王安忆引入时间和文明,希望建立感性博物馆,提醒时间和文明的搏斗痕迹,揭示当代社会生活的文化渊源,而在精神史建构过程中她也有意无意地放逐了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变得残缺和支离。吴宝宝的被绑架既是他和他的家庭对日常生活的脱离,也打乱了与之相连的周围世界的节奏,包括民营物流公司与麻和尚。更为显明的是,当基因配对相符,被福利院称为“老新”的失踪人即将回到上海的家里时,王安忆几乎是轻描淡写地叙述了辞行人的落水。与之相伴的是,“晚霞在天边一片绚烂,江鸥飞上飞下,江心淌着一注金汤,里面蹿着金针”。“老新”再也不能回归日常生活的境域,永远留在了时间之中,王安忆借时间塑造和提炼了日常生活的意义。当上部“归去”第四部分结尾写到哑子“终于知道了,把这个人带去哪里,就是带去山里边,带进无限的时间”时,王安忆实际上完成了对于日常生活的胜利和超越。
同样是从日常生活到意义的过渡,路内把王安忆的文明追问转向了宗教乌托邦。日常生活不再是分立的他者,而成了意义本身。值得注意的是,路内打破了革命与后革命的固定分野,把人生、命运贯穿于日常生活之中,强化了小说《慈悲》的主旨。主人公陈水生二十岁读工专,毕业后进了前进化工厂的苯酚车间,直到六十岁还挣扎在苦境之中。没有英雄情结,也没有传奇人生,小说着力呈现的是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和冷暖甘苦。一切自然、随缘,连时代和社会也自然化为自我,日常生活像缓缓流淌的河水,涨落起伏,流向不可知的时间之中。不同于《匿名》,这里的“时间”就是日常生活本身。《慈悲》中有庙宇,但没有神话,路内把希望置于冥冥之中。最后水生和弟弟云生(法号慧生)的相遇就是个象征,所谓“皈依”,所谓“勘破生死”,日常生活的终极正是对于灵魂的指引。虽然弟弟不愿承受人生的苦痛,不想再过俗世的生活,羡慕爬着进香的老太的虔诚和幸福,但乐便是苦,正如灵魂就是肉身一样。
二、日常生活精神
第九届“茅奖”五部获奖作品——格非《江南三部曲》、王蒙《这边风景》、李佩甫《生命册》、金宇澄《繁花》、苏童《黄雀记》*格非:《江南三部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王蒙:《这边风景》,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李佩甫:《生命册》,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金宇澄:《繁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苏童:《黄雀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下文中与此五部作品相关阐述均以上述版本内容为依据。,或是日常生活时代的结晶,或契合日常生活时代精神,既展示了日常生活对于文学(长篇小说)的塑造,也诠释了文学(长篇小说)走向日常生活的意义。
日常生活是现代性的产物,是普通人的时间和空间语境。拿《生命册》来说,李佩甫借小人物折射大时代,失败和死亡取代了成功和永恒,生命观照置换了崇高和神圣。李佩甫的生命书写无形中是一种反拨,疏离革命和政治模式。生命意味着人的日常生活化还原,骆国栋(骆驼)、吴志鹏、梁五方、虫嫂、杜秋月、春才、老姑父蔡国寅、蔡思凡(苇香)等都是生命的时代标本。耐人寻味的是,每一个故事都呈现了生命自然的本色,不无苍凉和悲壮的格调。骆国栋的跳楼自杀,梁五方的上访,虫嫂的死,杜秋月的失常,“很有骨气的失败者”春才,瘫了的老姑父,蔡思凡的“汗血石榴”,无一不是日常生活的真实。骆国栋的经历就是这样真实的象征。他相信,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又是一个在行进中、一时又不明方向的时代。落实到行动上就是一个“抢”字,“抢抓机遇”,“时间就是生命”,所谓“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打新股”、厚朴堂包装上市、贿赂副省长范家福、为夏小羽活动“金话筒奖”等,在“我”看来,并不表明“骆驼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却体现了日常生活的价值评判标准。
日常生活时代是对此前革命时代的平衡,也是客观历史规律的再度证明。相对于意识形态,日常生活重在个人立场,关心现场和经验。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连主人公形象的选择也富于日常生活意义:分别选取三位女性形象作为故事结构的中心。比较而言,历史题材的前两部更昭示了日常生活维度。陆秀米(《人面桃花》)、姚佩佩(《山河入梦》)的女性视角既是对历史肉身的重现,也是细腻、敏感的日常生活化改写。值得注意的是,根深蒂固的历史叙事霸权退入背景,革命话语以模糊和朦胧的方式让位于生动清晰的日常生活节奏。如革命者张季元的到来及其与母亲关系的扑朔迷离,直到秀米所读的日记中才清晰起来。同样,从事革命后的秀米也变得捉摸不定,失去了前此日常生活中的充沛和丰盈。《山河入梦》中姚佩佩与谭功达的真情也远过于后者的官场沉浮。看得出,格非对与他同时代人物性格的把握更加得心应手,这也从一个方面解释了《春尽江南》女主人公庞家玉的出类拔萃。虽然向死的悲剧“大同”,但日常生活深度的“小异”还是在其间区别开来。
和格非的女性叙事相比,金宇澄的《繁花》更直接更显豁。沪地方言和风情生发了日常生活的活泼,替逼仄的长篇小说天地开一新局面。作者表明:“《繁花》感兴趣的是,当下的小说形态,与旧文本之间的夹层。”[1]跋443金宇澄所说的“旧文本”,实际上是鲁迅所讲的韩子云《海上花列传》、周作人所谈的《常言道》一类。巧合的是,金宇澄的经验恰好印证了周作人的论断,也就是“如何说,如何做,由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1]跋443的写法。与后者“天然凑泊”“行云流水”“逢场作戏”“见景生情”的契合,可谓生活流的样式。以开头为例:
沪生经过静安寺菜场,听见有人招呼,沪生一看,是陶陶,前女朋友梅瑞的邻居。沪生说,陶陶卖大闸蟹了。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1]1
“进来看风景”便似作者的邀约,而“风景”也不难想见:菜场、大闸蟹、茶,都是再日常不过的“事体”。至于活动在其间的人物,第一眼看去的“沪生”二字显然是做暗示;打招呼者陶陶所说的“长远”带出日常生活的幽远;“前女朋友梅瑞的邻居”这一介绍几乎让人忍俊不禁,可见“编织人物关系”的功夫,寥寥几句显示了金宇澄对日常生活的瞭望和感触。
除感性具体的当下生存状态外,日常生活的解读还可以作文明历史意义上的延伸。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习俗形成超稳定的日常生活结构。和这一结构相比,当下生存状态的日常生活则显得捉襟见肘,苏童的《黄雀记》就是这种观察的产物。围绕着三个年轻人的强奸案仅是表象,它所传达的是日常生活的破坏和零乱。一错再错,保润的冤狱最终膨胀恶化,演变成又一起杀人案,苏童沿用他所擅长的象征手法,展现了日常生活的变异和创伤。除保润外,案件的另外两个当事人柳生和仙女(白小姐)也都深受其害。苏童一边呈现年轻人命运的改变,暗寓日常生活秩序的打乱;一边却也尝试修复和重建,祖父形象的设置就是这一意图的表示。开头的“拍照丢魂”表达了祖父遭遇现代生活的尴尬和无奈,正如鲁迅在谈到时人不爱照相的原因所说的“精神要被照去的”[2]那样。不幸的是,祖父再也不能回到属于他的时代,不仅魂没有找到,连他自己也被强行绑进井亭医院。苏童的用心不只是在开头,结尾更具匠心。如果说开头是写失落的话,那么结尾则重在回归。从“红脸婴儿”到“耻婴”再到“怒婴”,同此前保润左右臂上“君子”“报仇”的刺青一道,传达了对白小姐乃至她所代表的不正常日常生活世界的审判。对保润的“走”和白小姐的“不见了”的交待既是否定,也是希望。留下来的一老一小不只是对过去和将来的连接,更是新的敞开,是日常生活结构的传承和再造。难怪作者不惜以重复的写法为整部小说作结:“怒婴依偎在祖父的怀里,很安静。当怒婴依偎在祖父的怀里,他很安静,与传说并不一样。”[3]传统超越传说,成就了苏童的传奇。
三、日常生活与生命
笼统而言,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中,长篇小说最便于再现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永恒灌注了生气。2015年的长篇小说现场就有惊人的磁场,同时,不断生发的人和日常生活的距离越来越大,迷惘和无助的生命也随之而起。比较而言,日常生活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大地”,生命则是“世界”。
如果说《护士万红》是2015年《收获》杂志坚守精神的“收获”的话,那么《慈悲》则是日常生活的凝望。前者打造了英雄之上的英雄。护士万红之所以伟大,正在于她的坚持,连后来成为植物人研究专家的吴医生都在质疑,但万红坚信的可贵正在于对生命的尊重,对真理的追求,对道德的守护,对理想的执着。万红工作六年记下的四大本护理日志,一天不少,换来的却是青春和爱情的代价。在被功利和欲望污染的世界里,万红不只是“不识时务”的英雄,更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观音或女神。后者讲述了水生的一生,娓娓道来。岁月和人生的回响就像暮鼓晨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治退居背景,日常生活成为主角,活动于其间的众生只见其活命和苦难。六十年甲子轮回中,水生先后失去了父母、叔叔、师傅(岳父)、妻子玉生,还有孟根生吊死,段兴旺患癌死去,邓思贤中风而死。路内体会和玩味时代精神与社会心理,升华了日常生活哲学。
日常生活转向是时代的要求,对长篇小说而言既是开放又是深化,人或生命这一日常生活性母题成为作者聚焦的中心。李佩甫的《生命册》自不必说,王蒙的热情更是建筑在生命之上,他在《这边风景》的“后记”中提到最多的词就是“生命”,体会到“世界与你自己本来就是拥有生命的可爱、可亲、可留恋的投射与记忆”,相信自己过了时的文稿正是“得益于生命的根基”。从《欢乐而隐秘》中能感受到作者韩东的苦心也在生命中获得了平衡,《欢乐而隐秘》看似卑俗,却装嵌了崇高的内核,爱情的传奇,生命的瑰丽都寄寓其中。尚未出生的秦麒麟既成就了爱的神话,又是日常生活世界的狂欢。和秦麒麟相比,苏童笔下的怒婴则象征了控诉的叛逆生命,矛头直指生母白蓁(仙女、白小姐)及其颠倒的异化世界。
七十年前,鲁迅曾撰文称道哈尔滨人民“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4]。七十年后,现居哈尔滨的女作家迟子建就在继续先辈的事业,她的《群山之巅》无疑是飞速变化着的时代生命的记录。迟子建怀旧但不守旧,故而能写出“震荡”来。火葬场的建立及注射死亡的处决死刑方法只是大处落墨,迟子建最感兴趣的是新旧变迁中的生命形式,借以谱写生命的挽歌。辛欣来的强奸杀人;唐眉因爱生恨毒害同学陈媛;日本女人秋山爱子的毛边纸船坞;上海知青刘爱娣的临终托付;林大花的八万元卖掉初夜;龙盏镇镇长唐汉成对开发的抵制等等,都是社会转型阵痛期中沉浮的生命样式。小星河畔的绣娘风葬,土地祠中大声呼救的安雪儿,则是无比钟情大自然的作者的生命祭祀和呐喊,背后牵涉的是生命的健康和尊严,或者说是日常生活的家园焦虑。
浮躁喧哗和急功近利的心态使得坚守越发难能可贵,同样,压力和孤独的体验也将生命突显出来,升华为审美对象。《繁花》众多头绪的顶点恐怕要数小毛弥留之际一段,一句“上帝一声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在“珠环翠绕”的“繁花”中更富于生命感,难怪作者将之用作题辞。结句是“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黄安的歌声更如鸿鹄之鸣,渐入寥廓。格非同样把日常生活和生命连结起来。女性悲剧本身就是对男性英雄史诗的反拨,是日常生活态度的选择。如果说《人面桃花》中的秀米是革命悲剧,《山河入梦》中的姚佩佩是政治悲剧的话,那么《春尽江南》的家玉(秀蓉)就是生命悲剧。家玉一点儿也不完美,甚至还有点儿颓废和堕落,但就是这样再平凡不过的女人却不得不面对生命的残酷和社会的冷漠。绝症使她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对人世的告别则表达了某种时代情绪。作者坦言:“这个时代急转直下的一些东西,有时候会让人有悲伤,有无可奈何的感觉。我有时候不理解现代的人为什么活得这么高兴。”[5]庞家玉在交出了自己身体和精神之后最终被褫夺了生命。格非的“白日梦”正是文学的职能之一,如他所说:“在现实生活重压之下给我们提供一丝喘息。”[5]提供了回望和反思之机的李佩甫的《生命册》则是正面、朴素的生之歌,以骆驼为例,不断膨胀的欲望刺激自我挑战现实,梦与现实的冲突最终葬送了自我。其他如梁五方、老杜、虫嫂、春才等都是生命的奇迹,回响着日常生活的中国之声。
日常生活是人最自然、最恒久的生存状态,也是最美丽动人的心灵皈依的大地,长篇小说源于此,也终于此。苏童《黄雀记》中的祖父和王安忆《匿名》中的“老新”,都是日常生活的隐喻。前者不能适应时代,因丢魂而被送进井亭医院,红脸婴儿的安静寓意祖父传统和日常生活的宽厚。后者被绑架的命运同样是日常生活的噩运,一方的褫夺在另一方恰是天赐。“老新”的存活不无对文明和时间背后的日常生活的致敬,而即将回归却再遭噩运的结局也是基于日常生活的拒斥和抗议。最后一句“赤裸的时间保持流淌的状态,流淌,流淌,一去不回”,便是对于日常生活状态的呼应。同样,借罪案展开的《群山之巅》也回响着对逝去的日常生活记忆的呼唤。辛七杂的太阳火;李素贞的不服轻判,提起上诉;安平的不惧美色;刘爱娣的托孤等,都是这记忆的痕迹,是日常生活的风景。所谓“群山之巅”,其实就是一曲日常生活的挽歌。格非对女性身体的直视是他与历史协商的结果,也是挽歌式的日常生活节奏。
看得出,这些长篇小说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人,是生命,而非强加的先入之见。即便是三十多年前的旧稿,《这边风景》在王蒙看来也是以人为第一位的,而且“真实得无法再真实”,“细腻得胜过了实录”[6],可谓日常生活的影子。李佩甫的《生命册》也是这样的实录,只不过展开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三十年。小说满覆失落的焦虑,首尾城乡失衡的忧惧固定了全书寻根的主线,堪称日常生活的“清明上河图”。《繁花》则是上海生命与生活的“浮世绘”,所谓“上海味道”,正是日常生活的极致。其他如王果儿的“嫖”和齐林的死,看似离奇,实际上蕴含了补偿和改造的希望,是日常生活的召唤和自我修复。吴医生对万红“不可愈合”的爱,水生对亡妻玉生和爸爸灵魂的引领,都是重建的日常生活丰碑,而《欢乐而隐秘》“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的大团圆结局,更是日常生活式的皆大欢喜。
四、日常生活与悲哀
也许是太过匆促和功利的现实在作怪,过去五年中的长篇小说对于时代和社会的讲述总有种挥之不去的沧桑和凄凉之感。实际上,这一情感本身就是丰富复杂的日常生活的明证。如果说诗是日常生活普遍心理和情感的酝酿和释放的话,那么长篇小说则几乎就是日常生活本身,至少也是对日常生活的模仿和试验。就像迟子建所说的“莫名的虚空和彻骨的悲凉”[7]一样,长篇小说必然留存有现实社会情绪的余剩。《群山之巅》中安大营之死固然令人唏嘘,而划了长青烈士陵园安玉顺和安大营墓碑的杀人强奸犯辛欣来也一样值得同情。陈金谷的肾脏移植手术和辛七杂、安雪儿想见他最后一面的温情,都是这种同情的原因。小说的精妙之处正在于对这样“二律背反式”困境的揭示,从而将日常生活风景的冷峻和无奈显露无遗。“群山之巅”已不再是圣土,唐汉成的焦虑和忧惧正是上述浮躁和喧嚣的社会的镜像。
彻悟“改变精神”对于民族国家重要性的鲁迅曾解释悲哀原因道:“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着物不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此人世所以可悲。”[8]同一时期的周作人也以忧国忧民的心情指出悲哀之必要:“顾目击扰攘,而萧条之感乃不觉婴心而来,令人森然如过落日废墟,或无神之寒庙者,其凄清也如是,盖所谓死寂者是也。萧条唯何?无觉悟是。曷无觉悟?无悲哀故。”[9]周氏兄弟的悲哀建立在家国之上,到了2015年的长篇小说则是源于民间、源于日常生活情绪的结晶,其中,路内的《慈悲》最为突出。小说中的人物大都带有“生”字,诸如水生、玉生、根生、复生、云生等,“生”意味着生命、生存和生活。题目“慈悲”及最后第38节的“勘破生死”也暗示了“超生”的解决之道。巨变中的社会太过压缩,使得日常生活成了重载运转的机械,成为一个异化了的世界。显然,主人公水生的一生便是濡染了悲哀色彩的一生。从悲哀到慈悲不仅是大升华,也是大境界的见证,大有日常生活的宽容和厚重。不过,即便是作者自己也缺乏信心,所以他才写了庙宇钟声的“停下、飘散,世间的一切声响复又汇起,吵吵闹闹,仿佛从未获得一丝安慰”。而引领玉生和爸爸的灵魂“跟紧水生,不要迷路”的结尾,既平凡朴实,又深沉悲凉,萦绕着日常生活的回声。韩东的《欢乐而隐秘》虽以“欢乐”为题,又不无循俗和调侃之嫌,但它以齐林之死为底子的设置还是刻划了悲哀的日常生活侧面。此外,生命延续在王果儿身上所激起的冲动及佛菩萨的装点,也是对悲哀及日常生活的表达和补充。之所以没在车祸上戛然作结,以齐林和王果儿双双情死成就浪漫的传奇,显然寓示了韩东对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偏好。牺牲悲哀之题的代价与其说是消解,倒不如说是重建,重建了含有悲哀的日常生活诗学,所谓“化悲痛为力量”,也即是笑中有泪,苦中作乐。
女性身份赋予王安忆特别的对日常生活的敏感,她的《匿名》颇多社会症候的象征。主人公姓名的模糊性既暗示了命运遭际的普遍性,同时也隐喻了人的自我失落的悲剧性。在王安忆那里,当代人的悲剧性就在于日常生活的断裂和陷落,不可思议的错乱,恰是这一日常生活缝隙的表征。值得注意的是,吴宝宝在整个绑架过程中完全有自救甚至脱逃的机会和可能,但作者压根儿就未谋虑,当事人只是在“应激反应”和“自我保护”中平衡自身。显然,王安忆放大了日常生活风险。与之相对,吴宝宝不真实的拼搭却在下部以“老新”的方式获得了新生,是山野的化外之地和当代文明的边缘地带拯救了日常生活事件的受害者。表面上王安忆大谈时间和文明,实际上她是以传统的方式来批评异化了的日常生活。在此基础上,不无同情地挽留“老新”在时间的长河中,而不是让他重新回归现实秩序和日常生活,无疑是她批判和赞赏的选择态度使然。实际上,即便回家成为现实,假冒吴宝宝的他恐怕也难真正回到原来的日常生活轨道,这从上部“归去”中妻子杨莹瑛放弃的态度上不难看出。对这样一对老夫妻而言,他们牵手走过了不平静的政治和革命时代,却不能跨越似乎再平静不过的日常生活时代。两相比较,“老新”面对的哑子、二点和鹏飞虽受天谴,但却都生气蓬勃,正所谓“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而未尝不是王安忆对涣散的日常生活的警醒和救赎。
日常生活以时间的形式表达自身,同时,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克服时间,但结果往往不尽理想,悲哀之感便是其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鲁迅小说就是对时间的悲哀的记录。金宇澄的《繁花》也是对日常生活流的诗性发掘,像二十三章小毛老婆春香临产大出血,到了弥留之际劝告老公,“不可以忘记自家的老朋友”,就是日常生活的告白。有意思的是,格非的《春尽江南》中出现了苏童、臧棣等当代作家和诗人的名字,实际上也是对日常生活的召唤。《黄雀记》则是苏童日常生活凝思的产物。出狱后的保润并没有即刻复仇,而是静待一段时间之后,背后未必不是日常生活的窥伺。同样,保润、柳生和白小姐之间的早年结怨也沉淀于日常生活的河床。十年后的三人表面上似尚融洽,维持着相互间的均衡,所谓“黄雀”正是这种时间的力量,暗示某种日常生活的隐秘。更富有象征意味的是,在井亭医院的祖父看似被放逐于日常生活之外,实际上正是以不合作的极端方式来表达对日常生活的愤怒和攻击,而红脸婴儿在他怀里安静的结尾则更多回归和还乡的意味,意在日常生活的寻根。综合考量,王蒙的《这边风景》和李佩甫的《生命册》之所以能够荣获“茅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作品中的日常生活广度和深度,以及对人的日常生活观照和叙事。后者的生命形式不无时代和社会日常生活坐标的定位。同样富有象征意味的是《护士万红》。首先,女英雄万红本身就是对男性立场的颠覆。如果说男性是权力和欲望主体的符码的话,那么女性则昭示了弱势群体和日常生活的法则。这里万红的意义更表现为浮出地表的日常生活修辞。其次,万红的故事本身也凸显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美学。万红的护理日志详细记录了六年中张谷雨包括心情和食欲在内的每天的日常生活生态,一天不少。事实也证明了她对张连长不是植物人的判断和结论的正确。显然,严歌苓赞颂了日常生活之美。在主管医生“吴一刀”看来,万红就是不识时务的英雄。所谓“不识时务”,不正表明日常生活的永恒和神圣吗?
综览上述十二部长篇小说,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人的日常生活化。此前“大写的人”的先验模式被“日常生活的人”的审美范式所取代,如万红(《护士万红》)、陈水生(《慈悲》)、陆秀米(《人面桃花》)、姚佩佩(《山河入梦》)、骆国栋(《生命册》)、王果儿(《欢乐而隐秘》)、伊力哈穆(《这边风景》)等都解构了既成规范,凸显了日常生活旨归。《护士万红》中的万红、《欢乐而隐秘》中的齐林,看似英雄和传奇,实际上都经过了日常生活的洗礼。前者“白发苍苍的头”和后者的车祸身亡,就是日常生活的点睛之笔。二是日常生活的反思和重建。社会问题和现实困境筑成了长篇小说高地,批判精神和启蒙自觉也塑造了长篇小说的反思品格。一方面,日常生活成为反思的领地,呈现了浮躁喧哗背后的疮痍和创伤;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也作为乌托邦的符码,寓示了拯救和再生产的可能,如《群山之巅》《匿名》《春尽江南》《繁花》《黄雀记》等,既揭示了日常生活的异化真相,又暗示了日常生活的救济之道,重申了日常生活理想。可以预测的是,日常生活时代的长篇小说经典也许正源于此。
[1]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2]鲁迅.论照相之类[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83.
[3]苏童.黄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304.
[4]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M]∥鲁迅序跋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492.
[5]格非.山河入梦[M].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封底.
[6]王蒙.这边风景[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697.
[7]迟子建.每个故事都有回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329.
[8]鲁迅.摩罗诗力说[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7-68.
[9]独应.哀弦篇[M]∥钟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8.
(责任编辑:袁 茹)
2016-07-05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会科学艺术学项目“和谐社会下的陕西艺术价值体系及其战略建构研究”(201028);长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作为大众文化的电视解说的意识形态效果研究”(0929)
关 峰,男,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47.5
A
2096-3262(2017)02-005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