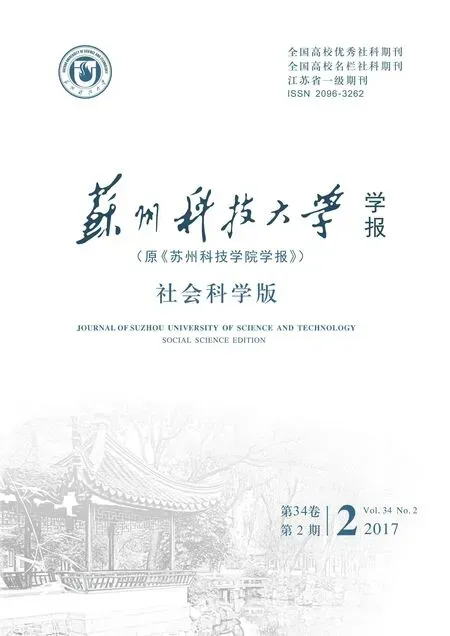《澄斋日记》所见恽毓鼎史论的特点与价值*
舒习龙,黄茹娟
(韩山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澄斋日记》所见恽毓鼎史论的特点与价值*
舒习龙,黄茹娟
(韩山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晚清史官恽毓鼎,久领兰台十九年,博通经史,为著名史学家。由于长年伴驾,恽毓鼎又掌握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信息,具备丰富的史学见解,其史学论述正是其史学思想的集中反映。基于此,以《澄斋日记》为核心史料,尝试对其史论进行分类,并结合恽毓鼎传统士人的心态,分析其史论特点,提炼其史论的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在评述其史论的价值基础上,将恽氏史论置于晚清时代巨变的背景下,客观地衡估其史论的得失。
恽毓鼎;史论;特点;价值
恽毓鼎(1862—1917),晚清著名史官,久领兰台十九年,历任史职,为光绪皇帝近侍,能够常伴圣驾,掌握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信息。其平生嗜史,推崇班固《汉书》,致力于学习陈寿《三国志》作史的义例体法,能洞悉《资治通鉴》本末,以《通鉴》、程朱诸大儒之书、《日知录》等经史为毕生身心性命之学,曾臆想令其八个儿子治八类经史,使“天下学问大宗萃于吾门矣”[1]430,或分为六家,诸子专注六书,使海内名之曰“史学恽家”[1]690。这样一位博通经史又身居清要史馆,生逢晚清乱世之时的史学家,其史学思想必定是十分丰富的,而其史学论述恰是其史学思想的集中反映。然而,揆诸目前对恽毓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个人的政治参与、心态思想及发掘其日记各方价值方面,对其史论思想则缺乏研究。笔者以《澄斋日记》为核心资料,尝试将其史论概括分类,并结合恽毓鼎传统士人的心态,总结其史论特点,从其史论的分布范围、思想根源、基本观念、表现形式及恽毓鼎治史特长等方面进行思考,考察其史论的学术价值与思想价值。研究恽毓鼎史论的特点与价值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恽毓鼎的学术人品,透视晚清士人处于时代大变革之下的心理状态,同时透过恽毓鼎时人评时事的眼光,追溯那些淹没在官修史传中的更为真实的晚清时局变象。
一、恽毓鼎史论分类
恽毓鼎的史学论述集中体现在其著作《澄斋日记》之中,该日记既有对客观历史的评述,又有对史著、史家、史学现象的分析,其评史论事常发新见,约举为三类论之。
(一)古人史事评论
恽氏点评人物以帝王将相为主,如曹操、宋武帝、萧衍、萧道成、杨坚诸帝王,如姚崇、宋璟、王叔文、王伾、王安石、蔡京等权臣;间杂对史家的评论,如刘歆、司马迁、班固、沈约、欧阳修等史学大家。其中尤以光绪卅四年读《通鉴唐纪》对唐朝诸皇帝的评论最丰富,如评唐德宗,“初政极好”,只可惜用人不当,“所用数大臣如常襄、杨炎、乔琳、张涉之类,俱不能初终一节,后遂尽人而疑之。一生猜忌之端,其病根实伏于此(明庄烈帝亦然)”[1]408;评唐穆宗,认为其不仅为主不明,还任用庸才,导致朝政“无不颠倒失宜”[1]411;评唐武宗,认为其“人品虽不纯”,但“其才实不可及”,以其措置泽潞及回鹘事为例,认为武宗“立志坚定,而办法则随机变化以应之”,不愧“行方智圆”四字[1]412;评唐朝亡国之君昭宗,为其抱憾,认为若昭宗承接的是唐懿宗,而非童昏败坏的唐僖宗,则唐朝不至于灭亡,并将昭宗与明思宗作比较,认为“思宗尤与昭宗异”,崇祯初年尚有一片大好形势,只是思宗用人失策,误杀袁崇焕,加速了明亡进程[1]414。从对唐朝诸帝的评点,可以明显看出恽氏重视人才的政治观念,他将唐、明衰败灭亡的大部分原因归咎于君主用人失当。
恽毓鼎所议史事多关于军事政治,诸如交战、养兵、选官、变法等。如其曾与门人吴厚庵交谈三国魏吴交兵地势情境,“厚庵湖北监利人,论三国魏吴交兵情势极明。蜀、吴分荆州,以江之南入吴。荆州门户险要尽失,长江处处可渡,故关侯守荆州,以无险可扼,致吕蒙渡江,无从防御,荆州遂不可守,非谋疏也”[1]402;与长年在关外的友人长少白将军讨论古今西北地区的养兵问题,“余问,以陇外一隅,十六国时并建数国,日从事于干戈,安得如许兵卒,如许粮饷?……其所用皆蒙古及回兵也。以时征调,故不养兵;其人逐水草而无城郭,故不须筹饷”[1]247;读《通鉴》总结唐朝养兵之弊“始于张说之召募壮士不问邑役优为之制”[1]25。在对这些史事的议论中也体现了恽毓鼎丰富的政治经验,如恽毓鼎读《通鉴》讨论唐朝铨选,先是“选司注官”,“唯视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后来裴光庭奏定《循资格》,“无问能否。选满即注,限年蹑级,毋得逾越”[1]25,官员只要在任期间没有犯错误,在吏部考核的时候可以按资历有升无降。此举在唐以后为历代沿用,其弊端是会造成某些官员庸碌无为熬资格,而有才之士可能因资历不到难以进阶,出现官场尸位素餐现象,但其也在促使官吏获得治事经验、限制凭荫入仕的达官子弟的过快升迁、解决选官制度下“员多阙少”矛盾、为官吏铨选构建平稳秩序方面发挥作用。[2]前人对循资格批评较多,恽毓鼎自认为循资注选不可废,但也要兼复汉代征辟之法,用循资注选来杜绝躁进之阶,可见其政治经验丰富。
偶有将人物及史事联系进行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如恽毓鼎评价唐朝“二王八司马”事件,认为“永贞革新”有可取之处:“其辅顺宗,首罢进奉、宫市二弊,起用陆贽、阳城诸贤,皆初政之美者。而夺神策宦官兵权,属之金吾大将军范希朝,尤为卓卓”[1]410,若革新成功,即可避免晚唐宦官乱政的祸害,但是因为改革的领袖人物王叔文、王伾“大抵志大才疏,不免近于狂躁”,不懂得周旋世故,“遂为朝论所嫉”,而后世史家因仍记载,对这一政治事件进行诋毁,恽氏认为“二王”人品“虽有可议,而其所行之政不尽可议也”,即“八司马”也是正人居多,不宜偏颇评论。看《宋名臣言行录》,恽毓鼎评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其性情上“一意执拗,好同恶异,专用一般邪谄小人,流毒当世”,导致后来有恶名,被后人与古代奸邪误国者划为一类,恽氏为王安石平反,认为其人立身处世无可非议,对其变法不可全盘否定[1]177,体现了恽毓鼎历史思想的客观公正之处。
(二)史著、史家、史学本身看法
恽毓鼎治史三十余年,其自省半生学问,唯历史致力最深,所读史著繁多,在其史学评论中有不少对史著、史家及史学本身的看法。
对史著的看法包括:(1)对史书的比较。如对《史记》与《汉书》的比较,对《陈书》与《梁书》的比较,对《明通鉴》与《明纪》的比较,对《明史》《明纪》《宋史》的比较,点评《宋史纪事本末》非胜于谷氏《明史纪事》,以《宋史新编》与《宋史》的对比为例论旧史胜于新史,等等。(2)对史著的褒扬或批判。对史著的褒扬,如对欧阳修《五代史·冯道传》、沈约《宋书》、《宋史》、《明史》的表彰,对王夫之《宋论》、鱼豢《魏略》、柯维骐《宋史外编》、《元史新编》、《正续宏简录》、周济《晋略》的赞赏,其中尤以对《宋书》及《晋略》的褒扬最多,认为“南朝诸史以及唐修晋、齐、周三史,文法皆祖休文”,但“而叙次浓郁工妙,词藻隽雅,皆不及《宋书》”[1]240;认为《晋略》为《史》、《汉》、《三国》后第一书,是真正的史学等[1]333。对史著的批评,如对《通志》尽录前史的批判[1]158,看《元史纪事本末》,点出其书史法不严之处,体现恽氏本人的正统思想,其议论如次:
太子即位,改元天顺。名分既定,统绪亦正,周、怀二王分封已久,安得干之?愚意泰定、天历之际,当书“帝崩,太子即位”,下即以“天顺”纪年,而于文宗之起兵则直书“图帖睦尔反,帝遣某某讨之”,下历书图帖睦尔陷某郡、陷上都,帝不知所终,梁王禅、丞相倒剌沙等死之,图帖睦尔称皇帝。如此叙列,史法始严。[1]93
(3)对史著内容或成书时间的考证。如考证《通鉴》中唐德宗护卫“行幐钉鞋”的典故,考证《水经》的成书时间,认为“《水经》上不逮汉下不及晋初,实魏人纂叙无疑”[1]30。(4)对史著体例的分析与评论。如看《明史》中附有元末忠臣的传记,认为其“用意之深,体例之苦,皆前史所无也”[1]38。
关于史家素养的要求,他认为史家应以实记史,要全面采集史料。以对国史记法的看法为例,恽毓鼎议论如果史家作传,只是根据碑志行状进行铺张点缀,那就难以尽信。他还以批评晚清国史只录公牍,没有依据为反例;以褒扬《通鉴》“温公于名臣奏议多见记录,名为资治,不虚也”[1]334为正例来说明全面采集史料的重要性。恽毓鼎史家素养观念的特色,即是其“史才”观。在日记中,被他称赞具有“史才”的史家有:赞班固为“孟坚史才不减子长,若论详实整密,足资实用,尽有胜子长处。即如此志,探源三代之制,直从富教立论,是何等识力”[1]446;称陈寿为“陈氏俱删去不录,即此可见史才”[1]706;称沈约为“叙次点缀之妙,直到史公,至如孟坚,且当让其出一头地,何论馀子。世徒以文士称休文,不知其实有史才也”[1]242。被他讽刺为“史才不称”的有《南史》著者李延寿,“李延寿通为南北史,自是通人卓识,惜史才不称,凡八史出自当时之手,其中谀颂隐讳之处,亦一律沿袭,不能畅叙而实书之,殊觉不满人意耳”[1]446。恽氏所褒扬者的著史特点是:史著内容详实缜密、史料考察态度严谨、史书体例提纲挈要、序论能“以一朝贯异代”。以对司马光的褒扬为例,恽毓鼎认为唐敬宗时期,“牛李党争”激烈,两党各自谀袒、互相诋毁,导致当时的实录及笔记议论偏私,记载不实,而后人修史没有多加考核,直接“据以立传”,所以是“往往歧出”,但是司马光修《通鉴》的时候,对这一时期的史料“详加考订,择其可信者而从之”。通过褒扬司马光这一严谨的治史态度,恽毓鼎表达了自己对史家素养的看法,认为史家下笔要“精核矜慎,务求公平,疏通证明,斟酌尽善”[1]411,如此才可称史才史识。而对李延寿的批判,则是因为其不能“畅叙而实书之”,沿用了所参考史料的“谀颂隐讳之处”。
恽毓鼎对史学本身的看法,以史学为经世之学,以史书为切实研究之书。他认为,史学的作用在于使后人师古人并从史学中得到益处,在于能使后人经世致用,“近专读《三国志》,其中名臣议论,指陈时弊,至二千年而犹信。其立身处世之道在在可师。史之有益于人如此”[1]335;认为《五经》中《春秋》《尚书》《诗经》皆属于史家,而《诗经》为古代史官采集民间议论,而陈于朝廷,“凡时政之得失,民情之乐苦,风俗之盛衰,皆于诗觇之”,从此论亦可看出,恽氏认为史学本身是时政、民情、风俗的反映。恽氏还认为《国风》相当于《史记》的世家,大小《雅》相当于纪传志,“诗亡而后史法亦失矣。班、范而后,史册专为一家一人之事,史学家更从事于体例考证之间,抑无当矣”[1]596。
(三)读史、治史方法见解
对于读史、治史方法,恽毓鼎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读史要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并且没有必要把史书中的所有人和事都给记住,“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1]24。他还强调“读史须统观全局,熟审其始末先后以定是非,方不致有偏漏”,如果总是计较一事一句,以记诵为能奈,就是程子所说的玩物丧志了。[1]79除了正史之外,恽毓鼎认为还应该看一些补充杂作,“正经正史为用固宏,若作序跋翰札,一副小笔墨,隽情别趣流溢楮墨间,则非多看此种书不能工也,诸史中唯《晋书》、《宋书》、南北史最有益于杂作”[1]239。恽毓鼎在读史书时重视结合历史地图,如他在读《通鉴唐纪》时,为了更好理解唐朝的藩镇形势,就参考了杨守敬的《历代沿革图》,发出“古人左图右书,洵不可少”[1]413的感慨。
恽毓鼎曾以读《汉书》的方法传授弟子苏诲卿,体现了其严谨的治史态度。他认为要按列传、本纪、地理、沟洫、郊祀、刑法、食货、艺文、各序表的顺序读,因为先读列传能开启对《汉书》的兴趣且明白事势,接着看本纪了解大纲,读史志和各表序文了解制度的大概还有政事的得失,进而对《汉书》的精神融会贯通。他还认为,治《汉书》应该“详训诂,正句读,一字不可含糊。讨论事实,必综贯其始末,虽人名地名亦不可忽略”,要对书的言外之意、谋篇布局反复斟酌品味。[1]184他还教导儿子宝惠治史要专一,要明白自己所研究的方向,“盖既治此史,即终身得此史之用,若一切琐琐异同考据,另是一种学问,今可暂置之”[1]583。
恽毓鼎十分重视史志的作用,他认为“作史以作志为最难,读史以读志为最要”[1]137,而且“读史志及通典通考时,只要眼光识得要紧处,洞达治体,灼见本原,应用时自然措施得当。至于名物度数,届时逐处讨论不迟(即如盐务一项,各省制法不同,名称不同,因而办法亦不同,断不能预先一一识记)。学者如作为专门之业,精力工夫并归一处,又当别论。然亦须洞达治体,灼见本原,方为有用之学。否则刻舟求剑,仍无益也”[1]583。
二、恽毓鼎史论特点
恽氏史论零散记载于日记中,爬梳剔抉始能见其精彩意蕴。总括而言,恽氏史论体现出:重宋儒义理之学,秉承正统史观的特点;以史学为经世致用之学,忧朝政于论史,希望借史学治乱兴衰之迹以观照晚清时局;他的论史方法以对比研究见长,最大特色是将西学思想与传统儒学对比,并希望以儒学为内核融贯中西,并发扬儒学;他甚为推崇班固《汉书》,因平生致力于《通鉴》之学而多处对胡注进行考证批驳。
(一) 重宋学义理
恽毓鼎史论最显著的特点是重宋儒义理之学,这也是作为传统士大夫的恽毓鼎的思想根源。观恽氏日记可知,对于宋学的研习,恽毓鼎曾受到其伯父的启发,“伯父勖以为学之要云:宋儒千言万语,莫妙于提醒二字”[1]64。或许是从小接受了教育,或许是因其所敬重的伯父的引导,恽毓鼎终其一生都对宋学一如既往地保持钟爱,其平生嗜好《近思录》《儒门语要》《潜庵先生集》《梦馀录》《思辨录》《理学宗传》《宋元学案》等义理之书,其“拟取宋、元、明诸儒切要语编成一书,名曰《正修要录》”[1]91,并且亲自编撰《励学语》。其最佩服顾亭林、黄梨洲、全谢山,在日记中写自己看《宋元学案》之好处,“可以推究一代治乱得失之迹,可以练达才识、经世,嘉言懿行可师可法,倾群经之沥液,穷义理之旨归”[1]261。
恽毓鼎曾借徐桐之言对清朝盛行的汉学发出了抨击,“今训诂之学盛兴,动斥义理为空虚之说,不知子臣弟友何者是虚”[1]66,甚至认为清史馆修的《儒林传》所记传的儒士为汉学家,所以“诸传草率殊甚,承修诸公不屑置意”[1]104。他认为,“任是博通经史末梢,必以宋儒书为归宿,盖义理之学颠扑不破也”[1]102。
之所以如此推崇宋学,是因为与只知训诂的汉学相比,宋学是经世之学,恽毓鼎认为挽救时局要依靠宋学,用宋学来团结学术人心,“天下最可忧者在人心风俗……向使讲学之风犹盛,宋儒之说大行,人心未漓,气运决不至此”[1]133。他认为,晚清“大局之坏,根于人心,而人心之坏,根于学术”[1]572,是张之洞等人推行新学而导致清朝灭亡的。晚年之后,恽毓鼎一方面试图融入新政权,一方面内心坚定“宋儒之教,尊君权,定民志,最有益于专制政体”[1]459。
(二)驳杂的正统史观
近代以来史家的正统史观呈现出两种趋向:一种是呼吁去除正统论,另一种是坚守儒学正统论,而又随着自身所处的时代及立场出发,自立标准,牵强解释。恽氏的正统史观即属于后者,一方面为有别于宋元以来“是蜀非魏”的习见,故发新见以体现其独识;另一方面,因为满清政权作为其侍奉的雇主,则废华夷之辨的大义,而有意为尊者讳。比如,对大部分史家笔下奉为正统的刘备,恽毓鼎有所嘲讽:“昭烈之称汉中王,其时献帝尚在位也,与魏武之称魏王何以异?南宋以后论者,乃一褒之而一贬之。”[1]634读《通鉴》,恽毓鼎多次认为后汉刘智远父子四年为一朝,是古今所无,“梁汉乃列于正史,最不平之事”,而后汉成一朝的原因又是因为“后人所以推尊南唐以绍土德也”[1]415;但他又认为南唐自称“吴王恪后,来历不明”[1]421,同样不是正统。
恽毓鼎盘点自汉朝以后篡位的人,列举了有功于国的曹操、宋武帝,无功德而倾人国的王莽、萧衍、萧道成、杨坚、徐知浩、石敬瑭,其中最为厌恶石敬瑭,议论其“勾引夷狄,以君父事之,竭中国民力以奉之,遂近贻契丹抄掠残杀之惨,远贻数百年之祸,实不为君”,认为“宋太祖之得国,亦极无道理,因其为开国正统贤君而恕之耳”[1]420,显然其故意忽略了皇太极也是明朝属臣的事实以及满清入关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看王夫之《读通鉴论》,恽毓鼎议论其“论古有深心卓识,无一门面语,如此方许读史”。只是作者生于明清,“两朝兴废之交,种族之见太深,掺入意见,便不尽公平”,不满意于王夫之对满清的偏见。由此可见,恽毓鼎的史论思想中不尽公允。
(三)忧朝政于论史
作为晚清官吏,清廷的命运与恽毓鼎的个人命运息息相关,而作为久领兰台的史官,恽毓鼎对风雨飘摇的晚清时局的忧虑也多在其史论中表现出来,同时,他希望以史学为经世之学,借鉴前代盛衰往事来整顿朝局,挽救危亡,此亦为恽毓鼎史论的一大特点。
恽毓鼎看《宋史纪事》方腊之乱时,发出“群奸满朝,老成谋国之言一不施用,事机屡失,坐致沦亡”的感慨,看书后“愤闷积胸中,夜几不成寐”,其在当天的眉批中写道“他人见此,如谓余代古人担忧,非知我心者也”[1]112。可见,恽毓鼎是以古事而论于今事,为晚清朝堂同样是无人可用、坐失沦亡而担忧。“连日看杨龟山全集卷一、卷二、卷三,皆奏书札子,所言靖康时金寇金盟情事,皆洞中今日之弊,为之掩卷太息”[1]149;听说日俄即将交战,而“须由中国济师”,忧心“亦危局也”,当夜在灯下看《兵考》,议论“兵制之坏,兵力之弱,至宋而极”[1]134;由南北朝人才之思,而联系到“我朝穆庙中兴,所用皆湘皖人,此则间气所钟耳”[1]449;以魏甄琛请罢盐池之禁,而彭城王勰的议论而引出“新进少年,逞其浅见,掠取浮光,动辄议更旧制。一行一改,国家所损实多”[1]461的看法;论王安石变法,认为以当日时势,“谓新法奉行不善则可,责荆公坚僻不虚心则可,谓法度不当更张,国家不当言富强,则不可”,又在议论后备注“戊戌之用康、梁,其情势亦如此”[1]463,表明自己对于变法的正面立场。清亡后,看《阅史郄视》,恽毓鼎追忆清廷旧事慨叹“所言与清末及近年朝局极相似,歧枝架屋,徒为安置私人之地”[1]690,遗恨依然难消。
恽毓鼎醉心诸史,一方面是他知道“时势日迫,事权不属”,认为“唯有随分读书,聊以遣日。如天之福,国事或有转机,尚将执此以往,拨乱世而反之正,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也”[1]149;另一方面是他仍希望当权者能以史为鉴,发挥史学经世致用的价值,他认为与其费心去研究西学不如踏实地研读经典,这是一个史官最朴素的愿望。他认为明代与清代的政治形势是非常相似的,主张学习《明史》经世致用;认为明朝虽然皇帝昏庸,但有人才治国,有宋学支持,而没有衰落,“与褚丈畅论《明史》,亹亹不倦。新学盛行,固富理想,然予终觉旧学深切有味也。有明一代,人才最多,法制最善,是以主昏于上,而政理于下,又士重气节,屡经摧折,曾不少衰”。与晚清今昔对比,“以今日视之,真可悲感”[1]335。论外之意,即希望当权者也能学习明朝在用人和发挥宋学上下功夫。而明朝末年国之将亡,大臣仍贪污腐败,与晚清沉疴也是相似,“三日看《明季北略》一函,末造大局已坏,而当道诸臣贿赂公行,益泄沓不事事。燕雀处堂不知大厦之将倾,国亡而身家与之俱尽,若辈居心真不可解。读竟为之泪下,盖无一字不触余怀也”[1]348。至于这一点,作为虽常伴帝驾,但游离于中枢之外的清要小臣,恽毓鼎也只能论史兴叹。
(四)善于比较评论
由恽氏日记可见恽毓鼎论史所用的最明显的方法是比较评论。如前所述,对史书的比较,如对《史记》与《汉书》,《陈书》与《梁书》,《明通鉴》与《明纪》,《宋史新编》与《宋史》等史书的比较;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比较,如对王安石变法、蔡京变法与戊戌变法的比较,宣统末年对“魏武、宋武、齐神武”与“杨坚、朱温”[1]564等人篡位行为的比较,论外隐含对篡清者的比较等。除此之外,最大的特色是恽毓鼎本人对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
恽毓鼎认为西方的历史与中国历史在某些时期有相似之处,看《西史纲目》感慨“罗马四分五裂,五日不寻干戈,其时正当中国晋宋五胡乱华之日”,“罗马军士立帝之世,武将骄横,废弑拥立皆出其手。一朝不过数帝,每帝各自一姓,与中国五代绝相似”[1]319;他与外国学者铎尔孟交流中西学派,认为中西学者有思想共鸣,“西儒论学宗旨,与中儒不甚悬殊”[1]400;他认为西方人所说的宪法、法律就是中国古代圣人所说的礼,“今世所谓法治国者,古圣名曰礼治国也”[1]678;他认为泰西所主公理,与《春秋》多合者,想与其友人立学会,专意研究经史有用之学,并将《春秋》之理发扬光大,与西方政体相结合,实现“合五洲而受治于《春秋》”[1]281的梦想。
恽毓鼎对西学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晚清时期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中国传统士子逐渐打开眼界,慢慢接触西方思想文化,而恽毓鼎对西学的最早了解是经过报纸,“志先送来新出《译书公会报》……所译西人记载,多有用之书,采录外国报,亦见精审”[1]144;其次是史著、小说,他偶尔看中译西史《海国大政纪》《英法俄德四国志略》《西史纲目》《英史纪事》等,看过西方小说《哥仑波》《忏情记》《鬼山狼侠记》《英孝子火山报仇录》等,后来通过留学门人获得日本书籍;此外,他自己也认识了外国学者铎尔孟,与之交流中西学术,并发展成为好朋友,晚年与梁启超相识,更倾心于其西学研究。
恽毓鼎一方面身体力行学习西学,一方面又在抨击学习西学的留学生,认为是他们导致亡国,“亡国三妖:一东洋留学生,一新军,一资政院谘议局”[1]561。究其根本,是其认为西学思想太过激进,而学习西学者又急于求成地将西方的理论全部搬到中国来实践,最终适得其反。恽毓鼎朴素地希望保持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稳固学术人心,又用西学开新知,将中西完美地兼容,这也是晚清大部分士子的心态。
(五)尊班史而批胡注
恽毓鼎博览众史,在日记中记下他对各史家史著的议论,于史家中对班固最是赞赏,于史著中对《通鉴》最有心得,所以他多处议论班史之长,而对《通鉴》中胡三省的注解,也颇有自己的见地。此亦为其史论一大特点。
与《史记》及其它史著史体的比较中,恽毓鼎更推崇《汉书》,他认为班、马应该并称,“《史记》固卓越古今,若以史体论,絮兴衰治乱之要,详人物政事之全,断以兰台为上”[1]115,又借《汉书评林》之论《汉书》与《史记》比较,肯定自己这一持论[1]117。恽毓鼎读《汉书严助传》,认为《汉书》体例严谨[1]123;读《汉书》诸志,认为“连日读《汉书》诸志,见班氏经世之识,实非寻常史家所及。以后惟《隋书》中《五代志》及《明史》志体大思精,最为闳括切要”[1]137;读《循吏传》,认为班固所列六人,皆以教养为政,“如此方可谓之循”,而后世史家杂入能吏,“失其旨矣”[1]138;读《货殖》《游侠》二传,认为其两序议论纯正,笔力劲厚,“诸传神妙,亦不减太史公”[1]138;读《霍光传》“旁见侧出,带叙于后。深服班氏史体之善”[1]178。对于前人对班史的批判,恽毓鼎在日记中据理力争,由《史》《汉》之《匈奴传》对比,指出“扬马抑班,殊属无谓”[1]113;讽刺郑樵《通志》对《汉书》的诋毁,使得“一瞽引群瞽”[1]137,后世史家也诋毁班史。
在日记中恽毓鼎共有34处提及《资治通鉴》胡注,其中有多处是对胡注的疏失之处提出质疑或进行订正。例如,看《唐纪明宗》评价唐明宗登基典礼,“胡注引徐无党曰:‘释衰服冕,可以见其情诈’”,而恽毓鼎以宣统帝登基礼仪现身说法,认为胡三省不必引徐无党作此注[1]419;看《唐纪闵帝潞王》,“潞王赏薄,军士怨悔,谣曰:‘除去菩萨,扶立生铁’”,胡注“菩萨,闵帝小名”,恽毓鼎则认为军士不至于呼加故君小名,菩萨是仁慈的称谓,正确的注解应该是说闵帝仁弱[1]420;看《陈纪宣帝》,认为胡注因分句错误而误读了文本的意思,从而怀疑宇文孝伯也谗坏乌丸轨,又认为突厥佗钵可汗所言“但使我在南两儿常孝,何忧于贫”,在南两儿应该指周、齐二主,而非胡注所谓“尔伏、步离”[1]456。类似对胡注的批判考证也体现了恽毓鼎本人严谨的治史态度,及其对《通鉴》学的热衷。
三、恽毓鼎史论价值
恽毓鼎本人是一个大藏书家,他博览经史,其对经典、史著的评论具有独到之处,可谓是一种学术观点,其史论为后世学者对这些经典、史著的进一步评价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参考。如恽毓鼎对《汉书》的推崇、对《通鉴》胡注的批驳、对《晋略》的褒扬、对《五代史注》《旧唐书》《旧五代史》的品评、对《通志》的讽议等等,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且透过恽毓鼎史论可窥见其学术人品,可分析其思想特征、心态变化,可以说其史论也是研究恽氏本人的一手史料。
恽毓鼎偶有阅读时人所撰时作,作为专业史官,他对这些著作的评价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可信度,如王闿运《湘军志》较真实地记录了曾国藩所训练的湘军平定太平天国的史实,但成书后受到部分湘军将领的斥责,要求王闿运毁版另写,恽毓鼎却对其进行高度评价,认为其客观真实,“直摩龙门、兰台之垒,为千古不磨之作”[1]258;对慈禧侍女德菱所写的《清宫二年纪》也进行了肯定[1]668,目前大部分学者也认同该书的史料价值。恽毓鼎史论的学术价值还体现在对现今历史文献学、编纂学、考证学等历史研究领域的启示作用。
如历史文献学方面,其史著评论中含有对影宋本《坡门酬唱集》的流落情况的介绍[1]352;对民国初年殿板《御批通鉴辑览》、殿板初印《历代诗馀》的提及[1]362;对《永乐大典》的存佚情况的记录;对《大云山房文稿》抄本和评点的思考等等。关于《永乐大典》,日记中共有两次记载,在光绪二十三年看《永乐大典》,“本系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今存者八百五十四本而已”[1]145;而光绪三十一年(1905),“与笏斋检视《永乐大典》残本。此书本一万二千余册,庚申之变仅存八百余册,庚子翰林院毁于兵火,书亦散失。乱后搜罗,不过二百余册矣。天壤之间只存此数,憾惜久之”[1]284。这些夹杂的感慨或议论对于研究晚清历史文献的留存情况甚有裨益。关于《大云山房文稿》,现有民国八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及民国二十五年七月初版、民国二十七年十月第二版的《国学基本丛书》本和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3],此三版本基本相同,使得学界长期以来对该书版本问题缺乏注意,但恽毓鼎却点出《文稿》中的朱批流传自抄本。有人认为是作者自加,有人认为是读者所评,一直都没有确定,但两种说法应该都不可信。“(文中有自记者,俱低一格标明自记。批本有称子居文云云,其非自加可知,且语气亦不类。初集文俱成于嘉庆以后,其时白本文已卒,不及加评也。)余意圈点或系自加,评语则当时友好知文者所加也。”[1]55恽毓鼎认为,圈点的是作者自加,评语则应该是当时读者所加。恽氏从用语和文体角度分析,别具只眼,对我们更好地利用《文稿》裨益匪浅。
历史编纂学方面,恽毓鼎对《史记》《汉书》等体例的评点、褒扬,对史志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的重点突出,对一些名声不显的史作体例、文法的评价,在丰富历史编纂学的研究范围方面具有学术价值。如恽毓鼎观看薛叔耘的《陈督臣忠勋事实疏》,疏文总共三千四百字,恽氏认为“可为繁矣”,但又觉得“而运实于虚,处处筋节,但觉其精神团结,不觉其长”,认为能够用柳子厚以“洁”字评价《史记》的高度来评价它。[1]143论写题跋认为本朝最厉害的如全谢山、朱竹垞、钱警石诸先生“皆可法”,翁覃溪则“专事考察,不以文字论矣”[1]343。后人可根据恽毓鼎的评价对这些史作的编纂特色或史家的文法特征进行进一步考察。
考证学方面,包括对史事真伪、史著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的考证。史事真伪主要是对《通鉴》胡注的错谬处进行考证,如《通鉴魏纪》中,“蜀后主东迁,诸臣无从行者”,胡三省注为“姜维既死,张翼、廖化、董厥必亦死于乱军中矣”,恽毓鼎检看《蜀志》进行考证,发现“张翼死于乱军;廖化迁洛阳,道病卒;董厥从降,屡历显职”,认为胡氏是“以意度之”“殊为可怪”[1]671。恽毓鼎的考证为《通鉴》胡注的校勘提供参考。关于史著的考证,如对定州王氏汇刻的《畿辅丛书》中灵寿傅维鳞所著的《明书》的学术价值进行考证,认为其是丛书中的“大宗”,其“本纪、表、志、世家、列传共一百七十一卷,较《明史》减十之五”,“纂于康熙时,当《明史》稿未出以前,盛行于世,乾隆后乃无人及之” ,曾在陆清献《三鱼堂日记》中有记载,流传到恽毓鼎生活的时代,已经在书坊间买不到了,“盖几至湮没矣”。光绪三十四年(1908),恽毓鼎得到这部书后“睹而大快。拟每日看数卷”,称赞此书“卷帙不繁,当易毕业”,只是在崇祯帝一朝“君臣事俱略,当是避祸,不敢叙耳”[1]373。恽毓鼎对其学术价值的肯定,可以作为今人研究《明书》的参考。
恽毓鼎曾在日记中披露清朝官修史书是按照上位者的意愿来修撰的,并不是完全客观真实的,因此他在日记中真实地记录下许多他曾经历过的历史事件的感受,因为同情光绪皇帝,他在民国初年撰写了《崇陵传信录》,揭开了许多被《清史稿》等官史所淹没的真相。恽毓鼎对光绪皇帝的评价,虽带有感念故君的主观色彩,但也为后人刻画了光绪皇帝更为生动全面的形象,让人明晓其不只是受制于人的傀儡,也是一位忧心国民的仁君,尤其是劝慰激进维新人士调和与顽固守旧大臣关系的举动,更体现了光绪帝心性的坚韧与细腻。此外,恽毓鼎对民国初年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也有颇多论述,这也是其史料价值之一。
恽毓鼎经常邀友纵谈经史、时事,在交流中也多表达出亡国之思,读恽氏史论亦可窥见晚清大变革下的士人心理。在维新变法之时,一方面恽毓鼎为裁撤冗官,焕新朝政而喝彩,另一方面又为变法太过激进,与友人谈论“乱将作矣”,“史馆、翰林院皆在当裁之列”,为自己的前途感到惴惴不安,或哀叹“吾奚适归”,或轻嘲“则无官一身轻”[1]161,体现了新旧激变中中小官吏矛盾茫然的心理。在清末新政时,听闻废科举,科班出身的恽毓鼎本意上是赞同的,认为“科举在今日诚可罢”,但他也担忧各省学堂没有完全成立,从前的奏定章程还不妥善,必须要重加订定,才可以培植人才,不然在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就废除科举,“恐十年之后圣经贤传束之高阁,中国文教息灭,天下无一通品矣”[1]276。在恽氏看来,科举作为选拔人才的手段可以被代替,但传统文教的精髓不能丢失,在变革中若否定传统礼教,便是触及类似于恽毓鼎等传统士人的底线,分析其史论即可推测晚清士人面对科举大变革下的普遍心迹。
四、余 论
通过对恽毓鼎史论特点的分析,可以发现恽毓鼎治史态度严谨,堪为史家楷模,但其史学思想中具有进步与落后的两面性。一方面,恽毓鼎思想中以史学为经世致用之实学、忧朝政于论史,希望借史学鉴明历代治乱盛衰之功用来挽救清末败象的特点,顺应了晚清史学的发展方向,与同时代的著名史家郭嵩焘、李慈铭、王闿运等人的史论思想相合,这是其进步之处,此外,其所坚持的学术人心、用人之论不失为整治晚清、民国时代变迁之时出现的社会乱象的救时良方。另一方面,恽毓鼎虽然主动接触西学思想,但基于传统士大夫的心理,其思想中坚守宋儒义理、秉承正统观念的特点,决定了其思想的保守性,直至清廷覆灭,恽毓鼎仍坚信专制政体,反对共和制度,以致民国初期,他加入孔道会,参与袁世凯复辟活动。从恽毓鼎的史论中可以折射出:处在中西思想激荡中被迫接触西学的传统文人士子,忧愤于民族危亡,试图融西学于中学以救时,却无法阻挡政权更替,遭遇西学不仅无法解决社会乱象、更是直接导致传统文教断裂的思想破产,继而无奈地龟缩回其固有价值观念,以晚清遗老的身份固步自封。
[1]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2]邓小南.北宋的循资原则及其普遍作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2):40-50.
[3]马延炜.再论《恽毓鼎澄斋日记》的史料价值:从学术文化史的角度[J].社会科学战线,2008(11):139-141.
(责任编辑:苏 南)
2016-11-04
舒习龙,男,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 黄茹娟,女,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学生。
K092.52
A
2096-3262(2017)02-008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