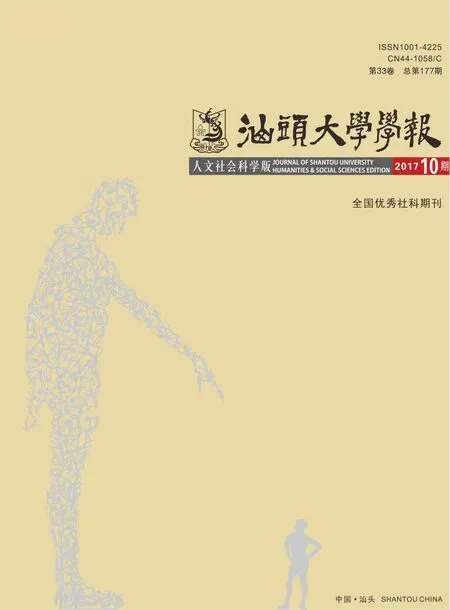判断与创造
——论托马斯·阿奎那的真理观
付 悦,陈高华
(1.南开大学哲学院,天津 300350;2.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部哲学系,辽宁 大连 116024)
判断与创造
——论托马斯·阿奎那的真理观
付 悦1,陈高华2
(1.南开大学哲学院,天津 300350;2.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部哲学系,辽宁 大连 116024)
托马斯·阿奎那并没把真理等同于实体意义上的存在者,而是阐释了真理的处境:真理既是在理智中又在物中,但首先在于理智中。它们分别对应两种涉及理智的活动——判断活动和创造活动。理智作为判断者,使得作为主词的被理解的存在者及其作为谓词的与之相似的形式的一致得以可能;理智也暗示了创造者与存在者的关系,使得存在者是真实的。这些解释最终使得托马斯融合了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的真理观。
托马斯·阿奎那;真理;判断;创造;理智
托马斯·阿奎那不仅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也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继承者。随着12世纪阿拉伯哲学家阿威罗伊等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译介,托马斯开始吸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并将之与基督教学说相结合起来。然而亚里士多德与基督教的真理观终究不同。就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而言,真理与存在者相关;就基督教学说而言,真理又与上帝相关。那么,托马斯如何协调这两种不同背景的真理观?易言之,在托马斯那里,真理与存在以及真理与上帝之间到底具有什么关系?本文以托马斯对真理的两种处境的论述为视角,将理智中的真理和物中的真理分别与判断和制造活动对应,以约翰·威佩的解释为基础,阐明托马斯如何融合了两种不同的真理观。
一、真理的划分方式
托马斯在《箴言》《论真理》《驳异大全》以及《神学大全》等诸多文本中都或多或少地探讨了两种处境中的真理——理智中(in intelliectu)的真理和物中(in rebus)的真理。晚期经院哲学家将这两种处境中的真理划分为判断的真理或逻辑上的真理以及本体论的真理。当代研究者也大都在这种划分的基础上,追溯托马斯真理观的来源。例如,有学者将前者视为托马斯对亚里士多德-阿威罗伊传统的继承,将后者视为对普洛克罗-奥古斯丁-阿威森那传统的继承。[1-2]不仅如此,现代研究者更详细地论述了这种区分本身。例如,彼得森(John Peterson)将理智中的真理看作理智(或心灵)符合于存在者的实在论真理,将物中的真理看作物(或存在者)符合于理智(或心灵)的理念论真理,并且表明,物中的真理包括存在者的真理、本性的或人造物的真理以及伦理的真理等诸多方面。[3]89-89然而,就托马斯的文本而言,这种划分方式既不符合托马斯对真理问题的诸多规定,更没有突出托马斯本人的问题意识以及其与其他哲人在真理观上的差异。尽管可以在实在论者托马斯那里找到真理与物或者存在者的关系,但采用托马斯本人提及的“理智中的真理”和“物中的真理”的划分显然更为贴切。因为,对于诸多存在者来说,托马斯承认某种发生在理智中的判断的真理,而并不承认在探讨诸“存在者之所是”的本体论维度上具有什么真理的本质或实体,进而有某种“作为本体的真理”。托马斯的真理并不是回答了真理之所是,进而给出真理的某种属性;而是说,托马斯的“物中的真理”只是涉及了谓词“真实”和存在者之间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在严格的意义上,托马斯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何为“真理”之所是?因为对于托马斯而言,真理并不是独立于理智外的实体或存在者,也不是内在于这些存在者之中的属性。
另一方面,托马斯之所以从这两种处境来探讨真理的问题,不仅仅出于其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等以往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也因为托马斯在其中发现了一些无法解释的问题。在托马斯看来,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奥古斯丁在对真理的问题上都存在一定的误解,他们都认为真理是在物中的,进而将真理作为物的性质,甚至将真理等同于存在物。在不同的文本中亚里士多德对真理的态度不同,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承认“物存在与否”是真的标准,进而认为真是存在于物中的,而在其他文本中,亚里士多德又认为凡是真实的都是由于真理而为真的,似乎确立了某个实体——真理(verum);而对奥古斯丁来说,真理是“是其所是”的东西。[4]这样一来似乎将真理当作了某种具有本质的实体,进而使得真理在物中,成为物的本质。对于这二者而言,托马斯认为,尽管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都叙述了一种关于存在者或关于物的真,但这并不能说明真理作为在物中的属性或偶性。与之相反,托马斯在论述真理时更强调“理智”的作用。他认为,无论是奥古斯丁还是亚里士多德的真理观都有一定的问题。前者将真理的东西等同于感觉认识到的东西,进而完全排除了我们的理智概念。后者则在某些文本中保证了真理实体特性的优先性。但是在诸如“健康”这种特性方面,其并不优先地存在于“医药”或“动物”这些实体之中。相反,实体的存在才有可能导致“健康”的产生。
尽管不能够为真理提供一种本质上的定义,进而宣称真理的本质,但是托马斯能够为其提供一种解释:即他能够回答真理的处所或所在。在这一方面,托马斯严格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真理的另一个描述。亚里士多德认为,“真假并不是存在于物之中,而是存在于理智之中”。托马斯深受这一解释影响,他进而宣称“既然真理是就其同所理解的物相一致而言而存在于理智之中的,真理的方面也就必定从理智过渡到所理解的物,以至于所理解的物就其同理智具有某种关系而言,也被说成是真的。”[4]不难看出,按照以往学者的划分方式来看,托马斯一方面反驳了奥古斯丁和亚里士多德本体论的真理观,另一方面也没有彻底排斥对于本体论的真理观的批判,而是将其称之为“真实的物中的真理”。而且托马斯保证了“理智上的真”相对于它的优先地位。
二、真理的两种处境
(一)理智中的真理
既然托马斯提出真理首先在理智中,那么理智中的活动则必然与理智中的真理对应。而在托马斯看来,理智涉及两个层面的操作,其一是理智理解了不可分的物之所是;其二是理智通过形成肯定或否定的命题从而进行组合或分离的思维活动。而且,前者能够揭示出物的实质(quidditas);后者涉及到了存在者。前者不必通过命题来认识物之所是或物的本质;后者通过形成肯定和否定的命题获得真理。(Super De Trinitate.pars 3 q.5 a.3 co.1)那么,理智中的真理与哪种操作活动相关?托马斯认为第二种操作活动和理智中的真理相关。在《论存在者与本质》中,存在者的第二种含义就是真理。就此而言,任何可以构成肯定命题的都可以说是存在者。[5]因此可以说,这种理智活动中的真理就等同于理智之中的第二种操作——形成肯定的命题的活动。或者我们可以借晚期经院哲学的术语,将之称作“判断”活动。也即是说,这种理智中的真理体现在命题中的主词和谓词之间肯定的结合,显现于主词和谓词的一致上。
托马斯多次谈及真理是否只是理智中的分离与结合,或者说真理本身是否只包括判断活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真理仅仅在理智中,而且仅是判断活动。“……严格地讲,真理存在于进行组合和区分的理智之中……不是存在于认识‘认识某物是其所是’的理智中。”因此,在狭义上,托马斯表明其所说的“理智中的真理”,其所提及的“理智和被理解的物的一致”就是指命题上的主词和谓词的一致。这一方面因为,只有通过判断才能够产生真理,当理智应用到命题之中的时候,要么组合主词表示物和谓词表示物的形式,要么分离二者。而当理智进行组合时,或者说理智判断某物符合其所认识的物的真理的形式的时候,我们就说理智首先就认识了且表达了某物的真理(De veritate.q.1 a.3)。由此,理智中的真理呈现出了作为认知的判断活动。理智作为认知者,而存在者或物作为被认知者,二者在理智中以命题的方式达成的组合就是理智中的真理。也即是说,理智中的真理暗含着判断活动,判断的主体是理智,而判断的对象,也即在命题中充当主词的东西就是可理解的存在者或物。
那么,既然命题的主词是存在者或物,也就不能将此种理智中的一致与非存在者关联起来。进而言之,真理和存在者是可以互换的词项。如上所言,托马斯将存在者的第二种含义看作真理。按照此种方式,任何可以构成肯定命题的都可以说是存在者。在此种定义下,真理的意思并不是说在实体上等于存在者,即二者的本质相同。而是说,在判断真理或理智中的真理所构成的命题中,主词必须是存在者而不是非存在者。由此,在这种真理所构成的关系形成的命题中,我们谓述的对象就必须是存在者。但是这种存在者不一定实在。这也是存在者的两层含义的意义所在。另一方面,托马斯认为,真理和存在者分别在物中和理智中互相转换。不仅仅真理是在物中和理智之中,存在者也分别存在于物中和理智之中。只不过,真理优先地存在于理智中;存在者优先存在于物中。存在于物中的真理依据实体而与存在者互换;而存在于理智中的真理作为显见者(manifetativum)和被显见者(manifestato)而互换。[4]
在理智的第一种活动中,理智只是将作为主词的被理解的存在者和作为谓词的形式组合起来,而没有提供存在者和其形式本身。那么,具体的被理解的存在者和抽象的形式来自哪里呢?对于具体的、实在的存在者来说,这必定是来自人的感觉。而对于形式而言这就体现在理智的第一种操作活动中。理智中不仅仅有判断活动这种操作,同时也通过理智对不可分的物之所是进行理解。我们称理智中的这种操作为理解活动,这种理解把握到了这种物或存在者的本质。而这一活动对于理智来说就是为理智的第二种活动中的命题提供了作为谓词的形式。而这个形式也就是理智对其自身提供的某种与外在之物的相似形式。与理智中的判断活动不同,理智的第一种活动把握到了外在物的形式,并将之纳入理智中,成为有待组合的半成品,成为真理得以形成的一个条件。因此,这种操作活动本身不能够称为真理,因此,“理智虽然能够认识它自己同可理解的物的一致性,却不能够通过认识一件物之‘是其所是’认识到它”。[4]
(二)物中的真理
托马斯首先确立了真实在理智中的优先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真理只存在于理智中,而是说,真实同时次要地处于其它处境中。“真实首先是存在于理智之中,其次是由于其作为物的本原而相关于理智而存在事物中。”也即是说,真实次要地存在于物或存在者中,因而这种真实也被他称作“物中的真实”。
具体而言,托马斯表明“真实的方面必定从理智过渡到所理解的事物,也至于所理解的事物究其同理智有某种关系而言,也被说成真实的”。也就是说,物中的真实能够使得所有的存在者或物都可以归结为“作为存在者的x是真的”这样的表述或命题。恰恰在这种意义上,“真实在本原上是在理智之中的,其次是在物中的,这是依据真实与理智的关系以及与真实与本原的关系。”[4]真实与理智的关系以及真实与本原的关系使得真理处于物中。但托马斯并没有明确地定义这两种关系是什么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因而在以往的学者中产生了各种不同解释。例如,在物中的真理或符合于理智的真理实际上体现了具体而特殊的存在者。这种存在例证了上帝的心灵(理智)中的理念或模型。[3]106又如,物中的真理首先意味着存在者对于人类理智的可知性和可接受性。[6]
实际上,物中的真理既非例证上帝的理智,也非人类理智的可知性,而是指向了理智的造物。如果按照上文存在于理智中的真实体现了判断活动,那么物中的真实则部分地体现了理智的另一种活动——创造活动。尽管托马斯表明,物中的真理表明了我们所理解的物与理智自身之间的某种关系,但是他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这种关系是什么,转而分析了理智和被理解的物之间关系的两种具体情况。对于某一物来说,要么是物的本质与理智相关;要么则是物的偶性与理智相关。我们称前者是本质相关性,后者是偶性相关性。本质相关性是在理智创造或生成某物的基础上;偶性相关性是在理智认识某物的基础上。因为对于前者而言,创造物的原因——理智是不可变的,而对于凭借理智来认识这个物来说,只要理智具备认识能力,任何理智都可以认识某物。前者表示的是创造和被造的关系;后者体现的是认识和被认识的关系。
对于创造万物的上帝来说,托马斯的这种区分似乎并不必要,因为上帝即是一切作为被造物的存在者的创造或生成者,同时也是一切存在者的认识者,上帝有能力认识一切物、一切存在者。而对于人造物而言,这种区分显得十分重要。因为基督教的一神论即上帝的唯一性,我们不可能找到第二个上帝的理智偶性地与物关联起来。而对于由诸多个人组成的人类而言,某个具体的人A1或某人类A的理智创造了物M,而由于人类具有认识物M的能力,因此没有创造物M的人,例如A3、B或C乃至其它任何人也可以认识物M。这一点用托马斯举出的例子也可说明,“正如我们说一栋房子从本质上相关于建筑师的理智,而偶然地相关于它并不依赖的理智。”[4]对于创造这栋具体的房子的建筑师而言,他的理智自然可以说是在本质上与这栋房子相关或者说他的理智与房子的本质相关,如果没有他的理智,就没有这栋房子。
而在对存在者或物的探讨中,托马斯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探讨的对象是“存在者之所是”或“存在者的本质”,而非存在者的偶性。这暗示说,我们所探讨的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认识物或存在者,而是被创造意义上的存在者。在理智和被造者之间有着一种必然的关联。这种关联可以被称作“真理”。我们将这种真理称作“物中的真理”,因为物是被理智真理地创造了的。因此,这种真理虽然也表明某种关系,但是它不同于理智中的真理。一方面,在其所构成的命题的表现形式上,理智中的真理表述为“[存在者]A是[与之相似的形式]A’”,而物中的真理表述为“[存在者]A是真理的”。“真理的”可以作为确定的谓词来谓述所有存在者。
另一方面,如上所言,托马斯言及物中真理的依据时,提到了真理与“本原”的关系。根据托马斯所举的例子,这个本原实际上就是指作为创造者的“理智”。因为“每件物如果就其相关于它所依赖的理智而言,便可以说是绝对地真了”。人造物、语词、自然物都绝对地可被谓述为真。那为何托马斯在上文中不直接用“本原”代替“理智”,将两种真理都看作是“理智”的结果呢?这实际上恰恰显露出不同处境中的真理的第二种区别。就理智中的真理而言,理智只是为主词和谓词的一致提供场合,并不摄入真理所要求的这种一致关系本身。真正的一致关系是存在者及其形式。而对于物中的真理而言,理智本身就是这种关系的一端。理智作为创造者和作为被创造者物或存在者之间产生了关联。当我们用“真理的”这个术语去谓述存在物时,我们实际是将此存在物作为某种被造物与创造它的理智关联起来了,因此,命题“[存在者]A是真理的”,也就等同于“[存在者]A是被理智创造的”。
那么,托马斯为何反复强调理智中的真理是首要的,进而使得“事物由于理智的真理而被称作真理的”。[4]约翰·威佩所提出的理智中的第二判断的解释给出了某种思路。他认为,在理智中不仅仅有如托马斯所描述的主词和谓词的组合的判断,也随之有一种新的判断。这种新的判断立足于第一种判断并将其与某种事态相一致,因而他称之为第二判断。例如,在第一种判断“苏格拉底是人”必须有某种实在中的事态与之一致。他认为这种观点符合托马斯对第一判断的反思,尤其是体现在托马斯对《形而上学》的评论中。在其中,托马斯认为根据理智中的第二种操作,即第一判断,理智不仅具有了被理解事物的相似性而且通过对这个相似性的认识和判断而反思。[7]尽管威佩提出了第一判断所产生的结果,但未阐明这种结果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表明其如何体现在命题中。而如威佩所述,托马斯对相似性做出反思,但他所要论证的是对第一判断命题的反思,而非对相似性本身的反思。其所引述的部分不能证明他所要强调的第二判断。尽管如此,不能否认这种第二位的或次要的判断。这种对判断的反思是体现在真理的第二种处境中的,也即是说,威佩所提出的第二判断是体现在“真实的”作为谓词的这一命题形式中的。对于这一命题而言,无论是作为第一判断的命题还是理智中的相似性都可以用“真实的”来谓述。这是由于,根据物中的真理所体现出的创造和被创造关系,无论是这种相似性和组合而成的命题都是理智的操作活动的结果,都是由理智所创造的。
三、作为真理本身的上帝
托马斯指出了真理的两种处境:真理在理智中,进而在物中。但如果我们将这种理解置入基督教哲学上帝与真理的关系的背景中来考察的话,则会发现其中矛盾之处。在基督教传统中,上帝就是真理,并化身耶稣这个历史人物来到人们中间,由此形成了一种由上帝来启示人类的启示神学的真理观(《圣经·约翰福音》17:4)。在这种观点中,真理是绝对、独一的实体——上帝。托马斯继承了这种基督教的观点,认为“上帝自身即是真理”(I Contra Gentiles.cap.60)。但如上所言,他也认为真理在上帝的造物中,在诸多存在者那里。如果说,这两种真理观分别代表了基督教传统和亚里士多德传统,那么,如何融合这两种真理观?
威佩借助蒙塔涅对托马斯的“类比的谓词”概念,给出了一种解释。他首先引述了蒙塔涅对托马斯“类比”概念的划分:第一种是只依据意向或意义上的次序,而不依据存在者的次序的类比,例如“健康”。尽管它根据其先天性和后天性类比谓述不同的存在者,但因为这种谓述必须由被类比的东西(例如“动物”)才能够实现,因而其只是意向或意义上的;第二种是只依据存在者的,而不依据意向或意义的次序的类比。这是一种单义的类比,两个类比的对象分有一个语义但具有不同的实存。例如,“天上的”和“地上的”实体。第三种是既依据存在者也依据意向的次序的类比,这种类比实际上指的就是实体与偶性关系。在此意义上,他认为,真理作为一个谓词在第三种类比含义上谓述上帝和存在者,进而分别将这种理论可以应用到理智中的真理和物中的真理上。[1]
尽管威佩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但并不能充分论证真理谓词能够分别且内在地谓述作为实体的上帝和作为偶性的被造者。而且威佩所得出的结论易产生误解。威佩认为真理内在于存在者中。但实际上,如上所言,托马斯认为真理就其严格意义而言只内在于理智中。如此一来,威佩违背了托马斯的原意。
如果我们从真理的两种处境看对第三种类比的这两条解释,则会发现这种类比关系所强调的两方面分别对应于判断活动和制造活动。蒙塔涅的第三种谓词类比关系是说:一方面,就存在者的次序而言,上帝这个永恒实体及其下涵盖的诸存在者具有同样的谓述——“真理”。我们既可以说上帝是真理,也可以说存在者是真理。另一方面,就意向或意义的次序而言,上帝和存在者都分有了这个谓词,上帝依赖其存在本身而使得真理完满地内在于其中;而存在者依据被造物的大和小使得真理或多或少存在于诸存在者之中。但这种谓词只是就意义而非实存而言的。
就前者而言,恰恰是托马斯对“物中的真理”的规定暗示了“存在者是真理”这样的判断。而在这个判断中,作为主词的存在者是上帝的被造物。而这种被造物的存在暗含着制造它们的上帝,因此我们通过“存在者是真理”这样的论述可以类比地得出上帝等同于真理。这种类比关系就依照于存在者与上帝之间的次序。
对于后者而言,托马斯的“理智中的真理”指的是主词和谓词之间的符合关系。真理是理智操作的结果,而理智没有通过更高的东西而只是凭借上帝自身就具有了神性;因此真理是关于上帝自身的,是上帝的本质。(I Contra Gentiles.cap.60)对于上帝来说,其内在地、先天地具有“真理”的属性。相比之下,理智通过对存在者的谓词和主词进行综合的过程,就必须要涉及到来自于感觉的经验对象与之形式之间的符合关系,因而其存在者在经验上具有“真理”的含义。因此,可以说,理智中的真理对应了意义或意向的次序。
从类比概念出发,我们最终可以看到作为真理的上帝和两种处境或两种活动中的真理的关系,进而在这个意义上将托马斯的基督教传统中的真理观和亚里士多德的真理观结合起来。
四、余 论
托马斯探讨了真理的两种处境:理智中的真理和物中的真理。这两种处境表明了理智的判断活动以及创造活动。在理智的判断活动中,真理联系主词和谓词,最终形成了命题。在创造活动中,真理通过“是真理的”这个谓词谓述存在者,使得存在者分有了作为创造者上帝的真理。但是仍有五个问题仍未解决:其一,如果说物中的真理体现出来的是理智的创造活动,那么这种活动是在理智之中还是在理智之外?如果这种活动是内在于理智的,那么其所造成的结果,无论是人造物还是自然世界都只是理智内的,由此走向一种极端的观念论。其二,托马斯承认在感觉中也有某种意义上的真理,但存在的方式并不与在理智中的方式相同,真理作为理智活动的结果存在于感觉中。感觉中的真理与物中的真理是什么关系,这两种说法是否一致?其三,虽然可以依循威佩的思路,借助“类比”概念论证上帝与不同处境的真理之间的关系。但是前两种类比概念是否与真理有关?其四,托马斯也曾按理智中的真理和言说的真理这种区分探求这二者是何种关系,为何在与理智中的真理相对之物中的真理中也能够得出被言说的命题形式?其五,“真理”可不可能是存在者,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则不得不再次区分两种维度的真理。以上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索。
[1]Wippel,John F.Truth in Thomas Aquinas I[J].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1989,43(2):295-305.
[2]张宪.依傍理性走向对神的信仰——托马斯·阿奎那真理论的探讨[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67-72.
[3]John Peterson.Aquina:A New Introduction[M].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08.
[4]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一卷[M].段德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97-317.
[5]托马斯·阿奎那.论存在者与本质[M].段德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5.
[6]Elders L.The Metaphysics ofBeing ofSt.Thomas Aquinas: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M].Bosto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1992:105.
[7]Wippel,John F.Truth in Thomas Aquinas II[J].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1990,43(2):562-563.
B503.21
A
1001-4225(2017)10-0081-06
2016-10-18
付 悦(1992-),男,天津人,南开大学哲学院硕士研究生。
陈高华(1980-),男,江西永新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部哲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资助项目“阿伦特思想视域下的马克思研究”(13CkS03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经典教育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DUT16RW101)
(责任编辑:汪小珍)
——论胡好对逻辑谓词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