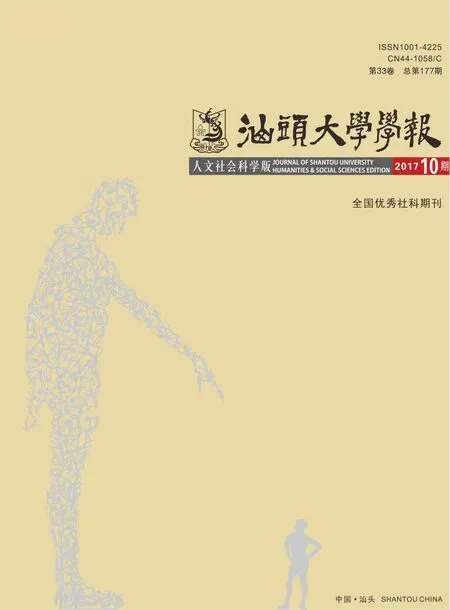责任分配视野下的归责体系重构
陈文昊
(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84)
责任分配视野下的归责体系重构
陈文昊
(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84)
归因和归责的区分必要性不在于事实与规范的二分,而是归责层面主要解决责任分配问题。责任分配问题在刑法中具有合理根据,对此方法论整体主义、结果归责理论、被害人教义学都可以提供理由。责任分配原则在刑法体系内主要应对介入因素问题以及共犯问题的处理。在行为人自己介入过错行为的问题上,如果行为人之外的人不存在过错,就不能因为行为人自己的过错导致行为人的责任减轻或免除。在介入他人过错场合的归责,“引起型归责”与“义务型归责”中行为人的责任并不能得到减损,而在其他场合,介入因素的可预见性、介入行为的过错程度、作用大小都是责任分配中应当考量的要素。
归责;责任分配;介入因素;重构
一、刑法归责层面所需解决的问题
现代各国刑法理论中的因果关系体系,基本上确立了区分“归因”与“归责”两个阶段的原则,这显然是受到了英美法系“双层次因果关系”的影响。在英美刑法理论中,事实因果(factual cause;cause-in-fact)与法律因果(legal cause;cause-in-law)被分别视为事实与价值的判定。因此,一般认为,归因与归责之间的划分,是基于一种必须对事实上的或自然科学上的因果关系与法律上的可归责性进行区分的固有信念而得出的结论。
然而,这样的结论却是值得反思的。一方面,为何需要区分归因和归责?这一问题在侵权法当中可以得到明确的回答,以车祸为例,被害人身体健康受侵害,是否因加害人追撞造成车祸所发生,属于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问题;而被害人支出的医药费、收入减少、住院期间加重财物被盗等损失是否因其身体健康被侵害所致,则属于责任范围因果关系的问题。[1]可以说,侵权法当中的归责理论主要是起到了限缩处罚范围的作用,避免责任范围无穷尽地扩张。但是,在刑法领域,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刑法所关注的并非法律关系的调整,而是直接的法益侵害客观事实。还是以车祸为例,在发生车祸以后,刑法关注的仅包括车祸当时所造成的法益侵害后果,至于被害人支出的医药费、收入减少、住院期间加重财物负担等问题,都不在刑法的视阈之内调整。既然如此,在刑法领域主张归责理论的意义体现在何处呢?
另一方面,归因与归责能否区分开?诚然,从康德所主张的理想状态来看,事实与价值是可以进行二元划分的。正是基于此,传统理论也将条件公式作为归因判断的代表,将其视为纯粹的事实判定;而归责则是一套价值判断体系,需要运用一定程度的政策衡量。但事实上,这一区分只不过是一种理想状态,尤其涉及到具体问题当中,即使是条件公式,在适用上也不可能完全价值无涉。例如,在“卡车超车案”①卡车司机以0.75米的距离违规超越被害人的自行车,因而违反了交通规则中1.5米的安全距离。超车的过程中,醉酒的被害人从自行车倒下,被卡车轧死。后来查明,即使保持1.5米的安全距离,仍有可能发生危害结果。当中,采用“被害人被轧死”这一抽象结果表述,还是采用“被害人被距离0.75米的卡车轧死”这一具体结果表述,在运用条件说进行判定的过程中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对此,劳东燕教授也指出:“归因是归责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与归责并列的独立因素”[2]。
由此可见,归因与归责的区分并非完全立足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相反,价值与规范论上的判断是贯穿整套责任体系当中的。但是,在现行德日刑法理论对因果关系的判定中,都是按照归因和归责两个步骤的范式分别进行。例如,日本刑法理论根据相当因果关系判断与相当性判断两个阶段展开,而德国理论中则是先运用合法则条件说,而后运用客观归责理论进行判定。那么,在德日刑法中,区分归因与归责的做法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分别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其实,如果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德日刑法因果关系判断中的归责阶段均涉及责任分配的问题。例如,相当性理论中对于介入因素大小的判断,以及客观归责理论中对于“参与他人故意的自危”“同意他人造成的危险”以及“第三人责任范围”的考察本质上都是在考察他人行为对因果认定造成的影响。
因此,在归因阶段检视行为人自身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联,而在归责层面考察责任的分配问题,两个阶段共同构成了刑法中因果关系的体系;或者可以说:归因阶段解决质的问题,而归责阶段解决量的问题。毫无疑问,在两个步骤中,由于归责层面触及了利益法学的核心,因此不仅具有更高的可塑性与价值渗透,而且在整个因果关系理论中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实际上,责任分配的原理在民法领域发展得已经相当成熟,说到底,民法体系本身就是一套利益衡量机制;而在刑法中,可能因为刑法是一门更加偏重于事实而非价值的学科,责任分配理论长期被学者忽视。但是,随着近年来被害人教义学的发展,被害人过错对行为人定性的减轻作用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这使得责任分配的思想在刑法学当中开始萌芽。
二、责任分配原则之于刑法领域的原理
他人的过错,尤其是被害人的过错,为何会导致行为人责任的减轻呢?即使在侵权法中,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并非不言自明。对此,预防必要说认为,若人人都能尽到自己最大的义务,则可以避免一些损害的发生,若被害人没有尽到这种义务,就使得获得的赔偿数额减少,这样就能对于预防损害起到良好的效果。公平正义说认为,被害人违反了诚实守信原则,其行为构成损害发生的部分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使被害人获得完全赔偿是不符合公平正义要求的。效率说认为,因被害人过错而减少赔偿额,可以促进其采取合理措施,防止损失的产生和扩大,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保护加害人说认为,混合过错中,被害人需要通过加害人填平的损失减少。[3]
显然,侵权法中的责任分配原则是围绕公平原则与诚实守信原则这两大基石展开的。但是在刑法中,只能另辟蹊径,从其他的进路进行解释:
首先,责任分配原则的机理可以从方法论整体主义之上找寻依据。事实上,在任何国家与时代,无论如何强调个体权益的保障,法律归根结底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作为单纯的个体而存在,而是以社会性的形式立足于世,因此必须要在社会性的人的层面上进行理解。[4]12个体的行为在违法的领域关系到的是人类以及社会上每个人相互尊重的请求。[5]正如雅各布斯所指出的,法律不是一堵放置在利益周围的保护墙,相反,法律是人的关系的结构。[6]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应该将社会现象放在自主的、宏观的分析层次上加以研究,更进一步地说,社会整体本身才是历史个体。因此,从社会整体即整个社会的制度、组织等非个体关系、事实因素出发去说明社会现象才是正确的分析进路。例如,从方法论整体主义出发,在因果关系的问题上,单纯地从行为人的角度考察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链条其实是割裂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以“条件说”为核心建立的因果律本身是存在问题的。可以做这样的归纳,在因果关系的考察上,如果说方法论个体主义提出的问题是“他是不是负责”;而方法论集体主义提出的问题则是“谁来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讲,刑法中的归责原则应当具有平息公众怒气、维护社会稳定的机能导向性。
其次,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看,犯罪呈现在公民面前的最直观体现即是危害结果。正如结果无价值论者所称的:“法益侵害说的基本立场是,只要有法益,原则上就有犯罪,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可以不构成犯罪。因此,在法益侵害说之下,犯罪的认定程序是这样的:首先要看有没有法益侵害结果,这是大前提。然后再看行为人有没有责任。最后再看行为在刑法上有没有明文规定”[7]。可见,如果采取结果归责理论,对社会中值得保护法益的戕害是启动刑法评价机制的触发点。至于具体损害由谁承担,则是考察各原因力所起作用大小的结果,如果作用力较大,就承担较多的责任,如果作用力较小,就承担较小的责任。而由于法益侵害结果系一个恒定的量,因此在对各个原因力的考察中,就会涉及到责任分配的问题。在此意义上讲,在结果归责的视阈之下,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是否归责”,而是“归责于谁”,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归责”。
最后,在他人具有过错的场合,他人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犯罪的发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视为行为人的“共犯”,以被害人过错为例,从被害人教义学的角度来看,犯罪不完全是一方加害于对方而被害人完全被害的简单模式,而是行为人与被害人间互动、两者之间双向相互作用的结果[8]。“犯罪原因、犯罪及犯罪人”是互动理论的基本模型,[9]三者相互依托、相互影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诈骗罪是典型的关系犯罪,它得以实现的前提是被害人对财产的处分行为。[10]例如,在诈骗罪中,由于被害人承担了一部分的责任,行为人承担的责任就相对减弱,这就导致行为人在处罚上相比盗窃罪更轻。事实上亦是如此:一方面,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是单独入罪的条件,没有数额较大的要求,而成立诈骗罪必须满足数额较大的要件。另一方面,根据司法解释,盗窃罪数额较大的标准是1 000-3 000元以上,而诈骗罪是3 000-10 000元以上。同样,盗窃罪中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也比诈骗罪要低得多。
在刑法因果关系认定的归责层面,引入责任分配的原理,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且对问题的解决颇有裨益。
三、责任分配原则在归责体系中的适用条件
毫无疑问,责任分配原则对于介入因素问题的解决是颇有帮助的。除了介入因素的问题以外,共犯理论本质上也是一套改头换面的归责体系。实际上,即使是采用区分制共犯理论体系的学者,也开始逐渐关注犯罪参与组合与结果之间因果力的认定,这一点在责任共犯说向因果共犯论的演进过程中体现得尤其明显。责任共犯说在为共犯寻找处罚依据时将着眼点落在正犯身上,将“正犯符合犯罪构成”作为共犯成立的依据;[11]违法共犯说认为“共犯的处分依据在于引发正犯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12];而因果共犯说主张,共犯者共同引起了正犯所实现的结果,以此为理由应当处罚共犯。[13]从这一理论的变化过程来看,共犯处罚依据理论的发展旨在逐步抽离作为媒介的正犯在共犯认定中的作用,而加强对共犯与结果之间因果链条的考察。在纯粹的因果共犯论看来,只要将遭受侵害的法益和参与行为之间搭建起桥梁,就可以轻易对参与者进行归责。从这个意义上说,因果共犯论甩掉了作为媒介的正犯考察这一枷锁,使得对于参与者的归责原则更加纯粹简单,更接近于单一正犯体系的归责方式。可以看到,责任共犯论或者不法共犯说的分析进路是先考察正犯,再考察共犯;而因果共犯说直接锁定“行为”与“法益侵害结果”两端,考察中间的因果关系,淡化作为媒介的正犯角色,这一逻辑思路与单一正犯体系不谋而合。这就意味着,随着因果共犯论逐步登上学术舞台,教唆、帮助者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显得尤其重要,这本质上也是一个责任分配问题。下列情形不能运用责任分配原理加以解决:
(一)在归因层面本身可以排除因果联系
归责理论是建立在归因基础之上的,如果结果与行为人之间本身不存在关联,也就不存在责任分配的问题。例如,如果行为并不在规范保护目的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否定归因,也就无需再进一步考虑责任分配的步骤。
例如,2005年的一天,被告人陈全安驾驶大货车至樵丹路北西科技园路口时靠边停车等人。期间张伯海驾驶机动车同向行驶,追尾碰撞陈全安驾驶的大货车尾部,被害人张伯海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被告人陈全安驾车逃逸。事后查明,被告人陈全安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张伯海酒后驾驶机动车,负事故的次要责任。[14]
本案中,不应当直接采用客观归责理论或者责任分配理论,因为仅从归因层面判断就可以出罪。毫无疑问,行为人唯一存在的违规行为就是其逃逸行为,问题在于,逃逸行为发生在后,交通事故发生在前,逃逸行为不是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从规范保护目的来看,将逃逸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入罪条件抑或加重情节,也是为了及时遏制行为人造成损害结果的扩大进程,但倘若损害结果本身与行为人无关的话,就不应当将损害归于之后的逃逸行为,这显然存在因果倒溯的问题。因此,即使是运用条件说,也可以在归因层面否定因果关系,无需动用责任分配理论进行判断。
(二)行为人之外的他人没有过错
毫无疑问,责任分配理论适用的前提在于多人存在责任的情况发生。如果仅仅是因为客观条件促进了结果的发生,也不能由此减轻行为人的责任。
例如,1994年某日中午,被告人殷红兵因其女友汤某被前男友伍某某打伤,便邀约吴某、杨某一同带汤某就医。当日14时许,殷红兵等四人准备返回汤某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上桥张家湾213路公交车站附近的家中时,在汤某住家附近一露天台球桌处遇到伍某某。经汤某指认后,殷红兵、吴某、杨某与伍某某发生打斗。打斗过程中,杨某拖走伍某某所持洋铲,吴某抱住伍某某,殷红兵遂持随身携带的猎刀捅刺伍某某后三人逃跑。逃跑时,因伍某某拦阻,殷红兵再次持刀捅刺伍某某。后殷红兵等人逃离现场。经法医检验鉴定:伍某某因系外伤致心脏破裂导致循环衰竭死亡。事后查明,被害人送医途中曾遇堵车,而被害人的死亡后果与就医不及时有一定关系。①(2014)渝一中法刑初字第00034号。本案中,除了行为人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存在过错,在这种情况下,将全部责任归于行为人这一点是明确的。即使存在堵车的客观因素,但由于堵车的引发者不可能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分担责任,因此行为人还是要承担全部责任。
运用责任分配原理,也可以对被害人特殊体质不影响归责的问题作出解释。
例如,2015年某日,被告人饶某某与被害人毛某甲在南昌县向塘镇向赣桥头东侧桥头美发店附近因生活纠纷发生肢体冲突,两人拳脚相向。不久,驾车行至桥对面的被告人饶良玉见其女婿饶某某与毛某甲发生冲突,亦上前与饶某某共同殴打毛某甲。后毛某甲被打倒在地并当场死亡。经鉴定,毛某甲颜面部、右手背、右膝前等处见皮肤挫擦伤或浅表皮肤裂创、青紫。据其损伤特征分析,符合钝性外力作用所致,纠纷、打斗过程中碰撞摔跌等可以形成。毛某甲的死亡原因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致急性心功能衰竭死亡,本次纠纷、打斗为诱发因素。②(2015)洪刑一初字第70号。
再如,2012年某日,被害人余瑞根与其妻子陈某甲、大嫂连某从某KTV门口乘坐被告人汪红宾驾驶的闽DT7007出租车,当车行至湖里区南山路农村信用社门口时,被害人余某丙指责被告人汪红宾故意绕路,二人遂发生口角进而引发互相打斗,被害人余某丙因打斗引发冠心病发作,经送医抢救无效死亡。③(2012)厦刑初字第146号。
这两个案件中,不能因为被害人的特殊体质阻断或减轻对行为人的归责。理由在于,被害人特殊体质不等于被害人的过错,不能仅凭被害人的特殊体质就分担行为人部分的责任,否则对于被害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因此,如果行为人以外的他人没有过错,就不能减轻对行为人的归责。
(三)“未知、可能”的介入因素
就责任分配而言,一定是建立在他人过错明确这一前提之上的。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可能存在介入因素”的案件,在这种情况下,不能适用责任分配原则。或者说,在介入因素无法得以明确的场合,与其说是实体问题,不如说是证明问题。
例如,被告人张万珍在滨德高速乐陵服务区保洁室内与被害人张某己因琐事发生口角,两人相互辱骂,继而被告人张万珍举起手中的铁簸箕,连砸被害人张某己的头顶两下,致其颅脑损伤死亡。辩护人提出,被害人张某己死亡地点及被害人的伤情鉴定反映该案不排除其他介入因素。④(2014)德中刑一初字第27号。
再如,在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楼院内,被告人李某乙因民事纠纷与他人发生争执。被害人李某甲上前劝架时拉住李某乙,李某乙挣脱过程中将李某甲摔倒致其受伤。经法医鉴定,李某甲之伤构成轻伤一级。辩护人提出,被害人从案发到就诊二个小时,中途转院三个小时,无法排除这两个时间段内被害人延误治疗、有其他加重伤情等介入因素的合理怀疑。①(2015)泰山刑初字第96号。
应当认为,以上的两个案件中,都不能适用责任分配原则,对被告人减轻责任。这是因为,即使控方具有对行为人符合犯罪构成的证明责任,但是对于介入因素此类的消极构成要件要素,被告人至少提供初步证明材料。只是表明存在介入因素的可能性,并不足以阻断或减轻对行为人的归责。
在责任分配原则对于具体问题的解决上,笔者分为两种情况加以讨论,一类是介入行为人自身过错场合,另一类是介入第三人或被害人过错的场合。
四、介入行为人自身过错场合的归责
在介入行为人自身过错的问题上,通说分成六种情况进行探讨:第一,在故意的前行为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高度危险,后来介入行为人的过失行为造成结果时,应当将结果归属于前行为;第二,在故意的前行为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高度危险,后来介入行为人另一个高度危险时,需要判断哪一行为的危险性大;第三,在过失的前行为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高度危险,后介入的故意或过失行为直接造成结果时,应当将结果归责于后行为;第四,故意或过失的前行为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高度危险,后介入的故意或过失行为不对结果起决定作用的,将结果归责于前行为;第五,在后行为对结果发生具有决定性作用,且前行为通常不会引起后行为时,应当将结果归责于后行为;第六,前后两个过失行为导致结果发生时,应当将两个过失行为视为构成要件的行为。[15]192
笔者认为,在所有这些规则当中,最终的处理方案无外乎两类:第一,将结果归责于前行为,后行为不加以评价;第二,将结果归责于后行为,与前行为数罪并罚。例如,日本著名的“氯仿案”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本案中,三名被告人意图用氯仿将被害人迷晕后将被害人连人带车从悬崖翻落致其死亡。但最终无法查明被害人是溺死,抑或是吸入氯仿导致心跳停止。一审判决被告人故意杀人罪后被告人提出控诉,认为在使用氯仿迷晕被害人时并无杀人故意,因此是伤害致死罪。第二审判决指出,即使是由于吸入氯仿死亡,也不过关系到实行行为开始到结果发生的因果流程错误而已。最高裁判所最终指出,被告人着手了将吸入氯仿昏迷的被害人连人带车翻入海中这一连串杀人行为,目的已经达到,所以即使和这三名行为人的认识不同,也不能否认行为人的杀人故意,因而承认三名实行犯成立故意杀人罪既遂的共同正犯。[4]58-61
在“氯仿案”中,到底应当将结果归于行为人的前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既遂,还是将结果归于后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未遂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想象竞合犯呢?笔者认为,前者的结论是妥当的。在罪名的认定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法定刑的问题,正如徐松林教授指出的:“按照公众的社会心理,‘量刑公正’才能代表刑法正义,‘准确定罪’只是实现量刑公正的手段而非目的。对于某一具体刑事案件,不管法院如何宣称自己的定罪是准确的、是依据法律规定作出的,只要量刑上畸重畸轻,社会公众都不会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判决。”[16]在“氯仿案”中,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既遂在法定刑上显然高于故意杀人罪未遂与过失致人死亡的竞合,②日本刑法中,故意杀人罪既遂最高可以判处死刑,故意杀人罪未遂减轻、免除处罚,过失致人死亡罪只能处以罚金,后两罪并罚也不可能高于故意杀人罪既遂的法定刑,我国刑法中结论相同。这就表明,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未遂与过失致人死亡的竞合犯,相对正常情况下的故意杀人既遂而言,实质上是对行为人责任的减轻。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行为人自身过错的介入要会导致本身责任的减轻呢?如前文所述,在没有他人具有过错的情况下,无论因果流程如何,全部责任应当是归于行为人一身的,或者说,在这种场合,根本不具有减轻责任的正当理由,也就不存在责任分配的问题。
因此,如果认定为犯罪既遂处以更高的法定刑,就没有必要因为行为人自身过错的介入评价为未遂犯与过失犯的竞合,进而导致法定刑的降低。当然,如果将结果归于后面的行为导致处罚更重,就有必要对前后两个行为进行数罪并罚,才不违背罪刑均衡原则。例如,行为人先是过失导致被害人重伤,为了逃避责任将被害人丢入水中淹死的,就应当将死亡结果归属于后面的行为,认定为过失致人重伤罪与故意杀人罪,进行并罚。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仅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一罪,显然量刑畸轻,难以令人接受。
总而言之,在行为人自己介入过错行为的问题上,必须遵守的最基本原则是,如果行为人之外的人不存在过错,就不能因为行为人自己的过错导致行为人的责任减轻或免除,这是由责任分配原则推导出的必然结论。在此意义上,笔者并不赞同从纯粹教义学的立场对“行为人自我行为介入”的界定框架,这样的处理不仅将简单问题复杂化,而且会导致理论与司法实践相脱节。诚然,刑法大厦的基底需要刑事政策与社会期许作为支撑,否则只能沦为法学家手中的无用塑具。在笔者看来,在行为人自我行为介入的场合,完全可以从一般人的观念出发,坚持“没有责任分配就没有责任减少”的原则,并运用“以刑制罪”的思想反制定罪。
五、介入他人过错场合的归责
介入他人过错场合的归责是整套归责体系的核心问题,这里的“他人”不仅包括被害人,也包括行为人之外对结果起到加功作用的第三人。传统的介入因素理论试图通过一套归责体系解决所有因果关系问题的做法,但从效果来看并不成功;实际上,由于归责体系是一套价值体系,在判定的过程中渗透了个案平衡的思维方法,因此,在归责的问题上,可以采用类型化与要素化的分析进路,以流动的、量化的衡量标准代替僵化的因果法则,这对问题的解决可能更有指导意义。在介入他人过错的场合,应当区分不同的情形:在有的场合,虽然行为人与结果之间存在他人过错的介入,但不影响将结果全部归责给行为人,“引起型归责”与“义务型归责”即是这样的类型;在其他场合,他人过错的介入分担了行为人的部分责任,导致行为人责任的减轻。
(一)“引起型归责”与“义务型归责”
“引起型归责”是指行为人通过他人的行为引起了法益侵害的后果发生,这种情形从表面上看似乎在行为人与结果之间横亘了第三人的过错行为,但这种情况的特殊性在于,介入因素的发生与因果流程的发展完全掌握在行为人的犯意投射之内。教唆犯与帮助犯是“引起型归责”的典型。在区分制共犯体系的内部,随着实质客观说或支配说的兴起,两大体系的争议焦点最终落在“是否需要借力正犯-共犯框架以及共同犯罪框架”这一问题上,并在以此延伸出的具体问题上存在争论。但是,随着区分制共犯体系内部最小从属性说、行为共同说、因果共犯论等理论的兴起,两大体系在诸多具体问题上的差异已经越来越小,至此,区分制共犯体系诉诸共犯框架的思考进路已经逐渐被消解,而对归责链条的考察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归根结底,共犯问题已经基于实用主义的立场逐渐蜕变为归责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共犯责任不同于实行犯责任者,恰恰在于其较弱的因果关系,共犯对结果有所贡献,但他们并未控制导向犯罪完成的进程。他们‘帮助’了‘犯罪的实施’,但他们既未‘实施’犯罪,也不决定犯罪的作用”[17]。各国刑法理论普遍承认,在教唆与帮助的场合,“介入”的正犯犯罪行为不能导致引起者责任的减损,这是因为,既然因果流程完全按照行为人预想的进程发展,引起者原则上就承担与正犯相同的责任,不存在责任分配的问题。
“义务型归责”发生在行为人对结果回避具有义务的场合,这种情况下,即使中间介入了被害人或第三人的异常行为,也不能发生阻断因果流程的效果。时至今天,“义务犯”的概念已经成为德国学界普遍承认的理论,并且“作为独立的犯罪类型已经不再可以被怀疑”[18]。毫无疑问,在存在论的视阈之下,对于因果链条的支配是归责的核心因素,在这种场合,异常的介入因素之所以导致因果链的切断,不过是因为支配流程被其他原因力打断。然而,在义务犯的场合,分析范式会明显有所不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本身就不存在因果流程的支配,也就不会有介入因素打断支配流程的问题。换言之,义务犯只为规范上的义务不履行承担责任。例如,我国《刑法》第186条的违法发放贷款罪,第397条的滥用职权罪中,结果的发生都是由第三人支配,并且远远超出了原行为人的操控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对行为人进行归责,表明与传统因果律的基础发生了悖离;此时对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人归责,实质上属于规范考察的范畴。因此,对于义务型因果的案件而言,关键是考察结果产生的危险是否处于行为人的保护管辖范围之内,至于介入因素,并不能导致因果链的切断。换言之,义务犯的责任并不因为他人过错的介入受到减损。
问题在于,如何确定义务犯的成立?实际上,相比作为犯与不作为犯的区分,义务犯与支配犯的区分本身是一组规范意义上的范畴,在很多情况下,对义务犯界限的刻画并非泾渭分明,而且渗入了大量的价值判断。在有些场合,作为行为导致作为义务,而行为人不履行该义务的,就成立义务犯,这相当于是将难以达到处罚程度的支配型犯罪转化为义务犯进行处罚。例如,被告人赵某率众携带一尺多长的砍刀7把去找马某“算账”,马某被众人追赶了40余米之后跳入河中,因水性不好而溺亡。[19]本案中,问题的重点在于,行为人“追赶他人导致他人跳河”的行为,是不是值得刑法评价的行为?不难发现,“追赶他人”的行为不仅在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实质危险性上略显不够,而且难以跨越传统理论中实行行为“类型化法益侵害行为”的藩篱。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视角转换,将评价的重点锁定为被害人落水后行为人基于先前行为不施以援手的行为,就可以轻易地得出成立义务犯的结论,在归责上更加简单。因为如上文所述,在义务型归责的场合,介入因素并不能切断原行为人与结果的因果力。例如,在上文所举的赵某杀人案中,如果从义务犯的角度考察,即使存在重大的介入因素,也不影响对被告人的归责。由此可见,义务犯的认定是规范意义上的问题,其中渗透了大量的刑事政策与社会期许的考量,并且具有很大的认定弹性。对于危险性大、可罚程度高的行为,就可以认定为义务犯进而进行归责,例如,在提供网络传播平台的案件中,如果肯定义务犯的成立,在这种场合,即使在中间介入了他人的犯罪行为,也不阻断归责。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义务型归责”的类型。例如,被告人刘某某于2011年5月任威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政策法规股(行政审批股)副股长,2012年8月为企业职工退休审批领导小组成员。在工作中,黄某某主持行政审批股的日常工作,主要负责全县参保职工的退休审批,刘某某主要负责行政审批股工伤认定和伤残等级鉴定。黄某某、刘某某作为企业职工退休审批领导小组成员,均要参加审批领导小组会议。由于二人在工作中不认真履行职责,对资料的审查把关不严,工作流于形式。导致沙湾煤业公司职工陈某某等14人办理假工伤提前退休手续,骗取国家社保基金124万余元,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①(2015)威刑初字第78号。本案中,被告人玩忽职守的行为所造成的重大损失有他人犯罪行为的介入因素存在,但由于本案中行为人具有监管与审查义务,介入者的犯罪行为并不能分担和减损行为人的责任,行为人对介入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由此可见,在“引起型归责”与“义务型归责”的场合,他人过错的介入并不导致责任被分配以及原行为人的责任减损。
(二)责任分配原则需要考虑的要素
在除了“引起型归责”与“义务型归责”之外的场合,介入他人的过错一般会导致行为人可责难性的降低。在这些场合,行为人承担责任的轻重主要受到下文要素的制约,而这些要素在对行为人责任大小的确定过程中都是需要考量的。
1.介入因素的可预见性。如果他人过错的介入在一般人看来可预见性极高,或者几乎是原行为必然导致的,那么对行为人可归责的程度就越高,且在大多数场合并不导致行为人责任的减损。例如,行为人将炸弹踢到甲的身边,甲立刻将炸弹踢到乙的身边爆炸导致乙死亡的,由于甲的行为是可以预见的,因此行为人对乙的死亡承担完全的责任,不存在责任分配问题;或者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暴行,导致被害人在仓皇中摔下楼梯身亡的,行为人的责任不发生减损。
在日本的一起判例中,四名被告人在深夜的公园内对被害人反复实施了持续两个多小时的暴行,接着又在公寓的居室内连续实施了将近45分钟的暴行,被害人趁被告人不注意逃跑,在距离公寓约763米的高速公路上被急速行驶的汽车撞倒,随后被后面的汽车碾压身亡。对于本案,最高裁决指出:“对于被告人等有极度恐惧感的情况下,在力图逃离必死之境地的过程中,刹那之中选择了那样的行为。这样的行动,作为逃脱出被告人等的暴行的方法来说,不能说是显著不自然、不相当的”[20]3-4。笔者认为,这一论证是相当客观的,本案中,行为人的行为导致被害人逃走在一般人看来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因此被害人不能分担行为人的责任,行为人的责任也不得由此减损。
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有这样的案例。例如,杨某丁伙同夏某乙、夏某丁、被告人夏某甲等人到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光明街40号被告人杨某乙家,将杨家的大门玻璃、柜台玻璃砸掉。正在家中的被告人杨某乙随即打电话告诉弟弟被告人杨某甲,同时打电话叫同学朱振丙过来帮忙。被告人杨某甲亦打电话叫同学吴某、朱某过来帮忙。尔后发生多人互殴,被告人杨某甲见状即持短刀上去砍刺夏某丁、夏某甲、夏某乙,其中一刀刺中夏某丁的腹部。随后,被告人杨某甲、杨某乙一起逃离现场。夏某丁受伤后经送医院医治无效死亡。本案中,存在医疗事故的介入,引起急性腹膜炎,继发导致被害人感染性休克死亡。辩护人指出:“夏某丁是由于医疗事故造成感染而死亡,杨某甲的行为仅造成夏某丁重伤或轻伤,杨某甲仅需对被害人的伤害后果负责,对其死亡结果不承担责任”①(2010)浙温刑初字第265号。。本案中,医疗事故的介入因素在一般人看来是难以预见的,医院也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对于行为人来说,责任分配导致行为人责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此,法院也指出,医疗事故等介入因素的存在,可以作为酌定情节对被告人的量刑在幅度内予以适当体现。
2.介入过错的大小。从责任分配的角度来看,介入过错的程度越高,对行为人责任的减损就越多。例如,在德日刑法中,被害人因为遭受犯罪侵害而自杀、自残的后果不能归责于行为人,当然,这其中渗透了大量的裁量因素。在日本的一起判例中,被害人受到他人伤害后就医,但在就医期间,被害人试图擅自出院,因此作出了从身体上拔出治疗用管子等等举动,成为病情急转直下的原因。最高裁决指出:“即使介入了被害人由于没有遵从医师的致使、未能保持安静而使治疗的效果未能发挥这样的事情,也应该说被告人等的暴行所产生的伤害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存在的,所以认定本案成立伤害致死罪的原判决,是正当的”[21]5-6。本案中,考虑到被害人自身的过错没有达到阻却对行为人归责的程度,因此还是将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归责于行为人,但在程度上显然有所减轻。
我国司法实践中类似的判例如:被告人徐纪涛在浙江省杭州市老汽车东站售票大厅门口,因打牌与被害人张某发生争执,并持一铁棍捅、击被害人张某腹部、手臂等处,致其小肠破裂死亡。经鉴定,被害人张某系腹部遭钝性外力作用致肠管破裂,并发弥漫性腹膜炎、败血症、感染性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②(2013)浙杭刑初字第32号。本案中被告人徐纪涛持细长状的钢管捅了被害人腹部,被害人被捅后即出现肚子痛的症状,但在被害人第一次就医时存在医院救治不积极或被害人不配合治疗等情况,所以可以酌情减轻被告人的责任。
3.原因力的作用大小。在责任的分配上,作用力大小的比较是需要重点考察的因素。显然,在对整体结果的造成上,介入的他人行为起到的作用越大,行为人的可归责性就越小。在归因层面,“条件说”所解决的仅是个人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联系这一问题,而在归责层面,则需要对各行为作用的大小进行判定。在区分制单一共犯体系中,日渐成为主流的实质客观说认为,应当采用实质的观点考察正犯与共犯的范畴。其中,重要作用说以对结果起到的作用程度作为区分正犯与共犯的标准;必要性说以对于犯罪事实的可替代性作为界分正犯与共犯的标准;优势说根据优势关系决定成立正犯抑或共犯;危险程度说认为正犯是侵害犯,而共犯是危险犯。[16]391通说采用“支配说”,主张正犯是对犯罪事实进行支配者,他在整个共犯体系中起到核心作用。[21]笔者认为,实质客观说与支配说在本质上没有过大的差异,这是因为二者都启动了实质判断,旨在运用各种标准对共同犯罪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的行为人进行锁定。也因为如此,有学者将“犯罪支配标准”成为“目的-客观论”抑或是“(新的)实质-客观论”[22]。不难发现,在实质客观说的语境之下,无论是重要作用说、必要性说、优势说、危险程度说,都针对正犯与共犯的划分提供了一定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其实都是立足于“作用”的考察,旨在为归责提供一套标准。这一点也恰好可以印证,共犯体系本质上是一套改头换面的归责体系。
在作用大小的判断上,可替代性是重要的指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行为人的行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往往就伴随着义务的产生。例如,原子弹的制造者制造出了原子弹,对于这一高度危险源就具有了管控的义务,他人犯罪行为的介入不导致行为人的免责;同样,网络平台的提供者在淫秽物品的传播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可以将这种情形在规范意义上认定为义务犯,对全部损害责任承担责任。换言之,行为的不可替代性越高,起到的作用就越大,对损害结果的责任分配就越多,如果不可替代性达到一定程度,可以直接适用义务犯的归责范式。
在日本的“大阪南港案”中,行为人作用大小的判定对案件的处理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本案中,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暴力,致其处于意志不清的状态后,将其扔在建筑材料堆场,其后,第三人再对行为人实施暴力,扩大了最初的暴力导致的脑出血的范围,提前了被害人的死亡时间。[23]本案中,考虑到前行为对死亡结果发生起到的作用具有绝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后行为的介入不仅不能切断因果链条,而且对前行为的责任减损作用也极其有限。
[1]王渊智.侵权责任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0.
[2]劳东燕.风险社会中的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00.
[3]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331.
[4]高桥则夫.规范论和刑法解释论[M].戴波,李世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ルーマン.法社会学[M].村上淳一,六本佳平訳,译,东京:岩波书店,1977:33.
[6]京特·雅各布斯.刑法保护什么:法益还是规范适用?[J].王世洲,译,比较法研究,2004(1):970.
[7]黎宏.结果本位刑法观的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27.
[8]刘丽萍.犯罪与被害互动关系中被害人过错法定化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2):77.
[9]白建军.罪刑均衡实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75.
[10]申柳华.德国刑法被害人信条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325.
[11]泷川幸辰.犯罪论序说[M].改订版.东京:有斐阁,1947:246.
[12]大谷实.刑法讲义総论[M].新版第三版.东京:成文堂,2009:411.
[13]山口厚.刑法总论[M].第二版.付立庆,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03.
[14]陈兴良,张军,胡云腾.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8.
[15]张明楷.刑法学[M].第五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16]徐松林.以刑释罪——一种刑法实质解释方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189.
[17]乔治·弗莱彻.反思刑法[M].邓子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484.
[18]何庆仁.义务犯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
[19]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二、三、四、五庭.刑事审判参考(总第 55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1.
[20]山口厚.从新判例看刑法[M].第 2 版.付立庆,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1]Claus 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2)[M].C.H.Beck,2003,S.14ff.
[22]冈特·施特拉腾韦特.刑法总论1:犯罪论[M].杨萌,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90.
[23]松原芳博.刑法总论重要问题[M].王昭武,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62.
DF613
A
1001-4225(2017)10-0046-09
2016-10-19
陈文昊(1992-),男,江苏镇江人,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汪小珍)
——以“被告人会见权”为切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