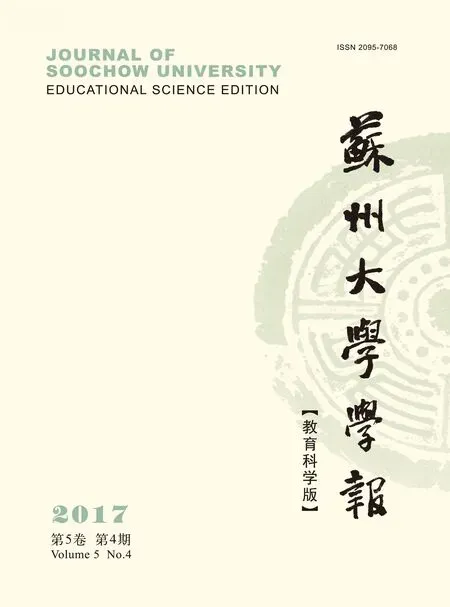身体、隐喻与教育:教育史研究中的具身视角
周 娜 周洪宇
(1.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2.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 理论前沿:身体视角下的教育研究
特约主持人:周洪宇(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话语:随着身体哲学的繁荣及认知心理学的发展,教育学界注意到身体视角的教育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研究。身体视角下的教育研究,是对教育生存转向的积极回应,是深刻认识教育中人的存在的学术新域。身体视角下的教育研究,不但给教育研究带来方法论上的冲击,也将动摇先前对“教育是什么”的本体性认识。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史研究团队,是国内较早展开身体视角的教育史研究的学术阵地。本团队在剖析探究我国教育历史中的身体生成状态及我国教育如何被身体生成所影响与塑造的同时,积极同国际教育史学界就此研究领域展开交流与对话,在教育身体史领域持续深耕。本期栏目所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周娜与主持人撰写的《身体、隐喻与教育:教育史研究中的具身视角》;另一篇是青年学者魏珂与李艳莉的文章《教育学视域下身体研究的进展及启示》。在第一篇文章中,作者以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参加国际教育史年会的所见与所论,从理论与方法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了近两年来为国际教育史学者推崇的“具身理论”对教育史研究的意义及其对教育情感史兴起的促进作用。这篇文章的一个相关的启示是:身体视角的教育史研究具有跨学科的丰富性与广博性。魏珂与李艳莉的文章运用综述的方式勾勒出近年来国内教育学界的身体研究整体图景。结合上一篇对国际教育史学界身体研究的介绍,可以发现中国教育身体研究从理论的原创性、主题的集中性及方法的多元化等方面仍有待深化。
身体、隐喻与教育:教育史研究中的具身视角
周 娜1周洪宇2
(1.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2.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具身视角的教育史研究是对教育史面临新问题的回应,为教育史提供了新理论与新方法。作为一种理论,具身观强调历史研究中身体的在场性与参与性,挑战“离身”教育史学的认识论研究范式,推动教育史研究的“身体转向”。在方法论层面上,具身观不但向教育史学者提供思考教育历史及其变迁的新视角,同时为话语分析、隐喻等方法在教育史学的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关注情感,则是具身视角下教育史研究的应然之态。具身观沟通了教育身体史与教育情感史,推动教育情感史由“治理研究”视角下情感史向关涉身体的“情绪史”推进。
教育史学;具身研究;身体;情感转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意识哲学主张的“心统治身”的理念受到质疑,“身体”实现对“心”的造反,摆脱了失语境地。摆脱“失语”的身体,一跃成为社会科学领域关注的焦点。尤其随着“具身认知理论”的日益成熟,哲学、美学、伦理学、文化学等纷纷从不同角度对身体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探究。教育史学在史学界与教育学界的双重影响下,确立了具身视角的教育史研究,目前不仅在实践层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在理论上也有诸多阐释①目前,国内教育身体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带领的团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在2016年第4期刊发了一组“教育身体史研究”的文章,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展开了教育身体史的研究。,而且,这一取向为全球国际教育学者所共享。
2014年,国际教育史学会(International Standing Conference of History of Education,下文简称ISCHE)在国际教育史学会第36届伦敦年会上讨论设立“校园中接触的身体”常设工作组(Touching bodies in schools standing work group)。②目前,ISCHE有5个常设工作组:“实物、感知和直观教学世界”常设工作组(Objects,senses and the material world of schooling SWG)设立于2015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年会;“校园中接触的身体”常设工作组(Touching bodies in schools SWG)与“反思教育史学科发展”常设工作组(Mapping the discipline history of education SWG)均创设于2014年英国伦敦年会;“教师的批判性思考”常设工作组(The teacher’s critical thinking SWG)设立于2010年,目前仍在工作中;“性别与教育”常设工作组(Gender and education SWG),初创于1994年,2005年工作组停止工作,2012年重新启动,工作至今。2015年,在37届伊斯坦布尔年会上,该常设工作组收到各国教育史学者的关于身体史研究的论文数十篇,分三次召开了专题研讨会,来自不同国家的7位代表做了专题报告。2016年,国际教育史学会第38届芝加哥年会的大会主题“身体与教育”,来自全世界的394名教育史学者围绕“身体与教育”组织召开了4场主题发言、数十场专题发言及圆桌讨论,把具身视角下的教育史研究推向新高度。笔者结合2015年、2016年参加国际教育史学会第37届、第38届年会的所见,及中国教育史学发展现状,谈谈具身理论对中国教育史学的影响。
一、“离身”教育史研究的困厄
教育史研究历经上百年的层积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与危机。在对中国百年教育史学发展进行后设性反思时,学者们或依据研究理论不同,或依据历史事件分期,把中国教育史学发展分为“三取向”式或者“五阶段”式。③周洪宇、李忠从“教育史学科研究取向”的转变把中国教育史学科发展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在借鉴西学中呈现出多元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前呈现出政治主导下的一元取向;改革开放后,在恢复重建中,中国教育史研究出现了一元多线取向”,本文称之为“三取向”划分法。侯怀银等以历史事件为学科发展阶段划分点,把百年的中国教育史学科发展历程细化为五个阶段:初创期(1901—1910)、突进期(1911—1936)、重创期(1937—1949)、徘徊期(1950—1976)、复兴期(1977—2000),本文称之为“五阶段”划分法。参见:李忠、周洪宇:《中国教育史学科研究取向的三次转换》,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侯怀银、王喜旺、李艳莉:《中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百年求索》,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对中国教育史学的审视,当然可以沿着上述分析与反思模式,但也存在第三种研究取向,即把反思视角放在百年教育史学演进中教育史研究对象的改变这一问题上。这个思考视角是历史观及教育观的双重呈现,可以有效洞察教育史学发展隐藏的内在性危机。
在此视角考量下,中国教育史学可分为两大阶段,也可谓两大取向:认识论取向教育史学与实践活动取向教育史学。近代以来,受思辨哲学“身心二元论”及工具理性主义的影响,人的活动被抽象化理解,教育学被定义为“研究教育现象的科学”,形成了“隐”身、“抑”身的教育观。受此影响,教育史研究对教育认识历史的考量优于对教育活动及教育事件的审视,精英论述的教育思想及官方制定的教育制度构成主要研究对象,形成了离身的、认识论取向的教育史学范式。此种情况不独中国教育史学,“二战”前西方的教育史学同样如此。直到20世纪60年代,英国教育史学的主流一直是:教育观念史、教育机构史的研究及教育制度的叙述研究。在美国,“教育史就是公立学校的历史”、“公立教育是好的,其成长即等同于进步的线性教育史观”等这样的认识为20世纪40、50年代以前美国教育史学者所共享。20世纪初期,中国虽然有学者对教育史研究对象曾作如下阐述,“故凡称为详尽的教育史书,必要对于教育事实之变迁发达分为教育的事实、教育者的活动与教育制度法规等详为记载,再要对于教育的思想学说即所谓理论者广为记录,或更加以评论”[1]1,主张教育史研究应囊括教育的事实、教育者的活动等。但这个声音在以“教育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学与“科学化”史学的双重围堵下终被淹没。
“二战”后,在新史学及“视教育为一种社会功能”的观点影响下,西方国家的“离身”教育史学遭遇严重批判,认识论取向教育史学出现变化,一些新的取向、角度、方法、主题等出现,不再仅关心学校教育史,还注意教育与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历史脉络梳理。在中国,类似的变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方缓缓而来。在哲学、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发展的冲击下,中国教育史学界尝试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做教育史研究,强调教育与社会的交互作用,扩大了研究范围,创新了研究方法。①20世纪80年代,以浙江大学田正平教授为领军人的教育史学者尝试把现代化理论融入唯物史观,考察中国教育变迁,开启了现代化取向的教育史研究。这种研究取向在20世纪90年代最为繁盛,并持续至今。20世纪90年代,以华东师范大学丁钢教授为带头人的教育史学开启了叙事取向的教育史研究。受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影响,以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为首的学术团队在对教育史研究对象进行梳理后,确立了“实践活动取向的教育史研究范式”。这些新变化,拓展了教育史研究范围,创新了研究视角,增强了教育史的“鉴往知今”功能,但仍然遵循着“大历史书写”路子,重视长时间历史书写,教育历史中人的活动被客观化、抽象化,人在教育史研究中被思想、制度等内容所遮蔽。
20世纪80年代,哲学领域相继形成的“主体哲学”“实践哲学”思潮深刻影响着中国学术思想及实践。在教育学界,“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的认识逐渐得到认可。教育研究开始引入“主体”“实践”等概念。进入21世纪,有关“主体”与“实践”的研究在教育学中继续深度汇合,达成了“教育活动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的新共识,关注教育实践、实施“实践品性”“实践逻辑”的教育学研究,关怀有“生命”的教育主体,产生了“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教育出现生存转向。在哲学与教育学冲击下,从实践的、主体的层面理解人的教育活动,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教育史研究逐渐确立起来,形成实践活动取向的教育史学,构筑了以人的教育活动为研究中心的教育史研究范式。当具身理论对其他教育子学科如教育哲学、课程论、教学论等产生影响时,具身理论也应该对教育史研究有一些启发与推动。承继了马克思实践生存哲学的身体理论,实践活动取向教育史学承认身体的主体性和历史性,认可“身体是文化和习惯的身体,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2],确立了教育史研究的身体取向。
二、具身观:教育史研究新理论与新方法
作为一个新视角,“具身观对社会的许多领域,特别是教育领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它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看待学生怎样学习、教师怎样教学和学校怎样组织”[3]7,把身体从教育的边缘拉至中心,教育及教学活动不再是与“脖颈以下”的身体无关,人的生成性存在得到承认和认可,给传统教育观带来巨大冲击。②此观点可见:叶浩生:《身体与学习——具身认知及其对传统教育观的挑战》,载《教育研究》,2015年第4期。
数世纪以来,身心二元论主导下的意识哲学中,“存在”被认识论所绑架,理性备受推崇和膜拜,身体及其欲望遭遇无视、蔑视及压制,导致海德格尔批判的“存在在者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益膨胀的理性主义(认识论哲学极度发展的后果)引起人们对人生存处境的反思,意识哲学、身心二元论招来持续的质疑和批评,身体摆脱失语,获得丰富内涵,人的生成性存在得到认识和讨论。尤其是脑科学及具身认知研究的迅速发展,从科学的角度论证了人的存在是身体与外界持续交互活动中完成的,身体的主体性、实践性得以确立。虽然目前对“具身认知”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根据我国学者叶浩生的研究,具身认知思潮包含以下几个命题:身体的结构和性质决定了认知的种类和特性;认知过程具有非表征特点,思维、判断等心智过程也并非抽象表征的加工和操纵;认知、身体、环境是一个紧密的联合体;身体和环境是认知系统的构成成分。[4]因此,以具身认知理论为基础的具身研究应该遵循身心一体原则、心智统一原则及根植原则,承认学习中身体的主体性、实践性,认可学习是认知、情绪、意志与行为共同参与的,与身体紧密联系的,并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完成的一个整体性活动。具身理论改变了人们对教育的看法,也使得从历史角度研究教育发生理论与方法层面的变革。
作为一种理论,具身观指导研究者对教育历史事实有了全新的捕捉。我们知道,历史研究者眼中的任何历史事实都不是自足的、独立的存在,而是借助一定理论视角的呈现。费伊曾说:“事实根植于概念框架之中。”[5]22换而言之,一定的理论视角显现一定的事实。吃喝拉撒这类人们每天都经历的事实,在历史唯心主义视角中会被视而不见,但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下,不但得以显现,而且被视为最基础性的存在。具身观倡导的身心一体论强调身体与认知是统一的:心智在身体中,身体在心智中;心智是身体化的心智,身体是心智化的身体。身体是认知、思维的主体,历史就是身体表达自己、生发自己的全部场景与结果。具身观对教育历史认知产生强烈冲击,带来了治史观念及视角的重大革新。历史研究者把人类的能动性视为研究的出发点,过去不入历史研究者法眼的,诸如发型、服饰、疼痛、姿态、情绪、垃圾等问题揽为研究对象,至于一些传统的历史命题则在新观念下被重新检视,以新的景象再度置于研究者及读者面前。
认识论取向的教育史研究建立在身心二元论基础上。身心二元论弘扬人的理性,提出“单凭我心里的判断能力我就了解我以为是由我眼睛看见的东西”[6]178,取消了看、听、感受等肉体功能的全部意义,并对通过感官经验获得的东西持怀疑态度,把获得知识和真理的可能都归于无躯体的心灵。在身心二元论看来,身体与心灵彼此虽有一定影响,实则是一种对立关系。在这种对立关系中,处于主流的是代表着理性与知识的心灵;代表着非理性与本能欲望的身体则处于从属与被支配地位。这种理论框架下的教育史研究对教育活动、教育活动的人的存在等历史事实习焉不察,当然也不奇怪。但“离身”教育史研究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是视知识传输的机械运动为全部教育事实,对身体、感性、情感、生理等与认知有很大关联的问题忽略不计,因此,对教育历史事实的呈现是片面的、残缺的。具身观的引入将填补教育史研究的“身体空场”,以具身视角作为考察教育历史事实的概念框架,突显了对教育活动中人的存在的审视与考量,形成对教育参与者的整全、细致的认识。
在方法论层面上,具身观不但向教育史学者提供思考教育历史及其变迁的新视角,也是话语分析、隐喻等方法在教育史学中应用的理论依据。受认识论取向影响,教育史研究者视教育历史事实为“心智活动”的结果。在这一信条下,教育史研究所彰显的教育事实的全部意义、特性及价值都在于阐释“心智”在教育活动中的表现及其发展、总结规律以启迪“心智”的持续发展。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美国学者G. Lakoff与M. Johnson提出具身理论有三大原则:精神本质上是具体化的,思想通常是无意识的,抽象概念主要是隐喻性的。[7]这三大原则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尤其是当代隐喻理论从认知的视角理解隐喻,并把人的身体经验和隐喻性概念看作是认知的基础,将大大改变我们认识历史的方式。当代隐喻理论也应引起教育史研究的关注。教育历史文本充满了隐喻性、形象性的语言,这种隐喻结构形式和理性认知的联系在认识论取向的教育史研究中,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或者被予以消极的、负面的、非理性的阐释。当代隐喻理论给教育史研究的启发:它所研究的隐喻,它所强调的身体经验,是教育历史中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然而,它通过对语言形式的实验性分析,把隐喻结构和图形经验模式放在历史认识的中心位置上,却是教育史研究尚未充分意识到的。身体史的隐喻研究侧重身体隐喻投射的过程及历史文化在此过程中的作用,注意探求身体喻源概念的变化,从而理解历史文化的变迁。目前身体隐喻的研究涵盖了“身体活动蕴涵的文化隐喻、文学作品中身体的隐喻、宗教中身体的隐喻以及身体隐喻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等”[8]。
“话语分析”在教育史研究中的应用,表现了新文化史力求用文化观念思考和认识历史的努力,也是基于对身体历史性的认可。根据福柯的界定,“话语”不仅是对社会诸种现象的表征,同时建构了社会各种现象及事物,尤为重要的是,建构了人的社会主体地位(诸如是看守或囚犯,是医生或病人)。而话语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实践功能,是因为“话语”表述的“知识”是权力在语言层面的反映,权力只有进入话语并有效控制话语才能发挥其力量,话语俨然是权力运作的一种表现。因此,关于一个历史事实的表述,诸如谁来表述、如何描述以及描述中的真假等问题,其实是经过权力斗争与平衡后的语言表达。对话语的分析,实则是揭示出一幅权力关系图。话语发挥威力的媒介是浸润在话语体系中的身体,通过话语对象、陈述、概念等手段,悄无声息地对身体形塑着、规训着。身体的在场性和历史性,为“话语分析”提供了切入身体表象、进行深描的绝佳路径。
三、构建具身视角的教育史研究
具身视角的教育史研究以教育活动中的人为研究对象,其价值体现在对“人是超越性存在”的追求上。台湾身体史研究学者黄金麟曾言:“进行身体主题的历史研究意在对自身的存在有一个不算全新但却深入的了解,从而澄清身体的存在和意义是怎样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中,因随着国族命运的更动而被积淀、形塑出来的。”[9]3关照人的生成性存在、关涉身体的教育史研究的展开必然是多学科的、多维度的。总览第37、38届国际教育史年会的会议论文,可以发现目前主要从三个维度构筑具身教育史研究,即空间、隐喻与女性主义。
1.空间与身体交融的教育史研究
20世纪70年代,人文社会学科开启了“空间的转向”。通过对空间的强调、对新空间思维的呼唤,哲学、社会学、地理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学科理论的空间化倾向,一种结合空间性的批判性视角在历史和社会研究中渐渐形成。空间性与历史性、社会性一起构筑了阐释历史与社会、解释人类生活的三维视角。换言之,人不仅仅是时间决定的,也是空间决定的。在人与空间的关系中,空间在针对着人、向着人的意义上而具有了自己的历史,同时,人在创造空间史的过程中持续、充分地发展了自己。身体是人与空间关系展开的起点。福柯最先把空间视角引入身体史研究。具体来说,他正是通过对医院、监狱等压制性的空间的具体研究,铺陈权力话语体系建构身体的历史。基于空间理论,教育空间不仅仅只是校园、教室、桌椅等物理性的,更是实施的教育思想、制度,是置身其中的教育参与者的变化与成长。教育空间是解读、阐释教育的另一个维度,而身体则是进入教育空间的逻辑起点。教育空间中的身体研究,作为教育身体史的研究路径之一,通过对身体与教育话语体系关系的探讨,展示身体与教育空间的互动关系。
现在来看福柯对空间与身体建构关系的考虑,是存在一定缺陷的,如消极的客体主义否定了身体的积极内涵和主体的能动性,但毕竟启发了我们对空间与身体问题的研究,特别是“以空间作为一个观照对象,论究身体的生成与空间发展的紧密关联,特别是纪律如何透过空间的细密安排而获得最大程度的体现”[9]190的研究身体史的思路,是我们受惠于福柯最大的部分。福柯关于“身体与空间关系”思考的缺陷,提醒我们对教育空间与身体的研究,不可陷入一味探究“身体在空间中被动表达及叙说”的单向度路径,关于身体对教育空间的影响及如何影响的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身体的能动实践性,决定了身体与空间关系的互动性,因此,教育空间中的身体研究,并非身体与空间单向关系的梳理,而是双向互动关系的剖析,只有这样,方可反映教育身体史对人的超越和生成意蕴的关照。
国际教育史学界对“身体与教育空间”的研究持续深入。2014年国际教育史学会第36届伦敦年会设立“校园中的身体接触”常设工作组,以“身体接触”为切入点,通过探讨历史上校园中的身体是如何接触,是以何种话语方式认识和理解身体接触,又采用什么策略和工具处理身体接触等问题,考察教育空间中的“身体”存在及生成。此次会议上,墨西哥学者Ines Dussel以学校建筑设计史为视角,以1870—1940年为时间段,通过分析比较墨西哥、阿根廷两国学校卫生间设计的历史变迁,讨论了卫生间如何成为校园内特殊的物理空间,以及学校如何利用卫生间的设计实现对身体的建构。在国际教育史学会、欧洲教育学会于2016年6月举办的第7届“全球教育史博士生夏季培训班”上,把教育空间史及教育空间与话语体系关系的研究列为培训内容之一。①“全球教育史博士生夏季培训班”(ISCHE&EERA Summer School for Postgraduate)是由国际教育史学会与欧洲教育学会共同举办,每年从全球教育史博士生申请人中遴选出30人,进行教育史学研究方法的培训与研讨。笔者有幸入选2016年的学习班。也就是说,教育史研究的空间转向切合国际教育史研究潮流。在此次研讨会上,英国学者Ian Grosvenor以“方法论问题的反思:教室内发生的活动史是否可知”为题,探讨了空间与身体交融的视角将对教育史研究带来何种变化。2016年8月,在国际教育史学会第38届芝加哥年会上,除了延续探讨教育空间中的身体,或者教育空间的设计对身体的影响,②此次会议上,相关的论文有:瑞士学者Marianne Helfenberger的《学校建筑与19世纪瑞士人的身体》;瑞士学者Comelia Dinsleder的《课桌设计的改变与被规训的身体》;德国学者Martin Viehhauser的《校园建筑物的教育意义:培育爱国主义情感》;西班牙学者Franciso Martin Zuniga的《西班牙的校园设计与校园卫生:相关性常被忽略的两个问题(1857—1931)》;奥地利学者Norbert Corube的《危险的空间与身处险境的女孩:儿童养育空间与性别塑造的相互影响》;等等。从跨文化、跨国的大空间观考量为教育革新而流动的身体,或因身体的迁移而带来的教育问题。
会议安排了两次圆桌讨论,以“移动的教育者:跨国教育”①此讨论组有三位发言人,发言主题分别是《帝国的身体:1883—1910年间韩国公立学校中的欧美教师》《移动中的教育家:1900—1945年间追求教育进步的中国人与美国人》《离场、距离与家庭生活:两次战争期间卡内基公司的教育专家——一项基于克拉克家族与劳伦姆家族的代际研究》。与“流动性与身体”②此讨论组两个发言,发言主题是《移动的身体: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儿童及其教育》《流动的身体:1960—1980年间美国大都市中的白人移居郊区与地理空间连续性研究》。为题,从教师身体、学生身体两个视角考量了身体与空间的双向互动,正如美国学者曼特(David M.Ment)在他的论文中总结的一样:身体在场的、浸入式的交流与学习,增加了教育交流与学习获得的效度。
2.隐喻视角下的教育史研究
隐喻视角下的教育史研究,主要是身体、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具身理论的持续发展为身体问题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当身体被视为历史性的存在,被视作经历和符号来加以研究,身体的文化隐喻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法国中世纪史学者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开启了姿态史领域。他的学生依据中世纪人们留下的文字和画像书籍,还原了中世纪的宗教姿势,并对其文化意蕴进行了解读。例如,经过研究,他认为,两手交叉、下跪等宗教姿势是作为封建臣服手势被引入宗教领域的。以身体隐喻视角切入教育历史,洞察教育活动如何建构了教育参与者的身体认知,这种身体认知究竟如何贯穿于教育活动中,以及如何影响了宏大的教育历史,甚至教育参与者的存在状态。
在2015年国际教育史学会第37届伊斯坦布尔年会上,笔者提交了以《对晚清女子学堂中女子身体生成的考察(1892—1912)》(Exploring Girls’Education in China(1840-1912):A Foucaultian Approach to the Education of Girls’Bodies)③此篇论文的中文版发表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第5期。为题的论文,通过对女子身体隐喻的话语分析,揭示了晚清政府对女子的规训与教化。以教育史、身体史、性别史融合的视角,运用文献分析法,笔者对晚清女子学堂中影响女子身体生成的多种因素作了历史分析和概括,澄清女子在晚清教育空间中的真实存在,也是对目前中国教育空间中女子实存状态的历史追溯。也是此次会议上,洪堡大学Marcelo Caruso提交了一篇探讨导生制初兴时期师生之间、生生之间身体接触的变化的论文,透视了教学组织方式变化下隐藏着的教育参与者的欲望、克己和肉体间的冲突的动态变化。受具身理论影响,2016年国际教育史学会第38届芝加哥年会再度提到隐喻在教育史研究中的问题,而且,具身理论在教育史研究中的应用,向教育史研究者提出了方法论的挑战,也即科学化史学的研究方法受到挑战。具身视角下的教育史研究采用跨学科,形成了话语、文本、隐喻及女性主义等具有“跨界”色彩的方法体系。本次会议的开幕式上,来自加拿大学者Mona Gleason以“隐喻应为教育史研究重要方法”为主题,做了题为《身体、隐喻与方法:教育史研究中“具身”的重要意义》的发言,探讨了“具身”及“隐喻”给教育史研究的问题、理论及方法将要带来的改变。笔者关于民国女学生剪发运动的研究④此篇论文中文版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年第4期。,打破了传统的以巨大的非个人结构考察近代教育的惯习,借助女学生剪发这一身体隐喻,通过爬梳近代女学生剪发的演变,动态呈现了近代国权、女权、政权在女学生身体上的角逐,以身体为切入点对近代教育历史进行了深度审视与考量。专题讨论中,各国学者继续这一议题的研讨。奥地利学者Sabine Krause组织了以“具身概念:教育实践中的身体与情绪”为主旨的讨论,来自美国、瑞士、奥地利等国学者在“身心合一”“心智统一”的理论前提下,探讨了身体建构在道德意识、爱国情感、种族意识等诸种情感养成中的重要作用。另一组以“身体:教育的隐喻”为主题的圆桌讨论中,来自德国、英国、美国、尼日利亚等国的学者集中批判了意识哲学主导下教育中的身体观及其带来的对教育的恶劣影响,提出把“人视为一个生态系统”,从生态学的视角出发看待教育中的身体。
身体隐喻视角下的教育研究,借助身体隐喻投射的过程,关注个人在教育变迁中的变化,重新审视以往的教育史研究,表达出教育史对人生成的关怀。
3.具身理论与女子教育史研究
具身理论给女子教育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别样视角。目前女子教育史研究参照传统教育史研究范式,表现为很强的男性视角下的女子教育史研究,未能突出女性性别特色在教育中的表现。近些年来,受社会性别理论影响,女子教育史研究中逐渐确立性别视角。性别视角下的女子教育史突破了对女子教育进程的宏大叙事模式,打破了男性视角,着眼于探究教育中女性意识及女性主体的建构,力求用理论概括女子教育现象的本质,理解女子教育产生发展的进程及原因。自身的学术反思、批判、发展力量及对现实的关照,使得探究教育与女性意识及女性主体建构的关系成为女子教育史研究新的取向。对性别意识及性别问题的批判与分析,很容易引起对身体的关注。而且,由于女性在父权制的正统历史中长期处于“失语”境地,研究女性及女子教育的资料匮乏,作为政治、历史、文化载体的身体,成为研究女子教育史的较佳着眼点。身体被很多研究者作为深入女性史的着眼点,以思考文化对身体的建构。美国汉学家高彦颐(Dorothy Ko)通过融合身体史与女性史,以中国女性的缠足为聚集点,借助绣花鞋、图像、文学作品等多样化的材料,用女性缠足的身体诉说还原“失语”的妇女历史,展现了中国妇女在自己的文化生存中的能动性。[10]其研究成果堪称融合性别史与身体史研究范式的典范之作。
女性主义与身体史研究可谓是相互推动、相得益彰。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r)谈到身体史的兴起时,曾说:身体史与性别史、性态史相联系。[11]欧洲中世纪史学者卡洛琳·拜纳姆(Caroline Bynum)也指出:目前有关身体的讨论实际上是有关性和性别的研究。[12]1-33英国著名的医学史研究者罗伊·波特(Roy Porter)甚至认为:最近较好的身体研究是由女性主义者完成的。[13]207身体作为社会历史、文化的载体,成为历史上未获得文本记录而处于失语境地的女性的活化石,受到女性主义研究者的关注,成为他们揭开社会意识形态秘密的切入点。2016年国际教育史学会第38届芝加哥年学会上,数位与会学者从具身视角来审视与考量女子教育历史的发言几度掀起讨论热潮。在“性别隔离与教育空间的重要性”议题的讨论中,学者们从身体、空间的角度探讨了教育空间通过对女性身体的建构,而对女性性别认知、主体意识等形成的影响。学者们一致同意教育空间的设计,比如学校卫生间的设计、寄宿学校宿舍的物理环境等无声地表达着社会主流的性别认知,同时,借助于空间,性别化的身体得以形塑。另一组“学校中性别化的身体”中,韩国、美国、巴西等学者分别讨论了学校教育规训女性国民、女子教育如何走出男女对立的阻碍等问题,提出了“学校是性别化规训的重要场所”这一观点。在“阅读、书写与性别化身体”小组,来自芬兰、美国、日本的学者从教育杂志、学生小说等对女孩子形象的塑造与描写,考察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女性角色期待,及其深层次的政治与文化原因。
具身理论的应用使得女子教育史研究获得了新的视角和产生了新的发展内涵。身体视角下的女子教育史,通过运用话语分析、文本阐释等方法,让身体张口表达沉寂久远的女子教育历史活动,再现和还原女子身体在教育活动中的历史书写,洞察教育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建构及影响。
四、关注“情感”:具身教育史研究之应然
具身观是沟通身体史与情感史的桥梁。具身观不仅主张身体和心智统合为一个整体,而且认为与身体紧密联系的心与智也是一种整体性活动,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发挥统一的作用。澳大利亚学者M O Loughlin指出:“学生的学习不可能没有情绪的卷入,而这种情绪的卷入不可避免是具身的。当然,这些被卷入的情绪既不在心智中,也不在身体中,而是位于与客观世界的具身性互动中。”[14]具身观强调的是人的实践活动是身体与环境互动的整体活动,既有意志和行为的成分,也有认知与情绪的成分,因此,对教育历史的研究与审视不能一味希求构建对教育的理性思考和行动,因为“教育空间”的形成及其影响,必然含有很多情感、情绪的因素。换而言之,教育空间内的许多行为,单从理性的层面无法给出完整的解释。但是,如果认为情感超越了时间与空间,也就无法在教育史研究中谈起情感,因为“史学关注的是事物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中所呈现的变化”[15]。实际上,目前史学界对“人类情感”几乎达成了一致的认识:“人的情感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改变;历史上无论是社会的变革或停滞,其中情感因素都扮演重要角色。”[16]质言之,肯定了“人类情感”具有时间性、社会性及历史性。2015年在中国举办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共有四大主题。其中之一乃是“历史中的情感”(Historicizing Emotions),由此可见“情感的历史化”研究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史学潮流,也说明情感建构的社会属性与文化因素为学者们所强调和重视。
20世纪90年代末期,英国学者Megan Boler出版了《感情的力量:情感与教育》(Feeling Power:Emotions and Education)一书,作者从文化史的视角考察了不同层次的教育及各种教育理论如何规训、压抑或忽视学生的情感因素,可谓是教育情感史研究不可多得的范例。目前,国际上教育情感史的研究主要是一种采纳福柯的“治理研究”视角的情感史取向①,比如探讨学校教育对学生“国家认同”“忠君爱国”“种族意识”等情感的培养。这种研究取向视“情感”为“可以习得的惯习”,是与其他行为一样可以控制、习得及退化的一种行为[17]21,因此,重视调控情感行为的各种规章制度及其他影响因素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治理视角”的教育情感史研究取向在今后一段时间仍将持续深入下去。荷兰学者Jeroen J.H.Dekker对“情绪调控”的研究体现了这一趋向。融合了身体史与情感史,该学者考察了17世纪在欧洲父母及年轻人中盛行的“道德素养”养成运动,剖析了支持该运动的“情感理论”,彼时感情被视为欲望、是恶的,应该受到压制和调控。这种“情感理论”与目前欧洲流行的、认为感情乃创造之源泉的“情感理论”相去甚远。
受具身观影响,教育史学者渐渐地从更为关涉身体的角度考察教育中的情感,有些学者称之为“情绪转向”。情绪转向的教育情感史研究最大的挑战在于确保之前“治理视角”下被忽略的、关涉身体的情感部分。这种转向将会扭转把学校理解为一个治理机构的传统认识,学校恢复其为启迪人成长与生成的空间的本真意义。这种转向也将在三个方面改变教育历史研究能力:一是弱化传统教育史研究中的“因果思维”定式,形成网状化的问题思考方式;二是更为关涉身体的情绪转向,强调教育机构的生成性,以生成性眼光指导历史研究;三是拓展了教育史研究范围,研究更为关注微观的、具体的、短暂的事实。[18]
①相关研究有:2016年国际教育史学会第37届伊斯坦布尔年会上,智利学者Pablo Toro Blanco提交了名为《表达国家情感的身体:国家主义与智利中等教育关于学生身体的话语(1870—1960)》的论文,考察了1870—1960年间智利中等教育通过建构学生身体,而激发学生国民意识和国民情感教育事实,继而试着回答以下问题:教育如何在不同时期通过身体影响学生既存的情感?青年人的情感如何通过一定的身体行为,例如学校体操和爱国仪式,得以宣泄?在智利将近百年的中等教育中,学生情感、国家主义与学生相应的身体表达间的关系模式应当如何认识?国际教育史学会第38届芝加哥年会上,来自德国、美国、智利、巴西等国家的学者提交了数篇“治理”视角的情感史研究论文,如美国学者Mary Ann Stankiewicz的《学生的身体、国家的身体:对艺术系学生近半个世纪的规训》、德国学者Martin Viehhauser的《学校建筑物的教育意义:爱国情感的涵养》、德国学者Michael Annegarn-Glab的《两次战争间教育影片中的殖民化身体书写》等。
[1]李浩吾.教育史ABC[J].上海:ABC丛书社,1929.
[2]周娜.呼唤关照儿童身体的德育[J].中小学德育,2015,(2).
[3]Bresler L. Knowing bodies,moving minds:towards embodied teaching and learning[M]. Bost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4.
[4]叶浩生.身体与学习——具身认知及其对传统教育观的挑战[J].教育研究,2015,(4).
[5]约翰·塞尔.心灵、语言和社会:实在世界中的哲学[M].李步楼,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6]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7]Lakoff G,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
[8]杜丽红.西方身体史研究述评[J].史学理论研究,2009,(3).
[9]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0]高彦颐.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M].苗延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11]彼得·伯克.西方新文化社会史[J].历史教学问题,2000,(4).
[12]Bynum C. Why all the fuss about the body? A medievalist’s perspective[J]. Critical Inquiry,1995,22(1).
[13]Burker P.“History of the b ody”,in new perspective on historical writing[M]. Pennsylvani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
[14]Loughlin M O. Paying attention to bodies in education :theoretical resources and practical suggestions[J]. Educational Philosophy & Theory,1998,30(3).
[15]王晴佳.当代史学的“情感转向”: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和情感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15,(4).
[16]诺亚·索贝.教育史中的情感与情绪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4).
[17]Reddy W M. The navi gation of feeling:a framework for the hist ory of emotion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18]Sobe N W. Researching emotion and affect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J]. History of Education,2012,(41).
Bodies, Metaphors and Education:the Importance of Embodiment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ZHOU Na1ZHOU Hong-yu2
(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2. School of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ment serves as a respond to new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his tory of education, offering new theories and m ethods to it. As a theory, embodied research emphasizes presence and involvement of body in the research of history, challenges the epistemological paradigm of the his tory of embodied education and promotes “turn of body” in the his tory of education. As a method, embodied research not only provides a new angle for scholars concerning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and its transition, but also theoretical basis for discourse analysis, metaphor, etc. Embodied research centers around emotion and links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al body and that of educational emotion. It transforms governmentality approaches into emotional ones which involve body.
history of education; embodied research; body; turn of emotion
周娜(1980— ),女,河南沈丘人,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女子教育史、身体教育史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学一般项目“教育活动史研究与教育史学科建设”(项目编号:BOA13011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教育学重大招标课题“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VEA150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G511
A
2095-7068(2017)04-0036-09
2017-09-12
10.19563/j.cnki.sdjk.2017.04.005
罗雯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