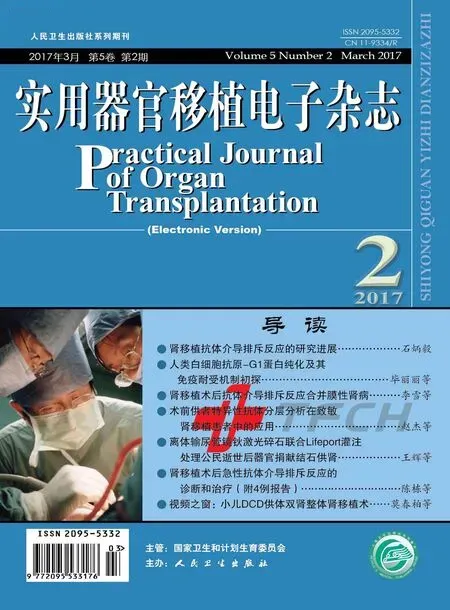肾移植抗体介导排斥反应的研究进展
石炳毅(解放军第309医院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北京 100091)
近年来,移植外科、移植病理学以及移植免疫学的研究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促进了人们对器官移植排斥反应机制、诊断及治疗的认识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初,Halloran等[1-2]确立了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 HLA)抗体在移植肾排斥反应损伤中的重要作用。Feucht等[3]把移植肾活检中的C4d沉积作为抗体介导免疫损伤的特异指标,此后抗体介导排斥反应(antibody mediated rejection, AMR)才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不断深入研究。HLA 抗体检测技术的发展使供体特异性抗体(donor specific antibodie,DSA)的研究更进一步深入,为AMR的病理生理机制和临床诊断提供了重要的工具,为AMR临床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1 AMR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
急性AMR主要表现为微血管炎,肾小球炎和管周毛细血管炎。急性AMR可迁延为慢性移植物损伤,包括移植肾肾小球病(transplant glomerulopathy, TG)、动脉内膜纤维化和间质纤维化/小管萎缩[4]。TG与移植肾失功具有密切的相关性。急性AMR可能在移植后任何时间发生,晚期发生的AMR是移植肾失功的主要原因,多与新生 DSA(de novo DSA,dnDSA)相关[5]。
AMR分为2种类型:1型AMR是移植前致敏的预存DSA所致,发生在肾移植术后早期;2型AMR则由移植后dnDSA所介导,往往发生在至少1年以后[6]。2种类型的AMR在病理特征方面有所不同,例如C4d是否阳性以及是否合并细胞免疫介导的损伤等。Haas等[7]将80例诊断为AMR的受者分为1型组(37例)和2型组(43例)进行比较,发现2型组受者AMR的发生多与HLA-Ⅱ类抗体相关,更多发生间质纤维化/小管萎缩等,且多合并细胞介导排斥反应。通过单因素分析得出结论,2型AMR组受者移植肾的存活时间低于1型AMR组。1型AMR多发生于再次移植的受者,与Ⅰ、 Ⅱ类DSA均相关,急性活动性改变较多见,一般不合并或仅伴有边界性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
研究表明,除了HLA抗体之外尚存在许多非HLA抗体与内皮细胞抗原相互作用而参与AMR的机制[8]。例如血管紧张素Ⅱ 1型受体抗体就是移植物失功的独立危险因素,其AMR病理损伤与DSA 并不相关[9]。MHC I类相关链 A(MHC class I-related chain A, MICA)抗体阳性的受者排斥反应以及移植物失功的风险增高[10]。许多其他抗血管内皮细胞的非HLA抗体也不断被发现,包括集聚蛋白、波形蛋白、凝集素内皮因子、Fms样酪氨酸激酶3配体、EFG样重复序列黏盘基蛋白I样结构域3和细胞间黏附分子4等[11]。
体液免疫的主要过程是:抗体与内皮细胞的靶点结合,通过经典途径激活补体,使补体从抗炎介质反转移为促炎效应机制[12]。补体裂解产物可以作为淋巴细胞的激活剂,最终形成膜攻击复合物(membrance attack complex,MAC),破坏内皮细胞的保护机制使其发生裂解[13]。激活的内皮细胞释放von Willebrane因子,快速结合和激活血小板,加速炎症和内皮损伤[14]。补体的Fc段与单核细胞、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和NK细胞结合。通过对AMR活检标本微阵列的分析表明,非补体依赖的C4d阴性的损伤机制主要以抗体依赖的细胞毒作用为代表。抗体的Fc段与NK细胞结合引起细胞毒颗粒的释放并刺激细胞因子〔包括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及γ-干扰素(interferon-γ,INF-γ)〕的产生,这一过程与慢性AMR相关。
2 分子病理学诊断技术的进展
由于DSA检测、C4d评估和组织学检查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促进了人们探索其他诊断方法的热情,其中一个热点问题就是分子病理学技术[15]。Sis等[16]研究发现,在AMR的组织中不论C4d是否表达,均有ENDAT的表达。相比于C4d, ENDAT表达能更好地预测移植物丢失,敏感度高(71%比31%),但特异度较差(71% 比 94%)[16]。Sellarés等[17]通过评估403例C4d阳性/阴性 AMR的活检组织病理特点,发明了AMR评分。常规诊断AMR的评分较高,并且高评分能够预测移植物丢失。Loupy等[15]在对早期AMR常规诊断的基础上加入了AMR分子评分和ENDAT评分,发现这些因素能独立预测移植物丢失。有时在组织结构相似的AMR病例中,其评分差异性却很大,优势更明显,更有助于危险分级和精准治疗。关于使用血尿样本评估基因转录和蛋白质特征的方法也在研究中[15]。
3 预后和风险分层
急性AMR、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和无排斥反应这三者相比,前者移植肾的转归明显较差。Lefaucheur等[18]基于10年随访的2 079例患者,定义了移植肾排斥反应的4种类型:T细胞介导的血管性排斥反应、抗体介导的血管性排斥反应、没有血管炎的T细胞介导排斥反应和没有血管炎的抗体介导排斥反应,与没有血管炎的T细胞介导排斥反应组相比,抗体介导的血管性排斥反应组移植物丢失率增加了9.07倍,没有血管炎的抗体介导排斥反应组增加了3.1倍。Orandi等[21]近期的研究表明,在2000-2012年移植的2 316例受者中 (10%HLA不相容受者并进行脱敏治疗),6%的受者在移植1年内出现临床确诊的急性AMR, 该组受者5年移植物存活率为69.5%, 而无急性AMR的对照组为92.5%,且早期发生排斥反应的受者移植物丢失率增加5.79倍。Dörje等[19]对2005-2011年移植的受者进行研究,发现67例临床诊断AMR的受者移植物丢失的风险与排斥反应发生时间相关,早期和晚期急性AMR受者4年移植物丢失率分别为25%和40%,早期和晚期T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受者4年移植物丢失率分别为19%和31%。
在一些研究队列中,HLA不相容的移植能将急性AMR的风险增至50%[20]。急性AMR的发生率和移植物丢失率与DSA浓度成正相关[21]。研究表明,导致急性AMR风险增加的DSA平均荧光强度(mean flurescence intensity, MFI)具体数值亦不尽相同[22]。例如,一项研究表明Ⅰ、 Ⅱ类DSA数值仅为100和200即可显著增加急性AMR的风险[23]。然而,Malheiro等[24]采用单抗原磁珠法对462例受者行移植前细胞毒性交叉配型,结果表明,35% DSA阳性者术后1年内发生急性AMR,而DSA阴性者仅为0.9%。DSA MFI大于3 000与急性AMR相关,大于11 000者急性AMR的发生率高达92.3%。Kannabhiran等[25]筛查了543例受者术前DSA,发现MFI值大于6 000能预测移植物1年存活率。在不同方法预测急性AMR风险的研究中,DSA MFI 的阈值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的原因包括不同研究中研究人群的差异、HLA不相容性水平、术前DSA检测方法、研究方案、脱敏方案以及术后DSA检测和治疗方案的不同。
尽管急性AMR的诊断依赖于术后DSA检测,但并非所有DSA都是有害的。大量研究致力于主要的致病变量,包括临床背景信息、MFI、补体结合和IgG亚群等。术后DSA常规监测能减少HLA不相容移植受体急性AMR的发生[26-27];但是对于免疫风险较低的受者而言,此类研究较少[28-29]。一项对于244例术前DSA阴性、术后新发DSA的前瞻性研究表明,119例患者出现dnDSA阳性和AMR,而只有3例患者在AMR发生前检测到DSA[28]。急性排斥反应前的任何形式在任意时段检测到DSA,对于移植物存活率的预测价值均较低[28,30],而延迟恢复、依从性差、小管炎、慢性肾小球炎、DSA MFI值等更能预测移植物丢失[31]。Everly等[32-33]的研究表明,急性AMR治疗后DSA MFI下降50%或更多,则明显改善移植物存活率。
考虑到DSA的出现常导致补体介导移植物损伤,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风险分级DSA。因为C1q是激活经典补体途径的第一步,所以DSA检测常结合C1q进行。Loupy等[34]对1 016例移植受者进行了补体结合DSA检测,研究发现这些抗体阳性者急性AMR的发生率较高、移植物损伤严重、移植物丢失率增加4倍。同样,术前DSA结合补体检测可以预测术后急性AMR的发生[35]。特定IgG亚群,尤其是IgG1和IgG3与补体结合力更强,能用于受者风险分级。Lefaucheur等[36]的研究纳入了125例术后1年内DSA阳性的受者,结果发现体内存在IgG3亚群者排斥反应发生更快、微循环损伤更重、C4d的沉积更多,而且多数发生急性AMR。
在“C4d阴性急性AMR”作为病理诊断之前,大量研究结果表明,与活检样本C4d阴性相比,C4d沉积阳性患者的转归较差[37-38],并且转归结局受C4d沉积强度的影响[39-40]。近几年,关于C4d阴性AMR的定义更趋清晰,新型分子诊断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C4d检测因其具有局限性而变得不再重要。然而,小管周围毛细血管C4d出现对急性AMR的诊断仍具有重要意义。Orandi等[41]的研究对比了156例C4d阳性AMR和51例C4d阴性AMR,发现C4d阳性容易更早出现移植物损伤。Kikić等[42]研究了1 976例组织样本,检测C4d和AMR组织损伤相关性,结果发现无论是否伴有AMR征象,C4d阳性受者移植物存活率均较低。相反,一些研究证明微血管炎症比C4d预测预后的意义更大[43]。
4 防治策略
AMR的治疗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① 抑制T淋巴细胞依赖抗体反应,如抗淋巴细胞抗体,霉酚酸酯,钙调磷酸酶抑制剂;② 清除循环HLA抗体,如血浆置换或免疫吸附;③ 抑制抗体,如静脉输注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IVIG);④ 清除B淋巴细胞、记忆B淋巴细胞、阻断补体激活途径。以减少体内B细胞和浆细胞池为目的的挽救性脾切除术可作为急性AMR治疗的最后选择。
AMR预防的意义大于治疗,两者所采取的措施相似。致敏患者肾移植术前进行脱敏治疗,清除和抑制抗体产生,可以有效降低术后AMR;术后充分的免疫抑制可以减少dnDSA的产生。急性AMR常用的治疗措施包括血浆置换、蛋白A免疫吸附、IVIG、ATG、利妥昔单抗等。多数治疗方案以血浆置换为基础,进行抗体清除,联合或不联合IVIG,其治疗有效率高达80%~90%[44-47]。IVIG可补充血浆置换造成的免疫球蛋白丢失,减少患者感染风险,大剂量IVIG对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具有免疫调节作用,可诱导B细胞凋亡和调节B细胞信号,也可抑制抗体和移植物的结合以及补体系统的激活,但其作用机制至今未完全明确[48-49]。应根据理想体重而非实际体重决定IVIG的使用剂量,且需在血浆置换后给予。无论是使用大剂量(2 g/kg)还是小剂量(100~500 mg/kg)IVIG,其治疗有效率为50%~90%[50-53]。血浆置换及IVIG治疗也存在某些风险,包括感染、血栓、溶血性贫血、肾功能衰竭和脑膜炎[54]。尽管血浆置换联合IVIG已广泛应用于AMR的治疗中,但目前有效的随机对照研究提供的高级别证据支持仍然有限。
目前已应用于治疗AMR的清除B淋巴细胞或抑制B淋巴细胞活化的方案主要包括ATG、利妥昔单抗以及阿伦单抗。利妥昔单抗联合血浆置换和IVIG (或不用)治疗急性AMR的报道较多,治疗有效率为75%~100%[55-59]。阿伦单抗虽然可以有效且迅速清除淋巴细胞,但T细胞在治疗6~12个月,B细胞在6个月内呈现恢复,且新产生的细胞有可能促进AMR的发生。硼替佐米(蛋白酶抑制剂,Bortezomib)可诱导浆细胞凋亡,阻止HLA抗体的产生,也有用其联合血浆置换和IVIG或利妥昔单抗成功的报道,治疗有效率为85%~100%[60-65]。移植术后6个月内的AMR,血清肌酐低于265.2 μmol/L或尿蛋白定量小于1 g/天时,硼替佐米的治疗效果更佳[61]。并且已经接受血浆置换、IVIG或利妥昔单抗治疗的AMR,再接受硼替佐米治疗仍可能有效[56]。
补体激活是AMR发生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治疗AMR的主攻方向。艾库组单抗通过抑制补体C5向C5a和C5b裂解,阻止炎症因子C5a的释放及C5b-9的形成,从而抑制抗体对移植物的直接损伤,但其对DSA作用甚微。TNT003是一种新型补体C1的单克隆抗体,可抑制由HLA-Ⅰ、 Ⅱ类抗体诱导的补体活化,阻止补体经典途径的激活,减少HLA抗体诱导的C3d沉积,阻断补体在内皮细胞的沉积以及补体裂解产物的形成[66]。
新型药物制剂还包括新型蛋白酶抑制剂 (ixazomib)[67],针对B淋巴细胞活化及存活的单克隆抗体(atacicept)[68],强效抗 CD20抗体奥法木单抗(ofatumumab)和奥克雷珠单抗(ocrelizumab), 抗CD22抗 体 依 帕 珠 单 抗(epratuzumab)以及以B细胞活化因子(B cell activating factor,BAFF)为靶向的药物制剂如阿塞西普(atacicept)和贝利单抗(belimumab)[69-70]。
目前,急性AMR的治疗仍处于探索阶段,共识和指南尚缺乏有力证据的支持,推荐意见包括单独或者联合应用糖皮质激素、血浆置换、IVIG、抗CD-20抗体和淋巴细胞清除抗体等。
亚临床AMR定义为活检存在免疫组织损伤证据但移植肾功能正常。持续存在的免疫损伤可造成慢性微血管改变导致慢性AMR,但是否对该类型进行治疗目前尚无定论。因此,建议对致敏、DSA阳性受者于移植术后3个月进行程序性活检,以决定有效的治疗措施与时机,改善患者预后。慢性AMR可造成移植肾组织不可逆的免疫损伤,明显降低移植肾存活率,治疗更为困难和棘手。
5 结 论
AMR是导致移植肾失功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人们对AMR病理生理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临床诊断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由于AMR治疗的复杂性和不统一性,新的治疗方案和新型药物也呈现出百花争艳的趋势。术前的免疫筛查、术后的DSA监测和合理选用免疫抑制剂方案可有效降低AMR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