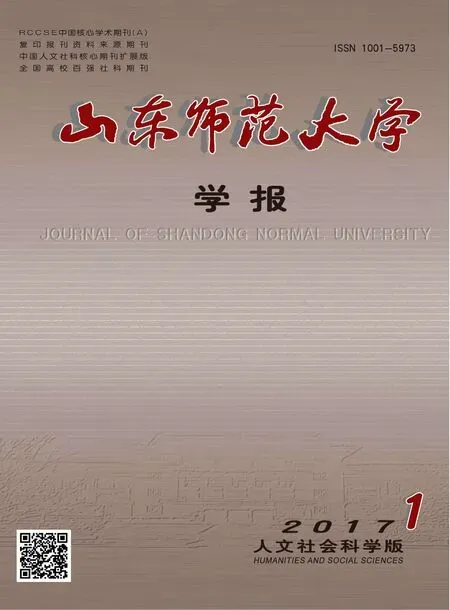汉代臣子承天变之责的理论基础与转折事件*①
陈敏学
(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
汉代臣子承天变之责的理论基础与转折事件*①
陈敏学
(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
臣子是汉代异常天象的主要责任承担者。汉代臣子承天变之责存在两种主流理论 :“阴盛阳衰”说和官员失职说。解析者解析异常天象时,或取其中一说,或兼采两说。韩婴生活的时期,三公各自对不同灾异负责的思想已经形成。新莽时,三公各司其责在国家层面上得以确认。汉灵帝时因日食策免太尉近乎定制,是宦官权势达到顶点的一种表现。
汉代;异常天象;臣子之责;理论基础;转折事件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17.01.012
学界对于古代异常天象等灾异的责任分配问题多有论述,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天象的信仰与天变的负责者”一章中阐述了从商至汉天变的负责者的演变过程。②顾颉刚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 :群联出版社,1955年。于振波的《汉代“天人感应”思想对宰相制度的影响》一文,探讨了“天人感应”思想演化发展的过程、汉代异常天象等“灾异”责任的转移,以及因“灾异”策免三公制度的形成等问题。③于振波 :《汉代“天人感应”思想对宰相制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6期。焦培民、刘春雨、贺予新合著《中国灾害通史·秦汉卷》,书中设专题讨论汉代“因灾免官”。④焦培民、刘春雨、贺予新 :《中国灾害通史·秦汉卷》,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263页。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一书中,“罪己与问责 :灾异咎责与汉唐间的政治变革”一节对汉唐间灾异责任分配方式的变化,以及灾异论影响和最终融入政治体制的过程,作了深入研究。⑤陈侃理 :《儒学、数术与政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9-210页。本文在吸收借鉴过往主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汉代官员承担异常天象之责的理论基础和转折性事件作进一步讨论。
一、官员承天变之责的两种理论
异常天象发生后,以臣子作为责任承担者,大体上有两类主流理论或曰推说方式 :一是所谓“阴侵阳臣颛君”即“阴盛阳衰”;二是官员失职或官非其人。
(一)“阴盛阳衰”说的源流
《春秋繁露·精华》曰 :“大水者,阴灭阳也。阴灭阳者,卑胜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贱伤贵者,逆节也。”*董仲舒著,苏舆义证,钟哲点校 :《春秋繁露义证》,北京 :中华书局,1992年,第86-87页。董仲舒认为日食是“阴灭阳”的表现,对应“下犯上”、“贱伤贵”的行为。类似思想在张敞给宣帝的封事中也有所体现,地节二年(前68),大将军霍光薨,宣帝亲政,“封光兄孙山、云皆为列侯,以光子禹为大司马。顷之,山、云以过归第,霍氏诸壻亲属颇出补吏”*班固 :《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3217页。,张敞上封事曰 :
臣闻公子季友有功于鲁,大夫赵衰有功于晋,大夫田完有功于齐,皆畴其庸,延及子孙,终后田氏篡齐,赵氏分晋,季氏颛鲁。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讥世卿最甚。乃者大将军决大计,安宗庙,定天下,功亦不细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将军二十岁,海内之命,断于掌握。方其隆时,感动天地,侵迫阴阳,月朓日蚀,昼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祅祥变怪,不可胜记,皆阴类盛长,臣下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襃宠故大将军以报功德足矣。间者辅臣颛政,贵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请罢霍氏三侯皆就弟。*班固 :《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3217—3218页。
张敞认为“月朓日蚀”等灾异“皆阴类盛长,臣下颛制之所生也”,以指霍氏之咎。成帝即位后,大权旁落外戚王凤之手,又久无继嗣,“阴盛阳衰”之说日兴。先是建始元年(前32)夏,黄雾四塞,“天子以问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对皆以为‘阴盛侵阳之气也。高祖之约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为侯,非高祖之约,外戚未曾有也,故天为见异。’”*班固 :《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4017页。但王凤集团亦不乏善说灾异者,杜钦对策建始三年冬十二月日食时,以臣为君之阴、子为父之阴、妻为夫之阴、夷狄为中国之阴,根据《春秋》把“卑胜尊”、“下犯上”等“阳微阴盛”的行为具体分为夷狄侵中国、政权在臣下、妇乘夫、臣子背君父几类,在承认“政权在臣下”是日食重要起因的同时,指出后宫女宠才是这次的日食真正起因,其结论也得到成帝认可。政治嗅觉敏锐的王凤迅速掌握了这一进言方法,言阳朔元年日食为“阴盛之象”,乃定陶王留侍京师所致。随后王章说日蚀之咎在王凤而非定陶王,使用的言辞同样是“阴侵阳臣颛君”。梅福亦曰 :“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夺,外戚之权日以益隆,陛下不见其形,愿察其景。建始以来,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灾亡与比数。阴盛阳微,金铁为飞,此何景也!”*班固 :《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2922页。可见此时“阴盛阳衰”一类的说法已成为各方政治势力发表意见、争夺话语权的工具,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哀帝即位后,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重振朝纲,对王氏外戚权势有所削夺,但君权日衰的情势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扭转,丁氏、傅氏外戚势力崛起,尤以傅太后为甚,“太后从弟子傅迁在左右尤倾邪,上免官遣归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复留迁……胁于傅太后,皆此类也。”*班固 :《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3356-3357页。此时解说日食言“阴盛阳衰”,多指傅氏之咎。王嘉曰 :“山崩地动,日食于三朝,皆阴侵阳之戒也。前贤已再封,晏、商再易邑,业缘私横求,恩已过厚,求索自恣,不知厌足,甚伤尊尊之义,不可以示天下,为害痛矣!臣骄侵罔,阴阳失节,气感相动,害及身体。”*班固 :《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3498页。晏指傅晏、商指傅商,并将哀帝宠爱的董贤也一同算入。东汉和帝时,丁鸿因日食上封事劝和帝收窦氏之权,曰 :“日食者,臣乘君,阴陵阳”,*范晔、司马彪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1265页。也是“阴盛阳衰”思想的体现。“阴盛阳衰”说,除个别情况下用以指责后宫外,大多数用以指斥臣子(含外戚)之责。
(二)官员失职说的源流
在异常天象与臣子之责的解说关系中,还存在着一种思想,即官员的不称职或曰官非其人是天变的起因。吏治苛酷是宣帝朝面临的最严重的内政问题之一,据《汉书·刑法志》所载,经宣帝和路温舒、于定国、黄霸等官员的努力,“狱刑号为平矣”。*班固 :《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1102页。但从其后宣帝一系列诏书中可以看出,吏治苛酷问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扭转,却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地方上吏治苛酷问题仍然比较严重。
(地节四年)九月,诏曰 :“朕惟百姓失职不赡,遣使者循行郡国问民所疾苦。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之……”又曰 :“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称。今系者或以掠辜若饥寒瘐死狱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班固 :《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253页。
(元康二年)夏五月,诏曰 :“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增辞饰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实,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称,四方黎民将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吏务平法。”*班固 :《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255-256页。
在这种情况下,五凤四年(前54)夏四月出现日食,宣帝借此机会再行整顿吏治苛酷之举。
诏曰 :“皇天见异,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称也。以前使使者问民所疾苦,复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班固 :《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268页。
宣帝公开表明发生日食“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称”,即皇帝和官吏共同为这次日食负责,并非宣帝转嫁日食责任一言以蔽之,除儒家灾异思想的影响外,更多的是对元康二年夏五月诏书中“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称”的重申,其用意重点在于改善吏治苛酷。这是官员不称职或曰官非其人会导致异常天象这一思想在实际中的运用,此后元帝所云“至今有司执政,未得其中,施与禁切,未合民心。暴猛之俗弥长,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错躬。是以氛邪岁增,侵犯太阳,正气湛掩,日久夺光”*班固 :《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289页。,哀帝所言“至今有司执法,未得其中,或上暴虐,假势获名,温良宽柔,陷于亡灭。是故残贼弥长,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错躬。乃正月朔,日有蚀之”*班固 :《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343页。,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此思想源于《尚书·皋陶谟》 :“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尚书》,十三经注疏本,北京 :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39页。,大意为,不要让不称职者旷废官位,因为是上天安排了官职,人承天职,代行天事。古人又将天上星官与地上官员一一对应,《公羊传》解诂引《春秋说》云 :“立三台以为三公,北斗九星为九卿,二十七大夫内宿部卫之列,八十一纪以为元士,凡百二十官焉。”*《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北京 :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219页。《春秋合诚图》对此有着更加详细的描述 :“天不独立,阴阳俱动,扶佐立绪,合于二六,以三为举,故三能六星,两两而比,以为三公。三三而九,阳精起,故北斗九星以为九卿。三九二十七,故有摄提、少微、司空、执法、五诸侯,其星二十七,以为大夫。九九八十一,故内列倍卫阁道即位扶匡天子之类八十一星,以为元士。凡有百二十官,下应十二月。数之经纬,皆五精流气,以立宫廷。”*[日本]安居香山、中村璋八 :《纬书集成》,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70页。《潜夫论·忠贵》称其为“王者法天而建官”。*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 :《潜夫论笺校正》,北京 :中华书局,1985年,第108页。馆陶公主曾为子求郎,明帝不许,而赐钱千万,谓群臣曰 :“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范晔、司马彪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124页。,明确表达了对这一思想的赞同。
官员不称其职会引发天变的思想常被君主用以敦促臣下尽心修职,据《后汉书·诸帝纪》 :*范晔、司马彪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50、52、106、111、117、261页。
建武六年(30)日食诏,“有司修职,务遵法度。”
建武七年(31)日食诏,“其令有司各修职任,奉遵法度,惠兹元元。”
永平三年(60)日食诏,“有司勉思厥职,以匡无德。”
永平八年(65)日食诏,“群司勉修职事,极言无讳。”
永平十三年(70)日食诏,“刺史、太守详刑理冤,存恤鳏孤,勉思职焉。”
阳嘉元年(132)灾异(含客星)诏,“间者以来,吏政不勤,故灾咎屡臻,盗贼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选举不实,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书》歌股肱,《诗》刺三事。今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其简序先后,精核高下,岁月之次,文武之宜,务存厥衷。”
儒家士大夫也常常基于此劝谏君主,左雄给顺帝的封事中曰 :“永建二年,封阴谋之功,又有日食之变。数术之士,咸归咎于封爵”*范晔、司马彪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2021页。,即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这本来是有益于朝政的,但当君权旁落,外戚、宦官掌权之后,这种思想就变得十分危险,成为外戚、宦官打压和控制士大夫的借口,为因天变策免三公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两种理论的合流
在异常天象的解说中,“阴盛阳衰”说和官员失职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有的解说者在解说天象时兼采两种理论。汉哀帝因息夫躬之议,“拜孔乡侯傅晏为大司马卫将军,阳安侯丁明又为大司马票骑将军”。*班固 :《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2186页。元寿元年正月辛丑朔临拜时,发生日食,杜邺对曰 :
臣闻阳尊阴卑,卑者随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虽贱,各为其家阳;女虽贵,犹为其国阴……案春秋灾异,以指象为言语,故在于得一类而达之也。日食,明阳为阴所临……当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前后,临事而发者,明陛下谦逊无专,承指非一,所言輙听,所欲辄随,有罪恶者不坐辜罚,无功能者毕受官爵,流渐积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觉圣朝。*班固 :《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3475-3477页。
显然,杜邺在承袭“阴盛阳衰”思想的同时,也承袭了无功能者受官爵则日食现的思想,并将两者综合运用在解说之中。
东汉永平十八年(75)冬日食,马严上封事曰 :
臣闻日者众阳之长,食者阴侵之征。《书》曰 :“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绩黜陟,以明褒贬。无功不黜,则阴盛陵阳。臣伏见方今刺史太守专州典郡,不务奉事尽心为国,而司察偏阿,取与自己,同则举为尤异,异则中以刑法,不即垂头塞耳,采求财赂。今益州刺史朱酺、杨州刺史倪说、凉州刺史尹业等,每行考事,辄有物故, 又选举不实,曾无贬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宜勑正百司,各责以事,州郡所举,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范晔、司马彪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860页。
章帝纳其言免去朱酺等人。按照传统说法,阴侵阳应为政权在臣下,或曰臣颛君,和官吏不称职没有太多关系。而马严之说在杜邺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了两种思想,将“无功不黜”列入“阴盛阳衰”的起因,进而引起日食发生。这种融合虽有助于加强对不称职官员的弹劾力度,却不利于儒家士大夫对抗外戚、宦官。以顺帝时郎顗的进言为例。
去年已来,《兑卦》用事,类多不効。《易传》曰 :“有貌无实,佞人也;有实无貌,道人也。”寒温为实,清浊为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厉内荏,以虚事上,无佐国之实,故清浊效而寒温不效也,是以阴寒侵犯消息。占曰 :“日乘则有妖风,日蒙则有地裂。”如是三年,则致日食,阴侵其阳,渐积所致。
又曰 :
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与岁星合于房、心……《尚书洪范记》曰 :“月行中道,移节应期,德厚受福,重华留之。”重华者,谓岁星在心也。今太白从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贼,而反同合,此以阴陵阳,臣下专权之异也。*范晔、司马彪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1059、1073页。
郎顗前后所言天象虽不同,但依其所言,都是阴侵阳、阴陵阳之象。前一条与马严之说相类,融合阴盛阳衰和官非其人两种理论,认为三公不称其职、无佐国之实,是造成阴侵阳,导致日食的原因。后一条直接承袭“阴侵阳臣颛君”的思想,认为臣下专权是造成阴陵阳,导致“金木相贼”的原因。这种对阴侵阳、阴陵阳原因一分为二的剖析,并不利于说服皇帝,反而会分散皇帝的注意力,无形间削弱了对外戚、宦官“臣颛君”的批判,同时将三公置于天变之责的浪尖上。
二、“天有异象,责之司马(太尉)”的确立与终结
《韩诗外传》曰 :“三公者何?司空、司徒、司马也。司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阴阳不调,星辰失度,责之司马;山陵崩绝,川谷不流,责之司空;五谷不殖,草木不茂,责之司徒。”*范晔、司马彪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1065页。其作者韩婴生活在汉文帝至武帝时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外传数万言……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班固 :《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3613页。。三公各自对不同灾异负责的思想形成不会晚于这个时段。由于现实条件所限,这一思想长期停留在理论上。直至绥和改制*改制运动与灾异问责三公的相关内容可参见陈侃理 :《儒学、数术与政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3-199页。,成帝根据何武的意见依古制立三公,才为这一思想付诸实践提供了现实上的可能,“以大司马骠骑将军为大司马,罢将军官。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封为列侯。益大司马、大司空奉如丞相”*班固 :《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329页。。之后建平二年(5)曾一度恢复汉旧制*班固 :《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725页。,但至元寿二年,再立三公,并改丞相为大司徒*班固 :《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725页。。新莽始建国元年(9),王莽策群司曰 :
月刑元股左,司马典致武应,考方法矩,主司天文,钦若昊天,敬授民时,力来农事,以丰年谷。日德元厷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圜合规,主司人道,五教是辅,帅民承上,宣美风俗,五品乃训。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图,考度以绳,主司地里,平治水土,掌名山川,众殖鸟兽,蕃茂草木。*班固 :《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4101-4102页。
三公各司其责在国家层面上得到确认。在此基础上,天凤元年(14)到天凤三年(16)间,发生了三次和太阳有关的天变,分别对应三位大司马策免或左迁。
(天凤元年)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策大司马逯并曰 :“日食无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马印韨,就侯氏朝位。太傅平晏勿领尚书事,省侍中诸曹兼官者。以利苗男欣为大司马。”
(天凤二年)是时,日中见星。大司马苗欣左迁司命,以延德侯陈茂为大司马。
(天凤三年七月)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复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石举四行各一人。大司马陈茂以日食免,武建伯严尤为大司马。*班固 :《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4134、4139、4144页。
但是,因天变策免司马并未就此成为定制,由于王莽性格使然,其施政时常朝令夕改,这件事上也不例外。地皇元年(20),日正黑又变成了兆域大将军王匡的责任。
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恶之,下书曰 :“乃者日中见昧,阴薄阳,黑气为变,百姓莫不惊怪。兆域大将军王匡遣吏考问上变事者,欲蔽上之明,是以適见于天,以正于理,塞大异焉。”*班固 :《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4158页。
东汉安帝之前,没有因灾异策免三公之事,只是在永平十三年(70),“冬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三公免冠自劾”。*范晔、司马彪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117页。明帝制曰 :“冠履勿劾。灾异屡见,咎在朕躬。”*范晔、司马彪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117页。这件事从侧面说明了三公当为灾异负责的思想从未消失。“经过儒家改制运动,执政大臣对灾异负有责任已成为朝廷的共识。”*陈侃理 :《儒学、数术与政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1页。安帝永初元年(107),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因灾异被策免,东汉因灾异策免三公自此始。*《后汉书·徐防传》曰 :“凡三公以灾异策免,始自防也。”《太平御览》引《典略》曰 :“安帝永初元年,以灾故免司空尹勤。凡以灾寇故辄免三公,多以卿为之,或再三退而还,复其故,桓、灵又甚,自此始也。”《后汉书·安帝纪》 :“九月庚午……是日,太尉徐防免。辛未,司空尹勤免。”两人之免,仅差一日。此处暂并存徐防、尹勤说。“东汉中后期,灾异思想用于士大夫与戚宦之间的权力斗争,最后成为外戚、宦官打压和控制士大夫的手段。灾异责任本身逐渐形式化,变得有名无实。”*陈侃理 :《儒学、数术与政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0-201页。这个结论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具体到天变与策免三公的联系上来,梳理相关史料后会发现,从安帝到桓帝时期,因异常天象而策免三公(尤其是太尉)虽屡屡见诸史书,却还不是一种常态化的现象。据《后汉书》帝纪和《五行志》统计,安帝朝共发生日食十二次,*十二次日食发生时间为永初元年三月、永初五年正月、永初七年四月、元初元年十月、元初二年九月、元初三年三月、元初四年二月、元初五年八月、元初六年十二月、永宁元年七月、延光三年九月、延光四年三月。另《后汉书·安帝纪》载,元初三年三月日食,《后汉书·五行志》未载,查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郑州 :大象出版社,1997年)与刘次沅、马莉萍《中国历史日食典》(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均无,陈遵妫著、崔振华校订《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所载,《中国日食表》虽依据《日月食典》计入此次日食,但据朱文鑫在《历代日食考》(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4年)中推算,此次日食实乃澳洲可见,综上所述此次日食存疑,暂不计入。只有永初五年(111)日食发生后,以阴阳不和为由策免太尉张禹,《后汉书·安帝纪》 :“春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丙戌,郡国十地震。己丑,太尉张禹免”,*范晔、司马彪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216页。《后汉书·张禹传》 :“以阴阳不和策免。”*范晔、司马彪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1499页。另有一次星变逆行,中常侍樊丰借此构陷太尉杨震,致使杨震被策免,“会太史言星变逆行,遂共谮震云 :‘自赵腾死后,深用怨怼;且邓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及车驾行还,便时太学,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绶”*范晔、司马彪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1766页。。顺帝朝共发生日食五次*五次日食发生时间为永建二年七月、阳嘉四年闰月、永和三年十二月、永和五年五月、永和六年九月。,只有一次日食成为三公被免的原因。永建二年(127),“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壬午,太尉朱宠、司徒朱伥罢”*范晔、司马彪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254页。。另《后汉书·桓荣列传附桓焉传》 :“汉安元年,(桓焉)以日食免”*范晔、司马彪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1257页。,但《顺帝纪》和《五行志》皆未言汉安元年日食。*《后汉书·顺帝纪》曰 :“冬十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刘寿免”,未说明策免原因。《后汉纪·孝顺皇帝纪》 :“冬十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刘寿以灾异罢,”未说明灾异种类。查陈遵妫著、崔振华校订《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所载《中国日食表》、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刘次沅、马莉萍《中国历史日食典》均无汉安元年(142)十月日食。《后汉纪·孝顺皇帝纪》曰 :“(汉安元年)及是之时,连有变异。上思(梁)商言,召(周)举于显亲殿问之。”因周举之言乃有八使循行之事。《后汉书·周举列传》亦曰 :“时连有灾异,帝思商言,召举于显亲殿,问以变眚”。由此看来,策免桓焉之因当是“连有灾异”,日食仅是其中原因之一,当为永和六年(141)九月日食。《后汉书·桓荣列传附桓焉传》所载策免原因不甚准确。桓帝朝共发生日食九次*发生时间分别为建和元年正月、建和三年四月、元嘉二年七月、永兴二年九月、永寿三年闰月、延熹元年五月、延熹八年正月、延熹九年正月、永康元年五月。,仅有两次日食导致策免太尉。永兴二年(154)“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太尉胡广免,司徒黄琼为太尉”*范晔、司马彪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299-300页。。延熹元年(158)“(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甲子,太尉黄琼免,太常胡广为太尉”*范晔、司马彪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303-304页。。
灵帝朝的情况则与之前大有不同,这一时期共出现日食十三次(详见表1),其中九次日食发生后太尉被免,频率远超前几朝。四次没有策免太尉的日食中,除首次日食(建宁元年五月)外,其他三次各有其特殊原因。熹平二年(173)“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国重译贡献。太尉段颎罢。鲜卑寇幽并二州。癸酉晦,日有食之。三年春正月,夫馀国遣使贡献。二月己巳,大赦天下。太常陈耽为太尉”*范晔、司马彪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335页。。说明这次日食发生前,原太尉段颎已被罢免,新太尉还未曾任命,太尉一职无人担任。光和元年(178)二月日食发生时的情况与此相类,“光和元年春正月……太尉孟彧罢。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月辛丑,大赦天下,改元光和。太常常山张颢为太尉”*范晔、司马彪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340-341页。。这两次日食发生时,太尉一职暂空,自然不存在太尉因日食被免的情形。再说中平三年(186)五月日食,从中平二年(185)八月开始,张温率兵讨伐北宫伯玉、边章等人,《后汉书·灵帝纪》 :“八月,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讨北宫伯玉。”*范晔、司马彪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352页。《后汉纪·孝灵皇帝纪》 :“秋七月,车骑将军皇甫嵩征边章、韩约无功免。八月,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讨章、约。”*袁宏 :《后汉纪》,张烈点校 :《两汉纪》,北京 :中华书局,2002年,第485页。次年春,张温在外被任命为太尉,直至同年冬天返回京城洛阳,“三年春,遣使者持节就长安拜张温为太尉。三公在外,始之于温。其冬,征温还京师。”*范晔、司马彪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2321页。也就是说,中平三年五月日食发生时,张温正以太尉的身份领兵在外,如果以日食之因将其策免,显然非常不利于军心稳定,故这次日食也没有策免太尉。综上可见,除几次特殊情况外,灵帝朝因日食策免太尉是一种常态化行为,近乎于定制。从第一次日食发生时的情形来看,是时这种做法尚未开始,从建宁元年(168)五月到十月间,究竟是什么推动了这一常态化行为的产生?

表1 灵帝朝日食与太尉策免表
灵帝在位初期发生的最著名政治事件莫过于陈蕃窦武谋诛宦官失败,以及第二次党锢之祸,灵帝朝因日食策免太尉成为常态化行为也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建宁元年五月日食发生后,陈蕃因之说窦武曰 :“昔萧望之困一石显,近者李、杜诸公祸及妻子,况今石显数十辈乎!蕃以八十之年,欲为将军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罢宦官,以塞天变。”*范晔、司马彪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2242页。窦武遂建议太后尽诛宦官,但由于窦太后犹豫未决,故久未动手。至八月,侍中刘瑜善天官,以“太白出西方”其占不利上书太后曰 :“太白犯房左骖上将星,入太微,其占宫门当闭,将相不利,奸人在主傍。愿急防之”*范晔、司马彪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2243页。中华书局标点本为“太白犯房左骖,上将星入太微”。按《晋书·天文志》 :“房四星……下第一星,上将也;次,次将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天驷,为天马,主车驾。南星曰左骖,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骖”。左骖即房南第一星,为上将。又《续汉书·天文志》 :“太白在西方,入太微。”可知入太微者为太白,非上将星,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窦武列传》点断有误,改之。,“又与武、蕃书,以星辰错缪,不利大臣,宜速断大计。武、蕃得书将发”*范晔、司马彪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2243页。。结果事泄,宦官先发制人,窦武自杀,陈蕃等人遇害,窦太后被软禁。回顾整个事件,两次异常天象在中间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而早在延熹八年(165),刘瑜就曾上书以诸侯与星宿之联系劝说桓帝整饬宦官 :“盖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关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竞立胤嗣,继体传爵,或乞子疏属,或买儿市道,殆乖开国承家之义。”*范晔、司马彪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1855页。注曰 :“四七,二十八宿也。诸侯为天子守四方,犹天之有二十八宿。”*范晔、司马彪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1855页。桓帝“特诏召瑜问灾咎之征,指事案经谶以对”*范晔、司马彪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1857页。。刘瑜所对内容没有流传下来,其“尤善图谶、天文、历算之术”*范晔、司马彪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1854页。,由此可知大抵“案经谶”所对之事与天变等灾异关系密切。刘瑜被害后,“宦官悉焚其上书,以为讹言”*范晔、司马彪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1858页。,足见宦官对刘瑜之言的恐惧厌恶之情。窦太后被幽禁,宦官独揽朝政大权,又恐惧厌恶士大夫关于天变之咎的言论,势必要在这一方面也夺取与其执政地位相适应的话语权,将全部异常天象归咎于士大夫。介于此前早有因灾异策免三公乃至因天变策免太尉的先例,太尉自然成为承担异常天象之责的最佳对象,于是灵帝朝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以日食策免太尉成为一种常态。而士大夫的势力由于第二次党锢之祸受到重挫,无力改变这种局面。换言之,因日食策免太尉几近定制,正是宦官权势达到巅峰、士大夫对朝政影响跌至谷底的一种表现。
中平六年(189)八月,中常侍张让等杀大将军何进,司隶校尉袁绍勒兵尽诛宦官。执政大权先后落入董卓、曹操等人之手,官僚士大夫们成为朝中最重要的政治势力,因天变策免太尉的局面也因此得到改善。献帝初平三年(192)以日有重珥*《后汉书·皇甫嵩列传》曰 :“以流星策免”,张璠《后汉纪》同。《后汉书》注引《续汉书》曰 :“以日有重珥免。”《后汉纪·孝顺皇帝纪》曰 :“日有重晕。”袁松山《后汉书》曰 :“日有重两倍。”皆同《续汉书》。难断两说是非,并存之。策免太尉皇甫嵩,兴平元年(194)以日食策免太尉朱俊只是之前做法的惯性使然,此后再无类似事件。至魏黄初二年(211),借由魏文帝诏书,因异常天象策免太尉之事彻底淡出历史舞台,《太平御览》引《齐职仪》曰 :“魏文黄初二年,日蚀,奏免太尉贾诩。诏 :‘天地灾害,责在朕躬,勿贬三公。’遂为永制。”*李昉等 :《太平御览》,北京 :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994页。
责任编辑 :时晓红
Theoretical Basis and Transition Events of the Officials Who Were Liable for the Abnormal Astronomical Phenomena in the Han Dynasty
Chen Minxu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Officials were primarily liable for the abnormal astronomical phenomena occurring in the Han Dynasty. There existed two kinds of mainstream theories: one was “excess of Yin and shortage of Yang”; the other was official incompetence. When the analysts analyzed the causes of abnormal astronomical phenomena that had occurred, they may apply one of the theories or both. The thinking that the Three Councilors (san gong 三公) should be respectively liable for the different disasters that had occurred was formed in the period when Han Ying lived. Such thinking was validated at the national level in the Xin Dynasty. During Han Lingdi period, when a solar eclipse occurred, to remove Taiwei (太尉) was almost the policy,which showed that the power of eunuchs had reached the peak.
the Han Dynasty; abnormal astronomical phenomena; official’s liability; theoretical basis; transition events
2016-12-02
陈敏学(1982— ),女,黑龙江鸡西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为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项目“秦汉时期星占文化和政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得到“中央民族大学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经费”资助。
K232,P1-092
A
1001-5973(2017)01-012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