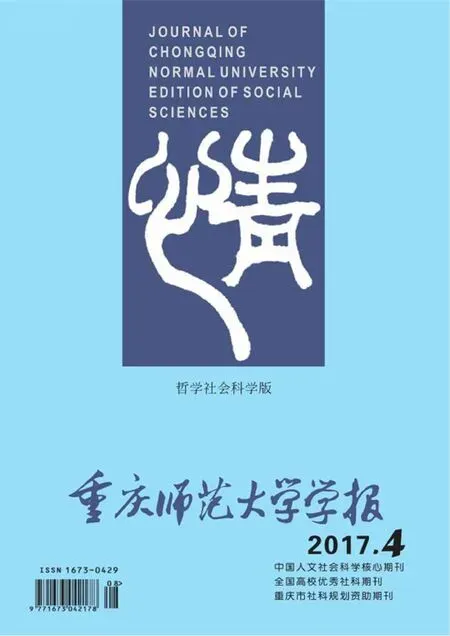董仲舒伦理教育思想探析
唐加祥 蒋 红
(1.重庆师范大学 学生处;2.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董仲舒伦理教育思想探析
唐加祥1蒋 红2
(1.重庆师范大学 学生处;2.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线,在吸收先秦法家、阴阳五行等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汉代儒家今文经学的伦理教育思想。董仲舒将伦理教育作为儒家教育思想的主线,其所主张的“三纲五常”“德主刑辅”的道德伦理教育内容,以及其教育原则和方法成为儒家伦理教育的典范。其思想既是对以前学说的继承,又有其自身特色,对西汉之后儒家伦理教育思想与人们的社会道德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汉;董仲舒;伦理教育思想
董仲舒不仅是西汉儒家今文经学大师,还是著名的教育家。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董仲舒早年刻苦习儒,志在经传,博览群书,继之收徒授业,汉景帝时就有了“专精于述古”的声誉,并担任博士官。公元前134年,武帝策贤良文学之士,提出“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1]《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以“天人三策”一举成名,被汉武帝封为中大夫。董仲舒一生著述甚多,但现仅存《春秋繁露》82篇,是研究其伦理教育思想的基本材料。
一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和公孙弘的提议,在都城长安设置了最高教育机构——太学。其中,以五经博士为教官,博士弟子为太学生。博士弟子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以儒家经学为教育内容的封建官学伦理教育的开始。随着儒学的独尊,西汉国家意识形态进一步儒学化,儒家经学逐渐成为汉代国家培养和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儒学伦理教育也随之扩展到私学、蒙学和家庭伦理教育各个领域,在汉代社会产生很大影响。
董仲舒的伦理教育思想可谓是应时而出。董仲舒学说以“公羊春秋”为典,以维护大一统封建王权为旨,以礼、法相兼为内容,将封建礼教纲常形而上学为“天道”的内涵,强调礼、仁的至上性、权威性,将“天道”观、封建伦理与社会治理有机结合起来。为此,董仲舒强烈主张实行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德教”,认为“德治”是天下唯一“大道之治”,“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2]《春秋繁露·保位权》董仲舒认为统治者应实行德政,以“德”为中心来治理国家进而达到“甘于饴蜜,固于胶漆”[2]《春秋繁露·立元神》的治理效果。董仲舒认为“圣人法天而立道”,“为政而宜于民者”,方可“受禄于天”。[1]《汉书·董仲舒传》上天是厚德薄刑,要改变民生困窘的实际,只有实施德政,“然后可善治也”[1]《汉书·食货志》。因此,王者要承天意以从事,修五常之道,“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1]《汉书·董仲舒传》,“以仁安人”,施教化,守等级,行仁政,采取任德教而不任刑罚的措施。
在董仲舒整个思想体系中,伦理学说占据其主要地位。为了说明封建伦理思想的合理性,董仲舒不仅将封建纲常上升到形而上学的“天道”高度,而且还从人性论的角度探讨伦理与教化的问题。董仲舒认为人性是“天”创造人类时赋予的一种先验的素质,这种素质秉承“天道”之善,因此从根源上看是人性善。人与万物同受命于天,但又超然于万物之上,为万物之灵,“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2]《春秋繁露·天辩在人》。正是由于人具备了万物所不具有的礼仪规范,并能主动地遵循一定的要求来约束自我,因而人比万物尊贵。人能明分使群,是具有道德意识的动物。人虽然有善端和善质,但同时人性并非天生就善,仍然具有作恶的可能性。董仲舒说:“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人的性情中有善之质而非善,“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米与善,人之继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为之内也。”[2]《春秋繁露·实性》在董仲舒看来,教化对于人性有着很大作用,“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虽生而具有善的品质,但其人格品质的形成则是后天教育的结果,由于人之性在成长中受到物欲的污染,因此又具有作恶的可能性。所以从人性上看,有三个不同等级。“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不可移易,而“中民之性”代表占据大多数人的万民之性,有着向善弃恶的广泛空间,因此方可“名性”。正是因为中品之人既有性善的一面,又有性恶的一面,因此董仲舒十分重视中品之人的伦理教育。董仲舒主张“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中品之人有性善的一面,有着善端和善质,就具备了接受王道、伦理教化的基础。所以,董仲舒认为封建道德教育具有“化民成性”的作用,其人性论的最后落脚点,仍然是强调王道教化对于万民成善的决定性作用,这也是儒家伦理教化思想的基本要点。
董仲舒在继承孟、荀人性论的基础上,融合阴阳思想,将人之情性纳入天人感应的“天道”思想中,提出了“性善情恶”的命题。董仲舒认为“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按照“人副天数”的推论,天有阴阳二气,人也就有贪、仁二性。有些人之所以具仁性是因为天施与的阳气多;有些人为贪性,是由于天施与的阴气多。董仲舒从自然法则中去寻找其主张的依据,把“法治”“德治”比附为自然界的阴阳关系,天意喜“阳”而厌“阴”,“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2]《春秋繁露·天道元二》“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2]《春秋繁露·天辨在人》。因此,最高统治者秉承上天的意志,按照“天道”的原则,来统治人间世界,以道德教化为主,刑为辅。“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也。”[1]《汉书·董仲舒传》因此,圣能的统治者必须任德而远刑。这就从理论上论证了“任德教而不任刑罚”的治术主张。
董仲舒进一步认为天下大治,此乃教化之功,伦理教育使人们在内心深处建立起一道防止贪欲的道德堤防,促使民众去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由于道德教化具备刑罚所不具有的优势特点,因而,古代的帝王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统治天下管理人民时,大多将道德教化放在首要地位。在中央设立太学,地方设立学校,进行封建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教化,使人民各方面行为习惯得到改善,触犯刑罚的人逐渐减少。而后世的子孙也在这种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下,遵守这样的生活习俗以及行为习惯,长此以往则天下就会得到大治,这些都归功于道德教化而非刑罚。因此,古代开明君主管理国家,没有不重视道德教化的。成康之世,以教化为主。相反,历史发展到了秦朝,则表现出不同,秦朝统治者推行法治,主张“以法治天下”,致使“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1]《汉书·董仲舒传》。所以,教化是本,刑罚是末,德刑互补,才能有效地维护封建统治。董仲舒认为,要想天下得到稳定发展,就必须要重视教化的作用,上层统治者需要对下层施行教化,进行思想意识方面的统治,从而在思想层面消除“作乱”的源头。
董仲舒还认为,情欲是造成社会罪恶的渊薮:“太富则骄,太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董仲舒指出情欲不加以约束,就会使“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2]《春秋繁露·度制》对人的性恶,董仲舒主张以礼、法来节制人的情欲,而民众是否依从礼、法,道德伦理教育就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天立帝王以教民,只有加强对“中品之人”的伦理教育才能稳定社会秩序。而统治者教化百姓也是受命于天,是其国家治理的基础。这样,伦理教育就成为社会整合与稳定的重要手段。
二
有学者认为:“西方文化的最高精神是外倾的宗教精神,中国文化的最高精神是内倾的道德精神。”[3]道德伦理教育是董仲舒经学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其成就儒家理想人格的必由之路。董仲舒以“儒学正统”的观念为出发点,将教学内容确定为儒家六经。其认为各经由于其阐释对象不一,各有其特点,因此其伦理教育的效果也不同,“《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4]作为“公羊春秋学”大师,董仲舒特别强调《春秋》的伦理教育意义。为了宣扬儒家伦理教育思想,董仲舒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儒家“仁、义、礼、智、信”形成其伦理教育思想体系。同时,由于儒家道德本体论的特殊形式,董仲舒认为在道德教化中应该结合 “天人感应”“阳尊阴卑”的观念进行。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2]《春秋繁露·基义》因此,道德教育的本体不是在物质世界中去寻找,而是在“天道”中去寻求。由于“三纲”是封建道德教化的一般标准,“五常”则是与个体的日常生活行为习惯相关的道德观念,是“三纲”总则赋诸个体并具体展开、广泛延伸于各种社会关系的个体品质的保证,因此将“三纲五常”作为道德伦理教育的中心内容即为顺理成章。
在伦理教育中,董仲舒主张 “躬自厚而薄责于外”,很注重“仁”的作用。
认为“仁人者,正其道不计其利,修其道不谋其功”。董仲舒对仁和智的辩证关系有充分认识,“不仁而有勇力才能,则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辩慧狷佞给,则迷而乘良马也。不仁不智有才能,将以其才能辅其邪狂之心,而赞其僻违之行,适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恶耳……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4]《春秋繁露·必仁且智》董仲舒强调“仁者爱人”,人和人之间应该具有良好的关系,互相爱戴,并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周围的人。而且也注重“吾日三省吾身”,用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提升个人的修养。他指出:“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1]《汉书·董仲舒传》认为在不断的道德修养过程中,德性就能逐渐养成,产生优良的效果。在“行道”中,使用“积少成多”的方法,循序渐进地养成良好的善行。在个人的品格养成方面,注重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积善成德,从而成就丰功伟业。董仲舒在道德教化实践中还强调“必仁且智”,主张教育过程中必须做到“仁”和“智”两者的统一。此外,董仲舒也强调礼乐教化,认为通过礼的形成对人的“欲”以适度的调节;乐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乐的利用可以陶冶情操,可以使人的品质更加完善。同时董仲舒也关注意志力的养成,认为只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力,才有可能迎难而上,不断开拓进取,进而达到博学的境界。
董仲舒认为,道德教化的关键在于对待“义和利”。他说:“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2]《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董仲舒主张对道义的追求应高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他明确义是封建统治下道德教化的尺度,利则是对个人欲望的满足。“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董仲舒对这一道德修养标准给予的总的表述。这一准则的提出也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教育产生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其与“天道”合一的道德教化内容中,董仲舒提出了道德教育的几个基本方法。
首先,董仲舒强调道德教育必须学习目的明确。董仲舒说: “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知先规而后为之。”[4]《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人们应该事先对“义”或“先规”(道德规范)有所知晓,如果“知之所不明”,那么就会影响其学习效用。在这里董仲舒强调了道德教育必须首先明确其学习目的的重要性,认为学习就是明白封建伦理纲常的大义,如果不能明确这个大义,就不会有很好的效用。
其次,董仲舒主张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博节适度。董仲舒认为,人的资材是不同的,有的人能够博、专兼得,有的人却只能够明其一理,因此应该使各自学习有所偏重。同时,还要博、节适度。从博的方面看,学习如果只通一经,局限性太大,不能真正领会圣贤思想。但是也不是越博越好,多则不容易消化,易于迷惑,不能真正理解经义。因此董仲舒主张“简六艺以赡养之”,并且参考《公羊传》等其它书籍,由此避免过博或者过节。董仲舒说:“大节则知暗,大博则业厌,二者异失同贬,其伤必至,不可不察也。”[4]《春秋繁露·玉杯》同时,道德教育要循序渐进,从容引导,“齐时蚤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4]《春秋繁露·玉杯》过疾或者过徐都不能收到很好效果。
再次,董仲舒强调学、思结合,教之以思的重要性。董仲舒认为圣人的思想深刻,道德教育很多是领会圣人微言大义。所谓微言大义,就是于词、文中蕴含的圣人政治观、历史观、社会观等,其往往是辞简而意深。“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孰能知之!”[4]《 春秋繁露·竹林》董仲舒引孔子的话说:“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4]《春秋繁露·竹林》提倡深思好学,认为没有深入思考,就不会有什么领悟。所以 “圣人思虑,不厌昼日,继之以夜”,“明其义之所审,勿使嫌疑,是乃圣人之所贵”。[4]《春秋繁露·重政》
第四,董仲舒要求在实施道德教育时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封建国家的具体形势而进行教化。对于教化对象,也要充分了解,知道其心志、善恶、性情等等,因材施教。所以,道德教育需要 “引其天性所为,而压其情之所憎者”[4]《 春秋繁露·正贯》。同时,受教育者在日常事务中应努力实践,“强勉学问,则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有大功”[4]《对策一》。
第五,董仲舒提出在道德教育中应以“明师”任教。董仲舒说:“善为师者,既美其道,又慎其行。”[4]《春秋繁露·玉杯》教师要美其道,慎其行,以自身道德修养去教育、启发、感染学生,使学生树立远大的志向和高尚的人格。在道德教育中,教师要注意教导学生道德修养与宽厚度量, “以仁安人,以义正我”[4]《 春秋繁露·仁义法》。待人要宽,薄于责人;严于责己,隐恶扬善,通过反躬自省的修养方法,提高自己的道德觉悟。董仲舒在对策中建议把“置明师”作为道德教育的首要条件,认为不重视“明师”,就不能很好从事道德教化。
三
在贤良对策中,董仲舒向统治者提出了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议,这些对两汉时期的伦理教育思想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董仲舒主张兴学校以广教化、育人才。其在贤良对策中说:“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认为养士是用贤的基础,推行德治的关键在于办学育才,推广普遍的教化。董仲舒建议在中央设太学以培养贤士,在地方设立学校以开民智,通过伦理教化,以达到统治者所需人才的目的。董仲舒还对如何办好学校提出意见,要求“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并加强考核选拔,“数考问以尽其材”。董仲舒认为兴学育才与广开仕路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建议“使诸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赏,所贡不肖者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1]《汉书·董仲舒传》,主张将学校养士与行察举选士结合起来,把教化看成是防止百姓趋利的有力工具。[5]提出通过变革教育引出官吏制度方面的改革,从而培养忠于皇帝且善于治理百姓的官员,最终达到加强上层统治者权力的目的。
其次,董仲舒提出王者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德治与教化。在《举贤良对策》中,董仲舒认为“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主张通过道德教化使人懂得“礼义廉耻”,进而养成良好的善性。太学是培养和聚集人才的地方,是道德教化的主要场所。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在办理太学的时候兼顾地方学校。因此董仲舒建议“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从而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目标。[1]《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极力提倡通过地方办学来推广经学礼法伦理教育,实施社会教化,认为这样可以加强社会控制与整合,形成“九州同风,万里同俗”,实现良好的社会风气和习俗,达到化民的作用。
再次,董仲舒明确教化贵在天道酬勤,潜心研思,才能达到“博学”之境。他说,事情均是在尽力而为的情况下做成的。学习只有刻苦用功、专心致志,研习真知,才能知“天道”。董仲舒主张在道德伦理教育中,“治我”要严,待人要宽,“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2]《春秋繁露·仁义法》“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4]《对策一》勤奋刻苦地进行道德修养,逐渐地就会取得优异的效果。
要之,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纳先秦诸家学说形成了一套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在该体系中,“董仲舒认为不仅要立儒家学说为正统,而且要将它作为判别是非、统一思想的唯一准绳”[6]。它使独尊儒术与兴学校、行选举三者紧密结合,这种伦理教育思想和方法不仅指导着西汉王朝的伦理教育,而且对中国封建社会伦理教育影响极为深刻。董仲舒作为其时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博采众家之言,广收众家思想之精华,建立起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最终使儒学登上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宝座,其伦理教育思想巩固和加强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统治,推动了西汉王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 促进了西汉社会的发展,为西汉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了理论基础。董仲舒的伦理教育思想不仅对太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有直接的推动作用,而且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1] 班固.汉书[O].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董仲舒.春秋繁露[O].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
[3] 余英时.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诠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
[4] 曾振宇,傅永聚注.春秋繁露新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5] 王永祥.董仲舒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6] 华友根.董仲舒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刘力]
OnMoralityEducationalIdeologyinNewTextConfucianismofDongZhongShuinWesternHanDynasty
Tang Jiaxiang Jiang Hong
(1.Students’ Affairs Offic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2.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Dong Zhongshu, a great Confucian Scholar, is a famous thinker and educationalist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aking Confucianism as the main line, he proposed the morality educational ideas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on the basis of the Pre-Qin Legalist’s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He took the moral education as the core of Confucian educational thought. The morality educational ideas of “Three Cardinal Guides and Five Constant Virtues” and “Morality-Guiding and Punishment-Supplementing” he proposed, together with his educational principals and methods, has become the model of Confucian ethics education. His theory is not only the inheritance of previous theories, but also a theory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onfucian moral educational ideas and social moral practice after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Dong Zhongshu; moral education
2016-11-12
唐加祥(1970-),男,重庆师范大学学生处,硕士,副研究员。 蒋 红(1978-),女,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助理研究员。
G40-09
A
1673—0429(2017)04—003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