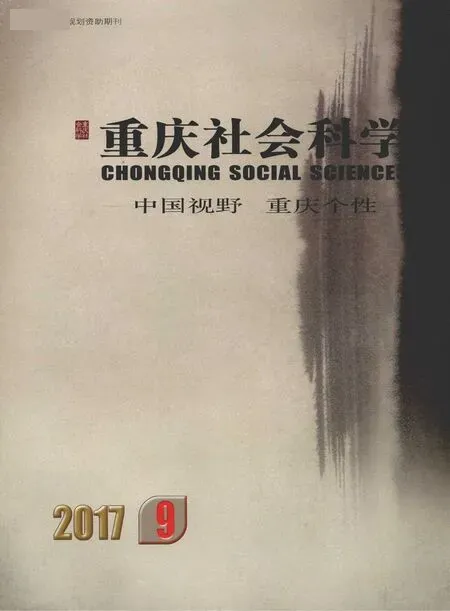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论争
宿 辉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论争
宿 辉
关于全国律协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司法解释(二)中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部分内容,这里提出以主体过错程度为线索,应客观地分析施工合同无效或未通过验收的工程实践层面的原因,并据此对优先受偿权进行重新配置。鉴于施工企业的专业性、工程价款债权的特殊性及建筑产品对社会生活的重要性,认为在配置优先受偿权时应秉持“于承包人分配更严格义务”的原则。
优先受偿权 法定优先权 施工合同无效 实际施工人
自《合同法》第286条确立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制度,并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为完善补充以来,国内学者就该项制度进行了渐次深入的研究。至今大抵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99年至2008年前后,焦点主要集中在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性质、理论基础、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民法体系中定位等问题上。梁慧星老师就该项权利的性质究竟是法定抵押权亦或优先权进行了剖析;[1]李建华老师在国内较早地从比较法层面分析了各国类似立法例及其对我国优先权立法模式的意义;[2]董慧凝博士对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立法基础和立法构想进行了阐释。[3]第二阶段自2008年至今,以王旭光博士的学位论文《建筑工程优先受偿权制度研究》为代表,研究方向逐步从理论层面转至实证分析及对策性研究上。
这里以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为线索,着重分析“当事人过错及其程度对优先权配置的影响”,然后从民事裁判的视角研究归责原则与裁判效率的互动关系,进而构建合同无效、工程未竣工验收等复杂情境下优先受偿权的裁判规则。
一、合同无效对于优先权的影响
关于合同无效对于优先权的影响,形成了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实际施工人请求依据《合同法》第286条规定对承揽的建设工程享有合同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应予以支持;第二种意见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实际施工人请求对承揽的建设工程享有合同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不予支持。
通过对上述意见的适用条件进行文义解构,可以得出以下观点:第一,争议焦点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情境下,优先受偿权的得丧问题;第二,导致合同无效的基础原因是“承包人转包、违法分包工程或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三,如果认定实际施工人享有优先受偿权,则还要考虑建设工程是否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条件。
然而,通过对两种裁判意见的分析,会发现其结构存在严重缺陷,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未能解决施工合同无效时优先权如何配置的问题。现分述如下。
(一)仅从“实际施工人”角度研究施工合同无效将导致规则结构失衡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条件下优先受偿权如何安排”本身是一个比较复杂和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因为导致施工合同无效的原因本身即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除《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一般情形以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结合建设工程领域的实际情况,列举了5种情形作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具体表现形式,分别是“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承包人非法转包和违法分包的”。由是观之,因实际施工人承揽工程而导致合同无效仅为客观表现之一,工程实践中施工企业以自己名义组织施工但因超越资质或未经强制招标程序致使合同无效的情况亦是常态,①事实上,在下文的分析中,笔者认为在存在实际施工人,即工程由承包人之外的第三人以不法状态实际实施的情境下,是不存在优先受偿权配置问题的。如仅从“借用资质”一个层面研究实际施工人是否享有价款优先受偿权未免失之狭隘,对于全面系统解决问题助益有限。
(二)即使仅从“实际施工人”角度出发,对于优先权问题的安排仍缺乏实施基础
事实上,我国的建设工程法律体系中并没有“实际施工人”的称谓,诚如《解释》起草人冯晓光法官所言:“此表述为《解释》所创设的新概念,意在表达无效合同中实际干活的单位或个人,包括转包、非法分包、没有资质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违法行为。”[4]由此可见,在总包单位违法分包导致合同无效情形下,分包单位无论是否具有相应资质其与总包单位签订的分包合同均为无效。但是,结合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5条规定“建筑业企业资质分为施工总承包资质、专业承包资质、施工劳务资质三个序列。”假使未经发包人同意,总承包人将一房屋建筑工程中的桩基础部分违法分包给具备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实际施工,则按照第一种意见,实际施工人请求对“承建”的建设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应予以支持。但是很显然这种意见并不具备操作可能,概因基础工程对于工程整体而言具有不可分割性,且基础部分工程造价占总价比例又很小,因此人民法院将很难适用该意见进行案件的裁判,即为实现基础部分工程实际施工人的优先受偿权而拍卖整栋建筑物。
二、工程是否竣工验收合格不是优先权得丧的必要条件
对于未竣工工程承包人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在我国法学理论研究和司法裁判领域均存有争议。在《合同法》实施初期,大部分学者认为优先权仅适用于竣工工程,未完工程承包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利。如梁慧星老师认为 《合同法》286条规定的权利属性为“法定抵押权”,并进一步将“建设工程已竣工”作为发生法定抵押权的前提条件,同时认为建设工程未竣工而中途解除建设工程合同的情形,亦不发生法定抵押权。[5]但随着我国民法理论的不断完善,尤其是物权理论的逐步发展,近年主张承包人对于未完工程仍享有优先权的观点趋于优势地位。
在我国建筑行业长期“买方市场”的交易环境下,设计“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制度”的法律价值,是实施社会政策的需要;是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是保护特种债权的需要。[6]其立法目的在于优先保障承包人的工程款债权,尤其是其中以农民工为主要构成的劳务工人的工资。因此只要已完工部分工程具备偿还拖欠工程款的经济价值,就可以成为优先受偿权的客体。如果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仅限于竣工验收合格工程,则有违《合同法》第286条的立法目的。且现代物权法已经认可了未完成之建筑物可以成为物权客体,如 《物权法》第180条明确规定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可以抵押。
可见,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作为实际施工人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前提条件,实无必要。而且在更深层次上,这种意见会与现行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既有裁判观点相悖。
(一)与《解释》的规定不符
根据《解释》第2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可知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的条件下,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导致的合同无效,承包人(即可能是转包、违法分包或出借资质的施工企业)是享有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请求权的,而该请求权的实现方式中,必然暗含着优先受偿的主张。而在工程由承包人以外主体实际施工、且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情况下,实际施工人(即可能是接受转包、违法分包或借用有资质企业的其他企业甚或包工队)亦可以主张优先受偿,这必然造成人民法院裁判规则的矛盾并引发承包人和实际施工人之间的权利冲突。
(二)与既有裁判观点不符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中,关于长城公司与宏伟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对于“未完工程承包人是否可以主张优先受偿工程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经研究认为:“《合同法》第286条的规定,是法律赋予承包人工程款优先受偿的权利。从《合同法》规定的条文表述分析,没有要求承包人优先受偿工程款以工程完工并经竣工验收为先决条件,在合同解除的情形下,承包人也对未完工程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7]可见,将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作为实际施工人主张优先权的前提条件,既无依据,亦非必要。
“教科研+”为培养能“提出问题”和“发现问题”的学生提供了保障,也为培养“研究型”、“专家型”教师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三、实际施工人语境下不存在优先受偿的请求权基础
若将请求优先受偿权的讨论主体限定为“实际施工人”,则已确定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为承包人过错,即转包中标工程、违法分包中标工程或出借资质给不具备建筑业企业资质的第三方使用,其可责性是非常明确的。因此,讨论实际施工人优先权的请求权基础,无论在正当性上还是可操作性上,均存在严重瑕疵。
(一)不具正当性
“任何人不得因自身的不法获得利益”,在承包人以自身名义获得了工程的承包权后,违反法律规定将其所承揽工程转包、违法分包或出借资质,不但有违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破坏了发承包双方在建筑市场交易行为中的信任基础,而且由不具备施工能力的第三方实际施工,亦带来了严重的质量安全隐患,危及建筑产品本身和公众安全。在此情境下,无论是承包人还是实际施工人,赋予任何一方就工程价款优先于其他正当交易的供货商、勘察设计等单位受偿,都是对交易秩序和公平正义原则的极大伤害。
(二)不具操作性
由于实际施工人往往是没有资质或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甚至包工队,如果赋予其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则按照建筑市场交易现状,转包、违法分包或出借资质的企业往往只能获得工程造价2%左右的不法“管理费”或“挂靠费”,其余工程价款将由实际施工人获得。但是与获得工程价款权利相对应的,承包人尚有其他后合同义务,包括缺陷维修和保修义务需要承担。从权义对等的角度出发,承包人由于并未实际获得工程价款,因此其履行保修义务的意愿和动力不足;而获得了工程价款的实际施工人,无论是基于合同的相对性还是基于其不具备资质的客观实际,由其履行缺陷维修和质量保修义务均不具备操作性。甚至由劳务工人临时组成的包工队根本不具备任何稳定性,在获得工资后即告解散。因此,赋予实际施工人优先受偿权不但无法宣示该项制度的价值理念,而且严重损害了发包人和消费者获得缺陷维修及保修的合法权益。
四、基于原因导向配置优先受偿权方案及规则
鉴于我国民法体系对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理论支持不足,致使学界对于该项权利的性质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司法审判机关,包括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对于同一问题所作出的指导意见立场不一,甚至相互矛盾。①例如,同样对于无效合同承包人是否可以主张优先受偿权的问题,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工作中如何适用〈合同法〉第286条的指导意见》(粤高法发[2004]2号)第7条规定:“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无效的情形下,承包人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皖高法[2009]130号)第17条则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承包人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可予支持。”这种“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客观存在极大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公信,也进一步凸显了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夯实优先权制度的理论基础,或通过司法解释统一裁判规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施工合同无效或工程未经验收合格均属对工程合同或工程本身所处状态的评价,以状态来配置权利而不追究达致此种状态的原因是不科学的。事实上,如果从导致合同无效、竣工验收不合格的原因入手,来决定是否赋予优先权以及如何配置优先权,将可有效地统一裁判规则,彰显法律价值。
具言之,施工合同无效、解除、验收不合格的原因大致包括四种情形:承包人完全过错、发包人完全过错、混合过错及第三方过错。以过错责任主体为导向,可以就优先受偿权配置形成如下规则。
(一)承包人的完全过错
1.因承包人原因导致施工合同无效,承包人向人民法院请求就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不予支持。考察《合同法》及《解释》中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涉及承包人原因的,均为比较严重地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包括越级承包、出借资质、串通投标等。值得注意的是,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审判指导意见中,很少考虑合同无效的原因,却往往以工程是否验收合格作为给予优先权的考量。②除前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皖高法[2009]130号)第17条规定外,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22条亦有类似规定。对此,笔者持不同的看法,承包人的上述“不法”已经严重动摇了双方的发承包关系,依据《解释》第2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可见,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请求权已经转变为以折价补偿方式进行的财产返还。而承包人的违法行为或根本性违约使得其作为特种债权的正当性亦不复存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仍然赋予其优先受偿工程价款的权利,无异于变相鼓励承包人的违法行为,必将加剧建筑市场脱序交易的发生。
(1)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承担修复费用后,可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2)如工程质量缺陷无法修复或修复费用过高的,除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情形以外,承包人应承担违约责任或减收工程价款。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减收工程价款或折价补偿后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应予支持;
(3)因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缺陷原因导致质量不合格或未通过竣工验收且无法修复的,承包人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不予支持。
提出以上优先权配置方案,是基于建设工程自身特性的考量。在建筑产品质量缺陷问题上,真正影响产品使用功能和公众利益安全的,应该是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的质量问题。如果这些部位存在不能够满足建设工程验收规范和质量安全强制性标准的情形,即意味着发包人丧失了建筑产品的可用性,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在此种情形下应适用与承包人完全责任导致合同无效相同的处理原则,即不赋予承包人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如果是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以外的部分存在质量瑕疵,可以由承包人进行修复并承担修复费用,进而可以主张优先受偿权。值得注意的是,工程实践中存在质量瑕疵无法修复或修复费用过高而无必要修复的情形。前者如钢筋等隐蔽工程的施工,后者如国外采购的重置费用较高的设备材料等。在此种情境下,如果合同文件对于此类质量违约责任有明确标准或计算方法的,承包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如果没有约定的,承包人应对该质量缺陷对于建筑产品价值和功能的减损程度,折价补偿或减收部分工程价款进而重新将双方合同权利义务调整至对等状态。承包人对于已完工程主张优先受偿权的,应予支持。
(二)发包人或第三方完全过错
因发包人或第三方原因导致合同无效或建设工程未能通过竣工验收的,不影响承包人优先受偿工程价款的请求权。此处所称“第三方”,不包括基于建设工程合同关系,例如承包人的专业分包人、劳务分包人或材料设备供货商等。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合同无效的,承包人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合同对竣工日期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或者由于发包人的原因,合同解除或终止履行时已经超出约定的竣工日期的,承包人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期限自合同解除或终止履行之日起计算;因第三方原因导致合同无效或未通过竣工验收的,应按照《合同法》第121条的规定,由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工程价款后,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其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
(三)发包人和承包人混合过错
在发包人和承包人对于导致合同无效或未通过竣工验收均有过错的情形下,笔者主张“于承包人分配更严格义务”的原则,概因承包人作为具有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专业单位,在法律规范和交易规则层面的自我约束应强于发包人,且行政机关对于其监管措施亦强于发包人。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制度设计的必要性之一,即是认可基于发承包关系所形成的债权是一种特殊债权,则进言之,承包人亦应严格规范自身的承揽行为,承担更为严苛的合同义务。
1.发包人和承包人均有导致合同无效行为的,承包人主张就承揽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不予支持;
2.发包人和承包人对于工程未能通过竣工验收均有过错,且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需综合考虑勘察设计质量、材料设备质量和施工质量对工程的影响程度,如承包人对于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承担主要责任且无法修补的,则其不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3.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原因导致工程未能通过竣工验收,但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合格的,承包人在承担了违约责任后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应予支持。
五、结语
如前所述,由于我国《合同法》中规定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制度缺乏体系化的理论支持,在民法体系其他法律模块中也缺少对应的关照,因此造成如今学者理论研究彼此观点矛盾甚至截然相反、司法机关个案裁判结果迥然、工程合同参与各方各行其是的尴尬局面。针对合同无效及工程未通过竣工验收两种情境下优先受偿权的得丧与配置问题,应该坚持的两个原则是:第一,以致使合同无效、未通过竣工验收的原因及责任主体为导向;第二,应秉持对于具有专业资质的承包人即施工企业课以更严苛责任为原则。
当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作为一项特色制度,在当前我国编纂统一民法典的时代背景之下,其从宏观和具象两个层面尚有诸多问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从宏观层面尚需研究我国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立法模式问题
就权利性质而言,目前关于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尚有不动产留置权说、法定抵押权说和优先权说三种观点。虽然近年来,不动产留置权说日渐式微,①日本是承认不动产留置权的国家,《日本民法典》第325条规定了有不动产先取特权的债务种类,包括不动产的保存、不动产的工事和不动产的买卖。并在第339条规定依不动产保存和不动产工事进行登记的先取特权,可以先于抵押权而行使。但是对于法定抵押权说和优先权说两种观点仍各有拥趸。②其中,梁慧星老师结合《合同法》的起草过程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法律性质为法定抵押权。参见:梁慧星:《是优先权还是抵押权——合同法第286条的权利性质及其适用》,《中国律师》2001年第10期,第44~45页。温世扬老师则认为该项权利为不动产优先权。参见:温世扬:《建筑工程优先权及其适用》,《法制日报》2000年10月22日。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赞同优先权说。优先权是“法律直接赋予特定债权人享有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的法律效力的体现”,[8]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性质应为不动产特别优先权,属非典型担保物权。
就立法模式而言,存在优先权体系化立法说和非优先权体系化立法说两种主张。在此问题上,笔者赞同应当选择优先权体系化之立法模式,即在编纂民法典时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作为优先权制度中之不动产特别优先权的一种,将该权利纳入担保物权体系中一并加以规定。
(二)在微观层面应对我国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进行完善
具体制度完善层面,应尽快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实行登记制度,并以登记作为权利效力保全的要件。同时,应明确优先受偿权的实行方法,即通过提起优先受偿权确权之诉抑或直接向法院执行机构申请启动拍卖程序实现优先受偿。
综上,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作为国家干预建筑市场交易行为、保护承包人和劳务工人合法权益的制度安排,应以民法典编纂为契机,明确其权利性质、效力内容和实施方式,以切实体现这一制度的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
[1][5]梁慧星:《是优先权还是抵押权——合同法第286条的权利性质及其适用》,《中国律师》2001年第10期,第44~46页
[2]李建华 董彪:《论我国法定抵押权制度的立法模式》,《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第182~187页
[3]董慧凝:《建设工程优先权立法基础与立法构想》,《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101~103页
[4]黄松有主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80~81页
[6]王旭光:《建筑工程优先受偿权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第75~86页
[7]奚晓明主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22~124页
[8]梅夏英:《不动产优先权与法定抵押权的立法选择》,《法律适用》2005年第2期,第49~53页
Controversy on Prior Right of Compensation from Construction Work Payment
Su Hui
Pay attention to ACLA’s (All China Lawyers’ Association) suggestion for the part of “prior right of compensation for construction work payment”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II of contractual dispute in construction project,this paper suggests to focus on the extent of subjects’fault,analyzing objectively the practical situations of construction to find the reasons of invalid contract or failing to pass the inspection and acceptance and accordingly re-attribute the prior right of compensation.Given the professionality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peciality of construction work payment obligation and importance of construction,the author believes when attribute the prior right of compensation should insist the principle of “setting more strict obligation to the contractor”.
prior right of compensation,statutory prior right,invalid construction contract,actual constructor
吉林大学法学院 吉林长春 13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