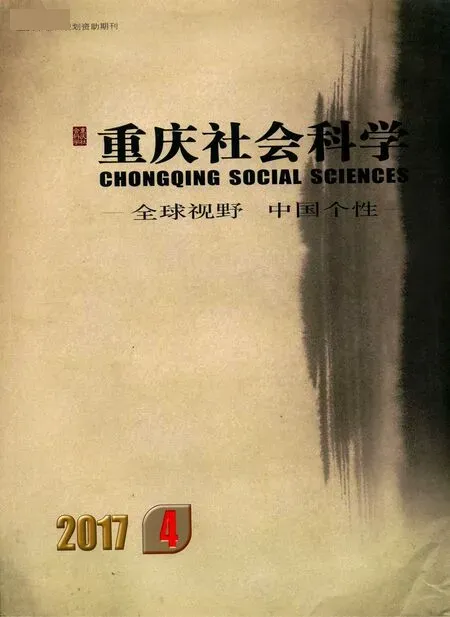公民道德观念的义务论*
乔欣欣
公民道德观念的义务论*
乔欣欣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需要厘清公民道德的本质内涵,而完整地理解公民道德,又离不开对“公民”一词的了解。通过对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以及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公民概念的阐释,说明公民身份不仅意味着一定的政治权利,即具有公民身份的人才享有统治权,更意味着一种对城邦的责任和义务。从义务的角度认识公民道德有助于完整地看待公民道德建设。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既要重视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又要重视对公民义务的培养和训练。
道德观念 道德与文明 中华传统美德
道德观念是人们对自身、他人、世界所处关系的系统认识和看法,属于社会伦理的范畴。从义务论的角度理解公民道德观念,对加强新时期公民道德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一、公民、德性与城邦
(一)公民与城邦
“公民”一词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对“公民”一词基本含义的理解离不开对当时基本政治生活方式的了解,即城邦生活。城邦由早期各种社会团体自然地发展起来,从公元前8世纪始,城邦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特殊形式的国家组织,即城邦内的居民形成了一个政治共同体,建立政府机构,成为城邦国家。城邦有两个不同于现代政治共同体的重要特征:一是直接民主的交往形式。希腊人在其文明发展过程中,并没有依循王宫文明的建制,而是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希腊式的思维方式和处理社会关系的民主方式——公民以对等性身份进行论辩和探讨各项公共事务。[1]与这种对等性、相互间性的交往方式相联系的是城邦以公众集会广场为中心建立起的公共社会空间,在这样的空间,言说的地位提高了,自由辩论和对立论证成为治理城邦事务的基本手段,每个公民都有机会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展现自我,包括身体的力量抑或头脑的智慧,而这激发了希腊人追求卓越的生活重心。因此,希腊人所理解的城邦与这种城邦生活方式紧密相关,城邦不仅仅是每个公民生活于其中的一片地域,并且公民通过直接具体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之中实现对城邦的责任和自身的卓越。
从这个角度来说,古希腊的公民观念中,德性是公民的基本内涵。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全称的公民应该是 “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而公民的普遍性质可以概括为:“(一)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二)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2]同时,亚里士多德指出,不同的政体有不同的公民,但在最优良的政体中,公民指的是,为了依照德性的生活,有能力并愿意进行统治和被人统治的人。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清楚地指出了公民概念与城邦制度,以及公民德性与城邦的善业之间的密切关系。一方面,公民的概念必须参照城邦的制度和统治得以理解,而城邦的本质特征正是通过以公民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和公共生活而体现出来;另一方面,城邦至善目标的实现,依赖于作为城邦构成要素的每个公民的德性,而只有在城邦以及城邦之至善目的的前提下,公民所承担的德性义务才是可理解的。
因此,城邦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至善的目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开篇即说到,“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3],而城邦则是那种所求善业最高而最广的社会团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不仅为生活而存在,而且应该为“优良的生活”而存在,因此,凡订有良法而有志于实行善政的城邦就得操心全邦人民生活中的一切善德和恶行,真正无愧为一城邦者,必须以促进善德为目的。[4]城邦的善业与公民德性有着天然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且作为城邦一份子的公民,只是因为分享了城邦至善的目标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因此他首要考虑的不是在城邦中享有哪些权利,而是是否履行了有助于城邦道德目标实现的义务,不仅包括公民政治统治职能的履行,还包括道德义务的履行。因此可以说,城邦政治是一种建基于公民德性的美德政治,城邦的终极目的是“优良的生活”这一道德目标的实现。
(二)德性与城邦
我们从荷马的诗歌中知道,希腊城邦最早从一种贵族式的族群结构发展而来,但是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希腊城邦成功地完成了其民主化的转型。与之相伴随的是旧的族群权力结构被打破,公民权扩大到多数人身上,以及对一种将城邦中的诸多公民整合为一个城邦单位的普遍有效的秩序真理的吁求。[5]因此城邦秩序的产生与维持不再依赖于少数英雄人物的德性,而是依赖于大多数公民的德性。
对德性的重视源自于苏格拉底的哲学,“知识即美德”是苏格拉底哲学的出发点,也是西方政治哲学的起点。“知识即美德”的信条,是对当时活跃在希腊城邦的,以传播知识为己任,人数众多的群体——智者所持观念的反对。智者来自五湖四海,千差万别,没有固定的道德原则,其基本观点是:“想当演说家,完全用不着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只要表现多数的意见就行了。这些多数的意见之所以被认为正当,并不是因为它们真的是好的、正确的,而只是表面上是好的、正确的。”[6]在苏格拉底看来,正是智者的这种伦理相对主义观念导致了城邦执政能力以及公民精神的丧失,进而造成城邦民主制的衰败。苏格拉底提出“知识即美德”,实际是将哲学的中心问题从人的一般感觉转向人的内心,准确讲是人的内在理性能力和道德准则[7],从而确立起以转变人的灵魂、重塑正义、道德兴邦的救治方案。
“知识即美德”的论断使得城邦秩序的产生与美德成为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就是说,城邦的维持与秩序现在转化为一个认知的问题,既包括心灵的认知,又包括灵魂的德性。在柏拉图那里,我们将看到,这个问题演化为这样一种见识,即存在一种关于社会和人的“真正”的知识,即理念,这种理念能够被认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将发现,不仅存在一种基于认知的美德,即求真的美德,也存在一种基于实践的美德,即伦理美德。既然城邦秩序依赖于灵魂的德性,那么对一种有利于城邦及其全体人民的共同善或者真正美德的追寻,就是古希腊公民德性理论的核心问题。古希腊人对正义、勇敢、节制等新美德的寻找,终结于一个发现:德性是灵魂的习性,它让人的生命与超越现实相调和;随着美德领域充分的分殊化,人的“真我”涌现出来,城邦的至善也就成为可能。
从个体层面来说,德性是公民身份的来源,而从城邦来说,德性则是城邦秩序的来源。首先,德性是灵魂的习性,公民不同于城邦中自由民以及奴隶的主要特征就是其对城邦公共事务的参与和治理,这不仅仅是一种权利资格,其实更多地是一种义务要求,例如必须有一定的闲暇时间,以及以此为条件的基本素质,包括正义、勇敢、节制、审慎等美德。倘若个体不具备美德,那么他也就不具备从事城邦治理的资格,从而也就失去了其公民身份。其次,如果说城邦是灵魂秩序的体现,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没有德性的灵魂如何能造就出一个善的城邦?城邦的秩序依赖于作为整体的公民社会的健康以及公民精神的蓬勃,也依赖于作为个体的公民灵魂秩序的超越,德性是将个体与城邦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个体倘若没有德性,那么个体在城邦中就不成其为公民,并且城邦因为公民社会以及公民精神的缺失,也将走向衰落。
二、公民德性的基本内容
(一)“德性”的内涵
“德性”这个概念最初被用来指武士英勇善战、无所畏惧的高贵行为,是属于少数人的品德。然而,随着城邦民主化的转型以及公民权的扩大,德性所适用的范围也在相应地扩展,被用来指称那些优秀的公民在城邦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优良行为和品质,这种转变的前提是将德性与知识挂钩。苏格拉底关于“知识即美德”的论断指出,“知识是高贵和统领一切的东西;它无法被快乐所征服;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智慧是一切德性之本”。然而苏格拉底同时认为,知识即绝对的存在或本质,也称为理念,是只有少数追随理智、掌握真理的哲学家才真正具有的,因此德性依然是属于少数人的品德。
如果说苏格拉底阐明了对于一个有理性的个体来说,德性是什么的话,那么在柏拉图那里,则阐明了个人的德性与城邦的德性分别是什么。柏拉图通过“社会是大写的人”这一原则来表达其洞见。《理想国》从关于个人正义生活的对话开始,但是正义不仅仅是作为个人的德性被谈论,也作为城邦的美德被谈论,因为城邦的秩序来源于个体灵魂的秩序,国家来自于它们之中的人的习惯。在他看来,正义不是外在的约束,而是内在的德性,并且只有内在的德性才是最重要的德性。[8]灵魂的德性在于灵魂的有序和健康,类似地,城邦的德性则在于城邦的秩序和活力,也就是说个体生活的正义是个体灵魂内部各个元素的分工合作,各居其位,互不代劳,城邦的正义则是城邦中统治者应该具备的智慧、卫国者应该具备的勇气、劳动工商者应该具备的节制,以及这几大社会群体和相应德性的协调。[9]
在柏拉图的德性概念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划分了德性所应包含的内容。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首先是一种品质,“灵魂的状态有三种:感情、能力与品质,德性必是其中之一……既然德性既不是感情也不是能力,那么它就必定是品质”[10]。那么,德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品质呢?亚里士多德接着说,“每种德性都既使得它是其德性的那事物的状态好,又使得那事物的活动完成得好……那么人的德性就是既使得一个人好又使得他出色地完成他的活动的品质。”[11]在亚里士多德的用法中,德性一词,与“卓越”(excellence)相近,它有两种用法:在非道德意义上,德性用来指任何生命物和无生命物的特长。而在道德意义上,德性特指人的德性。例如,勇敢、节制、正义、慷慨等品质。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指出,人的德性是灵魂的德性。他把德性分为两种:一种是理智德性,如智慧、谅解和明智;另一种是伦理德性,如慷慨、节制和勇敢。理智德性是由教导培养而生成的,因此需要时间和经验;伦理德性则是因风俗习惯而养成的。[12]我们看到,对德性的分殊使得德性与公民身份逐渐联系起来,从而成为一种可被培养的品质,并且不再只是少数哲学家才具备的品质,而是通过对德性所赖以产生的实践活动的重视,每个公民都可能具备的品质。
(二)德性与政治实践
德性概念与政治实践的结合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荷马式德性观念长期主导着希腊人的生活,而根据这种观念,人的德性是作为部族的国王或军事首领的英雄们天生就具有的自然属性,这是由他们的贵族血统所决定的,不会受到任何人力或人事的影响。随着希腊社会逐渐过渡到城邦社会,这种观念变得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在城邦社会,公民从等级森严的部族成员转变为平等的政治共同体成员,开始能够平等地参与城邦公共事务,在公民大会上充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在这样的背景下,德性不仅仅是少数英雄人物的品质,而是与政治生活相关,是所有公民都有可能具备的品质的观念就应运而生了。
反对天赋德性观是苏格拉底的基本主张,他试图证明一个行为是否正义、正当,不是由任何权威决定的,而是取决于这一行为本身的性质。这即表明,关于人的行为存在着客观、必然、绝对的“真”,行为抉择本质上是一个客观的“真值判断”,而非主观经验性的价值取舍,没有对“真”的这种知识和智慧,是不可能有任何真正正当的行为的。因此,追问事情的本质就成为苏格拉底哲学的基本特征。同样,在柏拉图看来,真正的知识就是关于人本身及其行为善恶的知识,也即善的理念。“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因为它是知识和认识中的真理的原因,关于正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才是有益的。”[13]显然,只有基于这样的知识才可能产生真正的德性行为。但是,柏拉图认为只有少数的哲学家才可能获得关于善的理念,并且由于真正的“好”不存在于现实的世界当中,因而对于真正的哲学家来说,要认识善的理念就必须远离现实世界。柏拉图显然认为最好的生活其实并不是政治生活,在柏拉图那里,作为哲学家的沉思的德性与政治生活的行动和实践要求仍然格格不入。
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的哲学基础之上,进一步推进了德性概念与政治生活的密切联系,他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人性命题将“认识你自己”之路,从一般的哲学领域推向了社会历史的伦理道德领域。我们前面说过,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并不是自然而生的,恶习作为德性的缺失,也不可能注定就有。也就是说,德性与恶习都是在人的努力范围内。那么,德性是如何得来或丧失的呢?在他看来,德性要通过“习养”而最终完善,通过做正义的事才成为正义的人,通过英勇壮举才获得勇敢,因此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得到德性。[14]因此,我们看到,从荷马笔下的阿基琉斯、奥德修斯等英雄,到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正义的人”,再到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有实践智慧的人”,德性概念最终得到了完整的阐释:德性并不是少数精英才能具备的天赋品质,而是每一个公民通过知识与实践都有可能具备的品质,并且德性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德性不仅需要通过对最高善理念的沉思来实现,也需要通过公民对城邦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来实现。这种德性观念与当时以城邦为中心的政治生活方式紧密相关,是对于城邦政治生活方式的反映,也是对城邦生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逐渐走向衰落的一种拯救。
三、义务取向的公民道德
(一)“好人”与“好公民”的区别
既然德性与公民身份,或说与个人所处的城邦政治生活紧密相关,那么公民德性的主要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公民是一个有德性的公民或说“好公民”?如何成为一个“好公民”?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厘清“好人”与“好公民”之间的区隔。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善人的品德和良好公民的品德应属相同,还是相异?”[15]在柏拉图那里,此问题同样存在,只是在柏拉图那里,问题转化为城邦统治者的品德和真正的哲学家的品德是否相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要回答的问题无非两个:第一,正义是什么?第二,正义之人是否快乐?他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明确的,而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看似是“主张正义有利说的人是对的,主张不正义有利说的人是错的”[16],但其实不然,因为如果在一个他所谓的正义国家里,即由哲学家来担任统治者的职责,那么哲学家显然得不到快乐。因为哲学家所追求的是纯粹的理念,是最高的“真”,而这种“真”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他们必须到政治之外寻找最高幸福。这就要求他们不同于或超越于普通公民,这最终导向对政治生活的贬低,也导致“好人”与“好公民”之间的冲突,而这一冲突只能以强制哲学家承担政治责任、牺牲个人幸福来化解。
亚里士多德虽然同柏拉图一样,也重视纯粹思辨的生活,但他同样强调政治生活的崇高性。亚里士多德在其两部著作的开头,都开宗明义地指出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最高的善是最好的、最幸福的。也就是说,幸福是最好的生活,但是他说这种幸福并不是享乐,而是符合德性的活动:“人的善就是灵魂的合德性的实现活动,如果有不止一种的德性,就是合乎那种最好、最完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17]城邦因为其最高目的是过一种优良的生活,即促成全邦人民的善德而成为一种重要的实践活动,而政治学也因为其目的是通过立法等方式致力于使公民成为有德性的人、能做出高尚行为的人而成为最高的学问。如果说柏拉图认为作为城邦的最高统治者在城邦里未必能够达到幸福,因为他们不得不承担他们所不乐意的政治职责,那么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政治统治是最有德性的人获得幸福的最佳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好人与好公民的生活并不冲突,相反,成为一个好公民是实现成为一个好人的基本途径。
(二)践行德性是一种义务要求
古希腊的德性思想表现出一种义务取向的公民道德观念。在现代社会中,公民“权利”已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诉求,各国的宪法、民法及其他法律体系都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了详尽的规定,主要有言论、出版、集会请愿、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按财产状况享有选举权。可以说,现代公民概念的特质是以权利为本位,权利是现代公民概念的基石,它不同于古代希腊时期以城邦为基础,以参与城邦的治理所要求的德性为内容的义务本位的公民概念。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是一种契约权利,契约是设定人们权利义务的常规手段。契约的本质是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因此用契约作为设定人们权利义务的手段,其实是当事人自己为自己设定权利义务,它主要依靠的是每个当事人自身的努力,通过自由竞争,自己设定权利、自己履行义务、自己承担责任。我们暂且不论在古代有没有个体权利的萌芽,但是作为城邦主人的公民的的确确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也即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并且这种权利是其公民身份的基本象征。但是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契约权利,古代社会的这种权利是一种身份权利,是否具有公民身份是决定其是否享有权利和义务的标准。在不同的政体中,对公民身份的规定不尽相同,在某种政体中,工匠和佣工都是公民,在另一些政体中,他们却不得为公民。
这种看似作为某种权利的资格,在古希腊城邦制的背景下,以及在城邦秩序与公民德性紧密相关的前提下,其实蕴含的是一种义务要求。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寡头政体中公民对政治的参与时说:“关于公民大会,全体公民都必须参加;但缺席罚款只行使于富户,或对富户缺席所罚特重。而关于行政职司,一旦具备了财产资格的人就不许他们仅凭誓言谢绝任命,但穷人则可以辞不就任。关于法庭的陪审职务,富户缺席,照例必须受罚,但穷人缺席不罚。”[18]参与城邦的治理,本应是公民的权利,但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这些措施,其意在督促公民政治义务的履行。这是因为公民身份虽然是根据血统和财产等因素取得的,但事实上公民的本质特征是在对城邦的政治生活的参与中,而且是一种有道德的参与中实现的。这样,德性便成为公民身份或公民资格的本质内容,而践行德性,也就是义务相比起权利来说成为更重要的事情。在这里,义务的范畴是宽泛的,不仅仅包括参加议事和审判的政治义务,还包括提升个人道德品质的道德义务,并且对哲学理念的学习与沉思也成为一种义务。
四、结语
如果把公共生活比作公民活动的舞台,那么在这个舞台上公民角色的扮演需要呈现两张面孔:一张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享有;另一张则是公民义务的承担。“一个国家的存续,不仅需要政治权利的消费,而且需要政治义务的生产。”[19]然而,不管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实践中,还是在关于公民道德观念的研究中,权利本位的公民道德观念大行其道,公民角色普遍表现出来的是权利诉求的热衷和责任意识的淡漠。从观念上来说,权利本位的公民道德观念是西方近代以来以权利为核心的公民概念的产物,“权利公民”一度因为与西方社会发展的同构性,为西方社会创造了丰富的政治文明,但同时也引发了现代生活的种种危机。其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表现就是:公民意识和奉献精神的衰退、公民参与和社会合作的减少、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的丧失、公民社会作用的削弱以及公共道德的侵蚀等。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政治冷漠,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滋长、蔓延以及精神空虚和宗教影响力的下降。
在经济社会发生深刻转型的当下,西方社会所经历的这种公共生活的危机,在中国社会也已见端倪,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运行,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开始流行。如果从观念上来分析,此种现象与西方社会生活的种种危机一样,其背后隐含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公民义务以及公民责任观念的缺失。
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意义重大。公民道德建设应该以这样的公民道德观为依据,既要重视对公民自由、平等、政治参与等权利的维护和尊重,培养公民独立自主、人格平等以及“为权利而斗争”的权利意识;又要重视由公民资格所赋予的并得到内心认同的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的道德义务和道德使命以及对他自身行为后果的善恶的承担,培养公民对公共生活的责任意识,对所属城市、村镇、社区等的发展有较强的使命感和明确的责任担当意识。当然,强调公民的责任与义务,并不意味着忽视公民权利的保护,强调公民权利的保护与强调公民责任的履行并不冲突,相反,它们相辅相成。
[1]曾令斌 刘铁芳:《城邦:教化之舟——古希腊城邦与教育的关系探讨》,《当代教育论坛》2013年第1期,第52~57页
[2][3][4][14][15][1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 114~116、3、140~144、355、123、215 页
[5](美)埃里克·沃格林:《城邦的世界》,《秩序与历史》(卷二),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 238~278页
[6]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页
[7]王乐理:《苏格拉底的魅力》,《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 2期,第 4~11页
[8][9][13][16](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72、144~174、260、382 页
[10][11][12][1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 43~45、45、35、20 页
[19]徐百军:《担当政治义务:公民角色的另一张面孔》,《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0月24日
An Analysis of the Deontology of Civic Moral Idea
Qiao Xinxi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c morality needs to clarify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civic morality,and the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citizen”.In this paper,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cient Greek city-state political life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indicating that citizenship not only means a certain political rights,but also means a kind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Based on this we believe that understanding the civic moralit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obligation can help us to look at the construction of citizen morality in a complete way.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respect and protection of citizens’ rights and the cultivation and training of citizens’obligations.
moral idea,morality and civilization,Chinese traditional virtues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法律研究所 陕西西安 710068
*该标题为《重庆社会科学》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试论公民道德观念中的义务论取向——古希腊公民德性思想研究》。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公民义务观念研究”(批准号:15XZZ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