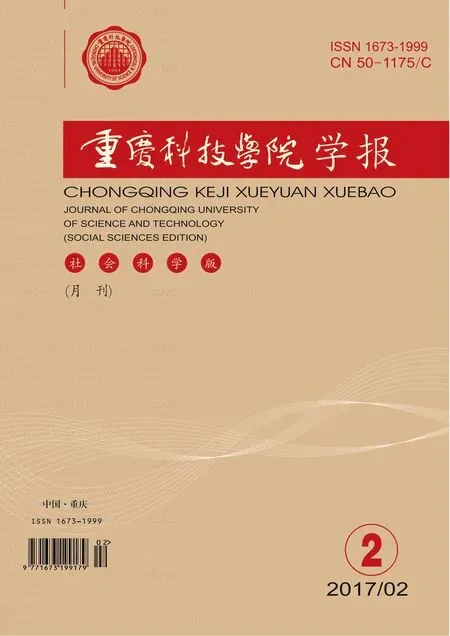英国玄学派诗歌的意象张力和文本间性
——以邓恩的《告别辞:莫伤悲》和劳伦斯的《虹桥》为例
陈贵才
英国玄学派诗歌的意象张力和文本间性
——以邓恩的《告别辞:莫伤悲》和劳伦斯的《虹桥》为例
陈贵才
玄学派诗歌是英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凭借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奇妙的诗学张力和强大的文本记忆力,玄学派诗歌不仅没有在英国诗歌乃至世界诗歌的百花园中黯然凋谢,反而在历史的涤荡和沉淀中历久弥新,甚至大放异彩。作为玄学派诗歌的先驱和大师,邓恩既为他的同辈诗人,又为他的后辈诗人提供了有本可依的范文。然而,生性敏感和超自觉的后辈诗人劳伦斯并未受传统的制约和束缚,反而在邓恩等前辈玄学派诗人“影响的焦虑”的集体作用下和充分施展个人才能的基础上,最终成了强力诗人,成了英国玄学派诗歌优良传统的继承人和开拓者,成了20世纪英国杰出的玄学派诗人。通过分析邓恩的经典玄学诗《告别辞:莫伤悲》和劳伦斯的玄学诗《虹桥》发现,邓恩所建构的天体意象、金箔意象和圆规意象与劳伦斯所建构的虹桥意象不仅具有强大的诗学张力,而且在文本的对话中呈现出明显的文本间性。
玄学派诗歌;意象张力;文本间性;《告别辞:莫伤悲》;《虹桥》
玄学派诗歌是英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它始于16世纪90年代,结束于17世纪90年代。在这100年的时间里涌现出了以约翰·邓恩、本·琼生、爱德华·赫伯特、罗伯特·赫里克、乔治·赫伯特、托马斯·卡鲁、爱德蒙·沃勒、约翰·萨克林、理查德·拉夫莱斯、安德鲁·马维尔和亨利·沃恩等为代表的大批玄学诗人。他们携手创作了许多以“爱情”“及时寻乐”“宗教”“女性世界”和“自然”为主题的不朽诗篇。在诗歌创作过程中,玄学派诗人总能把看似毫无关联的事物巧妙地联系起来,总能在看似牵强附会的意象中发现天然浑成的意境。这就是玄学派诗歌创作技巧中最显著的特征,即“奇思妙喻”。通过这种技巧,英国玄学派诗人为世人留下了大批经典的玄学意象。这些意象不仅丰富了英国诗歌百花园的内容,而且为它增添了光彩,增强了它的影响力。正如于宏伟所言:“玄学派诗歌是英国诗歌创作百花园里开放的一朵奇葩,以其突兀离奇的意象营造出别样的意境,为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引入了全新的视角,对现代诗歌产生了不同凡响的影响。”[1]在李正栓等人看来:“玄学派诗歌好似种在17世纪的一朵鲜花,经过18世纪的偃旗息鼓和19世纪的默默无闻,终于在300年后得以大放异彩,凭借其独有的艺术表现力和思想深刻度,成为英国诗歌乃至世界诗歌百花园中一朵永不凋谢的奇葩。”[2]77这朵红极100年而又遭遇200年冷落的奇葩最终在20世纪重新获得了人们的垂青并得以复活和绽放。除其本身的诗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之外,这一诗歌流派得以复兴不仅要归功于艾略特的推崇,而且要归功于劳伦斯的继承和发扬。在英国玄学派诗人特别是邓恩“影响的焦虑”的集体作用下和充分施展个人才能的基础上,劳伦斯不仅成了名副其实的强力诗人,而且成了英国玄学派诗歌的继承人和开拓者。在继承前辈诗人所创作的以“爱情”为主题的玄学派诗歌的基础上,劳伦斯同样开创性地创作了以“爱情”为主题的玄学诗歌。这些诗歌包括《爱情乱象》《新升的月亮》《亲吻》《发觉》《一朵百花》《月光》和《虹桥》等。它们不但充分展示了劳伦斯诗歌的艺术魅力和诗学思想的光芒,而且极大地拓宽了英国玄学派诗歌的疆域,开创了玄学诗歌的新局面,为其成为20世纪真正的玄学诗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研究将以邓恩的爱情诗《告别辞:莫伤悲》[3]57和劳伦斯的爱情诗《虹桥》[4]286为例,来探讨英国玄学派诗歌的意象张力和文本间性。
一、邓恩爱情诗《告别辞:莫伤悲》的意象张力
邓恩是英国玄学派诗歌的创始人,他的诗歌集中体现了英国玄学派诗歌的基本特质。“邓恩诗歌的多种层面都成为张力理论施展魅力的空间,无论是作品的意象、语言、内涵,还是整体的风格、主题、结构、文本,都能看到张力理论作用的身影。”[5]106其富含张力的爱情诗《告别辞:莫伤悲》是英国玄学派诗歌的代名词和诗歌艺术的经典。该诗是其诗集《歌与十四行诗》中的代表作之一,是诗人于1611年冬随其恩主罗伯特·特鲁里爵士出使巴黎前写给有孕在身的妻子安妮的离别诗。在这首诗中,邓恩通过平静而和谐的天体意象、绵绵无绝期的金箔意象和永不离分的圆规意象来同构诗思与情思,来展现诗歌的意象张力。
在文学作品中,“意象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恰如其分的点缀,还是文学作品精神本质的一部分”[6]1059。对诗歌而言,“意象是诗歌的灵魂”[7]88。“张力是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延和内涵的有机整体”[8]83,但这里所说的诗并不局限于诗歌作品,它包括一切文学作品。“张力是优秀诗歌的基本特质,而意象张力则是诗歌张力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9]129综合以上论述可知,诗歌意象张力是诗歌意象中所有内涵和外延的有机体,是“意”和“象”的对立和统一,是理性与感性的制约与平衡,是在有限的物象和心象营造中生成无限的意义。在诗歌《告别辞:莫伤悲》中,邓恩充分运用“巧智”和“奇思妙喻”技巧,把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语境糅合在一起。这极大地拓展了诗歌意象的内涵和外延,最大限度地展现了诗歌意象的张力美。
从诗歌的前3节来看,邓恩主要营造了极具张力的天体意象。根据托勒密天文体系,宇宙呈圆形,地球是中心,它外面有九重天,由里向外依次是月亮天、水星天、金星天、太阳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恒星天和水晶天。第九重天即水晶天的运动牵引着各重天的运动,由此产生了天体的震动。但由于它们都在各自的本轮或均轮上做匀速圆周运动,所以它们的运动是自然而和谐的,是让人察觉不到的,是不会对人造成伤害的。依据这一天文知识,邓恩营造了天体意象,把精神情侣的离别比喻为天震,把世俗情侣的离别比喻为地震。前者虽然时刻都在做匀速圆周运动,但人们既感受不到运动的迹象,又不会因此而恐慌或不安;后者虽然不常出现,但一旦发生,它就会给人带来巨大的灾难和恐惧。正是在这种和谐与动荡、似动与非动、似离与非离、不安与平静的反差对比中,诗歌意象的内涵和外延才得以无限地延伸和拓展,诗歌意象的张力才展露无遗。也正是因为在这样的反差对比体验中,诗人的妻子安妮才感到他们之间的爱是永恒而高尚的,如同天体一样在爱的轮子上做着匀速圆周运动,她紧绷的情感之弦才渐渐地松弛下来,她的情感张力才得以展现。
从诗歌的中间3节来看,邓恩主要营造了充满张力的金箔意象。在中世纪的炼金术家看来,贵金属黄金是由贱金属提炼而成的,而贱金属铜或铅之所以不像黄金那样高贵和富有韧性,是因为它们在性质上还不够纯正,还需要进一步的提炼。依据这一科学知识,邓恩敏锐地在黄金语境和爱情语境中发现并建立了联系,从而营造了金箔意象和书写了绵绵无绝期的爱情。透过这个意象,我们可以看到:邓恩与他妻子的爱情是经过时间的熔炉提炼而成的,是经得起岁月考验的,是纯洁无瑕的,是既可在空间上无限延伸又可在时间上无限延长的。他们的爱情金箔不会因他的离别而破裂,相反,他的离别只会延展他们的爱情金箔。正是通过高贵与低贱、纯洁与混浊、有限与无限以及柔韧与脆弱的反差对比建构,邓恩才营造出了充满张力的金箔意象。也正是透过这一充满张力的意象,邓恩的妻子安妮才体验和感受到了他们爱情的高贵、纯洁、坚韧、永恒和无限。正是由于沉浸在邓恩所营造的美妙意境中,安妮紧锁的心灵窗户最终才得以打开,她才能看到闪闪发光的黄金般纯洁的爱情,也才会体验到绵绵无绝期的爱情。既然他们的爱情已成了永恒,那又何必计较这短暂的离别,更何况这短暂的别离又意味着爱的延伸。因此,对他们而言,短暂即永恒,有限即无限。
从诗歌的最后3节来看,邓恩主要营造了饱含张力的圆规意象。在诗中,诗人借用圆规这一几何意象,把坚贞不渝的夫妻二人比喻为紧紧相依的圆规的两只脚:在家操持家务的妻子为圆心脚,在外为事业打拼的丈夫为圆周脚。在爱的作用下,作为圆心脚的妻子坚定不移地守住家这个圆心,作为圆周脚的丈夫不停地围绕圆心脚的妻子做圆周运动,但无论圆周脚远离圆心脚多远,他最终还是要返回原点,返回家这个温暖的港湾。这一妙笔生辉的圆规意象不仅呼应了前面的天体意象与金箔意象,而且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不仅“使诗歌的形式与内容达到了完美的统一”[10]220,而且让妻子在有限的意象体验中感到他们之间无限的爱,在别离的残缺中感受到爱情的圆满。因此,邓恩的圆规意象张力不仅凸显在圆规与夫妻的形似中,而且凸显在圆规所画的圆和夫妻所期盼的圆满婚姻的神似中。
邓恩的诗歌意象张力在于其意象组合而成的合力。该诗中的3个经典意象传递出的是诗人的情之真和意之切,出发点都是在劝慰妻子不要悲伤。天体虽然时刻运动不止,但它总是趋于平静与和谐,不会给人带来任何伤害。精神情侣的别离虽然会带来心灵上的震动,但它同样是和谐的,是不会带来伤害的。只有世俗情侣的别离才如同地震,会给人带来巨大的灾难和恐惧。通过这样的类比,诗人旨在劝慰妻子不要因他的离别而惶恐不安。金箔意象表明他们的爱情纯洁无瑕,没有任何杂质。一方面,黄金在金属中属于上好的金属,是经过多次提炼而成的,因而他们的爱情是精诚所至,是高贵无比的;另一方面,黄金的韧性和延展性表明他们的爱情是经得起时光打磨的,是可以无限延伸和拓展的,是绵绵无绝期的,每一次别离都是爱的延伸和拓展。因此,金箔意象的呈现拓展了他们爱情的广度,加深了他们爱情的深度,延伸了他们爱情的长度,展示了他们爱情的维度。圆规意象肯定了妻子与他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她的坚定不移和默默支持不仅让他后顾无忧,而且为他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和巨大的动力。与此同时,家成了圆心或中心,既是他事业的起点,又是他事业的终点,因为他要终止在出发的地点。在邓恩笔下,冷冰冰的圆规散发出暖洋洋的活力。在这3个意象的合力作用下,邓恩的妻子从别离的恐惧中找到了安宁、回归了平静,从不纯洁的世俗之爱中体验到了他们纯洁的精神之爱,从短暂的别离中感受到了爱的永恒,从别离的残缺中感受到了爱情和婚姻的圆满。正是在这种甜蜜的回味体验中,妻子生离死别的苦楚消失了,心中的暖意油然而生,脸上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二、劳伦斯爱情诗《虹桥》中的意象张力
劳伦斯是20世纪英国重要的文学家,他作为小说家的地位已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同,他作为诗人的地位也逐渐得到认可,他作为意象派诗人也得到了彼特·琼斯的肯定,但他作为玄学派诗人的地位还尚未得到承认。其实,劳伦斯是一位深受其前辈影响和极具自觉性的诗人。这两方面的因素成就了劳伦斯,他最终成了强力诗人,成了20世纪英国名副其实的玄学诗人。深入分析劳伦斯的诗歌便可发现,无论在诗歌艺术还是在诗学思想方面,他的很多诗歌与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一脉相承。作为爱情的祭司,劳伦斯不仅是意象营造的巧匠,而且是玄学意义生成的能工。在其诗歌和小说中,劳伦斯所营造的“彩虹”意象既有效继承,又充分发扬了英国玄学派诗歌的“奇思妙喻”传统。他的长篇小说《虹》中的彩虹意象是和谐的两性关系的象征,但它高悬于天空,可望而不可及。在《死亡并不邪恶,机械才邪恶》一诗中,劳伦斯营造了一个爱与恨交织的彩虹意象。在《彩虹》一诗中,劳伦斯营造了一个可望而不可想、不可及的彩虹意象。在《虹桥》一诗中,劳伦斯营造了一个双脚永远并不拢的虹桥意象。这个意象是劳伦斯式的“奇思妙喻”的结晶,是对前面3个彩虹意象的再现和升华,体现了他对两性和谐的终极关怀,充分展示了他诗歌意象的张力美。
劳伦斯所营造的虹桥意象有着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外延。在《圣经·创世纪》中,彩虹是耶和华神为了向诺亚兑现承诺而在空中设立的标志。它是吉祥的象征,是灾难之后的福音。空中彩虹的出现意味着吉祥即将到来和灾难将永远离去。在营造虹桥这一颇具玄学色彩的意象的过程中,劳伦斯不仅沿用了彩虹的“吉祥”这一意义,而且赋予了它更深刻的内涵和更丰富的外延。在彩虹和男女两性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语境之间敏锐地发现了他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最终巧妙地在他们之间建立起了恰如其分的联系。
劳伦斯诗歌中的虹桥意象张力体现在上帝与诗人的同构中。依据《圣经》故事,上帝造了万物之后又造了人类,但由于人类总是犯罪,因此他就用洪水来惩罚人类,企图让人类在49个昼夜的洪水中灭亡,只让听其旨意的诺亚存活下来。并告知诺亚,每当空中出现彩虹的时候,洪灾就将过去,他就会迎来吉祥和希望。而且,上帝还授意他繁衍后代,不断地生儿育女。依据这一传说,彩虹成了联系万能上帝和人类的桥梁,成了人类的希望之桥,成了诗人的希望之桥。然而,在诗人劳伦斯笔下,万能的上帝最终还是不能把弓形腿的彩虹变直,也无法让它的双脚并拢,正如诗人所言:
有个物体是弓形腿,
设法将双腿摆到一起。
这就是彩虹。
即使上帝大人高喊:
“立正!”
它也无法将双脚摆在一起①。
从这一角度来看,作为创造的主体,上帝真是无所不能,他不仅造了人类和诗人,而且还造了万物,造了象征吉祥和希望的彩虹。作为创造的客体,无所不能的上帝在诗人面前又显得那么的无能为力:一方面,他对自己所造的客体彩虹无能为力,无法改变其既定的形状;另一方面,他又要听从诗人的意愿,接受诗人的再创造,眼看着自己所造的物体按照诗人的意愿被改造。透过诗人所建立的彩虹与上帝的联系,我们在能动与受动、创造与被创造,以及无所不能与无能为力之间感受到了诗歌的本质所在。因为“诗歌的本质在于获取新的关注,在于在已知世界中发现新的世界”[11]52,感受到了作为大自然的立法者和造物主的诗人的魅力和诗歌意象的张力。
劳伦斯诗歌中的虹桥意象张力体现在它内涵和外延极为丰富的拱形结构中。在诗歌《虹桥》中,劳伦斯把彩虹比作了弓形腿的物体。这个人格化的彩虹极易让人把它与另一事物(即箭)联系起来。根据人们的传统认知,弓和箭天生就是一对,它们之间彼此依赖,谁离开了谁都发挥不了功效。弓的弹性决定了箭的射程和力度,箭的锋利程度又决定了弓箭的整体功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弓形的虹桥意象本身就具备弹性的张力。与此同时,这一意象还会勾起人们对“丘比特之箭”的遐想,让人顺利进入到诗人所要创设的意境:宛若丘比特的诗人正手持金箭准备拉弓,以射中他的恋人并获得高尚而永恒的爱情。
劳伦斯诗歌中的虹桥意象张力同样体现在它内涵和外延极其丰富的拱形结构中。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在所有的结构图形中,圆形的受力能力最强,它能承受的压力也最大。作为圆的一半,拱形所能承受的压力也同样很大,因为它有另一半的拱形在隐性地支撑着它。从这一点来看,拱形的虹桥意象同样具有弹性的张力。而且,呈显性的拱形虹桥与呈隐性的拱形虹桥天然地成了一个圆。这个由显性虹桥和隐性虹桥所构成的圆又与西方神话中人的构成基本一致。在西方神话中,人最初是一个球形体,之后被分成了两半,每一半都渴望和另一半成为圆周,都试图找到另一半以达到先前的状态。通过追溯文化传统以建立文本联系,劳伦斯不仅为读者呈现了一座内涵和外延极为丰富的虹桥意象,而且表达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合二为一的圆满的两性关系。这种合二为一的两性关系又可在他的前辈诗人邓恩那里找到幕本。在《早安》一诗中,邓恩把相亲相爱的男女双方比作两个半球:“哪儿能找见更好的两个半球:既没寒冷的北方,又没日落的西方?”[3]48正是由于对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记忆、再现、续写和重构,劳伦斯所建构的拱形的虹桥意象才充满诗意的张力。
劳伦斯的虹桥意象张力体现在彩虹与男女两性的不同语境中所建立起的同一语境。在诗中,为了营造他终极一生所要实现的意境,劳伦斯以他那敏锐的眼光和诗性的直觉,通过陌生化的手法,把看似并无关联的事物生拉硬拽地放到了一起:彩虹与弓形腿的事物、彩虹与拱桥、彩虹与喷泉、彩虹与火箭、彩虹与紫罗兰、彩虹与男人和女人、彩虹与男人的心和女人的心。这些看似生拉硬拽的联系实则是诗人“巧智”和“奇思妙喻”的生动体现。正是在这看似完全不同的语境中,劳伦斯才真正发现并建立起了他所要追寻的同一语境:和谐美满的两性之虹。然而,这只不过是一道希望之虹,一道不可能实现的虹。因为在劳伦斯看来,自古以来,男女两性之间永远处于不和谐状态,两颗心永远不可调和,他们之间没有共鸣,只有欲望,他们总处在控制与反控制和占有与反占有之中。正如上帝改变不了虹桥的弓形腿和不能让它的双脚并在一起一样,万能的上帝也改变不了男女的处境,也调和不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这艰巨的任务最终就落到自觉的诗人身上了。
虹桥意象是劳伦斯过去感觉上和知觉上的经历在心中的重现和回忆。这种重现和回忆未必就一定是视觉上的。这一独特的思维形式体现了诗人对两性关系的探索。在对两性关系的探索中,劳伦斯一生梦寐以求的就是达到虹桥境界,即在有血有肉的男女两性之间搭建起一座希望之桥,以实现性与美的交融、灵与肉的统一、世俗与神圣的结合和心灵与心灵的共鸣。
三、《虹桥》和《告别辞:莫伤悲》的文本间性
虽然这两首玄学诗看上去相去甚远,但它们为读者搭建了一个跨越时空的文本对话的平台。透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发现两首诗的意象文本间性、爱情观文本间性和文化观文本间性。文本间性(互文性)理论家认为,狭义文本间性是指“一个具体文本与其他具体文本间的关系,尤其是一些有本可依的引用、套用、影射、抄袭、重写等关系”[12]26。“互文性使我们可以把文本放在两个层面进行思考:联系的(文本间的交流)和转换的(在这种交流关系中的文本之间的相互改动)”[13]57。文本间性研究就是在阅读和阐释中探寻两个文本之间既有的多维立体的内在联系,挖掘隐藏在两个文本之间的共有文学性,追忆伟大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发现子文本对母文本和伟大的文学和文化传统的转换生成。
劳伦斯的虹桥意象与邓恩的圆规意象的文本间性。从意象本身来看,它们之间毫无任何关联,但从意义的生成来看,它们之间的联系极为紧密。在圆规意象中,邓恩将夫妻二人比喻为圆规的两只脚,圆心脚为在家操持家务的妻子,圆周脚为在外为生活操劳和为事业打拼的丈夫。为了画出一个美满的爱情、婚姻、家庭和事业之圆,他们紧紧相连、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相互牵引、相互帮扶、相互成全。当画好一个同心圆之后,圆周脚就返回到圆心脚身边,就回到原点或妻子的港湾。在虹桥意象中,劳伦斯同样把彩虹的两只脚比喻为男人和女人。虽然他们永远都并不到一起,但为了搭建完美的虹桥,他们便比翼齐飞,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并在最高点完成交汇,形成完美的虹桥。在以意象的形式进行文本对话的过程中,劳伦斯一方面充分继承了邓恩对男女二人双脚关系式的诗意探索,另一方面又有效地突破了这一既定关系,在男女两性之间建构了一道飞升的彩虹和美丽的虹桥。
劳伦斯的圆弧之爱与邓恩的圆周之爱的文本间性。在《虹桥》一诗中,虽然象征男女两性的彩虹的双脚没法并拢到一起,但由于它们的腿呈弓形,它们的脚始终并不到一起,即使并到一起,也会因失去其原有的形态而成为畸形的环:
彩虹的两只脚
想并拢到一起。
但是不能,否则就成了畸形的环。
于是它们一跃而起,如同喷泉。
他一跃而起,他一跃而起,
如同两枚火箭!
它们在上方弯成弧形①。
为了实现自身的完美,彩虹的双脚以喷泉般的美丽和火箭般的速度一跃而起、比翼齐飞,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在最高点完成了交汇,最终形成了优美的圆弧和完美的拱形虹桥。正如张中载所言:“虹是一个人的愿望的实现,它代表一种超越现实的未来,一种理想;它代表男人和女人和谐的关系。拱形的虹是圆周的一半,渴望同另一半结合成一个圆满的圆周。它是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呼唤,它是对人的愿望的实现的憧憬。”[14]31在邓恩所营造的圆周之爱中,作为圆心脚的妻子坚定不移地守在家中,随着圆周脚的转动而发生倾斜,而作为圆周脚的丈夫则倾斜身子转圈,围绕作为圆心脚的妻子做匀速圆周运动,但无论距离圆心脚多远,他都要终止在出发的地点,画出一个圆满的圆周。在邓恩的圆周之爱中,圆心脚只有坚定不移,圆周脚才能把圆画好,才能终止在出发的地点。这就是邓恩的终止在出发点的圆周之爱。从中不难发现,劳伦斯的圆弧之爱续写了邓恩的圆周之爱,但作为强力的后辈诗人,劳伦斯并没受到邓恩的圆周之爱的束缚。相反,他重构了属于他自己的交汇在最高点的圆弧之爱。
交汇在最高点的圆弧之爱与终止在出发点的圆周之爱的文本间性。在劳伦斯的交汇在最高点的圆弧之爱中,由于男女二人的两颗心始终无法靠拢,他或她只有成就完美的自己,才能到达人生的最高点和完美而壮丽的玫瑰境界,才能画出美丽的弧线,才能在空中搭建起象征希望的两性关系的虹桥。因为在劳伦斯看来,“男女之间的爱如果是完美的话,应该既是合力运动,又是分力运动,既融为一体,又保持个性的独立性。”[15]122在邓恩的终止在出发点的圆周之爱中,虽然夫妻二人紧紧相依,但要画出爱情同心圆、婚姻同心圆和家庭同心圆,他们必须既做合力运动,又做分力运动;既通力合作,又保持自我。在画成一个又一个的同心圆之后,他们就回归各自的本真和原来的位置,他就回到了她的港湾,终止在出发的地点。从他们的爱情观对话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无论是交汇到最高点的圆弧之爱,还是终止在出发点的圆周之爱,他们的基点就是实现圆满,但劳伦斯爱情观圆满的基点是自我,而邓恩则是男女双方。
劳伦斯的情感书写与邓恩的情感书写的文本间性。作为玄学派诗歌大师,邓恩的情感书写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肯定爱情;另一类是否定爱情。在肯定爱情的时候,邓恩认为他的爱人是十全十美的,他的笔触也表现出了超然的神圣性和鲜明的浪漫化的人文主义色彩。当他否定爱情的时候,女人在他眼里一无是处,他笔端上流露出的是极端的现实性和世俗性。正如吴笛所言:“玄学派诗人笔下所书写的女子,尤其是约翰·邓恩笔下的女子,不仅现实,而且善变。”[16]19从中可以看出,邓恩的情感书写虽然仍以人文主义为核心,但已明显表现出一定的危机性。虽然继承了邓恩的浪漫化的情感书写传统,但劳伦斯的圆弧之爱只不过是他站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交接点上情感浪漫主义的表现,体现了他对完美的两性关系的美好憧憬和深切企盼。但对劳伦斯而言,这种企盼竟成了永远漂浮的能指,可望而不可及。这就是劳伦斯式的情感书写:情感上的浪漫主义和笔触上的现实主义。
四、结语
玄学派诗歌在英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往前可追溯到16世纪90年代甚至更早,往后可延展到20世纪20~30年代甚至更晚。虽然历经了兴盛、衰落和复活的过程,但这朵奇花并未因其他诗歌流派的发展和繁荣而凋谢和枯萎。相反,凭借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奇妙的诗学张力和强大的文本记忆力,它在历史的涤荡中仍然历久弥新、经久不衰,在繁茂的英国诗歌百花园中永不凋谢、大放异彩,在庞大的英国文学系统中兼收并蓄、推陈出新,在众多的“读者反应”中妙趣横生、快感迭起。作为英国玄学派诗歌的先锋和大师,邓恩不仅创作了代表该诗歌流派最高艺术的诗作,而且在诗学方面深刻影响着他的追随者和后辈诗人。身为邓恩的后辈诗人,生性敏感的劳伦斯在诗歌创作中,既表现出一定的继承性,又表现出超强的自觉性。正是基于这样的结合,劳伦斯最终成了强力诗人,成了20世纪英国杰出的玄学诗人,成了英国玄学派诗歌的继承人和开拓者。从英国玄学派诗歌这个开放的系统中和一脉相承的联系中可以发现,劳伦斯的诗歌文本《虹桥》与邓恩的诗歌文本《告别辞:莫伤悲》虽然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但在文本间性理论的关照下,它们之间的子文本与母文本的密切关系就显现了出来:虹桥意象与圆规意象之间的多维立体的内在联系;子文本在对母文本的有效记忆和转化生成中所形成的共有文学性。
注释:
①文中诗歌为吴笛翻译。
[1]于宏伟.英国诗人邓恩的玄学派诗歌意象及其影响[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2]李正栓,汤棣华.邓恩对19世纪英国文学的影响[J].外语教学,2012(4).
[3]胡家峦.英美诗歌名篇详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D H劳伦斯.灵船:劳伦斯诗选[M].吴迪,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5]赵烨,李正栓.邓恩诗歌中张力实践与新批评张力理论关联性研究[J].外语研究,2014(3).
[6]辜正坤.世界名诗鉴赏辞典[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7]南健翀.精致的诗意之瓮:约翰·多恩的诗歌《太阳升起》的“形式主义”解读[J].外语教学,2010(1).
[8]TATE A.On the limits of poetry[G]//Selected Essays:1928-1948.New York:Swallow press,1948.
[9]杨斌.意象张力在劳伦斯诗歌中的语言建构[J].山东文学,2009(11).
[10]李正栓.邓恩诗歌研究:兼议英国文艺复兴诗歌发展历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1]LAWRENCE D H.Selected literary critiques[G].朱通伯Shang 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3.
[12]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J].外国文学评论,2004(3).
[13]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M].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14]张中载.独特的劳伦斯,独特的《虹》[J].外国文学研究,2000(4).
[15]伍厚恺.寻找彩虹的人:劳伦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16]吴笛.英国玄学派诗歌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编辑:文汝)
I106.4
A
1673-1999(2017)02-0066-05
陈贵才(1980—),男,硕士,滇西科技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英语诗歌和劳伦斯诗歌。
2016-10-08
2015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学科建设项目“劳伦斯诗歌与英国诗歌传统的互文关系研究”(XKJS201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