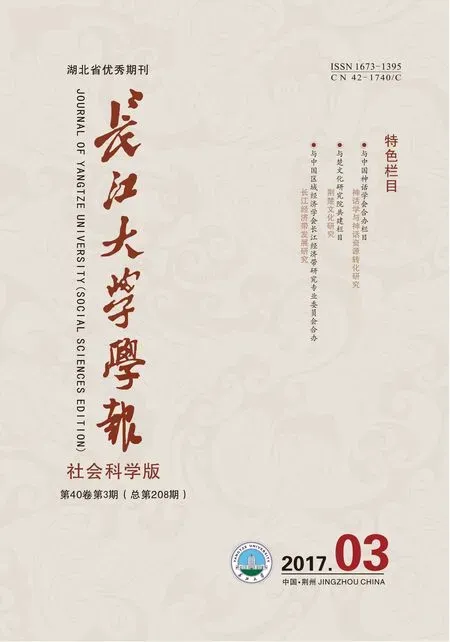张居正称孤与明人自称孤与不穀之风
周中梁
(香港理工大学 中国文化学系,香港 999077)
张居正称孤与明人自称孤与不穀之风
周中梁
(香港理工大学 中国文化学系,香港 999077)
张居正在书信中自称孤与不穀,被认为是其骄傲自大的表现,但这其实是他在服丧期间的自称,也是当时士人在书信中的习惯用法。孤本先秦王侯自称,唐宋以来,其在经学中的解释,逐渐从无父之人变成了缺少德、能,不再与居丧时的自称相关联。南北朝时期,居丧孝子自称孤子,后逐渐演化为孤,为元明士人所习用。不穀也是明代士人常用的自称,用法接近不佞。明代的好古风气,促进了这两个自称的使用。
明代;称呼;礼制;士人
一、张居正何以称孤
在讨论张居正的声名及其主导的改革在其身后何以落得悲剧结局时,论者多认为,其原因之一是,张氏在权位极盛时表现出的骄盈之气,使得神宗与其他一些官员为之侧目,在其死后群起而攻之。张居正曾在书信中自称孤与不穀的事实,常被人引以证其骄盈之态,如邓之诚先生云:“(张居正)与人书自称孤,或曰不穀。上表乞休,而曰:‘拜手稽首归政。’明明以摄政自居。”[1](P142)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期间的骄傲自大,有众多史料支持,已成定谳;[2](P810-840)但其在书札中自称孤、不穀一事,能否作为论述其骄傲自大的例证,还可以再商榷。实际上,已有学人初步解释了张居正为何会在书信中称孤。《张居正集》第2册《书牍》所收的第一篇张居正自称为孤的书信,为《答总宪高凤翥》。文中称:“不孝积愆累衅,遘此闵凶,叠辱吊唁,不胜哀感。比者屡沥血诚,恳乞终制,不蒙俞允,更荷踰分之恩。在主上虽自为国家计,而于孤之微情,则有歉矣。”[3]由“不孝”“闵凶”等用语来看,这篇书信无疑是张居正在服中所作。校注者在“孤”字下出注:“古时父死子称孤,因张居正在守孝服丧中,故自称孤。”那么,是否所有张居正称孤的书信都作于丧期中呢?该书所收张居正称孤的书札共40封,据校注者编年,其均作于万历五年至七年间。张居正之父张文明于万历五年九月去世,以三年之丧实际丧期27个月来计算,张居正服终于万历七年十二月,正与这些书札所覆盖的时间段相合,可证校注者的说法是可信的。不过,疑问还不能就此结束,为何身居高位的张居正,会不惮使用在今人看来难脱嫌疑的称呼呢?
事实上,居丧称孤,是当时士人笔下的习惯用法。明人方弘静云:“自称者……大夫自称不佞,而庶士袭称之,僭矣。乃有称不穀,居忧称孤者,不知其不可也”[4](P297),“孤与不穀,邦君之自称也,而士大夫或称之”[4](P444)。现再举两条明人书札中的用例作为参证。张四维《复王少方三》云:“盛使赍教至,披阅再三,忾叹无已。孤与公相知,可谓表里洞达。乃事变参差,难尽如人意。门下宏识通览,综于古今之故实,岂不审此,而何疑孤之深耶?”[5](P573)张四维在张居正身后继任首辅。此书作于万历十一年至十三年间,张四维当时丁父忧。王世贞《穆敬甫二》云:“至公之不及终爱孤,乃所以深爱孤也。孤生平乏实行奇节,万不足以望公之一,而不幸用薄技,有海内名。夫名者,兼知与忌而有之。公试观世之知我,孰与忌我者多也?知我而誉我者十,能胜夫忌我而毁我者一否?孤故筹之矣。”[6](P70)此书作于万历元年六月之前。王世贞此前任山西按察使,时在家丁母忧。张四维、王世贞都与张居正同时为官,其居丧时都在书牍中自称孤;尤可注意的是,张四维此书正是为了向王篆解释自己与张居正抄家一案并无干系而作,倘若此“孤”真有自比王侯之意,张四维是绝不敢在此时冒此大不韪的。由此而论,张居正称孤只是遵循当时的惯例,因此他人也不以为僭。
二、明人居丧称孤习惯之由来
明人居丧称孤习惯的由来,可以从礼制演化历程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来推求:一方面,孤是从儒家丧礼制度中逐渐演化出来的自称;另一方面,称孤习惯是明代社会中好古风习在士人文化中的具体体现。
《礼记·王制》云:“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说文·子部》云:“孤,无父也。从子,瓜声。”由此看来,孤字的本义即丧父之子。《礼记》中,孤被用作夷狄之君和小国诸侯的自称,而一般诸侯则自称寡人,遭丧的诸侯则降名改称孤。《礼记·曲礼下》:“诸侯见天子,曰臣某侯某;其与民言,自称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适子孤。”“适子孤”即居丧中诸侯自称。《礼记·杂记上》载有他国使者来吊唁本国国君之礼,相者称新君为“孤某”,也是类似的用法。赵翼《陔余丛考》卷36“称孤”条、卷37“孤哀子”条认为,孤的这种自称用法即从无父之义引申而来,并根据《左传》记载的辞令加以分类考辨,认为春秋时诸侯称孤的情况,或因尚未正式即位,或遭遇危难、兵败而自贬称呼规格。[7](P783-785,809-810)不过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先秦时期,称孤都是诸侯的专利。关于这种称谓的意涵,《老子》有云:“人之所恶,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为称”,“故贵以贱为本,髙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穀”。推其意,当指孤儿寡妇属于社会边缘人,受人轻贱,而王侯借以为谦称。这应该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看法。刘秉忠认为,孤作为王侯的自称用语,是用于指明自己的嫡长子身份,本源于丧期用语。[8]就其演变进程而言,这是有可能的。
春秋之后,孤一词作为王侯自称的用法一直沿用,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并由此衍生出称孤道寡等成语;但用法虽然延续,学者给予其的诠释却已发生变化。唐代官修《礼记正义》卷五《曲礼下》云:“孤者,特立无德能也”,“寡人者,言己是寡德之人”。[9](P137)元人陈澔《礼记集说》也沿用孔颖达说,以孤为“特立无德之称也”[10](P701)。由此可见,作为王侯自称的孤,在唐以后经学中的意涵已发生变化,与无父之义脱离关系了。这就为士人以孤自称扫除了障碍。与此同时,在士阶层习用的丧礼中,孤子这一自称逐渐兴起。这是后来士人称孤的滥觞。在先秦儒家礼制中,居丧孝子的自称本是哀子。赵翼云:“按古礼,父母丧,皆称哀子。如《杂记》云:‘祭称孝子、孝孙,丧称哀子、哀孙。’孔疏曰:‘祭谓卒哭以后之吉祭,丧谓虞以前之凶祭。’又《仪礼》筮宅之辞曰:‘哀子某为其父某甫筮宅。’又曰:‘哀子某来日卜葬其父某甫’。”孤子一词成为自称,当在南北朝时期。《宋书·桂阳王休范传》录有刘休范与袁粲、褚渊、刘秉等人的书信,刘休范时为其母荀太妃守丧,书信全篇自称孤子。同时的谢沈、袁粲等人,也曾自称孤子。这一在士人阶层中习用的自称,在唐宋时期进入《大唐开元礼》、司马光《书仪》等官私礼书中,并经理学大家朱熹所确认,成为定制。[7](P809-810)孤子与孤两种自称仅有一字之别,但在礼制中还没有相混。到了宋代,在孤子之外,又出现了新的自称不肖孤,如陈亮《先考卒哭文》:“呜呼!我先君委不肖孤而去之,于今四见朔矣。”[11](P735)这一称呼也为明人所沿用。前引王世贞给穆敬甫的信的第一封,开头就用了不肖孤的自称。[6](P69)
就笔者所见,最迟在元代,就出现了由不肖孤、孤子简化而来的新的孝子自称孤,与前两者并用。元人胡炳文《金氏孺人墓志铭》云:“程生霖衰绖诣吾门,再拜泣血言曰:‘孤不天,祸又延吾母。顾惟歙汪氏、严桂氏、信永丰韩氏,皆有节孝闻于官,旌表其闾,彰彰在人耳目。孤不克以闻于上,使母之(中阙)之孝将泯没无传,孤罪不容诛。’”[12](P780)值得注意的是,胡炳文为程霖代言,所用的“孤不天”典故,本出《左传·宣公十二年》郑襄公之口[13](P719),孤为诸侯自称,此时则已自然地嵌入文中,与普通儒生程霖的自称融为一体,而并不被认为是僭越之举。这样,从孤子这个居丧孝子自称衍生出来的孤,就进入了元明士人的书仪,成为时人用之不疑的自称了。
三、明人自称不穀习惯考
至于张居正的另一个自称不穀,明代也有士人以此自称。东林领袖顾宪成《尚行精舍记》云:“予向读孚如邹子衡言,有曰:‘今教化翔洽,家性命而人尧舜,而议论愈精,世趋愈下。维世君子惟以躬行立教,斯救时第一义乎!’作而叹曰:‘有是哉!何邹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也,不穀当佐下风矣。’”[14](P132)不仅当时士大夫如此自称,连生平并无科名,只是以儒生自居的建阳书坊主余象斗也自称不穀。余象斗《列国志传评林序》云:“不穀深以为惴,于是旁搜列国之事实,载阅诸家之笔记,条之以理,演之以文,编之以序。“[15](P10)与孤不同,不穀一词并无使用的特殊语境,但其用法与不佞有趋同的倾向。王世贞《华氏先贤像记》云:“学士鸿山公,今之最有闻于华者,汲汲其宗文献。家藏先五像,复于龙眠《兰亭图》中模上虞、长岑二像,取列传、告身论赞之,相及者合为一卷,而以记属不佞。世贞曰:“不穀敢以是尽华德乎哉!”[6](P285)文中“不佞”“不穀”相继出现,均为王氏自称。不佞义为不才,而不穀通说释为不善,均为谦词。
孤、不穀由王侯的谦称,变为士人的自称,虽自有其语义上的根源,但要突破旧有的礼制观念,还需要有其他方面观念变迁的助力。一方面,王侯自称之孤在经学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脱离了无父的本义,减少了士人以孤自称时的僭越顾虑;另一方面,明代后期社会文化中强劲的好古风气,对此也有所推动。李乐(嘉靖二十七年进士)《见闻杂记》云:“今天下诸事慕古,衣尚唐段、宋锦,巾尚晋巾、唐巾、东坡巾;砚贵铜雀,墨贵李廷珪,字宗王羲之、褚遂良,画求赵子昂、黄大痴。独作人不思古人。”[16](P268-308)这种好古风潮,既体现在服饰、文具、书画等有形的物质文化上,也体现在更抽象的精神文化上:在文风上,表现为李攀龙、王世贞等人所引领的古风;在称谓上,则表现为喜用古代官名代替当代官职,例如以周礼六官称呼明朝的六部尚书,称都御史为大中丞。明人于慎行在《称谓》中曾提到“至于锦衣掌印称为大金吾,顺天府尹称为大京兆”,并认为某些比附已涉无稽,实属孟浪之举。[17](P148-149)明人从孤字的本义入手,将这一古老自称,重新定义为士人使用的居丧自称,及启用其本来用法已逐渐废弃的不穀代替不佞,正是这种好古风气的又一体现。
张居正自称为不穀的书札,分布于万历四年年底至十年张氏去世之间。张居正为何从万历四年年底起开始自称不穀呢?据《明神宗实录》,当年十月丙子,张居正任大学士九年考满,神宗命其“特进左柱国、太傅,俸如伯爵”,均为特殊恩典。张居正辞去了太傅与伯爵俸,只受上柱国。[18](P1274-1275)笔者认为,张居正于此时开始以不穀自称,就其个人心态历程而言,虽可能有自高身份的意义,但也完全合乎当时士人的习惯,而并非引人侧目的骄盈之举,因此即便其生前身后的政敌,也未将其列为罪证。
综上所述,在礼制演化、经学观点转变,以及社会好古风气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孤、不穀等古老自称,被明人赋予了新的含义和用法。张居正等人的称孤之举,虽引来坚持以古礼为准绳的方弘静等人士的批评,但并未掀起更大的波澜。由此可见,当时士人的习用称呼所含之义,与先秦古礼所含之义,已经有了不小的差异。这一中晚明社会变迁多彩图景中的特殊现象,也提醒学人在解读文献时,要注意把握其背后所隐含的特殊的时代风气。
[1]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韦庆远.张居正与明代中晚期政局[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张舜徽,吴量恺.张居正集(第2册)·书牍[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4]方弘静.千一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5]张四维.条麓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6]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
[7]赵翼.陔余丛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
[8]刘秉忠.孤寡不穀本义探[J].理论月刊,1991(6).
[9]孔颖达.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0]陈澔.礼记集说[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
[11]陈亮.龙川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
[12]胡炳文.云峰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
[1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4]顾宪成.泾皋藏稿[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
[15]余象斗.列国志传评林[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6]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A].蒲慕州.生活与文化[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17]于慎行.穀山笔麈[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8]顾秉谦.明神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966.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2016-12-20
湖北省教育厅教育项目(2016260)
周中梁(1988-),男,辽宁本溪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史研究。
K248.3
A
1673-1395 (2017)03-002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