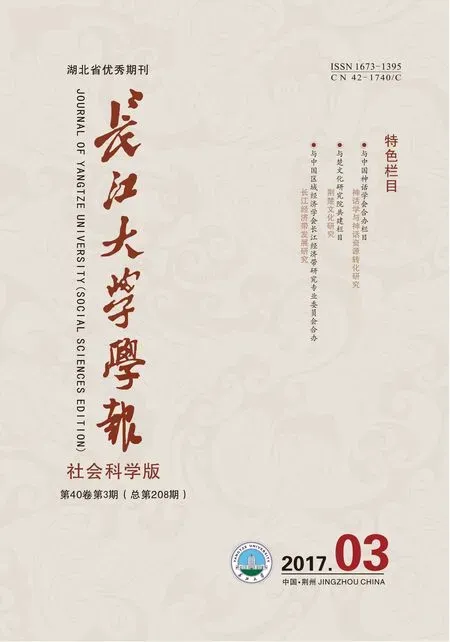五代赋家赋作的时代性与地域性
刘伟生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五代赋家赋作的时代性与地域性
刘伟生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五代辞赋题材多样,主题多元,除传统的颂美与讥刺外,更多乱世感伤与怨愤,以及虚无与娱乐心境。五代辞赋罕见长篇大赋,律赋风格由典重持正而转为凄美哀伤、修整甜俗。五代辞赋题材内容与艺术风貌的形成,与赋体自身演变规律有关,也多少受到时代政局、科考、经济文化乃至地域因素的影响。五代科考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自晚唐以来辞赋创作尤其是律赋创作的裂变:一面是对技艺范式的强调与竞奔之风的普遍,一面是对科考功令的游离与真我人性的发抒。五代经济文化如雕版印刷、宗教、绘画艺术、野史小说,也影响了辞赋创作。
五代;辞赋;时代;地域;甜俗
五代是一个分裂割据的时代,也是一个过渡的时代。这过渡不仅牵连唐、宋两朝政权,更关乎两型文化的转变。明人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序》云:“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 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 以至于唐, 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 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1](P1191)唐宋之变,既彰明于政治、经济、科举、教育,也表现在社会风俗与文化学术上。1910年,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认为唐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的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2](P10)。由此导出“唐宋变革”这一学术命题。内藤湖南的文章,论及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具体表现,其中关于文学变化的要点为:文章由六朝至唐流行的重形式的四六文,变为中唐韩柳以后重自由表达的散文体,诗、词、曲代兴,形式更加自由,语言由雅变俗,“文学曾经属于贵族,自此一变成为庶民之物”[2](P16-17)。许总《论五代诗》承此而来,提到五代文学性质的变化:“文人生活的贫寒化以及文化进程的世俗化,使得文学的本质属性表现为与宫廷文学的贵族化截然相反的平民化特征。”[3]就文体而言,五代是词的草创时代;就地域而言,五代而旁及十国,也“不愧为一个有文学的时代,而且在文学史上还可以称为一个灿烂的时期”[4](P2)。这灿烂主要就体现在词的成就上。五代的辞赋虽远不如词生机勃勃而又光辉灿烂,但我们依然可以尝试从仅存的赋作、赋集与赋学活动中,了解五代辞赋的题材、内容、风格、手法,体察五代赋家的情怀与作赋目的,然后从中窥探这个时代这些地域的政风、士风与文化特征,并反过来藉以分析五代辞赋的时代特质。
一、五代辞赋的题材范围与主题取向
晚唐赋坛,曾因杜牧、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罗隐、孙樵、刘蜕等人的批判锋芒而异彩纷呈,到了五代,这种源出忠爱的激愤也已消弭,代之而起的是感伤、悲悯、怨愤、怀疑、虚无的情绪,赋的功用也不止于应举、献颂、唱和,亦可以成为遣怀乃至娱乐的手段。
单以题材而论,五代的辞赋还在往多样化方向发展。举凡咏物、写景、艺文、仙释、咏史、怀古、论理、直接的抒情与讽颂,都是五代现存辞赋习见的题材。咏物的赋,有徐寅《斩蛇剑赋》《竹篦子赋》《铸百炼镜赋》《涧底松赋》,韩偓《红芭蕉赋》《黄蜀葵赋》,徐铉《木兰赋》,王损《通犀赋》,杨洽《铁火箸赋》,王澄《梓材赋》,张颖《形盐赋》,裴振《雉尾扇赋》,江文蔚《土牛赋》《螃蟹赋》,舒雅《鹤赋》,王翃《昭阳殿赋》等。写景的赋,有徐寅《御沟水赋》《鲛人室赋》《雷发声赋》《山瞑孤猿吟赋》,徐铉《新月赋》,李铎《密雨如散丝赋》《秋露赋》,朱邺《扶桑赋》《落叶赋》,张随《蟋蟀鸣西堂赋》,余镐《阆苑赋》,江文蔚《天窗赋》,李煜《登高赋》,朱邺《雷出地上震赋》等。以艺文为题材的赋,有徐寅《割字刀子赋》《歌赋》《玄宗御制卢征君草堂铭赋》《陈后主献诗赋》《太极生二仪赋》《玄宗御注孝经赋》,刘骘《善歌如贯珠赋》,荆浩《画山水赋》,张随《无弦琴赋》,杨遂《太极生两仪赋》,马郁《转转赋》等。以仙释为题材的赋,有释延寿《金刚证验赋》《法华瑞应赋》《神栖安养赋》《华严感通赋》《观音应现赋》,杜光庭《纪道德赋》等。咏史赋,如徐寅《勾践进西施赋》《过骊山赋》《驾幸华清宫赋》《再幸华清宫赋》《口不言钱赋》《荐蔺相如使秦赋》《朱虚侯唱田歌赋》《樊哙入鸿门赋》《江令归金陵赋》《管仲弃酒赋》《员半千说三阵赋》《文王葬枯骨赋》《卞庄子刺虎赋》,张随《上将辞第赋》《纵火牛攻围赋》,李琪《汉祖三杰赋》等。怀古赋,如徐寅《五王宅赋》《丰年为上瑞赋》《白衣入翰林赋》《朱云请斩马剑赋》《毛遂请备行赋》《避世金马门赋》《东陵侯吊萧何赋》《首阳山怀古赋》,张翊《潼关赋》等。论理的赋,有徐寅《京兆府试入国知教赋》《福善则虚赋》《外举不避仇赋》《贵以贱为本赋》《垂衣而天下治赋》《知白守黑为天下式赋》《止戈为武赋》《义浆得玉赋》,杨夔《溺赋》,张随《耀德不观兵赋》《庄周梦蝴蝶赋》《海客探骊珠赋》《叶公好龙赋》等。直接讽颂与抒情的赋,有徐铉《颂德赋》,张随《云从龙赋》,史虚白《割江赋》,徐寅《人生几何赋》《寒赋》《扣寂寞以求其音赋》《隐居以求其志赋》,梁嵩《代母作倚门望子赋》等。
五代辞赋题材既多样,主题也多元,除了传统的颂美与讥刺外,更多了乱世的感伤与怨愤,以及虚无与娱乐的心境。徐寅《山瞑孤猿吟赋》《雷发声赋》《涧底松赋》,徐铉《木兰赋》《新月赋》,朱邺《落叶赋》,裴振《雉尾扇赋》,韩偓《红芭蕉赋》《黄蜀葵赋》,江文蔚《螃蟹赋》,马郁《转转赋》等等,都是此类心境的写照。至于文士所共有的期用之心,也习见于杨洽《铁火箸赋》、张颖《形盐赋》、张皓《藏冰赋》、朱邺《扶桑赋》、张随《蟋蟀鸣西堂赋》等赋作中。这与中唐的典正,晚唐的激愤,是有所不同的。可见五代辞赋虽少大匠名作,也能展现一代风习。
二、五代辞赋的艺术风貌
五代辞赋的题材与用途既多元多样,形式上也不尊一统,多体多貌;但总体而言,罕见杨夔《溺赋》这样的长篇仿古大赋,律赋反倒因逐渐摆脱科举功令的束缚而变化多端,风格由典重持正而转为凄美哀伤、修整甜俗。
“修整”“甜俗”是李调元对五代辞赋的评价。李调元《赋话·新话》卷四说:“五代去晚唐不远,然风气迥殊晚唐,人之律赋,精密更甚,如起句云‘苍苍茫茫道远,倚倚望望情伤’,用六娟秀,而从前浑古朴至之气,荡然无存,且琢句过于修整,则渐就平芜,遣调必求谐靡,则转入甜俗,此流弊之所必至也。五代承唐制,亦以进士设科,以诗赋取士。如梁嵩《倚门望子赋》,则沿晚唐之格调,而流弊字句既拖沓无味,又萎靡不振,风气益下矣。”[5](P664-665)琢句修整,遣调甜俗,其实是体现在造句精巧典丽和用语柔靡散漫两方面的。以今人的眼光来看,梁嵩《倚门望子赋》以骈句叠词再加代言体抒亲子之情,实属甜而不俗、真淳动人的佳作。
典丽精巧,是律赋经中晚唐因试赋需要,而长期演练不断累积技艺的结果。李调元《赋话》综述唐代科考与律赋风格及名家作手时说:“唐初进士试于考功,尤重贴经试策,亦有易以箴表赞。而不试诗赋之时,专攻律赋者尚少。大历、贞元之际,风气渐开,至大和八年杂文专用诗赋,而专门名家之学,樊然竞出矣。李程、王起,最擅时名;蒋防、谢观,如骖之靳;大都以清新典雅为宗,其旁骛别趋,元、白为公。下逮周繇、徐寅辈,刻酷锻炼,真气尽漓,而国祚亦移矣。抽其芬芳,振其金石,亦律体之正宗,词场之鸿宝也。”[5](P642)律赋至于中晚唐而名家辈出,技巧日精,无疑是广大士子纷纷投入,“刻酷锻炼”的结果。以律赋在彼时的主要功能来衡裁,“清新典雅”,精巧工丽,也必为律体正宗,所以李调元又说:“《文苑英华》所载律赋至多者,莫如王起,其次则李程、谢观,大约私试所作而播于行卷者,命题皆冠冕正大。逮乎晚季,好尚新奇,始有《馆娃宫》《景阳井》及《驾经马嵬坡》《观灯西凉府》之类,争妍斗巧,章句益工。而《英华》所收,显从其略,取舍自有定制,固以雅正为宗也。元和长庆以后,工丽密致,而又不诡于大雅,无踰贾相者矣。”[5](P647)内容冠冕正大,技巧工丽密致,正是律赋用于科考的要求,也是赋选、赋话取舍评价的标准。
就律赋的写作技艺而言,五代承晚唐而来,有着太多可以凭藉的基础。这基础如同基因嵌入文化机体,而成为五代赋家与时俱来的资本。徐寅因赋体创作精致完善而成为一代专门大家自不用说,便是王澄《梓材赋》、张颖《形盐赋》、李铎《密雨如散丝赋》《秋露赋》、徐铉《木兰赋》,乃至御厨副使张皓的《藏冰赋》、画家荆浩的《画山水赋》,或古或律,莫不骈对精工,用语巧熟。还有释延寿《金刚证验赋》《法华瑞应赋》《神栖安养赋》《华严感通赋》《观音应现赋》、杜光庭《纪道德赋》等言释道之理,也假赋体阐释。再看那些留存的残句与时人的评价,也都以精巧工丽为准的。《旧五代史》所载有关李琪作赋的两则佚事说:“琪即縠之子也,年十三,词赋诗颂,大为王铎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铎召縠宴于公署,密遣人以《汉祖得三杰赋》题就其第试之,琪援笔立成。赋尾云:‘得士则昌,非贤罔共。龙头之友斯贵,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项氏之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铎览而骇之,曰:‘此儿大器也,将擅文价。’”[6](P782)“昭宗时,李谿父子以文学知名。琪年十八,袖赋一轴谒谿。谿览赋惊异,倒屣迎门,出琪《调哑钟》《捧日》等赋,谓琪曰:‘余尝患近年文士辞赋,皆数句之后,未见赋题,吾子入句见题,偶属典丽,吁!可畏也。’琪由是益知名,举进士第。”[6](P782)十多岁的少年就以辞赋典丽而知名,可见时代风尚之所在。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5《艺文二》也曾举江文蔚赋论五代赋作的工巧:“晚唐、五代间,士人作赋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窗赋》:‘一窍初启,如凿开混沌之时;两瓦鴥飞,类化作鸳鸯之后。’又《土牛赋》:‘饮渚俄临,讶孟津之捧塞;度关倘许,疑函谷之丸封。’”其所举江氏赋句,化用《庄子》倏忽凿混沌,《魏志》周宣解文帝“两瓦坠地”梦,老子骑牛度关,王元请兵丸封诸事,及牛渚、孟津、函谷诸地,“工丽密致”,诚非易事。
其实五代赋集、赋格的大量出现,本身即说明赋体技艺的高度发达。不论是集录唐人及近代的赋体选集还是当代作家个人的赋集,在五代都颇多见。赋论方面,和凝《赋格》是专门之作,其他有关诗文评述的著作,也可能道及辞赋创作的技艺问题。
造句精巧典丽源于对科举的粘附,用语柔靡散漫则因为对科考的游离以及受时代风习的影响。因为作赋不止于科考的需要,还可以用来表达个人情感,甚至成为嬉戏娱乐的工具,取材命题便不必篇篇冠冕正大,用语遣词也不必时时清雅纯正,于是靡靡之情与俗语散句都可以入赋。
韩偓的《红芭蕉赋》《黄蜀葵赋》便近于香奁体诗。《红芭蕉赋》云:
瞥见红蕉,魂随魄消。……谢家之丽句难穷,多烘茧纸。洛浦之下裳频换,剩染鲛绡。……赵合德裙间一点,愿同白玉唾壶。邓夫人额上微殷,却赖水晶如意。……莺舌无端,妒夭桃而未咽。猩唇易染,嬲浮蚁以难醒。在物无双,于情可溺。横波映红脸之艳,含贝发朱唇之色。僧虔密炬,烁桂栋以难藏。潘岳金釭,蔽绣帏而不隔。大凡人之丽者必动物,物之尤者必移人。不言而信,其速如神。……天穿地巧,几人语绝色难逢。万古千秋,唯我眷红英不尽。[7](P8738)
《黄蜀葵赋》云:
色配中央,心倾太阳。……萼绿华未遇杨羲,冠簪駊騀。杜兰香喜逢张硕,巾帔飘扬。……动人妖艳,馥鼻生香。千里鹄雏,滥得名于太液。三秋菊蕊,虚长价于柴桑。向日微困,迎风欲翔。……几多之金粉遭窃,一点之檀心被污。何须逼视,汉夫人之鸳寝多羞。不待含情,晋天子之羊车自驻。……懊恨张京兆,唯将桂叶添眉。怅望齐东昏,却把莲花衬步。骚人易老,绝色多愁。曷忍在绮窗侧畔,唯当居绣户前头。目断犹驻,魂消未收。映叶而似擎歌扇,偎栏而若堕妆楼。感荀粲之殷勤,誓无缄著。怨谢鲲之强暴,未近风流。……已而已而,唯有醉眠于丛畔。[7](P8738-8739)
两赋都多用艳人艳事艳物艳语,特显艳丽,与后来艳情词曲小说已然相似,有悖唐赋雅正之宗。
以雅正为宗虽不反对刻画雕琢,但一定要求隽不伤雅,细不入纤,不乖体制,所以李调元评林滋《阳冰赋》“刻画工细,隽不伤雅”[5](P653),说柳宗元《披沙拣金赋》“巧不伤雅”[5](P654),评陆环《曲水杯赋》“点缀依媚,而高雅之致尚存,正喜其略带一分质朴”[5](P655),而李铎《密雨如散丝赋》中那种“极力形容”纤细逼真的描写,便被认为“刻画伤雅”。其实以纯艺术的视角而言,李铎《密雨如散丝赋》《秋露赋》描摹刻画工丽纤巧,能道前人所未道,正是赋体体物艺术的演进。
产生媚丽、纤靡、萧散效果的,还有以俗语、散句入赋,以古赋结构写律赋等。浦铣《復小斋赋话》上卷曾注意到:“古诗中多用‘君不见’三字,黄御史滔用入律赋,倍觉姿媚。”[8](P185)浦铣注意到了律赋中用诗语,但并没有进一步分析这“君不见”三字是乐府中用以提倡的常用语,目的在于引人注目,提示后续内容的重要性;也没有提到乐府歌行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怨伤之意时,多以“君不见”为首,如李白《将进酒》、杜甫《兵车行》、高适《燕歌行》、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诗句首;当然,浦铣更不会想到这个源自口语俗言的“君不见”,在音律上有衬托的功能,在叙述上有转换视角的作用。徐寅《人生几何赋》后半云:
君不见,息夫人兮悄长默,金谷园兮阒无睹。香阁之罗纨未脱,已别承恩。春风之桃李方开,早闻移主。邱垅累累,金章布衣。白羊青草只堪恨,逐利争名何太非。尝闻萧史王乔,长生孰见。任是秦皇汉武,不死何归。吾欲挹玄酒于东溟,举嘉肴地西岳。命北帝以指荣枯,召南华而讲清浊。饮大道以醉平生,冀陶陶而返朴。[7](P8750)
赋写人生无常,祸福不定,抒发的是末世感伤之情。从“君不见”到“吾欲”是视角的回归,中间“白羊青草只堪恨,逐利争名何太非”两句,也是对叙事节奏的有意调整。这些技巧的共同运用,使赋篇摇曳多姿。杜光庭《纪道德赋》更将俗语人称及各种句式用到极至。其赋后半云:
岂不闻乎?天地非道德也无以清宁;岂不闻乎?道德于天地也有逾绳墨。语不云乎:“仲尼有言,朝闻道,夕死可矣”,所以垂万古,历百王,不敢离之于顷刻。怀古今,云古今,感事伤心;惊得丧,叹浮沈,风驱寒暑,川注光阴。始衒朱颜丽,俄悲白发侵。嗟四豪之不返,痛七贵以难寻。夸父兴怀于落照,田文起怨于鸣琴。雁足凄凉兮传恨绪,凤台寂寞兮有遗音。朔漠幽囚兮天长地久,潇湘隔别兮水阔烟深。谁能绝圣韬贤、餐芝饵术?谁能含光遁世、炼石烧金?君不见屈大夫,纫兰而发谏;君不见贾太傅,忌鵩而愁吟。君不见四皓避秦,峨峨恋商岭;君不见二疏辞汉,飘飘归故林。胡为乎冒进贪名,践危途与倾辙?胡为乎怙权恃宠,顾华饰与雕簪?吾所以思抗迹忘机,用虚无为师范;吾所以思去奢灭欲,保道德为规箴。不能劳神效苏子、张生兮,于时而纵辩;不能劳神效杨朱、墨翟兮,挥涕以沾襟。[7](P9679)
累用“岂不闻乎”“谁能”“君不见”“胡为乎”“吾所以”等附加语,再辅之参差多变的句法,直教人眼花缭乱,难怪此赋还可以被切分成宝塔诗。至于以古赋结构比如问答体写律赋,自晚唐来已属多见,兹不多述。
三、五代政局、士风及地域因素对辞赋创作的影响
五代辞赋题材内容与艺术风貌的形成,与赋体自身的演变规律有关,也多少会受时代政局、科考、经济文化乃至地域因素的影响。
五代十国是多政权并存及频繁更替的时代,也是礼崩乐坏的乱世,所以欧阳修感慨道:“甚矣,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9](P174)乱世中的统治者更加喜怒无常,凶残成性,为了在政治杀伐中求自保,士大夫们也变得趋时务实:或顺时听命,成为政治场中的不倒翁;或遁迹出世,成为山翁、渔夫、僧侣、道徒。冯道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外加契丹五朝,自称“长乐老”,并著《长乐老叙》,不以为耻,反以为乐,即可折射出当时的道德风尚。“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声音之道与政通,文风亦然,五代政风、士风影响及于文学,便是刚健消亡,委顿日多,凄美哀伤,修整甜俗,华过于实。
对汤武革命的评价,向称千古难题,因为这涉及到改朝换代的“革命”是否正义的问题,虽然孟子曾巧妙地将商纣称之为“残贼之人”以肯定汤武革命,但在现实政治中,总有难于确信的边界存在,所以聪敏的汉景帝干脆不让黄生和辕固生们谈论此事:“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10](P3123)与之相关的夷齐归隐,更具体指向新旧更替之际臣子的立场或出处问题。这样的千古难题摆在乱世志士面前,更显难上加难。徐寅《首阳山怀古赋》即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厚殷纣而薄宗周,曷称仁智。弃三隅而执一向,可谓昏蒙。……何不吊纣之不德,庆周之有国。而乃助于纣以申谦,怨于周而不食。鸿飞豹隐,亡情于浊浪之湄。蝉腹龟肠,化骨于孤峰之侧。”然后假逋客之口试图对此做出解释:“夷齐以让国无为,求仁立规。何历数之不究,曷兴亡而不知。非不知周之可辅,纣之可隳,所忧者万纪千龄,所救者非一朝一夕。恐后代谓国之可犯,谓君之可迫。强者以之而起乱,勇者以之而思逆。所以激其时,抗其迹。往者勖而来可惩,义要行而身不惜。”这样的阐释,既利于维护既有的君国体制,也可藉以表白士臣节义,在徐寅之世显属审慎而机敏的言论。当然言论归言论,便是徐寅,后来也不免游梁,依王审知、王延彬。据说徐寅在梁期间,曾因触怒朱温而献《游大梁赋》以讨好,中有“千金汉将,感精魂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风而胆落”之句,又为王延彬父王审邽撰墓碑文,碑文有“皇者天皇,绩者动绩”之语,人以为献谀。盖文士之言未可全信,况生变乱之世。《新五代史》卷31《周臣传第十九》记扈载曾作《运源赋》《碧鲜赋》而得周世宗赏识,与张昭、窦俨、陶穀、徐台符等俱被进用,“穀居数人中,文辞最劣,尤无行,……以进谀取合人主,事无大小,必称美颂赞”,而“载以不幸早卒,……而不为穀之谀”,然后有一通议论:“夫乱国之君,常置愚不肖于上,而强其不能,以暴其短恶,置贤智于下,而泯没其才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呜呼,自古治君少而乱君多,况于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胜叹哉!”[9](P345-346)其强调的也是时代对士人人格与文风的影响。
五代十国地域不同,自然气候不同,政治、经济、文化也有差异,文学创作包括辞赋也多少会呈现出一些区域性特征。西蜀和南唐两大文学中心,创造了词作的辉煌。辞赋创作则以闽地最为兴盛。自中唐以来,闽地不乏文学大家,如欧阳詹、林藻等,都算得上名冠一时的作家。晚唐五代律赋三大家王棨、黄滔、徐寅全为闽人,颇有闽赋即天下赋之感。此外谢廷浩颇以辞赋著名,与徐寅不相上下,时号“锦绣堆”。余镐作《阆苑赋》、朱邺作《雷出地上震赋》等,都可证闽地辞赋创作之盛。闽地赋作之盛,概缘于唐末文士避乱入闽,与闽地文士素重互相借鉴与推重。他如事楚武穆王马殷的李铎作《密雨如散丝赋》,其所写之景,所取物象,所用地名如“浣沙”“濯锦”“织妇停梭”“舟人罢钓”“湘浦燕飞”等,均富有南楚地方特色。吴越重佛,遂有僧人释延寿等作赋。大体而言,北中国时局动荡,朝代更迭,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南方则因战争相对较少,局部安定,地区经济文化反而有所发展。当然北方不同时期情况不同,后唐、后周也曾出现小康之局,也曾“讲求礼乐之遗文”[9](P345)。南方不同地区则差异明显,或自具面目,或得益于交通。各时期、各地区都有作家与文学活动,这些作家也可能生活于不同时期,往来于不同地区。如此情形,必然使文学的区域性呈现出诸多复杂的面貌。
四、五代科举、经济文化与辞赋
五代科考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自晚唐以来辞赋创作尤其是律赋创作的裂变:一面是对技艺、程文、范式的强调与竞奔之风的普遍,一面是对科考功令的游离与真我人性的发抒。
五代虽为乱世,但并未废止科考,而且“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11](P439)。《五代登科记总目》记:“五代五十二年,其间惟梁与晋各停贡举者二年。”[12](P282)据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统计:“五代时各个王朝共录取进士六百四十名、诸科一千五百三十名、明经六名、博学弘辞科二名,上书拜官一人。”[13](P87)十国中南唐、闽、南汉、前后蜀等也时兴科考,所以科考仍然是士人出仕的重要途径。不仅如此,在政权更迭频繁,割据局面长存,而家世阀阅不再成为必要条件的时代,科考的功利性反而得以强化。从科目来看,诸科取人多于进士。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选举三》解释说:“丧乱以来,文学废坠,为士者往往从事乎帖诵之末习,而举笔能文者固罕见之, 国家亦姑以是为士子进取之途,故其所取反数倍于盛唐之时也。”[12](P283)从评判标准来看,技艺受到特别重视,格赋、程文被当作范式。史载,李怿唐末举进士,天成中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累迁尚书右丞承旨,时张文宝知贡举,因中书奏落进士数人,请诏翰林学士院作一诗一赋,为举人格样,学士窦梦徵、张砺辈撰格诗格赋各一,而宰相未以为允,遂请怿为之,怿笑而答曰:“李怿识字有数,顷岁因人偶得及第,敢与后生髦俊为之标格!假令今却称进士,就春官求试,落第必矣。格赋格诗,不敢应诏。”[6](P1224)事虽未成,可见格赋格诗之通行。陆游《南唐书》列传第十二则载伍乔以《画八卦赋》中进士第一,元宗(中主李璟)命石勒乔赋以为永式事:“伍乔,庐江人,居庐山国学数年,……举进士,及试《画八封赋》《霁后望钟山诗》,……主司叹其杰作,乃徙贞观处席北,洎处席南,以乔居宾席,及覆考榜出,乔果为首,洎、贞观次之,人称主司精于衡鉴。元宗亦大爱乔程文,命勒石以为永式。”[14]不特程文、范式成为科考必备,干谒、荐举乃至贿赂、托附也成士子试外功夫。滥取现象常有发生,浅狭之辈每得进身。后周曾三次重试进士,其中显德二年(955)三月,新及第进士16人即被周世宗勾落12人。世宗诏令中提到:“国家设贡举之司,求英俊之士,务询文行,方中科名。比闻近年以来,多有滥进,或以年劳而得第,或因媒势以出身。今岁所放举人,试令看验,果见纰缪,须至去留。”[6](P1527)甚有误放及第者,如《册府元龟》卷651《贡举部·谬滥》载:“晋高祖天福三年, 崔棁权知贡举,时有进士孔英者行丑而才薄,宰相桑维翰素知其为人,深恶之。及棁将锁院,礼辞于维翰, 维翰性语简, 止谓棁曰:‘孔英来也!’盖虑棁误放英, 故言其姓名, 以扼之也。棁性纯直,不复禀覆,因默记之,时英又自称是宣尼之后,……棁不得已,遂放英登第。榜出,人皆喧诮。维翰闻之,举手自抑其口者数四,盖悔言也。”[15](P2175)可见五代科举的风气和秩序。这样的风气下,士子的水平如何呢?《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载:“有工部侍郎任赞,因班退,与同列戏道于后曰:‘若急行,必遗下《兔园册》。’道知之,召赞谓曰:‘《兔园册》皆名儒所集,道能讽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耶!’赞大愧焉。”[6](P1656-1657)因为这些缘故,官方会不断严格解送、验证、就试程序与录取标准,士子则一面须熟习应试技艺,一面忙着打通各路关节;而另一方面,因为考试制度的松懈,考试文体反得到某种程度的解放。当律赋从科考功令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赋家们便常藉以抒写个人性灵,或其他科考以外的社会世象与自然景致。徐寅凭赋中举,以赋酬唱,因赋自负,甚而在辞赋中喟叹历史境遇,抒写自我人生的种种行谊,即其显例。
五代经济文化如雕版印刷、宗教、绘画艺术、野史小说也多少影响到了辞赋的创作。
五代虽为乱世,经济文化的发展仍有可观之处。经济上除了局部地区不乏安定富庶外,印刷事业的发展尤其值得肯定。雕板印刷或肇于隋,行于唐,但多用于民间佛经、历书、字书、占梦书、相宅书之类的印制。五代则于规模、内容、质量、经营性质等,都有全面扩充与提升。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后周广顺三年全书刻成,后蜀宰相毋昭裔私人出资印刷《九经》《文选》《初学记》《白氏六贴》。此外,南唐刻印《史通》《玉台新咏》,后晋宰相和凝自刻诗文百余卷。凡此种种,说明于佛经及杂书外,儒家经籍、写作所用类书及文史名著也开始大量印行,而个人文集的刊刻,更属开先河之举。雕版书籍的大量印行,不仅有利于文学的创作,也便于文献的保存与文化的传播。
五代十国宗教盛行,社会对佛、道的崇奉,不特影响及于文士的思想与生活,也直接催生了释延寿、杜光庭等人的佛道题材赋作。五代画坛兴旺,名家辈出,山水、花鸟、人物并兴,绘画理论如荆浩《画山水赋》等也应运而生。五代音乐繁盛,“满城笙歌事胜游”(南唐李中《都下寒食夜作》)、“千家罗绮管弦鸣”(闽詹敦仕《余迁泉山志留侯招游郡圃作此》)的盛况折射于赋,则有张曙《击瓯赋》、徐寅《歌赋》、刘骘《善歌如贯珠赋》等作品问世。五代野史小说蓬勃发展,也与辞赋创作产生互动。其题材选择、叙述方式、形象刻画与环境描写手法等,均可见小说化、史论化的痕迹。以史事、寓言、神话、传奇入赋者,如徐寅《员半千说三阵赋》《口不言钱赋》《文王葬枯骨赋》《寒赋》《鲛人室赋》《斩蛇剑赋》等,均于礼乐刑政等传统正典外搜求题材。历史、神话、传说、寓言之类本属故事的题材,写入律赋中仍保有曲折完整的情节,而人称视角的转换、人物问对的虚构、俗语时言的运用等,也使律赋叙事有了长足的进步。
[1]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C].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2.
[3]许总.论五代诗[J].学术论坛,1994(6).
[4]杨荫深.五代文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5]李调元.赋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薛居正,等.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7]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浦铣.历代赋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9]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2]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4]陆游.陆氏南唐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5]王钦若,杨亿,等.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88.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2016-12-1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ZH055);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YBA116)
刘伟生(1970-),男,湖南涟源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辞赋及先唐文学研究。
I207.22
A
1673-1395 (2017)03-005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