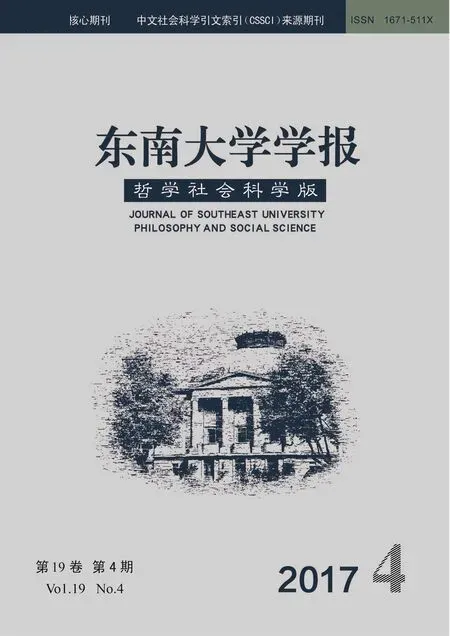人是否可以撒谎?
——从康德的视角看
刘 作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人是否可以撒谎?
——从康德的视角看
刘 作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康德认为,在任何时候人都不可以撒谎。这一观点引发很多批评。在康德那里,法权论涉及对外在行为的立法,不可以撒谎是一个无条件的义务。但是,人可以通过诉诸“事急无法”,即撒谎,来避免更大的恶。德行论是对内在准则的立法,但一些日常看似撒谎之行为是否被禁止,则需进一步反思。考虑到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在未出版的《伦理学讲义》中,他认为人可以撒谎。在当今社会,人们之间的信任出现了危机,不可以撒谎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可见,不可以撒谎是从理性存在者的角度来说的,在特定情况下,为了维护自由,人可以撒谎,但人要清醒地意识到,任何撒谎都不是道德的,只是一种例外而已,否则就会导致伪善。
康德;撒谎;法权;德行;自由;诚信
康德把诚信问题纳入其批判哲学的著作中。在论文《一项哲学中的永久和平条约临近缔结的宣告》中,他强调,我们所说的,不一定都是真实的,但是凡是所说的,都必须是真诚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欺骗。欺骗表现为两种方式:“1.如果人们把自己毕竟意识到非真的东西冒充是真的;2. 如果人们把自己毕竟意识到主观上不确定的某种东西冒充是确定的。说谎(“说谎之父,一切恶都借它来到世上”)是人的本性中真正腐败的污点;哪怕同时真诚的口吻(按照许多中国小商贩的实例,他们在自己的商店上方挂着金字招牌“童叟无欺”)尤其在涉及超感性事物时是惯常的口吻。”[1]429第一种欺骗方式是人把不能认识的对象误认为能够认识的。这就需要我们在认识开始之前,系统地考察我们的认识能力、范围以及界限等。第二种欺骗方式是人在与他人交往中,把自己意识到假的东西传达给别人。前者属于理论哲学的范围,后者属于实践哲学的范围,二者都属于批判哲学的内容。本文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来考察不可以撒谎的义务。
在康德那里,义务体系是在后期著作《道德形而上学》中得到展现的。康德把义务分为两种:法权(Recht,有“权利”与“法”的意思,英译为“right”,本文译为“法权”)义务和德行义务。在这两个部分中,他都谈到不能说谎的义务。另外在1797年的一篇论文《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法权》中,他提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说谎,乃至于对一个站在门口的杀人犯也不能说谎。这篇论文的观点引发学者们的争议。本文试图从这篇论文入手,结合法权义务和德行义务的区分来说明:法权论涉及对外在行为的立法,不可以撒谎是一个无条件的义务,但是,人可以通过“事急无法”,即撒谎,来避免更大的恶;德行论是对内在准则的立法,但一些日常看似撒谎之行为是否被禁止,则需进一步反思。考虑到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在未出版的《伦理学讲义》中,康德认为人可以撒谎,不可以撒谎是从理性存在者的角度来说的;在现实生活中,为了维护自由,人可以撒谎,但是人要清醒地意识到,这不是一种道德的行为,而仅仅是例外而已,否则就会导致伪善。
一、不可以撒谎之自由的根基
法国哲学家邦雅曼·贡斯当在其著作《1787年的法国》中对康德提出批评,康德认定说真话是一个无条件的义务,以至于断言:如果一个凶犯问我们,我们那被其追杀的朋友是否躲在我们家里,对之说谎也是一种犯罪。为了符合日常道德直观,贡斯当提出,义务的概念和法权的概念是相对应的。说真话是一个义务,仅当对方享有听取真话的法权。由于杀人犯不具有这种法权,所以我们应当对杀人犯撒谎。康德在《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法权》一文中做出反驳。他指出,贡斯当的“对真话有一种法权”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表述。人作为具有理性行为能力的存在者,有对真诚或者说主观的真话的法权。康德以人格来表述具有理性行为能力或者说自由属性的存在者。真诚是一个义务。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无法回避用“是”或者“否”来回答,同时,我们是在一种受强迫的场合下来反思真诚的问题。康德认为,真诚是对每个人的形式的义务,不管由此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如果我对杀人犯讲真话,那么我尽到自己的义务,行为的后果不能归责于我。如果我对杀人犯说了假话,告诉他,我的朋友不在我家里,那么我对行为的后果要负责任。康德做出如下论述:“谁说谎,不管他这时心肠多么好,都必须为由此产生的后果负责,甚至是在民事法庭前负责,并为此受到惩罚,不管这些后果多么无法预见,因为真诚是一种必须被视为一切都能够建立在契约之上的义务之基础的义务,哪怕人们只是允许对它有一丁点儿例外,都将使它的法则动摇和失败。”[1]436人具有理性行为之能力,他可以通过其行为开启一个现象的序列,而自己本身不在这个序列里面。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以先验自由来表达这种能力。先验自由处于本体的领域,不具有时间性。人的行为发生在现象领域,受机械的因果规律的决定。人性是目的之根据就在于人是自由的。他可以开启一个行为的序列,而自己不在序列之中。处于这种序列中的任何存在者都是手段。如果我们对这个杀人犯讲了真话,那么我们就听从了理性的声音,履行了理性的义务。此时我们让自己的意志保持在自由的领域,让自由成为自己的本真状态。如果我们从后果的方面来考虑是否应该讲真话,那么,我们让自己处于自然的领域之中,使得自己不自由,由此所发生的后果将由我们负责。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德行论”中,康德再次讨论说谎的问题。按照对象来划分,德行义务分为对自己的义务以及对他人的义务。康德在授课时所使用的是鲍姆嘉通的《哲学伦理学》。鲍姆嘉通把义务分为对上帝的义务、对自我的义务以及对他人的义务。对自我的义务分为对灵魂的义务以及对身体的义务等。康德反对这种划分,因为按照批判哲学的原则,无论从理性推论还是从经验观察,都无法确证灵魂的存在。同时,义务有赋予义务者与承担义务者。按照字面的意思,在对自我的义务中,我既是义务的赋予者,又是义务的承担者。义务的概念包含着强制,对自我的义务概念就是自我对自我的强制。同一个自我既是强制者又是被强制者,这包含一个矛盾。康德接着说,人们以如下的方式澄清(stellen ins Licht)这个矛盾:赋予义务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免除被赋予义务者的义务。义务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可以随时被解除的。这就取消了义务。所以需要区分自我的不同含义。
在康德看来,当我们说对自我的义务时,这里的自我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第一,作为感官的存在者,人作为动物物种之一而存在;第二,作为具有自由的理性存在者的人而存在。“现在人作为理性的自然存在者(现象的人),通过其理性的规定,作为原因在感官世界中行动,而在此尚未考虑责任的概念。但是,同一个人按照其人格性,也就是被思考为一个具有内在自由的存在者(本体的人),被看作一个有能力承担责任的存在者,确切地说,对自身(人格中的人性)的义务,所以人(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能够承认对自身的义务而不陷入自相矛盾(因为人的概念不是在同一个意义上被设想的)。”[2]262-263对自我的义务是对自身的人格性或者说自由的义务,我们有维护和完善自己的自由的义务。自由是人的“天命”,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放弃自己的自由和理性的存在。否则,人与动物就没有区别。
作为一个道德的存在者,不撒谎、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是对自我的义务。康德把撒谎看作对自我的义务的最严重的侵犯。撒谎可以分为外在的撒谎和内在的撒谎。前者是向他人撒谎,后者是自欺和伪善。外在的撒谎来源于内在的撒谎。自欺和伪善是一切恶之源。在理论上,它让我们无法确定理性能力的限度和范围;在实践上,它让我们无法正视自己的道德本性。行为的道德价值在于其行为的准则与法则的一致性。自欺者认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侥幸地没有产生恶的后果,没有丝毫内疚,反而心安理得,误以为自己是一个道德高尚之人。如果这种思维方式成为习惯,那么我们就丧失认识自己和反思自我的精神,无法判断自己的行为准则到底是否与义务的原则相一致。自欺从根本上破坏自己的道德意向,进而向外扩张欺骗他人,违背对他人真诚的义务。
康德在解释不可以撒谎的理由时,强调它不是基于撒谎的后果。我们不能说撒谎会给自己或者他人带来伤害,我们才不应该撒谎,而是因为撒谎本身就是恶的。对他人的撒谎,使得自己成为他人眼中受鄙视的对象;对自己撒谎在更大程度上使得自己成为没有价值的存在者。在《道德形而上学》中,他从两个方面论证我们何以不可以撒谎。第一,自然目的论的证明。撒谎就是放弃其人格性的尊严。人具有传达自己思想的独特能力,这种能力是维护人之社会性的需要。只有在社会中,人才能保持和完善人的理性和自由,所以“通过包含与自己所设想的相反的语词(有意的)传达给他人,是一个与其传达自己思想能力之自然合目的性相反的目的,由此是对其人格性的放弃,并且是人的一个纯粹欺骗性的现象、而不是人本身”[2]278。自然的合目的性是说,每一个存在者都有其特有的功能,完善这种功能就是行为所应当实现的目的。亚里士多德以自然的合目的性原理来论证幸福是基于德性的活动。近代机械论的确立,影响人们批判自然目的论的观点。要注意的是,康德并没有简单地回到古希腊的自然目的论,而是把它放在批判哲学的视域中。自然目的论不是对存在者的一种客观认识的原则,而是反思判断力的主观的调节性的原则。通过反思判断力,自然目的论充当沟通自然与道德的中介,说明自由何以在自然中得到实现。所以,当康德说,撒谎违背人传达思想之能力的自然目的时,他是在强调,撒谎阻碍人的理性和自由的完善和实现[3]。
第二,人性公式的证明。康德把人分为道德的存在者和自然的存在者两部分。在他看来,作为道德的存在者,人不能把作为自然的存在者的人仅仅当做手段来使用,从而把后者只是当做说话的机器,而是受制于思想传达的内在目的。人要承担起真诚的义务。这种义务要求我们与自身的人格性保持一致,真实地传达自己的思想。他举了例子,比如为了避免惩罚或者获得好处,我们向上帝表达自己的信仰,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信仰。因为真正的信仰不是为了获得额外的好处,而是应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
康德没有具体地解释,作为道德存在者的人何以能够欺骗作为自然存在者的人,只是说:“相反,这个人对于与他自称为道德存在者相一致的条件负有责任,并对自己本身承担有诚实的义务。”*康德的原文是:“Der Mensche als moralische Wesen (homo noumenon) kann sich selbst als physisches Wesen (homo phaenomenon), nicht als bloβes Mittel (Sprachmaschine) brauchen, das an den inneren Zweck (der Gedankenmitteilung) nicht gebunden wäre, sondern ist an die Bedingung der übereinstimmung mit der Erklärung (declaratio) des ersteren gebunden und gegen sich seblst zur Wahrhaftigkeit verpflichtet.”[2]279邓晓芒教授译为:“作为道德存在者的人(本体的人),不能把作为自然存在者的自己(现相的人)当作纯然的手段(会说话的机器)来使用,机器是不会对内在的目的(思想的传达)负责的,相反,这个人对于与他自称为道德存在者相一致的条件负有责任,并对自己本身承担有诚实的义务。”感谢邓晓芒教授对这句话的翻译。自由的存在者应该使得自我的自然的存在与自我的道德的存在者是一致的。然而,这个人把它们分开,一方面,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自我的自然的存在仅仅当作实现任意目的的手段来利用,另一方面,宣称自己是道德的。这是一种自欺和伪善。自欺和伪善看似是自由的,实际上是不自由的,从根本上毁坏了自由的根基。因为,自欺者仿佛做出自由的选择,实际上这种选择是自相矛盾的,只是一种例外,无法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
二、作为法权义务的不可以撒谎与作为德行义务的不可以撒谎
不可以撒谎作为法权义务和德行义务都是基于人的人格性,以实现人的自由为目的。但是康德对二者持有不同的态度。在法权的领域,不可以撒谎在任何时候都是必须坚持的,而在德行领域,康德对它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在“决疑论问题”中,康德提出了一些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一位作者问他的读者是否喜欢他的作品,读者不喜欢,但是为了顾及作者的情面,他是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还是应该幽默地隐藏自己的想法呢?这需要他进一步思考。决疑论(Kasuistik)“既不是一门科学,又不是科学的一部分;因为它将是独断论,不是我们如何发现真理的学说,而是如应当需要追寻真理一样的训练”[2]256。也就是说,不能撒谎这个普遍的规则是要遵守的,但是在具体情境中,一些日常看似撒谎的行为是否被禁止,康德留有余地。不可以撒谎是一个无条件的命令,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能否做出类似善意的谎言之行为。联系现实,在一位癌症患者面前,医生是否可以撒谎?我们都认为医生可以善意地撒谎,告诉患者疾病不严重。它一方面有利于患者减轻心理负担,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有益于患者康复。
作为法权义务的不可以撒谎与作为德行义务的不可以撒谎的区分,要结合法权义务和德行义务的关系来理解。依康德的观点,任何立法都有两个方面:客观的法则和主观的动机。由此存在两种立法:伦理的立法和法学的立法。前者是内在的立法,要求行为不仅合乎义务,而且以义务为其动机;后者是外在的立法,行为能够被外在地强制,合乎义务,不一定出于义务。伦理的立法是对外在行为和动机的立法,也就是说,它是对准则的立法。法学的立法是对外在行为的立法,对动机没有强制的要求。
法权义务和德行义务都是以自由概念为基础,分别对应着法学的立法和伦理的立法。由于立法的不同,与之相关的自由概念有区别。法权义务的基础是外在的自由,德行义务的基础是内在的自由。外在的自由要求你的行为与他人的行为能够按照一个普遍的法则共存。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只要我的自由不损害他人的自由就行,即使我很想破坏他人的自由。或者说,即使我很想伤害他人,然而我的外在行为没有阻碍他人的自由,那么我并非不正当的。因而,康德得出普遍的法权原则:“如此外在地行动,使得你的任意的自由运用与每一个人按照一个普遍法则的自由能够共存”[2]35。共存的原文表述是bestehen,其原意是“存在、有”的意思。康德用这个词表达,法权原则要求,你的任意与每一个人的任意按照一个普遍法则都能够存在,而不是相互矛盾。此时,bestehen有“共存的”意思。可以看出,法权的义务所关注的是外在的行为。人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者,不得不与他人交往。在交往的过程中,法权原则要求我们的外在行为不能侵害他人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但是它并不要求我们把这种外在行为本身当作其行为的动机。比如履行合同是一个义务,如果我们只是为了逃避外在的惩罚而履行合同,那么我们就是从法权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义务;如果我们还把它看作自己行为的动机,认为它是我们应当做的,即便没有外在的惩罚,那么我们就是从德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义务。
作为内在的立法,德行义务把行为本身看做我们应当做的。在德行论中,康德提出“同时是义务的目的”的概念。作为理性所赋予的目的,他论证德行义务是实现这些目的的义务。康德的基本意思是,德行义务基于内在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仅是意志的自律,而且是意志的自治(Autokratie)。后者预设人的有限性,即人有违背道德法则的感性欲望。所以内在的自由是属于人的意志的自由,要求人用理性来控制自己的感性欲望。理性如何控制人的感性欲望呢?在康德看来,与动物不同,人的意志具有自发性。感性欲望对人的影响,是通过意志把它当作行为的目的纳入准则来实现的。与之相反,理性要求人把理性所赋予的目的纳入其意志的准则之中,以此消除感性的影响,实现人的内在自由。理性的这些目的就是自我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
由于立法的不同,法权义务是对外在行为的立法,德行义务是对行为的准则的立法,因此,法权论对行为的规定非常精确,而德行论对具体行为之规定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Spielraum)。这就是德行论有“决疑论”的原因。如前所述,这种“决疑论”是为了锻炼我们的实践判断力,搞清楚普遍的道德法则如何运用到具体的情况之中。康德对二者的区分做出明确的表述:法权论“按照其性质应该被严格地(精确地)规定,正如纯粹数学一样,不需要一个判断力应当如何运作的普遍的规定(方法),而是通过事实使之成为真实的。与之相反,伦理学由于其不完全义务所允许的活动空间,不可避免地导致判断力要求去澄清的问题,即在具体情况中,一个准则如何被运用的问题……伦理学陷入决疑论,法权论不知道这种决疑论。”[2]256
理清二者的性质和区别,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康德对不可以撒谎的态度。在论文《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法权》中,康德强调,即使在那个撒谎能够挽救朋友之生命的场合,我们也不可以撒谎,这是从法权的角度来说的。法权论对行为的规定如数学般的精确,在任何场合都不可以撒谎,因为撒谎的行为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基本信任,与每个人按照普遍法则的自由不一致。在德行论的领域,医生在面对患者时,考虑其实际情况,允许善意的撒谎。善意的撒谎不是告诉患者错误的消息,似乎他已经完全康复,能够回复到过去的生活方式,而是用委婉的语气告诉他,身体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治疗,但是有改善甚至康复的希望。此时,医生所选取的不是蓄意的撒谎,而是促进他人幸福的准则。
三、现实中的撒谎与自由的维护
康德真的认为,如果我的撒谎必定能够解救朋友的生命,我依然不可以撒谎吗?在法权领域,我是不是绝对不可以撒谎呢?
在面对门口的杀人犯的例子中,由于情况的复杂性,我的真诚不一定导致对朋友的伤害。康德意识到这个问题:“毕竟有可能的是,在你真诚地用‘是’来回答凶犯他所攻击的人是否在家的问题之后,这个人不被察觉地走出去了,就这样没有落入凶犯的手中,因而行动就不会发生;但是,如果你说谎,说他不在家,而且他确实(尽管你不知道)走出去了,凶犯在他离开时遇到了他,并且对他实施行动,则你有理由作为此人死亡的肇事者而被起诉。因为如果你尽自己所知说真话,则也许凶犯在家中搜寻自己的敌人时会受到路过的邻居们的攻击而行动被阻止。”[1]436即使我告诉凶犯我的朋友在家里,朋友是否被害有多种可能。这些可能性受到一些自然因素的影响,并非由我的行为所直接导致的。我所需要做的就是尽我的义务,履行义务是我的自由的体现。
进一步,如果我的真诚会直接导致朋友的遇害,那我应该怎么办?假设我的朋友带着面具站在我的旁边,无处可走,如果我告诉凶犯我的朋友的位置,那么凶犯一定会找到他,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的真诚与朋友的被害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从法权的角度来说,我应该讲真话,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康德的文本中找到说谎的理由。康德在详细阐述法权的定义之后,在“附录”中,提出“论有歧义的法权”。法权概念是由法则来规定的,然而在特殊的情况之下,人们会想到没有法权规定的广义的法权。有两种这样的法权:公道和紧急法权。前者是没有强制的法权,一个人年终拿到其全部工资,由于货币贬值,其购买力比不上签订合同时的预期,他不能根据自己的法权来要求补偿,只能呼唤公道。后者是没有法权的强制。康德所举的例子是,船沉后,我与另外一个人在同样的危险中漂浮。为了活命,我把那个人从木板上推开。我的行为不属于自卫,所以没有法则认定我这样做是正当的。然而,在危机的情况下,这样的行为是无法惩罚的。在门口凶犯的例子中,如果我的真诚与朋友的被害存在直接关系,那么我可以运用紧急法权,于此来拯救朋友的生命。但是,我依然要清醒地意识到,撒谎的行为是不正当的,此时的撒谎只是一种例外而已。
Korgaard在“说谎的法权:康德对恶的处置”一文中区分伦理学的理想理论与非理想理论。前者基于一个理想的环境,后者是理性的法则在存在恶的环境中的运用。在非理想的环境中,正义的观念无法有效地实现出来,此时“特殊的正义观念变成一个目标,而不是一个不辜负的理想;我们必须努力创造它在其中得以实现的条件”[4]148。不可以撒谎作为一条绝对的命令,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只有在理想的环境中才得以可能。在非理想的环境中,比如在面对凶犯时,我们可以撒谎来拯救朋友的生命,这有助于实现理想的环境(按照康德的术语,目的王国)。在康德的理论中,我们应当以目的王国的成员来要求自己采取道德的行动,对上帝的信仰为我们解决恶的问题提供了希望。因而他没有区分这两种不同的理论,导致他虽然意识到恶的问题的存在,却没有处理好恶的问题[4]154。
Korgaard很深入地看到康德伦理学的问题。人性公式以及目的王国的概念都是在道德形而上学的范围之内的。按照康德的设想,道德形而上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纯粹意志的理念及其原则。所以,人性公式以及目的王国的概念都是从理想的角度来谈的。对上帝的信仰除了解决恶的问题之外,还与至善的可能性有关,涉及自然法则与自由法则之协调一致的问题,本文不做详细探讨。需要强调的是,康德也意识到恶的问题。在赫尔德的听课笔记中,康德认为:“如果我们的不真诚与我们的意图是一致的,那么它是恶;但是如果只能通过这种手段来扭转一个大的恶,那么……[5]27我们可以猜测省略号所省略的内容,即在此种情况下撒谎是允许的”*罗尔斯的看法有助于我们理解康德的观点。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提到:“对平等自由的否定能够得到辩护,仅当它是提高文明的水平,使得这些自由在一定阶段上能够被享有。”见参考文献[6]第152页。在罗尔斯看来,为了更大的自由,我们才可以限制自由。。在1784—1785年的《伦理学讲义》中,康德在谈到对他人真诚的义务时反思,我们对一个骗子撒谎,我们也是一个骗子吗?“如果他人欺骗了我,我反过来骗他,我肯定没有做错什么;既然他欺骗了我,他不能抱怨它,然而我还是一个骗子,因为我的行为违背了人性的法权。”[5]203他人欺骗我,把我仅仅当做其手段,处于实现其目的的链条的一个环节;我也欺骗他,把他人仅仅当做手段,把其置于保护我自己的链条的一个环节。他无法抱怨我的欺骗,因为我没有伤害他。但是,我的行为违背了人性的法权,我的欺骗行为如果普遍化,那么使得人们相互交往成为不可能。
综上所述,法权论是对外在行为的立法,不可以撒谎在任何时候都是人必须遵守的,然而在特殊情况下,人可以通过“事急无法”,即撒谎,来避免更大的恶。德行论是对行为准则的立法,撒谎之行为是否被完全禁止,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康德也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性。在其《伦理学讲义》中,他明确地提到,在特殊情况下,人可以撒谎。理解他的看似不一致的观点在于,义务的基础是自由,也是为了维护和完善人的自由。撒谎只能是为了维护更大的自由。当我们不得不撒谎时,我们要记住,这不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或者现实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自由本身。
在当今的社会,人们之间的信任出现了危机。从康德的角度来看,这种环境存在恶,不是理想的环境。所以,不可以撒谎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为了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权利,在适当的场合撒谎是允许的。然而,我们应该记住,即使撒谎避免了更大的恶,撒谎这种行为也是错误的,只是一种例外而已。我们不能自欺地把这种例外看作是道德的,让撒谎肆意横行,从而自我贬低。营造一种合理、公正的社会秩序,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在这样的理想的秩序中,不可以撒谎才可以成为无条件的现实的义务。
[1] 康德. 康德著作全集(八)[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 Kant. 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M]. Hambugr: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in Hambugr,1966.
[3] 刘作.康德道义论之自然目的论审视[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
[4] Korgaard C. Creating the Kingdom of End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5] Kant. Lectures on eth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6] Rawls J. A theory of justice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许丽玉)
2017-02-06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康德后期伦理学研究”(15CZX049)、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康德后期道德哲学研究”(14MLC005)以及2011计划“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成果”阶段性成果。
刘作(1983—),男,湖北仙桃人,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与科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哲学。
B82-067;B516.31
A
1671-511X(2017)04-003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