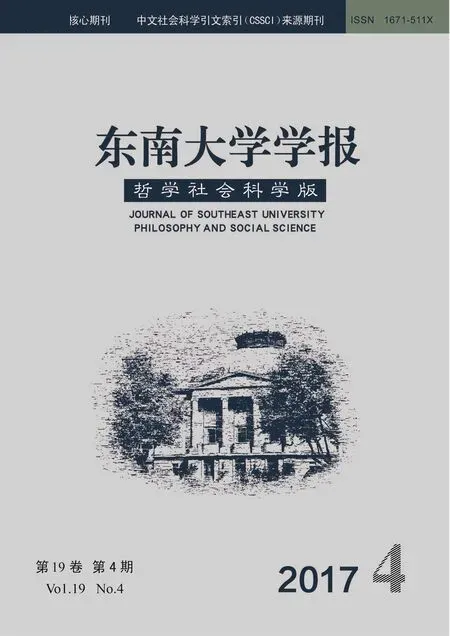法治秩序持续再生产何以可能:基于伦理精神维度
高兆明,肖迎春
(1上饶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1;南京师范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7;2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巢湖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巢湖 238000)
法治秩序持续再生产何以可能:基于伦理精神维度
高兆明1,肖迎春2
(1上饶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1;南京师范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7;2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巢湖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巢湖 238000)
法治秩序持续再生产何以可能?从伦理精神维度反思,宪法法律制度未必能使法治秩序持续再生产,除非它伴生一种伦理文化传统,此种伦理文化传统有牢固的宪法法治信念,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具有普遍承认、契约法治与公共政治参与的公民精神。
法治秩序;法治秩序持续再生产;伦理精神;公民精神;契约法制精神
美国新总统特朗普针对7国人员的入境行政令,刚签发没几天就被联邦法院暂停,尽管他心中气恼,但也只是发发牢骚后说法庭见。特朗普上台被称之为“黑天鹅事件”,特立独行的特朗普上台后又似乎不按常理出牌。有人据此认为西方民主制度遇到了重大危机。无论此种判断是否正确合理,它至少以一种特殊方式揭示:西方法治秩序正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特朗普现象为我们进一步观察思考民主制度与法治秩序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窗口。
本文所要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伦理精神才能与法治秩序相匹配,使法治秩序持续再生产成为可能?具体言之,一种罗尔斯意义上的长治久安政治共同体是否需要有某种伦理精神为前提?何种伦理精神既能使既有法治秩序富有生命力,又能给那些正在为建立起法治秩序而努力的实践活动提供精神动力与价值支持?本文的思考有两个前提:其一,已经建立起较为健全、成熟的宪法法律制度体系;其二,坚持法治的方向。本文所说的“法治秩序”与“人治秩序”相对立,与“宪法法律秩序”同义。它指称这样一种社会秩序:社会建立起宪法法律体系,且通过宪法法律确立了社会基本结构体系及其权力运行规则,所有社会成员与政治集团都受宪法法律的有效约束。“法治秩序”既是社会基本结构框架体系,又是社会基本行为规则体系。如果宪法法律秩序能够体现宪法法律的根本立法精神,保持稳定的社会政治活动基本框架体系及其运行规则,且社会各利益群体在此基本框架、规则内能够持续性地再生产合作性交往关系,则为“法治秩序的持续再生产”。本文所说“伦理精神”则指社会共同体的文化传统,此文化传统既是人们的普遍信念,又是社会共同体的核心价值,人们据此“伦理精神”观察、理解、评价社会是非善恶、正义与否,并规范日常生活。
一、问题的提出:制度是否可靠?
一个社会政治权力要能被有效约束,当然首先是要建立起制度“铁笼子”,然而,有了“铁笼子”,是否一定能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笼子”是否牢靠?即使现在牢靠,是否会因经年日久而渐渐变得不牢靠?①当如此说时隐含一前提性判断:权力这巨兽不会乖乖地蹲在笼子里,相反,只要一有可能,它就会打碎笼子跳将而出。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如何使此“铁笼子”牢固而有效? 如何捍卫制度?
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均有两种背景性框架,一种是如同罗尔斯所说的背景性制度框架,另一种是如同泰勒所说的背景性价值框架[1]。正是此两种背景性框架构成了社会共同体的两种基本规范。如果说作为背景性制度框架的是宪法法制体系,作为背景性价值框架的则是社会核心伦理文化价值精神,那么,此两种框架关系如何?是否需要彼此耦合?如果彼此不能耦合,此两种背景性框架各自是否还能屹立?罗尔斯在思考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可能时,将“公平正义”视为制度的首要美德,并提出了正义两原则。罗尔斯的正义两原则中隐含一前提:作为原初状态中的公民代表有内在规定性,这就是正义感与善观念的能力*“正义感即是理解、运用和践行代表社会公平合作项目之特征的公共正义观念的能力。善观念的能力乃是形成、修正和合理追求一种人的合理利益或善观念的能力。”参见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2]17。。这意味着,正是公民代表的正义感与善观念所蕴含着的社会伦理文化价值精神,不仅使公平正义的法治制度本身成为可能,而且还滋润着法治制度,使之生生不息。
人们对宪法法治制度寄以无限期待。这当然合理。不过,不能将制度神化,不能无视制度得以发挥作用及其持续再生产的社会伦理文化精神前提。“制度的历史常常是骗人和虚幻的历史;因为制度的作用取决于产生制度的观念和维持制度的精神”[3]4。也许阿克顿的这一说法有点极端,但却不能不承认其深刻。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是将宪法法治制度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形式的制度体系,而是理解为具有内在精神的一种生命体,那么,宪法法治制度就应是自由精神的“定在”(黑格尔),它不仅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有赖于人们基于自由精神的实践,而且还是一个开放性生长过程。另一方面,根据彻底的辩证法,任何事物均有可能经过诸多中介环节走向自己的对立面——正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早就以自己的方式所揭示的那样。因而,不可简单地以为只要建立起宪法法治制度就必定有永久的法治秩序。即便是好的制度,其持存仍然是有条件的,社会伦理精神即为关键:一方面,社会文化传统是否秉持法治精神;另一方面,人们是否自觉捍卫法治秩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社会伦理精神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人们如何理解制度、对制度有何种期待,制度就可能会是怎样的。如果没有对宪法法治有坚定信念、自觉捍卫宪法法治的人们,再好的宪法法治制度亦有可能经过复杂过程而蜕变。制度未必完全可靠,除非制度成为人民笃信的价值精神与心灵习性[4]。
确实,制度本身具有稳定性,一旦建立起成熟健全的宪法法治制度及其运行机制,通常便会沿着既有逻辑运行。然而,制度是生长着的。如果出现重大社会事件,如果有政治强人试图改变既有制度及其运行机制,那么,既有制度是否会经受得住“冲撞”?制度本身离不开人们为公平正义秩序的政治努力。这是因为:第一,制度是人的制度,离开了人及其经验性活动,就无所谓制度。第二,公平正义的制度不能自然来到。公平正义的制度是人们追求公平正义生活秩序的结果。第三,即使建立起法治秩序,有了基本公平正义的制度,此制度仍然有生长性与内在生命活力问题。一方面,再好的制度安排如果不能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另一方面,即便是好的制度体制,也需要人民的积极政治参与。离开了人民的权利意识、理性精神,离开了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自觉政治参与及对政治强人的积极监督,即便是建立起且有着成功记录的民主政治制度体系,仍然有可能崩塌。不能无视20世纪初德国的历史教训。为什么已经建立起民主制度的魏玛共和国依然产生了希特勒?这始终是当今人类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之一。
回到关于特朗普的特立独行与宪法法律限制问题,即为:包括掌有行政大权的总统在内的每一个人是否敬畏宪法法律,是否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行动?社会所有成员、群体的基本权利是否以及如何获得平衡?一个基本成熟的法治秩序需要何种社会伦理精神的滋养才能具有持续再生产的内在生命力?
二、普遍承认:承认与为承认而斗争
霍耐特在通过“承认”理论反思当代社会时,曾提出并思考过合作性社会关系持续再生产问题,并提出了“病态社会”概念。霍耐特认为:一个不能持续再生产合作性社会关系的社会是“病态社会”,“病态社会”的病因是“病态自由”、“病态权利”。他主张通过“社会自由”来克服社会“病态”[5]138-139,202-203。霍耐特的本意当然不是说自由、权利本身不再是我们的价值追求,而是要追问:我们究竟当如何理解自由、权利,自由、权利在何种意义上才是真实的。自由并非自明地成为行动的充分理由。是一个人、部分人的自由,还是所有人的自由,是纯粹自己的自由,还是包括他者的所有人的社会自由,是否“普遍承认”,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问题。
人类可能永远摆脱不了“为承认而斗争”,区别只在于争取“承认”的具体内容与为之“斗争”的具体方式。每个时代、每个人都有“承认”与“为承认而斗争”的问题。人类的历史似乎很长,但历史类型就是那么有限几种:一个人的自由、少数人的自由与所有人的自由[6]18-19。一个人、少数人的自由,只不过是要其他所有人承认其权威、服从其支配或统治。黑格尔在讲到人格、人格权时曾说过:世间最高贵的事莫过于“成为一个人”,并将“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视为法的命令[7]46。黑格尔此思想的核心是“普遍承认”。如果不是在“普遍承认”的意义上“为承认而斗争”,就没有彻底摆脱主奴辩证法的困扰。一个社会共同体只有确立起“普遍承认”的文化传统,才真的有可能长治久安。
在其现实性上,“承认”绝非仅仅是个体的,而是伦理实体的。任何个体的自由权利总是具体的、历史的,总是先在地受其所属伦理实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所规定。“伦理”生活中的“权利”或“法权”有两个不同层次的意蕴:实存性法权(existent right)与关系性法权(relative right)。具体法权制度是实存性法权,个体同此制度的关系则为关系性法权——正是此制度能具体实现某一个体的自由权利。任何自由权利都只有通过具体制度才能获得具体规定与落实。与此相应,任何人格、主体、自我等概念均在伦理生活中形成,任何个体、个体人格与身份意识均具有深刻社会历史内容[8]121-122,323。道德、权利等均是抽象的自我图像,它们只有在伦理生活中才能成为现实并被理解*“伦理生活较抽象法权与道德之所以更具体,不是因为它强调集体优先于个体,而是因为个体的伦理图像更具体。它指向个体自我的各个方面,将自我置于活的社会秩序中。”参见文献[8]第41页。。
西普在历史学—人类学语境中理解“承认”的思想,正是坚持了“承认”或自由、权利的具体历史性。西普认为“承认”包含尊重、非歧视、宽容、团结、友谊等五个方面的基本内容。[9]西普的“承认”思想有两个鲜明特点:其一,坚持由抽象承认到具体承认。他认为我们不应将“人权”、“社会正义”等视为僵死的抽象概念,而应将其理解为历史发展的结果。一切关于人权、社会正义等概念均形成于“令人痛苦的共同经验和不稳定的学习过程”。即,任何关于自由、权利的具体规定,均离不开人的社会组织及其具体生活形式;任何对于人权内容的具体理解过程,均是人“在组织和生活形式中找到自己的家”的过程。在当今,由于人权与公正等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关于人权的规范性共识可通过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的方式加以揭示[9]。其二,坚持从组织与个体双重维度理解“承认”。个体间的“承认”当然重要,因为没有个体间的“承认”,就不可能有组织与社会制度的“承认”。但是,个体间的“承认”还只是私人领域、偶然的,不具有公共性与客观性。如果单纯从私人间的关系来理解“承认”,即便是“尊重”,也不会具有普遍性效力,因为它终究会受个人偏好的影响。只有成为社会组织的“承认”,才具有普遍效力,具有客观性。西普关于“承认”有丰富内在构成及其层次性、坚持从组织与个体双重维度理解“承认”、视“承认”内在性地具有“爱”等思想,极富启迪性。然而,其关于“承认”的理解多少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福山曾揭示,人们为“寻求承认的斗争”会产生两种意识:与他人平等的平等意识,以及比他人优越的优越意识[10]197。这意味着:“承认”、“为承认而斗争”内在地包含着“平等”与“不平等”或“平等”与“自由”的张力。如何使此张力保持在合理限度之内,使“承认”成为社会法治秩序可持续再生产的内在动力机制?
西普、霍耐特等努力地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寻求某种统一:既坚守最基本的人权底线,为个人自由权利做强辩护,又坚持在社会共同体中理解自由权利,对个人自由做某种限制;既坚持基本价值底线,又具有程序规范性;既坚持个人自由权利的神圣价值,又在规范性意义上坚持普遍自由及其实现。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揭示:一个持续再生产合作性社会关系的社会,必定同时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一个社会共同体,如果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此等伦理精神,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在保持基本秩序基础上,通过对话、博弈找到新的平衡点,进而实现合作性社会关系秩序的持续再生产。
说到“组织承认”、“社会承认”,必然涉及“制度承认”。不过,首先必须注意,此处的“组织承认”、“社会承认”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那种组织、社会对个体承认意义上的,而是诸组织、社会间彼此承认意义上的,因而,至少在此处它们与“制度承认”不属同一个大的范畴。此处的“制度承认”有两个基本方面:其一,以制度性安排的方式对社会不同成员、组织权利的承认。这是个体、组织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的制度性安排,是制度对个体、组织的承认。其二,制度以强力的方式保证社会成员、组织间的承认。任何个人、组织的基本权利受到伤害,都能从制度那里得到有效保护与救济。这种“制度承认”是普遍承认伦理文化的客观化存在。当我们在关注“普遍承认”、“法治秩序可持续再生产”的意义上关注“制度承认”时,我们就会自然地将思想关注焦点指向:什么样的制度更易使生活在此制度中的人们承认“他者”?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使人们彼此“普遍承认”?或者换言之,生活在什么样的制度伦理文化之中才更有益于人们彼此间的“普遍承认”?对此问题的回答,似乎暂时还无法从根本上超出罗尔斯关于政治正义两原则的基本思想。如果事实上存在着某种身份人格差别、明显的机会不平等,如果社会阶层固化,如果社会底层弱者正当权利得不到应有关照,缺少有尊严生活的基本条件,那么,在此撕裂的社会中就很难有“普遍承认”。此种“制度承认”安排所显现的社会伦理精神,不仅会在不同群体间滋生相应的优越或自卑意识,而且还会滋生出怨恨与敌视。一个弥漫怨恨与敌视情绪的社会,不会有“普遍承认”的社会伦理文化价值精神,也很难想象法治秩序的可持续再生产。
现代宪法法治制度的“承认”是“普遍承认”。“普遍承认”的伦理文化承认每一成员、群体的平等自由权利,承认每个人、群体基于平等自由权利守护宪法法律制度铁笼的神圣权利。此神圣权利任何人都不能伤害。
三、公民精神:契约法治精神与政治参与精神
如前所述,即使是建立起宪法法治秩序的社会,仍然会有自由、权利问题,仍然会有“为承认而斗争”问题。只不过此种“斗争”不再是野蛮的,而是文明的。它会以文明规范性方式呈现,且因其文明而成为柔性的“为承认而商谈”:为自由权利而“斗争”的活动永不消逝,不过,它如哈贝马斯所揭示的那样,通过理性“商谈”、“对话”进行。理性“商谈”、“对话”的伦理文化,既能有效巩固社会的规则意识,又可以在全社会建立起一道防火墙,有效隔离暴戾、暴力、暴政。
宪法法治秩序中公民之间的对话、商谈及其妥协共识过程,既以彼此“承认”为前提,又是彼此“承认”的历史实践过程。没有彼此“承认”,就没有基于理性与契约理念的现代民主政治。宪法法治秩序中仍然会有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冲突,但是,这一切均有限度与法度,主体自觉处于此法度内并受此法度限制。
对话、商谈意味着彼此有共识“规则”,以及基于“规则”的倾听、理解、契约、守信等。近代契约论之所以在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就在于它表达了对人的存在方式、未来社会国家的一种全新理解:要走出野蛮丛林状态成为文明的社会国家,就应当建立在对话、商谈、契约的基础之上,唯此,社会、国家才会是自由的、人民的,国家权力才能获得正当性与合法性。契约论确实如黑格尔所说并不能合理解释历史上作为个体的公民与国家关系现象。但是,契约论却以极为简洁的方式揭示:现代国家不同于传统国家,它是文明的产物,在这里通行的不是野蛮的丛林法则,而是理性的文明规则;在现代国家中,每个人具有平等法权,是人格平等的“自由”主体——此“自由”含义非常清晰,是政治意义上的,是如哈耶克所说相对于“奴役”而言的“自由”,即人不再是生来就被区分为“奴役”与“被奴役”、“高贵”与“卑贱”的。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虽然曾明确反对以契约论理解国家,但是却通过“市民社会”环节充分肯定契约的形式普遍性。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有“特殊性”与“普遍性形式”两个原则[7]197。“特殊性”原则指个体“特殊的人”,“普遍性形式”原则指契约交换、平等互惠的普遍性规则。利己的个人通过契约交换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的。不仅如此,黑格尔还以自己的方式揭示:私人间契约具有偶然性,只有在宪法法治的国家制度中,私人契约才能摆脱偶然成为必然。黑格尔以思辨方式揭示:现代社会共同体不可或缺契约及其形式普遍性规则;人们在“市民社会”中养成契约与普遍规则意识,普遍契约与规则意识为现代宪法法治社会奠定基础。
哈贝马斯之所以提出“商谈”、“对话”理论,并试图在“规范”与“事实”之间寻求统一或平衡,就是要在民主法治的基本框架中平衡多元社会中的多元利益关系。“商谈”、“对话”当然有一系列“语言”、“语法”前提,是否愿意遵守“语法”法则、是否能在具体语境中准确理解他者的“语言”,这本身就是一开放性问题。在此意义上,哈贝马斯的“商谈”、“对话”不免带有理想化色彩。但是,哈贝马斯孜孜不倦追求的那种“商谈”、“对话”伦理文化精神,却是社会宪法法治秩序持续再生产不可或缺的。多元社会有矛盾与利益冲突乃属正常,只要彼此愿意在既有规则基础之上通过对话、商谈的方式(而不是暴力的方式)沟通、妥协,这个社会总是会保持生机与秩序的。当然,政客们可能会言不由衷、逢场作戏、阳奉阴违。但是,只要在宪法法治秩序中,只要多元社会本身还存在,只要这种商谈、对话、契约文化仍然是社会的主流文化,那么,政客们总会面对对公民的承诺及信守问题。宪法法治秩序中的“对话”、“商谈”伦理文化,维系着宪法法治秩序的持续再生产。宪法法治秩序的再生产、 “对话”与 “商谈”等,不是少数政客与精英的专利,而是所有公民的神圣权利与政治责任。这需要公民的积极政治参与精神。
一个自由的社会必定是有“道德”(个体自由意志)的社会,必定有社会成员的自觉道德批判。许多人习惯认为黑格尔反对诉诸“主观道德情感”反抗制度,没有给个体基于道德反抗社会制度留下任何空间[8]122-123。其实,此看法不合黑格尔本意。确实,黑格尔反对任何主观任性,反对基于所谓良知的任意,他要从“伦理”处为良知获得真实规定。这正是他从“道德”进入“伦理”的缘由之一。然而,黑格尔的“伦理”之所以能使“道德”成为真实的,不仅是因为“伦理”使“道德”获得了具体规定,而且还因为只有在伦理生活中,道德主观自由精神才摆脱了抽象性而成为活生生的。在活生生的伦理生活中,主体一方面从丰富的伦理关系中获得道德(义务)的具体规定性,履行那具体关系中的具体义务;另一方面主体的自由精神能够出于良知批判不合理现实,自觉为自由而斗争。黑格尔的“道德”良知拥有自由灵魂,善在心中,不屈服于外在强权与权威,独立审视现实生活——否则,其“道德”就不能作为“伦理”的内在环节存在。
法治秩序不会一劳永逸。如果法治秩序不能得到源头活水的持续滋养,就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此源头活水有两个重要分支:其一,普通民众基本权利、尊严、安居乐业等客观生活状况。民众会从日常经验生活中感受到自己是否有尊严、尊重、自尊,并以此判断自己所处其中的这个日常生活政治秩序的状况。只有民众尊严、尊重、自尊价值得到维护的社会秩序,才有可能持续再生产。其二,民众尤其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主观精神态度:是否有主体性精神,是否对一切反人道、反法治、反民主的行为持事不关己的态度。如果一个政治共同体能够尊重与保护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且生活在此共同体中的人民以积极的态度自觉反抗一切反人道、反法治、反民主行为,那么,此政治共同体的伦理文化必定光明而富有生机,并滋养法治秩序演进。
今天思考“法治秩序可持续再生产”问题,欧洲思想史上有两个内容值得特别注意。其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诸政体的论述;其二,阿伦特关于“平庸的恶”的思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诸政体分析时,洞悉并揭示了民主政体的局限性以及民主政体演变为专制政体的内在通道。人民的权利应当被尊重与维护。尽管人民往往可以隐忍诸多不公平,似乎是待宰的羔羊,然而,人民的权利总是需要被表达与尊重的。当人民忍无可忍时就会站出*与此伴生的往往是民粹主义乃至暴民运动。。特朗普当选既不是民主的胜利,也不是民主的失败,而是民主的呈现,是那些被忽略的普通民众权利的一种表达。特朗普的“任性”与被“关”进“笼子”,不是民主的堕落与混乱,而是民主自身的实践。有人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普通民众政治参与意愿低下是民主政治内在活力减弱的象征。此种认识有合理之处。不过,如果换个角度,也许会发现某种更有意思、更具积极性的理解。在宪法法治的民主制度中,普通民众大体上是现实主义者,如果能够安居乐业,他们总是倾向于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专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此意义上,较低的投票率,较少的公共政治参与热情,也许是民众安居乐业的显现——当然,做出此种判断时需要排除基于恐惧的逃避政治参与倾向。一旦普通民众能为某些极端异见吸引并被煽动起公共政治参与热情,至少表明普通民众的一种愿望:期待改变,希望被尊重、有尊严感。
阿伦特在反思德国纳粹现象时曾提出“平庸的恶”概念。阿伦特提出“平庸的恶”是要杜绝个人以制度体制为借口逃避责任的通道,是要唤醒每一个人的公共政治参与热情与主体的伦理生活态度。然而,这里必须直面几个重要问题:其一,如果人们生活在一个警察国家,处于恐惧之中,是否还会有勇气与能力积极参与公共政治生活。其二,权力体系中的精英分子成员是否有良知与勇气,不成为纯粹的工具,不堕入仅仅机械服从的“平庸的恶”——恰如特朗普内阁中的那位代理司法部长,以辞职的方式拒绝接受特朗普的相关指令。其三,根据常识,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大脑与良知,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是否有勇气自由思想,勇敢地发出批判声音。我们不能苛求社会所有成员均具有独立反思批判意识,但是,却无法否认社会精英知识分子有无法推卸的社会责任。如果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不能自觉承担起自己的这一社会责任,就会失却自身存在的价值。正是在此意义上,一个社会中有知识分子的批判声音,恰恰表明社会自身的生命活力。
四、结 论
如果有相应伦理文化传统的滋养,法治秩序的持续再生产是可能的。此种伦理文化传统是政治共同体的生命本体,它作为社会文化基因深入人民骨髓,人民愿意竭尽全力捍卫它。黑格尔曾将“爱国”精神理解为人的一种“自然情感”,所表达的正是这种伦理文化传统的生命本体意义。这种伦理文化传统不可或缺的要素有:
1.宪法法治权威。政治文明最终是要建立起一套宪法法律制度及其运作机制。人类历史迄今为止只有两种基本生活法则类型:丛林野蛮法则与文明法则。与此相应,人类迄今为止的制度、文化也只有两类:文明的与野蛮的。丛林法则是弱肉强食、强权暴政,文明法则是宪法法治,有理性规则与底线。文明社会不是没有强权与竞争,而是所有竞争都被置于宪法法律规则之下,所有竞争者都服从规则的规范,不再是以力霸天下,而是以法行天下;文明社会不是没有强权与暴力,而是强权者也尊重并服从宪法法律确立的基本行为法则,有所节制,有底线,即便强权者对既有行为法则不满,也会在既有宪法法律框架内通过既有规则改变规则。
2.人民尤其是精英分子对宪法法律的敬畏与服从。社会精英应有坚守法治、追求正义、服务人民的情怀。这不仅是当今文明社会人格类型对精英分子的基本要求,也是法治文化的内在规定——尽管人民对精英是否有此情怀总是持有怀疑,尽管权贵精英分子似乎不那么值得信任,人民总要睁大眼睛盯着他们,尽管王者不会自愿呆在“笼子”里,有权力者总是存在专权的倾向。宪法法律只有人民尤其是精英敬畏它、维护它,它才真正存在,否则,只是一纸空文。一个社会有能力蹂躏宪法法律的,不是人民或平民,而是权贵精英。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权贵精英分子不能坚守与服从宪法法律,宪法法律则无所谓权威。只有权贵精英们敬畏与坚守它,人民才能普遍敬畏与服从宪法法律。权贵精英们捍卫并服从宪法法律的约束,既为人民服从宪法法律垂范,又使人民的公共政治参与以规范化的方式展开。借用公牛闯进瓷器店的比方,如果法治秩序不是瓷器店,如果人民不是那些毫不设防的花瓶摆设,如果权贵精英不是发疯的公牛,法治秩序就可能持续再生产。
3.基于平等人格尊严的“普遍承认”、契约法治精神。文明社会仍然有“承认”与“为承认而斗争”问题,但是,这不是“特殊承认”,而是“普遍承认”;文明社会仍然有权利冲突,但是,这是建立在平等基本自由权利基础之上的“家族内部矛盾”,且此矛盾可依据宪法法律规则,通过对话、商谈、契约的方式解决;文明社会仍然有精英与平民大众之分,仍然有精英对社会日常生活的主导,然而,一方面,平民与精英人格尊严平等,另一方面,不仅精英敬畏并遵从宪法法律,平民亦会以积极政治参与的方式遵从并捍卫宪法法律。
4.基于理性与良知在宪法法律框架内积极政治参与的公民精神。人民基于理性与良知的积极政治参与,不仅是自身自由权利的表达,更重要的是可以抗衡权贵精英的政治专权可能,促使权贵精英们遵从宪法法律权威,使一切政治活动保持在宪法法律框架中。如果缺失人民基于理性与良知的积极政治参与,不仅宪法法律有可能沦为权贵精英的玩偶,而且还有可能在社会形成普遍“平庸的恶”现象。如果人民公共政治参与的合法正当表达渠道被堵塞,如果缺失权贵精英对宪法法律的敬畏与服从,那么在此双重因素作用下,人民的积极政治参与结果很可能是暴力革命或暴民运动。
[1] 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等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 阿克顿.自由的历史[M].王天成,等 译.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4] 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5] 霍耐特.自由的权利[M].王旭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6] 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 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7]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等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8] 伍德.黑格尔的伦理思想[M].黄涛 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
[9] Siep Ludwig. Aktualitaet und Grenzen der praktischen Philosophie Hegels[M].Mue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2010, S. 292-295.
[10] 福山.历史的终结[M].陈高华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 许丽玉)
2017-02-06
高兆明,男,哲学博士,上饶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伦理学基本原理及应用。
B82-051
A
1671-511X(2017)04-00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