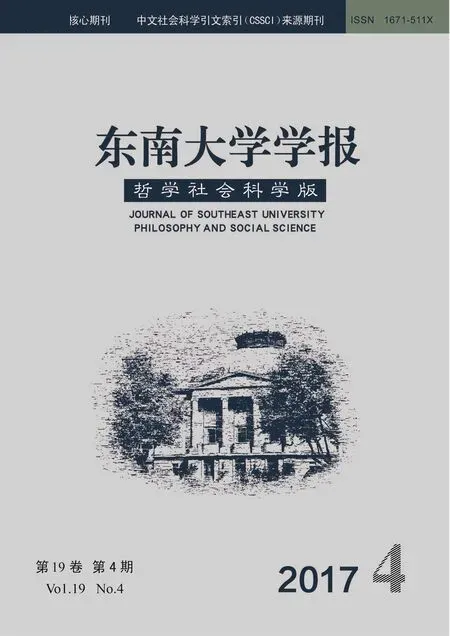明代江南质库经营与艺术品典当
——以浙江嘉兴府为中心
冯志洁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明代江南质库经营与艺术品典当
——以浙江嘉兴府为中心
冯志洁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明代江南质库经营,是一个逐步介入当地稻米、丝织业生产的过程。质库渗透到当地各项生产经营领域之中,成为一个可以获取暴利的行业。与此同时,典当艺术品的行为越来越普遍,作为抵押物的艺术品成为质库经营者接触收藏的重要渠道,并使其投资更加多元化。
江南;嘉兴;质库;艺术品;项元汴
质库是中国古代一种复杂的金融机构,主要经营典当、贷款业务,兼及存款、钱票发行等其他事项,涉猎广泛。关于我国典当业的发展历史,民国时期已有学者关注[1]。20世纪70年代,罗炳绵先生的论文《清代以来典当业的管制与其衰落》及《近代中国典当业的社会意义及其类别和税捐》对清代以来典当业的演变做了探讨[2-3]。后文考察了典当业对于调剂农村及城市下层社会金融的重要意义,梳理典当质押的区别与地域性划分,并指出典税与社会公益事业、国家军饷之间的直接关系。20世纪90年代,典当史研究专著《中国典当史》[4]出版,书中考察了中国典当业发展源流、典当行事与典当文化,并对典当与佛教文化、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社会风尚等关系进行多视角研究,其对古代文学作品材料的运用丰富了典当史研究的资料。此后,刘秋根先生对中国古代典当业做了更为全面的论述。《中国典当制度史》一书从中国古代典当业的起源、名称和分类谈起,之后讨论了典当业的资本组织、业务分类、营业制度、利率、税捐等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由此总结了典当业在古代经济史上的作用[5]。而《明清高利贷资本》一书在延续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更细致地分析了高利贷资本在明清时期农村和城市的不同地位和发展情况[6]。近二十年,以区域典当业发展史和典当经营者为主体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对于典当业经营与区域社会经济的有机联系,以及一些特殊的典当行为,论者甚少。有鉴于此,本文旨在具体分析典当业在一个地方的经营运作方式以及艺术品质押这一特殊的典当行为。
明代江南日益繁荣的市镇经济、逐步完善的市场体系,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质库作为早期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长迅速。典当借贷行为在江南丝织业生产中普遍存在。在蚕桑重地浙江嘉兴府,质库的运作与当地的稻米、丝织业休戚相关,同时还得益于赋役折银后白银作为货币被国家接受。商业的发达使得生意人有强烈的资金需求,向质库抵押典当是一种不容忽视的融资方式,资本市场的活跃带动了质库的兴盛。可以说,质库已逐步渗透到当地各项生产经营领域之中,成为一个可以获取暴利的行业。其中,艺术品典当这一特殊的质押行为,让部分质库经营者完成了向收藏者的身份转变,具有经济和文化上的双重意义。
一、嘉兴质库的经营
“质库”这一行业在嘉兴的经营运转,离不开当地稻米种植与蚕桑丝织业的发展。明中叶以后,蚕桑丝织业已成为江南地区的支柱产业,市镇商业活动大多围绕其展开。嘉兴是当时全国最主要的蚕桑产区之一。万历年间,文人李日华在夜晚乘船路过嘉兴府下属的崇德县时遇到的情境是“两涯比户皆缫丝声”[7]20。此处的农户几乎家家以养蚕缫丝为生。
为何种桑养蚕会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计方式?顾炎武曾引用《崇德志》记载给出解释:
崇邑田地相埓,故田收仅足支民间八个月之食,其余月类易米以供,公私仰给惟蚕息是赖,故蚕务最重。凡借贷契券必期蚕毕相偿。即冬间官赋起征数多,不敢卖米以输,恐日后米价腾踊耳。大率以米从当铺中质银,候蚕毕加息取赎。然当铺中持衡搭包,轻重其间,庾囷狼籍,一出一入,子钱外不止耗去加一矣。以故民间输纳,利蚕毕,不利田熟也。前征追此之难,有由然矣[8]46。
崇德县地稀人稠,可耕地有限且收益低,农户光凭稻米种植无法满足基本生活所需。蚕桑丝织业的发展给农户们的经济生活带来了新的转机。崇德县百姓为了缴纳田赋、维持生计,积极从事养蚕、缫丝。在此过程中,存在一个“以米从当铺中质银”的环节。秋冬之际,稻谷丰收,米价较为低廉,如果此时将大米卖出,对于农户来说很不划算,交易得来的收入可能难以养家糊口,但官府征收赋税在即,很多农户选择将大米典当,换银纳赋,等到来年春天蚕事结束,农户再用养蚕得来的收入去当铺赎回大米。正值青黄不接,米价腾升,农户能够获取可观利润。但是,在这一出一进之间,最大的受益人并非农户,而是当铺。当铺收取高额利息,还可能在斤两上做手脚,从中获得了优渥的回报。
此类典当行为在嘉兴一带并非特例,而是渐渐成为一种习俗。万历年间的《秀水县志》中也记载了类似的事:
迩来富商设米典。佃农将上米质银,别以下中者抵租,虽丰岁辄称歉收,迁延逋负。日者苕上奸民,聚党相约,毋得输租巨室。近岁稍息,然亦渐以成风。官司催科甚急,而告租者或置不问。于是,称贷完官而田主病,小民得银耗费,满课为难,其后利归典商。日复一日,逋负益积,而佃丁又病,两者交病,而廪庾焉得不匮,闾阎焉得不贫也。[9]97
这段材料讲述了当地佃农欠租的垢俗:佃农将上等米典当给质库换银,用下等米作为地租交给田主,且时常拖欠。当官府向田主催科时,田主只能借贷以完纳田赋。借贷的对象大多还是质库[10]775。几经折腾,获利的唯有典商。
嘉兴当地流传着一些民谚、诗歌,描写蚕桑业与质库的关系,如《加一钱》:“欲质长生库,奈无襦与袴,只有加一钱,赤手可收成交付。平时往诉吝至厘毫,蚕细如毛已为我豪。人以蚕为命,蚕能令人重,加一虽不廉,恃此庶无恐,但愿蚕花廿四分。新丝入市堆白云,得钱偿子母,人我俱欣欣,稽首蚕王应我闻。”[11]78诗中的“只有加一钱,赤手可收成交付”说明质库已直接借贷给养蚕者蚕桑生产所需资金,待新丝收成之后以高额利息偿还。高额的利息是质库盈利的关键。从买桑养蚕至卖丝不过一个月时间,质库放贷利息已达十分之一,质库的借贷基本上属于高利贷性质。虽然此诗产生时间较晚,却也可以反映质库与蚕桑生产之间的某种关联。
这些文献为今人呈现出嘉兴质库的运作方式,同时勾勒出明代江南典当业与稻米、丝织业之间的联系。稻米种植、养蚕缫丝都有着严格的时节要求,赋役的征收也有固定时间。典当业的出现成为沟通三者的桥梁,弥补了中间资金周转存在的时间差,使得农民的收益可以扩大,当铺经营者则在这一过程中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典当业开始直接介入蚕桑丝织业生产。质库长期以来都是资金融通的主要承担者,也因此获得巨额利润。刘秋根先生在总结宋代以后典当业发展的特点时曾指出:“典当业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并进一步分析道:“宋代以后,随着封建经济体制的变革及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典当业的放款大量走向生产者的生产经营领域及商品流通过程,尤其是佃户或自耕农民的‘工本’(即购买种籽、农具、肥料及耕种、收割的工食费用)借贷及商人的流动资本借贷更为盛行。因而其经济意义亦大为浓厚,对生产流通的影响也大大增加了”[5]26。明代江南典当业的经营运转,正是一个逐步介入当地稻米、丝织业的过程,农户的典当行为已属于生产性借贷,生动地反映了典当业对当地生产经营和商品流通过程的影响。
二、质库的暴利
典当业在明代的江南地区实属暴利行业。明中后期的赋役征收以田产作为主要依据,经营质库本身并不需要承担赋役,这大大增加了质库的利润空间。江南地区长期以来都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江南重赋”更是有明一代官员们讨论的重要议题。相较于沉重的赋役负担,质库生意确实获利丰厚。
生活在万历年间的刘世教(字少彝,海盐人)曾比较嘉兴府海盐县经营田产与质库之间巨大的收益差距:
夫素封之家,即有恒产,而要之践更输挽,其奔走于公家者,亦甚繁且苦矣,独旅人之质库不然,其拥资甚厚,其朘利甚渥,其经营又甚逸,而名不挂版图,事不涉催科,抑何其多倖甚也。请极言之。远不暇援引,姑以盐论。盐自均甲以来,田亩三百二十而役,役稍重则破矣。又重则荡矣,又甚则杀身者有之矣,何者?其最上腴不能及二千金,而瘠者仅三四百金耳。瘠无论,上田岁得粟可三百斛,以三之一输公家,积十丰岁而不能二千斛也。贾当中金千然,而十岁中俛仰倚之矣,公家之百需又荷之矣,其能有赢焉?鲜矣。质库不然。其上者母至盈万金,即寡亦不下五六千,是上者一而当沃壤之役田五六矣,下者亦不啻三之。其于瘠壤,则上者遂三十而盈,下者亦不啻十五六。岁以什一计,而子钱之入可知也。矧其二之而三之乎,是质库之最下者,其一岁之入已当上田之十岁矣!顾此,则终岁奔走,而不给彼第高枕卧而子母倍息矣。未几,子复为母,而又息之矣。其土著者,人弓人得,犹之乎楚也。不则一穙,载之而去,关讥之法未闻税金,遂令若曹据此全利。即比者榷使岀而始议及焉,然仅仅岁数金止耳。是以富室鲜累世之产,而质库多百年之业。当十岁而更版图,一里之中虑无不易其三四,甚且六七。而质库无论大小,凡三年必益其一。其甘苦利害,较若列眉,岂待智者而后辨哉!莫非民也,县绝乃尔。夫丰则朘其脂,侵则乘其急,而倍入焉,且又坐视其沟壑也,忍乎![12]92-93
海盐县万历年间实施均甲制改革后,额定三百二十亩为一役田。以一役田为单位计算,上等的土地缴纳赋税后,积十年得粮不到二千斛,折银相当于一千两。与之相对,当地规模较大的质库本金达上万两,小型质库本金也有五六千两。假设年利率为十分之一,大型质库年收益即可达一千两;若按年利率十分二或十分之三计算,小型质库一年收益也超过上等土地十年的收益。质库经营还不用缴纳税金,利润远甚于田产,获利差距高达十倍以上。
质库巨额的利润后来也引起了朝廷注意。到了明晚期国库空虚之时,常有官员提议让质库、典铺缴纳一定的贡赋。刘世教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写作此文。据学者考证,正式营业税性质的典当税,大体是从明朝后期开始的,约在万历年间,且当时税额很轻。天启以后这项税收成为重要税源之一[5]255。明末官员毕自严(1569—1638,字景会,淄川人,天启、崇祯年间任户部尚书)曾在奏议中提出,将典铺分为五个等级,每年向朝廷缴纳一定贡赋充当粮饷:“先该臣部题准会议条例省直典铺酌分五等,计资本万金以上者为一等,岁输银五十两。七八千金者为二等,岁输银四十两。五六千金者为三等,岁输银三十两。三四千金者为四等,岁输银二十两。一二千金者为五等,岁输银十两,全收完解充饷等。”[13]596这五个等级的划分反映了明代质库的基本规模。这些数据让我们对明代质库的资本规模有个量化的概念。
明代嘉兴著名收藏家项元汴(1525—1590,字子京,号墨林居士)就是一位典当商人。项元汴是艺术品收藏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同时也是一名富商,质库生意做得非常大。朱彝尊描述项元汴“坐质库估价,海内珍异十九多归之”[14]244-245。质库经营为他的收藏事业提供了巨额资金。明人王世贞(1526—1590)对项元汴的资产规模有过描述:
严世蕃积赀满百万,辄置酒一高会,其后四高会矣,而乾没不止。尝与所厚屈指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凡十七家。虽溧阳史恭甫最有声,亦仅得二等之首。所谓十七家者,己与蜀王,黔公,太监黄忠、黄锦及成公,魏公,陆都督炳,又京师有张二锦衣者,太监永之侄也。山西三姓,徽州二姓,与土官贵州安宣慰。积赀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前是无锡有邹望者,将百万。安国者,过五十万。今吴兴董尚书家过百万,嘉兴项氏将百万。项之金银古玩实胜董,田宅典库赀产不如耳。大珰冯保、张宏家赀皆直二百万以上。武清李侯当亦过百万矣。[15]2
项元汴身家将近百万,而质库是其最重要的资产,显然是资本万两以上的大型典当铺。项元汴善于经商,也有些文献透露出他唯利是图的一面。冯梦祯在为其兄长项元淇写的墓志铭中提到了一件事,即三弟项元汴在经营质库时惹上了官司:“季(项元汴)尝鬻质米万余石,而为其人所讼。琅琊王先生以参政守嘉湖道,当听之,宿高先生(项元淇)行,喜为之德,授指有司闻之先生。先生不可,以书报龚令曰:‘余不能庇弱弟,奈何乘其危而利之耶?’龚义之,闻于王,叹曰:‘俗吏污高士耳!’事遂寝。先生终不言。”[16]225项元汴擅自将别人抵押在质库的米在未到期之时卖了出去,结果被人告上官府。《嘉禾征献录》亦记载了此事[17]409。可见他在生意上过于钻营,有时甚至会不择手段。后世史料常把项元汴塑造成一个吝啬贪财的奸商形象,就是在这些故事的基础上加工而成,但恰恰是质库经营的暴利,为他浩瀚的收藏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项元汴这一类的典当商人,是如何与艺术品收藏联系在一起的?这与当时江南地区普遍存在的艺术品典当行为密不可分。
三、作为抵押物的艺术品
在明代江南的质库经营中,有一类特殊的典当行为——艺术品典当值得关注。艺术品典当在江南地区的日益频繁,让部分质库经营者成为收藏者,完成了社会身份的转换。
艺术品典当在明代以前的文献中并不多见。偶有一见,为南宋洪迈《夷坚志》载:“有携三画诣其质库求十千,掌事者靳之。客曰:吾买时用钱三十万,此名笔也。特以急阙之故,暂行权质,匆虑不来赎也。”[18]1814三十万的名家手笔,只求典当获钱十千,却遭到掌柜的奚落,可见当时艺术品典当不被重视,随意压价。
明代,有关艺术品典当的记载逐渐增多,其经营也渐趋规模化。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中提到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被典当一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旧云在南京一质库,后入魏公家;或云在王守溪相公公子处。”[19]251在比《客座赘语》稍早一些的明初小说中,有这样一则叙述:“其中有一员外,家中巨富,真个是‘钱过北斗,米烂陈仓’。家中开三个解库,左边这个解库专在外当绫罗段匹,右边这个解库,专当金银珠翠;中间这个解库,专当琴棋书画古玩之物。每个解库内用一个掌事,三个主管。”[20]10此时已有专门典当“琴棋书画古玩之物”的解库,证明在明代以前已有不少人典当艺术品,到了明代,艺术品典当业务已经专一化、规模化。我们不能确定书画典当起于何时,但是明代以后,典当书画的记载丰富起来,侧面反映出此际将艺术品作为抵押物的行为越来越普遍。
这类典当行为的增多,质押物品质的提升,让质库经营者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珍贵的古玩书画,锻炼了经营者的眼力,培养了他们收藏的兴趣。作为抵押物的艺术品也成为质库经营者收藏的重要来源。
明代江南的私人收藏家中不乏从事典当业的商人。除了项元汴,苏州太仓的收藏家王世贞也是一位质库经营者。在王世贞的文集中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质库。很多珍贵的书画作品,正是别人抵押到他的质库中,后来成为他的收藏品,如赵孟頫的《千字文》帖:“新安吴生以赵文敏篆书千文乞余跋。文敏此书极精整,有意出徐骑省、周右丞上。绢素用织成乌丝栏,是南渡后修内司物,目所未见。吴生别之二岁,所乃在余质库中。惊问主事者?生质之,得四十金,用为豪具,径去不顾矣。”[21]185据考证,此“新安吴生”是徽州歙县商人吴治,也是当时一位大收藏家,歙县溪南吴氏家族的收藏传统正始于他和同族兄弟吴守淮[23]。王世贞偶尔也会表现出“君子不夺人所好”的一面,比如将范仲淹所书《伯夷颂》归还主人:“此帖与忠宣公《告身》,跋之月余,而其后人主奉不能守,作余质库中物者十年矣。余闻之,数责其以原价取赎,不得。今年初夏悉理散帙,分授儿辈,因举此二卷以归主奉,且不取价。嗟夫,余岂敢以百金市义名,顾满吾甘棠勿剪之愿云耳。为范氏后者,时时念文正公之手泽;为它人者,远则念伯夷,近则念李总管。庶几其常为魏公家有哉。”[22]329另一件珍贵的书法作品《绛帖》(北宋潘师旦摹刻,汇集了历代法书名帖),则是别人当给了王世贞的女婿华叔阳:“此帖吴中黄勉之以十二千得之于市,人割去卷尾,却以泉帖淳化云云。装后勉之子淳父始辨其为《绛帖》,仍割去尾装,而属文寿承签题其首,后得五十千质之华礼部叔阳。归逾三岁,复得三十千,始真为华氏物。而叔阳病甚,寄余郧中为别。”[21]212华叔阳早逝,此帖后归王世贞所有。
王世贞自己也有遇到困窘的时候。据胡应麟记载:“王长公义振一世,其豁达大度,词场中汉高帝也。丙戌(公元1586年)秋,余尝偕汪司马过弇中,玩诸古帖。司马乞钟太傅《季直表》观之,长公默然良久,曰:‘是月以催科不办,持质诸欈李项氏矣。’余迴诣项氏,假其所藏彝鼎及遗墨,遍阅则此帖俨然在。”[10]775王世贞因为没钱缴纳赋税,只能将千古名迹钟繇《季直表》典当给嘉兴项元汴。胡应麟后来在项家看到此贴,心生感慨。
似项元汴这样的典商兼收藏家,在质库中应该过目了不计其数的古玩书画,经济利益的驱动以及自身对收藏的热爱,促使他培养出一定的鉴赏水平,偶然遇到精妙的艺术作品,当然更加欣喜。除了王世贞典当给他的钟繇《季直表》,项家不少藏品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据陈继儒记载:“宋高宗手书《龙王勅》向在三塔寺,寺僧信大源质项子京家。”[24]622这又是一个典型例证。
曾与项元汴一起被列为“天下富家居首等者”的“吴兴董尚书”,即嘉靖年间礼部尚书董份。他在家乡(今浙江南浔)称霸一方,田连阡陌,同时也经营质库。有文献称董份“有质舍百余处”,“岁得子钱数百万”[6]44,财力相当雄厚。虽然董份不以收藏见称,史料中指“项之金银古玩实胜董,田宅典库赀产不如耳”[15]2,但也有材料记录,曾有人将古玩字画拿到董份的质库典当,这些东西因此归他所有。朱国祯记载:
余镇中有御书阁,相传为宋高宗南渡过此,留徽宗《画鹰》一幅而去。又赵松雪有《滚马图》一卷。僧世守之。袁胥台戍我湖宿其处,题曰:“御书阁下鹰还在,名义庵中马尚存。”名义一曰法华,即御书所创处也。今庵阁如故,而二物失之已久。且胥台见时是嘉靖初年事。失去是六十年前事,盖小沙弥窃出,归董氏质库中,仅得银二两。事觉,僧往赎,不可得。诉于太宗伯浔阳公。公厚赠留之。[25]458
两幅名画被质库大幅压价,仅换得二两银子,这在质库行当并非孤例。艺术品的估价有很大的伸缩空间,质库经营者借机对抵押物压低估价也是获取厚利的常用手法。
明中后期,江南一带民风日益奢靡,崇尚攀比,在婚丧嫁娶方面更是一掷千金。当时的地方志直接点明了此地风俗“婚嫁死丧,竞为侈丽”[26]73。这种奢侈之风常常造成资金的短缺,很多人为了办一场婚事或丧事,典当了家中大量财物。作为“长物”的书画艺术品成为了质押物的首选。嘉兴的另一位收藏家汪砢玉(1587—?),从其父辈汪继美开始就热衷收藏书画,家中藏品富甲一时。“不意崇祯戊辰(公元1628年)春,遭内外艰,营殡事典质古玩”[27]791-792,汪砢玉为操办亲人丧事,将家中珍藏典当。“为先人窆厝费,因出家藏书画,宋元代名迹各百余册,卷轴称是,并虎耳彝雉卣汉玉犀珀诸物,易赀襄事,而古绘两函尤时在念也。”[27]818看来这批古董数量庞大,价值不菲,难怪汪砢玉一直念念不忘,反复提及。
苏州地区与嘉兴风俗相近。苏州文人中也不乏因婚丧嫁娶之事而典当书画的例子。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收藏享有盛名,其书斋“鹤适轩”藏有大量古籍,另一藏书楼“万卷楼”则收有不少珍稀墨迹,但王世懋也与哥哥有类似的经历,因为经济困难而典当书画:“余归卧一载,壬午冬复起浙江督学副使,亲故皆劝使就道,余竟坚辞。癸未春得请偃仰蔬圃中,益觉去先生不远。又岁遭屡侵,遣嫁两女,官逋甚急,生平爱玩法书名画,皆质钱以偿,仅此卷在笥耳。向所自谓饶裕愧先生者,今亦渐无怍色第。未知此卷能留贻儿辈否?一咲以识吾迁。”[28]711-712灾荒、缴税、嫁女,几件事凑在一起,令王世懋疲于应付。万历年间的苏州书画家陈元素,去世后“惟余玩赏物,又复归质库”[29]319,令人叹息。这几位收藏家辛苦积攒多年的珍藏,都因种种原因被拿去典当,法书名画遂流入典商手中。考虑到他们的经济情况,往往没有能力再赎回这些典当物,被抵押的艺术品成为典商的收藏品。
以书画艺术品作为抵押物的行为,甚至扩大到了典当业之外。有时私人之间的借贷,也会拿书画质押。比项元汴略晚一些的嘉兴收藏家李日华(1565—1635),虽然没有经营当铺,却有不少人到他那里用书画质银。他把这些事纷纷记录在案:“(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八日,夏贾复持文徵仲《秋林曳杖图》来质银。余不见此画凡三越岁矣,开轴谛视,如重游胜境,不觉留连太息。”[7]356“(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歙人吴雅竹以赵文敏行书庄生《说剑篇》求跋。…雅竹又以文衡山《千岩竞秀》与《江山积雪》二图求评骘,皆赝本也。又侯夷门懋功《秋山图》粗笔草草甚有子久风气。余披阅再三,雅竹因质银去。”[7]358-359“(万历四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吴雅竹以黄大痴《松溪草亭》小景来质银。此画壬子年余于武林寓楼借观者累月,知其笔法苍古疏宕,断不出俗手,但非子久真物耳。款印俱伪。”[7]365“(万历四十三年正月)十四日,胡雅竹以吴中名公手墨来质钱。”[7]437“(万历四十三年九月)三日,钟侍滨以汉玉鹅杂佩一枚,文衡山细楷《滕王阁记》、《进学解》、《克己铭》一纸,孙汉阳画一轴,质银去。”[7]484此类书画质银的事情在明清时期的笔记中时常见到。这一现象反映出书画作为资金借贷抵押物的普遍性,艺术品质押已不限于专门经营典当业的质库之中。
项元汴最重要的收藏习惯,是在部分藏品上标注价格并用千字文编号。在此之前没有藏家这样做过,项元汴以后也很少有藏家这样处理藏品。考虑到项元汴的另一个身份是当铺经营者,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新的解释:他的质库管理经验,影响到他对于藏品的处理。在今天仍然保留的当铺经营文献中,我们可以知道,明清时期当铺的管理与分工已到达很高水平,如何给物品估价,如何登记造册,都有明确指导。将当铺的造册方式与项元汴在书画藏品上的价格、编号形式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两者惊人的相似。罗炳绵先生曾对中国当铺的管理赞赏有加:“其对质押物品的分类管理,一如现代图书馆。货物入库前,须经过审查、估价、登录(当簿)、编目(当票)、编号、包装等程序,然后上架。而货架之排列,也一如书库,依号放置,依号索取,迅速而无错误。可惜此一科学管理技术,没有受到士人的注意,而应用到传统藏书楼及工商管理方面去。”[3]实际上,项元汴的收藏习惯正是受到当铺管理的影响。非常遗憾,今天我们看不到项元汴完整的藏品目录,无法更全面地考察项元汴的藏品管理方法。
质库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综合性金融机构。在明代江南地区,质库的兴盛沟通了当地稻米种植、蚕桑丝织业与赋役征收,介入到当地的生产经营与商品流通中。资金借贷由生活目的扩大到以生产经营为目的。质库的经营者也从中获得暴利,产生了一批新生的富户巨贾。质库生意给经营者带来丰厚的利润,也让经营者有机会直接接触到一些珍贵的古玩书画。明代以后,将艺术品作为抵押物的行为越来越普遍。比起传统的典衣当裤,艺术品质押获取资金要大的许多。法书名画、珍稀古玩,因不同缘由流向质库,造就了项元汴这样享有盛名的收藏大家,并且使其财富积累与投资更加多元化。书画艺术品能作为抵押物,前提是艺术品市场的完善。只有市场完善,艺术品有一套稳定的评价体系,有确定的、被众人认可的价格系统,艺术品成为当铺的抵押物才能普及。明代较完备的艺术品交易体系为艺术品质押行为提供了保障,艺术品的典当记录是我们了解当时艺术品市场的重要资料,这一特殊的经济行为成为经济史与艺术史的交汇点。
[1] 杨肇遇. 中国典当业[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29.
[2] 罗炳绵. 清代以来典当业的管制与其衰落[J]. 食货, 1977, 7(5): 10-34;7(6):18-31.
[3] 罗炳绵. 近代中国典当业的社会意义及其类别和税捐[J].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978, (7): 125-157.
[4] 曲彦斌. 中国典当史[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5] 刘秋根. 中国典当制度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6] 刘秋根. 明清高利贷资本[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7] 李日华. 味水轩日记[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5.
[8] 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十二册浙江下)[M]//续修四库全书(59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9] 李培. 秀水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
[10] 胡应麟.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七)[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290),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1] 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M]. 杭州:浙江社会科学院, 1985.
[12] 刘世教. 研宝斋遗稿(卷十二)[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663),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3] 毕自严. 度支奏议(新饷司卷八)[M]//续修四库全书(48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4] 朱彝尊. 曝书亭集(卷五十三)[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318),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5] 王世贞. 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十六)[M]//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5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16] 冯梦祯. 快雪堂集(卷十三)[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6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17] 盛枫. 嘉禾征献录(卷五)[M]//续修四库全书(54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8] 洪迈. 夷坚志(三补)[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19] 顾起元. 客座赘语[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20] 罗贯中. 三遂平妖传(第一回)[M]//明清善本小说丛刊(4),台北:天一出版社,1989.
[21] 王世贞.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一)[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281),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22] 王世贞. 弇州四部续稿(卷一百六十一)[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284),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23] 范金民. 斌斌风雅——明后期徽州商人的书画收藏[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13 (1): 43-57.
[24] 陈继儒. 妮古录(卷二)[M]//美术丛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25] 朱国祯. 涌幢小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6] 刘应钶. 嘉兴府志[M]//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
[27] 汪砢玉. 珊瑚网[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818),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28] 王世懋. 王奉常集(卷五十)[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3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29] 顾梦游. 顾与治诗(卷一) [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5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刘 英)
2017-02-06
冯志洁(1987—),女,江苏南京人,历史学博士,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社会经济史,农业民俗学。
K248;J124
A
1671-511X(2017)04-0139-07